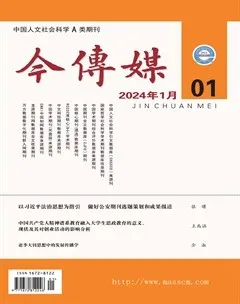浅析民国县级报刊的内容面向与保存现状
2024-01-16何雨蔓
何雨蔓
摘 要:民国时期新闻业是我国新闻史发展的源头与火种,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不一,因此,民国时期新闻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遂宁地处四川盆地中部,民国时期它的新闻事业受当时区县政府的限制,广播、报纸等行业发展较为缓慢,但是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因此,其新闻事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地域代表性。本文以1948年2月5日《涪声日报》第八四六期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容进行文本细读并作简要分析,且对民国文献的保存和利用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旨在为民国报刊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涪声日报》;县级新闻事业;民国报刊
中图分类号:G2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4)01-0075-04
一、引 言
近代来,我国新闻事业随着社会的变动而呈现出此起彼伏、革故鼎新的发展态势。民国时期新闻业是我国新闻史发展的源头与火种,是学术研究的重点。目前,大部分民国新闻史的研究主要围绕《大公报》等大报,并将目光聚焦在报业发达的大中城市,而对于区县报刊的研究较少。朱志刚、李淼等认为,报刊在基层的普遍出现标志着近代化在我国的广泛延伸[1],而从遂宁———四川腹地的民国报刊出发,可以窥探民国时期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缩影。
二、民国时期遂宁地区新闻事业概述
遂宁市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涪江中游,东汉建县,东晋穆帝永和三年设遂宁郡,民国时期为四川省第十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所在地,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遂宁县,建为省辖地级市。
据《遂宁市志》记载,遂宁最早的广播出现在民国22年,即1933年;最早的报刊出现在民国27年,即1938年[2]。在1936年许晚成主编的《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中,只查询到遂宁周边射洪县的《县政旬刊》、盐亭县的《新盐亭》等,未查询到遂宁县的报刊,佐证了这一事实[3]。
(一)广播事业
民国22年(1933年),遂宁县政府在所辖保卫团设有收音室,配有收音机1部,收音员1人。民国27年,收音室迁至民众教育馆,工作人员增至2人,每天印发《遂宁广播通讯》60-70份供县政府有关部门参阅。
根据《四川省志·广播电视志》,民国时期四川省内的广播电台主要分布于重庆、成都两地,重庆广播电台最早于1932年12月建立,1936年9月成都广播电台建成并开始播音[4]。而省内除重庆、成都之外,只有西康、自贡两个地区分别于1943、1947年成功建设广播电台,其他地区均配备收音设备接收信息。
(二)报刊事业
民国时期,登载遂宁县政治、经济、教育等相关内容的报纸寥寥无几,在《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第一~十一辑)》中对“遂宁”这一词条进行搜索,仅获得461條相关内容,时间主要集中在1930-1949年,登载报刊主要为《四川月报》及各省级部门公报。
据《遂宁市志》记载,民国27年(1938年)春,民众教育馆编辑出版4开版土纸小报《遂宁日报》,辟有副刊《战号》,后更名为《野火》,民国28年初,又更名为《后方文艺》。副刊先后由杨仲明、朱竹隐、曾似鸿任编辑,以诗歌、散文、小品、杂文等文学样式宣传抗日救国,共刊出20多期。
民国28年(1939年)冬,遂宁专署(即四川省第十二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黄绶命令所属接管《遂宁日报》后改组为4开版的《涪江日报》。报社由民众教育馆迁往专署内,为专区地方报纸,在专区所辖9县发行,日发行量万份以上。民国30年,黄绶调离时停办。
民国32年(1943年),遂宁专署创办了4开版的《涪声日报》,社址位于县城小西街帝主宫。民国34年底至民国35年约半年时间内,因报纸销路不畅,曾一度改名《涪声三日刊》,后复名《涪声日报》,直至民国38年接近解放时停办。
三、《涪声日报》县报实录
《涪声日报》共4版,双面印刷,从左至右打开,竖排版,通篇采用白话文写作。本文以1948年2月5日的《涪声日报》第八四六期作为文本研究对象,通过对报刊内容的详细解读回溯当时的社会民情。
《涪声日报》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民生、国际局势等多个方面,也穿插了当时时髦商品的广告及政府部门的公告。报头居中,标题“涪声日报”采用行书书写,报眉标有新闻纸类别、期数、登记刊号、发行人、报纸零售价及广告刊登费用等。《涪声日报》每期刊发50余篇文章,分为国内新闻、国际新闻、本县及周边信息、社论及特写、商业广告和登报启事等6个部分,其中国际、国内新闻均来自中央社。
(一)国内新闻
国内新闻主要分布在报纸头版,内容涉及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民生等各个方面,共计13篇。与军事相关的报道有《白崇禧将飞京》《鲁李两将军殉职蒋主席饬抚恤金》《严防偷渡长江江阴岳阳沙市等地加派船舰常州驻守》《军校招考新生二月截止报名》《鄂中国军完成缜密部署宣城当阳恢复常态刘匪受创徘徊塘港》等,其中,《鄂中国军完成缜密部署宣城当阳恢复常态刘匪受创徘徊塘港》一文标题加粗,字号最大,为本刊头版头条。与经济相关的报道有《抢运开滦存煤沈熙瑞抵平洽商并视察平津工业》《西藏代表团晋京洽商与内地贸易》《南京将配售食米每人每月配一斗》,其中《南京将配售食米每人每月配一斗》一文采用“中央社南京四日电”,报道了南京市全面配售食米定于三月一日开始,“受配人数按照一百一十万人计算,每人每月配食一斗”,“价格较市价为低”。与法律相关的报道有《孙副主席讲———宪法与宪政》,报道了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长孙科向人民群众普及宪法与宪政知识的消息。与政治相关的报道有《北方代表请愿团在京沪结果圆满》《同济学潮已告解决》。与民生相关的报道有《东北人民生活不易》《台北长寿桥下月可竣工》等。
(二)国际新闻
《涪声日报》在1948年2月5日当天登载了印度、英国、日本、美国4个国家的新闻,尤其对印度和平使者甘地的意外死亡进行了大篇幅报道。《甘地噩耗传出印度举国哀恸举行追悼绝食祈祷凶手为马拉泰会员》一文采用“中央社新德里四日合众电”,讲述了圣雄甘地在晚祷现场被枪杀案件始末,报道侧重于印度政府及其国民对于甘地去世的悲痛和惋惜。此外,还有报道日本暴徒毒杀银行员工并抢夺巨款的《日本杀毒案》,以及美国鉴于燃料石油缺乏而减少石油输出的新闻。
(三)本县及周边信息
《涪声日报》本县及周边信息共计16篇报道,内容包括政府公告、商情、娱乐等,主要分布在第三版。其中,《本区保安司令部分驻各县保警队如有违法舞弊情事准各县监督与检举》为特讯,本区保安司令部面向社会宣告6种保警队违法舞弊行为,即“好赌”“贩运烟毒”“纪律欠佳”“清匪不力”“勒索或欺压人民”“其他违法舞弊”,分令各县县长严密监督管理,并许任人检举,如查属实,决予严惩。标有“本报讯”的文章有《办理契税认真稽征》《呈报征实数额不得虚浮不实》《省府明令提示乡镇注意事项》《省县中等学校征费标准决定》《遂宁立委选举业已顺利完成》5篇,内容涉及契税稽征、田赋征收、学校征费标准等民生话题,以及乡镇公所幕僚长制、县立法委员会选举结果等政治话题,说明当时区县的报人拥有独自进行新闻采编并撰稿的能力,但是报刊的总体篇幅还是以摘录其他来源的新闻为主。
本县商情和娱乐信息与人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遂宁商情》罗列了遂宁县当日商品的价格,大米、棉纱等生活资料的价格以“万”为计价单位,通货膨胀程度可见一斑。娱乐新闻有《遂宁集贤剧社筹募冬令账济平剧公演节目》,罗列了《武家坡》《五花洞》等剧目,并标注了主要角色。这部分的报刊内容帮助当地居民了解了本地新近发生的新闻,发挥了报刊传递社会信息的重要作用;同时,这部分内容的呈现也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变迁的缩影,为后来人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四)社论及特写
《涪声日报》在1948年2月5日当天刊发了一篇名为《怎样使青年军有力量》的社论,作者沈健,标题后写有“续”,即表示该篇社论为连载文章。该文章提出:“我們要确立鲜明而光明正大的目标。就对外而言,第一是严惩出卖国家民族的反动集团,完成国家统一,保障建国成功;第二是打倒新的帝国主义;第三是惩戒反时代、反潮流、反民主、反私有的恶势力,实行民权主义;第四是清算官僚资本,实行民生主义。就对内而言,第一是人人有衣穿,第二是人人有屋住,第三是人人有工做,第四是人人有书读,第五是人人有车坐”。此外,该文章还配有山水树木的插图,这也是全报唯一的一张图片。第二版面的《迎春特写》的作者为本报记者单火,描绘了遂宁县年关将近的市井生活,现场感极强。
(五)商业广告
《涪声日报》第八四六期共刊登了《遂宁久太绸布号》《火车牌、白家牌电池》两则广告,占据报纸第二版下方近三分之一的版面。广告标明了店铺名称、经营范围、产品特点以及店铺地址,运用不同的字体和字号进行了区分,版面内容丰富,极具特色。
(六)登报启事
由个人或组织在报纸上刊登《启事》是《涪声日报》的重要内容。1948年2月5日,《涪声日报》共刊登了12篇《启事》,既有在报纸中缝刊登的有关报价调整事项《本报调整报价启事》《本报营业部紧要启事》,也有宣传各类组织内部相关事宜的《遂宁县私立慈幼教养工厂为感谢天成亨捐款启事》《川中师管区司令部启事》《省遂师蓬溪同学会启事》;既有刊登个人重要事项的《雷惊重要启事》《蔡绍明遗失启事》《蓬溪康家乡萧清廷紧要启事》《遗失启事》《从婚启事》《钟慎齐为三子书德脱离家庭关系紧要启事》等,也有为他人献上祝福的《萧纯夫先生杜天贞女士订婚纪念》等。
四、从《涪声日报》看当时县级新闻业的发展状况
《涪声日报》作为有记载的、民国后期遂宁县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其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南地区民国后期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
(一)从民营转向官办
《涪声日报》最初名为《遂宁日报》,由民众教育馆编辑出版,后被遂宁专署接管,转为国民政府专区地方报纸,并在专区所辖县发行。经查阅《四川省志·报业志》,四川省内多个县市的数家报纸都是从民营转为官办,类似于《涪声日报》成为全县仅剩的报纸也大有所在[5]。
《涪声日报》在报头清晰标明“中华邮政局第二类新闻纸”。所谓第二类新闻纸,又称立券新闻纸,指凡发行周期在10天之内,每次发寄数不少于500份的新闻纸,在邮局办理登记立券手续后,可按立券新闻纸交寄,资费按月交付,并享受折扣[6]。由此可见,当时《涪声日报》的发行量较为可观。
(二)新闻来源较为单一
《涪声日报》的国际、国内信息大多来自当时的中央社。中央社现为台湾中央通讯社,1924年4月创立于广州,历史上总社社址先后设于广州、南京、汉口、重庆、南京、广州、台北。从报纸登载时间来看,其新闻基本是前一日的电讯,由此可见,《涪声日报》的时效性较强。此外,《涪声日报》拥有专门的记者,可以自行采编,报纸中也有文章标明“本报记者单火”,但是“本报讯”的内容大多是省政府的会议结果、决议决策等,较少涉及非政府渠道的信息。从新闻来源可以看出,县级报刊在内容选择上范围较窄,能够为当地人民提供的新闻内容有限,新闻业发展较为缓慢。
(三)内容多反映时局变化
《涪声日报》共四版,第一版、第四版为国际、国内新闻,第二、第三版与本县发展和当地人民的生活关系密切。总体来说,不同类型的新闻在排版上趋于均衡。然而,从报纸的编排结构和新闻内容上,读者依然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到当时的时局变化。
首先,《涪声日报》作为区域性、权威性的新闻报纸,在特殊历史时期对战争时局进行了报道,为当时的百姓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消息来源,也为后来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了解时局提供了史料帮助;同时,报刊还传递了一些进步声音,一些有志之士发表社论文章,对社会现状针砭时弊,以期唤醒人民,为人民解放铸牢思想基础。
其次,从报纸内容来看,反映了时局的不稳定。一方面国民政府想要管理违法舞弊行为,不允许各县自行提高契税,对保警队在各县的违法舞弊行为也提供检举途径,加强对乡镇公所人员的管理等。然而,彼时解放战争已经进行到战略反攻阶段,并且社会通货膨胀严重,各地物价狂涨,(“大米法币六万元一斤,高粱米五万元”“潘阳街,到处是倒闭的商店、关门的饭店”),致使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四)人民群众公开表达的渠道
《涪声日报》第八四六期的50篇文章中,有12篇为私人启事,或是庆贺婚礼,或是失物招领,又或是表达感谢等。报纸作为一种公开发行的刊物,将群众私人领域的社交内容刊登于报纸上,增强了社会互动性。何秋红、刘洁等人认为,彼时报纸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这种在公开场域发布私人社交信息的行为,满足了群众的社会互动需求,契合当时的社会现实[7]。
五、对民国时期报刊保存与保护的反思
民国时期的报刊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是一个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历史记录,然而,目前的保护与利用工作不是很到位。就本次史料收集过程来看,遂宁档案馆馆藏纸质档案13.7万余卷、62万余件,民国档案34259卷,但多为图书和口述资料,现存民国报刊只有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十七日《遂宁日报》第一版,规格为57.5cm×40.5cm,是保存的遂宁市最早的报纸。与之对应,民间收藏家即使有保存完好的报刊原本,此類报刊藏品数量也非常稀少,很难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对于个别案例的研究也无法推演出当时的新闻业态和社会实情。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应加强对民国报刊的保护与研究,充实民国史料,还原当地历史,避免文献历史出现“民国断层”危险。
(一)征集民国报刊进馆
报刊的保存受纸张原材料和保存环境的双重制约,普通方式无法长期保存报刊原刊。早在2005年,《人民日报》就刊登过《如果不及时抢救,民国文献将在50至100年间消失殆尽———文献历史会出现“民国断层”》一文,并提到“在历代文献的保存中,民国时期文献的寿命最短,加之民国时期装帧工艺落后,造成民国期刊在使用过程中容易造成破损”[7]。因此,对民国报刊的保护不能仅寄希望于个人收藏家,而应交由博物馆、档案馆等具备专业设备和专业人员的机构进行保存,这需要我们明确报刊收集的主体责任,与当地档案馆、图书馆等文献资料保管部门相互配合,使史料保存和管理工作制度化、秩序化,方便读者利用文献搜索读取较为完整的地方民国史。
(二)录入电子数据库,丰富虚拟馆藏
目前,全国多数地区都实现了民国文献的数据库录入。数据库录入,即对图书、报刊等文献通过电子扫描、复印、制作微缩胶片等手段建立专题电子档案库,既方便保存,也方便读者和研究人员调取内容进行阅读,避免文献原本再遭破损,这是目前保存民国文献生命续存的最好方法之一。
六、结 语
《涪声日报》反映了当时该地政府治理、商业发展、娱乐生态、社会民情的变化,将社会宏大叙事与市井生活同时呈现,既为我们研究近代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来源,也为民国报刊及其他文献进行更好保存、避免地区文化断层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 朱至刚,李淼.被嵌入的主角:报刊基层化中的国民党县级党报[J].国际新闻界,2017,39(8):156-171.
[2] 谢志成,李剑华.遂宁市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
[3] 许晚成.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M].上海:龙文书店,1936.
[4] 陈杰,陆原,李放,陈立源.四川省志·广播电视志[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5] 汤霞.从“新知”到“新媒介”:晚清时期的译报实践与媒介新知[J].编辑之友,2022(5):94-103.
[6] 何秋红,刘洁.透过大众媒介的私人交往———以《通海新报》私人启事为例[J].华中传播研究,2016(2):70-87.
[责任编辑: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