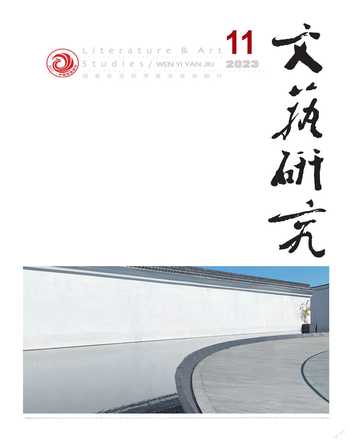《耕渔轩诗卷》的文本形态、话题指向与诗学意义
2024-01-11左东岭
左东岭
摘要《耕渔轩诗卷》是元明易代之际流行的一种独特文本形态,由书法、绘画与诗文题记等多重要素构成,其属性乃是众多文人对于同一话题的开放性表达。从其序、跋、铭文内容看,展现了易代之际文人对于“隐逸”话题的不同理解,体现了他们多重的人生选择;从题画诗所显示的诗学层面看,则是当时文人对耕渔轩诗意生活的综合描绘,同时表达了其自我人生意趣。该诗卷乃元明之际问世的数十种诗卷中的一种,具有文体的多样性、话题的开放性与内涵的丰富性,与宋元及明清易代的同类文本差异明显。将该诗卷作为重点个案予以剖析,能够立体呈现那一时代文坛的真实状况与诗学内涵,具有探索研究范式的方法论意义。
徐达左(1333—1395),字良夫,又作良辅,号耕渔子、松云道人,平江人。对于其耕渔轩诗学活动,学界在研究元明之际的文学史,尤其是研究玉山雅集与清问必阁雅集时,常有提及,然而集中研究耕渔轩本身的成果却寥寥无几①。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主要作家徐达左存留作品及相关文献相对较少,无法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二是《金兰集》所存作品涉及诗学理论较少,且创作内容较为单一,无法掘发有深度的诗学内涵。但我想还存在着另外的学术盲区,现有研究仅仅将其作为文人雅集的文献予以处理,显然未能触及其文本所体现的真正价值,从而也缺乏对那一时代文坛状况的真切认知。
一、《耕渔轩诗卷》文本形态的独特属性
学界一般将耕渔轩诗学活动比照玉山雅集之模式,称为“耕渔轩雅集”,其实并不准确。记载耕渔轩诗学活动的文献,目前有《耕渔轩诗卷》与《金兰集》两种形态。
许多学者均将其视为同一类文献不同累积阶段的产物,比如有人便称《元人徐氏耕渔轩卷》“是《金兰集》结集之前的‘样稿”②,此种认识过于笼统。在元明之际诗坛上,诗卷与总集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文献。诗卷一般由当时名人题端、画家所绘画面与文人所题诗文等要素构成,除《耕渔轩诗卷》外,当时其他著名诗卷还有很多,仅朱存理《铁网珊瑚》所收便有《春草堂诗卷》《贞寿堂诗卷》《听雨楼诗卷》《破窗风雨诗卷》《秀野轩诗卷》《安分轩诗卷》《植芳堂诗卷》《崔氏友竹轩卷》等,此类诗卷后来均未能进一步形成诗集,当然不能说是所谓的“样稿”。诗卷所题之诗往往针对同一画面、同一景象或同一话题而表达各自理解,很少有溢出画面之外者。《耕渔轩诗卷》即文人针对耕渔轩画面所题诗文,并非一时之作,显非文人雅集性质。《金兰集》则辑录与徐达左本人往来的相关诗作,其中就包括四次诗歌唱和之作。若研究耕渔轩雅集,则须依据《金兰集》而非《耕渔轩诗卷》,这是首先要区分清楚的。
现存记载《耕渔轩诗卷》的文献,主要有朱存理《铁网珊瑚》、赵琦美《铁网珊瑚》与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籍,其中差异主要是赵氏《铁网珊瑚》前有《倪云林耕渔轩图》,其他则没有;赵氏《铁网珊瑚》缺西涧翁与坚白叟二人题诗;另外还有个别人名出入③。综合三家所载,该诗卷除倪瓒图画外,共有高巽志《耕渔轩记》、杨基《耕渔轩说》、唐肃《耕渔轩铭》、包大同《耕渔轩铭》、王行《耕渔轩诗序》与道衍《耕渔轩诗后序》6篇文,倪瓒、周砥、隆山(虞堪)、张纬、陈寅(陈汝秩)、高启、张羽、徐贲(二首)、王隅、刘天锡、仇机(沙大用)、王禋、西涧翁(苏大年)、坚白叟(周伯琦)、陈宗义、余诠16人18首诗。
仔细分析该诗卷的作者构成,会发现诸多值得深究的问题。首先是某些著名平江文人并未出现在诗卷中。比如饶介、陈基、谢节、张经、陈汝言、顾瑛等,均为玉山雅集常客或当时文坛名宿,却未现身诗卷。最奇怪的是王禋,乃元代高官王都中的孙辈。王都中官至江浙省参知政事,深受朝廷信任,由于其父功劳,被世祖皇帝赐田八千亩于平江,并定居于此。他共有八位子嗣,其中长子王畛(字季野)、第三子王畦(字季耕) 和第五子王?(字季境),均在诗画上颇有造诣与名气。另有七位孙辈,王禋年龄最小④。为何王禋叔父辈无缘在耕渔轩诗卷题诗,而偏偏孙辈王禋却跻身其中,颇值得探究。不过王禋确有诗才雅趣⑤,故能名列诗卷。
其次是对某些身份特殊文人做了淡化处理,包括周伯琦(1298—1369)、朱德润(1294—1365) 和苏大年(1296—1364)。这三位文人元末均曾入仕翰林,在文坛享有盛名,晚年又皆寓居平江。周伯琦,字伯温,号玉雪坡真逸,江西鄱阳人。至正间曾任翰林修撰,后奉命召降张士诚,被留平江十余年。史书载其“仪观温雅,粹然如玉,遭时多艰而善于自保,博学工文章,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⑥。朱德润,字泽民,号睢阳山人,平江人。元代著名画家,元末曾任国史院编修,官至征东儒学提举,晚年隐于吴中。其山水画当时颇负盛名,倪瓒有诗赞曰:“朱君诗画今称绝,片纸断缣人宝藏。小笔松岩聊尔尔,道宁格律晚堂堂。”⑦苏大年,字昌龄,号西坡,又号西涧,真定人,后侨居扬州。元末任翰林编修,“天下乱,寓姑苏,为文有气”⑧。他诗书画俱佳,名气颇大,孙作《杞鞠轩记》曰:“赵郡苏先生避地吴中,士大夫争走其门,因辟轩以延客,环艺杞鞠。”⑨无论官位、才气还是名声,此三人均为元末吴中名流,许多文人雅集场合均有其身影。比如周景安建秀野轩,便由周伯琦题匾,朱德润作画并题记。奇怪的是,朱德润亦曾为耕渔轩作画,并有赠徐达左诗作,却未现身耕渔轩诗卷,诗卷用的是隐士倪瓒的画与诗⑩。诗卷尽管收有周伯琦与苏大年题诗,却未请周伯琦题端,而且二人诗作分别用了“坚白叟”“西涧翁”的别号,显然是一种淡化处理。
其三是关于张雨与诗卷的关系,最难理解。就目前所见文献而言,署名张雨的《耕渔轩》是所有耕渔轩诗中创作时间最早者,其诗曰:“幽人薄世荣,耕渔夙所喜。朝耘西华田,莫钓洞庭水。浮沉干戈际,无誉亦无毁。酿秫云翻瓮,鲙鱼雪飞几。客来具杯酌,客去味經史。缅怀清渭滨,何如鹿门里。往者不复见,庶免素餐耻。”诗中所写与徐达左之隐居目的、生活情调若合符契,而且此诗也在诗卷之中,但署名却是“荆南山樵者张纬”。张纬字德机,元末著名诗画家,与倪瓒、徐达左皆为挚友。如果作者确系张雨,以徐达左与其关系的亲密程度,断不至错归之张纬,故而该诗之著作权暂归张纬。不过《金兰集》中还录有张雨另一首《寄山中隐者》的七言律诗。张雨卒于至正十年(1350),则此诗可另证二事:一是耕渔轩之建成时间应在至正十年之前,徐达左邀约众人为其题咏集中于至正二十年前后,此时该轩已建成十余年;二是诗中所写内容属于徐达左乐于个人隐居而不是群体雅集,如“山中高士眼如漆,落落意气非常群”“明日城南一相见,依然归去卧松云”,都透露出超脱闲散之情趣。或许这是耕渔轩建成虽较早,却并未造成像玉山雅集那样轰动效应的原因。
以上三点似乎零散而缺乏关联,若加深思则会发现,均展现了徐达左辑录耕渔轩诗卷的低调倾向。他有意隔断与元朝廷官员及张吴政权中权贵的来往,显示全身远害而深隐不显的良苦用心。他低调处理与台阁名宿之间的关系,亦为晦迹低调心态之体现。他与张雨的关系则显示出其隐居生活的内敛与闲散,透露出耕渔轩何以能够在元末明初的战火乱局中始终巍然不倒的原因。
二、“儒隐”内涵的多元解读
从《耕渔轩诗卷》内容看,尽管作者颇为复杂,包括吴中好友、文坛前辈、流寓文人甚至流落江南的少数民族作家,但话题指向则颇为明确,那便是对“儒隐”的内涵、性质、目的与状态的集中描绘、评述,文主要用以叙事、议论,而诗则主要用来颂美与抒发感想。
该诗卷有各体文共六篇。高巽志《耕渔轩记》被置于首位,自然最为重要。他采用了颇为独特的主客对话模式,先从士、农、工、商的行业属性起笔,然后收归至士之属性,“学成于己,行孚于人,其大而用天下,小而为天下用”,“苟得其位”,“发于事业”,“万钟之禄不足为其富,百里之封不足为其贵”。然而,“弗际可为之时,固不能行其道。弗得大有为之君,亦不能成其功。是以豪杰奇伟之士,有潜身于农者,寄迹于工商者,宁藏器而有待,殁世而不悔。噫,岂特士之不幸哉”。这是从正、反两方面来总论士之不同遭遇,为下文议论做好铺垫,随后方从容引出主客对话:
吴人徐君良辅,世家笠泽之陂,慕学,无所不读。凡往古之成败污隆,人物之是非得失,莫不周知而有要,愈扣而不穷。其为人平易以坦夷,尊贤而好礼,弗矫激以干名,弗□ (苟) 偷以趋利。予得而友之。一日造予曰:“不肖生居山澤,躬耕以具箪食,无所仰给于人。遭时乂宁,野无螟螣之灾,乡无枹鼓之警,官无发召之役。获于田而观黍稷之敛穧,缗于水而遂鳝鲔之涪湛。而又暇日,挟册以学,思古人之微,以适其适。吾于是充然而有余,嚣然而自得,怡然以尽夫修年,而无所觊觎矣。因名居室曰‘耕渔,所以寓吾志也。敢求文以为记。”予闻叹曰:“士之抱朴蕴贤,固不欲自售于世,亦不可遗世而弗顾也。苟振耀一时,而事业不足以堪之,又不若独善而食其力也。以君之才而所志如此,抑岂有待而然与。”盖士必有待,然后能有所立,何独徐君也哉。是为记。至正二十一年夏五月,河南高巽志谨书。
可见,该文陈述了主客双方对于隐逸的不同认知。依高巽志之意,徐达左之隐于耕渔,乃“有待”之为,在其看来,既然徐达左所学内容为“往古之成败污隆,人物之是非得失”,自应入仕以行道,成就一番事业。如今的隐居选择,无非是等待机遇之来临。徐达左本人则认为:“挟册以学,思古人之微,以适其适。吾于是充然而有余,嚣然而自得,怡然以尽夫修年,而无所觊觎矣。”其核心在于“自适其适”“无所觊觎”。高巽志则坚信:“盖士必有待,然后能有所立。”存在如此理解差异,自然与二人出身及人生信念密切相关。徐达左乃隐逸家族。高巽志虽生卒年已不可考,但名列当时以高启为首的平江“北郭十友”中,自然是年龄相近的青年才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逊志,字士敏,河南人。元末侨寓嘉兴,徙吴门,授业于贡师泰、周伯琦、郑元祐。”入明后曾任侍读学士、太常右少卿等职,靖难之役后下落不可考。这些信息尚难以显示其在元末文坛的影响,据徐一夔《师友集序》,高巽志之父元末为浙东宣慰司都事,与周伯琦、贡师泰、危素等台阁文人交往密切,故而高巽志才有机会从其学文并受其夸赞推奖。高巽志亦曾编过一本《师友集》,“稡其师与友赠遗唱酬之文与诗也”。就在其撰写《耕渔轩记》的同一年,他还编成了自己的诗文集《辛丑集》,被高启誉之为“有舂容温厚之辞,无枯槁险薄之态”。高巽志拥有如此仕宦家世、文坛众名宿推奖,加之年轻气盛,他虽因政局混乱而一时难觅进取机会,但隐以待时显然是其此时应有的心态,故与徐达左决心归隐的志向拉开了距离。此种对隐逸理解的差异,不仅使高巽志《耕渔轩记》形成一种开放性结构,也成为整个《耕渔轩诗卷》的主调:众人认为徐达左乃隐而“有待”,徐达左则自称隐“以适其适”。对话体的好处即在于可以各自陈述看法与主张,而将选择权留给读者。
杨基(1326—1378)《耕渔轩说》显然受到高巽志《耕渔轩记》影响,他同样设置了化名“穹隆山牧”与“耕渔子”的对话。穹隆山牧将耕渔概括为三种类型:“羲农之耕渔,所以教天下;虞舜之耕渔,所以化天下;伊尹、吕望之耕渔,所以待天下。”后世之隐自然难以与羲农、虞舜之圣王相提并论,而将耕渔子之行为归结为“逃兵革,避乱祸,或耘于高,或钓于深,以待天下之清”的伊尹、吕望之隐。耕渔子则反问道:
“子饮牛而行,饭牛而歌,岂所谓箕山巢许之友欤?南山扣角之俦欤?否则乘蒲鞯、挂《汉书》,徘徊而相羊者欤?”结果是“牧者不答,策牛而去”,留下一个余音袅袅的结尾。杨基此时虽仅三十余岁,但已经历诸多人生波折,“著书十万余言,名曰‘论鉴。试仪曹不利。会天下乱,归隐于吴之赤山。张士诚时辟为丞相府记室,未几辞去。又客饶介所”。他在至正二十年左右撰写该文时,正处于半仕半隐状态,对于徐达左之隐居选择有更为深入的体验,其“以待天下之清”的“待”与高巽志“士必有待”仍存在明显差异。杨基之“待”是要等待天下太平,高巽志则是藏身以待机会。
对于这些猜测,徐达左全都采取回避态度。
到了唐肃(1318—1371) 与包大同的铭文,已不再纠缠于隐居动机问题,而是就其效果落笔。唐肃铭文曰:“朝华其宫,莫或易而翁;昨鼎而食,今或脔其骼。勿舍予田,勿忘予筌,于以老吾轩。”祸福总相依、富贵常难保,本是历史的常态,但真正能够见幾而作、未雨绸缪者却寥寥无几。据钱谦益记载,唐肃“至正己亥,中浙江乡试,授黄冈书院山长。己巳,转嘉兴儒学正”。此种山长、学正之类的低级职位是最能体会官场之变幻无常的,更何况处于至正后期诸方豪强混战之时,他是否真能到位履职都是疑问。因此,在唐肃看来,还是徐达左隐于耕渔是上策。包大同的铭文不仅是对唐肃铭文的深化,还提出了“道”的核心概念:“安乎其庐,载耕载渔,或以鄙子之迂。澹乎其荣,载渔载耕,或以薄子之行。孰鄙孰薄,耕渔自乐,将以乐乎丘壑。君子乌乎,予以宁其处若吾子者,志于道而已。尔世孰知其为龙蛇为尺蠖也耶?”隐于耕渔,乐于丘壑,不计一己之荣辱,不顾世人之鄙视,是因为耕渔子有“志于道”的高远追求,那些凡夫俗子如何能够通晓龙蛇之藏与尺蠖之屈的妙理。由此,便从高巽志、杨基的仕隐之辩转向“志于道”的探讨。王行(1331—1395)《耕渔轩诗序》对此作了进一步引申:“盖耕渔野人之事耳,以野人之事而得咏歌于大夫士者,其必有道矣。吾意其耕也足以养其家,渔也足以奉其亲。在堂有余欢,在室有余乐,混迹于乡人之涂,致意于哲人之言,而存心于圣人之道也。大夫士求之于内而嘉其志于道,故时而称扬之。”在王行看来,徐达左的“志于道”分两个层面:一是“在堂有余欢,在室有余乐”的养家奉亲之乐;二是“致意于哲人之言,而存心于圣人之道”的高远境界。然而,王行在此并未言及“道”之内涵,而是在结尾处引用孔子“以友辅仁”的格言,以回应高巽志的发端之文,断言“今其友有高君焉,高君多文而好学,良辅既得而友之,必不至于怠也”。此言当然不错,后来徐达左便是以此意命名其《金兰集》的,可惜此处乃针对高巽志而发,偏离了对“致意于哲人之言,而存心于圣人之道”内涵的阐发。
其实,最能说明徐达左“志于道”内涵的并非此类序、记、铭文,而是其好友倪瓒的题画诗:“邓山之下,其水舒舒。林庐田圃,君子攸居。载耕载渔,爰读我书。唐虞缅邈,怆矣其悲。栖迟衡门,聊得我娱。敬慎诚笃,德罔三二。四勿是克,三益来萃。彼溺于利,我以吾义。彼弃懦顽,我以仁智。匪今之同,惟古是嗜。虚徐消摇,隐约斯世。”诗前有小序曰:“予既为良夫友契作耕渔图,复为之诗。”可知该诗乃专门为咏其圖而作,是对画面寓意的揭示。倪瓒对徐达左隐居耕渔行为的概括,显然超越了普通友人的认知。他对“虚徐消摇,隐约斯世”的理解,除文人必备的诗酒山水外,更包括研读经史的“爰读我书”、期盼唐虞盛世的高远理想、“敬慎诚笃”的高尚品德、“四勿是克,三益来萃”的道德检束、“彼溺于利,我以吾义”的君子小人之辩以及“彼弃懦顽,我以仁智”的明智选择。“儒隐”品格乃是徐达左区别于顾瑛、倪瓒以及许多元明之际隐逸文人的明显标志,更是他能够与此二人鼎足而三的主要原因。关于此一点,徐达左曾经师从过的邵光祖题诗表述得更为清楚:“贱事宁我志,其如时命何。非耽田野乐,为养性情和。把钓遂安适,躬耕且咏歌。嘉苗无助长,止水讵容波。晚饭炊菰米,烟蓑挂薜萝。此中有真理,不独首阳阿。”从外在行为看,“把钓遂安适,躬耕且咏歌”,“晚饭炊菰米,烟蓑挂薜萝”,的确与一般隐逸之士无明显差别,但其隐居“非耽田野乐”,而是“为养性情和”,所以“嘉苗无助长,止水讵容波”便非自然景色之描绘,而是理学静心修为、从容涵养之举。由此,“此中有真理,不独首阳阿”的表述,不仅明确将其与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等狂狷之士区别开来,也与“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拉开距离。尽管“真意”与“真理”仅一字之差,却将玄学与理学的底色差异和盘托出。倪瓒、邵光祖与徐达左亦友亦师,这使其能更为深刻地了解徐达左的为学品格与内心世界,从而相当清楚地指明耕渔轩隐居的真实意向。
对于徐达左为人处世了解的深浅不同,决定了不同作者对其耕渔隐居的认知差异。这或许仅为问题之一面,另一面是:身处张士诚治下的士人,倘若要安然生活、独善其身,须在行文时故意掩饰其拒仕而隐的行为。高启曾在《娄江吟稿序》中采用此种笔法,说身处天下崩离多事之秋,“孰不愿出于其间,以应上之所需,而用己之所能”,遗憾的是,“余生是时,实无其才,虽欲自奋,譬如人无坚车良马,而欲适千里之涂,不亦难欤!故窃伏于娄江之滨,以自安其陋”。整篇诗序,毫不涉及诗学问题,却反复论说自己的无能及无用,其小心翼翼以自解的心态显露无遗。道衍《耕渔轩诗后序》采取了大致相近的行文方式,围绕着求乐自适的主旨展开,一入笔便感叹其闲居无聊,“求志相得语相合者尤甚,常郁郁不自乐”,由此引出徐达左的自我介绍与求诗序之请:“某家太湖之滨,读祖父之书,亲耕渔之业,不求知于人,不谋庸于世。乐乎其心恒犹有余,忖乎其己每若不及。既饫其实,又燠其裳,故吾适其适而不外之也。”并言“将求子文以序其后,子弗吾拒也”。他强调了自己隐居的两个目的:对外“不求知于人,不谋庸于世”;对内自“适其适”。道衍通观诗卷诸作后,以众人之誉肯定其贤德:“吾友数君子,学广而识明,行高而德厚,树期业如古先贤,凡毁誉人一弗妄,人得其言亦弗易也。今良辅交其人而得其言,予以见良辅之贤信不虚矣。”通过夸赞诗卷中众位友人之贤明,烘托徐达左之“贤”德,一笔双写。随后笔锋一转,方言归正传。倘若论及志趣相投,享受隐居自适之乐,唯有自己堪与徐达左相配。因为“数君子或出于仕途,或羁于异方,或处于城郭,虽欲适良辅之居,叙耕渔之乐,不可得也”。唯有自己此一浮屠闲人,“愿从荷锄于町畦之间,听鸣榔于烟波之上,倦则休于轩,醒而歌,醉而卧,或倚于床,或枕于股,冥然出于万物之表者。良辅非我,其谁与俱乎”。道衍序文无论从对话结构的设置还是余音缭绕的结尾看,均充满诗意的表达,突出了徐达左高远闲适的志趣、性情相投的快乐以及诗情画意的人生,乃是对隐居状态与效果的审美化书写。有了该序,有关《耕渔轩诗卷》的讨论才算完整。因为全身远祸是精心的算计、待时而动是功名的谋划、志道修德是伦理的检束,尽管这些对于元末“儒隐”来说,皆为不可或缺之重要元素,但缺少了性情的陶冶与适意的快乐,便是僵硬刻板的说教,从而遮蔽了“儒隐”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现场效果。后来明人徐有贞赞誉徐达左说:“当胜国之季,更运之初,士大夫能自善而终其身者,难矣。而良夫独龙蛇其间,从容去就,不激不污,卒以不屈,声名俱全,不亦哲哉。至考其学术行义之实,盖庶几所谓君子儒者。”说徐达左“声名俱全”当然是历史事实,说他是“君子儒”自然也没错,但说他所有的选择均系“龙蛇其间”的“哲”人之举,仿佛一切都经由谋划而尽在掌控之中,则非但是倒看历史的后见之明,更属于榨干历史多样性的抽象概括。
三、《耕渔轩诗卷》的诗学内涵与意义
从诗学角度讲,道衍对徐达左隐居行为的诗意描绘或许更为重要,因为在《耕渔轩诗卷》中,诗才是主体,文不过是对诗与画寓意的揭示而已。除了道衍的《耕渔轩诗后序》,其他几篇序、说、铭文几乎没有讨论任何诗学话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诗卷缺乏诗学品格与意义。事实上,对徐达左隐居生活的诗歌书写本身便充满诗意。诗卷初次结集的16人所题18首诗作中,周砥之作从总体上描绘了其隐居状态:
夙存迈往志,结茅依山泽。不辞沮溺劳,更慕濠梁逸。既耕亦以钓,四体欣暂息。新稼登场丘,嘉鱼荐晨夕。蒸尝无足患,喜复留我客。野田荒烟翳,平湖微景寂。开檐睇孤云,窅然无遗迹。缅怀高世士,何尝异今夕。识达理自周,情恬虑非易。念子属纷纠,抗俗愿有适。束带趋城府,愧予尚促戚。百年诚草草,会当谢兹役。
周砥(1324—1363) 是玉山雅集与北郭雅集的常客,《姑苏志》载其生平曰:“周砥,字履道,吴人,号匊溜生。博学攻诗,豪放自好。尝寓居无锡,转徙宜兴之荆溪,与马治孝常者穷山水之胜,著《荆溪唱和集》。晚归吴中,复与高、杨诸人结社。兵兴,去客会稽,竟死于兵。砥效坡书甚工,亦工画山水。”在以高启为首的北郭文人群体中,周砥属于年龄稍长者,自然也较受尊重,故而其题诗仅在倪瓒之后,位列第二。他此时大约正在张氏政权中担任记室之类的低级文官,故而有暇厕身耕渔轩题诗者行列。这首五言古诗是对徐达左耕渔隐居的全面叙写。首六句总写其隐居自适之志,“沮溺”代指其耕于山,“濠梁”隐含其渔于泽,并有人鱼相得之乐。接着引出主题“既耕亦以钓,四体欣暂息”,随后四句写耕渔生活:新稼登场为耕之收获、嘉鱼之享为钓之结果、献祭无忧见孝道无缺、留客而饮显友朋之乐,可谓“儒隐”生涯之再现。再后四句为耕渔环境之勾画,荒烟笼罩,平湖幽静,抬头观云,窅然无际,一派自然和乐景象,这些应是对倪瓒所绘画面之描绘,乃题画诗之常规笔法。此后四句乃联想,只要见识高超而通达天理,便可获“情恬”之意趣,古今皆然,何尝有异!最后六句归结于自我感叹:身处如此纷争混乱时代,实在羡慕您这超越世俗的快适生活,可惜我依然忙碌奔走于官衙之中,人生短暂,希望及早卸掉这官场俗务,隐于山水中。全诗对徐达左耕渔生涯叙述完整,层次井然,有叙事,有写景,有赞慕,有感叹,可谓用心之作。尽管这仅是周砥的一时感慨,隐逸并非其现实选择,他依然在官场奔波,并最终在会稽“死于兵”,但高启在《荆南唱和集后序》中依然对其诗赞赏有加:“读其诗者,见其居穷谷而无怨尤之辞,处乱世而有贞厉之志。”由此也就不难明白,周砥何以能够参与耕渔轩题诗并写出如此诗作。倪瓒四言长诗与周砥长篇五古奠定了《耕渔轩诗卷》的基本内容与话题范围,随后14人的作品在书写方式与意义指向上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对徐达左隐居之举与高人形象的称赞与向往,如周砥、虞堪、陈惟寅、仇机、王禋、苏大年、周伯琦、余诠等人诗作。此类题诗一般均将徐达左隐居喻之为汉人徐稚,如云“出处不惭徐孺子,文华能敌马相如”(沙大用),“千古清风仰高节,南州孺子彼何人”(苏大年),“试问虎丘山下客,当时箕颖(颍) 果何如”(周伯琦)。按,徐稚,字孺子,东汉名士,世称南州高士,曾屡次被朝廷及地方官征召,但终其一生隐于乡里而未仕,被后人誉为淡泊明志的隐逸典型。余诠题诗云:
朝耕鄧山云,暮钓具区雪。兹焉寄幽悰,孰云事高洁。石田虽跷确,贡赋岁不缺。烟波空浩荡,踪迹讵能灭。矧非沮溺俦,畎亩耰不辍。宁同羊裘子,翩翩与世绝。林庐颇深幽,门巷寡车辙。暇日肆微勤,追踪古先哲。素志谅不违,余生自怡悦。
作者认为,徐达左的隐于耕渔并无借隐居以邀名之动机,他尽管在邓尉山过着耕渔生涯,却不同于长沮、桀溺或者严光之类与世隔绝的高人隐士,他并非以隐居博取高洁虚名。其耕渔山泽完全是为了追求一种幽静、安宁的环境,从而满足自我“怡悦”之志。此乃为友人之隐居行为作淡泊明志的善意说明,刻画出一位心态宁静、志向高远的“儒隐”形象。与徐稚等传统儒士相比,徐达左形象中渗透着浓厚的修身、齐家色彩。比如张纬之诗以“浮沉干戈际,无誉亦无毁”为主旨,写其忘怀世事、心地超然,与传统隐士如出一辙,所以才会说“缅怀清渭滨,何如鹿门里”,即不必以自我之清高显世俗之污浊。但徐达左之隐居自有其独特的内涵,既有“酿秫云翻瓮,鲙鱼雪飞几”的饮食之乐,更有“客来具杯酌,客去味经史”的儒学修为,客去客来一任自然,既不像顾瑛那般盛情相邀而共聚求乐,又不像倪瓒那样高标自傲而鄙视世俗。其经史之乐、自我修为与家族教育的生活内容,绝不比朋友间的杯酌之欢分量轻,此乃徐达左隐居之真实写照,更是元末“儒隐”的时代特色。
二是对耕渔轩优美景色与人生情调的诗意描绘,如徐贲、陈惟寅、倪瓒、陈宗义等人诗作。倪瓒诗曰:“溪水东西合,山家高下居。琴书忘产业,踪迹隐耕渔。积雨客留宿,新晴人趁墟。厌喧来洗耳,清泚绕前除。”首二句写实,谓东西皆有溪水环绕,隐逸居舍随山势高低参差而立。倪瓒既到过耕渔轩,又系为自己画作题诗,自然精炼而准确。后六句抒发自然、清新之感受:环境清幽、志趣闲远。全诗具有超然、闲适的审美格调。徐贲(1335—1380) 诗曰:“荷锸喜逢春雨,鸣榔又近黄昏。谁道南阳渭水,不似桐江鹿门。”“门泊陶朱归棹,家住张翰故乡。霜落鲈鱼出水,秋晴嘉谷登场。”徐贲此诗尽管用了姜子牙、孟浩然、陶朱公与张翰等历史上隐逸高人的典故,但其叙述重心还是对徐达左隐居境况的赞美。陈惟寅诗偏于抒情:“一具牛,二顷田,力耕而食度年年,若人之乐无比焉。”“一叶舟,五湖水,风引钓丝鱼不起,闲咏沧浪一乐耳。”二诗一写“耕”、一写“钓”,紧切“耕渔”诗题,用“若人之乐无比焉”与“闲咏沧浪一乐耳”以表达隐居生活之轻松惬意,诗境自然开朗。陈宗义诗曰:“筑室远尘嚣,开轩更清绝。闲锄南山云,时钓东湖月。犊背晚山青,船头秋水白。安得往从之,使我心如结。”如果说倪瓒诗虽然清新自然、情景如画,但依然具有写实特点,那么,陈宗义此诗则完全是虚化的诗意想象。一开篇即写居处远离“尘嚣”而格调“清绝”,为全诗定调,然后便是锄云钓月的诗意勾勒和“犊背晚山青,船头秋水白”的背景烘托,这样,就将徐达左隐逸生活提升至一种诗意高度,显示出其闲逸的审美品格。
三是通过对耕渔轩隐逸行为的赞誉,表达自我人生意趣。高启、王隅、张羽等人诗作即属此类。高启诗曰:
朝闻《孺子歌》,暮听《梁父吟》。岂无沧州怀,亦有畎亩心。昔贤在泥蟠,终当起为霖。钓获溪上璜,锄挥瓦中金。兹世方丧乱,伊人邈难寻。既迷烟波阔,复阻云谷深。嗟我岂其偶,聊将学幽潜。惟子是同抱,相期清渭阴。
高启本有建功立业的志向,但因遭遇战乱而不得不隐居赋诗,故其诗反复引述吕尚、华歆君臣遇合典故,渴望重演“昔贤在泥蟠,终当起为霖”的历史故事。但眼下战乱四起,时局混乱,一时难有机遇,不得不“聊将学幽潜”。同时他认定徐达左亦有隐以待时之志向,故而结语勉以“惟子是同抱,相期清渭阴”。意旨虽然不难理解,表述尚较含蓄。王隅诗则直言不讳地将此意点明:“主人可能从我请,借我开轩对烟暝。与君极谈济世略,君抱长策玉在矿。借令刖足亦可笑,圣贤出处有要领。吕望岂意遭周猎,伊尹却负干汤鼎。吾以吾手奉君锄,君以君力为我骋。聊将榔板敲一声,鲛鼍跼敛风波静。清明有才亦如此,奚必区区事箕颖(颍)。鲙鱼飞雪落牛蓑,暂赏湖光三万顷。”在所有耕渔轩题诗中,王隅诗写得最为气势飞动而境界开朗,一句“暂赏湖光三万顷”,将所有的耕渔隐居生活与自然风光均置于视野之外,口中谈的是“济世略”,心里想的是“为我骋”,求的是“鲛鼍跼敛风波静”。在他看来,既然具备了修齐治平的才能、品格,何以还要有“事箕颖(颍) ”的隐居之举呢?可惜的是,这仅为王隅的人生理想,而非徐达左的现实选择。高启、王隅的隐居吟诗乃是待时而动的蛰伏,与徐达左所思所为全然不同。其实,作为寄居平江的北郭文人群体成员,他们本来就有各不相同的生活经历与人生理想,尽管隐逸是他们身处战乱的共同选择,但动机却又各不相同。关于此点,张羽之诗提供了坚实证据:“之子住铜坑,人传好士名。如何同甲子,未得尽平生。野岸风中钓,湖田雨后耕。秋天渐凉冷,或可赴前盟。”张羽(1333—1385),字来仪,又字附凤。由其诗可知,他仅仅由传闻得知徐达左有“好士”之名,但自己却“未得尽平生”,那么“野岸风中钓,湖田雨后耕”也仅为想象揣测之词,从结语“秋天渐凉冷,或可赴前盟”看,他尚未能够见识此位深隐不出的名士,自然只能从自我感受来写想象之辞了。由高启、王隅与张羽的诗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耕渔轩诗卷》展现了元末吴中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与不同志向的文人对于“隐逸”话题的理解与兴趣,传达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情感诉求与审美感受。
余论
《耕渔轩诗卷》中所讨论的“隐逸”话题具有独特的时代典型性。就儒家思想传统而言,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本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经典《大学》便是如此设置“三纲领”“八条目”的。然而《耕渔轩诗卷》中所谓“有待”的进取观念,却并非唯一的价值取向,甚至不是主要价值取向。徐达左及部分诗友显然是将个体道德修为与品格操守作为追求目标,但又和政治参与无关,更有甚者,将山水审美、个体适意与家族教育、理学涵养融为一体。同时,在元末风雨飘摇的危局中,他们在谈论“隐逸”话题时显得如此从容不迫、悠游淡定,无论是待时而动之权且隐居还是往而不归之融入山水,均系从个体生命角度考虑,而无关乎朝代之兴衰、政权之更替。这显示出元明之际士人的独特立场,与同为易代之际的宋元、明清时期相比,差异甚为明显。宋元与明清易代之际的主调是愤激、悲凉、忧伤与绝望,士人关注的是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诚如黄溍论元初方凤诗作所云:“遇遗民故老于残山剩水间,握手歔欷低回而不能去,缘情托物,发为诗歌……故其语多危苦激切。”这些时期的画风亦与诗风大体一致。拿最具代表性的郑思肖(1241—1318) 与朱耷(1626—1705) 看,郑思肖所绘兰花无根,乃因土地为异族所占据,“此中的兰花因而也象征着画家本人,漂泊不定,羸弱无力,但是仍然怀抱一片孤忠”;朱耷亦善画兰花,其格调也怪诞而孤冷。更具比较价值的是钱选(1239—1299) 的绘画,《浮玉山居图》是其最为后人欣赏的代表作,该画乃钱选为其隐居的霅川浮玉山所绘之景,画中山势峻峭,湖雾蒙蒙,隐者所居茅舍白云缭绕,隐含着作者隐居山中的孤寂、冷漠心绪。钱选自题诗曰:“瞻彼南山岑,白云何翩翩。下有幽栖人,啸歌乐徂年。丛石映清泚,嘉木澹芳妍。日月无终极,陵谷从变迁。神襟轶寥廓,兴寄挥五弦。尘影一以绝,招隐奚足言。”诗后题云:“余自画山居图,吴兴钱选舜举。”诗人对日月流逝、陵谷变迁已释然于怀,逍遥自在地徜徉于白云嘉木中,啸歌闲适,安度岁月。此种隐逸情怀显然已与陶潜略无二致。然而,此画在钱选生前却并未获得亲朋好友的应和,直到延祐四年(1317) 钱选逝世近二十年后,方有画家仇远(1247—1326) 为其题记赋诗。可知关于“隐逸”的话题虽在宋元之际亦为文人所难以回避,但并无多样化的理解与认知,故而没有形成话题集中的题画诗卷。彼时文人在隐居山间水涯之时,总难以忘怀那种刻骨铭心的亡国之痛。即使是钱选那些充满隐逸情趣的画作,依然被后人读出弦外之音:“钱选的萧散洒脱中,隐隐然仍流露着一丝惆怅,一种对逝而不复的伤挽情怀。”该图重新成为文坛关注的对象乃在元明易代之际,诸如张雨、顾瑛、倪瓒、郑元祐、黄公望、琦楚石等文坛名宿纷纷为之题诗品评,并寄寓自我隐逸情怀,从而与周景安《秀野轩图》、徐达左《耕渔轩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构成当时的“隐逸”话题诗卷。其中,《耕渔轩图》由于徐达左“儒隐”的品格而受到更多文人的青睐。由此可知,只有具备了元代文人长期被政治边缘化的旁观者心态以及吴中暂时偏安一隅的历史环境,方能为“隐逸”话题的多元表达提供适宜的场域,从而使其拥有独特的历史品格。
从诗学史的角度看,《耕渔轩诗卷》呈现了元明之际书、画、诗、文共为一体的独特文本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其主要特性便是文体的多样性、话题的开放性与内涵的丰富性,既能展示书法、绘画的高超艺术水平,又能充分表达不同作者对于同一话题的不同理解,还能展现各自的诗歌创作水准与诗学观念。通过这样的诗卷研究,能够立体呈现出那一时代文坛的真实状况与诗学内涵。对于此种文本形态,以前学界很少关注,无疑放弃了观测文学思想整体的一个有效角度。倘若以类似方式系统研究该时期像《听雨楼诗卷》《破窗风雨诗卷》《秀野轩诗卷》《安分轩诗卷》等数十幅同类的诗卷,必将有效推进相关研究,从此一角度看,本文的研究或许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探索意义。
①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仅有祝军《金兰集考论》(《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王媛《元明之际耕渔轩文艺活动考论》(《阴山学刊》2014年第2期)、王露《金兰集研究》(山西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王露《耕渔轩诗歌写作时间考证》(《汉字文化》2018年第2期)。
② 杨镰:《金兰集前言》,徐达左辑,杨镰、张颐青整理:《金兰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页。
③ 比如朱存理《铁网珊瑚》载有题诗作者“三山王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则作“三山王禋”,据考,实为“王禋”,“机”乃笔误,参见朱存理辑录,韩进、朱春峰校证:《铁网珊瑚校证》,广陵书社2012年版,第611页;卞永誉纂辑:《式古堂书画汇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7页。
④ 王都中及其子孙辈情况见黄溍《正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王公墓志铭》(王颋点校:《黄溍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40—745页)。
⑤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王蒙《谷口春耕图轴》,有王禋题诗曰:“满眼荆溪入画图,数椽茅屋倚苍梧。秫田二顷躬耕处,坐石看山酒旋沽。”署名“三山王禋”,并有“王仲明”印章。知其与王蒙亦有交往,并具诗才。
⑥王鏊:《姑苏志》卷三四,《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789页,第436页,第641页。
⑦ 倪瓒:《题朱泽民小景》,倪瓒著,江兴祐点校:《清问阁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页。
⑧ 朱存理辑录,韩进、朱春峰校证:《铁网珊瑚校证》,第580页。
⑨ 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38页。
⑩ 朱德润曾为耕渔轩作画,有倪瓒《题朱泽民为良夫作耕渔轩图》为证:“寂寂溪山面碧湖,轻舟烟雨钓菰蒲。晓耕岩际看云起,夕偃林间到日晡。汉书自可挂牛角,阮杖何妨挑酒壶。江稻西风鲈鲙美,依依鲙食待樵苏。”(《清问必阁集》,第199页) 又朱德润曾有《题云山图》与《题雪夜读书图赠良夫》,后收入《金兰集》中,却没有题耕渔轩的诗作。朱德润逝世于至正二十五年,而道衍《耕渔轩诗卷后序》也作于本年,知朱德润的图与诗均作于此前。
吴迪点校:《张雨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
卞永誉纂辑:《式古堂书画汇考》,第896页,第894页,第894—895頁,第895页,第895页,第896页,第896页,第898页,第896页,第897页,第897页,第897页,第898页,第897页,第896页,第897页,第896页,第897页,第897页,第1822页。
徐达左辑,杨镰、张颐青整理:《金兰集》,第119页,第2页,第22页。
杨镰曾说:“积极参与徐达左耕渔轩唱和者,蒙古、色目人(西域人) 有沙大用(沙可学)、马肃、钮安、包大同等。”(《金兰集》,第2页) 杨镰又在《全元诗》仉机沙小传里说:“仉机沙,字大用。西域回回。汉语名为沙大用。”(杨镰主编:《全元诗》第52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0页) 马明达、陈彩云《元代回回人沙可学考》(《回族研究》2008年第4期) 则引元末僧人释来复在沙可学所作《奉题定水见心禅师天香室》诗前题注“哈珊沙字可学,西域人。至正壬午年拜住榜登进士第,枢密院都事”,知沙大用又名哈珊沙。元代汉族学者在汉译蒙古及西域人名时多为音译,故有诸多不同译名。至于杨镰所言马肃、钮安与包大同等人的民族归属与身份,则缺乏更多材料支撑,或许是根据其命名习惯作的推测。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第113页。
徐一夔:《师友集序》,徐永恩点校:《徐一夔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05页。
高启:《题高士敏辛丑集后》,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点校:《高青丘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25页。
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点校:《高青丘集》,第892页。
周砥生卒年系参考汤志波《元代周砥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4期)。
高启:《荆南唱和集后序》,《高青丘集》,第878页。
卞永誉纂辑:《式古堂书画汇考》,第897页。关于倪瓒此诗的写作时间,文献记载存在较大差异。张丑《清河书画舫》(徐德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0页) 及倪瓒《清问必阁集》(第83页) 所录该诗前均有小序曰:“仆来轩中,自七日至此,凡四日矣。风雨乍晴,神情开朗,又与耕云、耕渔笑言娱乐,如行玉山中,文采自足映照人也。喜而赋此诗。”黄苗子、郝家林《倪瓒年谱》(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据此将该诗作时定为洪武六年(1373)。但此诗早已出现在元末《耕渔轩诗卷》上,《式古堂书画汇考》(第897页) 与朱存理《铁网珊瑚》(《铁网珊瑚校证》,第612页) 均录此诗,而赵琦美《铁网珊瑚》无载。道衍《耕渔轩诗卷后序》作于至正二十五年,据此,倪瓒此诗作时不当早于此年。一般来说,当以出现较早的《耕渔轩诗卷》作为作时依据,除非能够证明《耕渔轩诗卷》为明人伪作,否则不当推翻此结论。如果要寻找二者相互矛盾的原因,或许《金兰集》的记载能够提供一些线索。《金兰集》将该诗编入卷二(第20页),但其小序变为诗后跋语,其他内容皆与《清河书画舫》《清问必阁集》同,唯有最后两处不同:一处为“而又与耕云、耕渔笑言娱乐”,《金兰集》作“又与耕渔笑言”;另一处为“喜而赋此诗”,而《金兰集》作“喜而复赋此”。萃古堂抄本《金兰集》则将此诗编在卷一。这些差异不应视为无关紧要的文字疏漏,而是存在着重要的学术信息。其中“喜而复赋此”之句,此“复”可有二解:一是当年画《耕渔轩图》后,先题有那首四言诗,后来又到轩中“笑言娱乐”,“复”题了该首五言诗;二是元末为《耕渔轩图》题了这首五言诗,明洪武六年再与耕云一起访问徐达左耕渔轩时又重写了此首五言诗,“复”乃即兴重书之意。此二种说法均可通,本人认为系第二种情况。但无论是哪一种,均可从侧面证实该诗最早应作于元末至正二十五年之前。元末集部文献错综复杂、真伪难辨,该问题有待新文献发现,方可做出定论。
黄溍:《方先生诗集序》,《黄溍集》,第397页。
高居翰:《隔江山色:元代绘画(1279—1368)》,宋伟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9页。
于偲璠:《八大山人绘画构图的“孤”式表达》,《美术大观》2019年第11期;张静:《观八大山人绘画中的“怪诞”与“孤冷”形式》,《美与时代》2021年第1期。
刘中玉:《元代文人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陈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