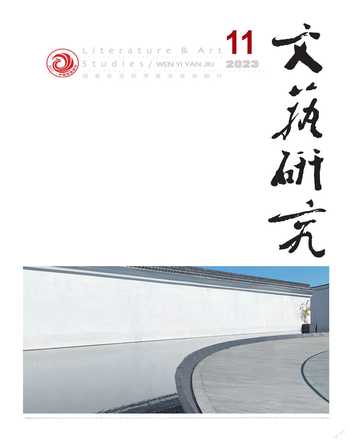贝瑞斯·高特的艺术集束论与析取式艺术定义取向
2024-01-11黄应全
黄应全
摘要在分析哲学中,用集束的方式理解概念源自希拉里·普特南,但贝瑞斯·高特的艺术集束论的理论基础是维特根斯坦和塞尔的专名理论。高特认为,用集束的方式可以界定但不能定义“艺术”。他主张,不存在某种可以把某物确定为艺术作品的普遍性质,存在的只是一组具有局部性、情境性但足以构成充分条件的性质。高特从直觉的充足性、规范的充足性、启发的有用性三个方面为其理论做了辩护,而他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集束论为何不能是一种定义类型;二是更一般的非难,即无论是否属于定义,集束论都包含着析取式艺术定义取向对“艺术”概念分裂或杂糅本质的信奉,这也是集束论的争论焦点。
在关于概念本质的辩论中,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 提出了一个新术语——“集束概念”(cluster concept)。他认为,在古典力学向相对论转化的过程中,动能理论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能量概念”(e) 的外延(即它所指称的东西) 并未发生变化,能量的形式和行为还是原来的样式,无论在爱因斯坦之前还是之后,它都是同一种东西。为了理解这种现象,普特南发明了所谓的“规律-集束概念”(law?clusterconcepts)。规律-集束概念由规律-集束语汇表述,这种语汇可以出现在对众多科学规律的不同陈述中,放弃其中任何一种陈述都不会改变该语汇所传达的那个概念。比如,如果我们把表示能量的“e”视为规律-集束语汇,就不难接受这样的看法:当旧的能量方程式被放弃的时候,“e”却未发生变化。普特南以“人”(man) 为例说明什么是集束概念。如果我们要问人是什么,回答“人是理性动物”或“人是无羽毛动物”在今天显然已经行不通了。假定我们列举出构成一个正常人所需的一系列特征P1、P2……那么可以接着提出这样的问题,“没有P1,人还存在吗”,“没有P2,人还存在吗”,每一次得到的回答也许都是“还存在”。这似乎意味着“人”这个词根本不具有任何含义,但这显然是荒谬的、不可能的。“为了解决这种困难,哲学家们引进了一种可称为‘集束概念的观念。”①普特南明确表示“集束”是个隐喻,它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对应的是“粗绳”(rope)。粗绳由很多股细绳编织而成,没有任何细绳能够达到粗绳所具有的长度。据此,集束概念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概念类型,它不需要具备某个单独说来是充分必要条件的特征,甚至不需要具备某个单独说来是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的特征,而只需要具备一系列界定性特征,其中任何特征单独说来都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但这些特征的某种组合足以构成充分条件,从而确保该概念得到正确使用。
既然哲学界已经有人可信地证明了集束概念的存在,那么不难设想美学界迟早也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艺术”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集束概念?英国美学家贝瑞斯·高特(Berys Gaut) 便是回应这一问题的关键人物,他在2000年发表了《作为一个集束概念的“艺术”》(“Art”as a Cluster Concept) 一文,尝试用集束概念来“界定”(characterize)“艺术”这一概念。由于高特坚持认为只能通过“给出一组单独说来是必要条件、结合在一起是充分条件的性质”②来界定艺术,他拒绝把自己的集束论视作一种艺术定义。如果我们更宽泛地理解“艺术定义”一词的话,高特的集束论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析取式艺术定义,甚至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析取式艺术定义③。对此,哈罗德·奥斯本(Harold Osborne) 和詹姆斯·D. 卡尼(James D. Carney) 等人的批评表明,析取式艺术定义只是理解“艺术”概念的诸种范式之一,而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 的倾向说明,析取式定义依然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
一、高特艺术集束论的基本内容
高特认为,20世纪50年代新维特根斯坦艺术观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艺术”概念只能根据家族相似加以界定,这总体上是对的,其错误实际上仅在于用相似于既有经典作品来理解家族相似,如果用集束概念来理解家族相似的话,就可以避开那些针对家族相似说的批评。不过,高特的集束概念不是直接照搬普特南的观点,而是来自维特根斯坦和塞尔的专名理论。高特说,维特根斯坦在阐述其家族相似说时还提出了作为家族相似说一部分的专名理论。维特根斯坦说:
但我现在说出一个关于摩西的命题,——我总是准备好了用诸种描述中的一种来代替“摩西”吗?我也许会说:说到“摩西”,我理解的是那个做了《圣经》里说摩西做过的那些事的人,或者是做了其中大部分的那个人。可到底是多少?我是否已经决定了其中多少证明为假之后,我就认我的命题为假而加以放弃?“摩西” 这个名称是否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对我而言都有一种固定的单义的用法?——实际上像不像是:我准备着一系列支撑物,抽掉一根,我就依靠另一根;反之亦然?④
这段话的要义在于,它一方面主张专名具有含义,不是仅具有指称;另一方面又主张专名的含义并非固定的和单一的,而是依赖于一组变动不居的性质。高特认为,塞尔在维特根斯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有关专名含义的更详细、更清晰的集束式理论,维特根斯坦和塞尔展示了集束论的基本特征:“就这种概念的使用而言存在着多种标准,尽管没有一种是必要的;就一个对象如果要置于该概念之下必须使用这些标准中的多少而言,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在全有与全无的极端情况下是很清楚的。”⑤
高特说,集束论如果要适用于某个概念,就必须存在一些性质,这些性质在某个对象上的实际体现被看作把该对象纳入那个概念之下(即对那个概念的使用) 的概念必要性问题。这句话有些晦涩,大意是集束论并不适用于一切概念,它只适用于某种类型的概念,这种概念在一组性质与对该概念的使用之间存在特殊关系。高特把这些性质称为“标准”(criteria),一个概念往往包含多个标准。从集束概念与其性质的关系出发,高特认为一个概念要成为集束式概念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如果全部性质都具体体现在一个对象上,那么该对象就必定被納入那个概念之下,也就是说,所有性质结合在一起便构成该概念使用的充分条件。不仅如此,集束论甚至主张,即使并非全部标准而只有部分标准具体化在某个对象上,也可能构成该概念使用的充分条件。第二,不存在任何性质单独说来是把对象纳入该概念之下的必要条件,即不存在纳入该概念之下的所有对象都必须包含的性质。必须满足的一点是,尽管存在集束概念使用的充分条件,并不存在单独说来是必要的、合在一起是充分的条件。第三,虽然不存在这种概念使用的单独式的必要条件,但存在析取式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对象要被纳入该概念之下,那么某些标准就要得到使用,这一点必须是真的。
就艺术来说,假定我们构造了一系列性质,如美、表现性、再现性、复杂性、统一性、原创性等,再假定可以表明只要一个对象获得了由这些性质所构成的各种亚系列中的一种,此对象就是艺术作品,而这些性质中没有任何一种是所有艺术作品必须具有的,但所有艺术作品又都必须具有它们中的一些,那么我们就不能根据单独说来是必要条件、结合在一起是充分条件的方式来给艺术下定义,但我们仍然可以给艺术一种界定,即“根据标准或特征阐明它是什么”⑥。值得注意的是,在“获得某种特定亚系列是否就是某物成为艺术作品的充分条件”方面,这种界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存在很多无法确定是否如此的不清晰情形。关键之处在于,存在某些亚系列是某物成为艺术作品必须获得的充分条件。关于此处的“亚系列”,高特指的是从一个集束概念的全部性质中挑选出来的某些性质所构成的次级系列。比如就“艺术”概念而言,美、表现性、技巧性可能构成一种亚系列,表现性、原创性、意图性、统一性可能构成另一种亚系列。高特显然认为,真正决定某物是否为艺术作品的不是艺术的全部性质,而是艺术的某个或某些亚系列性质。与特定对象相应的是特定的亚系列性质,因而这里充满了情境性和不确定性。
高特认为,要想确定哪些性质可以成为艺术集束的组成部分,其基本方式还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不要想,而要看”⑦。高特指出,过去人们误以为维特根斯坦的“睁眼看看”说只针对艺术的显明性质,遗漏了艺术的非显明性质或关系性质,但维特根斯坦实际上要求我们考察相关概念在语言中是如何使用的,其中当然包含了非显明性质或关系性质。先前的美学流派也把某些性质作为某物成为艺术作品的条件,“集束论的新颖之处只在于它把它们作为标准来接受,而不是把它们全部囊括在一起去确定艺术概念”⑧。当然,发现艺术标准还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即考察那些针对某物(如杜尚的现成物) 是否为艺术品的争论,因为此时争论者必须表明他们断定某物是或不是艺术品的理由。
于是,高特列举了十种通常用来断定某物之为艺术品的性质:
1. 包含肯定性的审美性质,如美的、优雅的或精致的(即一些为产生感性快感能力奠定基础的性质);2. 具有情感表现性;3. 具有思想挑战性(即质疑了流行的观念和思维模式);4. 具有形式的复杂性和统一性;5. 具有传递复杂意义的能力;6. 展示个人视角;7. 是一种创造性想象的运用(即具有原创性);8. 是一种作为高超技艺产物的人工制品或行为;9. 从属于既定的艺术形式(音乐、绘画、电影,等等);10. 是一种制作艺术作品之意图的产物。⑨高特说,有人可能会对上述性质中的一种或一些表示不满,或者想添加另一些,这都无关紧要,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捍卫艺术集束中的哪一种或哪一些特殊性质,而在于捍卫艺术集束论本身。当然,列出这些具体性质的确有助于捍卫艺术集束论的形式。
二、高特对艺术集束论的辩护
高特认为,他对集束论的捍卫是要表明其在方法论上满足了三个基本条件:“直觉的充足性”(adequacy to intuition)、“规范的充足性”(normative adequacy) 和“启发的有用性”(heuristic utility)。所谓“直觉的充足性”是指关于某概念的理论阐述必须与我们关于该概念的直觉保持足够的一致。如果一种理论阐述认为某对象满足其所讨论的概念,但我们的直觉认为并非如此,这就构成了对该理论阐述的某种反驳。所谓“规范的充足性”是指理论阐述必须与某种反直觉的原则保持足够的一致,因为直觉并非都是正确的和清晰的,应在直觉与原则之间建立某种反思的平衡。这主要体现为理论阐述必须包含一种“错论”(error theory),以说明为什么某些人会拥有错误的直觉,以及这些直觉为什么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可靠的。在理想情况下,这种错论能够解释为何敌对理论可以得到廣泛接受。所谓“启发的有用性”是指关于某概念的理论阐述在讨论该概念所应用的对象时应该出现在关于对象的真的理论中,或者至少是有启发性的理论中。典型的例子是“科学”概念,其定义(通常是约定式定义) 的提出是为了此后让它出现在相关现象的真的理论中。高特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对其艺术集束论进行辩护的。
先说直觉的充足性。高特说,最简单、最直接的为集束论辩护的方式就是表明那些作为候选者的性质确实适用于把一个对象看成艺术作品,也就是说,它们充分符合我们的语言学直觉。不过必须牢记的是,这些性质只是候选者,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完全可以用另外的性质替换它们。这里重要的只是捍卫集束论本身的可靠性,而非坚持某个特殊标准的必要性。
高特从集束概念的第二个条件开始为“艺术”概念的集束本质辩护,按照前述十种性质说明“某物成为艺术品的标准个别地说来不是必要的”⑩。1. 并非所有艺术作品都是美的、优雅的或精致的,某些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遵循的是“反审美”方针,它们对感性愉悦不感兴趣,而执着于质疑、挑衅、冒犯,用丑与无序作为颠覆策略,如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2. 并非所有艺术作品都表现情感,20世纪60年代客观理性的抽象作品感兴趣的只是色彩的形式关系,如约瑟夫·亚伯斯的《向正方形致敬》系列。3. 并非所有艺术作品都具有思想上的挑战性,传统宗教艺术首先关注的是再现众所周知的宗教观,而非探究、质疑或超越它们。4. 并非所有艺术作品都具有复杂而统一的形式,马列维奇的某些绘画(如《白底上的黑色方块》) 只包含极其简单的形式。5.并非所有艺术作品都具有复杂的意义,伊索寓言和《天路历程》的寓言结构就是例证。6. 并非所有艺术作品都关注原创性,大多数艺术作品都是派生性的。如果一种传统得以延续不断,那么其大多数作品必定是派生性的,有些传统如古埃及艺术还刻意回避原创性。7. 并非所有艺术作品都表现个人视角,例证仍然是古埃及艺术。8. 并非所有艺术作品都是高超技艺的产物,如杜尚的现成物和阿尔弗雷德·沃利斯的绘画。9. 并非所有艺术作品都从属于既定艺术门类,否则不会有新的艺术门类产生。10. 并非所有艺术作品都是制作艺术作品之意图的产物:原始社会不存在“艺术”概念,但我们把原始人的产品作为艺术作品来接受;我们接受民间艺术,但其制作者可能并无制作艺术作品的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性质单独来看都不是艺术作品的必要条件,高特对这些性质的说明正是对“艺术”概念不能合取式理解、只能析取式理解的说明,因为对适用于所有艺术作品的必要条件的否定本身便意味着使不同对象成为艺术作品的是不同的条件,这就是析取式艺术观的要义所在。实际上,虽然不存在合取式必要条件,但必须存在析取式必要条件,这正是高特所说的集束概念的第三个条件。他说:“有理由认为所列举的标准或它们的某种扩展对于一个对象成为艺术作品在析取上是必要的。”
或许有人会说高特所举的例子都是原始艺术或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所以只要像某些人类学家或美学家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否认原始艺术或现代主义艺术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把范围缩小,就会发现可能存在所有艺术作品共同具有的性质,因而单独说来也可能存在使对象成为艺术作品的作为必要条件的性质。但高特认为,即便把原始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排除在外,也不难发现合取式必要条件仍然是不存在的。比如,19世纪已经存在作为艺术作品的丑的绘画(那时的艺术已经不必是美的了);很多传统建筑和音乐并不关注情感表现,个人视角的缺乏可见于大量衍生艺术中;偶生杰作是可能存在的(传统艺术也有无技巧的),某些纯粹为了练习技艺或记录思想而作的素描并无艺术制作意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视为艺术作品。此外,高特宣称,就克里斯特勒所谓18世纪现代艺术系统形成之时的五种艺术形式(绘画、雕塑、建筑、诗、音乐) 而言,虽然巴托认为一种被称为“对美的自然的模仿”的性质是所有艺术所共有的,但不难发现此说是站不住脚的,比如音乐和建筑如何模仿美的自然?实际上,只有集束论可以解释把不同“美的艺术”聚集在一起的真实根据,这种根据不是巴托所说的“同一原理”,而是“几种交叉重叠的考虑”。可见,在高特看来,现代的“艺术”概念从诞生伊始就是集束式的,此后不过在认定标准方面有所扩充而已。
从集束概念的第一个条件来看,高特认为获得恰当的艺术标准亚系列是使对象成为艺术作品的充分条件。一方面,并非获得任何亚系列都是使某对象成为艺术作品的充分条件,比如某些哲学论文包含这样的亚系列:具有思想挑战性、复杂且统一的形式、深奥的意义、原创性,但这个亚系列并不能让这些哲学论文变成艺术作品。另一方面,获得某些特定亚系列是某对象成为艺术作品的充分条件,比如一幅缺乏复杂意义、只是简单赞美乡村景色的绘画,由于它是艺术意图的产物,是优美的、精致的,同时拥有前面提到的其他性质,它便是艺术作品的一个明确例证。也就是说,缺少艺术标准整全系列中的一项或若干项,这种艺术标准亚系列只有在恰当的前提下才能使某物成为艺术作品。值得注意的是,高特一再强调,标准或特征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扩展。因此,如果我们发现所获得的标准对某对象成为艺术作品而言不是充分的,那么有可能不是该对象本身不能成为艺术作品,而是我们的标准需要修正,即增加一些标准以构成恰当的亚系列,从而使该对象成为艺术作品。质疑集束论的具体内容(即所使用的具体标准) 并不能证明集束论的形式(即诉诸标准本身) 是错误的。
高特说,要表明一种理论阐述具有语言学直觉的充足性,一个重要方面是表明它可以避免其对手曾遭遇的难题,集束论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它能避免功能论、体制论、历史主义艺术定义所面临的困境。功能论的主要问题在于艺术功能太过多样和开放,难以被单一定义所囊括,功能论对此的回应是寻找一个支配性功能,通常是审美功能。但“审美”之类的概念本身就难以定义,并且无论怎样削减审美的含义,审美功能论都很难包容杜尚现成物之类的艺术作品。与此相对,集束论强调那些使某物成为艺术作品的因素的多样性,不会为艺术功能的多样性所困扰。除了是否真的存在拥有适当权力并授予某物艺术身份的体制,体制论主要还面临一个困境。如果艺术界代表有很好的理由授予某物艺术身份,那么正是为这些理由奠定基础的东西(主要是对象拥有某种性质) 证明了对象是艺術,体制性授予实则无关紧要,我们完全可以将之弃而不顾。如果艺术界代表没有很好的理由授予某物艺术身份,那么我们也没有很好的理由认可这种授予,在这种情况下授予权同样是无关紧要的。集束论不使用“艺术界体制”这样的观念,仅以标准作为对象成为艺术作品的基础,从而避免了这些问题。
历史主义根据与具有认知优越性的艺术对象的艺术史关联来定义艺术对象,因而面临着“相似于经典”说曾经遭遇的问题,即它必须解释我们如何辨别出那些具有认知优越性的艺术对象。更为关键的是,历史主义本身就是不充分的,因为很可能存在与我们的艺术根本没有艺术史关联的艺术作品。比如我们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挖掘出一些东西,它们的形式非常相似于我们的艺术作品,而且与我们的艺术作品具有相似的功能,但它们是由一个与我们没有来往的消亡很久的外星文明所创造的,历史主义要么认为它们不是艺术作品,要么认为外星人不知道自己在创造艺术作品。集束论不必诉诸艺术史关联就可以很自然地解释为何这种对象是艺术作品。即使诉诸艺术史关联,在集束论看来它也不过是标准之一。因此,集束论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当代主要艺术定义所遇到的问题。此外还有一种对集束论语言学充足性的支持,集束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活动(如烹饪) 虽然近似于艺术却并非是艺术,那是因为它们虽然与艺术共享了某些性质(个人创造性的运用、能够产生感性快感等),但同时又缺乏其他相关的标准(难以表现情感、不能传达复杂意义、不是艺术意图的产物等)。较之直接了当的定义,集束论的一个标志性优势就在于它可以维持这类情况的“硬核性”(hard?ness),并且解释清楚是什么让它们如此“硬核”,即这种情况可以被解释为是真正边缘和不确定的情况。
再说规范的充足性。高特说,诉诸语言学直觉本身已经包含了某种反思的平衡:借助原则来抗衡直觉,比如抛弃某些人所拥有的原始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的直觉。这种抛弃要想不引发怀疑,就必须建立在一种充足的错论基础上。如前所述,错论的作用是解释敌对理论为何有吸引力。集束论可以直接解释为何许多艺术定义都很有魅力,即它们都抓住了一种特殊标准并将其夸大成充分必要条件:表现主义针对的是情感表现,形式主义针对的是复杂统一的形式,功能主义针对的是审美经验。集束论对体制论和历史主义的解释稍微复杂一些,它们产生于对先前种种定义尝试之不足的意识,试图为集束论也认可的更多成分留下空间。
集束论还可以简明扼要地说明为何“什么是艺术作品”这一问题存在大量分歧,即分歧的至少一方把某个标准转化成必要条件,从而误用了“艺术”概念。这里的情况就像维特根斯坦举过的例子:有人否认单人纸牌是游戏,因为他们认为所有游戏都必须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加者,实际上他们不过把游戏的一个标准转化成了游戏的一个必要条件。集束论还可以具体解释分歧在每种情况下的特殊本质。由于存在各种标准,把不同的标准转化为必要条件必然导致关于某对象是否成为艺术作品的相互矛盾的判断。否定现成物或拾得物是艺术作品的人可能把采用高超技艺或者获得重要审美性质转化成艺术的必要条件,否认原始艺术是艺术的人可能认为具有艺术创作意图是艺术的必要条件(他们注意到部落文化缺乏“艺术”概念),否认摇滚音乐或舞蹈音乐是艺术的人可能认为艺术意图性或形式的复杂统一性是艺术的必要条件,而认可上述三种艺术是艺术的人则否认上述性质单独说来是必要条件,认为它们只是一些标准。集束论不仅可以解释分歧的存在,还可以解释分歧的结构。虽然像某种形式的历史主义那样,一种足够复杂和开放的艺术定义或许也能解释这些分歧,但不会像集束论这样简洁明了。除了可以解释不同立场的分歧为何产生,一种充足的错论还必须能够表明至少有一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错论不能只是关于分歧的理论,还必须是关于错误的理论。集束论似乎无法满足这一点,它无法包含规范性维度,而只能坚持标准的多样性。高特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集束论有其自身的规范性,有足够的资源来断定在任何情况下对艺术有争议的各方中至少有一方是错误的。
最后说启发的有用性。从这方面为集束论辩护就是要表明它对美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意义。高特认为,美学领域最好的著作大都没有关注艺术定义问题,而是试图理解艺术所包含的各种能力,比如再现、表现和符号形式。再现、表现和符号形式并非艺术独有,而是艺术、语言、身体姿态和心理状态共有。因此,最好的美学著作不仅关注艺术所特有的东西,还关注艺术与人类其他领域共有的东西,比如美学与心灵哲学、行为哲学、语言哲学的联系。集束论既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思路是卓有成效的,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它,因为在集束论看来,使某物成为艺术的是它拥有的一系列性质,而这些性质是艺术与其他人类领域所共有的。在美学领域内部,这种立足于性质多样性的艺术界定方式既可以促进一种包容多种行为、赋予对象多种性质的拼凑式解释理论,还可以与一种强调价值多元的艺术价值理论保持一致。“因此,艺术集束论鼓励美学家们考察哲学美学与其他哲学分支的联系,同时也为那种对艺术形式和艺术相关性质的多样性更敏感的行为提供合法性证明。这两种美学研究方案单独看来都是有魅力和启发性的。集束论解释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并对那种认为二者可能还将继续富有成效的观点提供合理依据。”
三、对高特艺术集束论的质疑
关于高特的这种集束论,戴维斯认为很难理解为什么高特要假定它与艺术定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完全可以被重构为一种析取式艺术定义,比如它可以采取下述定义形式。某物是艺术作品当且仅当:1. 它包含十个艺术相关性质中的任意九个;2. 或者它包含第五个性质和任何其他六个性质;3. 或者它包含第二、第四个性质和任何其他五个性质,等等。这里的清單可以列得很长,尤其是如果还要把性质所关涉的程度也囊括进来的话。但是,假如这个清单可以列举完备并且比可能艺术作品的清单要短得多,那么它仍然不失为一种复杂但值得重视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满足清单所列举的艺术相关性质组合中的至少一项便是某物成为艺术作品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集束论也许最好被解释为是对一种充分定义所要求的析取式复杂性程度的展示,而非对艺术不可定义论的证明。”
对于这样的观点,高特在他的文章中早有预料。他说,可能有人认为集束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定义,不是所有定义都采用单独说来是必要条件、结合起来是充分条件的方式,也存在析取式定义,比如罗伯特·斯特克(Robert Stecker) 的功能主义。如果事实真的如此的话,高特似乎在自欺欺人或自相矛盾,虽然提出一种定义,却又否认定义的可能性。高特说,这里所涉及的东西从一定程度上说不过是一种用语上的争论。如果非要说既存在合取式定义也存在析取式定义,那么没有理由非要坚持只有合取式才是艺术定义方式。但高特想强调的是,人们不能根据单独说来是必要条件、结合起来是充分条件的方式给出一种艺术定义,事实上合取式定义往往是哲学家在追求艺术定义时想要的东西。随着集束论所要求的分支数量持续增加,把它看成定义的可靠性也会越来越低。高特之所以坚持集束论不是定义,主要是因为他不仅用析取式来看待“艺术”概念,而且把“艺术”概念的析取式结构看作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假如艺术相关性质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根据形势发展适当添加的,那么戴维斯所说的那种完全列举就是不可能的,因而“艺术”概念即使是析取式的,似乎依然是不可定义的。
当然,高特否定集束论是一种定义也是有代价的,即他的集束论没有具体指明究竟是哪些艺术相关性质组合(即他所说的艺术性质亚系列) 可以让某物成为艺术作品。斯特克曾经批评集束论是一种糟糕的理论工具,因为集束概念包含惊人的模糊性,把“艺术”概念视为集束概念将难以确定是哪一系列的性质及其在何种程度上对某物成为艺术作品而言是充分的或必要的,这意味着最困难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高特列举了十种艺术相关性质,并声明绝非只有这十种,暗示决定某个具体对象是否为艺术作品的乃是这些性质的某种组合。但如果没有详细列举出这种组合的清单(哪怕这种清单只是暂时的,我们仍然可以根据艺术的未来发展进行增补),那么艺术作品身份的具体决定因素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然而,这个性质组合清单是否可以按照艺术史的既成事实相对完备地列举出来,这一点是非常可疑的。说到底,谁敢断言一定是某一种或某几种性质的组合使某对象(如杜尚的《泉》) 成为艺术作品的呢?
维斯在另一个地方对高特乃至丹尼斯·达顿(Denis Dutton) 的集束论提出了与斯特克有些相似的批评。他肯定集束论对艺术界定特征复杂性和多面性的强调,但他担心该理论包含西方偏见,诸如原创性、认知复杂性之类属于西方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以来的标准。他接着说:“但在目前的语境下,最贴切的批评是集束论并没有提供我们所寻找的东西,即一种允许我们通过指明哪些东西可归结到它名下来图绘这个概念的理论阐发。换句话说,集束论对我们识别艺术本身几乎毫无帮助。”他举例说,假如我们面对一个可能是艺术作品的东西时注意到它包含高特清单中的第2、3、4、5、7、9条特征但不包含第1、6、8、10条特征,这将毫无帮助,除非我们确切知道这六种性质的组合就是某物成为艺术作品的充分条件,并且我们知道一些没有争议的艺术实例的确是基于这些性质才成立的。但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当前这一对象的艺术地位,即使我们清楚认识到它包含的那些艺术相关性质,所有类似的实例是否就是艺术作品将仍然是可争议的。因为就算包含同样的性质,在从这个实例到那个实例的过程中,某一性质或某些性质所占据的地位或拥有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由于没有准确说明哪些性质组合在哪种情况下构成了充分条件,集束论是无用的。
高特否认他的艺术集束论是一种艺术定义,但其他艺术集束论者却无所顾忌地称他们的理论为一种艺术定义,比如朱利叶斯·莫拉维西克(Julius Moravcsik) 和达顿等。他们的基本前提是把艺术作品确定为一种包含集束式结构的“自然类型”(naturalkind),再给出集束论的定义。按照正统的克里普克-普特南理论,自然类型必须拥有隐蔽的本质,它是只能由专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艺术缺乏隐蔽的本质,不能成为由专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艺术不是一种自然类型。这同时意味着,艺术是不可定义的,因为某物要想有实质定义而非仅具有名义定义,它就必须是一种自然类型。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些学者提出了一种非正统的自然类型观。按此理论,艺术可能是一种自然类型,也可能有实质定义。比如,戴维斯认为艺术是一种非正统意义上的自然类型,它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本质,却包含一种并非只是纯名义的本质,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某些被广泛分享、受到生物学条件制约的人类能力。集束论艺术定义的前提条件就是假定艺术属于这样一种特殊的自然类型。达顿把他的集束论艺术定义称为“自然主义艺术定义”,他列出一份包含12种性质的清单:直接快感、技艺或精湛技艺、风格、创新或独创性、批评、再现、特殊焦点、表现个性、情感满足、思想挑战、与传统和体制的关联、想象性经验,这些被他称为“识别标准”的性质有时单独出现、更多时候相互结合,这便是某物成为艺术作品的充分条件。但有人批评这种清单式的艺术定义就像塔尔斯基的清单式真理定义,缺乏用来说明清单上的东西为什么在清单上以及如何扩展该清单以容纳新情况的原理,因而欠缺解释能力。因此托马斯·阿达建(Thomas Adajian) 认为,以博伊德等人的“自我平衡式性质-集束类型”(homeostatic property?cluster kinds) 理论为基础构想一种集束论艺术定义或许更为有效。这意味着无论集束式艺术界定方式是否被视为艺术定义,其本身都还存在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四、对以集束论为代表的析取式艺术定义的权衡
包括集束论在内的析取式艺术理论似乎成功达到了对先前理论扬长避短的目的,因而显得更具说服力,但它存在一种根本缺陷,即牺牲了“艺术”概念的统一性。析取式艺术理论实际上假定了“艺术”概念实质上的杂糅性。金在权指出,英语中的“翡翠”(jade) 所指的并不是一种统一的东西,而是“硬玉”(jadeite) 和“软玉”(nephrite) 的混合。高特等人显然认为“现代艺术系统”中的“艺术”与此相似,也是几种异质事物杂糅在一起的结果。析取式艺术理论似乎先把“艺术”概念的混合性视为毫无疑问的事实,然后试图对它加以界定。但问题是,“艺术”真的只是一个混合式概念吗?“艺术”概念的统一性真的不存在吗?仅因为我们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一种或数种令所有人都满意的性质或原理就认为“艺术”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统一性的混合概念,这是否太过仓促和武断?毕竟现代“艺术”概念的开创者夏尔·巴托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追求同一原理难道不是现代“艺术”概念一以贯之的目标吗?难道因为寻找起来太困难和麻烦,我们就应该放弃“艺术”概念的统一性吗?
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 或许是最早涉及析取式艺术定义但对其表示断然拒绝的人,他在1968年出版的《艺术及其对象》一书是从艺术的定义问题入手的。沃尔海姆在开篇就明确表示他不认可采用析取的形式去定义艺术这一思路,因为人们传统上追求的是统一的艺术定义,但“很明显,‘统一一词的使用就是为了表明人们不想要的是任何类似于‘艺术或者是诗(无论诗是什么),或者是绘画(无论一幅画是什么),或者是……这样一种形式的东西”。他认为,统一艺术定义的根据在于各种艺术之间可能存在一个交叉重叠的领域:“在那个可能属于交叉重叠的领域里,我们或许会拥有一个传统式解答的基础,即使后来我们发现无法从这个基础出发继续前进了,理由是超过某一点,不同的艺术仍然包含着难以克服的特殊性。因为这只是表明,传统的要求不能完全得到满足,而并不表明提出这种要求本身就是错误的。”因此与高特等人相反,沃尔海姆虽然意识到追求析取式艺术定义的可能性,却断然否定这一取向,转而肯定对统一艺术定义的传统追求。
实际上,最早的析取式艺术定义是塔塔尔凯维奇在1971年给出的:“艺术是一种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它或者是对事物的再现,或者是对形式的构造,或者是对经验的表现,只要这种再现、构造或表现能够唤起愉快、情感或震惊。”这个定义把历史上出现过的六种基本艺术定义(再现现实说、表现情感说、创造形式说、产生美说、产生审美经验说、产生震惊说) 区分为两个方面的析取项:艺术家意图方面的再现、表现或构形,欣赏者效果方面的唤起愉快、情感或震惊,这可以说是非常简明精妙的析取式艺术定义,但它遭到了奥斯本和卡尼的严厉批评。奥斯本认为,这种析取式概念假定了现行“艺术”概念是几种互不相容之物的混合,此种定义意味着相信现行“艺术共和国”完全是非理性的。他说:“确实有可能,一些不完全一致或不完全兼容的艺术概念会在我们继承而来但尚未完全阐明的传统中留存下来。像塔塔尔凯维奇提出的那种‘析取式定义暗示事实确乎如此。它暗示艺术共和国的结构中存在着相当彻底的非理性,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的认可就相当于对由几个互不相关的标准所辨别出来的事物的异质选择采取相同的态度和行为。”奥斯本的意思是如果析取式艺术定义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面对几种互不相容的选择(几种把某物确定为艺术作品的方式) 时,艺术界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这只能说明艺术界毫无理性。奥斯本说,这还只是第一层次的非理性,进一步审视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个析取项也同样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们(如表现、再现、形式等) 单独说来都不足以把通常被視为艺术作品的东西与非艺术作品区分开来。奥斯本在这里表明的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析取式艺术定义主张者忽视的事实,即他们之所以提出析取式艺术定义,本来是因为像塔塔尔凯维奇所说的六种定义那样的先前的定义全都无法成立,但他们在构建自己的析取式定义时无意中假设这些学说在某个局部是成立的,如某物根据表现而成为艺术作品,另一物根据模仿而成为艺术作品,等等。即使是高特的不是定义的析取式艺术理论,也必须假定某一组性质的组合在某个时刻足以使某物成为艺术作品。但在奥斯本看来,如分析美学早已指出的那样,表现、再现、形式等并不足以把某物确认为艺术作品。如果析取式艺术定义的主张者同意这一点的话,便意味“每个析取项(如表现) 如何将某种的确包含相关性质的东西(如一首乐曲包含情感表现) 构成为艺术作品”这一问题是无法回答的。简言之,奥斯本的意思是我们只能说这是人为决定的。所以他说:“然而,过早地认定我们艺术共和国的结构像这里暗示的那样如此非理性,将是不负责任的标志。在其他一切都失败的情况下,止步于此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极端绝望的行为,因为这会摧毁人们对人类终极理性的信仰。”奥斯本自己最终选择了一种审美式艺术定义,把艺术定义的“区别性标准”归为“审美经验”,即“以自己本身为目的的直接意识或最广意义上的知觉”。
卡尼則根据克里普克和普特南关于有些概念可能没有名义本质但有真实本质的观点,认为“艺术”可能属于这种概念。人们通常指出的那些识别性特征也许都不足以定义艺术,但这并不表明它没有真实本质。他质问塔塔尔凯维奇:“为什么我们不能更深入地观察一下这些类别,看看是否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实际上可以将艺术作品与作为非艺术作品的人工制品区分开来呢?”卡尼认为,奥斯本所说的“审美经验”也许就是这种共同特征。如果我们并不认为艺术就是所有人称之为“艺术”的任何东西,并且“如果克里普克-普特南模型适用于‘艺术作品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是可以回答的,尽管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回答”。因此,他显然认为“后撤”到析取式定义上去的做法是错误的。
如果认为奥斯本和卡尼等人的观点很有说服力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析取式艺术理论也不过是理解“艺术”概念的诸种范式之一,而非其终极形态,寻找统一的合取式艺术定义仍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西方艺术哲学的最新趋势是反析取式定义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虽然析取式定义取向并非艺术定义问题的唯一正确思路,但当下分析美学的天平似乎正朝着有利于它的方向倾斜。或许没有其他分析美学家能像戴维斯那样执着于探讨艺术定义问题,其《艺术的定义》一书至今都是分析美学关于艺术定义问题的重要著作。他坚决主张艺术是一个准自然类型,因而具有真实本质,并且花费大量精力试图找出这个本质。但是,戴维斯最终给出的仍然只是一个析取式艺术定义:
某物是艺术:(a) 如果它在实现有意义的审美目标过程中展示出了技能和成就方面的卓越性,并且或者这样做是它基本的、身份认证的功能,或者这样做对实现它基本的、身份认证的功能做出了关键性贡献;或者(b) 如果它属于在某个艺术传统中已经建立起来并得到了公开认可的艺术门类或艺术形式;或者(c) 如果其制作者或提交者具有将其作为艺术来看待的意图,并且其制作者或提交者采取了必要和适当的措施去实现该意图。
这个定义中的很多“或者”已经明确显示出其析取式特征,戴维斯自己也承认“该定义是析取式的”。这似乎表明只要大体上认可如今西方世界通行的“艺术”概念,析取式定义便有其合理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艺术”概念可能确实如高特所相信的那样在根本上就是不统一或混合的。无论奥斯本和卡尼等人如何坚持“艺术”概念可能的统一性,事实似乎更偏向非统一性。且不说“艺术”概念本身,甚至“文学”“绘画”之类的所谓“艺术亚概念”都有确凿的事实表明它们似乎是不统一的。埃利斯说服力强且对文学理论影响深远的“杂草”隐喻的一个基本层面即表明“文学”概念的混杂性。至于“绘画”概念(此处指的是作为艺术类型的绘画,而非单纯的绘画行为,后者的确是普遍的),塔塔尔凯维奇指出:“如果说确定艺术是什么很困难,那么更难的是确定单一的艺术是什么在巴洛克时代,戏剧表演、凯旋门的建造、多洛里斯城堡、烟花,甚至园艺都被视为是绘画。”如果“艺术”及其主要亚概念都是异质成分的混合物,那么析取式定义就是最合适的选择之一,戴维斯的艺术定义不得不采用析取方式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虽然包括高特集束论在内的析取式艺术定义存在诸多缺陷,但如果我们相信“艺术”概念事实上就是杂糅性的,同时又不认可过于极端的艺术不可定义论,那么析取式艺术定义就是目前的优先选择。
① Hilary Putnam,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2.
②⑤⑥⑧⑨⑩Berys Gaut,“‘Artas a Cluster Concept”, in Noёl Carroll (ed.),Theories of Art Today,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0, p. 27, p. 26, p. 27, p. 28, p. 28, p. 31, p. 33, p. 34, p. 41.
③ 斯蒂芬·戴维斯说,高特没有承认其他版本的集束论。戴维斯提到E. J. 邦德、米尔顿·H. 斯诺伊恩波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发现”。他引用了埃伦·迪萨纳亚克在1988年发表的一段与高特观点非常类似的话,还提及了理查德·L. 安德森、H. 基因·布洛克尔和丹尼斯·达顿(see Stephen Davies,PhilosophicalPerspectives on A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0)。但他似乎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即这些人并未明确使用“集束”这个概念来讨论艺术,他们的观点或许都属于析取式艺术观,但并非都是集束论艺术观,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高特是艺术集束论极具权威性的代表人物。
④⑦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第37页。Cited in Berys Gaut,“‘Artas a Cluster Concept”,Theories of Art Today, pp. 33-34.
Stephen Davies,The Philosophy of Ar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pp. 33-34.
Robert Stecker,Artworks: Definition, Meaning, Valu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p. 25.
Stephen Davies,The Artful Species: Aesthetics, Art, and 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8.Stephen Davies and Ananta C. Sukla (eds.),Art and Essence, Westport: Praeger, 2003, pp. 3-7.
Denis Dutton,“A Naturalist Definition of Art”,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64, No. 3 (Summer2006): 367-377.
Thomas Adajian,“Defining Art”, in Anna Christina Ribeiro (ed.),The Continuum Companion to Aesthetic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12, pp. 49-51.
Richard Wollheim,Art and its Obj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 p. 2.
该定义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对“艺术”的定义和对“艺术作品”的定义,其中对“艺术作品”的定义是“一件艺术作品或者是事物的再现,或者是形式的构造,或者是经验的表现,从而有能力唤起愉快、情感或震惊”。See W?adys?aw Tatarkiewicz,“What is Art? The Problem of Definition Today”,Th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 11, No. 2 (Spring 1971): 150.
See T. J. Diffey,“The Republic of Art”,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 9, No, 2 (1969): 145-156.Harold Osborne,“What Is a Work of Art?”,Th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 21, Issue 1 (Winter 1981):9, 10, 10.
比如金子具有黄色、延展性、发光金属等表面特征,但这些都不足以将其和黄铁矿等物区别开来,所以它缺乏名义本质,但有真实本质,即金子是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See James D. Carney,“What Is a Workof Art?”,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ol. 16, No. 3 (Autumn 1982): 87.
James D. Carney,“What Is a Work of Art?”,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ol. 16, No. 3 (Autumn 1982):90, 91.Stephen Davies,“Defining Art and Artworlds”,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73, No. 4 (Fall2015): 377-378, 378.John M. Ellis,The The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A Logical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 39.
W?adys?aw Tatarkiewicz,A History of Six Ideas: An Essay in Aesthetics, The Hague, Boston and London: MartinusNijhoff, 1980, pp. 70-71.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