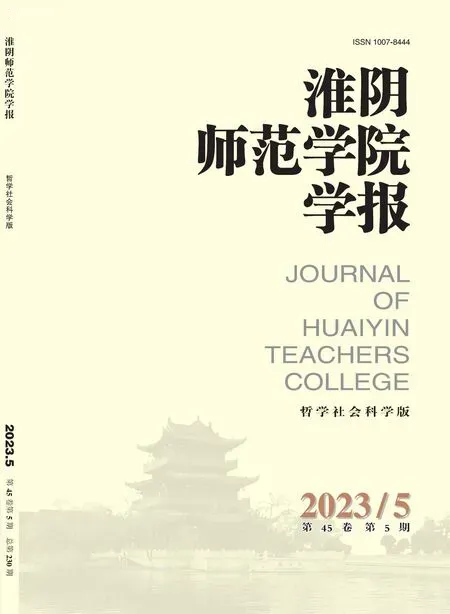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确立
——纪念中共三大召开100周年
2024-01-09汪浩
汪 浩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中共一大上,与会代表对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中共二大虽然作出了国共外部合作的决议,但与列宁的相关思想有较大差距,这导致西湖会议到中共三大确立统一战线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一、中共三大的主题: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1923年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张国焘、谭平山、刘仁静、罗章龙、何孟雄、向警予、阮啸仙、陈潭秋、徐梅坤、冯菊坡、林育南、于树德、邓培、项英、刘尔崧等30多人[1]23,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出席会议人数一说40人,依据联共(布)档案,陈独秀会上选举时得票40[2]303。这个会议是中共二大后不到一个月,即根据1922年8月29—30日召开的西湖会议关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精神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国共内部合作统一战线的确立。这个“确立”是三个相关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三个相关方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就“结果”言,又有三方面的必然依据:一是革命大势,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革命大势风起云涌。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如饥似渴地吮汲俄国革命的经验。二是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以下简称《提纲初稿》)事实上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策略,适应了中国革命大势的需要。三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陷入陈炯明叛变后的困境,急于重新组织革命力量,再求奋起。这三个必然性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契机推向历史前台。
(一)统一战线源于列宁一个崭新的思想
《提纲初稿》是列宁1920年6月为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文件,是共产国际第一个关于民族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列宁在1920年7—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国家革命理论,即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由于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这个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因此这是列宁的一个开创性思想,列宁自谦为“提纲初稿”。列宁指出,“一战”和十月革命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3]97。列宁的这一思想在这次大会上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和贯彻。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革命目的的正确道路。”[3]97《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此指出:“在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如分配土地等。”[3]97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中,因突然碰上这个新问题而激起了许多波澜。
(二)马林对推进国共合作的努力
1.统一战线是个舶来品,首创者是荷兰人马林(菲利浦)。统一战线在国际共运史上被称为斯内夫利特战略,是以马林在出生地使用的名字亨德立·斯内夫利特命名的,所以统一战线战略“亦即马林战略”[4]368,是以马林在东印度(今印尼)爪哇领导殖民地的民主革命的经验为依据的。他后来回忆说:“我提出这些意见时……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由此就能理解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了。”[4]368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前夕,马林受到列宁接见,列宁与他和印度人鲁易(罗易)讨论民族与殖民地国家革命的问题,马林汇报了他在爪哇的经验,因而受到列宁的重视。
2.马林的建议再度受阻于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马林提出国共合作的建议受到会议组织者张国焘与李汉俊、李达的强烈反对。马林没有出席一大最后一天在南湖的会议,但他继续留在中国,为推动国共合作努力,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一大后即派包惠僧拜访陈独秀,望其尽快来沪履职,意在让陈独秀改变一大上他的国共合作建议被否决的被动局面。但陈独秀来沪后,马林在翻译张太雷的陪同下,拜会陈独秀谈国共合作,没想到急性子的陈独秀遇到一样急性子的马林,两座火山碰在一起便爆发了[4]316。不久后陈独秀等人被捕,在张太雷的斡旋下,马林花500大洋使陈等脱险,陈、马的关系得以缓和[4]318。二是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南下两广调查研究,主要是在国民党桂林大本营住了9天,与孙中山频繁接触,劝说孙中山改造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从反对到接受上述建议,还在马林提议下组团赴莫斯科考察,同列宁会晤。在列宁的倡导下,孙中山表示,他“虽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一致的地方”[4]331。马林知道,接下来就是如何让陈独秀接受国共合作的建议了,他意识到只能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于是他开始给共产国际起草报告,于1922年4月24日起程返回莫斯科,并于7月17日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称他在上海“没有见到他所熟悉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对革命完全漠不关心”。[2]296这是一份不符合实际的报告,后来产生了负面影响。1922年8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作出支持马林意见的决议,紧接着马林再次来华,并迅速采取非常举措,召开特别会议。
(三)马林果断决定召开西湖会议,为中共三大准备了主题
马林成功借得“尚方宝剑”[4]331,即共产国际维经斯基(也译作维金斯基)给陈独秀的指示信。这是因为1922年3月22日马林从北京到上海后,他与陈独秀的“分歧达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地步”[4]329。陈独秀也意识到马林不好对付,遂主动给跟自己有较融洽关系又能跟共产国际领导人说上话的维经斯基去信,意在纾困,改变他的处境。马林也洞悉了这一点,只有借助共产国际的组织手段,否则不足以说服陈独秀接受国共合作。马林回莫斯科后首先与维经斯基会晤,争得了维经斯基的完全支持,二人又一同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做了汇报。7月18日,执委会作出决定,支持马林的意见。于是马林带着具有“尚方宝剑”般威力的衬衫(衬衫上打印着维经斯基致陈独秀指示信的秘密文件)返回中国。1922年7月27日,“苏俄政府派出外交代表越飞,共产国际派出马林与他一起来华”[4]318。马林一到上海便会见陈独秀,并取出那件特殊的衬衫,衬衫上是几行英文(译文):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此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移到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菲利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5]
陈独秀看罢,“久久沉默着”,除了沉默,他还能怎样呢?此前,刚刚结束的中共二大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组织领导,是组织原则。他已经无话可说了,他反对同国民党合作的意见,已经被共产国际否决了!
马林看了二大的文献后,果断决定召开西湖会议。出席西湖会议的中央委员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等五人,马林与张太雷也出席了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会上他还是受到了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强烈反对。“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了一个调和的立场”[4]331,他同情陈、张的意见,“称许陈独秀提出的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4]333。他认为国共外部合作不易实现,采取内部合作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易于通行的办法”[4]334。会议最终采纳了李大钊的建议,同时决定由李大钊代表中共赴沪与孙中山会面,商定国共合作大计。
二、中共三大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确立
(一)“党的二大——西湖会议——党的三大”,统一战线确立的曲折过程
陈独秀并没有出席一大,但他支持一大的宣言与决议。一大后,陈公博与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商量,抄一份文件送新当选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陈公博也自备了一份,后转带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这就是中共一大孤本文献的由来[4]314。马林派包惠僧到广州劝陈独秀来上海履职,但两人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关于中共是否应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认为,中共处于幼年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不久陈独秀等人被捕,在张太雷、马林的帮助下得以保释,陈、马的关系有了缓和。后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南下两广,继续为国共合作努力。
从反对到接受国共合作,陈独秀的主动进击与无奈退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给维经斯基去信。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书记,陈以为他能向共产国际转达他反对与国民党合作的意见。其二是中共二大上,他主动作出让步,接受马林的建议,加入共产国际,中共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不再坚持中共一大的立场。陈独秀的主动示弱是以退为进,想换取马林的让步,即放弃国共合作、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其三是西湖会议上陈独秀作了反对马林建议的最后努力。在张国焘、蔡和森作反对马林建议的发言后,作为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4]333,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就不承认它的资产阶级基本性质”,“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表现出服从组织原则但又“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那并不放弃原有立场软中带硬的姿态。当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后,陈独秀则表示“只能有条件地服从”,“只有孙先生取消宣誓服从他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4]333
陈独秀与刘仁静等出席共产国际四大,陈独秀让刘仁静在会上发言,表示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决定实行国共合作”,“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实行统一战线了,其形式是我们的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是中共第一次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公布于世”[4]334。陈独秀在党的三大上,服从多于反对,一定程度上附和反对者的意见,表现出西湖会议到三大后那种无奈退守政治态度的主基调。
(二)中共三大的胜利召开
西湖会议名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其实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只有5人,“即便在中央委员之中,也有几位只是服从共产国际领导这一点而认可国共合作,在思想上并未弄通”,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张“把讨论国共合作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题”。[4]337
三大上,陈独秀作了工作报告,传达了西湖会议精神。他说,“起初,大多数人反对加入国民党……共产国际的代表说服了参会者……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改变……”他在报告中总结和承认了中央委员会工作中的错误,批评了有些同志反对加入国民党,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他自我批评说,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他批评了党内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该退党。他还点名批评了中央委员张国焘,说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他也批评了一些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和广州,唯独表扬了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的工作。[4]338-339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的现状……中国现有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强调“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决定。[4]339他的报告反映了他被动接受共产国际决定的心态,也反映了他照搬马林过高估计国民党、贬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倾向,为他此后的错误倾向埋下了种子。
党的三大没有完全改变党内一些同志的抵制态度,批评一些同志因反对国共合作而脱党但未能挽救这些对中共创建有功的同志,致使三大后,虽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等多人加入国民党,以示带头,但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人数并不多。
其后,在大革命过程中,陈独秀的思想经历了波动历程:他从起初的反对到被动接受,后又有进步,从“自觉地接受到努力地执行”。他在这期间,发表了多篇写国共两党合作的文章,反映了他从反对加入国民党到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3]108的过程。贯彻马林的主张他是努力了,但他又陷入了不提和不争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错误中。再后来,他又一度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的错误主张。大革命失败后,他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不接受党内的批评和教育,把一切责任推向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甚至受托洛斯基思潮的影响和裹挟,组织反对派,误入歧途。但他晚年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坚决不接受国民党的施舍,守住了共产党人的气节。他与马林、杨明斋、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茅盾等中共早期创始人,或因反对国共合作或因所谓托派的影响,陷入人生的悲剧,这是中共党史上令人悲怆又发人深思的公案。
马林、陈独秀阐述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他们依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相关指示精神提出,“中国现时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民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应成为国民革命中心势力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都很幼弱,全体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3]108马、陈的这些意见,当然有列宁思想的影子,但也有违背列宁思想的东西。比如,过高地估计国民党,过低估计中国共产党[2]304,特别是只字不提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有违列宁精神。共产国际二大的《补充提纲》明确指出:“殖民地革命的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会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向达到最终革命目的的正确道路。”[3]97这句话中暗含着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共产主义先锋队应争取革命领导权,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积累经验,教育民众最终走上正确道路。马林和陈独秀都没有阐明暗含其中的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担当精神。
张国焘、蔡和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应有自己独立性的主张。他们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但中国共产党还有自己的特殊任务,那就是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项任务,应同时进行”。他们反对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代表们在讨论中批评张国焘等人怀疑同国民党合作的‘左’的观点。也不同意由马林提出得到陈独秀等人赞同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2]304。以陈独秀和张国焘为代表的“争论双方都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存在片面性,相比较而言,陈独秀等人造成与国民党合作的意见,更符合国民革命的中心任务”[3]109,因为这代表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李大钊难能可贵地提出了领导权问题,“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毛泽东也说:“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6]
中共三大达成共识,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使全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3]109
(三)国共合作的达成与大革命高潮的掀起
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的“指示”因迟到而引发领导权问题的大讨论,成为三大的一场余波。三大结束不到一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信》“才传到中国”,强调“领导权问题当归于工人阶级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指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而且“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它把“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何认识资产阶级和农民,如何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等诸多新课题,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中国共产党历史》评论说:“这个指示,对于克服三大的不足,对于共产党人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3]110
这个“指示”的重大性,特别是关于农民与土地革命问题,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实践所验证。然而1925年,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都没有认识到它的重大性。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六大时“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7]。在党内引发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关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争论尤为激烈。争论中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等人都公开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中共三大一次会议达成共识,尽管多数党员对“领导权”问题“缺乏认识”,但通过对国民党相对集中于中国南方,中国北方许多省市还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实际这种不平衡性的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的组织可依据具体情况做到“尽可能团结国民党中的革命派,是有可能‘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的,后来也是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3]113。
陈炯明叛变成为国共合作的契机。中共三大后,国共合作并没有很快形成好的态势,原因在于国共双方都没有做好合作的准备,一是孙中山还没有认识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二是共产党还在热烈讨论“领导权”问题,还没有形成共识或者还没有来得及把共识付诸实践,再加上党内一部分同志因反对国共合作而脱党造成了不良影响,致使不少人在观望。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发生了两件事,成为国共合作的推动力。一是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陷入困境的孙中山认识到依靠旧军阀的革命前途渺茫,他在困惑中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决心改造国民党走国共合作的道路。二是国共合作在旅法青年学生中发展迅速,打破了国共合作进展迟缓的局面。
关于共产国际对三大指示的讨论,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共合作的认识,并转化为行动。马林对国共认识的片面性,陈独秀对国共合作由反对转而被动接受的消极态度和对工人运动的冷漠,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绊脚石,“各地共产党人,如北京的李大钊,直隶的韩麟符、于方舟,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夏曦,湖北的刘伯垂、廖乾五,山东的王尽美,浙江的宣中华,山西的王振翼等,都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3]142,推动国共合作。从这方面说,不能不提旅欧支部及其领导人周恩来。
周恩来是国共合作的开路先锋。中共三大期间,孙中山派王京岐赴欧洲组建国民党旅欧支部。1923年3月1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举行青年大会。经周恩来与王京岐多次磋商,6月16日周恩来等三人到里昂与王京岐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80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由于共青团员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的成员扩展到比利时、德国。11月25日,在里昂召开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郭隆贞为妇女委员会主任。这个支部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3]114。《周恩来传》比较详实地描述了周恩来与王京岐促成国共合作的过程,还特别介绍了周恩来在王京岐(回国途中病逝)回国前,委托周恩来为国民党旅欧支部代理执行部部长。期间,周恩来领导了国共旅法支部中的共产主义者同旅法勤工俭学生中以曾琦、李璜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代替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批判其“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的错误观念与破坏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理论和行径。更重要的是,周恩来还针对党内部分同志对国共合作存在疑虑,失去信念、失去独立性,“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等问题发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共产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关系,“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党史专家金冲及说,年轻的周恩来在中共创建初期,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8]
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旅欧中国共产党人的异军突起,对国内国共合作是个很大的推动,周恩来因此受到国共两党的重视。1924年7月,周恩来奉调回国,不久成为领导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和中共党内军事工作的职业革命家。
三、中共三大的历史地位及对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相关方贡献的评价
(一)中共三大的历史功绩
1.中共三大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使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确立,是中共三大的主题。从基本面说,中共三大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使命,它的现实价值和历史影响都是很大的。从中国革命现实说,国共合作促成了中国革命史上两大政治势力,即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迅猛发展,几乎在两三年间便造就了中国革命前所未有的大势;北伐战争一两年内,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从历史影响说,不论是它的历史功绩还是严重缺失都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影响。从功绩说,统一战线成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之一,其影响直至今天,以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从缺失说,它使中国共产党在巧争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过程中变得成熟起来。这为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此后复杂多变局面,装备了一个制胜法宝。总之,统一战线重大战略的确立,能够在孙中山这个比较有号召力的旗帜下,通过国共合作,加速推进国民革命的进程,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是“党的三大重大的历史功绩”[3]109。
2.党的组织在日益壮大之中。中共从“二大——西湖会议——三大”,经历了曲折,尽管其“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并没有完全肃清,有的还严重地存在着,但党的主导方面一直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党员总数从一大的58人,到二大的195人,再到三大的420人,并在奉天(今沈阳)、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州、浙江、山东、满洲等地建立了党的组织,在此后领导工人和农民运动中发挥了作用、扩大了影响。
3.党坚持自我革命的精神。在组织内部展开不同倾向思想和认识的交锋,通过批评、自我批评,虽然在广泛性和彻底性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但终究实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转变”,从这时起,“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1]24,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从书斋学问迈向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伟大的转变。
(二)关于中共三大缺失问题的考察
1.关于党的三大。党的三大既有伟大功绩,又有严重缺失。它的功绩在于坚持了列宁开创的新思想,关于落后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战略思想,结合中国实际,确立了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开创了新局面。但是它的成功与失败是相伴而生的,成功于统一战线的形成与贯彻,而缺失也在于统一战线形成和贯彻过程中存在的对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原则的背离。这个背离主要集中于对统一战线中领导权问题存在右的错误倾向,与此相联系,又存在着对农民和土地问题、工人运动和革命武装问题的“注意不够”[1]28,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妥协性缺乏认识,更疏于防范,为大革命大好形势的断送留下祸根。
2.关于国共合作相关方及其领袖人物相关缺失的考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是三个主要相关方,都各有功绩与缺失。
(1)关于马林。《红色的起点》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统战鼻祖”,“是提出国共合作重大战略第一人”,是“首创者”。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建立‘统一战线’这一重大政策”,可以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他的这个估计在后来成为现实。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可以说马林“立下两大功劳”,第一,“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马林出了大力”,“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了很大作用”;第二,制定国共合作方针使当时幼小的中国共产党借助与国民党合作迅速得以壮大[4]341。党史界有人提出马林是统一战线的大专家,可他指导中国共产党确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推动大革命,为什么会遭遇挫折?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当时的情况与他熟悉的东印度(印尼)不同。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军阀势力要比东印度殖民总督统治势力强大得多、复杂得多,中共又遭遇蒋介石这个奸诈狡猾的对手。再加上孙中山的早逝,国民党左派势力迅速削弱,以及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估计不足,因而他遭遇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后来又因列宁早逝,俄共内部斗争复杂化,马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又被鲍罗廷取代,这些重大因素影响了他的注意力,也制约了他的指导权力,1923年秋他被降职,1924年他辞职回了荷兰。1925年,罗章龙在荷兰出席国际会议时遇到马林,罗在马家住了一个星期,马林向罗倾诉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和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唯有通过工人运动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通向民主的道路可谓徒劳。”[9]1927年中共处于困难之中,马林曾对罗章龙说“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当正视错误,努力前进,历史车轮自会循正当轨道前进。”[4]369马林后来参加了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争,1942年4月在给女儿留下壮烈的永别信后倒在了法西斯的枪口之下,至死信念不改,是一位值得中国共产党人纪念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2)关于孙中山。有人说:“国共第一次合作,既得力于孙中山又缺失于孙中山。”这种说法不能说全无道理。孙中山无疑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理想的领袖,他经马林的艰辛说服,从反对转为赞同合作,他重新阐释三民主义,事实上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带有纲领性的指导方针,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他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贯彻国共合作改造国民党的举措比较得力。与国际代表合作也较恰当,他对国民革命大势的形成功不可没。他的缺失在于:他对旧军阀抱有幻想,带有资产阶级革命家妥协性的烙印,正如邓中夏所说的,不能将革命“贯彻到底”[2]309。他的北京之行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对国民党也表现出妥协性,对左派廖仲恺、邓演达的使用、保护不到位,而对汪精卫、蒋介石等善于伪装的所谓新右派缺乏鉴别,轻率地将党权、军权拱手相送,给大革命留下致命的隐患。
(3)关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国共合作主要推动方和决策方,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总体上说功大于过。从“得”方面说,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国共合作起码在当时难以成为现实;从“失”方面说,共产国际过分相信派出代表个人,组织的力量、民主的力量相对薄弱。从代表个人而言,马林过于自信武断,高估国民党、低估共产党,脱离了实际。鲍罗廷及其后几位代表容忍国民党尤其是容忍蒋介石多,听取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正确意见少。
促成国共合作的三个相关方的缺失和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主导诱因,令人扼腕痛惜。但不论是“得”还是“失”,都与马林战略直接相关。马林战略的输入导致的强烈抵制让中国革命变得更加复杂,但它也让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和壮大,最终让中华民族迅速站起来并继而奇迹般地富起来、强起来。
结语
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这一重大战略确立是个历史大事件,它带来的辉煌与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人以良多的帮助和经验教训,其中最深刻、最关键的一条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其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也在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合作中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