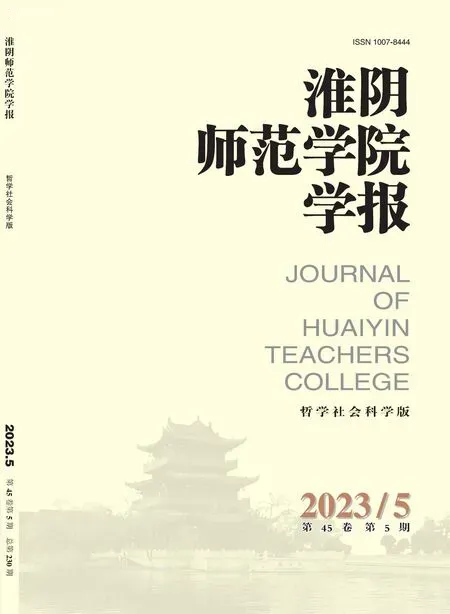创造性阐释中国史学的优良遗产
——陈其泰教授著《历史学新视野》读后
2024-01-09黄学友
张 峰, 黄学友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在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史学最为发达。法国学者弗朗斯瓦·魁奈曾中肯地指出:“关于历史学,这是中国人一直以其无与匹伦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门学问。没有什么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自己的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存自己的历史典籍。”[1]可以说,与西方史学相比,中国历史记载世代相续,未曾中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非凡成就。过去,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史学名著的文献价值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对于中国史学长期连续发展的优良传统进行了总结。但是,我们对于历代优秀史学名著的探讨不应止步于此,还应看到有些史著的价值超越了时代,对后世的历史书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2]以此作为指导思想,陈其泰教授近著《历史学新视野——展现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商务印书馆2017年11月出版,以下简称《历史学新视野》)一书,冀图站在当今时代高度对史学名著的魅力作现代审视,拿出具有深度研究价值的创新成果向外传播,从而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供有益借鉴和智库支持。作者在该书《前言》中说:“琳琅满目的史学典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文化遗产。尤其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历代流传下来的史学名著,它们的成就或是在客观史实记载上,或是在编纂体裁体例创新上,或是在历史学的理论思维上,为我们提供了民族文化创造力的生动例证……今天,我们把其中超越时空、具有永久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精华进行认真总结和大力发扬,就能为推进当今史学的发展、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文化创造力提供宝贵的思想营养。”[3]1-2正是秉持这一学术理念,作者对中国史学的优良遗产进行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阐释。
一、对史学优良遗产作贯通性研究
陈其泰教授认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宛如一条浑浩流转的长河,中间有岸阔流畅的河段,有渟蓄汇聚的湖泊,也有狭谷险滩,甚至出现回流曲折。如果仅仅截取其中一段孤立地作考察,显然难以恰当地把握其演进的特点。放在全局之中上下联系起来分析,才能明了其前因后果,对其价值和意义作出正确评价。”[4]职是之故,在《历史学新视野》中,作者对历代史学名著的研究,并不囿于史著本身,而是自觉地运用贯通研究法,将史学名著置于学术演进的总趋势中予以考察,进而探究其底蕴,提出真知灼见,犹如作者所言:“贯穿于整个40余万字书稿的学术旨趣实际就是:贯通上下的研究。”[3]439
在《历史学新视野》中,作者以史学名著为关键点,运用通识的眼光,试图建构一种传统文化走向近现代的研究模式。这一著述特点,在该书篇章的设置与布局上有着充分的体现。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凡12章,40余万字。上编“传统史学与民族文化创造力”下设“《国语》的史学价值”“司马迁著史的杰出创造力”“《汉书》:继《史记》而起的巨著”“《史通》: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章学诚的学术创造精神”等篇章;下编“时代新课题与学术新探索”涵括“晚清今文公羊学盛行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时代剧变与学术的新探索”“梁启超:近代学术文化的奠基者”“萧一山与清史研究”“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珍贵的思想遗产”等子目。作者探讨的范围贯通古今,上起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经典《国语》《史记》,下至近代新史学思潮、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者在篇章结构设置上的深层意蕴还在于,他以文化从古代走向近现代的研究视角将全书12章内容贯穿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有机的整体”在外部形态上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传统史学的出色成就和精华,二是传统史学如何向近代史学嬗变,三是近代史学如何由“三大干流”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主导地位。本书想要向读者呈现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如何创造辉煌,如何经过嬗变向近代发展,再到当代出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局面。
从微观层面来看,作者对每一部史学经典的论述,都自觉地做到上下贯通,如论《汉书》,认为它承上启下,“一方面,是继承了司马迁《史记》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是“断代为史”,影响了后世《三国志》《后汉书》直至《明史》的编纂,解决了“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的难题。[3]137-138论《史通》则先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谈起,继而论述唐初史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存在的不足,然后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作者提出刘知几编纂《史通》,是要对前代史学的成就与得失“从史学评论角度,进行一番总结”[3]193。此外,作者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贯通考察,并按其演进特点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划分为创建、壮大、发展和繁荣四个阶段。可贵的是,作者并不认可学术界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为“战时史学”的说法,认为这种认识割断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上半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在联系。作者以长时段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民国时期向新中国时期的演变,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翦伯赞撰著了《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著成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范文澜相继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和《中国近代史》(上册)等代表性论著,进而通过对这些史著内容的深入分析,认为此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五老’,都已做出重要的建树”,这是他们能够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学术话语权的内在基础与重要条件,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术界居于领导的地位,这种情况绝不是靠行政力量扶持而形成的”[3]404。这一观点是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内在逻辑演进的分析得出的宝贵认识,结论自然值得我们珍视。
《历史学新视野》一书的贯通性特点,还表现在作者重视将史学名著与文化传统、学术潮流、社会条件和时代变迁相互联系作整体性考察。譬如,作者对《史记》《汉书》这两部史学名著的探讨,不仅将其成就归功于司马迁、班固的杰出创造才能,而且还从汉代作为统一王朝、国力强盛、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学术指导思想等层面作出考察。这种对《史记》《汉书》的解读模式,实际上跳出了就史著论史著的窠臼,故而能够提出许多具有创新价值的新论题。
作者对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的研讨,亦不再简单地将其视为一部史学评论名著,而是更加重视发掘“它作为18世纪中国学者哲学探索的重要著作的价值”。作者从“《文史通义》的命名”“《文史通义》的篇目内容”和“章学诚的夫子自道”三个维度对《文史通义》的著述旨趣作出考察,指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大大超出了史学评论的范围,证明他要探讨的是自六艺以来讫于当代学术的指导思想及其演变,探讨二千多年来不同著作家学术根本观念的得失”[3]248。沿着这一思路,作者对章学诚以“史义”为指导品评历代史著编纂得失、提出历史编纂改革的新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尤其是,作者打破经史子集的畛域,从学术史的视角重新探讨了章学诚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论证了“道出自然”“道在事中”等哲学命题的重大意义与学术价值。如果仅从史学角度去理解《文史通义》,就易陷入局部而难窥其学术全貌,唯有采用整体性考察的视角,才能对其学术思想的本旨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阐发。
又如,下编《晚清今文公羊学盛行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一章,更是体现了作者贯通古今、打通经史的著述宗旨。从纵向上看,作者首先勾勒了公羊学说在先秦、两汉时期的产生与发展,继而重点探讨了公羊学说在清代经历了“重新提起—张大旗帜—改造发展—达于极盛”的发展历程,最后论及公羊学说对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蔡元培和陈垣等人的影响,以至在晚清时期形成了“爱国志士—喜谈公羊—服膺西方进化论”三位一体的现象。从横向上看,作者超越了从经学或史学的单一视角研究公羊学说的局限,做到打通经史,同时将公羊学说的发展与时代思潮、晚清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这是把晚清今文公羊学说的研究放在了历史发展的纵横坐标中予以考量,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其他,如对《射鹰楼诗话》《日本国志》《国闻报》等著作和期刊的解读,无不重视结合时代思潮与学术走向观照史学名著的编纂特点,凸显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
总体来看,作者在《历史学新视野》一书中运用贯通的、整体的眼光对史学名著作出的考察,弥补了以往我们研究史学史的不足,对于突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瓶颈、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创造性阐释史学名著的独特魅力
《历史学新视野》一书之“新”,还在于作者独辟蹊径,从“史学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视角对中国古代史学名著如何做到多方位反映客观历史,作出了创造性阐释,读之使人启发良多。
(一)发掘新的学术增长点,对优良史学遗产的精华作出新探索
作者重视对中国史学优良遗产作贯通研究,进而能够从中发现一些以往研究重视不够的闪光点。以下略举几例,以管窥作者论史眼光之敏锐、学术见解之独到。
《国语》作为一部古典名著,所载史事屡被学者引用,但“长期以来却被边缘化对待”,于是作者重新审视《国语》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首先,从编纂思想上指出《国语》记载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宗周及列国的成败盛衰教训,继承了《尚书》开创的“殷鉴”传统。其次,总结了《国语》在历史编纂上具有“‘记言’与‘记事’紧密结合”,“恰当运用对比手法”,“多方位、多层面展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生动性”和“提供了‘纪事本末法’叙事的成功范式”四项突出成就。作者将《国语》及其后史学的发展相互联系考察,指出《国语》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表现在,《国语》为西汉史学之高峰突起准备了条件,贾谊的出色史论,司马迁的杰构《史记》,都直接继承了《国语》的成就;《国语》创设的“记言”为主的体例和高度成就,直接影响了《史记》《汉书》及其他史书中有意识地将名君贤臣、卓识之士的有价值论议,大量采入史著之中;因《国语》分国记载体裁的影响产生了一批史著,计有《战国策》、孔衍《春秋后语》、司马彪《九州春秋》等书;《国语》叙事之技巧、文采之华茂,成为后世许多史家揣摩效法的对象。根据以上史实分析,作者自然得出了《国语》在中国史学上的历史地位,认为它“不是编纂《左传》剩余的材料抄辑而成,也不是依附《左传》之书,以前有过的‘春秋内外传’之说并不符合实际,它是一部有独立思想价值和编纂特色的史学名著”[3]22。作者又站在时代的高度,总结《国语》记载了国家治乱盛衰的经验教训,分析局势、预言成败,叙述典章礼法、保存民族记忆,表彰优良品德、要求提高人们思想修养的谠言高论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以及《国语》对“和而不同”哲学思想的深刻阐发,说明产生于战国初期的《国语》“为提高我们的民族智慧和发扬优良的文化传统,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3]42。作者从“史学传承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新视野重新“发现”了《国语》这部史学名著,揭示了它长期以来被掩盖的思想价值、编纂成就、历史智慧和独特魅力,所论多发前人未发之覆。
作者同样以新颖的视角,精辟地论述了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将乾嘉学术等同于考证学,是学术界长期流行的一种观念。作者别出心裁,重新思考乾嘉时期学术的发展,认为应当超越单纯学术考证的尺度,深入分析和正确评价乾嘉学者在“义理”层面的成就。对此,作者通过对乾嘉学人论著的研读和治学倾向的审视,强调:“乾嘉学者中确有一些特识之士,能够超出广搜材料、严密考订的‘朴学’范围,对一些问题进行具有理论意义的探讨,做出很有时代特色、足以发人深省的回答。举其最为显著者,如戴震,不但擅长于精密考证,而且精心撰写哲学著作,勇敢地打破‘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枷锁;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在其考证学著作中揭示出‘追求历史真实性’的价值取向,对于流毒极深的滥用褒贬手法痛加抨击,并且表达出对经国养民问题的关怀;如章学诚,他逆于时趋,抨击考证学末流以‘补苴襞绩’为能事造成的严重流弊,倡导‘学术经世’,并且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大力探求作为人类社会演进客观趋势的‘道’。”[3]216进而,作者围绕戴震对理学家否定情欲说的批判、考史三大家在义理层面的建树,展开论述,新见迭出,向读者呈现了乾嘉学术中长期被学界忽视的面相。
再者,以往我们对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家治史特征的研究,多重视他们“实证考察”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们“贯通认识”的研究风格。作者举出王国维对卜辞中先公先王的考证、陈寅恪对唐与周围各民族广阔范围的考察、陈垣由大量校勘实例上升到“校勘四法”理论的总结、傅斯年运用“民族—文化”观念对《诗经》中“大东”“小东”问题和殷周之际民族间互动关系的探讨,说明新历史考证学家治史范围各不相同,学术旨趣和方法也各有特色,但是在他们身上,都出色地做到了“实证考察与贯通认识”二者相结合。作者以发展的眼光,指出这种“实证考察与贯通认识”相结合的治史风格,在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考证学家的治史实践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譬如蒙文通、谭其骧、唐长孺、赵光贤等学者都成功地做到了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考证研究,从而开辟了历史考证学研究的新境界。
(二)从才、学、识、德的标准评析史家的历史编纂成就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以史家之史著为基础,由此引申出史学上的其他问题。然对历代史著进行研究时,不少学者认为史家采用何种体裁记载史事、对于史书内部结构如何编排等方面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故而未能深入总结这些史学名著的精华。作者一改过去视历史编纂为技术层面问题的偏颇看法,倡导“历史编纂是史家才、学、识、德之重要载体”,其间“包含着进步的史识,渊博的学识,高明的治史方法,合理、严密的编纂方法,这些具有宝贵价值的东西都承载在历史编纂的成果之中”[5]。以此新视角看待中国史学优良的遗产,便会发现许多史学名著仍是有待开发的学术宝藏。作者在《历史学新视野》一书中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国语》《史记》《汉书》《日本国志》《清代通史》等名著的编纂思想、体裁特点、内容特色、体制结构、体例运用和叙事技巧等项进行了内容翔实的分析与研究,尤其擅长通过典型个案分析,达到以小见大之目的,进而揭示中国史家历史编纂的杰出成就。
《李斯列传》是《史记》中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但是过去我们仅将《李斯列传》看成李斯个人生命历程的写照,作者认为这种传统的观点实未能深解司马迁历史编纂的旨趣。作者将《李斯列传》分为上半篇、下半篇和余论三个部分,指出上半篇的记载极其生动地刻画了李斯贪慕权势而又富有才能、善于判断时局作出正确应对的性格特点,以及其辅佐秦始皇实现统一大业的功绩;而到了下半篇,司马迁记述的格局明显发生变化,即组织材料的方法由单线条叙述变为多线条结合的记述,在记载内容上超出了李斯本人的传记,而是写出了李斯、赵高、秦二世三人在秦帝国晚期阴谋策划、倒行逆施,直至最终覆灭的下场。作者认为,《李斯列传》写到李斯被处死之后,并未终止,又以余论的形式补写了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赵高逼令二世自杀;子婴的即位、迎降及被杀。这部分内容,看似与李斯已无关系,为何司马迁要组织到《李斯列传》之中?作者深挖其意,认为:“《李斯列传》记载史实以李斯的活动为主线,而其发展则是记述秦皇朝最后覆亡的历史。司马迁在结尾精心记述的这些史实足以说明:此篇设置的用意,正是与《秦始皇本纪》互相配合,以完整地写出秦皇朝如何由成功的顶点,到经由赵高、二世、李斯之手而迅速灭亡的!”[3]102《李斯列传》只是《史记》鸿篇巨制之其中一篇,作者通过对这一典型个案精致而细腻的分析,使司马迁高超的历史编纂手法和高明的历史见识跃然纸上。
作者对《汉书·武帝纪》编纂旨趣的阐幽抉微,也颇具典型性。汉武帝统治时期的历史,在《史记》和《汉书》之中都有呈现,作者将两书的记载相互比较,指出:“今本《史记·孝武本纪》系后人截取《封禅书》内容以充篇幅。班固的出色贡献是重新搜集了丰富而确凿的史料,浓墨重彩,详载武帝时期历史。”[3]169作者通过对《汉书·武帝纪》中所载相关史实的分析、归纳与提炼,总结出班固状写了汉武帝抱负宏大、兴造工业、任用贤才,吏治做到赏罚分明、执法不阿,晚年统治虽有弊政,但能及时悔改,避免了亡国的命运。作者认为,班固后来居上,很少依据《史记·孝武本纪》的内容,而是重新搜集大量新史料,运用睿思,展开对武帝时期历史的全面记述,这是班固在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大贡献。故而,作者得出结论说:“班固不愧为一代良史,他有卓越的史才、高明的史识和高尚的史德。同时,此项研究对于深刻认识和恰当评价武帝鼎盛时期的历史,并从中获得治国施政的启示,也大有裨益。”[3]181作者通过对《汉书·武帝纪》编纂成就的析论,说明班固是以极其审慎、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汉书》的编纂,这也对过去长期流行的班固于武帝之前历史记载“尽窃迁书”[6]的观点予以了有力的驳斥。
(三)运用比较方法凸显史学名著的价值与特色
通过对相关的、具有可比意义的不同史著或史学现象做比较研究,能够更深刻地揭示出其相同和相异,开发出新的研究课题。季羡林说,比较方法“会大大扩大我们的视野,会提供给我们很多灵感,会大大有助于讨论的推进和深入。……中国的社会科学,其中也包括人文科学,想要前进,想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除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外,利用比较的方法是关键之一”[7]。《历史学新视野》一书很注重比较方法的运用,如对《史记》与《汉书》,《史通》与《文史通义》,20世纪的新史学流派、新历史考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分别做了比较研究。以作者对《史记》与《汉书》的比较为例来看,这两部产生在两汉时期的杰出史学名著,以往也有学者从比较的视野对它们进行过研究,但是比较的基础却是套用“对立面斗争”的模式,即为了赞扬司马迁史学的进步性、创造性,就需要寻找一个“对立面”作为反衬,班固和《汉书》不幸就成为贬低和苛责的对象,作为“正宗史学”“神学体系”“唯心主义”的代表,甚至被加上“封建皇帝忠实奴才”的恶谥。这种比较研究曾经长期阻碍着对《汉书》学术价值的客观认识。作者认为,《史记》与《汉书》交相辉映,应贯彻《史记》与《汉书》并举的研究理念,这样才能够对史学名著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如班固的《汉书》相较司马迁的《史记》,对西汉开国重要史实作了大量补充,首次概括出“文景之治”这一概念,对《武帝纪》基本上加以重写,等等,这些方面只有通过对《史记》与《汉书》加以比较考察,才能真正发掘出《汉书》的史学价值与编纂成就。[3]154-167当然,除了对上述名著直接进行比较研究之外,作者在全书之中还设置了两条隐性的比较线索,一是以《左传》为标准,考察《国语》的史学价值;二是以乾嘉历史考证的盛行为背景,映衬戴震、章学诚对“义理”之学探讨的光辉成就。因而,全书通过显性与隐性两种比较方式,不仅大大彰显了研究对象的不同特色,而且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成为本书的又一特色。
三、从哲理层面对史学名著的成就作出新概括
《历史学新视野》是一部展现民族智慧的创新之作,凝聚着作者对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诸多问题的哲理思考,其中概括的“司马迁多维历史视野”“哲理探索是历史编纂革新的动力”“实证考察与贯通认识”“20世纪史学三大干流”“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等项,均具有学术前沿性价值。这里以作者总结的“司马迁多维历史视野”和“20世纪史学三大干流”为例,略做分析,以窥本书的理论价值。
先秦时期的史著主要以时间维度记载史事,因而观察历史的视角较为单一,但至司马迁编纂《史记》,则创造了气魄宏伟的著史体系,被赵翼称为史家著史之“极则”[8]。历史编纂何以从先秦时期到西汉时期会形成如此巨大的飞跃?作者认为,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在哲理高度和认识本原上,发现并掌握了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即“多维历史视野”。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史学的成就,并且加以发展。《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互相配合而成,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则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包括时间维度、人物活动维度、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为主轴的多维视角。作者将之概括为“多维历史视野”。司马迁以多维视野观察历史的发展,故能将事件发生、演变的年代先后,历史变局的因果关系,人物的活动和风采,典章制度的传承演变及复杂的社会情状,有条不紊地呈现出来。作者认为,“多维历史视野”是一种抽象和概括,它“是司马迁杰出创造才能在哲学思维上的体现,是笼罩《史记》全书的哲学光华。唯其成功地运用了多维度历史视野,而非单线式、单角度的观察,他呕心沥血著成的《史记》才为我们展现了华夏民族有史以来全景式的、丰富、生动的画卷,有血有肉,内涵深刻,令读者百读不厌,感悟奋起!”[3]61-62司马迁的“多维历史视野”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它深深地影响了梁启超对《中国通史》编纂的设想以及白寿彝对《中国通史》“新综合体”的探索。作者对此问题的考察,从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上说明了司马迁以“多维历史视野”著史的哲理思考在两千多年之后的史学家那里产生了共鸣,在新时代产生了回响,尤具卓识。
作者在《历史学新视野》下篇的后四章设置了三个主题,一是梁启超和萧一山出色的史学成就,二是新历史考证学,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三大主题是作者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中总结出来的影响最大的三个“流派”,故而将它们合而观之、并重考察,寓含着作者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与认识。我们熟知的情况是,新历史考证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两大“干流”,对于梁启超开创的新史学,过去则将它视为“学术思潮”,“没有明确地认识到事实上它已经形成一个重要‘学派’”。这一学派,除了梁启超之外,还有萧一山、吕思勉、张荫麟、杨鸿烈、姚名达、周予同、周谷城、陆懋德等人。他们共同尊奉进化史观,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注重扩大史料范围,重视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关系,主张撰写史学著作的意义在于教育民众,有的还有明显的学术传承关系。因此,作者提出:“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不是‘两大干流’,而是‘三大干流’,而且不同学派之间不是互相对立、互不相干、壁垒森严,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借鉴、互相影响。这样,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全局的认识,才会更符合学术本身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9]《历史学新视野》将“新史学”流派、新历史考证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放在一起加以探讨,正是要从实践上诠释作者提出的“20世纪史学三大干流”的新概括。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格局以及不同学术流派力量的消长,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自有深入研究之必要,同时,中国史学又是世界史学的一部分,这要求我们在考察中国史学时,需将其放在世界史学发展的背景下,与世界史学相互联系加以考察,才能更加凸显中国史学遗产的优良传统与鲜明特色。于此方面,《历史学新视野》一书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再者,关于史学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关系,作者因限于篇幅,仅仅列举了《国语》《史记》《汉书》《史通》《文史通义》等典型名著做分析,而对于民族文化创造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明时期的史学名著中的呈现及其阶段性特点,则缺乏相应论述。实际上,作者已经意识到这一工作意义重大而又“十分艰巨”,“本书只能选取若干重点问题做初步探讨”[3]2,对于其他未能论及的问题,则留待后学完成。具体来说,这两点遗憾,并不影响《历史学新视野》一书的开拓意义和理论价值。
综上,我们认为,《历史学新视野》一书首次从史学传承的角度探讨了民族文化创造力,阐发了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中所蕴含的民族智慧,彰显了当代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有助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是一部兼具学术前沿价值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