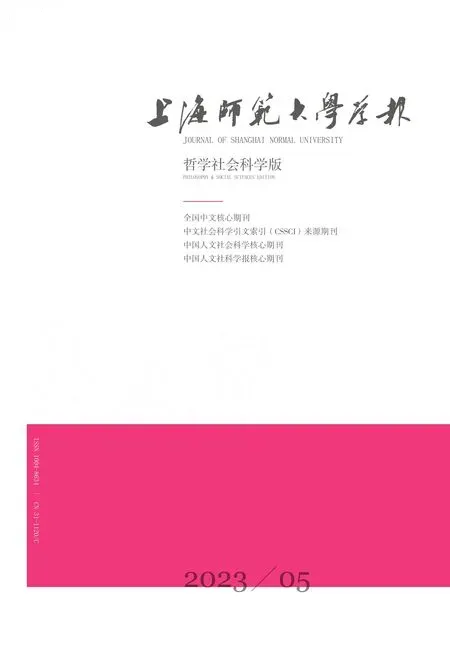“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维度与思考
2024-01-09汪朝光
汪朝光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是个非常有意思也很重要的主题。最近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强有力的、富有成效的国家治理和良善有序的社会治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国际关系与国际交往,乃至无远弗届的网络世界,我们都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平等化、民主化、本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的意义。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深入研究也不够,只是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观察出发,就这个问题,从几个方面谈点个人意见,算是小小的引言,期待大家的讨论和批评。
第一,是讨论的主题。
我们今天说的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当我们谈到国家治理的时候,在多数情况下会理解为是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国家的内部关系;而后面谈的全球治理,则主要是国际关系层面的概念,是国与国之间的外部关系。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家治理,只是因为讨论他国的国家治理,牵涉方面甚广,往往力非能及,姑且不论。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国家治理,更多谈的是中国的国家治理,而当我们谈全球治理时,更多感受到或者想到的是世界范围的国际性体系下的治理。所以,如果我们谈中国的国家治理,基本是一个中国史或中国政治的范畴;如果我们谈全球治理,则是一个世界史或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范畴。把这两个不同的范畴或体系结合起来进行讨论或者互动,在主题上或者选题上也就有了中国史与中国研究和世界史与国际研究相交融的意义,非常适合现代学科融合发展的潮流。当下,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之间的边界已经越来越交融为一体了,理解中国离不开世界,理解世界同样也离不了中国。这个主题实际具有相当广阔的研究拓展性和可能性,其中的某个个案,就可以写成博士、硕士论文,或者有更多研究的思考和发表。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主题的选题意义。在学术研究中,选题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很多情况下,选题本身就体现了研究的眼界。好的选题、具有开拓性的选题,可以做到事半功倍,而且可以做出来;反之,那就是事倍功半了。这个主题如果我们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有了更多的积累,甚而也不妨考虑可以做成系列性研究,出多卷本成果,立项为国家级的重大课题。也许那时我们再回望今天的讨论,会觉得本身就是开拓,我们都与有荣焉。
第二,从讨论的主题——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出发,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其评价标准如何?
历史观察无非两大主要维度,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如果我们从时间维度观察,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国家治理是有明显区别的。古代的国家概念还不完整,与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的国家概念有很大分别。近代民族国家具有严格的边界限定和主体(主权)意识,在这样的前提下,近代的国家治理更具有我们当下所理解的国家治理的诸多要素。而随着世界一体的发展,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关系如何?当代国家治理与近代国家治理的异同何在?全球治理是从以国家治理为基础、讲究国家主权的国际关系出发,还是可以超越这样的国际关系而走向更广泛、更平等、更民主的全球协调共治?这样的时间线及其产生的问题,从古代到近代、再到当代,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再就空间层面观察,虽然我们谈的是国家治理,但是,国家是处在不同的空间之中的,而且这个空间的概念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例如中国,具有广大的陆地空间,一般被理解为一个大陆国家。其实,中国是有着广阔的海洋和漫长的海岸线的国家,我们的先民早就有过相当规模的出海史、出洋史,大规模的“下南洋”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中国也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海洋国家。但是,因为我们对中国历史空间的先验性意识,在相当程度上约束了我们的思考,当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大陆国家之后,我们对国家治理、国家安全等的思考和应对,可能就会偏向于这个所谓大陆国家的体系,这对我们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再比如说美国,因为其面对两洋的地理环境,我们大多把它理解为一个海洋国家,其实美国也有广阔的陆地空间,同样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大陆国家。导致美国最终成为面对两洋空间的所谓海洋国家的重要环节之一,恰恰是它的西部开拓,也就是大陆扩张。而这样的西部开拓和大陆扩张,在美国人的历史记忆和精神生活中的意义,完全不亚于、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那些海洋开拓史。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中美两国在空间环境方面是有共通性的,既是大陆国家,也是海洋国家。不像日本或者英国,它们都是本土面积不大的岛国,将它们理解为基本是一个海洋国家自有其理。也不像俄罗斯,虽然它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多半位于严寒的、一年中有大半年在封冻的极北方,如何获得温暖的、能够全年自由进出的出海口,几乎是与俄罗斯近代发展共始终的话题。再加上俄罗斯世界第一、横跨11 个时区的广袤大陆空间,其对俄罗斯的重要意义自在其中。由此观之,空间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对我们认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诸问题的意义,也值得我们去思考。
进而言之,当我们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中讨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这样的治理。比如说制度的作用。制度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都可以理解的。再有,和制度相关的,组织的作用。或者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和组织,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还有,我们现在越来越感受到技术的作用。尤其是经过新冠疫情,全世界都能理解并感受到技术在国家治理甚至全球治理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技术的作用发挥又是与一定的制度和组织密切相关的,全球的新冠疫情防控可以说是这方面情况的一个验证。再比如说,文化传统与思想认知能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举个例子,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电影市场,从时空层面而言,对上海这样近代兴起的沿海大都市、北京这样的数朝古都、成都这样的内地省会、合肥这样当时甚少为外界感知的内地城市,其电影观众在看时装片时有相当的感受差别,有不同的爱好,但是,所有这些城市的电影观众也有着基本共同的爱好,就是他们都爱看武侠片,这说明武侠片中反映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认知,在相当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代表了当时中国人所具有的共通性价值观的。至于这个价值观是什么,我们还可以去探究,究竟是义气豪气,还是忠孝仁爱,还是信义和平,也就是归结到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但无论如何,这个事实的表象及其蕴含的内容,说明中国人是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与思想认知的,这也是中国历数千年历史而从未中断并始终屹立于世界的内在因素,而这一定会反映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中。至于全球治理,同样如此。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出发,确立平等而民主、非强权而霸凌的全球治理观,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我们具体讨论这个话题时,我们还是要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确定讨论的原则。不同的时空可能有不同的判断标准,用今天的标准去套古代的国家治理或者全球治理未必适用(甚至古代就不存在我们现在理解的全球治理)。同样,在今天的制度、组织、技术、文化、认知等方面,也需要有新的适应这个时代的判断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良善与否的标准。在这方面,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 卷,外文出版社2022 年版,第475 页。这也是我们评价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时的题中应有之义,历史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更应当有一份责任。
第三,学以致用,以史为鉴,我们从中国的实践,更多是从近代中国的实践来看我们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参与这两方面究竟做得怎么样?
比如说全球治理,中国在参与20 世纪上半叶的全球治理体系方面是有成功之处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其表征。
20 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的感受可能没那么深,但我们也是参战国,并且是胜利方。就“一战”的起源、进程和结局来说,可以理解为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全球争夺所致,即便是西方学者也不否认这一点。本来这场战争发生在遥远的欧陆,与中国并无多大关系,但是,日本和德国的帝国主义利益争夺,却使中国的山东成了战场,后来又由于种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中国也被裹挟进这场战争。既然中国参战了(虽然并未出兵),就有个站队的选择问题。而中国的选择使自己在战争结束时站在了战胜国这一边,这是有它的意义的。近些年来,近代史学界关于“一战”的研究取得许多进展,认为中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外交可圈可点,虽然是被动参战,但在战后收回了德奥的特权;虽然在巴黎和会期间遭遇外交屈辱,但通过一定的外交运用,还是在后来的华盛顿会议上收回了山东主权;同时,中国通过在战后参与国际联盟的活动,也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获得了表达的可能。所以,“一战”本身是资本—帝国主义矛盾的产物,但是中国在被动卷入之时,做出了于己有利的合理选择,对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来说,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
“二战”的情况则与“一战”根本不同,“二战”有明确的正义、文明、民主的阵营和非正义、野蛮、专制的阵营之分别。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在“二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野蛮对外侵略扩张,比如说纳粹的屠犹和日本的战争暴行,使它们成为全人类文明的公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在“二战”前,当时的中国同样也有选择站队的问题。例如,战前中国和德国的关系还不错,尤其是双方有密切的军事合作,所以可以选择和德国站在一边,而且看上去德国似乎也很强大。中国和日本更是所谓“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在中国有很深的利益纠葛,培养出不少亲日派。在当时中国的执政者内部,比如汪精卫这一派,便倾向于选择和日本合作。但是,历史事实说明,中国既没有选择站队德国,更不会选择站队日本。在面对日本入侵时,大多数中国人选择的是坚定地抵抗。共产党人坚定抗日,一切爱国的中国人也都是如此。中国通过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打响了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侵略扩张的第一枪,不仅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中坚力量,“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445 页。而且参与形塑了战后国际体系,成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体系也就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成员,并负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规则的重要使命。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 卷,第477 页。当我们讨论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时,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各国皆然。这也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如上所述,客观而论,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形塑或者互动方面,有其成功的一面,但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缺少深层次的讨论。作为一个大国,也是弱国的中国,当时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如何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当时外交的主事者,如顾维钧等新一代外交家,自青年时期起即长期留学欧美,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知道如何与西方打交道,“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但是问题绝不止于此,就像顾维钧表述的那样,他是一个中国人,他有坚定的中国立场,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坚定地站在中国立场上的。因此,对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选择,其实我们还可以有更深透的研究。当然,他们的作用可能更多是在技术层面的运用,在更重要的战略决策层面,我们会注意到,作为领袖人物的孙中山,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关注国际局势对中国的影响。而井冈山和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虽然身处山野偏僻之处,但他从来都是将中国革命与世界形势相联系的。无论是他论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还是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战为什么最终能够胜利,以及中国为什么必须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其中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敏锐观察和睿智思考,都是不可或缺的方面。而说到底,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正确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如何理解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中国地位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的作用。
但是,在国家治理这方面,中国近代确实不那么成功,这是一个事实。举个简单的例证,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以前,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现代的、科学的人口统计,自己有多少确切的人口都不知道,还怎么实行现代征兵制度,怎么实行人力资源在战时的高度动员?结果国民党的征兵只能靠“拉壮丁”。本来是大家动员起来保家卫国的战争,却因为国民党治理体系的低效无能搞到民怨沸腾。日本战败时全国有七八千万人,但有700多万军队,说明其动员能力相当之高。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数倍,但军队总数却差不多,说明我们当时的动员力严重不足。尽管日本的治理体系发展到了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一面,但是它在社会动员力方面当时确实高于我们。所以,这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抗战时期,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参与形塑了体现公平、正义、民主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及其战后体系和秩序,但是,一个良好的或者相对成功的融入世界的过程,一个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选择,其正面效应为什么没有能够相应地传导到内部,反而是国民党政权战后不久就在革命浪潮中垮台了?这对我们理解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进程,理解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之间的复杂互动,也具有启示意义。
相比较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几乎是毫无障碍地融入了西方体系,摆脱了与西方之间曾经的不平等地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一跃而崛起为亚洲强国。应该说,日本在国家治理方面有其成功之处。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其野心膨胀,军国主义兴起,开始了野蛮的对外扩张,成为稳定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非正义挑战者,最终站在了人类公平正义的反面,导致其军国主义对外战争的彻底失败。也就是说,日本看上去相对成功的内部治理,也没有传达到其外部关系,在“二战”前的全球治理方面,日本只是留下了失败的记录和可资汲取的教训。
所以,怎么理解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关系,其实不那么简单,其间的互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二战”前日本相对成功的国家内部治理,并没能传达到日本融入世界体系之后的全球治理中,反而使其成为一个挑战世界既有秩序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而“二战”前的中国已经在融入全球治理的世界体系,并且通过自身抵抗日本的侵略,参与形塑了一个代表历史正确的战时和战后全球治理体系;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所产生的正面效应,也没能相应传导到国内,国民党政权还因站在中国民众的对立面而失去民心并最终垮台。由此观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其实是一篇大文章,其异同何在,如何互动并扬长避短,如何兼容并蓄,等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最后,谈谈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未来展望。
最值得关注的是,当高科技日渐发展,并越来越多地融入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之时,我们怎么去面对?高科技有非常方便的一面,利于每个人的生活,也就是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们已经充分享受到其成果。但是,其也确实有值得我们警惕的一面,而且其发展存在诸多可能影响我们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可能需要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惕。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国家治理还是全球治理,未来的发展都需要有更高的自由度、更大的创造度、更广泛的平等度,这也是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达到良治善治的必由之路。中国是一个大国,未来国家全方位的发展,不仅仅是我们理解的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发展、价值观的塑造,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大国,经过改革开放的40 多年,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有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在当下的新时代以及未来的发展中,还能够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新成果,总结出什么样的具有普惠性的经验,也是学者的应尽责任。
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大体上仍然是“二战”以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这是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阵营的胜利成果,需要我们大力尊重并维护,反对脱离这个体系另搞一套。当然,这个体系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有许多事情可能超越了过往国家治理或者全球治理体系的经验,在原有体系下不一定能够完善地解决,比如说近三年的疫情,还有其他一些事关全球和全人类的问题,如环境问题等。日本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贸然决定向公海排放核污水,如何去应对,对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就是个挑战。因此,我们就要思考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应该有什么样的与时俱进的发展,同样,也应该思考国家治理体系在各国如何有新的发展。
马克思说得好,未来世界或者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毛泽东也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今天我们谈论国家治理或全球治理的话题,也是为达成这样的目标而思考、贡献。这个话题是可以不断扩展的话题,值得去不断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