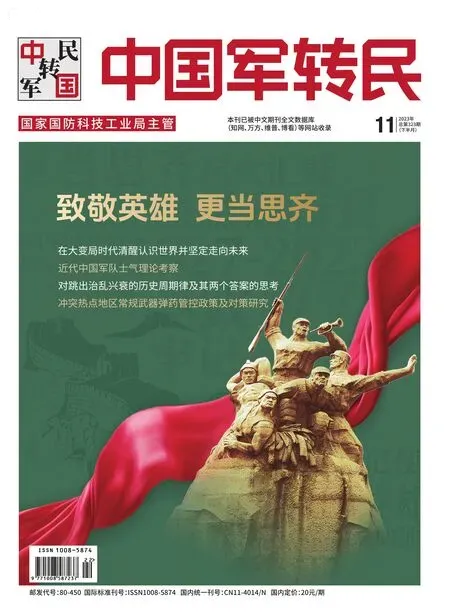近代中国军队士气理论考察
2024-01-06张喜燕
张喜燕
近代是一个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古老的中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敞开了大门。外族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深的屈辱,也带来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冲突与碰撞,促使爱国志士不得不从思想文化层面反思中国的未来。特别是军事上的不断失败,更促使爱国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从理论层面去思考一支军队战败的原因,包括武器装备,尤其是精神培育的状况等问题。这一时期既是传统士气思想集大成的时期,同时又是新的士气思想极度活跃的时期。近代军事将领在保持“忠诚守信”等传统军人价值观的同时,认识到传统文化存在的积习与弊病,久衰不盛的国家精神对于士气的破坏,试图从屈辱中奋起,挖掘民族精神中的积极因素,并注重大胆向西方民族学习,认为这不仅是重振军队士气的需要,同时也是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军队士气理论的重要转型时期,代表性的士气理论有“良心血性”说、“国魂”说和“主义”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蔡锷、蒋百里、孙中山等人。
一、“良心血性”说
“良心血性”说是近代军事理论家从军人道德修养的角度提出的士气理论。蔡锷在其《曾胡治兵语录》的序言中痛心指出:“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救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为此,他十分重视“气”对于一支军队战胜的重要性,“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并指出,“军中取材,专尚朴勇,尚须由有气概中讲求。特恐讲求不真,则浮气、客气,夹杂其中,非真气耳”,而“良心血性”造就的才是“真气”。“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提出“良心血性”说。所谓“良心”,就是指对国家的“良心”、对军队的“良心”以及对自己部下的“良心”,是一种崇高的责任与担当;“血性”则指的是一种来自于军人内心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义从肝胆生,挟裹着凛然正气的血性之勇,是敢于为国慷慨赴死的决心与品质。蔡锷说道,曾国藩在谈论为将之道时提出要具备“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汲汲名利、耐受辛苦”四者,才能担当大任,并指出,“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是而非四者,终不可恃”;胡林翼指出,“带兵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蔡锷认为,要造就“良心、血性”,必先修养自身,“舍命报国,侧身修行”,强调军人伦理尤其是军官伦理品质对于士气的重要性。蔡锷提出带兵之人应具备“诚实”“勇毅”的品质,此一品质最能凝聚人心,激励斗志,“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胞无间,不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蔡锷还认为,“勇”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临难不苟,义不反顾,此狭义的、急剧的者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广义的、持续的者也。所谓浩然之气者也”,真正的军人不能只有“匹夫之勇”,应具备“勇毅”的品质,即“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誉、荣辱、死生,皆可不必计较”,才是军人之根本、士气之所在。“良心血性”说从军人的职业伦理角度谈士气问题,体现了近代军事理论家已充分认识到在军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军人的职业意识对于士气的重要性。
二、“国魂”说
“国魂”说是以蔡锷、蒋百里为代表的近代军事理论家反思民族文化,从重振“国民性”的角度提出的士气理论。近代列强入侵,逼迫国人在饱受屈辱中去反思自己的文化。为什么中华民族在世界竞争中节节败退?如何使积贫积弱的祖国重新崛起?如何在对外的战争中制胜?如何激发民众的报国热情?……蔡锷等人对此做出了深层次的文化思考,并提出了“国魂”说。他认为,“国魂”不仅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是军队士气的源泉。蔡锷在《军国民篇》中指出,一个民族想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必有“国魂”作为民族精神的脊梁。什么是“国魂”呢?蔡锷指出:“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其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阵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中之指南针,如枪炮之照星,如星辰之北斗,夜光不足喻其珍,干将不足喻其锐,日月不足喻其光明,海岳不足喻其伟大,聚数千年之训诂家而不足以释其字义,聚凌云雕龙之词人骚客,而不足以形容其状貌,聚千百之理化学士,而不足以剖化其原质”[1]。这里的“国魂”即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在他看来,“日本之武士道,日本之国魂也;德国于国土蹂踏之后,亦形成了自己的国魂,从其《祖国歌》中可以读出;美国则有孟鲁主义;俄国有斯拉夫人种统一主义等等。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1]。蔡锷认为,只有拥有“国魂”的军队才能够士气高涨、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如何陶铸国魂呢?蔡锷提出,“国魂者渊源于历史,发生于时势,有哲人以鼓铸之,有英杰以保护之,有时代以涵养之,乃达含弘光大之域,然其得之也非一日而以渐。其得之艰,则失之也匪易。是以有自国民之流血得之者焉,有自伟人之血泪得之者焉,有因人种天然之优胜力而自生者焉”[1]。然而,他寻遍汉族四千年的历史,却找不出中国的国魂所在,但蔡锷并不否认,“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其实,蔡锷详细描述,但未明确指出的中国所谓的“国魂”,就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期迸发出的绝不屈服的爱国尚武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只有通过实行“军国民主义”教育训练,改造文弱不堪的国民性,激发民族活力与斗志,同时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加强军事准备,才能产生。“国魂说”代表了近代以蔡锷为首的一批爱国志士,尤其是军事将领对于如何拯救国家、挽救民族以及激发军队士气的深层次文化思考。
三、“主义”说
“主义”说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等人为提升军队精神战斗力而提出的士气学说。“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是孙中山社会政治理想的核心。这种政治信念也贯穿到孙中山等人的治军思想当中。他认为,军队的灵魂是“主义”,中国革命军队的灵魂是“三民主义”,有了“三民主义”灵魂的军队才有士气,士气源于革命的精神,为革命牺牲,就是为“主义”牺牲。他指出:“军队的灵魂是主义。有主义的军队,是人民和国家的保障。举例如法国,他们将平等、自由、博爱做主义,三色的国旗,便是表示出三种主义来的。法国有了这种军队,所以能革命成功。军界同胞,也应像法国般,勉为有主义的军队才行”[2]。他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三民主义”的士气理论。一是必须对革命军人进行革命精神教育。孙中山认为革命军人必须接受非常之军人教育,必须与“当兵吃粮”的旧军人有所区别,也就是说要“同负革命之责任”“非有革命精神不为功”,即革命军人须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不屈斗志。他认为反帝反军阀都必须有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克敌制胜的强大动力。二是确定“三民主义”为军人革命精神的核心。孙中山要求革命军人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他认为革命军人高尚思想的根本表现就在于为“三民主义”而英勇献身。军人一旦具有了这种献身精神,就能吃苦耐劳、视死如归,表现出最大的勇敢,就能战无不胜。三是军人必须具备智、仁、勇的精神要素。他说:“所谓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即为军人精神之要素。”军人之智是指军人能“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强调“军人之智,须以合乎道义为准”。而军人之仁与智不同,他说:“所贵乎智者,在能明利害,故明哲保身,谓之智。仁则不问利害如何,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无怨矣。”革命军人之仁就在于为实现三民主义而不怕牺牲,军人之勇就在于不怕牺牲。他常说:“为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他鼓励军人说:“诸君既为军人,不宜畏死,畏死则勿为军人。”而这三者之间并非独立的,而是把智慧和道德相融,把勇敢精神与革命理想联系起来,是极有份量的,为革命军队的士气建设铺设了一条新路。孙中山的“主义”说,真正将“理想信念”纳入到军队士气要素当中,有意识地培养军人内心对于国家制度和政治理想的追求,将其作为激发军人内在动力的思想源泉,比之过去的士气理论,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近代转型时期,中西军事文化剧烈冲突、对抗与融合,传统文化所推崇的“良心”“忠义”“勇武”等积极因素仍然是近代士气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但同时,爱国进步人士从西方学习先进的军事文化理念,以此作为重振大国雄风的救世良方,重塑“国魂”,唤醒民族尚武精神,用“三民主义”启发民智,以政治化的“主义”武装军人头脑,明确提出军人价值、军人使命的概念,赋予军人以政治责任意识,以此作为军队士气的重要动力,彰显了时代的需求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