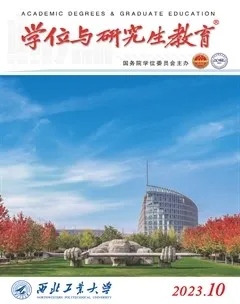德国硕士留学生课程教学中的跨文化互动问题及协商实践
2024-01-03赵倩
赵 倩
德国硕士留学生课程教学中的跨文化互动问题及协商实践
赵 倩
借助质性研究方法,从跨文化互动视角入手对中方教师和德国硕士生的跨文化教学互动进行动态深层透视,旨在了解双方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行为方面的互动问题、不同期待及为此进行协商实践的实然状态,探讨提升硕士留学生教学质量的路径。在中德民族文化、学术文化、高校传统以及中德硕士生教学互动场域这一情境因素和双方个人因素的影响下,中德师生在跨文化教学互动中经历着碰撞,并通过在地协商彼此影响、不断调整,使部分问题得到理解或解决,维持着动态平衡。研究发现,提高中德硕士生课程教学品质的核心领域在于教学内容,为此须进一步在个人和组织层面做出调整。
德国硕士留学生;课程教学;跨文化教学互动;在地协商;研究生教育
一、引言
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主要形式[1],优质的研究生教育既能加大国内人才培养力度,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吸纳高层次人才[2]。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强调要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针对这一议题,在观念层面上存在高校管理者与教师对质量保证缺乏深入认识等问题;在实践层面也存在诸如缺乏系统的配套设施,内外沟通互动机制不畅等问题[3]。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强调要“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留学研究生教育作为传播中国学术理念,吸纳国际人才的重要阵地,其质量问题逐步成为当前我国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命题[4]。而作为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之一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其教学质量是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品质的直接表现。
此外,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快速增长给我国研究生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群体,德国留学生来华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5],迄今为止已有500余所中德高校(中方高校300余所,德方高校200余所)建立了实质性的校际交流关系[6]。目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包括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保证仍然面临诸多问题,须有效统筹多元主体的力量加以解决[3],而作为教学主体之一的教师肩负着核心使命,其与学生在课堂内外的有效互动是保障留学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根本。本文从中德硕士生课程教学互动的微观层面入手,聚焦中德师生在该场域中的实际困难、产生原因及双方协商实践的实然状态,探讨提升留学研究生教学质量的路径。
二、研究背景和方法
近年来,学者针对中外高校教师普遍特点开展研究的同时,也对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教学问题进行了探讨。陈丽等指出,来华留学研究生对教学的满意度不高[7]。齐忠方指出,留学生人才培养的不足主要体现在语言沟通障碍、教材版本差异和专业能力要求上,认为“我国的留学生人才培养无论是在教学理念还是在方式方法上仍然稍显滞后”[8]。刘水云的调研也有类似发现:留学研究生对中国相关高校的课程设置、学习内容、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的满意度较低[9]。究其原因,孔兰兰等指出中方导师和留学研究生的互动存在“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方面的文化差异”[10]。
对中外高校教师的对比研究也为本文提供了借鉴:在教学内容方面,中国高校教师更重视专业理论知识的讲授,对实践和应用的重视不足[11]。在教学方法方面,中方教师“多‘以教材为中心’,以经验为中心组织教学,外籍教师则更多‘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12];中方教师的教学方法常常是“填鸭式”的,以“灌输为主”,而“国外的教育教学过程注重师生互动”[13]。在行为方面,英美研究生往往期待在教学互动中更加自主和独立[14],而在中国“教师处于权威地位,师生互动较少”[13];“国内教师多为指导者、命令者、督促者”,国外教师则多为课堂的引导者和辅助者[15]。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以静态对比为主,鲜有从中外师生双视角入手,对双方在具体互动情境及个人经验等多因素影响下的实际教学问题与问题协商互动的聚焦;大多一边倒地认为国外教学优于国内;且缺乏对德国硕士留学生群体的关注。
为提升硕士留学生课程的教学质量,中外师生在教学互动中会根据对方的行为特点及双方共同打造的即时教学情境相互影响和调整。作为该协商过程的结果,硕士留学生课程教学须应对的核心问题必然与中外教学静态对比得出的应然状况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中外硕士生课程教学互动的实然问题进行探究。本研究采用跨文化互动研究范式,遵循“过程化—互动性”原则,将互动和交际放到特定情境中,“分析跨文化互动中的迷惘及误解,理解通过社会协商产生互补性”[16]的过程;注重交际双方切实感知到的对方特点及在具体语境中对对方的阐释[16]。根据以往研究的核心问题,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师行为三大类属,本研究从两所大学三个学院2017—2020级德国硕士留学生中随机选取15人,同时选出其跨文化商务沟通类课程全外语授课的5位中方任课教师为研究样本,使用质性访谈法收集资料,借助质性内容分析法分析资料,探索中方教师与德方硕士留学生在跨文化教学互动中实际感知的问题。从文化、学术文化、具体情境和个人角度做出归因,观察双方的协商过程,探讨提升留学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的可能。
三、结果与讨论
(一)教学内容
受访中德师生在教学内容上感知到的差异和问题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1.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
多位德国硕士生感觉中德院校的课程设置在系统性上存在差异。尽管“跨文化商务沟通”等课程与实践密切相关,但德国高校常会配置其来源学科的专业理论课,如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
德国大学设置了一些基础理论课作为专业选修课,这里没有。其实比如用德文或英文授课的“中国文化导论”可能很有用,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德硕N)。
受访的中方教师也都发现了德国硕士生在这方面的知识缺口,并逐步在自己的课堂上增加了中国文化的相关内容,但却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我的课程主题是中德跨文化商务沟通,对中国文化的讲解本来就是辅助性的。我会讲到“关系”这个话题,但在选择文献时,就遇到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课时有限,留学生课下阅读时间也不多;另一方面“关系”这个话题内涵丰富。我不想只是点到为止,因为这容易造成片面理解甚至偏见……”(K老师)
尽管表述不同,但中德师生聚焦的问题却不谋而合:即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基础性内容系统地融入跨文化商务沟通类课程体系中。在通过沟通发现这一问题后,中方教师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对中国文化深层内涵的讲解,其所在高校也陆续开设了诸如“中国文化解读”等课程,但由于目前授课语言是中文,难度超出了绝大部分德国硕士生的中文水平,因而这一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涉及教学大纲方面,中德师生关注的问题不尽相同。德国硕士生指出教学大纲不够细致,缺乏计划性,而中方教师提及的则是与留学生来源高校教学大纲的匹配问题。“中德老师都会在开学前公布教学大纲,但细致程度不同”(德硕Ma);“这里的大纲比较粗略”(德硕F)。此外,“有的课没按计划讲,讲不完就拖到下次,导致一些计划内的知识讲不到,很可惜……不过这种问题在德国也有”(德硕K1)。
对此受访的中方教师无一例外地认同“教学内容的设计是重中之重”(M老师),教学大纲应尽可能详细,“国外大学一般很重视这个,国内院校在这方面还不太严格”(K老师);不过“要为留学生的专业课做跨文化、跨学科的课程设计难度更大,有时确实需要随时调整”(C老师)。此外老师们强调了“教育衔接不畅”[11]带来的问题。由于“每年来的德国学生专业基础都不一样……有时不得不在学期中间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调整”(L老师)。能否在确保有针对性的同时将教学大纲固定下来,这一问题在教师备课时一度造成困扰,不过通过与德方相关专业的教授以及连续几届德国留学生的沟通,问题“不像开始时那么棘手了”(K老师)。
在上述问题当中,中方教师提到的中外教育教学衔接最为根本,其解决有利于规避德国硕士生提出的教学大纲的具体问题。
2.教学内容的侧重点
德国硕士生认为德国课程中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前沿理论更多,“这里用的理论更保守”(德硕V)。还有学生希望教师能把自己的专业实践经验融入课程,在这方面,很多学生觉得德国老师经验更丰富。
关于课程内容前沿性这一问题,中方教师也有提及。
跨文化交际领域的不少新兴理论本身就来自德国,甚至就是德方授课教授自己提出的,他们讲起来得心应手。更关键的是,有些新兴理论在欧洲适用,放在中国就水土不服了。比如欧洲有种新观点认为文化是完全开放的,“民族文化”的概念完全过时了。这其实是从西方移民社会的视角阐释的结果,中国人往往并不这么看,所以在这里很难讲得通(K老师)。
对于何谓前沿理论,中德师生间也有不同理解:德国硕士生所说的前沿理论大多产生自欧美移民社会;而目前中方教师眼中的“前沿”则更多的是把中国视角和本土概念引入专业视域。部分德国硕士生理解了这一点,提出“这里的东方视角是德国课程所欠缺的”(德硕Mo),“课程内容的设计体现了中德学术文化的差别,各有千秋”(德硕C1),当然也有不少学生对此不太认同。
此外,尤其在“跨文化商务沟通”等与实践密切相关的课程中,德国硕士生看重教师的实践经验,认为它也“能体现教师的专业水平”(德硕G),“如果老师有跨文化培训经验,能把实践案例拿到课上来讲,那课程的专业性会更强”(德硕Sa)。在这一点上,德国硕士生显然对中方教师还有更多期待。受访的中方教师也认为,“具备专业实践背景更容易获得学生的认可和信任”(C老师)。M老师也表示,因为缺乏相关实践经验,“我课上的案例比较陈旧”(M老师)。
针对以往研究的结论,如中方课程“往往讲了基本原理之后就结束了”[11],受访德国学生的体会并不统一。有人认为“德国老师会用案例去讲解比较抽象的理论,更有利于对理论的理解”(德硕C)。言下之意,中方教师在这方面做得不足。但也有学生的感受恰好相反,“中国的课更注重实践,就是让我们体会怎么把专业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德硕Ma)。而之所以学生在这一点上意见不一,显然与具体专业和课程的特点以及任课教师的个人风格密切相关。
3.教学资料
以往研究发现,中方教师常使用已出版的教材开展教学,教材虽全面系统,但通常多年不变[11]。但本研究的中方教师使用的教学资料大多是多样化的期刊论文和理论专著,只有个别老师使用了固定教材。
还有学生提出:“德国教师会在开学前把所有阅读材料上传到网络平台,我们可以按需要和偏好提前阅读,很方便”(德硕Ma),而中方教师则常常“是在每次上课前才把阅读材料发给我们”(德硕H)。
上述发现之所以与之前的研究有所不同,是因为本研究的调研对象,即外语院校全外语授课的教师们大多有国外留学经历,对国外高校的做法有所了解,并不断根据往届德国硕士生的特点调整做法。不过针对德国硕士生提出的教学资料发放形式的问题,中方教师持保留态度,有教师指出,如能利用学术交流平台与德方相关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师沟通衔接,则这一问题不难解决。
(二)教学方法
根据受访德国硕士生的体验,中方教师也使用了不同的教学方法以便适应德国硕士生较强的主体性要求。在经历了适应过程之后,其在教学法上显现出与德国高校教师的趋同:也开始使用师生共建和启发式教学法,如“作报告、小组讨论等”(德硕B),或通过“互动式讲授”(德硕Sa)创造机会让德国硕士生发表见解,而并非如以往研究发现的那样,使用以灌输为主的“填鸭式”教学法。
事实上,受访中方教师在最初承担涉外专业课时使用的教学法确实比较传统,L和M老师觉得是惯性使然,因为中国学生“往往不愿意在课上被提问,他们喜欢听老师讲”(L老师)。或许正因如此,有教师一度相信:“专业课和技能型课程如外语课不同……专业课应以老师讲授为主”(K老师)。C老师也曾认为专业课更注重知识传授,“所以开始时就采取了主导型的教学法”。但通过观察和沟通,教师们发现了德国学生的特点:“德国留学生大多不习惯专业课成为老师的一言堂”(K老师);“一般我讲上15‒20分钟,底下学生的表情就呆滞了”(L老师)。于是教师开始有意识地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留学生Mo表示不喜欢老师把知识“嚼碎了”“喂”给自己,希望能有机会独立思考,表达观点。其他德国学生也大多认为“讨论有助于发现规律”(德硕Ma)。
中国的教学原本更重视清晰而明确的知识转移;而德国人则更早开始采用共建式学习法,认为做报告和小组讨论比单独学习更为有效[17];提出教师有必要与学生对话[18]。本研究的中方教师身处中德跨文化教学场域,根据观察及与德国硕士生的沟通,主动调整了教学法。
不过德国硕士生仍然认为德国教师的教学法更加多样。比如德国较为常见的“学生间协作式”教学法,它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有模拟游戏和推演谈判等练习方式,强调教师不再是掌握唯一正确答案的课堂权威,练习由学生通过协作独立完成。此外,还有德国教师会让学生在课上以“准教师”的身份给同学们讲解。而德国教师的教学法之所以更关注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度,与欧洲高校的历史沿革以及《博洛尼亚宣言1999》中的教育理念有关,即欧洲高校教育核心“从教到学的转变”、教学范式从“教文化”到“学文化”以及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推行这种理念激发了欧洲高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性、自组织性和责任感,也使教师在教学互动中转为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辅导和监督,而非“直接教导”[18]。
(三)教师行为
教师行为包括课上行为和课下行为。课上行为主要指教师进行课堂管理、专业点评以及应对质疑和负面教学反馈的行为;课下行为则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私人生活的关怀。
1.课堂管理行为
德国硕士生认为中方教师“会更多地管着学生,还会选出班长协助管理”(德硕Kl),她们普遍不适应某些课程每次都要签到、三次不到就取消考试资格的威慑性做法;而且“有的老师不提前通知就做小测试,万一当时谁没来就没成绩”(德硕S);并认为测试的规则必须“清晰而公开”(德硕E)。而对通过让学生在课上做和专业不相干的事进行课堂管理的做法,也有学生表示不解:“有一次迟到,老师就要求我们给全班唱歌,结果因为我唱歌跑调,全班哄堂大笑,特别尴尬”(德硕G)。
学生认为,出现上述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教师在课上掌握着更为宽泛和绝对的权力。而德国教师通常对此管得不多。留学生L如是描述了她对硕士阶段师生关系的理解:
教师就像知识的推销者,学生是采购知识的顾客,师生之间其实是一种专业合作关系。研究生已经是成年人了,有能力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知识,如果有人不去听课,就说明他能承担学不到相应知识的后果,老师没必要干涉(德硕Mo)。
对此,受访的中方教师大多认为,至少在课堂上,教师理应拥有管理权。
我们知道研究生可以自主决定很多事,但受中国社会普遍观念的影响,还是会把研究生看成没跨入社会的大孩子,会对他们进行管理(Y老师)。
而且这种管理行为源自学校的规定:“学院有规定,所以我会管理出勤,包括是否迟到”(L老师);C老师也表示认同。受访教师认为在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通过课前小测验抓考勤行之有效,既避免了留学生旷课迟到,也考察了他们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至于这是否会让研究生感到不满,L老师坦言:
入乡随俗吧……他们既然选择来中国,就应该接受这里的一整套教育方法。学校的制度不可能去适应每一个人(L老师)。
也有教师表示,学校没有相关规定,所以不会记考勤,“毕竟他们有自己的学术文化”(K老师)。可见受访教师在这方面的行为方式既受到文化的影响,也与院校的规章制度直接相关。
2.即兴专业点评
德国硕士生觉得中方教师较少批评学生的专业观点。在德国,教师一般“会直接给出评价,有时会提建议”(德硕C)。“如果老师不知道答案,可能会说‘这个我也不确定,你自己查查,下次上课告诉大家’”(德硕Ma)。一旦学生跑题了,教师一般也会直言不讳。而中方教师的回应有时会“模棱两可,甚至不置可否”(德硕C),让研究生无从了解自己的回答是否准确。个别教师“甚至对我举手发言视而不见”(德硕Mo)。德国留学生觉得教师的“即兴点评能最好地体现出其专业水平”(德硕K),回避则适得其反。
对此,中方教师表示“一般会直接指出学生的错误”(M老师);还有教师觉得德国研究生的思维比较发散,“有时候天马行空,我一般不会生硬地指出”(C老师),“有些观点和课程的核心内容无关,我就不会纠结于这种问题,不然会耽误课程进度”(L老师)。有教师还表示,“有些答案不是唯一的”(Y老师),或者在“不确定德国学生的核心观点时,也可能一带而过”(K老师)。此外,有时不做点评“可能是不自觉而为之……或许是不愿意用对方的母语跟她们争论吧”(K老师)。使用德语授课的教师还谈到了专业外语的影响,认为它间接导致了自己即兴点评较少。K老师曾一度因为对专业外语缺乏自信而焦虑;Y老师也表示:“任课之前确实有点担心自己用专业德语能不能在争论时说服德国学生。”英语授课的三位教师虽然对此没有这么敏感,却也坦言,“语言是一个很大的束缚,用中文上课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讲段子,让学生既开心又专心,用外语就很难”(M老师)。
由此看来,教师是否进行细致的专业点评主要取决于该问题是否涉及课程的核心内容;另外,在专业外语上的不自信也会对此产生影响。事实上,德国硕士生并未对中方教师的外语水平不满。“中方教师当然不可能像德国教师专业语言那么娴熟,毕竟德语不是她们的母语”(德硕F),但“我们不是来学语言的”(德硕Ma)。因此,如果中方教师能抛开在专业语言方面的心理包袱,增加专业点评,不想做回应时交代原因,一定更有利于中外教学互动。
3.面对质疑或负面教学反馈的反应
C老师曾在课堂上受到德国研究生的质疑。当时她计划邀请一位校外专家作报告,结果由于专家的自身原因报告一拖再拖,这时就有德国研究生当堂提出质疑,“挺难堪的,我尽可能做了解释,这件事我印象很深”(C老师)。
K老师也谈到自己的一次教学安排曾因研究生的质疑而搁浅:
学生当面质疑老师的做法在德国大学并不罕见。虽然能理解,但被质疑时我心里仍旧很不舒服。我既没解释也没坚持,那个教学安排就这么搁浅了(K老师)。
但后来,研究生却又提出想恢复之前的安排,这让K老师意识到:
教师应该坚持自己的教学主张,尤其在跨文化教学中必须自信,在与德国学生见解不同时,应该据理力争(K老师)。
受访的德国研究生表示自己一般不会直接反对教师或表达不满,因为这会“伤害老师的面子”(德硕A),“在这里大家更看重面子”(德硕N)。
加尔滕对撒克逊式、条顿式、高卢式以及日式学术风格的显著特点进行了描述和对比。中德两种学术文化分别接近“日式”和“条顿式”风格,二者在以何种姿态面对其他学者的研究论断、借鉴他者和学术创新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19]。本研究的中方教师倾向于回避在专业问题上进行批判或与他人争辩,崇尚和谐并注重借鉴;而德国硕士生则更看重相互批判,更重视个性化思考,双方学术文化的差异可见一斑。
4.课下关怀
跨文化交际研究者特姆彭纳斯和托马斯分别提出“关系弥散型与关系特定型”的文化维度及“公私分区”的文化标准。德国文化更偏向关系特定型,不习惯将课上的师生关系扩散到私人领域,工作与生活、课上与课下的边界更加分明。就如同本研究中德国研究生的总体看法那样:“师生关系是教和学的关系,不应该进入私人层面”(德硕CL),否则会让人怀疑“教师评分的公正性”(德硕C)。而中国则讲究教师既要教书也要育人,要授业也要传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课上课下界限模糊,教师在课外也须关怀学生,并会得到学生的特别尊重。
不过,本研究的中德师生在跨文化互动中却偏离了上述论断。最初,基于对德国文化中诸如“关系特定型”及“公私分区”特点的了解,中方教师普遍认同“师生间是契约关系,不该掺杂私人感情”(M老师);“公私分明代表着职业素养”(L老师),因此刚参与德国硕士生教学时,老师们极少与德国研究生交流私人话题,但同时也觉察到了问题:
我感觉他们来中国生活学习,肯定很多东西不了解,生活上需要帮助,却又不确定自己应该怎么帮,该把握什么“度”,有时会有种“失范”的困惑(K老师)。
对此,当时的德国研究生也坦言,原本期待中方教师会更多地关心她们,“比如推荐几个好饭馆”(德硕Ma)或“组织大家聚餐”(德硕C1)等,但老师们却并没有这么做。经历了起初的迷惘后,有教师表示,虽然“还没找到确定的‘游戏规则’,但会主动就此和他们沟通”(Y老师);比如“在疫情中会帮助没有入境的德国学生登录学校网页,和中国同学建立联系等”(L老师)。德国研究生也逐渐“和老师有了默契”(德硕N),“遇到问题会找老师帮忙”(德硕Ma)。
四、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从跨文化互动视角入手所发现的中外师生在跨文化教学互动中遇到的实然问题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在教学内容方面,中外师生的分歧主要在于:课程设置的系统性、教学大纲的细致程度和计划性、教学资料的发放时间及教学内容的侧重点(如对前沿性专业理论的使用和教师专业实践经验的展示)。涉及教学方法和教师行为,中外师生均在协商的基础上做出妥协:中方教师逐步采用了互动型和协作型教学法,增加了对德国硕士生主体诉求的关注,同时保留了部分传统教学特色;德国研究生也适应了中方教师诸如单向知识输入的传统教学法。双方在教师管理行为上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
本研究中的中国高校教师与德国留学硕士生组成的跨文化教学实践共同体,在经历碰撞和摩擦时,借助微观层面的即时性在地协商,自我调整的同时部分保留自己的行为特点,使部分教学互动问题得到了理解或解决,保持着动态平衡。而其中的核心问题集中于教学内容,主要涉及专业水平的提升和常态化机制的构建。
为此在个人层面上,首先,中方教师应继续致力于用外语建构中国特色的专业话语体系,打磨全外语授课的专业课程,推动中国理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立足,同时须提升专业和外语自信;其次,中外师生有必要事先了解对方的学术文化特点、教学风格及可能遭遇的问题,以开放的心态即时协商,根据具体情境共同确立跨文化教学实践共同体的规则,并加以传承。组织层面则应提供保障,有效确保课程体系的系统性,尤其是设置以外语授课的诸如中国文化解读等辅助课程;建立中外高校交流平台,推进中外教育教学衔接;注重为全外语授课的涉外课程培养专业教学人才,为其提供深造机会;明确专业课教学大纲的内容与形式,确保其细致度与计划性;此外还可与国外高校共同建立线上、线下跨文化培训机制,提前调整外国留学生对中国高校学术文化的现实期待。
[1] 邱均平, 汤建民, 赵蓉英, 等. 2019—2020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前言.
[2]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课题组.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3[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69.
[3] 张艳宁, 李卫卫, 肖敏. 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构建及运行效果[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3(1): 39-46.
[4] 程立浩, 刘志民. “一带一路”倡议对来华留学的影响效应评估——兼论来华留学生教育高质量发展[J]. 高校教育管理, 2022(2): 110-124.
[5] 梅薏华, 任仲伟. 首批来华的德国留学生介绍[J]. 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 2006(2): 66-75.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教育处. 中德高教合作概况[EB/OL]. (2023-02-02). http://www.de-moe. org/article/read_one/1959.
[7] 陈丽, 袁雯静, 李爽. 范式转换视角下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对策研究[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8(9): 45-52.
[8] 齐忠方. 教育国际化视野下的留学生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研究[J]. 科技展望, 2016(35): 334.
[9] 刘水云. 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质量调查[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7(8): 26-31.
[10] 孔兰兰, 李新朝, 李瑾. 导师跨文化适应性指导对来华留学研究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J]. 高校教育管理, 2022(3): 68-79.
[11] 王丽娟, 吴陈, 李洪梅, 等.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中外教师教学方法比较[J]. 中国电力教育, 2012(10): 42-43.
[12] 李琼. 中外教师大学英语教学风格的比较研究[J]. 青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3): 102-104.
[13] 赵峰. 中外教师品格的比较研究[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2(9): 127-128.
[14] 王松, 刘长远. 跨文化沟通视域下研究生与导师关系质性研究[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0(6): 20-27.
[15] 罗恋梅, 沈帆, 范正阳, 等. 中外学生对教师不同素质的重视程度比较[J]. 卫生职业教育, 2020(9): 118-119.
[16] BARMEYER C. Konstruktives interkulturelles management[C].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8: 92-114.
[17] BARMEYER C, FRANKLIN P. Intercultural management: a case-based approach to achieving complementarity and synergy[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38-50.
[18] HOCHSCHULKONFERENZ S. Qualität in studium und lehre kompetenz——und wissensmanagement im steirischen hochschulraum[C].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6: 121-144.
[19]BOLTEN J, EHRHARDT E.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C]. Sternenfels: Verlag Wissenschaft & Praxis,2003: 151-192.
10.16750/j.adge.2023.10.011
赵倩,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9。
2018年度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中外师生教学互动中大学德语专业教师之角色协商”(编号:2018JJ008)
(责任编辑 黄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