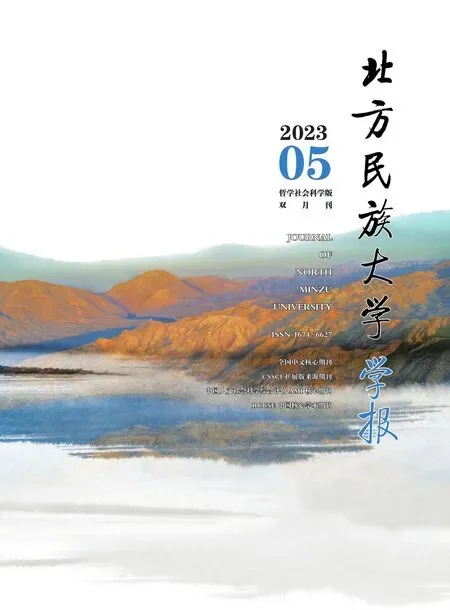道路、空间与文化图式
——基于湘西边城的民族志研究
2024-01-03彭秀祝刘重麟
彭秀祝,刘重麟
(1.吉首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2.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一、问题的提出
列维-斯特劳斯曾言:“现代道路的修建,也意味着孤立民族志研究传统的终结。”[1]赫茨菲尔德甚至指出,很多人类学家因此而出现了“道路恐惧症”[2](270)。然而,道路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很常见的基础设施,是民族志研究难以回避之物。毫不夸张地说,在现代交通快速发展的今天,文化接触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具有归属感、联结感和历史感的“人类学之地”越来越少[3](41~60)。马克·欧杰通过对比巴黎的传统道路和现代道路发现,那些传统道路规划线路上的交会点通常是社会关系密集的空间,现今的公路、隧道、立交桥、机场、地铁站等则是“非地方”(Non-place),“非地方”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流动性,因为难以聚集足够的地方意义,所以成了超现代性的生活体验空间[3](37)。具体来说,“非地方”指的是后现代社会中那些格式化、标准化,因追求速度和效益而失去了深度社会关系交集的空间。“非地方”是一个历史感逐渐消解和社会关系疏远的场所,代之而起的则是不确定性和切身的差异性。
虽然“非地方”有着很大的理论潜力可挖,但并未引起国内路学研究者的足够关注。周永明在《路学:道路、空间与文化》一书中将其翻译为“虚无场所”[4](22),并对此进行了解读。遗憾的是,后续的研究缺乏相关实证分析与阐述。同样着眼于道路的高速流动性特质,路学研究者更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背景材料或基础设施而讨论与之关联的生计转型[5]、族群互动[6]和聚落变迁[7]等。当然,不同学者基于自身的理论偏好给出了道路研究的思路:一是将道路视为一个兼具时间性、空间性、开放性和移动性的特殊空间;二是将道路视为一种区域研究窗口,尝试以“路域”讨论族群互动等议题;三是将道路看作一种流动的空间,关注道路网络及其节点上人和物的流动。
道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种可视、可感的物,它同样承载着丰富的内容。马克·欧杰以道路交通作为视点提出“非地方”这一概念,用以总结后现代社会中高速流动、空间过量和同质化等社会特征。尽管上述研究对路有了充分考察,可在以下两个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一是将过多目光聚焦于实体道路的社会经济意义生产上,缺乏对“虚体之路”和道路文化图式的研究。作为个体储存文化背景的知识,以及协助理解文化经历和文化表达的文化图式[8],道路涵盖了习俗、传统、民俗及文化象征秩序等[9]。人们先验存在的道路文化知识和图像结构并未被置于重要地位予以考量。二是“非地方”概念的运用不应该局限于线性的描述思维和“地方—非地方”二元对立分析框架,而更应该注重传统元素和现代性元素在“非地方”场所中碰撞和调适的过程。
本文研究的田野点为边城,又名茶峒,它位于湘黔渝交界之地,因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而为人所知。2021年年末,边城总人口24 680人,其中苗族占41%,汉族占40%,土家族占19%①该数据来源于花垣县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清代,边城因水路运输而兴起集市,因“苗防”战事而筑路修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修筑的湘川公路穿越此地,边城因地理位置缘故,一时间成为湘黔渝界邻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20 世纪80年代修筑的319国道,2012年修通的吉茶高速公路,以及近几年的多条旅游公路规划,使得边城出现了许多具有“非地方”特征的场所,它们同样具有高流动和标准化等特质,但也被注入地方文化。笔者于2019—2021 年在边城做了近一年的田野调查,针对道路交通和地方感进行了专题研究。本文借由边城的公路、隧道、街道和停车场等具体地点试图阐明一个基本观点:在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和人口快速流动背景下,从“地方”到“非地方”的变化也是道路文化图式调整的过程,那些具有“非地方”特质的场所不仅是现代化和标准化的象征,它们同样沉淀着文化秩序、社会关系和历史记忆。
二、实体道路与社会转型
道路交通状况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运转情况的重要指标。施坚雅指出,一个被现代道路绕开的集市,很难发展成为现代市镇[10](102)。申言之,一条实体道路的走向和运行状况会对聚落空间格局以及地方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形塑作用。若以实体道路去观察边城社会发展历程,会发现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水路运输和市场兴起时期;水陆并行时期;水路运输式微和依托公路转型时期。
明清时期,湘西地区的道路修筑主要与王朝治理有关。严如熤在《苗防备览·道路》一书中这样说道:“转输军实,必曰水陆交通。”[11](293)凌纯声等也曾指出:“苗疆自明中叶以至清初,历代用兵。官兵防守,最重要的是运兵输粮的交通。故在本区内,对道路桥梁的修筑,呈一巨观。”[12](37)清中后期,边城不仅是苗疆边地的重要治所,也是道路交通网络的一个节点。边城的集市依托酉水河运之便利,能连接洞庭湖和长江水运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湘黔渝界邻地区的重要物资中转码头和贸易集散地。当地的商人将土特产(桐油、药材、木材、豆子等)用船或木排运载到常德等地出售,又将下游的棉花、纱、布匹、铁、盐、糖等运到边城销售。比如,侯姓商户在其鼎盛时期,有几十条商船往返于河道之上[13](136)。可以说,水路运输奠定了边城作为湘黔渝三地边贸集散中心的地位。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因战略布局考虑,修通了湘川公路。这条公路起于沅陵和辰溪之间的三角坪,经泸溪、所里(今吉首)、永绥(今花垣)到达边城,全长187.66公里[14](95~98)。边城通车之初,汽车从老隧道穿过,至西门码头,搭载轮渡过河进入重庆[13](136)。从当地的文史资料记载看,现代公路加速了边城人口的流动和商品交换,但并未冲击水路运输的主导地位。抗日战争时期,内地商人、公教人员及其他难民纷纷涌入边城。《西南公路》刊载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从五月西南公路公务局成立茶峒桥公处和七月茶峒师范迁来以后,人口增加了六七百。因之物价会有小小的波动。”[15]外来人员为当地市场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出现了“逆反现象”。常德、长沙、汉口等地的客商纷纷在茶峒设点开店,据统计,各类商号、店铺、旅社等共计102家,船舶木排停靠在上下码头,塞断河流,每日犹如在赶集[13](136)。另外,根据当地文史资料记载:“每天数十只货船,排列在花垣河水两岸;百余辆汽车,驰骋于川湘公路间。”[16](156)大量外商的进入刺激了当地商户,加快了桐油、盐和棉花等商品的交易。在这一时期,贵重商品和急需应市的紧俏物资多数是用车运输,只有那些笨重的“上货”以及桐油、碱、五倍子等“下货”才用船运输。由此可见,在原来的水路运输基础上,公路大大加速了人和物的流动,更大限度地实现了信息的共享和商品的交换。
20 世纪50—70 年代,河道上下游修建了大量的水库和电站,水路运输受阻,边城市场出现了萧条。据统计,1988 年319 国道贯通后,在水陆运输总量中,公路货运量和客运量分别占94.6%和97.85%[17](42)。至此,水路运输基本被公路取代。近20 年,边城依托国道和高速公路大力发展旅游业。2008 年,边城景区被国家旅游局评为3A 级旅游景区,当年接待游客超过40 万人次。2016 年,边城成功入选中国特色小镇,当年接待游客逾100万人次。原本依靠集市谋生的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旅游业,客栈、餐馆、酒吧、游船等商业活动兴起。2017 年,为了推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319 国道开始升级改造。边城借国道改线之机设立了曲乐新区,并在此地规划了大型停车场。交通堵塞和人流量过大是国道改线的主要因素,此前集市主要集中在沿河的几条街道上,后来赶集地点搬迁至319国道附近,人与物在公路上大量聚集,导致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
现代公路的修建也是景观重组和聚落空间结构调整的过程。雷尔夫曾言:“公路、铁路和机场将景观切割了开来,对景观横加干涉,却并没有让景观本身得到发展……非本地的人造事物与外来的信息像洪水一般袭来,令地方性失去了自身的意义。”[18](144~145)伴随现代公路的修建,多样化的景观和饱含历史感、归属感的“地方”正在消失,这也意味着我们自己也在不断遭受“非地方”的冲击,逐渐失去了原本具有的地方感。时至今日,边城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不再经由水道运输。依托湘川公路和319国道修建的店铺不断增加,集市也从河边挪到了公路上。到了21世纪,政府着力发展旅游业,并将边城作为宣传地方的名片。在这种背景下,边城开始从传统集市转变为旅游小镇。边城因水路运输而兴,早期的聚落分布多集中于酉水河道两岸,人们“逐水而居”的历史也在当地的文化图景中有所展现,白龙传说、“玉带环腰”格局均与此相关。20世纪30年代以来,湘川公路的修筑不仅重塑了边城的聚落格局和空间秩序,当地人对路的认知结构和文化图式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转变。
从道路的实体层面来看,边城大致经历了“逐水而居”“逐路而居”的历史过程。现代公路“非地方”元素的进入使得原本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聚落空间秩序、市场辐射范围和民间信仰等不得不重新调整。综合而言,“非地方”场所对地方性的改变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快速流动。实体道路的通达为人、商品、信息等的快速流动和交换提供了场域。道路基础设施及新型交通工具不仅为边城的人群交往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国道、高速公路和周边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人群流动,地方与“非地方”要素不断汇聚联结,由此,边城进入更大的政治经济网络之中。二是时空压缩。快速交通所带来的空间过量和时间过量的问题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时空的感知。民国时期,由边城去往重庆和长沙大约需要半个月时间,而今乘坐高铁只需要3小时左右。因此,时空压缩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地方”意义的消除。三是场所的标准化和同质化。依托现代公路而建的客栈、停车场、酒吧、农贸市场等场所成为人群聚散之地,但这些场所更多地被陌生人和外地人使用,地方的社会关系难以在上述场所聚集。简言之,“非地方”及其连带的场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人们快速抛离原有的社会轨道,并以一种高效和标准化的方式将边城整合进广阔的网络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意义并非就此消散,而是以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存活”于“非地方”场所。“非地方”对地方性的改变也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并联结。
三、道路隐喻与文化图式
道路充满隐喻,并且与文化图式相关联。德格洛珀通过考察台湾地区鹿港镇的移民历史及社会转型历程发现,道路沉淀着地方文化秩序[19](60)。吴重庆认为道路犹如基层社会有机体的血脉经络,把相对独立的村落连接为跨聚居单元的经济(市场)区域和文化圈,道路其实隐喻着“权力的文化网络”[20](111)。实体道路类型和使用状况的变化反映了边城社会转型,与之相关的文化图式也出现了调整,从“玉带环腰”到“镰刀煞”的风水格局转变可视为道路文化图式转换的体现。
(一)“玉带环腰”与文化图景
茶峒古城三面环山,当地人将古城比喻为一张太师椅,西南方向的崔龙山为青龙,东北方向的马鞍山为白虎,酉水河从西边环绕而过,古城如同玉带,人们用“玉带环腰”形容此番风水格局。
“玉带环腰”与一则神话故事相关。相传在远古时期,有一条白龙从西边飞到边城,给当地带来了丰沛的雨水,大地得到滋养,土地愈加肥沃,人口得以繁衍。白龙产下了9条小龙,后来化作九龙坡,白龙则变成了酉水河,当地人称其为白河。白河的一处水源在边城的八排悬崖,悬崖上有一个洞,传说是白龙栖居之地。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包括边城在内的十几个村落社区都会派人到此地祭谷,以求风调雨顺。早在道光十年(1830)就有人在洞口题了“沛降济民”四字。神话故事见于人们的口述和地方文本中,然而真正构成人们感知的存在,还得聚焦于具体之物。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地人在述说九龙坡时,经常会将它与天气预报联系在一起。白龙传说、“沛降济民”“九龙施雨”等构成了边城人关于“玉带环腰”这一格局的叙事元素,它们同样反映出当地人水崇拜的文化特质。
“玉带环腰”文化图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酉水回澜。近年来,随着边城旅游业的发展和社会转型,酉水回澜之景被包装成一个卖点。1975年,由于上游修建红卫水库,河流水位下降,加之20世纪90 年代周边地区开采矿业,地表水下渗严重,河道水位进一步落低,此前的酉水回澜之景消失不见。21 世纪初,为了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酉水回澜之景的规划被再次提及,并且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为了符合沈从文《边城》的文学叙事,当地人建造了翠翠岛(原本为沙丘),并在该岛下游建造了一个堤坝,将原来的两条小河之水引入此处,以成回澜之景。酉水河道(或白河)被当地人视为具有吉祥和富贵寓意的“玉带”而进入风水神话中。“玉带环腰”体现了当地物质元素与精神内容的融通,它沉淀着地方历史记忆和文化秩序,是人们追求富足生活、获得福祉和远离灾难的理想文化图景。
酉水河道曾是边城聚落形成、集市兴起和人群汇聚的基础,它被人们勾勒成了“玉带环腰”文化图像,与此相关的神话故事仍存留于当下人们的记忆之中。公路建设改变了当地的聚落形态,集市地点也从原来的河边挪至国道附近。原本在河街附近谋生的小商小贩受到很大冲击。在旅游业的带动下,景区入口附近接连规划了茶峒隧道、停车场和从文路。吊诡的是,这些颇具现代化和高流动性的场所却成为当地人口中的“不祥之地”,与路相关的“镰刀煞”故事开始浮现。
(二)隧道与“镰刀煞”
2009年,出于旅游建设的需要,当地政府着手改善当地交通拥堵问题,试图将319国道与河边的老街连通,于是规划了一条新路,取名“从文路”。自此以后,三条主干道也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在不少边城人看来,从文路完工之时也是整个古镇“镰刀煞”风水格局定型之日。
“镰刀煞”形容的是道路的凶恶之状。在风水理念中,当一条或多条道路犹如弓一样对着房屋和村落时,则会形成煞。当地人认为,这可能会招致血光之灾,家庭和村落的运势会因此变坏。观察边城的道路系统会发现,从文路犹如一把弓,从茶峒小学开始蜿蜒而行,直至茶洪大桥;319 国道像一根箭弦;湘川公路的老路段则似一根箭,这把弓箭所指的地方则是茶峒古街。
从“镰刀煞”的形态看,它形成的关键点在崔龙山头。修筑隧道时,原计划将该山头挖掉,但遭到了当地人的反对。有人认为挖掉崔龙山头会损害龙脉,整个边城人都得倒霉。面对此类说法,工程负责人并不理睬。可在施工队要动工时,一群人突然出现在工地上,并躺在挖掘机前阻止动工。双方僵持不下,最后,一位老干部道明了缘由。当然,他并未用风水之说来劝阻工作人员,而是从地理学角度指出了崔龙山头的价值。他认为该山头延伸进入白河中,起到了阻洪的作用,如果挖掉,一旦发生洪水,大水将直接冲进古镇核心街道,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他的劝阻收到了很大效果,原本的劈山修路计划被停止,进而改为修隧道。
2009 年秋季茶峒隧道凿通,巧合的是,“邪事”也在这个时间点频频出现。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先后发生4起交通事故,死了8个人,而且每次车祸死的人都是成双成对。死者中,要么是父子,要么是夫妻,这种事故被视为“绝后”。一时间,人心惶惶,甚至传出谣言说:“要死满18 人!”在恐惧和抱怨中,人们开始将其归罪于隧道工程。这件事即便过去了十几年,很多人回想起来仍充满恐惧。令人不解的是,人们为什么会将事故原因归结到修路凿隧道。这原本是一件利民工程,却引起了恐慌。调查发现,凿隧道与一连串车祸发生的时间靠近,而且隧道的地点很特殊。当地一位道士告诉笔者,隧道背后的小山丘像一只乌龟趴在河边喝水,这样的风水格局本来是很好的,有着吸财进宝的象征,但是隧道偏偏修在了乌龟嘴巴上,断了茶峒人的财路,整个城的风水也遭到了破坏。从当地人的解释可知,他们表面上用风水、神鬼来解释车祸发生的原因,实际上是在发泄内心的不满。
为何当地人要将财路和隧道联系起来?一方面,隧道工程确实与当地人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修隧道对于突破地理阻隔有着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小山丘阻挡茶峒古镇核心区域与319国道的连接,对茶峒和重庆洪安镇的居民生活非常不便,而隧道的修通可以将河街、从文路和319国道连为一体。此外,凿隧道也是当地集市搬迁计划的一部分,在此之前,集市一直在河街,农历逢五逢十,便有成千上万的人来此地赶集,热闹非凡,然而,人流量过大导致了交通堵塞问题。因此,当地政府决定将集市搬到319国道附近,并将河街规划为核心景区。从古镇的开发和建设来看,这些举措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出现了新的矛盾,即集市的搬迁和旅游开发的滞后。核心景区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旅游开发而受益,相反,市场的搬离和景区的隔离让很多人断了财路。面对这些负面影响,当地人将根源归咎于隧道的修建,并用“镰刀煞”和金龟吸财等风水之说加以解释。
在风水理念中,道路上车与人的流动、道路的形状都会影响住宅的吉凶,风水吉利的道路可以招财,有利于事业的发展;风水不祥的道路容易招致意外事故、破财之灾等。煞,常见于风水学中,分为有形煞和无形煞,其中有形煞指的是那些可视之物,例如,道路、电线杆、桥梁等;无形煞多指我们无法看见,但能通过器官感受到的气味和声音等。细而分之,煞大约有30 多种,其中有6 种煞与道路走向密切相关,它们分别是“镰刀煞”“枪煞”“穿心煞”“冲背煞”“斜枪煞”和“剪刀煞”。路是人与物流动的载体,煞则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不幸或意外时,无法用科学解释时,转而寻求风水知识来慰藉。
在边城传统社会中,人们喜欢聚族而居,建房也会避开风口位置,其实这是一种寻求安全感的反映。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倾向于“逐路而居”,将房子修建在路口或者多路交叉地带,这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路上行人和车的干扰。因此,路的交会地段成了是非之地。这里的“煞”其实是秩序失衡的表现,人们用“煞”这样颇具玄学色彩的东西去解释,实则是对道路所带来的困扰的文化构建。
(三)修路平坟与阴阳之隔
茶峒隧道是319 国道与从文路的连接点,从贵州、重庆来的游客均要通过此道进入茶峒古城。当地旅游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对隧道两侧进行了改造,还请人题了“茶峒”二字,铭刻于隧道之上。当下,这个隧道俨然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地标,来到茶峒古城的游客多半会在此驻足拍照以作留念。在从文路未修之前,茶峒古城的居民集中分布于隘门口和水井湾一带,即崔龙山和香炉山环绕下的“窝坨地”。道路修通以后,从文路与国道连接,河边的居民和外地人向这条路上集中,成为茶峒古城最重要的街道,崔龙山头两侧街道的人气渐长。
在当地人的文化认知中,崔龙山头是生与死的重要分界点,一侧是人口密集分布区域,也是古城的核心地带,另一侧是坟墓区。现在这些坟墓被铲掉,原址上修建了客栈、餐馆和停车场。根据当地ZH 道士的估算,被铲掉的坟墓数量在200 座左右。部分老坟无人认领,直接被铲掉;部分坟墓则属于新坟,需要给予一定的补偿款迁移,一般在4 000—5 000元。墓地是死人的栖居之地,房屋则是活人的栖居场所;墓地属于阴气聚集之地,民居密集区属阳,阴阳相对使人们有了文化上的区分。关于墓地的性质同样有区分,即便属于同一片墓区,因死亡年龄、死亡方式的差异,下葬点也会有所不同,故而,墓区又被分割为多个模块。例如,正常死亡的人一般埋在崔龙山延伸地带,坐东朝西向;非正常死亡的人,集中埋葬在靠南的小凹地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这是传统阴阳观念在现代社会的延续。以坟为重要观察点,它反映的是一种阴阳之隔和人们的恐惧之感。段义孚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坟地通常在村边或外面,它位于活人居住的阳界边缘,是通往死人所在的阴界出口[21](103)。通常来说,坟被视为亡灵的居所,人们在选择墓地时,都会放在生者的生活空间之外。坟不仅是人鬼间的边界之地,也与人们的情感相关。华如璧曾指出,在中国,对于崇拜祖先的人群来说,对亡者的安置是与风水观念相关联的,亡者的尸体被认为是力量与复兴的来源,拥有来自自然的力量,因此,若坟穴的位置与尸体安置方式得当,能与龙脉相合,祖先的灵魂得以安抚,从而去除其可能对后代造成的危害,还能护佑后代的繁盛[22](203~227)。申言之,如果坟地位置不当,或遭到外力的改变,那么就有可能影响后代的运势。在边城地区的道路规划和修建过程中,有些坟墓被夷平或迁移。国家自上而下进行的筑路工程改变了当地的信仰空间格局。当地人认为,筑路过程中的迁坟、铲坟等行为让“鬼”失去了栖居场所,它们因此变得不安分,四处游移,并进入活人的生活区域。阴阳二元是中国文化和宇宙观的重要观念,阳间被视为活人居住的场所,阴间则被视为人死之后鬼魂的归宿和神灵所在的世界,阴间是阳间的反面,彼此相依才能相互界定。芮马丁对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当地人认为他们在阴间都有对应的房子和树,这些物的状况与他们在阳间的身体状况相联系[23](237~244)。正如“阴阳一路隔”和“阴阳失衡”所暗喻的那般,阴阳之间并不遥远。坟地所连带的阴间不仅与祖先、人死后的世界有关,也与阳间人的活动相联系。阴间虽然在某些时刻给人造成了心理阴影,是人生的终点和人们不愿触及的存在,但它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阴间与阳间既近又远,彼此相异但又平行存在。当我们在看待道路背后的“玉带环腰”“镰刀煞”“阴阳之隔”等文化图像时,不能简单地将之以好和坏进行区分,而更应该注意的是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外来等内容如何在道路场域中相遇、碰撞和融合。从“玉带环腰”到“镰刀煞”,其实是道路“实”与“虚”的生动展现,其暗含着边城由水路到公路转型的历史过程及其连带的社会问题,也是不同类型道路文化图景的展示和变化。
四、结 论
“非地方”概念的引入有益于全面把握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脉搏,而马克·欧杰将目光聚焦于流动性上,忽视了对地方社会结构“打破—重组”过程的分析,其中所涵盖的文化图式及其转变方式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事实上,很多快速流动和交通网络的节点同样能成为文化意义的汇聚之地,而并不是“非地方”[24]。马斯奎勒也认为现代公路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非地方”,而是一个风险与机遇、恐惧与欲望并存的混合空间[25],换言之,地方文化图式和象征体系仍然在现代公路场域中运行和实践。边城因酉水河道而兴起,因湘川公路而繁荣,水路与公路的交会及其使用状况的变化是理解当地社会转型的一个窗口,可以说,由水路到公路的转型是实体道路社会意义生产的过程体现。在实体道路研究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延伸讨论的是道路的虚体含义。研究认为,道路是地方社会记忆和人们情感认同的储存器。边城风水格局“玉带环腰”“镰刀煞”和“阴阳之隔”的变化正好说明了道路文化图式的转换,借此也构成了路之虚体意义的解读:道路修建融合了文化与自然的秩序,是人们直接体验世界的意义场所。
路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字眼,在汉语中单独使用时指街道和道路的名称及其本身,当它被赋予隐喻意义时,则指一种哲学遗产,具有更广阔的含义,这个字就是“道”[26](18)。道路经过边城所带来的转型不仅呈现在其社会经济意义生成层面,它也会浸入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为不同族群理解其共有精神家园的窗口。现代公路在推动人与物快速聚散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个标准化和充满流动性的“非地方”。人们在面临公路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的时候,对某些地点的恐惧之感也逐渐浮现出来。现代社会中宽阔的街道和疾驰的汽车有时也会造成混乱,使得道路的使用者迷失方向。诚如段义孚所言:“人们对有些街道产生恐惧,是因为这些地方被认为有鬼怪、巫婆、盗贼等出没。”[21](4)在边城社会中,那些充满“非地方”特质的街道、隧道、停车场、客栈多是人和车快速流动和汇聚之地。道路规划原本是为了矫正聚落中存在的混乱和失序问题,但间接造成了风水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调整,进而成为神、鬼和煞的叙事题材。毋庸讳言,得益于道路的通达,边城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网络之中,但人口流动的加速导致地方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现代公路所营造的“非地方”并非全然没有历史感的场所或景观,相反,传统社会中的文化图式和文化秩序仍沉潜其中,并在这些充满现代性的“非地方”场所发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