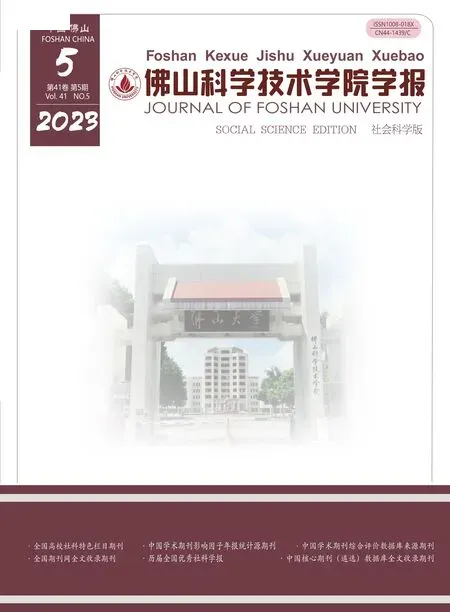从“离身”到“具身”:关于身体在教育中复归的审思
2024-01-02徐瑞萍曾嬿桐
徐瑞萍,曾嬿桐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
人类原始的教育活动是基于身体的技能传授和习俗承继,是“根身性的教育”。在近代教育的发展中,受传统主客二分哲学的身体观念的影响,身体与教育学之间潜含着一种互不关涉的隐喻,教育趋向于离身(disembodied)。离身教育强调对学生进行“灌输式”的理念培养和“训练式”的心智培训,身体只是心智(mind)的“容器”。近年来,随着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发展,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Embodiment Cognition)将身体从与教育割裂的关系中抽出,开辟性地重塑了心智、身体与环境三者之关系,为具身教育、具身学习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审视和实践诉求。本文尝试从传统“离身教育”的困厄出发,立足具身认知理论,对身体在教育中的复归进行新的审思。
一、从“离身之教”到“具身之教”
教育从“离身”到“具身”的演变,首先从哲学领域开始对身心二分论进行批判,在现象学领域形成进一步思考,继而发展至心理学领域,近年来被引至教育学,在教育领域备受关注。具身认知理论系统地重塑了教育中的“身体在场”关系,使教育的身体面向成为可能。具身教育具有具身性在场、情境性统一、创生性发展和体验性延伸等四大特征。其中,具身性在场作为其根本特征,是其区别于离身教育的本质;情境性统一与创生性发展基于具身性并蕴含于具身性中,而体验性延伸是具身性在场特征的新进展。
(一)教育的身体转向意蕴
自柏拉图以降,“灵魂在上,身体在下”的观点问世,并逐步走至西方哲学的正殿。他认为灵魂是人的核心,身体与灵魂是两分的,身体无法认识世界。这种观点被移植到教育中,从此身体遁退至教育之纯物质实体的位置。虽然柏拉图认为心灵在身体之上,但他并未将身体与心灵置于两立。中世纪时,基督教基于柏拉图身心两分的主张继续拔高灵魂的存在意义,身体非但无法理解与探索世界,而且还阻碍着灵魂与世界相联系,因此“节欲令”降生,身体在教育领域遭到贬损与规训。勒内·笛卡尔将“身心二分体”观发扬光大,让灵魂与身体完全处于互相孤立的状态,身体降格为心智产生的“容器”和载体,教育被认为是纯粹心智的活动。“身心二分”对传统西方哲学与认知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 世纪以来,一批来自现象学派的哲学家们打破了这种对立。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在反思已有的认知理论的缺陷中对身心二元论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在此之前,身体哲学已开始受到关注。尼采将身体视为权力意志,坍塌了西方的宗教信仰,把身体从受压抑的状态中唤醒。福柯继承了尼采的身体谱系学,在权力与话语中对身体做出诠释。现象学的出现彻底崩塌了身心二分观,身体存在论重回教育的舞台。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真正开始把身体作为教育的主体,确立了身体对心智的塑造作用。他的“肉身化的身体”颠覆了传统的“意识主体”,解释了身体在认知与学习中的前提作用。身体是知觉的主体,是认知的工具与手段。教育从此重新面向身体,从受“规训”与“惩罚”的位置被重新召回和肯定。
(二)具身教育的特征
1.具身性在场
身体的在场是教育教学的首要前提,教师是课堂教学的重要主体之一,教师的亲身参与凸显了具身性在场的意义。具身性是具身教育的本质特征,具身认知理论根植于身、心、环境三者融为一体的原则,强调教师与学生的心智“嵌入”身体,身体融入环境,其中身体是必要基础和前提。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于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1]112-114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的亲身体验者,体现于各个教育场域中。在师生个体层面,教育教学的内容表现在教师授课的肢体语言、表情神态、口语表达和气质特征,涵括于学生听讲的感知觉调动、情绪体验、姿态动作和行为倾向;在教学环境层面,教师的身体与世界的联系影响着教师的认知过程、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进而影响课堂教学的任务设置、内容架构、组织管理与评价机制体系。
2.情境性统一
在具身认知理论看来,认知是“认知主体与环境之间的有机性、创造性以及生成性的交互作用”。[2]情境性的统一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因素,教学实践对教师与学生的人格成长影响重大,并继而对社会大众的道德意识、情感和意志等心智表现有规范作用,具有深刻的情境性。教师的以身作则、耳濡目染的行为态度和精神引导通过教学实践对学生进行情感、文化、态度和价值的传递。在教育教学中,除了学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等显性教育外,教师对学生的关注鼓励、对同事的相互扶持、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等潜在教学情境在学生的价值联结上愈来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教育的情境性统一有助于学生完整、健康人格的造就,从而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3.创生性发展
智利认知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等人用生成性来强调,认知不是一个预先给予的心智对独立于知觉者之外的世界的表征,而是知觉者以此在的、具身的方式的生成。[3]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在实践的过程中构建了创生性特征。“身体为环境与认知的生成、交流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媒介,将认知与环境有效连接在一起,能够保证认知在身体的实践中不断生成,身体这一有机体对于认知的生成具有决定性意义”。[4]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认知学习发生在不同的教育教学场域中,并且由于教育场域和学生个体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教育教学具有浓厚的创生性,兼容了不同教师的教学情感、教学方式、教学组织形式与教学观念。在具身教育中,教师在多变的教学场域和千姿百态的教学对象中创造出不同的教育教学内容,这不仅反映了教师的教育理念,还不断延伸至教师的社会生活中。具身教学实践在教师的创新性思维和教学行动中得到展现,为教师的教学开发提供了创生性可能。
4.体验性延伸
体验性延伸是具身教学特征的新发展。每个时代皆有以区分于其他时代的典型特征,若将中世纪作为信仰时代,近代为科学时代,那么现代则是体验时代。具身教育理论强调,学生以自然的身心状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通过具身交互和知觉体验进行学习,实现技术与身体、环境、资源等要素的耦合和动态演化。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技术与身体的关系受到关注。在《技术中的身体》(Bodies in Technology)的导言中,唐·伊德将“身体”区分为身体一(body one)和身体二(body two):前者指一种现象学所理解的定域化、动机化、知觉化和情感化的“在世存在”,它是我们之所是的身体;后者指我们在社会和文化中所经验的“身体”,它是一种身体化的意义空间。在他看来,联结身体一和身体二的是一种技术化的第三维度,即作为一种技术而存在的具身关系。[5]具身环境下的体验式教学并非技术、教学、学生、教师这些元素的机械叠加,而是一个多要素耦合且动态生成的过程。在现代教学实践中,依托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数字孪生、元宇宙等虚拟实体化技术实施教育教学实践,有效促进了教育教学的体验性延伸。学生置于虚拟沉浸式的教学场景与情境当中,“虚拟身体”赋予学生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多向扩展,再造和重塑了学生的身体,提高了身体参与程度与体验感,有助于学生与抽象概念和空洞理论之间产生更宽泛、更深刻、更多元的交互融合。
二、身体在教育中的隐喻与缺失
在二元论的影响下,认知与身体是对立性的、相孤立的,在此之下的教育是“离身”的。离身教育在教学认识论上受到“以心代身”的挟制,师生被视为“去身体化”的“合理人”。在教学方法论上以“以心训心”作为教条,使教育沦陷于“去生命化”的僵局。“我-他”教学关系的对立与情境化的沦陷忽视了学生身体的情感体验、价值传递与感知觉运动,这种困缚了思维与潜能发展的“去人性化”的倾向,体现出传统教育观与学习观的“预设”。
(一)教学认识论:“以心代身”的挟制
传统认知科学坚守“身心二分论”立场,认为感知活动与心理过程即是计算机的运算过程,构建了“人脑类似计算机”的隐喻,主张认知是不涉情境的抽象符号的表征过程和加工模式,与身体无关。“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二元论思想的广泛影响,认知被认为是一种人所独有的、单纯的理性过程,认知活动也就处于一种离身的认知状态:人的身体、活动和内在经验被排除,认知过程只是对符号、信息的加工与处理,人作为认知主体的感知活动、情绪体验、身体的参与等要素都让位于抽象符号的加工。”[6]这在传统教学中容易让教师过于注重学生的心智训练和理论传授,使学生陷入与身体实践和生活经验相背驰的“傀儡式”空间。学生以设想、思索、忖量和评介替代感觉,并非潜心专注于身体的感觉。譬如,在课堂教学中,当教师讲解学习近代散文诗时,应使用有感情诵读的方法,这样利于发挥语言文字本身的感染力,能充分调动受教育者的感官参与认知,有助于学习与记忆。受教育者也深感此种方法在散文学习中的重要意义,然而他们并未亲身进行诵读,只是大脑中存有这种方法有利于学习的初步认知,其本质是以心灵的预想替代实际的体验。
在“以心代身”固化思维的禁锢之下,教师作为“去身体化”的理性存在出现,情感与经验消匿在逻辑推导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以心智的参与代替身体的出席,知识只是符号和客观事物的镜面映像与外在反映,认知仅发生于“脖颈”之上。在知识和身体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意识至上的心智观贯彻到教育中,心智就成为一种发生于大脑的中枢过程,与身体无涉。学校因此成为培养心智、规训身体的精神训练营。[7]教师秉持“以教育者为中心”“教会学生知识”“重结论轻过程”以及“关注学科”等程序化、脚本化和模式化的教学观,难以向“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学生学会学习”“重结论更重过程”及“关注人”的合理转化。教师在设计教学与实施教育教学组织管理上忽视学生的身体活动、情感体验与感知觉运动,易致使教学陷入身心分离、主客对立、知行不合的尴尬局面。
(二)教学方法论:“以心训心”的僵化
在理性主义和本位主义的裹挟下,现代教育较注重精神培育而对身体“在场”进行遮蔽与贬抑。“教育与教学的目标定位在促进认知发展、提高心智能力。这种目标定位是在忽略身体甚至是压抑身体。在这种背景下,学生们活生生、活动的身体被认为具有破坏性,甚至是一种麻烦……心智给我们带来知识,身体却是在吸取教训,需要加以驯服……”[8]教学的目的偏离,只向学生传授精致知识,从而产生“合理人”。长期以来,灌输式教学消解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使学生困于狭小的“木偶戏剧”当中,变得刻板木讷,缺乏生气。教师过分关注基础的、理论的和系统的传授,学生具体实践中“动手”时的经验、感知、情绪被淡化;过度强调外力干预的效用,学生的身体时空被“人设化”,以至他们的精神绿源开始断流与枯涸;过分地要求一致,麻木了思维,钝化了想法,设计了道路,否弃了个性,致使人生道路转入轨道,而不是旷野。在学校教学场域中,学生的身体让位于教学目标与任务。在传统教学中,学生的身体始终处于被束缚、被克制的状态。部分课堂之上,教师往往过多关注学生的听姿、坐姿而忽视课堂本身。“以心训心”将学生的身体体验与感知觉活动隔绝于课堂之外,学生从此不再以一个独立意义上的人的身份出现,独立个体的生命特质在线性的教学范式中被隐没。
(三)教学关系:“我-他”关系的对立
在传统教学范式中,课堂话语权归于教师,课堂丧失了对话的旨归和意蕴。学生被置于教师“绝对权威”的权力话语之下,教学沦为教师的个人旁白与表演。这导致教学关系长期以来异化为主客关系,教师始终以主宰者的身份出现,学生是教师意志的绝对服从者。教师将学生的身体感受、感知觉活动与情绪体验排斥于课堂之外,造成孤立的“我-他”主客对立关系。在“我-他”关系中,师生关系是纯粹的思想交涉与灵魂对接,而不是容纳身体的身体交互。
在奥地利-以色列-犹太人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对话哲学视野下,世界处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世界存在两种关系。其一为“我-你”关系,这种关系是最纯粹的、最实质的,我与你的相遇出于本真,不带有双方的目的与需求。其二为“我-他”关系,人被置于“我-他”世界中,我为主体,他为客体,他只是被我经验与利用的对象。这种关系犹如传统教学范式中的师生关系,教师以“自有生命体”的我出现,对学生的身体进行驯服与限制。教师重视认知训练与知识“灌输”,瓦解学生的身体活动体验,忽视师生的身体互动与沟通,从而啃噬学生的经验、情感与感知觉。在传统课堂中,身体的参与、经验的进入与主体的感知受到贬损,师生关系深陷于相互孤立的“我-他”僵局。
(四)教学思维:情境化的沦陷
身体与教育过程密切相关,身体的功能、结构和关系对教育过程和教学效果有着必然性的影响。然而,历史进化演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人,人的身体结构和功能是人不断适应环境的产物,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身体制约了认知、学习、记忆、思维、情感和态度等心智活动过程。在赫尔巴特传统教学三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与“教材中心”的影响之下,教师的权威作用与中心地位得到强调与突显。传统的教育教学过多地重视公式、法则、理论、定理等系统的、逻辑性的知识体系,对教育情境和教学情景漠然处之。这加深了教育教学过程是排斥情境的、孤立的符号运算的偏见与误解,致使学生无法激起学习热情,难以充分发挥求索创新、开拓创造的能力。整齐划一的教学设施与沉闷乏味的教科书限制了学生的想象空间,学生的身体被束缚于看得见的课堂之中,而不是以宽广的天地空间作为头脑探究的情境。这弱化了学生身体与对象世界的接触、参与和体验,学生的学习活动与现实情境相脱离,被认为是不具根植性的内部心理过程,情境化在教育中随着身体的缺失和离席逐渐沦陷。
三、走向具身的教育教学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心智与环境是认知过程中的有机统一体,认知和心智都是基于身体的。基于对离身教育观的批判与反思,我们更应走向教育教学的身体之维。避免“以心代身”与“扬心抑身”的偏失与谬误对现代教育的影响,需在教育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进行涉身化转变,构建基于“心嵌于身”教学关系与“身融于境”教学思维之上的新教育模式。
(一)“转心面身”:教育认识和理念的转变
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人不是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心智,而是一个有着身体的心智,即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他之所以能获得事物的真实性,恰恰是因为其身体仿佛就根植于这些事物”。[9]“身中之心”的核心思想在于:心灵不仅不是脱离身体的某种实体或者属性,它原本就是行为或者身体活动,并且任何心灵活动都植根于身体活动之中。[10]教育教学的认识和理念转向对于教育具有先决性的引领作用。教育教学的“转心面身”必须跨越“重心抑身”的旧有认知,击破对身体存在的先入之见,让身体和心灵产生共鸣、相互契合,由强调受教育者的心智认知转向重视受教育者的身心一体。
在教育的身体转向过程中,我们必须摈弃传统的反映式表象认识论,而坚信身体代表的是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肉体与心灵、现象与本质、存在与虚无的完全交织与融合,也是生物性和文化性的融合。[11]教育教学中教师所面对的不仅是一具灵魂空壳,而是有血有肉的学生身体。在以往的认知科学背景之下,教师教的过程和学生学的过程往往被定性为一种狭隘的纯粹大脑学习活动。这种基于知识体系客观化的教育观弃置了个人身体运动、感觉经验的影响,仅把教学与学习认为是知识的心智加工与操作过程,将生活世界与知识割裂开,我们应屏除这种局限性。在现代教育教学实践中,首先应转变离身性的教育认识和理念,构建具身性的教学认识论基础。通过学生用身体感官、知觉和体验掌握事物本身,面向事物本质,进而逐步使遮蔽在庞大知识体系背后的价值意蕴清晰化、明了化,让隐喻的身体重回教与学的舞台。其次,需将基于具身性在场的教育观和学习观贯彻到具体教学实践中,使学生所学与学生生活世界相连,学习过程与学生具体活动实践紧密连接。切勿把身体的存在作为通向真理的鸿沟,以高效之名褫夺身体的体验,而需尊重学生身体的独特的思考、知觉与体验。最后,避免通过人为干预分离学生的“身”与“心”,防止只注重学生教育理论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而漠视乃至否弃学生身体的舛误。总之,将身体的位置置于与心智同等重要的高度上,通过具身教学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身心一体”:教育场域的涉身化
在教育场域中,学校、家庭、社会和个体在教育与教学中发挥着内生作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场域”概念,他认为“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2]。目前教育场域中身体缺席现象严重,学校场域的身体弱化、家庭场域的身体窄化、社会场域的身体淡化及个体场域的身体消解化,难以构成布迪厄场域理论的“网络”与“构型”的有机关联。在具身教育模式的构建中,我们需重新审视离身的教育场域,通过教育场域尤其是家教的涉身化对具身教育进行再探索。
教育中没有了身体,就会出现“人的空场”,教育生活意义的发生就会直接依赖于无身性的抽象知识和抽象理性。[13]在现代教育教学中,应不断促进各场域的动态联动。一是重视家庭场域的“言传身教”。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对子女有着深刻影响,家教中父母应以身作则,以身体力行之正向行为引导子女,通过肢体语言、身体姿态与神情神态引导子女“在做中学”,注意家庭内部及家庭间的身体交流与互动,如通过亲子攀岩、亲子铁人三项等涉身活动促进子女对身体在团队合作中重要性的理解,让子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充分调动身体在家庭场域中的教育教化功能,培养良好的道德意识以规范自身行为;二是注重学校场域的“身体出席”。学校教育应让学生身体得到解放,科学设置涉身的体育课程,开设独立化、专门化、精细化的劳动课程,让学生身体回归至学校教育场域中,在身体体验、感觉运动中启迪心智;三是强化社会场域的“身体融合”,如果书本不能够回归生活,那它只能成为规制人、束缚人的“紧箍咒”;如果一味地沉于书本,那只能是一种知识权威式的话语霸权的压制,而不是一种平等的交流与对话。[14]社会教育场域应加强受教育者的涉身教育以应对功利主义的席卷,避免片面强调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而漠视涉身的教育教学。防止学生沦为社会的“应试机器”,不断拓宽社会场域涉身教育的多元化资源和渠道,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涉身的实践场地,提升学生的体验感与幸福感。
(三)“心嵌于身”:教学关系的亲密化
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基于现象学的“身体间性”理论,构建平等互助与和谐共生的师生关系,对教育教学活动从“离身”到“具身”的转变,具有重要价值。在发生现象学时期,胡塞尔认为“先验自我”并不能防止其学说走向“唯我论”,唯有从“主体间性”之视域出发,才能由“我”构筑“他”。然而,由于胡塞尔的“自我意识活动”仍停留于认识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并未向认识主体与对象世界二者的联系开始转向,其“主体间性”亦只能到达认识论层面,始终未至本体论。依托海德格尔共同在世之概念,借助萨特在身体和他人问题上对传统哲学冲击的经验与教训,梅洛-庞蒂为此做出了修正。梅洛-庞蒂将躯体意义与情感、环境意义之间的观念相联系,革命性地提出将“主体间性”解读为“身体间性”,将纯粹身体意识观念斥出现象学的视域,脱离了纯粹的意识哲学的藩篱。如梅洛-庞蒂所说:“因为我有各种感觉功能,有一个视觉、听觉、触觉场,所以我已经与也被当作心理物理主体的其他人建立了联系。”[1]445
梅洛-庞蒂对胡塞尔“意识意向性”持否认态度,他明确提出现象学还原的彻底化是不能达之境,因此真正的意向性不是纯粹意识的意向性,意识始终是和对象世界与身体相互纠缠的,发生着关系的,“意识就是以身体为媒而朝向事物”。意识是世界的现象,而不是绝对的、透明的。“感知的心灵是一肉身化的心灵”。梅洛-庞蒂认为,“这个可见的在可见的之上缠绕可以经由和刺激其他身体,就像它经由和刺激我的身体那样,如果我弄懂了这种模糊性是怎样出现在我身上的,那边的可见的是怎样同时为我的视景,我另外会更能理解它是自我关闭的,除了我的视景还有其他的视景。如果它任凭它的碎片之一所吸引,吸引的原则就确认了;这个场就为了‘身体间性’而开放,向其他的自恋者开放”。[15]基于梅洛-庞蒂的身体间性,师生间的关系应由控制与被控制的主客关系变为“以我之身体度他人之身体”的亲密无间的平等关系,由单纯的心灵沟通变为灵魂相遇前的身体联系。首先,教师应以“我”之身与学生的“他”之身产生同质性、关联性,师生关系之船驶向平等互助与和谐共生。在身体间性之下,师生关系更应抛却主客体之辩,逐步成为双主体之联,在教学中以学生作为核心主体,以学生之身作为有效链接;应逐步弃置教师纯粹的“灌输式”“满堂灌”说教,接通教师与学生身体在教学中的合作与对话。其次,教师应将教学活动视作教师身体的情感价值和心灵体验对学生经验的唤醒,师生之间由压制超压到彼此激勉,由“强加”转入“汲取”,静态知识能够通过身体的诠释而实现动态的发展。教育知识的意义价值在师生身体的碰撞与交流中得以积淀、崭露与呈现。
(四)“身融于境”:教学环境的虚拟实体化
在身体哲学看来,认知过程不是去情景化的心智参与过程,认知、学习、情感、态度绝非与文化、语境脱节的价值无涉行为。相反,认知是身体融入环境的活动所塑造的价值关联行为。具身教学视域下的教育教学受一定的空间场域、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制约,是教师与学生在特定情境下的双主体认知行为。在具体实践中,不论是义务教育时期抑或是高等教育阶段,都更重视教师主体的身体经验、教育需求、教学特点及学生主体的感知、经验的加入和身体的参与,如自主探究、小组讨论与特定空间实验等。“为了促使学习者有效知识学习的发生,应重视情境化因素之于知识学习的重要作用,提供有利于学习者知识学习的学习环境。”[16]
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形态与存在方式,并不断重塑着教育中的身体和教育实践。在现代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学环境的虚拟实体化成为提高受教育者学习体验感的重要途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了虚拟教学技术高速发展,虚拟教学情境在教学中的应用愈发广泛。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以兴趣性、智能性、自主性与共享性等鲜明的技术特性在教育领域异军突起。以沉浸式技术为基础的虚拟教学环境是一种基于现实,又跨越现实的教学交流环境,从而突破了传统教学面临的时空距离限制,为教育的身体转向提供了技术条件和现实可行性。
技术应用需树立“育人为本”的观念,以优化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基本追求,摒弃单纯追求知识传播效率、节省劳动量、炫耀教学技巧等功利性思想。[17]在现代教学实践中,一是应积极创设促进教学情境的虚拟实体化,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多样化的感觉呈现,将学生的学习过程游戏化、娱乐化,达到寓教于乐,助于学习者战胜现实疲怠,重燃学期热情,引发情感共鸣,进而跨越学习障碍。譬如,利用VR/AR技术创设栩栩如生的恐龙世界,向儿童普及恐龙历史起源;利用智能设备向中高年级学生重现红色长征路,重温红色峥嵘岁月。二是应转变旧有教学手段,开阔学习通道,将单一乏味的课堂式学习重新面向天地自然与社会,通过社交媒体、智能软件等形式多样的工具增强学习者学习的兴趣与情感,丰富教学场景,不断更新优化学习者的学习路径,提升学习的效用。三是教育领域应注重虚拟教学环境智能设备的引入,不断更新升级虚拟实体化教学情境的资源开发技术,充分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和元宇宙等整合教学路径,提升具身教学的学生体验,以促进学生实现知识迁移与实践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