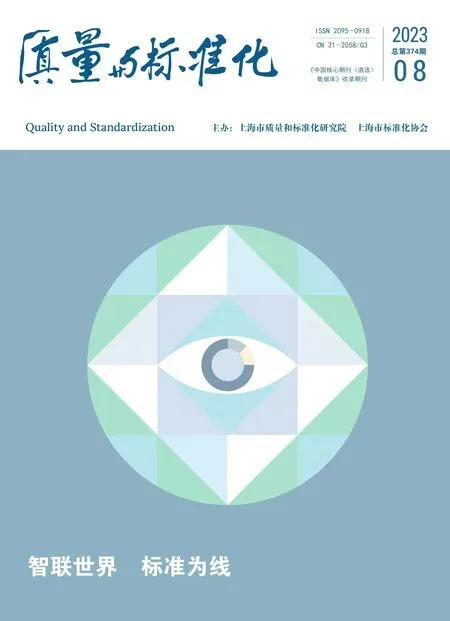中国古代地图测绘理论的创建者裴秀
2024-01-02关增建
文/关增建
地图测绘是空间计量的重要内容。我国有着悠久的地图测绘传统。在古代地图测绘发展历程中,西晋的裴秀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提出的“制图六体”成为古代地图测绘的基本规则。
一、裴秀的生平
裴秀,字季彦,生于三国时期曹魏黄初五年(224 年),卒于西晋泰始七年(271 年),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官宦世家出身,其祖父裴茂、父裴潜都曾官至尚书令。据《晋书·裴秀传》记载,裴秀自幼聪慧且受到良好教育,据说八岁就能写文章了,名声外播。他的叔父裴徽在当地很有名望,家中常有宾客来往,然而这些宾客拜会过裴徽后,往往都还要去找裴秀交谈,听取他的意见,而这时的裴秀也才只有十几岁。裴秀的生母出身卑微,其嫡母宣氏看不起她,曾经让她给客人端茶送饭,但客人见进来的是她,都起身行礼。裴秀的母亲感慨说:“我出身这样卑贱,客人对我却这样客气,应该是因为小儿裴秀吧。”宣氏得知此事后,从此也不再轻视她了。当时的人们都传言说,裴秀是年轻一代的领袖人物。
裴秀的一生都在宦途。因为才华出众,他得到了各方面的欣赏,在曹魏时期,渡辽将军毋丘俭把他推荐给当时掌握着辅政大权的大将军曹爽,说他出身高贵,性格好,而且“博学强记,无文不该;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诚宜弼佐谟明,助和鼎味,毗赞大府,光昭盛化”(《晋书》卷三十五《裴秀传》)。曹爽于是任命裴秀为黄门侍郎,并袭父爵清阳亭侯,这年他25 岁。
正始十年(249 年),司马懿发动政变,解除了曹爽职务,并以谋反之罪灭其三族。裴秀因此受到牵连,被免除了职务。但司马懿明白,裴秀是可用之才,不久就起用他,任命其为廷尉。此后,裴秀在司马氏门下逐步升迁,开始参与谋划军国之政。当时的魏国皇帝曹髦也喜欢裴秀,经常找他谈论学问,但裴秀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对曹氏政权的忠心。260 年,曹髦因不满司马氏专权而奋起反抗被杀,司马昭立14 岁的曹奂为帝,裴秀因参与谋立而被晋爵为鲁阳县侯,迁任尚书仆射。
裴秀真正在司马集团树立起牢不可破的核心地位的关键是他对司马氏立嗣一事的介入。随着司马昭年事日高,他开始考虑立嗣之事。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嫡长子,其胞弟司马攸 “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晋书》卷三十八《司马攸传》),名声高过司马炎。司马昭之兄司马师无子,司马攸自小过继给司马师,司马师临终时司马攸才10 岁,司马师没有把权力交给司马攸,而是交给了弟弟司马昭。司马昭对此颇为感激,因此对司马攸“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晋书》卷三《武帝纪》)。面对这种局面,司马炎颇为着急,曾私下向裴秀求援,《晋书·裴秀传》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
初,文帝未定嗣,而属意舞阳侯攸。武帝惧不得立,问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后言于文帝曰:“中抚军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
原来,司马炎长相有异于常人之处,他站着时头发能拖到地上,手臂垂下时能超过膝盖。古人迷信,认为帝王受命于天,也会在长相上表现出来。司马炎向裴秀展示了自己的异相。古人不剪发,平时将头发盘起来,看不出有多长。司马炎要说服裴秀,专门向他展示这一点,就需要将头发打开,让其垂地。裴秀被说服了,也借此站到了司马炎一方,并通过向司马昭进言,打动了司马昭,最终使司马炎做上了皇帝,就是后来的晋武帝。
司马炎当上皇帝后,对裴秀特别关照。裴秀平时也有一些缺点。有一次,安远护军郝诩在写给故人的信中说道:“我之所以跟裴秀交好,是指望能从他那里得到关照。”这事不知怎么被外人知道了,有关部门奏请皇帝将裴秀免职。司马炎替他辩护,说人无法阻止别人诬陷自己,这事是郝诩的过错,不能让裴秀负责。后来,司隶校尉李憙再次上书,指出骑都尉刘尚替裴秀霸占官方稻田,要求处罚裴秀。事实俱在,司马炎“以秀干翼朝政,有勋绩于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晋书·裴秀传》)的理由搪塞,最终使裴秀逃过此次责罚。
裴秀的为官之道未能得到人们的肯定,真正使他名垂青史的是他在创建传统地图测绘理论方面的贡献。
二、我国古代悠久的地图测绘传统
我国古代统治者对地图的重要性早就有清晰的认识,同时也有悠久的地图测绘传统。在我国,有夏铸九鼎的传说。据说,在公元前21 世纪,新兴的夏王朝用各地诸侯朝贡的铜铸造了9 只气壮山河的大鼎,各鼎有不同的图像,表示不同地区特有的山川、草木、禽兽。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我国在四千年前的夏代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在一些崖壁或器物上绘有表示山川的图形。这些图形就是原始的地图。
对地图重要性的认识则反映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言行事迹的《管子》一书中。《管子·地图篇》曾专门论述了地图对军事行动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在准备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军事负责人必须先熟悉和研究地图,以详尽地了解地形地势、交通状况、植物分布、地理远近、城郭大小等。对地形交错复杂的地方,军事负责人要胸中有数,然后才能出兵打仗。地图对于军事的根本功能即在于此。
古籍中有关地图的记载更是比比皆是。《尚书·周书·洛诰》就曾记载,周朝初期,周公负责营建洛邑,建好后向成王报告说,他再次勘察了洛邑,经过占卜,洛邑适合建都,“伻来以图及献卜”。“伻”指仆人或特使,这里指专门派人把地图及占测结果给成王献上。这里明确提到了地图,表明西周时已经能够绘制城市地图。
对于地图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周礼·地官司徒》有详细的描述: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
地图包括了如此多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治国者必须要了解的,因此要由大司徒负责。《战国策· 赵策》详细记载了苏秦以地图为依据,说服赵王同意参加合纵反秦。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地图在诸侯国争霸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一个历史见证。另一个更有名的事件是荆轲刺秦王。荆轲以向秦王敬献燕国督、亢地区(今河北涿州一带)地图为名,意图获得接近、刺杀秦王的机会。虽然此事以失败告终,但当时地图为各诸侯所重视,却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先秦时期没有纸张、印刷术,地图一般绘制在丝帛等难以长期保存的材料之上。先秦时期地图绘制水平究竟如何,由于缺乏实物证据,现在很难知晓。幸运的是,出土文物中的地图使我们得以对我国两千多年前的地图测绘水平有所了解。
1973 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3 幅地图。这3 幅地图都绘在帛上,一幅是地形图,一幅是驻军图,另一幅是城邑图。马王堆三号汉墓墓主是汉初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之子,其下葬年代是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距今近两千两百年了。显然,地图的绘制时间要更早。马王堆地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绘制的地图。
从出土的这3 幅地图尤其是其中的地形图来看,其主要部分反映的是当时长沙国南部的地形地貌,就是现在湘江上游潇水流域一带。这部分图的精度相当高。鉴于这部分区域山峦起伏、地形复杂,要达到出土地图所显示的绘制精度,当时的测绘者除了直接测量之外,一定还采用相应的数学方法进行间接测量。当时数学中有一种“重差术”,可以利用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原理,解决间接测远、测山高、测城邑大小等问题,古代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数学著作《九章算术》等对之都有介绍。将合适的数学方法应用到地图测绘,是我国古代地图测绘的一大进步。
汉代的地图测绘也有不足之处。就以马王堆出土的这3 幅地图来说,地图的比例尺不统一、方位不够准确、边缘地区绘制粗疏等,都是比较明显的缺陷。但无论如何,汉代的地图测绘为裴秀建立其地图测绘理论奠定了基础。裴秀是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创建了被后人称颂的地图测绘理论。
三、裴秀的“制图六体”理论
裴秀在34 岁时曾随司马昭讨伐诸葛诞,因有功而升任尚书,参与掌管国家机密,这使他得以了解地图与军事的密切关系。西晋泰始四年(268年),他又被晋武帝司马炎任命为司空,并兼任地官。司空专门掌管工程、水利、交通、屯田等事宜,与测绘密切相关。地官主管全国的户籍、土地、田亩赋税和地图等事宜,能接触到各地山川、地势地形,掌握地名及其沿革情况。裴秀能够在地图学上取得成就,与他的这些经历有很大关系。遗憾的是,3 年后,他因为服寒食散又饮冷酒,遽然去世,年仅48 岁。
裴秀任职地官期间,因为职务关系,经常需要了解地名,查阅地图,发现了这个领域存在的重大问题。《晋书·裴秀传》对此有所记叙:
(裴秀)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
过去流传下来的《禹贡》,其中的地理名称因为年代久远,变动很大,而后来的解说者又牵强附会,以讹传讹,导致谬误很多。他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于是收集资料,对各种地理古籍进行考证甄别和作注,考辨正误,完成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并上奏朝廷。这是见于文字记载的中国最早的一部地图集。地图集完成以后,被藏于秘府。
遗憾的是,裴秀的这部藏于秘府的《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其抄写本虽然也曾流传于世,但无论是秘藏本还是流传本,后来都散失了,未能保留下来,以至于现在无法通过地图本身了解裴秀的绘制水平。
虽然地图本身散失了,但裴秀为该地图集写的序言被完整地保留在了《晋书·裴秀传》中,其中就包括他的地图绘制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制图六体”。《晋书·裴秀传》是这样记载他的“制图六体”的: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像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这“六体”概括来说,就是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和迂直。前3 条阐述的是地图比例尺、方位和距离,这些是地图测绘的核心要素,只有把这3 条搞精准了,绘制的地图才不会失真。后3条关注的是如何正确确定实地上两点间距离,这些是地图测绘的方法。核心要素确定了,如果没有合适的方法去确定它们,同样无法绘制出准确的地图来。
根据裴秀的说明,“分率”指的是比例尺,这是没有疑义的。绘制地图,首要因素是确定比例尺,裴秀将之置于“六体”首位,是理所当然的。“准望”,按裴秀的说法是“所以正彼此之体也”。彼此之体,说的是两个地体如山脉、村落等,准望是要确定它们彼此之间的正确位置,显然,这是指的辨方正位,即确定被测物体的方位。所谓“道里”,是“所以定所由之数”,这里的“所由”,当然是人之“所由”,即人经历的地方,也就是地图上两地之间路程的远近。这对地图的使用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信息。
但是,所行之路不可能是笔直的、水平的,如果按照行路里程绘制地图,就会使地图面目全非,完全不能反映真实的地理地貌。正如裴秀所言:“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即是说,如果道路有上坡下岗,高低不平,就需要按“高下”之术取平;有迂回曲折,则应按“方邪、迂直”之术取平。否则,绘制出来的地图就失真了。裴秀特别指出,按照“制图六体”,绘制地图所应遵循的原则应该是“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即地理范围的大小,应通过地图的比例尺确定下来;两地之间的道路里程,应通过地图的标示得到了解;两地之间的直接距离,则需要通过“高下、方邪、迂直”之术,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来。最后,地图绘制当然是以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直线距离为准,这样绘制出来的地图才会准确。
裴秀“制图六体”所需要的数学方法,在当时已经发展成熟。在他主导绘制《禹贡地域图》,提出“制图六体”测绘理论时,与他同时代的刘徽已经完成了对传统数学著作《九章算术》的注解,并在注解中提出了系统的测高望远之术。唐代曾把刘徽《九章算术注》有关测量的内容即第十卷“重差”摘录出来,单独编撰成书,以《海岛算经》命名,并将其列入《算经十书》,供学子研讨。《海岛算经》的全部内容都是利用两次或多次测望所得的数据,来推算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的高、深、广、远,这些方法为传统地图测绘提供了充足的数学支持。裴秀在“制图六体”中提出的“高下、方邪、迂直”问题,全部能在《海岛算经》中找到解答方案。
在裴秀之前,我国的地图测绘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裴秀“制图六体”说的提出,弥补了传统地图测绘学的短板,为后人所遵循。裴秀的“制图六体”对后世制图工作的影响十分深远,唐代的地图学家贾耽、宋代科学家沈括等都对该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直到明末清初欧洲的地图投影技术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之前,“制图六体”都是中国学者绘制地图时遵循的基本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