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友
2023-12-30颜士州
颜士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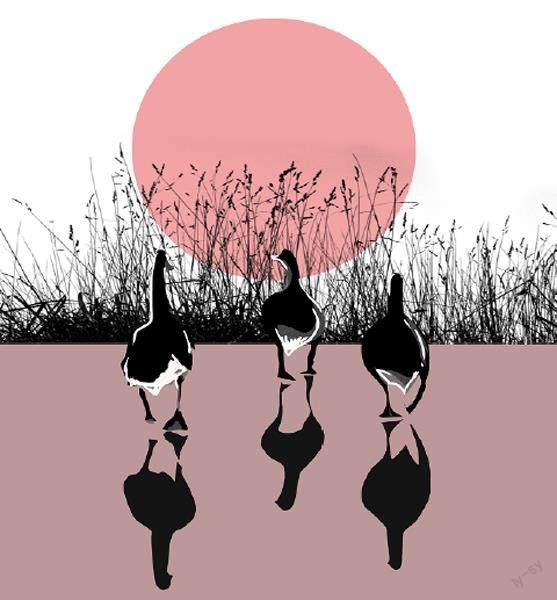
一
至今,我仍深深怀念着在通天河无人区结识的小“禽友”——两只小斑头雁。
我们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去年6月间从沱沱河下水后,就进入“荒凉世界”。除了流水淙淙,便是万籁俱寂。而这独有的淙淙水声,更加重了自然的沉寂。
两三天后,头顶上突然有大鸟“刚,刚”地鸣空。电感一般,空气里便有了一种回响!我们以为那是一种黑天鹅——那长颈、那体态、那声音,都酷肖“鹅类”。后来,有几只胆大妄为的“黑天鹅”降到沙汀上,使我们看清其头颈黑一截、黄一截,色斑交错,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早已听说的斑头雁,世界上栖翔最高的鸟类!作为只能用相机抓拍下来的“远鸟”,它们始终同我们的探險船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6月21日,探险队漂到一处沙洲附近,蓦然发现左边洲渚上,斑头雁列成了“雁阵”,不飞不鸣,挤挤挨挨,情态十分怪异。十来艘橡皮船一只接一只在这里泊住,大家都来“检阅”这高鸟群落。我们张开大大小小的“机头”,慢慢地向雁阵推近,生怕惊飞了它们。怪哉!群鸟只是慢慢地往后退却,并没有要飞的意思。镜头中的斑头雁越来越大,到距离不远时,才发现它们的队列里,有一团团的“黄毛球”——是刚出壳不久的“雁崽”!雁阵的后面是广袤的陆地,无法像在水面一样携家带眷地凫水逃走。而大斑头雁又不会衔起幼鸟起飞,唯有从陆上后退,却又要照顾小雁的嫩脚丫,因而步履缓慢。当我们近到不能再近时,大雁的“拖延计”宣告失败,纷纷起飞逃跑,抛下了那一团团“绒毛”。
我捉住了一只倒地装死的小斑头雁。它有着幼儿般的浑圆的、嫩嫩的可爱的模样。它在我掌心里吱吱不休地“哭闹”着,扑动着翅膀拼命地挣扎着,使人顿生“握紧了怕死,放松了怕跑”之感。我有心要做一个“养父”,将这“小咪咪儿”(四川方言,意即很小很小的物什)养大、驯化,从长江上游带到长江中、下游,待整个探险活动结束时,它将长成一只羽毛丰满的大鸟,并同人类建立密切的关系。那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呀!也许,还能为科考内容增加一点篇章哩!
二
我继续划船。
“小斑点”就在船舱里不停地弹射,像一枚肉弹,边跳跃,边哭闹,总想逃到外面的江水里去。我知道每个“抱养人家”,都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就让它自个儿去闹腾一阵吧。没想到,整个下午,它都在精力充沛地跳高,好几次已经跳到我的大腿上,差点儿就真跳出去了!我只得频频停止划桨,把它又逮回舱里。这样没完没了地闹了半天,我开始担心起来:它该不会就这样把自己累死?我脱下一只旅游鞋,把“小斑点”放进去,周围用手套塞住它的“小体格”。小家伙在这“鞋公馆”里暂时安顿下来,那一颗惹人爱、逗人怜的小花脑袋,在“鞋屋”上面扭来扭去地看,不明白它究竟进入了何种异境,弄不清是祸是福。过了好一阵,它似乎恍然大悟,又在里面拳打脚踢,最后竟将手套挤松,从“鞋公馆”溜了出来。
另一艘船上,也有小斑头雁在吱吱高叫。原来,漂流队员小王也抚养了一只。我突然醒悟,雁类是最怕孤独的!苏东坡曾写过孤鸿诗,描写极其哀怨悱恻,显然是经过观察的。于是,等船停靠后,小王便将那一只送了过来。两小见面,气氛大变,不再大叫大嚷,而是呢喃起来,发出蟋蟀一般的啾啾之声,还用喙儿互相摩擦。
但小斑头雁并没有皈依人类。它们以绝食抗争!我用自己食用的压缩干粮,掰成粉渣喂它们,不吃!又弄一瓣糖水橘子饲喂,仍不吃!给一点牛肉干,又不吃!我一时感到束手无策了。因为我们的食物品种,就这几样。突然间,我想起小雁是吃大雁咀嚼和半消化后呕出来的东西,名曰“返哺”,于是也就东施效颦,把压缩干粮放进口里咀嚼一番,咬成糊状,再来喂它们,没想到它们竟然还是不吃!
于是,我渴望着靠岸,能弄到一点水生虫子。晚上七八点,探险队全伙停船宿营,并开始为全天唯一的一顿热食忙碌。全体出动,搜集燃料。我不能特殊化地先去侍弄自己的“雁娃子”,便也去草甸上捡牛粪。但两只小不点怎么办?我打开羽绒衣的领口,把它们放进去,就这样兜着小雁行走拾粪。须臾,两只小雁都从羽绒衣下摆里漏了出来。于是我又改成将其揣在两边的口袋里,两边都用手套塞住。它们于是又成了“囊公馆”的居民,吱吱哇哇地在袋口东瞅西瞅。在拾粪中,我发现了一只高原壁虎,大喜,立刻捉了来,在石头上切成许多碎块。但“雁娃子”并不感兴趣。
三
它们究竟要吃什么呢?真是愁煞人!
有了!雁类最嗜鱼虾。藏族队员汉布正在撒网打鱼。他用的是一种藏式打法:牵着小小的拉网慢慢往下游移动。一网最多能打上一条两斤重的鱼。全队生活异常艰苦,这点鱼是要用来聊补炊事之需的,人吃都不够,哪能用来喂斑头雁?我不好意思去要一条鱼,却在搜索口袋时,发现了一包鱼干。太好了!马上撕下一些来,把它们弄成鱼屑,摊在掌心。两只小鸟嗅到了鱼香味,果然来了馋劲,不停地用小小的、扁扁的喙儿来掌中取食。那吞惯了“返哺”的细喉咙一时吞不下干鱼片,就拼命地甩脑袋助吞,结果把鱼片甩了一地,笑死人了。
现在,总算是有了办法了!蓄长髯的老徐,听说终于有了一道小斑头雁喜欢的“菜”,马上把自己“窖”着的两包鱼干捐了出来。
“雁娃子”总不能老占我的旅游鞋或衣服口袋。我用一个装方便面的纸盒,在上面挖了十来个通气孔,做它们的房子。比起它们的家族那种露天的藤草窝子,这真该算是“公馆”了。但它们一进去,照样先来一顿拳打脚踢以示抗争,脑袋硬是从小小的通气天窗里挤了出来,仰天啁啾,好像戴枷的犯人!但不久,它们也就随遇而安了。到夜晚,当帐篷里鼾声初起时,它们的叫声显得格外清晰——一定是冷坏了!于是我把它们从盒子里取出来,塞进自己的鸭绒睡袋里。这时我分明地感觉到它们在瑟瑟发抖。这一夜,我便难以睡得深沉,总担心小雁被翻身压死。
两三天下来,“雁娃子”野性大泯,我已经不必使用任何强制手段来带它们,就让它们在脚边自便。你走到东,它们跟到东;你走到西,它们跟到西。要叫它们喝水了,也不必捉到河畔,只消自己走去,它们也就跟着来到河边。一发现水,两只小雁立刻欢欣鼓舞地下水嬉戏。这时,它们的野性似乎抬头了,一个鱼鹰似的猛子扎出去,便有差不多一米远,浑如水下弩箭。然而,我不必担心“小斑点”逃走,只消踩着很响的脚步,向高地走去,它们马上就会收起那份悠闲劲,跌跌撞撞地追上岸来,唯恐失去保护人。它们会一直追到你脚下,近到走路时稍有不慎就会踩着它们的那种距离。我由此相信,任何幼小的动物,都有可能与人类建立感情。
慢慢熟络起来的小雁就这样跟着我们,直到我轮岗出高原,回家休息,把它们交给了战友照看。等我再次回到通天河畔,据说两只小家伙已经放归大自然了。
(水月摘自《龙门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