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们变得疏离的,从来不是网络
2023-12-30奥利维娅·莱恩
[英]奥利维娅·莱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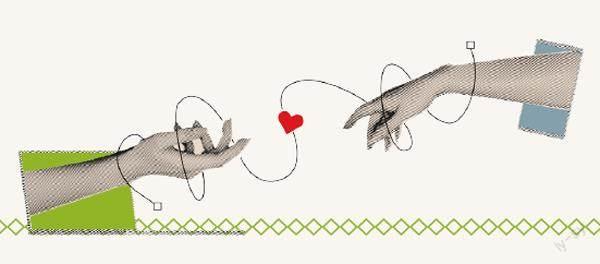
“在这个被预先构造出来的世界上,将私人事物转化为公共事物的行为能够产生强烈的反响。”沃纳洛维奇曾这样说过。
每天醒来时,在我的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前,我就会把手提电脑拽到床上,立刻登录Twitter,它是我每天看到的第一样和最后一样东西。这个不断滚动的页面中的大部分信息来自陌生人、机构和朋友。
在这个转瞬即逝的社群里,我是一个没有实体的、不断地变化着的存在。我在源源不绝的消息中浏览着国内和市内的动态:隐形眼镜药水、书的封面、一则死讯、抗议的图片、艺术活动开幕、关于德里达的笑话、马其顿森林里的难民、“耻辱”的话题标签、“懒惰”的话题标签、气候变化、丢失的围巾。
这一连串的信息洪流、态度和观点在某些日子里(可能是大多数日子里)比现实生活更多地吸引了我们的关注。
而Twitter只是通往互联网这个无尽之城的一扇门。一天又一天,时间在点击鼠标中过去了,大量的信息夺去了我的注意力,我就像是一个不在场的、热心的见证人一样看着这个世界,像背向窗户的夏洛特小姐一样看着出现在她的魔法镜子里的真实世界的倒影。
过去,在那个已经完结了的纸书和报纸的世纪里,我也曾习惯于把自己埋进一本书里的阅读方式,而现在的我正盯着屏幕,盯着这个令我全神贯注的银色的爱侣。
我像是一个永远在监视着一切的间谍,像是又一次回到了青春期,一头扎进沉迷的深渊里,踩着摇动的汹涌的水波和变幻的碎浪向前移动。
我阅读着那些关于囤积、折磨、真实的犯罪和国家的不公的事情,阅读着聊天室里人们用有拼写错误的对话讨论着的瑞凡·菲尼克斯死后萨曼莎·马希斯所经历的事情,抱歉这听起来有点傲慢,可你确定你看过这个采访了吗?
纵身跃入,随波逐流,由无止境的链接构成的迷幻黑洞,随着点击的动作,我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过去,跌跌撞撞地踏进当下的恐怖里。
科特妮·洛芙和科特·柯本在一片沙滩上举办的婚礼,沙子上的一个血淋淋的孩子的尸体:这些会引发各种情绪的图片将无意义的、惊骇的和令人渴望的意象全都重叠在了一起。
我想要什么?我在寻找什么?无数个小时过去了,我都做了些什么?相互矛盾的事情。
我想要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我想寻求刺激和鼓舞,想与世界保持联系,可我又想保留我的隐私和私人空间。我想要不断地点击点击再点击,直到我的突触神经键爆炸,直到我被過剩的信息淹没。我想要用数据和彩色像素自我催眠,让自己变得空白,克服所有日益加剧的关于“我究竟是谁”的焦虑感,彻底抹去我的感受。
同时,我又想保持清醒,参与到与政治和社会相关的问题中去。
此外,我还想表明自己的存在,列出我的兴趣和异议,告知世界我还在这里用我的手指思考着,即便我几乎已经丧失了语言这门艺术。
我想要去看,也想要被看见,而出于某种原因,透过扮演着中介角色的屏幕,这一切变得越发容易了。
网络确保人们可以发生联系,并且在匿名性和可控性方面做出了美好而狡猾的承诺,可想而知它对于一个长期承受着孤独的痛楚的人会显出怎样的吸引力。
你可以寻求陪伴,却不用承担被暴露的风险,而你的渴望和那种希冀或匮乏的状态也不会被人发现。
你可以去触碰外界,也可以躲藏起来;你可以潜伏在屏幕后面,也可以展露精心设计和改造过的自己。
从很多方面来看,互联网都让我感到安全。
我喜欢在网上和人接触:积极的致意一点一点地积聚起来,Twitter上的“喜欢”,Facebook上的“点赞”,还有那些被设计出来并编入程序的、用来维持关注和提升客户自负心的小策略。
我愿意成为那个傻瓜,公开我的信息,把透露出我的兴趣和支持取向的电子痕迹留给未来的公司,让他们将其转化成任何一种他们会使用的货币。
事实上,这种交换有时看起来对我也有利,尤其是在Twitter上,将表露出我的兴趣和支持取向的推文分享给他人是一个促进陌生人间发生对话的诀窍。
在我上Twitter的头一两年里,它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社区,一个欢乐的地方。事实上,它成了一条生命线,要不是有它的存在,那时的我不知会陷入怎样与世隔绝的境地。
然而,在其他时候,这整件事看起来都是疯狂的。我在用时间去交换某种根本无形可触的东西:一颗黄色的星星,一粒魔法豆,一种亲密的假象。我为此放弃了自我身份的所有碎片,放弃了我表面上还占据着的肉身以外的一切。
而只要有几条链接被我错过了,或是收到的点赞太少,孤独就会重新浮现,我的内心又会充斥着因没能建立联系而生的挫败的无望感。
虚拟排斥所触发的孤独感与真实生活中的遭遇一样令人痛苦,几乎每个上网的人都曾在某个时刻经历过这种突然袭来的难受的情绪。
事实上,心理学家用来评估排挤和社会排斥给人带来的影响时所使用的手段包括一种名叫“虚拟传球”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被试者会跟电脑生成的两名玩家玩抛接球的游戏。按照程序的设置,在前几次投掷中,虚拟玩家会正常地抛接,但是后来,互动会停留在两个虚拟玩家之间——这种体会跟处在一段对话中的你的虚拟自我、你的化身突然被排斥在外时所引发的即刻刺痛感是一样的。
可当我能够从对话中抽身,接着又被“观看”这种令人上瘾的行为所拯救时,我还在乎什么呢?电脑提供了一种愉悦的、流动的、没有风险的凝视,因为没有一样被我观看的东西意识到了我这个观察者的存在和我那起伏不定的注意力,尽管我留下了一连串标示着我的访问路径的本地终端数据。
徜徉在被互联网点亮的林荫大道上,停下来扫一眼人们用自己的兴趣、生活和身体组成的展览,我能感到自己与波德莱尔产生了某种血亲关系。
他在散文诗《人群》里为漫游者,也就是城市中的不受约束的、无关政治的流浪者奠定了一份宣言,用梦一般的句子写道:
“诗人享有这无与伦比的特权,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成为自己和他人。就像那些寻找躯壳的游魂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人的躯体一样。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敞开的。”
有时,我拉动着页面时瞥见了镜子里自己的脸,这张脸毫无生气,沒有灵魂,被屏幕的光线照亮。
也许我的内心会被我看到的东西吸引住,从而感到焦躁不安或是彻底被激怒,但从外表看来,我就像一个半死不活的人,一具被机器吸走了全部注意力的孤独的躯体。
几年后,在观看斯派克·琼斯执导的《她》时,我在华金·菲尼克斯饰演的西奥多·通布利的脸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表情。
这个在真实的亲密关系中受到巨大挫败并对此心生戒备的男人爱上了他的操作系统。
让我产生认同感的并非那一幕幕他和电话一起旋转的画面中的令人疑窦丛生的快乐,而是影片开头的一个场景:他下班后回到家,在黑暗中坐下,开始玩一局电子游戏,狂躁地上下移动着他的手指,操纵游戏里的化身登上一个斜坡。
他脸上全神贯注的表情令人感到悲哀,他那瘫坐着的身体与巨大的屏幕相形见绌。他看上去是那么无望、可笑,完全与生活脱节,而我立即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个21世纪的遗世独立的、对信息产生依赖的标志性形象。
到了那个时候,人类也许能和一个操作系统发展一段浪漫关系,这一想法已不再显得荒谬不堪。数字文化正在以超快的速度发展着,快得让人很难跟上它的节奏。
前一分钟某件事情还是科幻小说里的带有明显的滑稽可笑意味的想象,下一秒它就成了一种随意的日常行为,成为每日的生活机理中的一个部分。
在到纽约的第一年里,我曾读过詹尼佛·伊根的《恶棍来访》。小说里的部分情节被设置在不远的未来,涉及一名年轻女性和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之间的一次商业会晤。
在交谈了一会儿后,对话所需的精力开始让这女孩感到不耐烦起来,于是她问那个男人她能否直接“打字”给他看,尽管他们是肩并肩坐着的。随着信息无声地在他们两人的头戴式耳机里流动着,她看上去“放松得几乎要睡着了”,她把这种交流称为纯粹的交流。
我能清楚地想起自己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感到的震惊,我感觉它虽然有点牵强,却是段了不起的情节。几个月后,它似乎不仅显得真实可信,而且完全成了一种可以理解的需求。
现在这就是我们行事的方式:在公司里打字,给同一张办公桌上的同事发邮件,避免人与人的接触,代之以一对一的邮件往来。
这是虚拟空间带来的放松感,是插上电源后把一切都掌控在自己手中所产生的安慰。
在纽约,无论我是坐在地铁里、咖啡馆里,还是在街上步行,我都会见到人们都被锁在他们自己的网络里。
手提电脑和智能电话的奇迹在于它们让人们从实体的人际交往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在身处所谓的公共场合时还能一直躲在一个私人的泡泡里,在享受着表面的独处时还能跟其他人进行互动。
似乎只有无家可归的人和没有财产的人过的才不是这样的生活,但那不包括整天泡在百老汇的苹果体验店里的街头浪荡儿们。即使他们夜里都没有睡觉的地方,他们也会一直停留在社交网络上。
每个人对此都心知肚明。每个人都知道那看上去是什么样子。
我记不清自己读过多少篇关于我们变得彼此疏离的报道了,这些报道说我们被捆绑在了自己的设备上,对真实的交往怀有戒心。这些报道还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一场亲密关系的危机,因为我们的社交能力正在衰退。
但这就像是在透过望远镜的镜头反方向看出去。并不是因为我们把社交和情感生活中的太多部分转交给了机器我们才变得冷漠,疏远彼此。
这无疑是一个能使其自身永久存在的循环,但发明并购买这些东西的部分冲动源自人们在交流上遇到的困难和对沟通的恐惧,以及交流这一过程偶尔会导致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危险。
尽管那时在地铁上随处可见的一则广告声称“拥有智能手机最棒的一点是你永远都不必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但这个小机器致命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它会免除其所有者对人群的需求,而是在于它会为他们提供联系。
更进一步来说,这是一种毫无风险的联系,其中涉及的沟通需求将永远不会被拒绝、误解或遭到打击,或是要求人们付出超出他们愿意付出的关注度、亲密感或时间。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孤独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