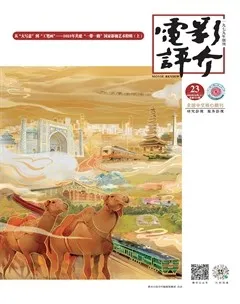“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闽南电影地缘题旨的三重解码
2023-12-29肖家豪黄钟军
肖家豪 黄钟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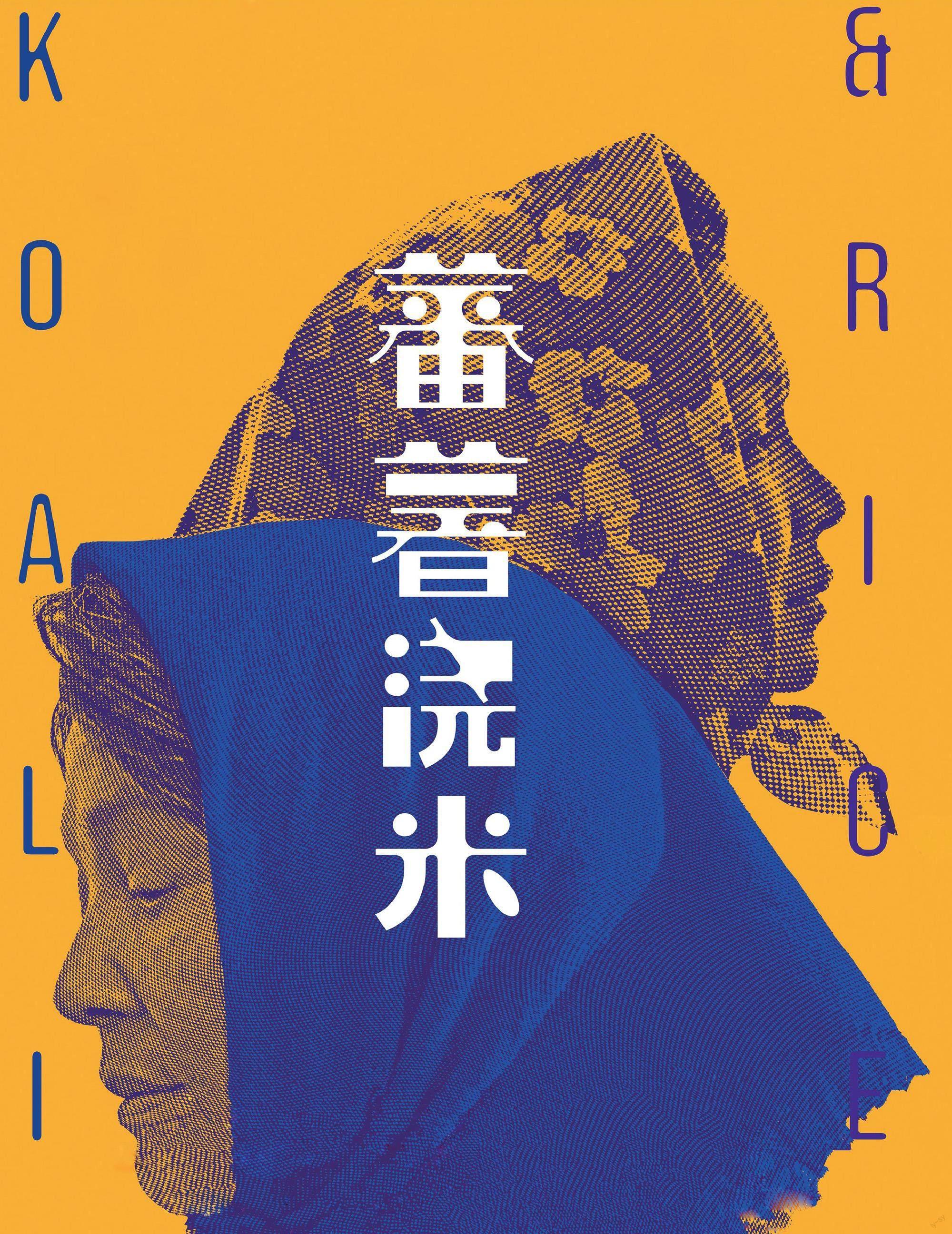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肖家豪,男,广东阳江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区域电影研究;
黄钟军,男,浙江衢州人,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批评及理论研究。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始于秦汉,尔后宋元两代的繁荣成就了泉州港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支点,漳州月港“海舶鳞集,商贸成聚”的空前盛况。[1]这条始于经贸而深化为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海上枢纽,不仅直接促成了闽南文化的海洋色彩及海洋精神,更将其开放包容、多元互鉴的表现及内核熔铸在闽南地缘文化之中。目前学界对于“中国电影的地缘文化研究”的倡议,为电影精神特质与文化属性的研究从美学视域转向地缘文化视域,创作主体研究转向地缘客体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差异性考察”方法。[2]地缘文化正是明晰闽南地域的地理空间边界以及文化通约性的关键,同样也是确认与地缘文化“共生”的闽南电影与其他区域电影之间独异性的关键。在特定的电影创作体制的框范以及本土历史(革命)资源发掘的自觉下,闽南电影创作统摄在“国家话语-地域讲述”的影像序列中,同时,在“出洋”“归乡”“交汇”的地缘文化主题方面表现出极强的统一性——闽南电影文本中的海洋观念、原乡想象、景观呈现源于对“海丝”内涵的历史追溯与拓展,强化了闽南电影创作特殊且无可替代的地缘属性。
一、闽南电影的概念及其创作流变
本文指称的“闽南电影”,是以闽南地缘景观为空间特征、以闽南在地的人和事为呈现对象、具有闽南地缘文化特色的电影。需要补充的是,该定义在具有准确的地域对应性的“题材标准”与“文化标准”上进行了严格的界定,而在“创作主体标准”上给予了较大的包容度:一方面在于,我们过去主要是按照行政区划的方式来划分中国电影的地理版图,并且按照同样的方式建立了对应的电影创作生产机构,然而与闽南行政区划相对应的福建电影制片厂并没能获得充分的建设与发展,从而如同长影、西影一样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地缘文化品质突出的电影作品群。另一方面,对所在地域文化资源进行挖掘、传承并不是对应区域电影生产机构或影人的“专权”,比如《刘三姐》(1961)、《五朵金花》(1959)产生于东北电影制片厂,而这两部电影作品的产地与电影本身所表现的故事风格具有较大差异,更不必言当前电影生产主体的多元化事实与趋势。因此,不应该将眼光局限于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创作,从作者身份出发既应该容纳闽南籍作者、福影厂的创作,也应该容纳非闽南籍创作者与非福影厂的创作。
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福建电影制片厂人本土创作意识的觉醒,闽南电影在中国电影风景中惊鸿一瞥;又因创作后续乏力而渐渐淹没在中国电影的市场化进程中淡出人们的视线;近年又以一部闽南语为语言体例、在地经验为特色的作品《蕃薯浇米》(2020)“忽然而至”,在中国电影银幕中大放异彩。
(一)地缘文化意识初现
《小城春秋》(1981)是福建电影制片厂获得“新生”并且进行电影创作(故事片摄制)的开端。①当时制片厂定下调子——“拍摄的故事片必须取材于一部成功的、为社会所认可的小说,而且要能体现福建地域特色”[3],最终选定了厦门籍作家高云览创作的厦门故事《小城春秋》進行电影改编。可以见得,《小城春秋》是福建影人有意而为的选择,厦门鼓浪屿、中山路、思明电影院等城市景观的出现为电影注入的闽南气质,以及对爱国华侨人群的刻画来对厦门城市精神风貌进行展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闽南电影创作的开启,代表了本土题材创作的地缘文化意识初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电影史上没有更早的“闽南故事”,比如天马电影制片厂(上海)拍摄制作的《英雄小八路》(1961)。作为故事发生地的厦门只居于电影舞台的次要位置,厦门的独特景观、地缘文化被时代的共性同化到无法辨认;电影中作为故事主人公的一群“厦门少年”,也在这一叙事模式下被概念化为“少年先锋队”。可见,该片虽是闽南故事,但却缺乏“闽南讲述”,其中的闽南地缘景观、闽南文化气息更是模糊,因而不纳入本文所指称的“闽南电影”概念之中。
(二)地缘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
将革命历史主题与地缘文化的呈现相结合,是《小城春秋》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取得成功的关键,也为闽南电影创作走向“历史题材——闽南面向——地缘讲述”的突围之路提供了优质范例。此后,闽南电影创作开启了对地缘文化更为深入的挖掘与呈现。《海囚》(1981)捕捉到了厦门在鸦片战争时期作为殖民地通商口岸的特殊地缘,领事馆、洋行以及殖民者、买办这些与特殊地缘相对应、得到确认的场所和社会身份,在影片中得到了深刻的复现,电影对地缘文化的表现贯穿整部影片,以影像艺术表达地缘政治史实,达到了真实性的历史品格和地缘文化品质的两结合。《苦藏的恋情》(1986)将闽南婚恋习俗、丧葬习俗、祭鬼敬神仪式、海洋崇拜等丰富的民俗影像穿插在两岸隔绝的史实讲述中,浓厚的闽南音画及地缘文化要素运用,赋予了影片较高的地缘文化质感。《欢乐英雄》(1988)、《阴阳界》(1988)的故事时空设置在20世纪30年代的闽南农村,弱化了原著小说的革命叙事,更多地将呈现重心放置在对“人”的讲述上,而活动在这一空间里的人们,其性格、伦理、价值取向与地缘文化同构。
(三)闽南语方言的回归
最早使用闽南语方言作为主要语言体例的电影,可以追溯到1934年12月在厦门中华大戏院上映的《陈三五娘》。闽南语电影随着影人和受众的迁徙尔后流行于东南亚及中国香港等地区;更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中国台湾催生了以闽南语方言为主的中国台湾电视剧的空前繁荣,电影的闽南语方言体例也借由以闽南语方言为主的中国台湾电视剧及中国台湾电影得到传承。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及电影目标,大陆电影中始终难觅闽南语的踪迹,直到《金门新娘》(2009)、《蕃薯浇米》(2020)的出现,闽南语才以一种重逢的姿态回归国产(大陆)电影的创作。《金门新娘》虽然没有使用闽南语作为主要语言体例,但作为联结两岸亲缘之线索的闽南语,占据了电影生活场景的很大一部分,闽南语方言成为推动电影“亲情融合”主旋律叙事直接而又到位的动因。《蕃薯浇米》的故事时空设定在当下的闽南海乡,影片在秀妹姑与青娥的交游中完成了对闽南沿海特有的捡渔获、挖海蛎、晒盐等生活内容的展现,在青娥之死中完成了对闽南民生的生死观、丧葬习俗、戏曲的仪式展演,绘制了一副具有浓郁闽南风情的乡土画卷。全片使用闽南语方言对白是影片进行地缘文化表达最直接而又鲜明的处理,是影片最大的开创意义所在,闽南语方言在与地缘景观、在地知识以及地缘文化性格的深层互动中,营造出一个深具真实感的闽南海乡。
二、“出洋”——闽南电影的海洋观念
闽南靠山面海的地理环境,让闽南人在面对浩瀚大海时往往激发出极高的冒险热情,再加之闽海居于东南亚诸岛国家之间“黄金航道”的地位,自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及兴盛,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下,拓耕海上、经商异域的传统已然深深嵌入到闽南民生与闽南文化之中。自宋元始,不少闽南人以泉州港为始发口岸从事海上商贸并移垦东南亚,泉州诸港淤塞之后又崛起了漳州月港;明清以来,在官方海禁政策的夹缝中崛起的海上商业武装集团大多系闽南族群;清末民初,频发的战乱和灾祸迫使大批闽南人远走南洋,客观上延续了这条曾经中断的海上丝绸之路。[4]
与上述人口迁移情况同样重要的还有闽南人获得成功的个体经验传颂,也就是在“出洋”的人群中,无论是出于开拓事业还是天灾人祸、无论是主动向海还是被迫出洋,都存在着大批于侨居地取得巨大成功的个体,这也就使得“爱拼敢赢”的精神在闽南民间心理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这些个体的成功经验被奉为经典并化为闽南民生的座右铭。可见,离开族居地而“出洋”,既源于地理环境、“海丝”地缘影响下生发的冒险与开拓精神,也是闽南人面对狭窄的生存环境的被动选择,表征着闽南地缘文化中独特的海洋观念。与闽南地缘文化“共生”的闽南电影,自然不能忽视对这一独特海洋观念的呈现。
(一)拓耕海上的民生基质
海洋是闽南区域最为显著的自然景观,也是闽南民生赖以生存的物质性场所,“船在海上、行耕其间”的景观构成了闽南电影空间的关键标识。《蕃薯浇米》对闽南民生的生活内容进行了丰富的展演,秀妹姑的生活内容有“传统乡村”的普遍性:如农忙季在天微亮之时就要动身前往农田劳作,农闲时则在居住的石厝门前养禽种菜。但影片更为着重的是其生活内容的“闽南海乡”特殊性,即海洋地缘为闽南民众带来的沿海生活方式:如退潮时分秀妹姑与青娥一同到海边赶海捡拾遗漏渔获,常常去晒盐场帮自己的媳妇分担一些工作。影片对闽南民生特有的生活内容及生产场景的书写,构建起了具有浓郁闽南文化韵味的生活空间,观影者由此被邀请漫步于影片构建的闽南海乡空间,感受在地性生活内容的美与质感。
(二)崇敬海洋的情感寄托
海洋不仅是闽南民众赖以生存的物质场所,也是闽南民众敬畏崇拜的精神对象,海洋地缘空间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承载闽南民众生活内容以及信仰仪式最为生动的舞台。《蕃薯浇米》中的秀妹姑早年丧夫,将两个儿子抚养成家之后渐渐“不被需要”而处于家庭关系的边缘:一方面是经济关系的边缘,于是她虽年事已高,却依然每天到海边滩涂拾捡遗漏的渔获来补贴家用或是丰富家庭饮食;另一方面是情感关系的边缘,暮年没有伴侣相随,儿子又忙碌于事业,与孙辈的代际隔阂更加重了她的孤独感受,这种孤独只能在亘古不变的海洋上找到共鸣,于是海洋成为了能抚慰其心灵的信仰对象。海洋同样是青娥的信仰对象,她信仰海洋、信仰渔家的保护神“妈祖”,希望大海和妈祖能够保佑正在海上行船捕鱼的儿子顺风顺水、平安歸乡,大海的广阔壮丽亦能够让她暂时忘掉酒鬼丈夫的懒惰和暴戾。《苦藏的恋情》中月芳与丈夫陈当贵苦藏的恋情在浓浓乡情的包围下得到许可和接纳,这对因战争对峙被阻隔海峡两岸的爱侣终于重逢。然而她在中秋月夜等待丈夫归来时,海面却只传来战争的火光,于是她与祭海的渔民们一同跪拜在海边,虔诚地向海洋诉说着自己的悲痛。
(三)向海而生的气节彰显
闽南电影对“走向大海”这一情节或人物行动如此集中、丰富的书写,与海洋地缘、“海丝”地缘相生相伴,赋予影像一种勇敢而悲壮的气质。电影《海囚》以汹涌的浪涛猛烈拍向近岸的礁石开幕,海洋汹涌的能量以及与陆地隔绝的地缘,生发出被镜头表现所强化的未知、凶险体验,由此,观影者更能体会到活动在这一特殊时空中的人物将要遭受的凶险与苦难——一方面是陆地闭塞的生存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乃至殖民者对生存空间的挤压,闽南百姓生活在困顿之中,于是勇敢地走向大海寻求生的可能;另一方面是战争与殖民带来的屈辱苦难以及清政府当局的腐朽,让厦门百姓毅然决然选择暴动反抗,为“走向大海”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三、“归乡”——闽南电影的原乡想象
闽南文化亦是一种农耕文化,对土地的情感体验、儒学传承以及宗族延续的深刻认同形塑了闽南民众“安土重迁”的传统。闽南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大量创业、谋生于海外,无数例证都足以诠释客居异乡的闽南族群无论穷达均难以磨灭对故乡、家园的深深眷恋之情,漂泊与放逐的感觉经验反而更加深化了故土情结在文化记忆中的继承与延续。闽南电影中或显或隐的“归乡”地缘文化主题,表征在电影文本对于原乡的呈现,而这种呈现又随着创作者乃至时代话语的差异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向。
(一)原乡作为美好崇高的心之归处
《情归鹭岛》(1991)中的台商杨凤武,是一个40年前随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退败中国台湾的老兵;两岸融通新政的推行终结了他40年的“情感流浪”,让重归故乡从期盼变成现实;两岸关系的时代新篇章开启,激活了他的故园情结和念祖情怀,于是他放弃了自己在泰国的产业布置并将企业迁回厦门,回到厦门他马上寻回了自己的故居和宗祠,在宗祠前认祖归宗并与故人重逢,接续了断裂40年之久的血缘、乡情。《海囚》中的城市流民张天乙,因为武艺高强且私利熏心,被买办洋行雇佣为头号“拐子手”,强烈的故园情结和乡族意识是他完成“英雄转变”的最大推动力:作为华工贸易全部环节的亲历者,他目睹了殖民者对本族人尊严的蔑视和生命的轻视,被自己阴差阳错下劫掳而来的儿子,也没能得到殖民者的赦免,一直作为同谋者、施难者的他在乡情与亲情的感召下,最终选择以身体抵住迸发的土炮,通过牺牲自己拯救他人完成了“英雄转变”。《小城春秋》中的老华侨薛嘉黍,本着祖国安危为每一位华夏子民心系之事,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祖国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苦藏的恋情》中的丈夫陈当贵,海峡对岸是他的爱妻、家庭和故乡之所在。上述人物所具有的家国情怀、故园情结以及敬祖认宗的精神性寄托,源于对作为“离乡”之出发港和“归乡”之登陆港的闽南地缘自觉,闽南故土即是这些离散者对于美满原乡之想象的承载。
(二)原乡作为落后野蛮的生死场
闽南电影对于原乡的想象与呈现并不局限于“吾心归处”般的美满想象,而更常见于以“出洋”的经验反观原乡的落后、封闭及野蛮,进而以启蒙的姿态呼唤文化的现代性。例如《欢乐英雄》中的蔡老六,在电影故事中设定为一个漂泊南洋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共产主义活动的开展与南洋诸岛国家陷入低潮时逃难而归乡;蔡老六的视角其实就是电影作者的视角,经由蔡老六的人物行动及故事参与,将故乡的落后、野蛮、积弊毫不留情地放置在一个个生死场里面:影片中的两个本土宗族之间不明所以地进行械斗,宗族子弟一个接一个的致残疾、被杀害,不断继承着“宗族要打冤家,我们这些后辈也还要打冤家”的世仇,缠绕着人物的生和死;国民党反动派军官林雄模被派遣坐镇“为民镇”以化解革命矛盾和宗族矛盾,然而作为外乡人的林雄模并不是一个“解铃人”,他一味信奉武力以降服或“斩草除根”的方式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却又激化了一个更大的“生死场”,将两支宗族屠杀几近灭族。正如创作者吴子牛所言:“这两部影片虽然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矛盾纠葛纷繁,但归根结底,它展现的是一个生死场……我们毫不留情地展观自相残杀引起的死亡和毁灭,唤起来自方方面面或多或少的戒备与思考”[5],影片“冷静”地将人物放置在这样一个又一个、一环扣一环的“生死场”之中,毫不留情地将宗亲关系、宗族制度与人物悲鸣、屈辱、死亡的结局缠绕在一起,让人物的生死命运大于政治斗争的胜负,以冷峻的“薄情”对闽南地缘文化的另一面进行反思和批判,唤起现代人对传统糟粕的戒备和对生命的思考,这是影片最具冲击力的表达。
四、“交汇”——闽南电影的景观呈现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使广阔海洋上的诸多国家和地区与闽南产生了紧密的经济联系,与此伴生的文化层面的接触交互、共生共融,成就了闽南既是本土文化的出口又是外来文化之入口的“交汇”,不同文明、文化的交汇,不断结构与重组着闽南文化的符号和信仰系统,既保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内在肌理,又展现出如同海洋一般斑驳陆离、难以捉摸的特质。这一特殊地缘形塑下的“交汇”景观,表征在闽南电影文本对民间信仰特质的影像言说以及多元混杂的文化符号书写中。
(一)信仰景观的奇异丰富
一般来说,我们把民间信仰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原始先民因无力抵抗自然灾害而对自然力产生畏惧,于是在精神世界里逐渐形成信仰心理并在实践中产生祭祀活动。闽南背山面海、耕地稀缺的恶劣生存条件,叠加闽越蛮荒之地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状况,闽越先民的生存只能听命于自然,自然力的兇险和强大助长了其对大自然的敬仰与崇拜。[6]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下,闽越先民“信巫事鬼”的传统被从中原迁入的汉民继承,再加上宋元以后的海上丝绸之路带来“万国宗教”、明清之际出海“冒险犯禁”等地缘文化特质的浸入,一方面奠定了闽南民众广泛的信仰群体基础,另一方面则使闽南民众普遍产生了功利主义即“是神则灵”“为我所用”信仰景观。
闽南电影对民间信仰形态的影像言说,首先落足于对民间信仰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盛大信仰仪式的展现:《苦藏的恋情》中,人们无论是生育还是丧葬、进宅还是婚嫁,都少不了对神灵进行祭祀的仪式。《欢乐英雄》《阴阳界》中,上上木和下下木之间存在世仇而不断进行械斗,唯有在中元节祭祀鬼魂的仪式中才愿意放下干戈,共同操办仪式。《情归鹭岛》中归乡的中国台湾同胞,重返故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前往宗祠及神庙祭拜,告知祖上先灵自己对故土的眷恋。《金门新娘》中的金门洪家,无论是离家还是归家,考试还是生病,平日还是时节,生活中的所有事项都不忘在家庭的祭台或者前往庙宇进行祭祀。《蕃薯浇米》中秀妹姑作出参加“夕阳红”腰鼓队的决定,以及腰鼓队作出接纳秀妹姑这一位耄耋老人的决定,都是经由“妈祖”的指引,甚至于秀妹姑对小孙子能够接回到自己身边的念想,都是寄托于神明显灵。
其次是对于“是神则灵”“为我所用”信仰特征的提取以及电影叙事参与。“闽越好祀鬼神的巫觋文化,使闽台长期具有多神崇拜的信仰习俗,举凡大树、巨石、灵禽、猛兽,或风或雨,或人或鬼,甚至一段枯骨、一处山水,只要能避灾却难、赐福降瑞,不问其神灵系统,都可以作为信仰对象。”[7]例如,《欢乐英雄》中被传统伦理紧紧束缚的玉蒜,将这份无法实现的需求寄托在村落古老的榕树中,希冀榕树之灵能够宽慰自己的“污浊”、能够显灵改变自己与丈夫当下隔阂的处境;《海囚》中的张天乙在为攫取经济利益而参与到“卖猪仔”的罪恶勾当之后,不论体系、无需仪式地在各路神佛之下跪拜而祈求一种“罪恶的安宁”;《阴阳界》蔡老六的“复仇”情节中,人的力量和行动上的局限性在闽南地域这股神奇的信仰力量中得到了弥补。
(二)文化景观的混杂共融
这种表征在景观中的文化互相交融和混杂现象,是“海丝”文化最重要的底色。景观作为闽南电影最表层的印象,成就了闽南电影地缘空间的标识,同时涵化了其最深刻的地缘文化基质。例如民居建筑,闽南地域的历史遗风、传统文化的继承构成了地域民居建筑的基本形态,对所在地域产出的建筑材料以及地形气候的适应塑造了其独特风貌,又在与“海丝”带来的海外文化的交融下产生了新的变化,因此,人们能够看到《蕃薯浇米》中秀妹姑、青娥生活其间的石厝构成了影片意图复现的闽南海乡的基础;《小城春秋》镜头表现的鼓浪屿万国别墅、骑楼、“番仔楼”,是影片撑起“小城”地域支点及进行地域性表达的载体;《金门新娘》镜头对厦金两地风格一致、形态相当的红砖大厝的展现,完成了厦门、金门两地之间“民生之缘”的表达。再如电影《海囚》对“领事馆”“洋行”等故事空间的影像形塑,从空间的摆设观之:木质带有中式纹理的窗户上挂着精致的西式布艺窗帘,中式书桌上既有笔墨纸砚亦有羽毛笔,红木色的茶桌、博物架上排满了红酒与威士忌;环视整个领事馆空间,居于正中地位的是一副维多利亚女王像,四周摆放了代表西方殖民者的狮像、鹰像等物件。西方文化符号与中国文化符号的并置,使空间呈现出一种文化混杂感,这一文化混杂感正是来源于厦门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既是本土文化的源生地又是外来文化入口的想象,契合厦门作为殖民口岸的特殊地缘。
结语
闽南电影“出洋”“归乡”“交汇”的地缘文化主题,既是绵延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回响,亦包含着在不同时代同一地缘的文化交互与拓展。闽南地区从未断裂并随着时代发展愈发显示出其价值意义的地缘文化,对所在区域的电影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地缘文化既是闽南电影得到命名合理性的标识所在,亦是推动闽南电影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完成正名、扬名过程的关键所在。
可以预见,闽南电影将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程中以更加清晰、多元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积极参与到中国电影地理版图的构建之中,共同描绘中国地域电影更加绚丽的未来。
①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作为福建省唯一拥有电影生产条件的福建电影制片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才得以创作本厂的第一部故事片。
参考文献:
[1][4]刘登翰.海上丝绸之路、海丝文化与闽南[C]//第三届两岸文化发展论坛论文集(上册),2015:43-44.
[2]贾磊磊,李震,牛鸿英等.作为理论方法的地缘文化视域:中国电影文化图景的一种阐释路径[ J ].艺术广角,
2020(03):4-14.
[3]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57.
[5]吴子牛.第二自然——《欢乐英雄》、《阴阳界》导演心得[ J ].电影通讯,1989(02):18.
[6]郑渺渺.民间叙事与精神追求——闽南民间故事中的民间信仰[ J ].文艺争鸣,2006(05):145-150.
[7]刘登翰.海峡两岸文化发展丛书 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