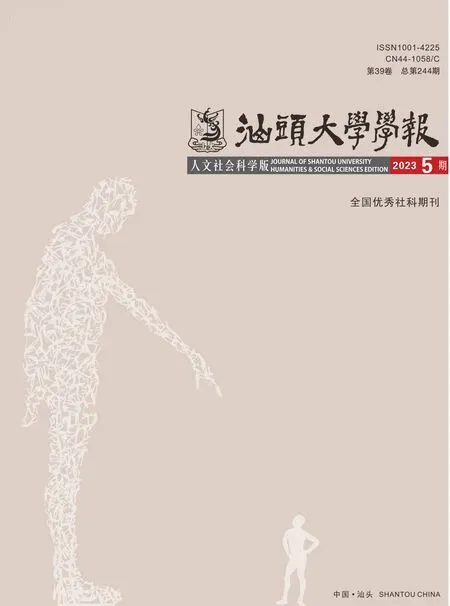杰克·伦敦的亚太叙事与种族伦理意识
2023-12-28王丁莹
王丁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虽然杰克·伦敦因其北疆小说声名鹊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通过海洋进入文学世界的”[1]。维罗妮卡·瓦申克维奇(Weronika Łaszkiewicz)更是将他誉为“写作中的水手、航海中的作家”[2]。13 岁时,衣衫褴褛的伦敦攒钱买下了一条旧船,开始在旧金山湾上练习航行技术[3]23-24。由此,贯穿其一生的海洋情结便开始生根发芽。到了1907年,成为畅销书作家的伦敦才真正拥有了自由航行的经济实力。于是,他循着约书亚·斯洛克姆(Joshua Slocum)的足迹开始环球航行。尽管环球航行因伦敦身体恶化,最终未能完成。但率先完成的亚太航行成了他人生最后阶段的创作源泉。亚太叙事是19 世纪美国文学的传统母题,自赫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将泰比岛塑造为“人间天堂”以降,美国作家就追随着其步伐对亚太地区展开了浪漫的文学想象。到了20 世纪,恰逢美国对外扩张,它将自己的“后湖”扩张到整个亚太地区。作家们对该地区的文学想象与帝国扩张互补互动,伦敦的作品自然也在其中。不少学者都从帝国意识形态的视域解读伦敦的亚太叙事。罗德·爱德蒙德(Rod Edmond)从疾病与身体入手,探讨了殖民入侵对土著文化的破坏。而詹姆斯·伦德奎斯特(James Lundquist)认为,伦敦在种族书写中表达出了对被压迫民族同的情感,使他摆脱了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但是,这些非黑即白的解读都忽视了作家复杂多样的主体意识和含混杂糅的伦理选择。亚太叙事是伦敦根据旅行见闻加工而成的,那么,聂珍钊的“脑文本”将会拓展这一过程的阐释空间。本文将借助“脑文本”的概念,从《麻风病人库劳》(“Koolau The Leper”)的改写入手,探讨以民族抗争取代家庭情节,是否真的是种族正义的伦理选择?那么,为何亚太叙事又对中国疫病化,呈现出种族伦理的悖论呢?文章聚焦于伦敦四次亚太旅行所形成的文本,将其种族伦理意识置于19 世纪初末的历史语境中,解开文本中的伦理悖论。
一、库劳故事的改写与脑文本
如果要试图阐释《麻风病人库劳》的改写,就要先厘清伦敦亚太旅行的动机与原因,这一动机也促成了他将如何展开亚太世界的文学想象。据伦敦传记记载,伦敦夫妇是在阅读了斯洛克姆的《环球独航》(Sailing Alone Around the World,1900)燃起了冒险的激情,放弃了加州的农场生活,开启了亚太航行。不过,从伦敦作家身份的角度看,他的航行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自己的创作找寻更多的灵感与素材。据船上的厨师马丁(Martin)回忆,“蛇鲨号”就如一座海上的文学宝库,满载着杰克写作用的纸,打字机用的纸,数以百计的纸;还有杰克挑选的五百本书籍,涉及不同的主题[4]。此外,伦敦的亚太旅行也有经济收益方面的考虑。他在出航前就与《妇女家庭之友》(Woman’s Home Companion)签定合同,承诺将南海冒险记录下来呈现给对“远西之地”充满好奇的美国读者,后者为他提供经济支持。但是对于亚太叙事的创作而言,彼时经济收益已不是伦敦的主要驱动力,因为他已誉满国内,技艺也日臻完善。也即说,在创作前期,“他期待写作的投资能得到回报,他长期约束自己,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但“一旦技艺娴熟,地位稳固,他又信心满满地对这项职业表现出几乎不屑的态度”[5]。于是,他成了自己笔下马丁·伊登(Martin Eden)的幽灵,内心的真实感受成为其亚太叙事的首要表达目的。那么,伦敦的亚太叙事是如何体现其内心感受与伦理选择的?
伦敦对库劳故事的改写之处就体现了他的伦理选择。据推测,故事的原版本由“蛇鲨号”的水手伯特·斯托尔兹(Bert Stolz)口述而得[6]。该版本比较可靠,因为斯托尔兹的父亲是14 年前被库劳(Ko’olau)杀死的白人警长。根据他的口述,库劳是夏威夷岛的土著,因为患上麻风病,当地政府要求其去莫洛凯(Molokai)隔离。库劳同意隔离,但希望和自己的妻儿在隔离区共度余生。因为他的妻儿都没有感染麻风病,政府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库劳带着他的家人逃到了考艾岛(Kauai)的山谷中,还杀死了一个前来抓捕他的警长。两年后,库劳的儿子因染上麻风病死去,随后库劳也死去,妻子派拉妮(Pi’ilani)埋葬了他们后回到家中①Kahikina Kelekona(John G.M.Shelton)在1906 年用夏威夷语将派拉妮的口述记录下来了,然而并没有考证表明伦敦懂夏威夷语且读过Kelekona 的版本,并且这份原住民原始档案一直被学界忽略。。而在《麻风病人库劳》中,伦敦删去了浪漫的爱情与家庭故事情节,代之以夏威夷首领库劳带领族人的反殖民抗争。他笔下的库劳是一位魅力十足的尼采式少数族裔英雄。
在做出这一改写时,伦敦其实是把斯托尔兹的口述文本储存成了脑记忆,再呈现成了书面文本。聂珍钊提出的脑文本概念恰巧为解释这一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撑——“当一个人通过听觉器官接收到另一个人通过发音器官转化成声音符号的脑文本时,就转化成记忆存储在自己的大脑里,变成又一个脑文本”[7]。构成脑文本的基本单位是脑概念,伦敦借助脑概念进行思维,根据某种伦理规则不断对脑概念进行组合和修改[8]33,并将其转化成以文字或符号为载体的书写文本,伦敦通过修改脑概念加入了自己的伦理选择。另一方面,聂珍钊将“人的大脑类比于计算机中的中央处理器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脑文本类似计算机中的运行程序”[8]30。而根据乔纳森·奥尔巴赫(Jonathan Auerbach)的《男性的呼唤:成为杰克·伦敦》(Male Call: Becoming Jack London,1996)一书所言,20 世纪初自然主义的风行,使得作家们重新审视了从身体(大脑)到机器(打字机)的写作机制。在提到这一机制时,伦敦使用了输入/输出的隐喻,他把打字机想象成作者和文本之间的接口。伦敦声称,修改只发生在打字过程中,通过打字定稿后,提交的手稿就会变成印刷品被出版[9]。虽然,此处伦敦试图强调写作的机械化生产模型,但是这一隐喻将打字机延伸为脑文本的生产场所、人体的外挂中央处理器,使得脑文本到物质文本的过程更加具象化,进一步证实伦敦的改写并非灵光乍现,而是有意为之。通过比较库劳故事的变化,可以看出伦敦脑概念重新编码的过程中的伦理倾向。
《麻风病人库劳》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改写之处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从人物设定上,伦敦放弃了妻子和儿子两个人物,增加了一群与库劳共同藏身山洞中的夏威夷麻风病人,淡化了家庭与爱情的因素,构建了一个民族共同体。故事开头库劳以“我们”[10]47、“兄弟”[10]52与麻风病人相称,与“他们”(白种人)划清界限。因为拒绝被送到莫洛凯,库劳作为首领,与族人共同建立了一个岛外伊甸园,“一个鲜花盛开的峡谷,有着令人生厌的悬崖和峭壁,上面布满野山羊的粪便。三面墙壁布满着热带植被和洞穴入口——里面是臣民们的岩石巢穴”[10]51。其次,与流传的口述版本相比,伦敦将大量笔墨用于麻风病人体貌特点的描述。他将他们比作造物主发癫时失手造出的怪物:
他们曾是男人和女人,但现在不再是了。他们是怪物——在面孔和形态上都是人类的怪异漫画。他们可怕地扭曲着,看起来像是在千年地狱中被折磨过的生物。他们的手就像鹰身女妖的爪子。他们的脸奇形怪状,犹如发狂的造物主在生命的机器中随意玩弄的产物,被碾压、被擦伤。到处都是造物主抹去了一半的痕迹。有一个女人正在流泪,从两个看不出来是眼睛的可怕的洞里。[10]49
伦敦对病态肌体的细致描写绝非只是想渲染麻风病的恐怖,而是想借机“揭露殖民体系对当地文化产生的影响”[11]203。这种影响对脆弱、自给自足的南海生态系统往往是毁灭性的。由此,在原故事版本中,未被强调的疾病表征被伦敦刻意放大了,而夏威夷人的病态肌体与巴赫金(Bakhtin)所谓的“怪诞形象”(grotesque image)相呼应。怪诞形象是指在死亡和诞生、成长和形成阶段,处于变化、尚未完成的变形状态的现象特征,犹如一种活死人的状态[12]29。它是开放的身体,与世界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它与世界、动物、物质相混合[12]32。正是这种阈限性具有颠覆白人权威话语的力量,使得伦敦的版本将叙述重点放置在库劳带领其族人的英勇抗争上。再次,伦敦也将叙述人从原版本中的妻子派拉妮转化为无名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与《骄傲之屋》(The House of Pride)中其他两部以白人为主视角的麻风病故事不同,他(她)仿佛站在库劳的立场,赞美其对前来逮捕他的士兵发出的“我曾生得自由,也将死得自在”的宣言[10]50。故事中,即使山谷家园被炸得稀碎,库劳也没有投降,他带着毛瑟枪躲进丛林中,直到手指溃烂到不能扣下扳机,他将毛瑟枪放在了胸前[10]86,以这种姿态死去。伦敦对库劳临死时这一细节的描写表达了他对夏威夷人至死抗争的赞赏。
上述改写塑造出一位尼采式的夏威夷勇士,由此表达出伦敦对夏威夷民族的欣赏与同情,这一内心感受透露出他在脑文本的重组过程中对种族伦理的思考。伦德奎斯特将这一伦理选择进行了过度地渲染,他认为“伦敦对波利尼西亚人还是西瓦什印第安人公开表达的同情之心,使得他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的错误的指控被推翻”[13]。诚然,库劳故事的改写为分析伦敦的种族伦理倾向提供了文本支持,但是对于伦敦这样一位身处美国发展关键期的文化研究对象来说,非黑即白的绝对判断未免太过简单,其思想具有复杂的悖论性,我们需要更加全面地解构他的亚太书写,从而为其改写作出更为深刻的伦理注解。
二、亚太叙事与种族伦理悖论
伦敦曾借库劳之口将麻风病的来源归咎到在蔗糖种植园中干活的中国苦力身上,这一情节将黄种人妖魔化,显然与他对夏威夷少数族裔的欣赏相悖。麻风病被称为“中国疾病”(mai Pake)[11]195的说法显然缺乏科学依据。1865 年,夏威夷政府在出台《防止麻风病扩散法案》时,将麻风病的官方名称改为了“隔离疾病”(mai ho’okawale)。然而,在多数美国作家的夏威夷书写中仍保留了这一称呼。“按照瘟疫文化理论的解释,疾病之前附着种族或者地名。并非无意之举。它是将疾病归罪于他者的一种很自然的手段”[14]。将麻风病命名为“中国疾病”,无疑同将肺结核称为“犹太人疾病”的做法类似,具有妖魔化他者的意识形态目的。
纵观伦敦的整个亚太叙事可以进一步读出他对东亚黄种人的歧视与蔑视,从而引发对其种族悖论的深入思考。他一生曾四赴亚太航行,使他得以深入认识东亚的地域环境和东方人的性格特征,因此,他的亚太旅行叙事成为研究其笔下东方形象的重要文献。他将亚洲人称作“亚洲佬”(Asiatic),认为黄种人天生精明狡诈,表现出一种仇视与憎恶的态度。与上文中对夏威夷族人英勇坦荡的赞颂形成对比,使得亚太地区成为其伦理悖论的试炼场。可以说,伦敦的日本之行开启了他的写作生涯。17 岁时,他随“苏菲·萨瑟兰号”(Sophia Sutherland)到日本海域猎取海豹,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在母亲芙罗拉(Flora)的劝说下,他用《远离日本海岸的台风》(Story of a Typhoon off the Coast of Japan,1893)一文参加了《呼声》杂志举办的写作比赛,并夺得了一等奖[3]40,这件事情坚定了伦敦要靠脑力赚钱的决心。《台风》一文对风暴进行了生动的记叙,但并未突出故事的发生地。而同时期创作的《夜游江户湾》(“A Night’s Swim in Yeddo Bay”,1902)则投射出伦敦对贪婪的日本性的厌恶。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展开,讲述了一位名叫查理(Charlie)的美国老水手醉酒于横滨,被日本水手钳制后,要求以衣物抵船票的故事。该作品只将美国水手的视角单向地传递给读者,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目的性。在查理看来,“日本人通过狡诈的伎俩来夺得西方物质文明”[15],这种急切的渴望则侧面表达出作者的种族优越感。1904 年,当伦敦受赫斯特邀请,前往东亚报道日俄战争时,他的亚太文学创作出现了转折点。赫斯特报业政治倾向明显,一向以煽动民族矛盾著称。比如,它曾在1896 年煽动美西战争,支持美国侵略扩张的行径。而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赫斯特报业带头呼吁对电影进行严厉检查,美国电影业因为害怕而几乎瘫痪[16]。鉴于此,伦敦的战地报道一定程度上与其雇主的倾向同音共律,表达出对白种人的欣赏和对黄种人的贬低。他在报道中将日本比作猴子,把日方的胜利归功于民族的好斗与狡诈。他写道:“你有没有体验过站在一个笼子面前……那只猴子的表情如此天真、友善,两只眼睛紧盯着你,毫无恶意,而暗地里却在挪动着脚,妄想趁你不备向你突然袭击。所以,要加倍提防笼子里的猴子……当心日本人!”[17]可以看出,他对日本人的态度由厌恶转为恐惧。日本战胜沙皇俄国意味着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西方国家此时感受到了来自明治日本的威胁。而伦敦为大和民族贴上“军事黄祸”的标签。这些战地报道成为伦敦日后亚太叙事的前文本(pretext),构成了他的种族伦理与国家身份认同。
伦敦笔下的东亚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国形象在“黄祸论”的整体基调下呈现出与“军事黄祸”不同的民族特性。在1902 和1903 年创作的系列短篇《白与黄》(“White and Yellow”)与《黄手帕》(“Yellow Handkerchief”)中,伦敦首次将中国人塑造成文本的主角。他以青年时期在旧金山湾当牡蛎海盗与渔警的经历为蓝本,复刻了白人渔警与中国捕虾者的冲突。伦敦借少年渔警之口表达出他心中中国人精明重利的民族特性——他们将网弄成最小的格,“甚至连那些不到0.25 英寸长的新孵化的小鱼卵都不放过”[18]。中国性在1904年的《黄祸》(“The Yellow Peril”)一文中被进一步定义。炮声轰隆下,中国百姓一点也不惊慌,他们仍照常耕作、沿街叫卖。这些日常情景的描述看似是对中国人的欣赏,但伦敦接着表达出的担忧否认了这一观点:中国地广物博加之勤奋的民族特性,若有人唤醒了这头拥有四万万人口的睡狮,一定会威胁西方的安全。西方人永远不可能唤醒它,而“棕色”的日本人极有可能做到。彼时,联合的亚洲必定会给美国的经济与安全都带来重创。所以,伦敦呼吁西方世界决不能容许“黄祸”发生。“虽然伦敦并非‘黄祸论’的始作俑者,但根据自身经历对亚太时局的分析和预测与帝国时代需求相吻合,而他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叙事也基于同样的全球性视域”[19]86。在其乌托邦叙事中,伦敦幻想以中国人的种族灭绝消解了“黄祸”的威胁。创作于1907 年的两部短篇小说《史无前例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和哥利亚(Goliah)主题相似,以科幻的形式对《黄祸》做了进一步的注解。不妨拿《史无前例的入侵》做例子进行解读。《入侵》将时间推进到1970 年,中国的人口已达5 亿,远远超过世界上白人人口的总和。西方各国担心他们很快就会被黄种人的移民浪潮淹没。一位美国科学家提出用细菌弹对中国进行轰炸,然后进行长达5 年的“卫生消毒”。伦敦显然关注到了新兴的优生学话语,因为他在作品中把孟德尔学说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策略。一旦人口增长远超过可用资源,就在多民族的融合中培育出一个最优秀的种族存活[20]。而这一策略的代价是牺牲不可同化的中国人。勤奋且聪明的中国人在以商业化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给美国人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使得伦敦笔下的中国成为不同于“军事黄祸”的“经济黄祸”。
在亚太叙事中,伦敦对同处于东亚的朝鲜虽着墨不多,但通过少量的叙述可知其族人贫穷又怯懦,充满了奴性,是天生的“仆人”。斯通的伦敦传记《马背上的水手》(Sailor on Horseback,1938)记录了他在日俄前线与朝鲜人的冲突。他的马夫向军司令部索取马料时,一个朝鲜人不肯给他全份。当伦敦指责那个朝鲜人克扣了马料,对方用刀子做了恐吓的姿势,而伦敦则一拳把他打倒在地[3]171。这一小插曲充分展现出他心中朝鲜人的民族特性——他们贪婪但是缺乏力量,这源于被占领几个世纪后形成的奴性。当日本人经过时,朝鲜的村庄和城镇都被遗弃了。没有农田,也没有人做买卖。几十个朝鲜青年抽着几码长的烟斗,他们精力旺盛、身材健美,但却习惯了被打、被抢,从不反抗。总得来说,伦敦认为他们的政府很腐败,人民缺乏主动性。但是,作为役畜,他们却很完美。所以,伦敦在离开东亚时,给了忠实的朝鲜少年马仰箕旅费,雇佣马仰箕到他美国的家中,为他收拾房子、做饭[3]174。由此可鉴,伦敦对朝鲜人的忠诚表示认可和赞赏。但是,又因认为其民族不具有自主性和自强精神,伦敦将朝鲜人视为劣等人,表现出白人的优越感。
伦敦的亚太叙事充满了矛盾与悖论。在“黄祸论”的整体基调下,东亚三国族人呈现出异质性——他视日本人为“军事黄祸”、中国人为“经济黄祸”、朝鲜人为最忠实的仆人人选。这与前文所述的夏威夷话语相对比,呈现出极大的张力。所以,对伦敦的种族伦理观念不可做单一的决断。正如里斯曼(J·C·Reesman)所言:“他对亚洲、对种族的看法与态度显然要复杂得多。虽然伦敦曾认同其所处时代对亚洲人的种族偏见,但他(对种族伦理)的思考远非止步于此”[21]。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停留在矛盾观念的展现上,而是要去挖掘与理解其亚太叙事中种族悖论形成的脉络。这正符合聂珍钊提出的文学文本批评的本质任务——具有矛盾与冲突的观点构成了文本的伦理结,“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任务就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发现伦理线上伦理结的形成过程,或者是对已经形成的伦理结进行解构”[22]13。
三、伦敦的种族伦理意识
如前所述,当伦敦将库劳故事的口述版和其他亚太旅行所见所闻以文字的方式写下时,这一过程必然涉及伦理意识的反映。那么,在亚太叙事的脑文本加工成文字文本的过程中,伦敦是受何种伦理规则的支配表现出如此强烈的种族伦理悖论的呢?总得来说,伦敦一生接受的思想学说极为繁杂。斯通将“达尔文、斯宾塞、尼采、马克思”[3]92归纳为指引其创作的“四驾马车”。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斯宾塞、尼采、马克思都曾受到进化学说的影响。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1867)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发表于同一时期。在随后出版的序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引用了进化论来加强自己的观点。他们写道: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斗争[23]。斗争与进化是进化学说的核心观点。《资本论》把社会看作是一个进化到目前阶段的有机体来研究。尼采也是进化论的支持者,因为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生命意志[24],“超人”是进化论发展的最终产物。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的序言中,尼采对进化表达出更加明确的观点。他说:“人是深渊上的绳索,在动物和超人间拉伸”[25]。我们可以把人看作是动物和超人间进化的某一阶段,人类的未来或是返祖、或是永恒超越。由此,达尔文的进化论为马克思和尼采的学说提出了有力的注解。
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达尔文框架上发展出来的,在内战后传入美国,彼时正值美国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资本家将其奉为圭臬,因为它恰巧为商业竞争和适者生存提供了理论依据。据考证,1860 年至1903 年期间,斯宾塞的著作在美国销售了368 755 册[26],使他一跃成为19 世纪末美国的文化偶像。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分析了斯宾塞热的原因,他说“斯宾塞用一种表面上很深刻的语言来表达自己,但实际上完全可以被视为未完成教育的、自学的,甚至是文盲这类群体理解接受”[27]。伦敦就是在自学期间大量阅读了斯宾塞的著作并将其作为其文学创作的理论依据。《海狼》(The Sea Wolf,1904)中,拉尔森反复强调一种“酵母哲学”——“大吃小才可以维持他们的活动,强食弱才可以保持他们的力量,越蛮横吃得越多,吃得越多活动得越长久”[28]。“酵母哲学”就是斯宾塞学说的翻版。尽管纵观伦敦的一生,其思想一直处于波动与流变中,但以斯宾塞哲学为主导的进化学说贯穿于他的创作之中。正如他借“另一个自我”马丁·伊登之口说:“进化为生命的万能钥匙”[29]。那么,亚太叙事中伦敦对夏威夷的同情与对东亚三国的贬低也是与进化学说同音共律的。
伦敦对夏威夷土著的同情并非源于对种族压迫的反思,而是对斯宾塞伦理的实践。斯宾塞将道德、幸福、价值等概念融入进化学说,提出“道德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所谓行为的善恶,都是由行为能否有利于生命的自我和繁衍决定的”[30]。“自然进化”有着趋利避害、保护自我的倾向,从有助于生存的行为中获得快乐。这种进化的结果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这种幸福是建立在利己主义的基础上的。在伦敦夫妇开始“蛇鲨号”航行的十年前,也即1898 年,夏威夷已被美国吞并,导致亚太地区的争夺开始成为美国的战略重心。在夏威夷作品创作之时,夏威夷与东亚相比已不是“他者”,而是美利坚共同体的一部分。在已确保自己国家“前哨”安全的情况下,伦敦赞美夏威夷土著库劳的英雄行为,间接为1901年美国颁布的“海岛案例”(Insular Cases)对夏威夷不平等的公民权而发声,这正与斯宾塞所倡导的“最大幸福”相呼应。同时,伦敦还借助作品中对美国和夏威夷政治冲突的淡化和改写来消除美国吞并夏威夷的不道德感。在去世前最后一次游历夏威夷时,伦敦创作了短篇小说《我的夏威夷之爱》(“My Hawaii Aloha”,1916)表达出他对夏威夷的归属感。他认为,“夏威夷人是任何外来人能得到的最引以为豪的荣誉……总有一天,当我谈起我自己,我会说,‘我是一个夏威夷人,我属于夏威夷’。这便是我的夏威夷之爱了”[31]。
而对于未被纳入美利坚共同体的东亚三国,伦敦在其脑文本转化为文学文本的过程中,受到斯宾塞伦理的无意识影响,采取了打压与丑化的态度。在亲历了“东亚现场”的伦敦看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进入了帝国主义行列,撼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新的世界史将会开始。若中国这条东方巨龙觉醒,必然使得太平洋成为各国争夺的中心。那么,基于斯宾塞伦理的第一原则,伦敦将个人和国家幸福置于首位,幻想将东方“他者”消灭。这种幻想在他的科幻乌托邦叙事中达到高潮,他将中国置于病毒灭种的危机下,展现出一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的极端应用。伦敦以美利坚民族共同体为核心创造的完美世界不仅用投掷病毒的手段剥夺了东亚人的生命权力,更是剥夺了东亚种族的生育与繁衍后代的权力。他笔下人类发展的终极状态是让黄种人永远留在历史之中,只有这样,美国人的幸福才有保证,太平洋地区才不会成为东方的“前哨”。早前国内研究形成了伦敦是一名社会主义作家的刻板印象,而本文得出的种族伦理意识似乎与社会主义的“全人类共同体”相矛盾。其实,伦敦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始终流露着一种故作姿态,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利用社会主义为自己建立一种保护制度,确保自己不会从已登上的白人精英地位跌落。也即说,伦敦的社会主义不是设计出来为全人类谋幸福的理想制度,而是为有着同样血缘的种族谋幸福的,其目的是使那些拥有特定血缘的“优等种族”更加强大,使他们生存下来,继承土地,消灭“劣等民族”[19]264。由此可见,《麻风病人库劳》的改写与亚太叙事所展现出的种族伦理悖论实则都被斯宾塞伦理所支配与渗透。
现实世界的伦敦处于美国19 世纪向西运动的浪潮中,作为帝国冒险家,他乘着时代的浪花来到远西之地,试图循着麦尔维尔的步伐,重拾东方伊甸园的美好想象。而在其亚太叙事的文本世界,远西之地并非一块同质化的土地,夏威夷与东亚三国呈现出了巨大的悖论与张力,使得伦敦本人的伦理意识变得更加复杂、难以分析。但是,若参照聂珍钊的观点,将挖掘作家的伦理意识与剖析文学人物的伦理选择进行比对,都“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22]4,就能解开这一伦理结了。伦敦受19 世纪末美国社会上斯宾塞风潮的影响,并结合自身感悟与经验将自己的种族伦理意识投射到亚太叙事的文学影像中去了。在现实与文本的交汇地带,正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riticism and Imperialism,1993)中所强调的“文化与帝国扩张之间的关联”:我们要把艺术放到全球的现世背景中来考察,所以,帝国主义时期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或多或少会受到时代的影响[33]。至此,亚太地区在此被抽象化,不仅成为伦敦种族悖论发生的场域,更是东西方文明冲突与争夺的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