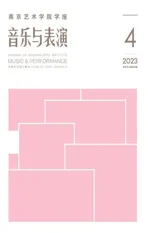21世纪以来国内音乐“摘引”研究的回顾与思考①
2023-12-26王婷婷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安徽合肥230013
王婷婷(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合肥 230013)
在音乐创作中,一首作品中摘引另一首作品相关元素(通常为曲调)的现象,古今中外尽皆有之,引发了中外音乐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诸多学者从作曲技术、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对这一现象的命名、分类、历史、文化功能、美学意蕴等问题进行了饶有建树的探讨。
国外相关研究较早关注到这一现象,如美国《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1]、德国《音乐的历史与现状》[2]中均设有阐释该问题的相关条目,并有一批围绕该专题的论文乃至专著。②这些文献包括Motives for Allusion: Context and Cont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Music.Christopher A.Reynolds As Theorist[M].US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克里斯托弗·雷诺兹的《影射的动机:19世纪音乐中的语境与内容》(Christopher A.Reynolds: Motives for Allusion:Context and Cont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Musi[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王遒.马赛之魂——19世纪欧洲音乐对《马赛曲》的摘引与改编[J].人民音乐,2014(5);刘博.贝尔恩德·阿洛伊斯·齐默尔曼音乐创作中的拼贴技法研究[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20;叶贝.二十世纪西方音乐“拼贴”技巧初探[D].北京:中央音乐学院,2010,等等。
国内有关此论题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以钱仁康先生于2001—2003年相继在《音乐艺术》上发表的《巴赫〈b小调弥撒〉中的“旧曲新歌”》《莫扎特“借题发挥”的创作实践》《“音乐典故”刍议》3篇论文开先河。作者以其广博开阔的学术视野、扎实精湛的音乐分析与外文阅读能力,为国内的西方音乐及相关学科研究引入并展现了一片别致的景象。近20年来,国内学者相继发表了一批围绕该专题的文论。现述评如下。
一、前人研究回顾
对于这样一种中外音乐创作中皆有的现象,学界有诸多不同的命名。仅就国内学者而言,就先后有钱仁康提出的“旧曲新歌”“借题发挥”“音乐典故”,李彦频、张晨等提出的“摘引”[3][4],吴慧娟、王旭青等提出的“曲调引用”[5][6],张彬彬等提出的“借用”[7]以及多人采用的“拼贴”“影射”等,这反映了不同历史背景以及不同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差异。这些命名虽各不相同,但并不妨碍学者们在总结归纳其概念定义上的统一性,即都认为“摘引”(抑或是“引用”)中,被引曲可以是专业创作,也可是民间音乐;多为他人所作,但也可是自己的作品;可以摘引一首,也可同时摘引多首乐曲;通常引用片段,较少整体摘引;摘引多集中于曲调层面。
近20年来,国内围绕音乐摘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方专业创作领域, 涉及曲目多为西方各历史时期名家所作(或民间音乐)并在创作中得以广泛摘引、传播的音乐名典。从“创作曲”与“被引曲调”之间的关系来看,西方“音乐摘引”可分为器乐作品或声乐作品各自内部的互引以及器乐作品对声乐作品片段的摘引三种类型,或可表示为A-A、B-B、A-B三种组合。而在排列组合理论上成立的B-A,即在一首声乐曲中摘引某器乐曲片段的类型,由于在西方音乐中尚为少见,暂可忽略。
第一种类型A-A,即在器乐曲之间的互引。作为西方专业音乐创作中最为常见的“摘引”类型,这是前人研究中关注最多的。在诸家反复征引的个案中,如以表达活跃向上性格为主的“曼海姆主题”,就常被西方作曲家引用于创作性格与其相关联的作品中。这一主题在贝多芬《f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主部主题、《第五“命运”交响曲》第三乐章、门德尔松《e小调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主部主题以及舒曼《F大调弦乐四重奏》第三乐章中均有出现,以表达一种活跃、奔放的情绪,以此体现该典故中较为显性的象征功能。
此外,较具典型的个案还有圣—桑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第四曲《乌龟》引用自奥芬巴赫《地狱中的奥菲欧》序曲之加洛普舞曲主题。同一组曲中,第五曲《大象》中则引用了柏辽兹《浮士德的惩罚》之《精灵之舞》的开头旋律以及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中“谐谑曲”的首句,两曲都通过速度、节奏、音区、音色的变化,塑造较为笨拙的乌龟与大象的形象,都是通过对原典故材料进行夸张变形以达到反讽功能的经典之作。这一类型的摘引,由于专业音乐创作器乐曲写作中对较为复杂体系化的作曲技术的要求,而更多见于西方专业音乐创作之中,常表现为西方专业作曲家对同行之作的互引,以表达反讽、赞美,抑或向传统经典的致敬。
第二种类型B-B,即声乐曲之间的互引。在一首声乐作品中征引圣咏曲调片段是西方音乐中该类型摘引的开端。如著名的中世纪安魂弥撒曲《末日经》的开始乐句被运用于柴可夫斯基的《新希腊之歌》和布里顿《战争安魂曲》等多首声乐作品中,用以暗示死亡。而由马丁·路德所作,反映宗教改革、被恩格斯喻为“16世纪的《马赛曲》”的《上帝是我们的坚固堡垒》的曲调,以不同的方式被引用于J·S 巴赫的《第八十号康塔塔》《圣诞清唱剧》、亨德尔的清唱剧《所罗门》、梅耶贝尔的五幕大歌剧《胡歌诺清教徒》中。此外,该类型还体现为歌剧创作中对民间音乐的摘引。莫扎特就经常在歌剧中借用民歌曲调,其在《费加罗的婚礼》第一幕第二场和第八场费加罗的谣唱曲和咏叹调中,分别借用德国民歌《违法的猎人》和《乡曲民兵》的曲调,体现了莫扎特在歌剧创作中对德国民族主义的重视与追求。
第三种类型A-B,即在一首器乐曲中引用另一首(圣咏)歌曲或民歌曲调。被广泛征引的声乐典故,如前文提及的《上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也被门德尔松的《第五交响曲“宗教改革”》、瓦格纳《皇帝进行曲》、德彪西双钢琴组曲《黑与白》所引用。圣—桑的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还体现了对民歌曲调的征引,在第十二曲《化石》中分别采用了三首法国民歌《妈妈请你听我说》《明朗的月光》《出发去叙利亚》,作为B、C、D部分与引用了罗西尼歌剧中《塞尔维亚的理发师》罗西纳谣唱曲的E部分构成了“A-B-C-A-D-E-A”形式的回旋曲 ,“表示一切美好的东西最终都要化为尘土,变成化石”。[8]
整体而言,前人研究成果可分为对摘引手法的音乐形态分析与文化美学特征阐释两大类型。
(一)音乐形态分析
音乐形态分析可分为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两类。在整体研究中,以钱仁康的《音乐典故刍议》最具代表性。该文在浩如烟海的西方音乐作品中,撷取了若干最具代表性的个案,并列举出运用该“典故”的作曲家和作品20例。钱仁康从作曲技法的角度将其进行分类,分为借用前人音乐主题动机、整个主题,以及对原主题采用模拟、演绎、组合等共七类手法,是形态分析中较有价值的探索。该文提供的研究思路,尤其是文中例举的大量相关作品,均成为后来国内其他文论学习参考、引用的重要母体,奠定了该专题研究的基本思路与作品个案资料的基础。个案研究,除前文所提及钱仁康以J·S巴赫和莫扎特为题的研究以外,还有以马勒、艾夫斯、乔治·克拉姆、B.A.齐默尔曼[9]等作曲家摘引创作的研究。其中针对作品的个案研究,则以围绕《末日经》《马赛曲》等乐曲的系列研究较具代表性。
从历史分期的角度来考察西方音乐“摘引”中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较为清晰地勾勒出相关研究的基本面貌。
音乐“摘引”自中世纪伊始就广受作曲家青睐,至巴洛克时期更是佳作迭出。钱仁康《巴赫〈b小调弥撒〉中的“旧曲新歌”》[10]一文就分析了巴赫在弥撒曲中借用教会康塔塔音乐的创作实践。作者选取《b小调弥撒》中《荣耀经》《信经》《圣哉经》《羔羊经》四部分的八首曲目,对比分析了“旧曲”与“新歌”之间的关联,探析其中的摘引手法规律。
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摘引”以莫扎特的创作较具典型。钱仁康在《莫扎特“借题发挥”的创作实践》[11]一文从借用“素歌曲调”“曼海姆主题”“JC巴赫主题”“克雷门蒂主题”“狂飙主题”,以及“钢琴奏鸣曲中的借用主题”“交响曲中借用歌剧主题”和“歌剧中借用民歌”八个方面阐述莫扎特音乐作品中“借题发挥”的背景与构思。作者以此说明,正是莫扎特对前辈作曲家作品的刻苦钻研以及对自己创作的精益求精,才得以实现“借题发挥”,推陈出新。
至浪漫主义时期,音乐摘引之风更为盛行。如表达黑暗、死亡情绪的中世纪安魂弥撒曲《末日经》(又名《末日审判》《震怒之日》《愤怒的日子》)就在圣—桑、马勒、布里顿等多位作曲家的作品中被大量引用,以充分表达人们内心的沮丧与恐惧。闫威集中分析了该曲在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和《第三交响曲》与柏辽兹、李斯特等浪漫主义其他作曲家作品中的摘引手法,并将摘引方式归类为“原型引用”“模进展开”“附加‘前缀音’”“旋法的内部扩展”四种方式。[12]
浪漫主义晚期的马勒作为通往20世纪音乐的桥梁,在其创作中也大量运用摘引手法。张晨分析了该曲围绕着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永恒”动机进行创作的摘引手法。[13]交响曲结尾借用李斯特《浮士德交响曲》中的“神秘合唱”曲调,重新解读了“圣灵降临节赞美诗”和歌德的《浮士德》,表达了对生命的思考。其另一篇文章《探寻音乐文本中的“隐喻”——马勒晚期交响曲“摘引”研究》[4],除论述《第八交响曲》外,还指出马勒的《大地之歌》与《第九交响曲》都摘引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告别》中的“告别”动机。前者以“乐圣”的典范之作作为结语,表现无限的留恋和憧憬;后者则是表现哲思性的思索。两篇文章均以“摘引”为切入点,为解读马勒作品的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
较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时期,20世纪的音乐摘引则以“拼贴”手法为主要特征。不同于仅对单一素材的摘引,这一时期的摘引将大量其他作品细碎的旋律片段融于创作当中,乃至是对核心音列、整体结构等更为精简化形式的引用,亦不遗余力地追求新技术、新风格,用特定的技巧将他人或自己曾创作的多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片段进行并置、组合,赋予其新的内涵。这一时期的摘引个案多聚焦于齐默尔曼、艾夫斯、乔治·克拉姆等作曲家及其作品。齐默尔曼是最早使用“拼贴”技术的作曲家。魏启元、李明月[14]等都探讨了其第一个运用了“拼贴”技术的作品——1958年的歌剧《士兵们》。魏文以阐释齐默尔曼作品中的“拼贴”技术,以及“多元主义”“复合风格”的取向为基础,进而提出决定其音乐内在统一性的“时间概念”的要素,以及“拼贴”技术的文化意义。李文则通过拼贴的素材、观念、手法等方面,透视作曲家在创作歌剧《士兵们》时纯熟的技术以及音乐拼贴所产生的戏剧功能。另一位作曲家艾夫斯也是西方20世纪音乐创作中摘引研究的重要个案。班丽霞以构成管弦乐组曲《新英格兰三地》的第一乐章与第二乐章的分析入手,对作品中的“拼贴”现象及其深层内涵进行探究。[15]乐曲以欧洲音乐创作手法与摘引美国本土音乐旋律素材相结合,在保留音乐传统的同时寻求突破创新并赋予作品独特的个性,亦以反映本民族的伟大精神而活跃于世界舞台。而围绕乔治·克拉姆的“摘引”则以王旭青《乔治·克拉姆〈四个月亮的夜晚〉中的引用与象征》之研究较具代表性。该文指出该曲借用马勒交响乐《大地之歌》和海顿《第四十五交响曲》的音调,以表现其“与一直以来带有神秘、诗意色彩的月亮的内心告别”[6]。
值得一提的是,围绕20世纪音乐“摘引”的研究成果中还有一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其中以专事于艾夫斯的作品展开研究的数量最多。在此不赘述。
(二)文化美学阐释
近年来,音乐摘引研究也出现了立足于音乐本体分析,在相关创作的文化背景、美学表达等方面进行思考的成果。如李彦频将“摘引”的美学功能总结为“象征”“反讽”“暗示”三种“语义性”功能,与“实用”“形式需求”“风格并置”三种“非语义性”功能,并从“隐含听众”和“作曲思维的变革”的角度,透视西方音乐观念的发展与演变,探究摘引手法背后的深层内涵。[3]
此外,吴慧娟、陈静竞通过对中西方“曲调引用”现象的大量例举,从作曲家角度围绕其可作为投射标题性构思、展现对某给定素材处理加工的手段,以及赋予音乐作品抽象的表现或象征意义等方面的“表现性”,可成为唤起听众对所引素材“身份”认知的“社会性”,以及作曲家之间进行精神交流的“人文性”,三种不同指向性和侧重点的创作诉求展开学理性论述,揭示其“用典”的实质。从对音乐作品的欣赏和理解,以及理性思辨和学术研究的角度,探讨其接受问题。提出“曲调引用”是值得审视的音乐史学、音乐分析、音乐批评等多学科交叉论题的观点。[5]
二、对前人“音乐摘引”研究的思考
应该说,目前国内有关“音乐摘引”的相关研究,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呈现出了较为蓬勃的发展态势。但整体上仍存在若干不平衡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围绕音乐摘引文化意蕴、美学阐释的研究
因为学者出自不同的学科背景、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故呈现出对音乐摘引现象多学科、多视角的认知与阐释。如李彦频立足于西方音乐史之专业音乐创作史的研究视角,将其定位为一种作曲辅助技法;钱仁康从文学创作出发将其理解为等同于诗文的用典;王旭青从修辞学切入,将其视为一种修辞手法;还有学者将其阐释为一种音乐社会现象。
从音乐的形式要素层面来看,音乐摘引首先作为一种作曲技法存在,与之相关的研究必然要将立足于音乐本体的形态分析作为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只有经此之途,方可言及其他。另一方面,音乐摘引既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文化现象,又是一个具有一定文化意蕴的音乐现象,如果止于音乐形态层面的分析,亦无法完成对其由表及里的认知与阐释。整体而言,在以往研究中占有绝对比例的仍是从作曲家作品个案出发的音乐形态分析的成果,明显缺乏对摘引的背景、意蕴、文化功能以及创作诉求乃至接受心理等方面的深层挖掘。
音乐摘引的研究建立在音乐分析的基础之上,只有在对音乐作品形式构造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之后,才可能触及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等其他领域,以拓展研究的视野。其研究不应限于对其现象逻辑的发现与分析,而应回归到更深层次的、对音乐史实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挖掘,以及对作品本身及其引用曲调的文化意涵和艺术价值的探讨。这样方可深入理解作曲家创作的真实意图以及他们所运用的具体“引用”方式,进而探究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民族作曲家作品的创作特征。
(二)缺乏对国外有关音乐摘引研究成果的关注
前文所涉研究主体与研究成果均限定于国内范围。但音乐摘引作为一种生发于西方音乐,即中世纪以来在已有片段基础上组织音乐作品习俗与精神的传承的音乐现象,西方音乐学界早就对其给予了关注,并产生了一批围绕该专题的论文乃至专著。
早在20世纪中叶,波兰音乐学家丽萨就在其《音乐摘引的美学功能》[16]一文中对音乐摘引的美学功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其后,还有布德的《摘引、拼贴、剪辑》[17],布克霍德的《艾夫斯交响曲中的摘引模式》[18]以及梅策尔的《20 世纪音乐中的摘引与文化意义》[19]等围绕西方音乐中音乐摘引的个案及文化意义进行研究的论文。
在相关著作中,以克里斯托弗·雷诺兹的《影射的动机:19世纪音乐中的语境和内容》[20]较具代表,将影射分为融化性、对比性以及音符象征性等多种类型,并借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等德奥作曲家作品中音乐影射的意图进行了解读。劳伦·雷德黑德编辑的《20世纪与21世纪中的音乐借用现象》作为一本手册性文集,旨在检视 20世纪以后西方作曲家和批评家们对素材借用这一实践的各种评论,进而揭示受众在接受以及感知此类音乐时起作用的理念和理论机制。
此外,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于2011年举办的第七届“20世纪音乐国际研讨会”也设有“20世纪以来音乐中的借用现象”专题研讨板块,可见西方学界有关摘引研究的丰富态势。
遗憾的是,西方音乐学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有关摘引研究成果尚未得到国内学界及时引进、译介,只是在一些文论中涉及以上成果的内容摘要而未知全貌,更难及全面学习吸收、同步共进。
(三)缺乏对国外音乐创作摘引中国音乐的研究
从被引曲来看,前文所涉相关研究成果的另一共性特征还表现为都是围绕着西方作曲家对同行之作以及西方民间音乐的摘引。这一类型的摘引的确占据了西方专业音乐创作中的主体,但在西方音乐创作中也不乏以中国音乐为典的作品。被学者频频提及的案例首推普契尼歌剧《图兰朵》中的《茉莉花》与辽宁海城民歌《妈妈娘你好糊涂》两曲。钱仁康较早关注到了这两个典型案例,并写下了《妈妈娘你好糊涂和茉莉花在外国》一文。这方面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有毕明辉的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西方音乐中的“中国因素”》[21]。作者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西方音乐创作中借鉴“中国因素”的历史、题材(标题、情节、歌词)、音乐语言(曲调、调式、节奏、音色)、思想(哲学、宗教)等内容,但并未涉及更多较具典型意义的摘引个案。
显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薄弱。究其原因,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中国近现代音乐(交流)史研究有“重史轻乐”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界对近现代西方作曲家借鉴“中国因素”进行创作的音乐本体分析的忽视。从当代音乐的研究层面来看,在充分关注跻身国际乐坛的诸中国当代作曲家群体作品之余,却较少能够反向观察西方当代作曲家在创作中对中国音乐的摘引与借鉴。从创作层面来看,这一缺失反映出的事实是,中国近代以来仅百年左右的专业音乐创作历史,尚未产生足够丰富以供西方摘引的音乐素材。而实际上,近现代以来诸多与中国有着较多关联的西方作曲家,在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地与中国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俄裔犹太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创作的交响诗《北平胡同》、歌剧《孟姜女》、歌舞剧《凤凰涅槃》,俄籍作曲家齐尔品创作的钢琴曲《敬献中华》和《第二交响曲》,德国作曲家华丽斯创作的歌曲《浪淘沙》等,这些作品都不乏对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诸“中国因素”的摘引。
西方专业音乐创作中对中国音乐摘引的这一学术研究上的缺失,实质上还折射出中国音乐的专业创作力以及海外传播、海外影响的不足,反映了文化传播输入与输出上的“逆差”。更多优秀的中国传统音乐以及不断涌现、跻身世界乐坛的中国当代作曲家的优秀之作,都亟待为西方作曲家所了解,以使其可能成为西方音乐创作的摘引材料而扩大中国音乐的国际影响力。
(四)缺乏对中国音乐创作中摘引现象的研究
以往的研究虽不乏提及诸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钢琴协奏曲《黄河》等作品中摘引《国际歌》《东方红》的手法,但大多数成果都还是围绕着西方音乐自中世纪至20世纪现代音乐的创作领域,鲜有专门的文论探讨中国音乐创作中的摘引现象,这也是摘引研究最大的缺失。
实际上,中国近现代新音乐创作不乏大量运用音乐摘引的个案实例。早在1929年黄自创作的管弦乐序曲《怀旧》中就摘引了巴赫《众赞歌》音调,以寄托对亡友的哀思。至20世纪末,随着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发展,中国作曲家更为普遍地引用外国音乐名典。如秦文琛的《五月的圣途》引用贝多芬“命运主题”,而著名的“贝九”中的《欢乐颂》则分别被郭文景的《御风万里》与谭盾的《交响曲1997—天地人》等作品所征引。刘湲的《台湾民谣抒情组曲》和高为杰的《缘梦Ⅱ》则分别征引了德彪西的《月光》与《牧神午后》。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作曲家还都将目光投向了丰富浩瀚的中国传统音乐,如陈其钢的《逝去的时光》与朱践耳的《第十交响曲》都以琴曲《梅花三弄》为典,表达人类对精神家园与独立人格的向往与追求。
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并未充分关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的摘引。除了如赵冬梅《中国传统音乐的音高元素在现代音乐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22]、邹舒《中国新音乐的拼贴技术及复风格运用技法研究》[23]以及丁艳《江苏民歌主题在专业音乐创作中的技法解析》[24]等为数不多的文论涉及某些摘引的个案(且多呈零散态势),目前尚未见对此进行相对系统的分析、阐释的专文出现。
无论是从音乐创作还是从理论研究来看,加大对中国作曲家音乐创作中摘引作品个案的关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新音乐”以来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存在音乐摘引的作品,并从摘引的类型、技法、音调来源等方面进行形态分析,进而总结其摘引的文化意蕴与美学内涵,对中国作曲界与音乐学界来说,都是亟待提上日程的重要研究课题。
结语
自21世纪初钱仁康围绕“音乐摘引”的三篇系列专题论文发表以来,国内学者从最初多集中于对西方作品个案形态分析,到兼及对“引用”现象深层文化意涵的探究,再至对本土音乐创作“引用”现象的关注,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宽、研究深度的加强,产生了不少围绕该专题领域的成果,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学者们从各自学科背景出发,对音乐摘引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而相关研究的补充与完善,从国内学者围绕音乐摘引研究立足于音乐形态个案分析来看,应加大对音乐摘引相关文化美学的阐释;从研究主体来看,应增强对国外学者的相关文论的引进与译介,以更好地吸收其前沿研究成果;从创作主体来看,应加强对西方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摘引中国音乐的相关作品的关注。
从音乐摘引这一独具表现意蕴的作曲技法切入,可以小见大,折射出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技法以及音乐社会表现的变迁轨迹,在总结独具中国特色的音乐摘引艺术特征的同时,探索构建中国话语下的音乐创作与音乐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