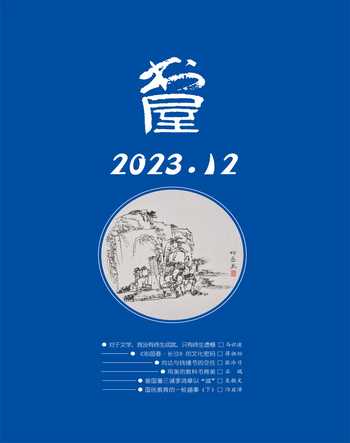陈布文的小说《假日》
2023-12-25李兆忠
李兆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一篇名叫《假日》的小说(载《人民文学》1957年第一期),发表后波澜不惊,没有引起批评家的注意。
随着时间推移,这篇貌不惊人的小说越发显出不同寻常的价值。它绵里藏针,不动声色地演绎了那个时代“几乎无事的悲剧”。艺术上,它白描清逸、虚实相间、惜墨如金,有丰富的象征意蕴,经得起长久的咀嚼,给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历久弥新感。
因某种特殊的因缘,作家王蒙最早为文,激赏久为岁月封存的陈布文的艺术才华。在以陈布文为人物原型的“非虚构小说”《女神》(《人民文学》2016年第十一期)中,王蒙这样评价陈布文:“文气浩然,信手拈来,胸有成竹,琳琅满目。”“熟练大气,举重若轻,得心应手,优雅而不免——说不清为什么,我觉察到了你心灵上的一点似乎可以叫作高处不胜寒的憔悴。”末一句,笔者以为说得最到位。
《假日》从女性的视角,描写一对新婚不久,平日两地分居,只有周末才能相聚的恩爱夫妻令人沮丧的“假日”,故事梗概如下:
怀着对又一个周末假日的热切期待,小玉冒着十二月的严寒,从郊外赶回京城,走进机关宿舍大院,来到自己的家,惴惴不安地敲起门来。之后发生的一切,仍是过往假日的翻版,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丈夫不仅比留言约定的时间晚很多才到家,而且喘息未定,又受到部长的传唤,匆匆离去,直到半夜方归。凌晨五点天不亮,又匆匆起床,赶去机场送一位外国客人。九点半,还要到某地送某要人的殡至西山公墓。下午两点半,有画展开幕式(不邀请夫人出席的开幕式)。四点,还有副部长主持的茶话会。第二天早晨,同学吕英来敲门,他是丈夫的同僚宋主任的新婚妻子,同住机关宿舍大院。吕英神情沮丧,正经历着与小玉相同的苦闷。一番商谈后,两人作出决定,结伴踏上了回郊外学校的路……
如果是一对头脑简单、情感粗糙的夫妻,事情也许会简单很多。小玉与小林偏偏不是这种情况,他们情深意笃,趣味相投,“虽然结婚了一年多,仍然像新婚不久似的”。这次,小玉花了一个礼拜的课余时间,为小林编织了一件驼色毛线衣(因为小林不肯穿那种颜色俗气的毛线衣,而商店里又买不到合适的),小林则于百忙之中赶到王府井新开的熟菜铺,为小玉买了合她家乡口味的菜肴,并声称:“我早就变成南方人了,我觉得各种菜里都放一点糖很好吃。”由此可见,这种有名无实的“假日”,對他们确实有点残酷。
而且,与那种缺少独立人格、甘作工具之辈不同,小林和小玉都是有见识、有思想、才情丰沛的人。小林喜欢文学艺术,尤其爱读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其中译笔较好的作品都被抄录在小本子里,还自度一首《迷开会》,与老马的《开会迷》唱和,嘲讽那些“迷失于纷繁会议中的人,迷恋会议胜于一切的人,迷信会议可以解决一切的人”。他对文山会海的厌恶,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作为一名文化机关的资深干部,小林对上司的传唤和组织上的差遣,似乎已习以为常,即便心有不甘,也总是无条件执行。从他的隐忍中,可以看到大公无私的美德,对个人欲望与自由意志的规范与抑制。相比之下,尚在大学读书的妻子小玉显得更独立不羁。小说一开始写她走进温暖如春的家,看到丈夫“至迟六点五分准到家”的留言,便愉快地洗脸,坐到镜子前,将辫子打散梳起头来。
在学校里,一个礼拜繁重的学习,生活的弦是绷得太紧了,只有现在,只有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才松弛下来。她一边低低的唱着,一边将自己头发编成许多条细细的长辫子,然后在室中转动着身子跳起舞来……于是在那长大的穿衣镜内,便照出一个穿粉红色毛线衣的苗条少女的美妙舞姿。
咚咚咚……
“谁?”她吃惊的问,连忙停住,两只手一齐向头后按住那许多条摆动的辫子。
“林同志的信。”是老王的声音。
“好……”她将门打开一条缝,伸出去一只手,“给我好了,——谢谢!”她赶紧把门关严,将信塞在玻璃板下边,又走到镜子前面,注视着那微微泛红的脸与乌黑的头发,叹了一口气,坐下来,重新把一条一条辫子又拆散开来。
“唉,维吾尔族的姑娘有多么快乐啊!她们可以梳那美丽的头,我们是不行的,如果我那样走出去,他们会当我有神经病,就是头脑最开通的人,也会斜着眼睛瞧我,在肚子里说:‘要漂亮,爱出风头,轻浮的女人!”
她嘟着嘴,把头发梳来梳去,最后,她决心一把总,梳成一条大辫子,把它高高的盘在后脑上,像一个印度妇女。
这段文字,将一个才情丰沛、充满活力,热爱家庭而又独立自主的女子形象生动呈现,其收信时的动作细节,表明她对私人空间的“家”有一种习惯性的守护,而一句“头脑最开通的人,也会斜着眼睛瞧我”的牢骚,暗含批判的锋芒:既然连头脑最开通的人都是如此,那么,头脑不开通的大多数人又会怎么样呢?
小玉这个形象,令人想起当年追求“个性解放”的中式娜拉,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激荡,她们勇敢地冲出家庭,投身社会。小玉与她们不同,她是少数的“透网金鳞”,在那个时代依然保持独立的个性与孤迥的气质,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小玉对个人幸福的要素——一个温暖如春的“家”怀有执着的追求,这个家的陈设与氛围必须优雅朴素,不能与那种粗鄙简单的宿舍相混淆,房间里要有花,书桌上要养水仙……
《假日》没有吸引眼球的故事情节与戏剧性冲突,小玉对爱人相聚的期待、失望,再期待、再失望,直至绝望的心理过程,是整篇小说的基本内容。其间,夹杂各种不期而至的打扰声:门房老王频频的送信、电话传呼,陌生人的脚步声及代表宋主任的屡次催问,除此之外,还有催人的汽车喇叭。这种种的刺激声响,至夜深人静于沮丧困倦中不知不觉睡去时化作梦魇。小说写到这里,开始走向“意识流”,变得梦幻、缥缈起来,“她朦胧的觉着林回来了,他那冰凉的手,他那冰凉的面颊……他还说着什么话,自己虽然很想招呼他,虽然勉强睁了睁眼,感到了房内刺目的灯光,但一切似乎隔得很远,那么朦胧……”“忽然,房子里似乎布满了月光,她可以清楚的看到房内的每一件东西,特别是那大穿衣镜,它使她不安,仿佛正有什么东西,要从那不可测知的玻璃深处走出来……正在这个时候,门忽然开了,她想,是林回来了吧?不,那绝不是林,恍惚着有一团黑东西一下子扑到床上来,她拼全力喊起来:‘啊——啊——”
这段文字幽微精妙,令人想起张爱玲《金锁记》里对月光的描写,两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整篇小说有画龙点睛、烘托渲染之功。梦魇中奇异的月光、深幽的穿衣镜,尤其是那破镜而出的“一团黑东西”,神秘而恐怖,令人悚然。那么,它代表什么呢?
品读这段文字,笔者每每惊异:作者的艺术直觉令人惊叹,竟能透过如日中天的时代光芒,看到“一团黑东西”。显然,这种艺术直觉,远远超越了作者当时的理性认知(这种理性认知能力经过曲折的历史过程十多年后方为有识之士具备)。
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史上,《假日》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文学之河受时代大潮激荡,尽管迂回曲折,其底层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基本一致。《假日》遥接“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继承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叙事传统而推陈出新,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枝“报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