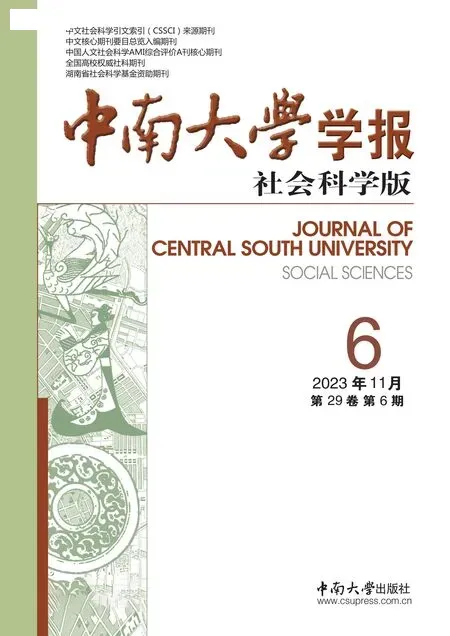波斯统治时期叙利亚地区的政治制度
2023-12-23李继荣
李继荣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古叙利亚文明作为中东地区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被誉为“文明交往十字路口”[1](7)。对波斯治下叙利亚政治制度演进的探索和理解,不仅是“叙利亚学”①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古代政治制度交往与演进理论的研究意义重大。公元前6 世纪中后期是波斯帝国②的开端,更是古叙利亚文明政治制度演进的分水岭。公元前539 年,居鲁士大帝(约公元前559—前530 年在位)将叙利亚地区纳入波斯帝国统治下,该地兴盛约三千年之久的闪米特文化走向衰落,其政治制度“自主”发展的模式亦被打破。波斯“印欧”外来异质文明对这一地区开始长达千余年的统治,促使该地区形成了“他者+自我”的文明融合发展模式。
但民族来往增多和政权更替频繁,使这一文明因无主导性文明因素而呈现出政治制度演进的“杂乱化”与“碎片化”特质,有学者甚至认为叙利亚是“一个从来没有实现政治统一的古代社会所在地”[2](315),加之该文明延续过程复杂和留存文献匮乏,学界对波斯统治下的叙利亚地区政治制度的研究非常薄弱。《剑桥古代史》对其政治曾有所涉及,德国学者霍斯特·克伦格对公元前3000—前300 年的叙利亚政治史也进行过梳理,但有关波斯时期叙利亚政治制度的篇幅很少。菲利普·希提在叙利亚通史中涉及了政治制度的内容,但局限于探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特雷弗·布利斯对叙利亚政权的更替进行了全面论述,政治史的构建却略显简要[3-5]。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学界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使这一文明的政治制度研究始终处于“附庸”地位。国内学者郭丹彤和刘健分别从埃及学和宗教学的视角,关注了外族政权和宗教文化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政治制度的影响[6-7]。近年来,因埃卜拉文献和近东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翻译以及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8-10],王新刚教授团队依托教育部重大项目,将古叙利亚文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探讨了该文明的流变与特征[11-15]。这些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关联式的零散探讨,但对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特点和逻辑等的探讨缺乏系统性。鉴于此,本文在依托文献学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拟以波斯帝国时期为时间轴,以叙利亚地区政治制度构建为主题,探讨波斯统治下叙利亚地区政治制度演进的阶段、模式、特点与影响。
一、波斯时期叙利亚地区政治制度演进的主要阶段
历史地看,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叙利亚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形成过程十分复杂,经历了从地理概念演变为政治概念的长时段磨合过程,地理名称与政治实体之间长期存在着差异性。叙利亚这一名称源于地理概念,最早以“舒尔云(Shryn)”的形式出现在乌加里特文献中,可能指某一城邦或小范围地区;后希伯来文献中记载为“叙伦(Siryon)”,主要指外黎巴嫩地区;巴比伦人称其为“叙利(Su-Ri)”,主要指幼发拉底河北部地区;希腊人将其称为“叙利亚”,指北到陶鲁斯山、南达西奈半岛、西自地中海、东抵阿拉伯沙漠的地区[16],至此古代大叙利亚地区的地理所指基本成型。在政治实体上,上古时期并未有叙利亚这一政治单位,而是隶属于西亚北非的文明存在,同其他文明一样,叙利亚地区出现了大量城邦,各城邦以自身的地缘环境发展演变。公元前539 年,印欧语族的波斯人到来,虽打破了叙利亚地区城邦与王国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但二百余年的统治为叙利亚政治单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主要经历了如下阶段:
(一) 居鲁士大帝的初建阶段
林志纯先生认为“西起欧洲,东至南亚中亚,国家和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大都以城邦始,以帝国终”[17](34),言明了人类进入文明后形成的第一个政治形态是城邦政治,之后逐渐形成帝国政治形态。上古叙利亚亦是以闪米特人建立的城邦政治为肇始,经历了内部城邦的兼并战争及外来民族的干扰,在内外矛盾与妥协中逐渐走向帝国的次生政治形态——盟邦。而公元前550 年,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征服战争中逐渐改变了叙利亚地区的文明演进模式,以行省制为核心的“大行省、小自治”的波斯-叙利亚的政治制度模式在居鲁士大帝时期开始初建。
公元前539 年是叙利亚文明政治实体的开创之年。这一年,波斯王居鲁士战胜了巴比伦末王那波尼杜斯,巴比伦连带叙利亚地区归入波斯人统治之下。而居鲁士对叙利亚的统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居鲁士以“解放者”的姿态向来自叙利亚的犹太人(巴比伦之囚)颁布了“返乡敕令”[18](444),还将当年巴比伦王从耶路撒冷抢夺的金银器皿一并交由犹太人带回耶路撒冷的圣殿中。
其二,居鲁士在叙利亚地区设置行省,为叙利亚政治单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波斯人到来之前,叙利亚的称谓比较混乱,闪米特史料中,阿卡德语的“Ebir Nari”,阿拉米语的“Cabar Nahara/Naharah”和希伯来语的“Eber Hannahar”专指“河西地区”,希腊语史料中则经常混用“叙利亚”“叙利亚全境”和“叙利亚与腓尼基”三种表述方式[19](141)。居鲁士改变了这一局面,他在巴比伦接待了叙利亚诸王,后下令将叙利亚、腓尼基和巴勒斯坦与巴比伦合并为一个大行省,名为巴比伦-伊比尔·纳里(bābili ú ebir nāri),意为“巴比伦-河西行省”。“河西”指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地区,包括陶鲁斯山以南、幼发拉底河以西、地中海东岸以东和西奈半岛以北的地区,是古叙利亚文明的核心地区。居鲁士任命其亲信戈布利亚斯为大行省总督,总督任命下级官吏。从诸多行政文献可知,原先的官吏一般保留了原职。戈布利亚斯统治着这一大片辽阔的、绵延的和肥沃的地区,几乎像独立的王国一样。
总体而言,居鲁士对叙利亚地区的统治采用了宽容的政策,无论是在对待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上,还是在对巴比伦-河西行省官员的任命上,都保留了叙利亚地区政治上的相对独立自由,这为原本地域分散和民族复杂的叙利亚独立政治制度的统一与演进提供了形式上的保障。
(二) 大流士一世的完善阶段
公元前530 年,居鲁士去世,冈比西斯继位。冈比西斯是居鲁士的长子,身份显贵,很早就被立为“王储”,在居鲁士对巴比伦人发布的公告中,提到“主神和主马尔杜克已经赐福于他本人,还有他的儿子冈比西斯”[20](107)。因此,曾目睹和参与居鲁士对叙利亚地区统治的冈比西斯基本延续了其父的治策。从现有的史料看,在其短暂的统治期间(公元前530—前522 年在位),自公元前526—前525 年入侵埃及后,他基本忙于埃及事务,根本没有时间致力于叙利亚地区的行省建设。公元前522 年他去世时,留下了23 个行省,“巴比伦-河西行省”作为其中一员,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保持了居鲁士时期的理念。但居鲁士在叙利亚地区的体制组建时间较短,行省规模过大,容易引发地方权力的尾大不掉,叛乱时有发生。公元前522 年的“高墨达运动”便是重要案例之一,对此《贝希斯敦铭文》曾载道:
僧侣高墨达从冈比西斯手里夺取的王国,自古以来属于我们的氏族,僧侣高墨达从冈比西斯手里夺取了波斯和其他诸省,侵占了它们,把它们占为己有,并组成了王国……从我们家族被夺走的王国,我将之夺回;在其基础上我重建了它。对高墨达毁坏的圣所,我予以修复,被高墨达夺走的牧地、牧群、家奴和房屋,我将其归还给民众,我把国家恢复如前,无论是波斯、米底或是其他诸省……当我在巴比伦的时候,下列诸省叛离了我:波斯、埃兰、米底、亚述、马尔吉安纳、埃塔基提亚和西徐亚。[21](60-61)
从铭文可见,高墨达运动及大流士执政初期的起义,表明行省过大的统治模式并不牢固,故而在镇压各地起义后,大流士以征收赋税的名义对行省进行了改革。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大流士将原来的23 个总督区重新组建为20 个新总督区,第5 总督区囊括了塞浦路斯、腓尼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很多学者据此认为,在镇压叛乱后,大流士就将巴比伦-河西行省分开了。实际上,根据大流士统治期间巴比伦的法律文献依旧经常提及“巴比伦-河西行省”的状况来看,自公元前521—公元前486 年,分别有乌什塔尼、胡塔科斯和帕加卡安纳担任大行省总督,塔特奈担任“河西行省”总督,说明大流士期间并未将该大行省一分为二,而是在这一行省之下划分出了二级行省“河西行省”,以分割大行省总督的职权。
总体而言,大流士改革中将巴比伦-河西行省重组,下设二级河西行省,分散了大行省总督的职权。河西行省不仅是政治单位,还是经济单位,中央对地方的政治与经济控制力加强,有利于帝国的稳定,其治下的叙利亚地区开始脱离于巴比伦地区,使得这一文明在政治与经济统一模式的推动下,内部交流加剧,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体,叙利亚的独立政治体印记日益凸显。
(三) 薛西斯一世的成型阶段
大流士的改革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削减巴比伦-河西大行省的规模,下设更小级别的河西行省,以此将权力自下而上进行集中,使得帝国保持了长期稳定的状态,促进了波斯帝国政治与经济上的巨大发展,为大流士开启希波战争奠定了基础。公元前500 年,米利都起义拉开了希波战争的序幕。大流士镇压这场起义后,开启了远征希腊的计划,由于马拉松战役失利,加之大流士去世,战争暂告一段落。但薛西斯登基后,国内的局势再次骚乱起来。骚乱的原因大致如下:第一,新王薛西斯刚刚登基,地位不稳;第二,虽然大行省下划分了二级行省单位钳制大行省总督的权力,但腓尼基一带仍以城邦的形式存在,犹大地区的地方自治性亦很强。在这一背景下,薛西斯登基后,巴比伦地区发生了两次严重叛乱,一次是公元前484 年贝尔史曼尼领导的叛乱,另一次是公元前482 年沙马什埃利巴领导的叛乱。
虽然薛西斯以铁腕手段平息了巴比伦的两次叛乱,但是其影响甚远,从《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记载看,巴比伦的叛乱也引发了犹大(河西)地区的反波斯活动。《以斯拉记》中总督写给薛西斯的信中提到:
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筑立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我们既食御盐,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之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我们谨奏王知,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18](447)
这段话表明,可能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在巴比伦的叛乱影响下,也有自己的反叛举动,至少根据之后的《尼希米记》来看,在薛西斯王20 年,河西地区可能因为反叛波斯而遭受了严厉的惩处:“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18](454)
因此,巴比伦与河西省内的叛乱,致使薛西斯的统治政策发生改变,他一改居鲁士以来的宽容政策,代之以更为严厉的管控措施治理叙利亚地区。他不仅下令将河西地区与巴比伦进行了分离,使河西成为一个独立的大行省,而且在河西行省之下按照地域与传统分出四个小行省,分别是腓尼基行省、犹大行省、撒玛利亚行省和阿拉伯-纳巴泰行省③。叙利亚地区作为独立单位的政治制度就此成型。在波斯统治的后半叶,特别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和三世(公元前404—前338 年)虽然延续了前任国王的统治政策,但内外斗争造成的帝国根基削弱,使河西行省的独立性愈发加强,犹大行省和腓尼基行省接连发生叛乱。在镇压一系列叛乱后,阿尔塔薛西斯三世也效仿前辈对行省进行了调整,将河西行省与西里西亚合二为一,由参与镇压腓尼基地区的西顿叛乱的西里西亚的总督马扎欧斯担任“河西地区与西里西亚行省”的总督,但总督权威与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波斯帝国的衰弱,作为帝国代表的总督在叙利亚地区的地位和权威也被弱化,行省内的祭司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最终大约在公元前332 年,随着波斯在河西地区统治的瓦解,波斯的总督也在叙利亚的政治制度中消失。但是,经波斯行省制统治后的叙利亚,却不自然地接受了行省制下的统一政治单位和地理范围,为之后叙利亚的民族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波斯统治下叙利亚地区政治制度的模式
波斯对叙利亚的统治采取的是“行省体系”,似乎与波斯在其他地区的行省统治无异。这是从波斯帝国的角度而言。如果从叙利亚独立的政治单位视角来看,波斯统治下的“行省体系”是波斯的政治外来统治与叙利亚本土政治模式融合的结果,具有其自身的制度模式特点,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 机构设置
在波斯帝国早期,“河西”只是与巴比伦共同构成大行省的一部分。居鲁士大帝为了方便统治,于公元前535 年设“巴比伦-河西行省”,行省的官员被称为总督,意为“王国的保卫者”,不仅担负着行省管理职责,还拥有行省的军事指挥权。据文献记载,公元前535—前486 年,从居鲁士至大流士统治期间,共出现了古巴鲁、乌什塔尼、胡塔科斯和帕加卡安纳在内的至少4 位大行省总督[19](154),总督出身波斯贵族,多为波斯王的亲信。总督也会因权力世袭而对中央造成威胁,为了牵制其势力,国王会在总督下设立总督秘书、总督首席财政官、省会要塞驻军将军,直接对波斯王负责。不过,随着波斯王统治的需要和“河西行省”自身的发展,大约在公元前486年前后,大行省逐渐失去了往昔的地位。
大行省之下,“河西行省”为二级行省单位,居鲁士时期主要为幼发拉底河以西、地中海海岸以东的大叙利亚地区,行省内基本保持了原来的官职。大流士继位后,为了方便征税,将塞浦路斯归入河西行省,组成了所谓的第五行省,“河西行省”总督正式职位也大约缘起于大流士一世。河西行省的第一任总督为塔特奈,在任时间为公元前518—公元前502 年。薛西斯一世继位后,也奉行了这一任免原则。到公元前332 年为止,先后经历了贝莱徐斯一世、贝莱徐斯二世和马扎欧斯等河西行省总督[19](154)(见表1)。需要注意的是,薛西斯一世时期,为了对巴比伦-河西行省的叛乱进行惩罚,将其一分为二,河西行省上升为一级行省,机构设置不变,除总督外,亦设有相应的牵制官员。

表1 公元前518—前332 年河西行省总督任职表
在“河西行省”之下,有较小级别的行省单位,这一级的行省单位比较稳定,主要包括四个部分:沿海的腓尼基行省、内陆的犹大行省、撒玛利亚行省和南部边境的阿拉伯-纳巴泰行省。行省内部的机构设置差异较大。这几个行省均有一定的自治权,多数由当地有名望者担任总督。根据圣经文献、史家记载及考古发掘,居鲁士时期,犹大的所罗巴伯为犹大地区的长官,可能由于叛乱,于公元前521 年被波斯王免职。大流士一世之前,撒玛利亚行省总督由当地的“参巴拉”家族成员担任,犹大行省总督一职则由“大卫家”的成员担任。之后,这些家族也丧失了领导地位,其成员名字很难被看到,波斯王开始亲自任命这些地方的总督,如以斯拉、尼希米和叶赫兹卡亚。不过从名字看,这些总督均为犹太人,即便文献中提及公元前408 年要求重修耶和华神殿的犹大行省总督拥有“巴戈西”这一波斯名字,但学者认为这位总督只是拥有波斯名字的犹太人。
四个行省中,拥有最大自治权的是腓尼基,山地环境和靠近海洋的影响,使这里形成了以推罗、西顿、比布罗斯等海上贸易城邦为主的政治单位。因海军力量强大,这些城邦享有很大的自治权,无需交纳贡赋,甚至拥有铸币权。不过,在薛西斯一世执政后,为了强化波斯王的控制,助推腓尼基城邦建立了行省联盟,因西顿王在希波战争期间的卓越表现,任命西顿王为腓尼基行省盟邦的盟主。与行省划分相对应的还有省府所在地的设置。“巴比伦-河西”大行省的省府在巴比伦城,但史料中并未明确“河西行省”的省府所在地,根据斯特拉波《地理志》提及的“大马士革是一座重要城市,波斯帝国时期它在该地区(叙利亚)是诸城中最著名的”[19](154),推测这里就是“河西行省”的首府,河西行省之下的犹大行省的首府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的首府是撒玛利亚城,腓尼基行省盟邦的总部则在特里波利斯城,阿拉伯-纳巴泰行省的府邸可能在埃勒乌拉。
(二) 运行方式
1.波斯王与行省总督
由于行省总督由波斯王亲自任命或认可,故各级总督均要受命于波斯王。在薛西斯一世统治之前,“巴比伦-河西行省”合为一体,据公元前535—前486 年的巴比伦法律文献记载,行省的治理者为“巴比伦与河西地区的总督”,出身波斯贵族,为波斯王的亲信,由波斯王任命,代波斯王统治,直接对波斯王负责。比如大行省的第一任总督古巴鲁,不仅是居鲁士的亲信,还追随国王南征北战,因功绩卓越被封为行省总督。在波斯早期,因波斯王的宽容政策,“巴比伦-河西”行省总督的主要职责是征收赋税、维护地方稳定,并未过多干预叙利亚地区的政务。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总督甚至没有巡防过叙利亚地区[3](235)。
因巴比伦和河西地区的反叛,大流士一世时期,在大行省之下划分出“河西行省”这一二级行省单位,设置总督职位,在政治规制上隶属于“巴比伦-河西”行省。从“大流士统治前期,河西地区塔特奈隶属于巴比伦与河西总督”[19](153)来看,大行省总督在很长时间内都具有权威性。不过,随着薛西斯一世针对这一地区持续的动乱,采取了将巴比伦与河西进行分省治理且河西行省之下设置三级行省单位的改革后,大行省逐渐失去往昔地位。波斯王对各级行省总督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各级行省总督宣布对波斯王效忠,波斯王则对总督进行任命。一般情况下双方达成稳定的服从与隶属关系,总督代波斯王治理河西行省,但是双方也会发生嫌隙。特别是在波斯统治早期,由于“巴比伦-河西”行省范围很广,总督权力过大,总督“统治着这一大片辽阔的、绵延的、肥沃的地区,几乎像独立的王国一样”[20](67)。波斯王与总督之间不完全信任,王会在总督身边安插一些耳目。如大流士时期,为了限制总督的权力,总督之下设置军督和司库各一名,分管军事与税务,以牵制总督,而充当波斯王“耳目”的情报系统,也成为波斯王与总督之间的重要力量。
2.各级行省总督之间的互动
这三级行省或二级行省单位的运行是帝国得以运转的保障。最高一级的行省总督是代波斯王统治地方,而各级别的总督之间有自上而下的监管和自下而上的监督之责。所谓的监管,主要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一般奏折的递请不能越级,要逐级上奏,经河西总督或大行省总督,最终上达波斯王之手。所谓的监督是上下级的约束关系,特殊情况下,如下级总督发现上级总督有“不当行为”或紧急要务,可以越级直接诉诸波斯王。如在大流士一世时期,河西总督在对犹大行省进行圣殿修建巡视时,就居鲁士曾下令让其复修圣殿之事存疑,于是直接上书波斯王进行询问[18](448)。因此,在各级行省总督之间的监督和监管之下,各自行使权力,互不处置对方,由波斯王做最后的裁决。
除了行省内各级行省总督之间要相互隶属、监督与制约外,当某一级行省总督受王命对行省进行管理或治理时,行省总督之间还必须相互支持、援助与配合,完成波斯王的期望。以犹大行省为例,虽然在薛西斯一世时期,因巴比伦和犹大地区的叛乱,波斯王剥夺了当地犹太贵族担任犹大总督的特权,改由波斯王任命亲波斯的犹太人为该地总督,但犹大地区的自治权依旧较高。于是,尼希米被薛西斯一世任命为犹大行省的总督,由其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临走之时,波斯王问尼希米有何要求,尼希米回答:“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18](454)因此,尼希米不仅获得波斯王派遣的军队和马车的护送与陪同,还受到河西总督的保护,为其提供耶路撒冷重建工程所需要的木材。
当然,从尼希米返回耶路撒冷重建该城的叙述来看,新任行省总督上任时不能随意迁移,要在波斯王应允的范围内,通过波斯王颁发的“通关文牒”实现过境或跨境,总督个人的任意过境可能是不法行为,甚至会受到另一级别的行省总督的阻拦。因此,当某一级别的行省总督要履职,先要拿着波斯王的诏书前往所过境的行省,交给该行省的总督过目后,才被允通行。这一行省管理模式也是为了控制行省总督的权力,防止一些行省总督以履新的名义给地方带来混乱。
三、波斯统治下叙利亚地区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
波斯设置“河西行省”加速了叙利亚地区政治文明一体化的进程。根据这一时期古典史家的著述、铭文及圣经文献,波斯人并非最早在叙利亚地区设置行省的民族,新亚述征服后,亚述王将叙利亚嵌入了“行省”中,不过这与波斯帝国的行省有着本质区别:第一,新亚述的行省与亚述王的征服相伴随,带有很强的偶然性,波斯帝国在叙利亚设置行省是将其作为帝国统治疆域的一部分,具有长期与成熟的特点;第二,在亚述与埃及的争霸中,行省的设立加剧了叙利亚政治状态的分离,而波斯在叙利亚建立行省后,使这一地区的政治呈现出整体与统一的特质;第三,亚述的行省制度还未形成,地方依然为独立王国,而波斯时期将行省制作为一种较为完善的帝国统治模式引入叙利亚,促使叙利亚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但“河西行省”内拥有独立性较强的城邦文明、宗教信仰顽固的犹太文明以及松散混乱的联盟力量,民族和文化多元的河西地区之所以被波斯人划为一个行省,可能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这里自古便属于民族种类与政治实体众多的地区。多样性是叙利亚地区的历史常态,将其归为一体,有利于波斯采用“历史借鉴”的方式与河西行省的臣民达成平衡。其二,出于提升行政效率、兼顾各群体利益的考虑。与传统的以“政治-地域”为单位的统治模式不同,波斯帝国已经尝试建立“各民族-帝国”的统治单位,表明波斯人希望在政治制度构建上具有超越性。其三,这里的政治实体在与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竞争的过程中,大多被削弱或清除,为波斯帝国在此设置行省建立多民族政治实体减少了阻力。波斯的行省统治使叙利亚的政治制度呈现出如下新特点:
(一) 自上而下的集权统治政治模式
正是由于波斯行省体系的独特性加上河西行省内部叙利亚文明的差异性,使得古叙利亚的政治制度在兼容并蓄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质。文明交往论认为,制度文明决定着文明交往的协调与和谐。制度与秩序的好与坏,对文明交往至关重要[22](24),推动着社会文明规范的完善。政治制度是制度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制度演变是政治发展的外在表现,可内化为政治观念的交融与变革。早期闪米特人在此建立的诸多城邦开启了城邦间的交流与交往,体现在叙利亚作为贸易中心衍生出了以埃卜拉为代表的诸多政治中心,而城邦间时常会因人口、土地和资源而爆发战争,加剧了叙利亚地区走向王国的统治趋势,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雅穆哈德王国和夸特那王国的出现。据文献记载,雅穆哈德王国原本只是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城邦,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在雅利姆-里姆统治时期有了20 个“追随者”;南部的夸特王国亦是如此,也有10 至15 个“追随者”[3](57)。这表明,这一时期叙利亚地区的政治制度开始走出了城邦的局限,但未形成专制集权模式,而以松散联盟王国的状态存在,中央王国与地方小国之间是一种攻守同盟的权利义务关系。
公元前539 年,波斯人结束了叙利亚地区由闪米特人统治的历史,形成了一套维系和管理帝国的成熟的行省治理体系。在统治理念上,波斯帝国以帝国观念强化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思想。它与之前的亚述王国和巴比伦王国有着本质区别,后两者主要将叙利亚城邦或联盟王国作为藩属国进行管理,双方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波斯帝国则将王权至上的理念引入叙利亚地区的政治制度构建中,在将巴比伦与河西行省划为一个行政大区后,居鲁士发布的敕令中称:
我,居鲁士,世界之王,伟大的王,强有力的王,巴比伦王,苏美尔阿卡德王,天下四方之王,伟大的王,安善城之王冈比西斯之子,伟大的王,安善城之王居鲁士之孙,伟大的王,安善城之王铁伊斯佩斯之玄孙。[23](71)
这些称号彰显出波斯王神化王权的目的。居鲁士驻跸巴比伦时,为了彰显王权至上,曾让叙利亚诸王以亲吻国王之脚的方式表示他们的崇拜之情[20](66)。大流士继位后则进一步融合了两河流域与埃及的君主称号:
伟大的神阿胡拉马兹达,他创造了这大地、天空。他创造了人类和人类的幸福。他立大流士为王,使之成为众(王)之王,众(号令者)之号令者。我(是)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万邦万民之王、这辽阔大地之王、叙斯塔佩斯之子、阿黑门宗室、波斯人之子,一个雅利安血统的雅利安人。[23](50)
可见,为了强化王权,波斯王构建了一套管理庞大帝国的政治运行制度,王权至上的政治理念融入河西行省治理中。虽然亚述人最先设立这一机构,但是正如学者奥姆斯特德所言,“在亚述的省与居鲁士建立的20 个行省之间,主要区别实际上是行省取代了独立性极大的君主国”[20](77)。波斯帝国的行省制使中央集权得以实现。在波斯帝国的行省制度中,主要由波斯王任命一位大行省总督进行管理,总督下由一大群官吏协理,大行省下又分为二或三级小行省,官制大约同大行省建制类似。中央与地方主要通过交换命令和向上奏请的方式保持着紧密联系。当然,在行省设立新官职或安插密探也是波斯王加强中央集权的主要手段。
因此,波斯人将中央集权式的“异质”政治制度因素引入叙利亚地区的政治制度构建中,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贯彻与执行。当波斯王在叙利亚地区设置河西行省时,原本以松散与自治为特征的联盟王国被迫融入了王权至上和中央集权的观念。虽然行省总督要听命于波斯王,但在行省内部,总督的权力也是比较大的。在波斯帝国早期,总督被作为波斯王的代理人,在行省制度建立后,总督成为地方官员,担负着管理行省民政与军队之责。一般而言,二或三级行省总督之间形成上级行省对下级行省的监管之权,下级行省不可越级上报奏章,这符合自上而下集权监管的逻辑运行规律。
(二) 自下而上的自治分权政治理念
闪米特人的统治使叙利亚地区的政治制度在自身发展和内外竞争中形成了独特的模式与演进规律。无论小国寡民的城邦,还是松散的联盟,均与帝国集权统治理念存在较大差异。在波斯“异质”政治制度到来前,叙利亚文明的政治观念中“自治性”比较浓厚。地中海东部沿岸以推罗和西顿等为代表的腓尼基地区保留着城邦自治传统,内陆的王国也是以某一大城邦为中心,联合周围的众城邦形成了“众邦之盟”,从邦国虽对主邦国拥有义务,但亦享有地方自治。即便在亚述帝国时期,叙利亚地区的众邦国在政治上依旧保持着独立性极强的君主国地位。
波斯对叙利亚地区的统治管理,实质上是将波斯的“异质”政治理念与叙利亚的政治实体进行调试和融合的过程。河西行省之下的犹大和撒玛利亚两个地方行省,在遵从波斯王与上级行省总督监管的前提下,拥有很大的自治权。而波斯帝国将王权至上和行省监管的集权统治模式自上而下地引入叙利亚政治制度中,促进了叙利亚地区集权思想的发展之时,也激发了本土“自治”思想自下而上的抵触,典型的表现是巴比伦和犹大地区的叛乱。腓尼基地区(行省)尤为体现了两种政治制度与理念的融合:因自身环境限制,这里形成了小国寡民式的城邦政治制度,各城市的自主性更强一些,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军力量亦迫使波斯人到来后基本遵循了该地的政治统治模式。不过,据史料记载,波斯将帝国集权统治理念也逐渐渗透到了该地,如公元前5 世纪中期之后,“波斯大王有意扶植西顿,不仅给予领土封赏,还建立了三个城邦居民组成的盟邦城市‘三城(特里波利斯)’,作为几个城邦会商要务之地”[19](157),使之具有了联盟王国的意味。因此,波斯帝国的统治者通过“妥协—折中”的方式融合外来波斯“异质”的政治制度与本土叙利亚“同质”的政治理念,最后形成了波斯-叙利亚式的多元统一政治制度,核心是集权与自治并存。
文明交往论认为,文明的“冲突与整合表面上是政治文化方面的矛盾或统一,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传统人们之间的碰撞或选择”,而“冲突作为一个过程,也有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整合的作用。冲突与整合是交替存在和相互转化的”[24](37)。两种异质政治制度在交往过程中,要经历抗拒—碰撞—渗透—冲突—渗透—整合的交往与鉴融的过程,正是在这种逻辑下,波斯治下的叙利亚政治制度实现了不同政治模式交融后的“平衡”。
总之,波斯统治下叙利亚政治制度演进的特点是集权与自治的碰撞、交锋与融合,背后的演进逻辑是两种文明在交往中逐渐达成一致,表现为波斯人自上而下的集权和叙利亚人自下而上的分权。正如晏绍祥在对波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观点的新解读中所讲到的,波斯大王的权力虽然足够专制,掌控着上至王公、下到升斗小民的命运,但所谓的中央集权,因为总督权力的放大和地方共同体的自治,实际上已经被化解[25](7-26)。虽然这一论断关注的是波斯帝国的统治模式,但在位于十字路口的叙利亚文明的政治制度演变中,这一特征更为凸显。
四、波斯统治下叙利亚地区政治制度的后世影响
波斯在叙利亚地区的统治始于约公元前539 年,终于约公元前330 年,客观而言,波斯帝国对叙利亚地区的统治,打断了叙利亚地区独立的政治发展道路,但亦让古叙利亚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发展模式,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促成了古叙利亚地区之作为“政治”层面的单位
古叙利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是地理概念上的一种称呼,而非政治概念,更何况这一地理概念所指范围也模糊不清。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约3000 年,闪米特人在后来被称为叙利亚地区的土地上建立了城邦文明,比如乌加里特、埃卜拉、古不拉等城邦,之后因城邦内部兼并战争和外部赫梯、亚述和埃及等政权的干涉,叙利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以雅穆哈德和夸特那为代表的盟国。在与外族政权建立了藩属朝贡体系后,叙利亚盟邦内部的政治制度演变为以某一城邦君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互助体系。盟邦最高君主负责率领盟邦成员对外抗击外族入侵,对内协调各邦利益关系,盟邦成员则要听从君主调遣,承担各自义务。虽然盟邦的形成有助于叙利亚地区文化的融合统一,但是政治上的松散,导致这一地区依旧呈现出分散状态。
波斯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波斯帝国将叙利亚划为“河西行省”进行统治,自此,叙利亚拥有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这个政治单位虽然依附于波斯文明,但是波斯帝国集权政治模式与叙利亚松散盟邦统治方式发生了碰撞与融合:一方面,波斯王通过强化王权和建立中央官僚体系,再由各级官员自上而下推行这一制度模式,终在叙利亚地区构建起了地方对中央、中央对君主的层级式帝国政治统治体系。作为地区的实际管理者,叙利亚行省的总督通过监管下级行省的方式,亦将王权与集权思想融入叙利亚的政治制度中。集权统治的帝国政治理念在叙利亚地区得以深化,促使叙利亚行省也建立起了以总督为中心,下设腓尼基、犹大、撒玛利亚和阿拉伯-纳巴泰次级行省,次级行省又直接管理地方城市的集权统治模式。另一方面,在波斯人到来之前,叙利亚地区已形成了以自治为特征的地方共同体或联盟王国的政治统治模式。自治政治思想遭遇到中央集权思想时,又发生了自下而上的层级抵触,进而弱化了王权思想的贯彻。因而,两种政治思想在斗争中最终走向妥协,波斯王为了帝国统治的稳定,于行省制度构建中,在强调集权之时,亦充分给予地方自治。在政治制度与理念的“交往”与“鉴融”中,波斯统治下的叙利亚地区最终演变为叙利亚-波斯的政治制度模式,由上而下的王权集中与由下而上的地方行省自治统一并行成为其最显著的特点,“大行省、小自治”成为对其最核心的政治制度内涵概括。
(二) 奠定了古叙利亚地区之“节点文明”的范式
在人类文明史上,古叙利亚文明是很难定义的一个概念。虽然波斯行省划分确立了叙利亚文明形式上的政治独立单位,但是,在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和外族政权不断干扰等因素的影响下,叙利亚地区并未形成独立政治实体、主导民族单元和统一文化态势,故而该文明具有发展的独特性和构建的复杂性。汤因比试图以凸显古叙利亚文明价值的方式对其进行构建,却陷入了“西方中心论”。斯塔夫里阿诺斯想跳出“西方中心论”,但忽视了它的古今差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多极化世界简单化为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具有明显的迎合西方称霸世界的需要。林志纯的“城邦—帝国”理论和吴于廑的“整体史观”,为叙利亚文明构建提供了启示,但主要适用于对其他几种古文明的认知。
因此,古叙利亚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文明范式,传统的文明构建理论并不能概括古叙利亚文明的概念范畴。叙利亚地区处于东西方世界的十字路口,波斯人到来之前,这里大多数情况下处于“混乱”状态,或者城邦间战争不断,或者与外族政权处于竞争关系,内部文明发展态势的多元性和民族成分的复杂性,使其文明整体特点模糊不清。波斯人将其归为一个行省的统治模式,加速了叙利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交流与外部交往。因此,对处于几大文明交往中心的叙利亚地区,用“文明交往”的理论来解析,更符合这一文明的演进规律。从文明交往的视角看,叙利亚文明具有“节点文明”的特质,犹如大网上的“节点”,既是诸文明的交汇地,也是新文化的发射台。在“交往”与“鉴融”的助推下,叙利亚文明凭借“文明交往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采用“节点文明”聚合与发散的方式与异族文化展开了长期的交融与合作,形成了波斯-叙利亚文明特质。应该说,正是波斯人的行省统治模式,让叙利亚的政治文明在兼容并蓄中,衍生出独特的“节点文明”范式。这不仅丰富了世界古文明的文明种类,更为之后叙利亚文明内部的加速融合与持续输出文明成果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三) 确立了古叙利亚地区之“疆域”地理的边界
历史地看,在波斯人到来之前,古叙利亚文明地理上的疆域边界概念并不清晰,闪米特人在这里建立了城邦文明,各个城邦更为关注的是城邦的疆域范围,城邦间战争也是为了这一目的。战争作为古代叙利亚文明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兼并的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会促进政治制度上的统一,但是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特别是受外族政权干扰的情况下,其本身也有可能会在冲突、无序的交往关系中阻碍政治统一。古叙利亚作为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埃及、亚述、赫梯等诸多文明在这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冲突、相互抗争,政治制度文明经常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这也决定了古叙利亚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政治上的分散、文化上的多样,导致其在疆域上的不确定。
波斯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状况。虽然这一地区的文化或文明仍然处于多样的状态,但是以王权之名将其归为一省进行治理,促使其地理疆界首次在叙利亚文明史上得以确立。应该说,地理边界的确定对古叙利亚文明意义重大,不仅为其政治制度上的进一步融合及独具特色的制度文明的形成提供了“物”的条件,也为叙利亚文明的“名实”一体化奠定了基础。叙利亚已经不再是一个模糊地区的代名词,而成为一个具有实实在在文明特质与特点的“疆域”文明。随着“疆域内”文明的碰撞融合,“疆域”中的人逐渐被称为“叙利亚人”,“疆域”中的文化逐渐被称为“叙利亚文化”,“疆域”内的文明逐渐被称为“叙利亚文明”,叙利亚“疆域”地理的边界形成亦促使叙利亚文明实体的形成。
五、结语
总之,古叙利亚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特文明。经过闪米特人的统治后,于公元前539年迎来印欧语系的波斯人统治,经历了居鲁士王的初建“巴比伦-河西”大行省,大流士将大行省划分出“河西行省”二级行省,薛西斯一世取消大行省,代之以“河西行省”升格为一级行省,下设犹大、撒玛利亚、腓尼基和阿拉伯-纳巴泰四个小行省,之后的君主基本维持了这一统治方式。行省内的各级总督有隶属关系,也有互相监督之责,波斯王有自上而下的集权手段,叙利亚行省也凭借自治的制度方式消减王权的干涉。因此,正是这一行省设置促使叙利亚地区将波斯的政治制度与叙利亚本土的政治模式进行了融合,创新发展出中央集权、地方自治和全面管控在内的“混合式”政治制度模式,体现出了叙利亚文明为“节点文明”的特质,对古叙利亚的政治制度单位、文明概念范畴和疆域边界范围的形成产生了奠基性作用,之后的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基本上延续了波斯人建立的政治制度模式,唯一不同的是它们的统治沿着这一道路进行了深化。
注释:
① 目前国内外学者并未将叙利亚文明作为文明主体进行整体、系统研究,而是以“附属”的形式“碎片化”呈现,故“叙利亚学”这一概念并未被明确提出。笔者认为,叙利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将其作为文明主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等角度,系统研究叙利亚地区自古至今文明发展的规律与特质,进而探析叙利亚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如埃及学、亚述学等,是为专门研究叙利亚文明的“叙利亚学”。
② 本文涉及的波斯帝国为古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前334年)。
③ 前三个小行省比较固定,南部的阿拉伯—纳巴泰行省的存在及其延续争议较大,也可能是个短暂的行省或者半行省,不过并不影响对河西行省下次级行省的总体阐述与理解。文中虽将这一地区列为行省,但主要还是以前三个小行省作为主体论述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