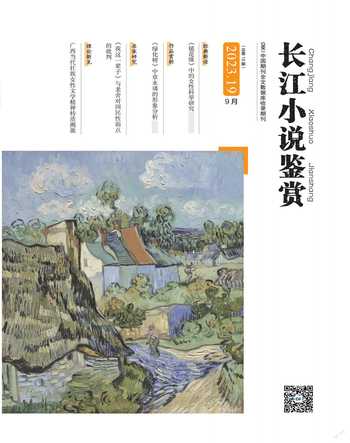《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的跨界书写
2023-12-20赖同方
[摘 要]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是当代波兰最具影响力的女小说家,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波兰文坛出现的一颗璀璨新星”,也是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基于对不确定性的关注,托卡尔丘克在长期写作中密切关注着“跨界”这一主题。小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在叙事视角上有意对叙述者进行淡化和模糊,使文本呈现出开放的效果;在文体上又以极具实验性的杂糅形式为读者带来新奇的阅读体验;同时,小说中又充溢着对国别、性别、生死、梦境与现实等多种界限的探讨,展现了托卡尔丘克对当下世界多元文化的深切关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跨界书写不仅开拓了文学的多维诗意空间,呼唤着人类找寻逐渐丧失的诗性精神,同时也是托卡尔丘克在后现代的当下积极思索多元未来的体现。
[关键词]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 跨界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9-0047-04
“跨界”是托卡尔丘克在作品中频繁叙述的一个主题,这源于波兰社会历史的剧变和其家族历史。托卡尔丘克的祖辈曾生活在加利西亚省的一个小村庄,由于地缘关系,加利西亚长期是俄奥争夺的目标,曾经被不同的国家统治过。二战后,加利西亚归属苏联,于是托卡尔丘克的整个家族不得不迁居到波兰南部与德国和捷克接壤的西里西亚地区[1]。出生于1962年的托卡尔丘克在其成长过程中见证了波兰半个世纪以来的动荡不安,又深受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熏陶,这使得她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在《圣体圣血节》一章中,她如此写道:“世界是运动的,而且是摇摆不定的。对于世界而言,不存在任何可以记住和可以理解的零点……风景是最大的错觉……人在风景中看到自己内在的不稳定瞬间。人到处看到的只是自己。”[2]不确定性是对世界的一种存在状态的认知,而世界具有的无限性、发展性和复杂性注定了不确定性在人类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是一种必然。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而在这种变化中很多事物镶嵌在一种模糊和暧昧不清的图景之中,确定的意义和答案则变得缥缈。也正是因为托卡尔丘克对不确定性的深信,象征着一种划分方式的“界限”在其作品中不断被探讨,而她也一直致力于去跨越那些人为界定的“界限”。
一、叙述界限
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叙述者“我”与现实中的作者托卡尔丘克的叙述界限是模糊的。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叙事者“我”是一位收集梦的女性。叙述者与其先生R搬到位于捷克和波兰边境的新鲁达附近的郊区居住,远离尘嚣,追求一种自然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态度。“我”每天收集梦,并将收集梦这一行为比作用珠子串项链,期望“从中就可弄出一个有意思的结构,做出一条独一无二,但本身是完整、美妙、无瑕的项链”[2]。而小说的现实作家托卡尔丘克与叙述者一样定居于波兰小镇的郊区,与大自然为伴,可以说叙事者“我”的集梦人身份与现实作者托卡尔丘克的文学家身份形成了互为隐喻的关系。备受托卡尔丘克推崇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就认为,文学创作本身就可以直接等同于梦幻虚构,可以说文学家其实就是一个做梦、收集梦的人。因此,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有意模糊了文本叙述者和作者的身份界限。
此外,小说中叙述者“我”与邻居玛尔塔的叙述声音也彼此交融,难以分清界限。小说的第一章以《梦》为开篇直接点出了这部作品最核心的内容——梦,紧接着第二章《玛尔塔》就立即引出文本的叙述者“我”的邻居,也是文中的关键人物,一位神奇的老人玛尔塔。在第二章中,“我”用大量笔墨描写了玛尔塔的神秘,“我”对于玛尔塔知之无多,玛尔塔并不热衷谈论自己,因此“我”只能想象和虚构玛尔塔其人的经历,“我创造了一个玛尔塔,连同她的过去和现在”[2]。玛尔塔对于“我”而言是个在夏天存在,冬天消失,身上有着“勉强晾干的潮湿气”的不识字的乡妇,然而,玛尔塔又自始至终随着“我”贯穿于小说之中——“我”所了解到的新鲁达的人事物往往就是源自玛尔塔。“她喜欢谈论别人……她还喜欢谈起那些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过的人——从而我找到证据,认为玛尔塔喜欢瞎编。”[2]小说中的“我”更像是玛尔塔讲述的故事的记录者,甚至“我”的记录方式就深受玛尔塔“碎片化”讲述方式的影响,“她不像别人,试图把所有重要的事情放在时间的框架里”,“她能说上几个钟头,直到我听腻了……有时她会无缘无故让自己的谈话戛然而止,一连几个礼拜不再返回到这个话题,然后又莫名其妙地重新开始”[2]。例如,小说关于圣女传记的作者的故事并非以一个章节或者连续的几个章节一口气叙述至结局,而是将故事割裂为几个部分,各个部分之间又插入了“我”的日常生活的章节。这种叙事安排就如同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了解、查询资料的真实经历——并非一次性全部了解完毕而是一段一段地将信息整合。而文本里的“我”也如此叙述道:“我永远不能肯定,在玛尔塔所讲的和我所听到的事物之间是否存在着界限。因为我不能将她和我区分开,将我俩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事物区分开。”[2]然而,“我”的叙述又并不完全等同于玛尔塔的叙述,玛尔塔为“我”提供了故事,影响了“我”的叙述,但是“我”与玛尔塔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玛尔塔身上的自然性、神秘性为“我”与玛尔塔的身份进行了区别,玛尔塔拥有一套自己的哲学思想,而“我”有时尝试理解接受瑪尔塔的想法,有时又对其有所保留,许多章节中都存在着两人思想的对话碰撞。
可以说,在整个文本中,故事的叙述者是不确定的、开放的,文本中的“我”是托卡尔丘克思想的主体部分,而玛尔塔同样反映着托卡尔丘克对这个纷繁复杂世界的一些创造性的思考。同时,托卡尔丘克对叙述者的淡化与模糊化的处理,突破传统物理时间观念的束缚,使时间呈现出虚指性、模糊性,让时间随着意识自由流转,从而将理念化的世界、虚构的想象世界、现实的世界三个空间整合起来,使“我”的意识在历史的碎片、现实的碎片、梦的碎片中反复跳跃,呈现出浑然一体的神秘诗性状态。
二、文体界限
文体杂糅是《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结构上最显著的特征。在小说中,托卡尔丘克将圣人传记、地方志、神话、笔记甚至菜谱等各种文体都融入创作之中,并使这些文体独立成章,可谓极具实验性的写作。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也随之不断变化,在当下的世界里,大量的生活叙事和生活事实已无法在传统叙事模式中得到容纳,部分先锋作家认为,传统作品中那种逻辑严密的结构已不能反映这个世界,表现人物最真实的状态,而应以符合世界复杂性的破碎形式去描述才能做到对世界真正的还原。而托卡尔丘克就试图以其极具实验性的“文体杂糅”去表现当下社会人们日常接受信息与思考的“真实”。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作者将小说背景置于波兰与捷克边境的一座小镇新鲁达,并通过迁居这座小镇的“我”在这片乡野中的日常生活将小镇的当下与历史一一揭开。如同小说的名字“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托卡尔丘克将小说分割成两个世界,一个是“我”的视角下现实中的新鲁达,这个主线时空里主要是“我”的日常,其中充满了生活的碎片,而小说又正是通过“我”在新鲁达平淡自然的生活引出另一个世界——小镇人们各自的故事、教堂里圣女画像的故事及圣女传记作者的故事等。
将某些过于日常化的文本——例如菜谱——单独成章作为小说的内容,似乎还是颇为令人匪夷所思,也不禁让人想到后现代下的“文学性蔓延”问题。是否正如鲍德里亚所认为那样:艺术在日常审美化的过程中解体,成为形象的无止休循环,并最后沦为一种陈腐的泛美学[3]?然而,细观小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整体,我们可以发现现实和日常生活在其中并非被彻底文本化,托卡尔丘克随着叙事的发展有意识地在小说整体中引入片段,从而消解了“文学性”对文类界限的彻底颠覆。例如,小说在叙述完孩子因吃下毒蝇菌而不治身亡的故事后,紧接着附上一份毒蝇菌的烹饪菜谱,这使文本间呈现出一种荒诞的联系,从而使读者能够获得一种阅读的陌生感。在文学创作中,由于文本间的意义生成,虚构与现实之间依旧存在着不可磨灭的界限,文学的语言和审美经验决定了被精心构建出的文学世界不可能直接等同于琐屑平庸的日常生活世界。因此,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托卡尔丘克将不同的文体文本杂糅拼贴而非定序排列,这使得文本间的逻辑被淡化,此外通过有意识地引入和模拟其他文本,使得文本与文本间互为语境、意义与意义之间互为阐释,形成一种如同莫比乌斯环般的拓扑空间。显然,在托卡尔丘克笔下,各种文类的碎片并非只是单纯的无序拼贴,而是在消解了自身主体性的同时融入他者之中,从而彰显了其他物体的价值和异质事物之间的联系,以达到一种深度自由的状态。因为所谓自由并不是一种绝对突出自我性的孤立状态,相反,自由只有在无论如何也无法逃离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才得以存在,而自由的深刻程度也正取决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紧密程度。正如鲍曼所认为的自由,是一种历史的建构,是一种社会关系[4]。而后现代文学正是在游戏情节之下,以已知的语言创造游戏去言说不可言说之物,话语的迷宫、情节的碎片在文本的“狂欢”中,使异质间的冲突得以消融,在一种反逻辑的艺术逻辑中创造多元性,从而构建出一种深度自由的话语空间。
托卡尔丘克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结构中实现了对传统小说模式的颠覆,通过不同文体的剪切拼贴,在看似散漫自由的叙述中,为小说的情节结构制造了空缺和留白,从而使现实与想象于其中共生,营造出似真似幻之感,而这种非线性叙事模式潜藏的异质文本间难以被察觉的关联也对读者的审美活动提出挑战,这种关联不仅体现了作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创作状态的原生态的思维轨迹,同时这种非线性的“漫想”也使阅读成了探秘作家思想的旅程,读者得以在文本间留下的空间中自由遐想,从而参与小说意义的生成过程,读者在自主建构小说内涵的过程中体会到一种由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陌生新奇的阅读体验。
三、其他界限
除了叙事界限和文体界限之外,小说在叙述各类故事时也展现出国别、性别、生与死、梦境与现实等界限的模糊与跨越。
托卡尔丘克往往将故事的发生地安排在地理边界处,并试图在边界处创造世界中心。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托卡尔丘克的叙述就围绕着德国和波兰边界的小镇新鲁达,可以说小说里的边界既是真实的也是象征的——“通往边界的路已经被毁,机动车无法前行,但动物蔑视人类的边界随意穿行,当地的居民和外来的旅客也会在此抄近路或是寻求越界的刺激”[1]。同时,小镇内部也存在着德国的历史与波兰的现实之间的无形边界。在《彼得·迪泰尔》一章中,一个曾在捷克和波兰边界的村庄生活过的男人在暮年重回故地,然而这个男人却意外死在了波兰与捷克两国的边境线上,他的尸体横跨两个国度,而当两国的边防军先后发现他的尸体时,都将他的尸体像踢皮球一样拖放到对方的一侧,犹如一场无声的荒谬剧。这个故事里平时形同虚设的边界,在生死之时显得冷酷与可笑,同时也映射着历史。
除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界限,作为女性主义者的托卡尔丘克还十分关注性别界限。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有两个关于性别的故事在文本中交相呼应,一个是圣女传记,另一个是圣女传记的作者的故事。虔诚信仰并侍奉上帝的少女库梅尔尼斯不断地反抗着父权的压迫,最后她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她以长出胡子成为耶稣面孔的方式对男权社會进行了最终的反抗。而写出了圣女传记的作者是一位有着性别认知障碍的男修士帕斯哈利斯,他在生理与心理性别倒错的痛苦中不断发现自我、成就自我,从而写就了圣女传记。这两个故事反映了托卡尔丘克“双性同体”的女性主义观。“双性同体”最早由伍尔夫提出,其理论意义在于强调个体精神上两性的融合及男女两种性别气质的交互,这不仅使传统父权社会中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得以被打破,并且对西方传统思维中的“逻格斯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解构[5]。而托卡尔丘克正是通过圣女与修士两个故事的性别书写展现了其对父权历史中以男性价值为单一仲裁尺度的反叛。
此外,生与死、梦境与现实的界限也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被不断探讨。托卡尔丘克以敏锐的哲思和非凡的想象,使小说中的人物不断穿梭在生死之间、梦境与现实之中。在小说里,人可以处在半生半死之间,“吃桩菇的时候,人是同时处于既可活也可死的瞬间”[1];人可以站在生死的边界看见自己,占卜师狮子“开始生活在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完全是一种错觉,是由直觉、本能产生的梦境,是感官的习惯”[1];人也可以处于永生之中,“没有任何有关《圣女传》叙事者死亡的记载,再说又怎么会有这种记载呢?这个人既然是在娓娓动听地讲述圣女的故事,那就必定是个活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永生的,他超越了时间所能包容的氛围”[1]。在《库梅尔尼斯Hilaria中的幻景》一章中,托卡尔丘克如此写道:“我明白我们最后的审判将是惊醒……我们的世界住的是熟睡的人,他们死了,却梦见自己活着。”[1]于是在小说中,现实与梦境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如克雷霞在现实中执意找寻她的“梦中情人”,梦境成为可以浸入现实、指导现实的存在。通过生与死、梦境与现实的交融,托卡尔丘克突出表现了人物的“精神现实”,塑造了许多不同时空下不同经历的人物,并通过夸张和变形使这些人物自由穿梭于亦梦亦醒、人神相通、生死轮回等“神奇”之中,这些人物在现实层面为理性与秩序所驱使,同时在心理层面他们得以在混沌之中探寻最本真的自我,找回那些被理性与秩序所束缚住的本性。
四、结语
人们如何体验世界,便如何讲述故事。当世界被各种信息、声音分化、分裂,当时代,又是一個“界限”被不断模糊、解构的时代,托卡尔丘克舍弃了中心的视角,大胆挑战传统的文学创作方式,她以自由梦幻的书写姿态游荡在世界的各种边界,以轻灵的笔触抚慰历史的伤痛,引领读者挣脱国族与男性话语构筑起的现实世界,在不同的文体与叙述声音中去捡拾那些隐匿于历史细缝中最真实地反映着人类经验、生存境况和记忆的微小碎片,她的跨界书写不仅开拓了文学的多维诗意空间,呼唤人类找寻逐渐丧失的诗性精神,同时也是其在后现代的当下积极思索多元未来的体现。而托卡尔丘克创造性的写作形式,也为我们展现着文学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栾天宇.跨越边界的寻根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J].当代外国文学,2019,40(4).
[2] 托卡尔丘克.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M].罗丽君,袁汉镕,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3] 米勒.论文学的权威性[N].国荣,译.文艺报,2001-08-28(2).
[4] 鲍曼.自由[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5] 张婷玉.弗吉尼亚·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9.
(责任编辑 夏 波)
作者简介:赖同方,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