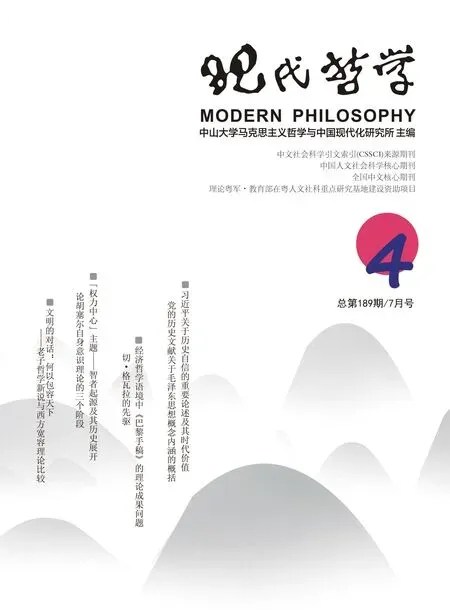切·格瓦拉的先驱
2023-12-20叶健辉
叶健辉
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蜚声世界,其肖像出现在这个星球的各个角落。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切·格瓦拉,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称呼:“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尘世基督”等。除了这些标签之外,很少有人认为需要认真对待切·格瓦拉的著作和思想。基本上,人们认为,切·格瓦拉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道德浪漫主义者”。切·格瓦拉仿佛是一个飘渺的精灵,栖息在另一个世界,跟现实的人类社会和历史没什么关系。笔者认为,不能这么轻易地打发切·格瓦拉,他不是“无根的游魂”,其“新人”思想深植于拉丁美洲传统之中,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
集中体现切·格瓦拉“新人”思想的是其1965年发表在一份乌拉圭杂志上的著名文章《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ElsocialismoyhombreenCuba)。(1)Ernesto Che Guevara,Ernesto Che Guevara:obras completas,Buenos Aires:MACLA,1997,pp.204-222.这是一封信,意在回应外人对古巴社会的如下质疑:古巴社会是一个没有个人自由的社会,所有人都听命于国家。从形式上看,这篇文章很像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回应了对共产主义的种种指责一样,切·格瓦拉也在《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中回应了对社会主义古巴的质疑。因而,《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有“古巴的《共产党宣言》”(2)Néstor Kohan,De Ingenieros al Che,Buenos Aires:Biblos,2000,p.342.之称,对于理解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简要回顾了古巴革命的历程。古巴革命起于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等人领导的对蒙卡达兵营的袭击,袭击以失败告终,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等人入狱。之后是古巴革命的另一个阶段——游击战阶段。武装的游击战士进入古巴马埃斯特腊山区,不断展开革命活动,像催化剂一样促进了古巴人民的觉醒。越来越多人加入游击队伍,最终迎来了1959年1月1日革命的决定性胜利。革命政府成立,古巴革命进入新阶段。古巴革命政府标志性的举措是进行群众广泛参与的土地改革,除此之外,还有经济国有化等。对外方面则是在1961年4月进行反击美帝国主义入侵的吉隆滩战役。此后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接着,《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提出了意在回应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在古巴,个人服从于国家,群众以巨大的热情和纪律完成政府确定的各项任务,而发起任务的往往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或其他高级官员,因而对古巴的批评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国家经常出错。当国家出错的时候,集体热情会显著消退,导致事情无法进行,最后迎来纠正阶段。国家不能依赖机械主义实现预期目标,必须善于倾听群众的声音、注意群众的反应,才能解决问题。而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倾听群众声音的大师,所以在古巴,在国家和人民、领导和群众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辩证统一”(unidad dialéctica)。(3)Ernesto Che Guevara,Ernesto Che Guevara:obras completas,p.207.古巴人并不是机械地服从国家的指令,由此,《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驳斥了古巴没有个人自由的指责:古巴人民积极参与国家集体意志的形成,古巴国家是古巴人民自觉行动的结果。与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个人与社会之间自觉的、有意识的辩证互动形成对照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之间冰冷的、盲目的抽象关联:联结人与社会的纽带是价值规律,像狼一样互相竞争的孤立的人、作为商品存在的“异化的人”受到看不见的价值规律的支配。(4)Ibid.,p.207.在此,“新人”已经呼之欲出:“新人”是与资本主义旧社会有别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
但是,新生的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就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那样,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在帝国主义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要获得解放,还需要进行反对外部压迫、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在技术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欠发达状态和资本外逃等因素使奇迹般的变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社会主义建设将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由此,《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明确提出了“新人”思想:建设社会主义不仅需要物质基础,还需要“新人”。(5)Ibid.,p.209.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个物质基础,但现实的历史没有为社会主义提供这样的物质基础,因而人们需要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在物质基础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人的因素就特别重要。需要不一样的人推动历史走向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人”。《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指出,虽然物质激励不可或缺,但道德因素在创造“新人”的过程中将具有根本性的作用。(6)Ibid.,p.210.或者说,根本上要靠道德激励动员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这看上去是在企图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切·格瓦拉的“道德浪漫主义”。
这无疑是一种“浪漫主义”,但并非“不切实际”,在物质基础不雄厚因而无法进行大规模物质激励的情况下,能怎么办呢?不得不依靠道德激励。实际上,这更像是一种“道德现实主义”。我们不能离开20世纪60年代古巴的社会现实来讨论切·格瓦拉的思想和行动。同样,看起来主要靠道德激励动员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任务”,但古巴革命就通过游击战完成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不可能的任务”。1956年11月,82个知识分子乘坐格拉玛号从墨西哥出发前往古巴,登陆古巴的时候遭到伏击,只有12人活下来。就是这12人走进了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始打游击,在古巴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击败了数量和装备明显占优的政府军,取得革命的胜利。政府军方面物质条件优裕但失败了,游击队方面物资匮乏却是胜利者。这是一个奇迹:得到人民支持的少数武装力量可以战胜被认为不可战胜的军队。(7)[古]格瓦拉:《论游击战》,吴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72页。在艰苦的游击战过程中,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像“蜗牛”(8)同上,第56页。一样把家背在身上的游击战士靠什么自我支持呢?根本上就是靠道德。这种道德还具有宗教色彩:切·格瓦拉在《论游击战》中将游击战士称为“战争中的耶稣会士”“苦行修道者”。(9)[古]格瓦拉:《论游击战》,第10、48页。或者说,游击战士在其间行军的山山水水就是其修道的道场,战争对于游击战士而言是一种苦行修道的方式。这种道德上的根本性优势使游击战士经得住严峻的考验,最终战胜了政府军。切·格瓦拉的“新人”在根底上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游击战士。
就像游击队员在游击战中不断锤炼自己成为为人民解放而战斗的先锋一样,切·格瓦拉相信,古巴人特别是古巴青年也可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锤炼自己,成为为人民解放而劳作的先锋。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信念,古巴革命的经验就可以支持这种信念。这意味着,劳动是游击战士的新战场。“社会主义就是生产力”(10)Ernesto Che Guevara,Ernesto Che Guevara:obras completas,p.84.,劳动和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就像革命时期的马埃斯特腊山区是锤炼游击战士的学校一样,革命后的整个古巴社会成为锤炼“新人”的学校。所以,切·格瓦拉在《共产主义青年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Quédebeserunjovencomunista)、《对待劳动的新态度》(Unaactitudnuevafrentealtrabajo)等文章中一再强调,需要培育对待劳动的新态度,将劳动视为“人的最高尊严”,号召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成为劳动的先锋、学习的先锋。(11)Ibid.,pp.99-112,155-171,106,169.也就是说,“新人”集战士、劳动者和学者于一身,不仅将战场上的战斗视为一种对人的锤炼,而且将劳动和技术的发展视为一种对人的锤炼。这样的“新人”是在一个共同体中与他人共同劳动、学习、战斗的人,是与人民的甘苦、技术的进退、历史的成败紧紧相连的人。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仍然对劳动和技术抱持一种陈旧的态度,将劳动视为一种对人的折磨和奴役,将机器视为对人的自由的限制。人们往往有一种“逃离意向”(intento de fuga)(12)Ibid.,p.215.,不愿意劳动,不愿意投身于缓慢而艰苦的技术革新。或者说,人们往往在根本上仍然把人视为一个“孤立的人”,将自由视为一种“逃离”,将与他人“脱钩”视为一种“解放”。这个孤立的、抽象的、逃离社会的人就是与“新人”相对的“旧人”。资本主义就建立在孤立的“旧人”的基础之上,靠这样的“旧人”显然无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种与之相对的、热情参与社会建设的“新人”。可见,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怪念头,而是现实的要求。
总之,“新人”的基本内涵是社会建设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具有热爱劳动、追求技术发展等基本特征。这是在回应古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新人”的根底则是古巴革命时期致力于土地改革、有“大地守护者”形象的“游击战士”。因而,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根植于古巴的社会历史现实。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可以在阿根廷社会主义思想家阿尼瓦尔·庞塞(Aníbal Ponce,1898-1938)和秘鲁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1894-1930)那里找到渊源。
二、阿尼瓦尔·庞塞:格瓦拉的阿根廷先驱
有“阿根廷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理智精神”(13)Sheldon B. Liss,Marxist Thought in Latin Ame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49.之称的阿尼瓦尔·庞塞在写于1935年,出版于1938年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Humanismoburguésyhumanismoproletario)一书中明确提到“新人”。此书曾于1962年在古巴再版,阿根廷学者内斯托尔·科安(Nestor Kohan(14)或译内斯特·可汗,[南非]格雷泽、[英]戴维·M·沃克尔编:《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王立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6页。)认为,此书是切·格瓦拉“新人”思想的直接来源之一。(15)Néstor Kohan,De Ingenieros al Che,p.200.《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一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涉及从文艺复兴时期代表性的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到20世纪法国文人罗曼·罗兰等一系列人物,第二部分以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为中心讨论无产阶级人道主义。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将伊拉斯谟视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典型,是资产阶级时代在文化上的标志。资产阶级与封建领主或诸侯相对,文艺复兴代表了资产阶级在文化上超越中世纪的尝试。文艺复兴所倡导的古典文化复兴运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重新解释和占有古典文化的运动。在贵族地主和僧侣主导的中世纪,朱庇特是克里特国王,忒修斯是雅典公爵,维吉尔是耶稣基督的宣告者,奥维德的诗歌则被用于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16)Aníbal Ponce,Humanismo burgués y humanismo proletario,La Habana:Imprenta Nacional de Cuba,1962,p.38.也就是说,在中世纪,古典文化被解释为封建等级制度的捍卫者。文艺复兴颠覆了这种对古典文化的解释,以人的尊严和优越性为中心提出对古典文化的新解释:首要的现实不再是来世,而是今世。(17)Ibid.,p.41.古典文化不再是神圣的文化,而是世俗的文化。随着世俗生活的扩展,计算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此,不注重日常计算的贵族日渐没落,贵族所追求的神圣的崇高逐步让位于资产阶级所崇尚的世俗理性。而用来衡量世俗生活之理性与否的尺度是黄金,黄金是资产阶级计算理性凯旋的标志。伊拉斯谟的《愚人颂》实际上是一曲“黄金颂”(canto al oro):(18)Ibid.,p.64.
卡俄斯、俄耳库斯、萨图恩、伊阿珀托斯以及其他过时老朽的众神都不是我的父亲,但本身就是丰饶财富之神普路托斯,却是“诸神与众人的唯一生父”,不管荷马和赫西俄德甚至朱庇特会说些什么。他只需点一点头,今天也和过去一样,所有的东西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全都被搅得颠倒倾覆,乱七八糟。无论是战争、和平、政府、议会、法庭、集会、婚姻、合同、条约、法律、艺术、喜庆、严重之事……一句话,人间一切公务和私事,全都按照他的意志来安排处理。(19)[荷]伊拉斯谟:《愚人颂》,许崇信、李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0-11页。
在伊拉斯谟笔下,财神普路托斯是支配古典世界的神,其他神在生机勃勃、熠熠生辉的财神面前全都黯然失色。而“愚人”是支配天上人间一切事务的财神普路托斯之子,出生于“不知有辛苦、衰老和疾病”的“福岛”。生命的起源要归功于来自“福岛”的“愚人”,只有通过“愚人”的祝福,生命才能繁盛。(20)同上,第13页。苏格拉底这样追求“智慧”的哲人在实际生活中毫无用处,而正是“智慧”使苏格拉底送掉了性命,柏拉图所赞许的哲人则“会把国家糟蹋到无以复加的程度”。(21)同上,第28、29页。整个庄严肃穆的古典世界在“愚人”的笑声中坍塌:贫穷和饥饿总是和贤人同在,而作为财神之子的“愚人”则财源滚滚,并掌管国事,一派欣欣向荣。(22)同上,第91页。“愚人”不仅是古典世界的颠覆者,同样是基督教世界的改造者:真正的基督教乃是“愚人”的宗教,因为“基督教与愚昧有着某种血缘关系,但与聪明却毫不沾边”(23)同上,第103页。。《愚人颂》中的“愚人”就是资产阶级的化身。就像中世纪的古典研究者为封建贵族量身打造一个古典世界一样,“愚人颂”为资产阶级打造了一个新的古典世界和一种不一样的基督教,“愚人颂”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颂”。
“愚人”或资产阶级主宰世界的手段就是黄金所代表的财富。黄金则与哥伦布和新世界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哥伦布对新世界的“发现”,使得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在16世纪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贵金属的广泛流通带来市场的高度繁荣,最终使布商出身的银行家雅各布·富格尔权倾天下,不管是国王还是教皇都要在雅各布·富格尔面前俯首。(24)Aníbal Ponce,Humanismo burgués y humanismo proletario,pp.41-42.黄金是资产阶级大踏步征服世界的标志。“黄金颂”的作者伊拉斯谟则是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的代表,因而,伊拉斯谟所代表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除了反封建这一特征之外,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还有恐惧“小民”(popolo minuto)或“下民”(bajo pueblo)的特征。(25)Aníbal Ponce,Humanismo burgués y humanismo proletario,pp.50-51.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具有这种两面性或双重性,一方面反贵族,另一方面又反人民。伊拉斯谟在《愚人颂》中将人民称为“强有力的巨兽”,(26)[荷]伊拉斯谟:《愚人颂》,第32页。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则将人民描述为“章鱼”:“一种无头、多足的动物”。(27)Aníbal Ponce,Humanismo burgués y humanismo proletario,p.50.可见,资产阶级蔑视人民,因为人民像章鱼一样没有头脑、注定与文化绝缘;同时也害怕人民,因为人民强壮有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理性对抗贵族和教士所宣扬的宗教,却对人民宣扬宗教和隐忍。伊拉斯谟说:“与人民同感是一种耻辱。”(es vil e indigno sentir con el pueblo)(28)Ibid.,p.71.不为人民所代表的充满激情的身体的律动所干扰,远离人民的斗争,知识分子飘渺的灵魂才能保持平静。(29)Ibid.,p.79.文艺复兴所推崇的理性、人的尊严和优越等,只为远离人民的孤立的精英保留。知识的奥秘也不能向人民透露:意大利历史上英勇无畏地走向火刑柱的科学圣徒布鲁诺拒绝向人民传授科学。(30)Ibid.,p.52.可见,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一种要“逃离人民”的抽象的人道主义。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将莎士比亚1611年的传奇剧《暴风雨》中的角色“爱丽儿”——一个飘渺的精灵——当作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象征。《暴风雨》(31)参见[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8卷,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80页。有两条故事线:一条讲的是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与其弟弟安东尼奥、那不勒斯王阿隆佐等人之间的纠葛;另一条讲的是流落到荒岛的普洛斯彼罗与岛上的爱丽儿、凯列班之间的纠葛。第一个故事是宫廷政变的故事: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的弟弟安东尼奥串通那不勒斯王阿隆佐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因究心于法术而疏于政务的普洛斯彼罗,成功篡位,成为新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和其女儿米兰达乘坐一艘船流落到一个荒岛。第二个故事是“殖民新世界”的故事:流落到荒岛的普洛斯彼罗用法术救出了被女巫西考拉克斯囚禁在一颗松树缝里的精灵爱丽儿,在爱丽儿的帮助下使西考拉克斯的儿子凯列班为自己劳动。两个故事由于新米兰公爵安东尼奥和那不勒斯王阿隆佐及其儿子腓迪南王子等人来到荒岛附近的海域而交织在一起。普洛斯彼罗役使精灵爱丽儿制造了一场暴风雨,使那不勒斯王子腓迪南与其父亲阿隆佐失散,并使腓迪南与女儿米兰达相遇;普洛斯彼罗由于女儿米兰达与腓迪南王子的联姻而使自己得以离开荒岛,回到米兰继续研究法术。最后的结局是一派大团圆,所有来自“旧世界”的人一起回到“旧世界”。另一方面,那不勒斯王阿隆佐的厨师斯丹法诺和弄臣特林鸠罗由于暴风雨而遇到凯列班,斯丹法诺的酒使凯列班痴狂,凯列班策动两人“起义”,杀死普洛斯彼罗成为新的岛主。但精灵爱丽儿获知消息并报告了普洛斯彼罗,“起义”以失败告终。
一般而言,人们把凯列班视为“野蛮”或“肉体”的象征。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对凯列班的设定是“野性而丑怪”。(32)同上,第3页。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所引用的《暴风雨》译本中,凯列班是“红色的怪物”(monstruo rojo)。(33)Aníbal Ponce,Humanismo burgués y humanismo proletario,p.83.按剧中角色的说法,凯列班“有些隔宿发霉的鱼腥气”。(34)[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8卷,第38页。总之,凯列班具有丑、怪、臭等与“野蛮”相连的负面特征。“凯列班”(Caliban)一词可以回溯到最早来到新大陆的哥伦布的日记,来自“食人者”(Caníbal)一词,“食人者”又与“加勒比”(Caribe)联系在一起。(35)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Todo Caliban,Buenos Aires:CLACSO,2004,p.23.与之相对,《暴风雨》中飘渺的精灵爱丽儿通常被视为“文明”或“精神”的象征。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在1900年出版的《爱丽儿》(Ariel)一书中就用凯列班代表强调实用的美国,而用爱丽儿代表注重精神的拉丁美洲,将爱丽儿视为拉丁美洲“拉丁性”的守护神。但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一书中,凯列班是“受苦的群众”(36)Aníbal Ponce,Humanismo burgués y humanismo proletario,p.83.或人民的象征,而爱丽儿则代表鄙视劳动的旁观者或知识分子。爱丽儿的自由建立在凯列班的劳动之上,但却鄙视凯列班。鄙视凯列班的爱丽儿让人想起将人民视为“强有力的巨兽”的伊拉斯谟。凯列班的故事并没有在《暴风雨》中终止。260多年后的1878年,法国人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以《凯列班》为题续写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凯列班的“起义”以失败告终不同,在受到巴黎公社经验冲击的欧内斯特·勒南的《凯列班》中,以“打倒拉丁文!”为号召的“起义”成功了。(37)Ibid.,p.91.但没有懂“拉丁文”的爱丽儿的帮助,凯列班的权力不能持久。凯列班的“起义”成功了,但凯列班的事业仍然以失败告终。欧内斯特·勒南也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谱系的一个环节,也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前辈一样将人民视为“无头、多足的章鱼”,注定与文化绝缘。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一书第一部分最后讨论了标志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向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过渡的人物:罗曼·罗兰。罗曼·罗兰是欧内斯特·勒南的学生,早期秉持抽象人道主义的立场,专注于精神和理性的世界,远离滋扰精神独立性的人民,但他逐步发现这种爱丽儿式的飘渺的独立是一个幻象,并不真正独立,受制于外部社会条件。(38)Ibid.,p.98.促使罗曼·罗兰走向“人民的剧场”、走向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是1914年开始的欧洲“文明”国家之间“野蛮”的互相屠杀和1917年十月革命。1914-1918年战争是“资产阶级的黄昏”(crepúsculo burgués),战争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幻灭使怀疑的阴云不断蔓延,资产阶级无意间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成为替罪羊——“机器主义杀死了灵魂”,因为正是精良的机器使欧洲成为惨绝人寰的绞肉机。(39)Ibid.,pp.105,107.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看来,机器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灵魂要“逃离”机器世界才能获得自由。而在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得到集中体现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则认为,机器为“全面发展的人”创造了基础,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才导向人的异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40)[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6-557页。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同,对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来说,劳动不是对人的折磨和囚禁,机器不是限制灵魂自由的障碍,而是人实现全面发展的途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用“新人”(41)Aníbal Ponce,Humanismo burgués y humanismo proletario,p.113.或“本真的新人”(auténtico Nuevo Hombre)(42)Ibid.,p.158.指代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全面发展的人”。与资本主义“旧人”不同,社会主义“新人”自觉地接过机器这项人类文明的成果,使之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从而结束人类的史前阶段,开始真正的人类历史。因而,走出貌似独立的精神世界、走向在历史中劳作的人民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是“真正的文艺复兴”。(43)Ibid.,p.174.
可见,阿根廷人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与阿根廷社会主义思想家阿尼瓦尔·庞塞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中所表达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一脉相承,都强调“新人”区别于“旧人”的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走向人民,另一个是肯定技术或机器的解放作用。简单地说,“新人”是一种“新型知识分子”,一种不再恐惧、蔑视人民而是走向、融入人民的知识分子。由于人民生活在劳动和机器的世界中,“新型知识分子”同样致力于技术的发展或机器的改进,为人民的解放和发展创造物质条件。如果用《暴风雨》中的角色来描述,那么“新人”就是与凯列班站在一起、为凯列班的解放而斗争的爱丽儿。古巴学者罗贝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在《凯列班总论》(TodoCaliban)一书中就将切·格瓦拉描述为这样的“新人”,说切·格瓦拉是他所见过的“最凯列班化的爱丽儿”(el más calibanesco de los Arieles)。(44)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Todo Caliban,p.140.
三、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格瓦拉的秘鲁先驱
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不仅可以在1962年于古巴再版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一书中找到明显的踪迹,还可以回溯到切·格瓦拉参加古巴革命前在拉丁美洲的游历。在1952年游历到秘鲁时,当时还是医学专业学生的切·格瓦拉曾住在秘鲁医生乌戈·佩塞(Hugo Pesce(45)或译乌戈·佩谢,[古]格瓦拉:《摩托日记:拉丁美洲游记》,王绍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03页。)家里,他们就拉丁美洲社会、政治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乌戈·佩塞是秘鲁共产党党员,在1929年曾接受秘鲁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委托在拉丁美洲第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非常熟悉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切·格瓦拉在1962年版的《论游击战》中表示,乌戈·佩塞医生极大地改变了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46)Néstor Kohan,De Ingenieros al Che,p.198.而在1954年游历到危地马拉时,切·格瓦拉结识了另一个当时在危地马拉流亡的秘鲁人伊尔达·加德亚(Hilda Gadea),他们讨论过马里亚特吉1928年出版的《秘鲁七论》(7ensayosdeinterpretacióndelarealidadperuana,中译为《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和1950年出版的《清晨灵魂》(Elalmamatinal)两部著作。(47)Marc Becker,Mariátegui and Latin American Marxist Theory,Athens,Ohio: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3,p.75.切·格瓦拉可能还阅读过马里亚特吉1934年在智利出版的《为马克思主义辩护》(Defensadelmarxismo)一书。(48)Ibid.,p.76.唐纳德·霍奇斯(Donald Hodges)认为,《清晨灵魂》是切·格瓦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49)Ibid.,p.79.
马里亚特吉在《秘鲁七论》中给出了一种对拉丁美洲历史的总体解释,将拉丁美洲历史分为四个阶段:部族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就秘鲁而言,第一阶段为印卡帝国的古代共产主义时代;西班牙在16世纪的征服和殖民使秘鲁进入封建主义时代;19世纪初的独立战争则使秘鲁进入资本主义时代;1914-1918年战争之后,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秘鲁将进入现代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时代。但与欧洲历史呈现出某种整齐的线性特征不同,拉丁美洲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更替并非截然分明,而是呈现出某种犬牙交错的形态。印卡帝国时代的因素在20世纪仍然有其现实影响,这在马里亚特吉生活的时代表现为印第安人问题或土著问题。马里亚特吉在《秘鲁七论》中说,印第安人从来没有真正“抛弃那种不向理性而向大自然寻求答案的生活观念。在瓦努科省的印第安人的意识中,三位家神,即瓦努科省的三座小山比基督教的‘来世’更加重要”(50)[秘鲁]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白凤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87页。。就像西班牙人从来没有完全征服印第安人的山区一样,在19世纪独立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的秘鲁资产阶级也从来没有完全推翻封建殖民贵族的统治:“在共和国的一百年间,我们秘鲁不曾有过真正的资产阶级,不曾有过真正的资本家阶级。原来的封建阶级乔装打扮成了共和派资产阶级,保持了它们的地位。”(51)同上,第33-34页。独立战争之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没有根本改变秘鲁的封建性质,没有根本触动贵族地主和教会的特权。或者说,领导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是雅各宾式的、具有坚强意志、要以自己的信念塑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的领导阶级,而是抱持殖民地心态的资产阶级,时时把目光投向原宗主国所在的欧洲,把自己看成是在拉丁美洲生活的欧洲人。资产阶级的平等纲领在理论上理所当然地包括解放印第安人,独立后的秘鲁也制订了保护印第安人的法律。但这些法律由于没有强有力的执行人而只是一堆具文。这样,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印第安人依然是印第安人,依然像西班牙殖民者主宰的封建时代一样遭受沉重的压迫。马里亚特吉特别指出,印第安人占秘鲁人口五分之四,是“真正的秘鲁”,却对秘鲁民族性的形成几乎不发生作用,“秘鲁的骚人墨客几乎从来没有感到与人民有什么联系”。(52)[秘鲁]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第177、178页。也就是说,秘鲁的文学仍然是一种殖民地文学,不是真正的秘鲁文学,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秘鲁人民的感情在其中得不到表达。
一句话,资产阶级所主导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秘鲁仍然具有封建和殖民地性质,既不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未能真正独立。需要具有坚强意志的“新人”(53)José Carlos Mariátegui,Invitación a la vida heroica,Lima:Instituto de Apoyo Agrario,1989,p.285.来创造真正独立的“新秘鲁”,完成19世纪独立战争的英雄们未竟的事业。马里亚特吉的“新人”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相对的“新人”,与拉丁美洲的真正独立或“第二次独立”(54)José Carlos Mariátegui,The Heroic and Creative Meaning of Socialism:Selected Essays of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tr.,Michael Pearlman,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96,p.130.相联系:“新人”的革命将不再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而直接是“社会主义革命”。(55)José Carlos Mariátegui,Invitación a la vida heroica,p.347.哪些人是推动秘鲁或拉丁美洲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人”呢?除了马里亚特吉这样的走向人民的新型知识分子,“新人”的主体是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印第安人,而不是一般理论所设想的工业无产阶级。马里亚特吉所创立的意在唤起印第安人革命热情的杂志名叫《阿毛塔》(Amauta),“阿毛塔”是秘鲁古代印卡帝国时期的通用语克丘亚语,意为“智者、导师”,马里亚特吉后来也常常被称为“阿毛塔”。也就是说,用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要带领古老的印第安人挣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锁链,走向社会主义。显然,马里亚特吉在这里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非常规的社会主义,他将这种社会主义称为“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56)Ibid.,p.349.跟切·格瓦拉要靠“道德”推动人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类似,马里亚特吉的“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也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因为当时的秘鲁还几乎不存在工业无产阶级,“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意味着要在无产阶级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除了秘鲁或拉丁美洲的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之外,马里亚特吉之所以提出“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这种超常规的“浪漫主义”设想,还跟欧洲资产阶级在1914-1918年战争之后的明显没落密不可分。1914-1918年战争表明,资本主义文明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资产阶级曾经引以为豪的进步的神话已经沦落,已经为虚无主义所腐蚀而丧失了感召人的魔力。马里亚特吉在《清晨灵魂》中指出,在战后资产阶级世界里游荡的是颓废的“黄昏灵魂”(alma crepúscular)。(57)José Carlos Mariátegui,El alma matinal y otras estaciones del hombre de hoy,Lima:Empresa Editora Amauta,1950,p.178.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在1914年以前,欧洲白人资产阶级视其对有色人种的统治为自然而然、无可置疑之事,将“东方”和“野蛮”视为同义词。(58)José Carlos Mariátegui,The Heroic and Creative Meaning of Socialism:Selected Essays of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p.40.而东方人也“对欧洲社会、对资本主义文明有一种迷信式的尊重”(59)Ibid.,p.36.,因为资本主义时代确实涌现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但在1914-1918年战争中,人们看到的是,欧洲“文明”民族以史所未闻的“野蛮”彼此杀戮。此后,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天然的优越性再也不是一个无需质疑的神话。尚未在战争中完全化为灰烬的精良的机器使欧洲依然有能力施行自己的意志,但欧洲的“道德武器”已明显失效。(60)Ibid.,p.36.战后的资产阶级仿佛行尸走肉,缺乏神话、信仰、希望,但唯有神话这种伟大的存在才能使人生机勃勃地生活。马里亚特吉说:“神话引导人在历史中前行。没有神话,人的生存就没有任何历史意义。历史是由那些为一种更高的信条、一种超人的希望所占据和启明的人们所创造的。”(61)José Carlos Mariátegui,El alma matinal y otras estaciones del hombre de hoy,p.24.资产阶级的没落在缺乏神话这一点上明白无误地展现出来,在战后资产阶级世界里弥漫着没有生气的颓废感。资产阶级已经生活在黄昏之中,只能回忆自己曾经辉煌但已褪色的往昔,而无力完成新的事业。新的历史只能由那些有别于资产阶级的“新人”来创造。只有那些拥有神话、拥有“清晨灵魂”(alma matinal)(62)Ibid.,p.14.的“新人”才能开启新的时代。无产阶级正是这种拥有神话的“新人”,这个神话的名字叫做社会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正以无比坚定的意志朝着这个神话前进。(63)José Carlos Mariátegui,El alma matinal y otras estaciones del hombre de hoy,p.28.马里亚特吉直言:“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宗教的。”(64)[秘鲁]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第208页。那些批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在白日做梦,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的人无法理解这一点:“革命者的力量并不在于其科学,而在于其信仰,在于其激情,在于其意志。这是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精神性的力量。这是神话的力量……革命情绪乃是一种宗教情绪。宗教的动机已经从天上转到了地上。”(65)José Carlos Mariátegui,El alma matinal y otras estaciones del hombre de hoy,p.28.在革命神话的指引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来也不曾有过问题无法解决、前方没有出路的念头。就像初生的资产阶级曾经大踏步征服世界一样,如今的无产阶级也将创造自己的新时代。马里亚特吉所谈论的拥有“清晨灵魂”的“新人”具有浓重的道德、宗教色彩,与切·格瓦拉的“新人”异曲同工。
四、结 语
切·格瓦拉的“新人”是以高度的道德热情投入古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热爱劳动、追求技术的发展或机器的改进,最终致力于古巴和拉丁美洲的真正独立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样的“新人”可以在古巴革命时期发挥关键作用的“游击战士”那里找到基础和原型。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是对古巴社会历史现实的回应,并根植于古巴革命历程之中。此外,“新人”所具有的肯定技术或机器的解放作用这一特征可以在阿根廷社会主义思想家阿尼瓦尔·庞塞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一书中找到,而“新人”所具有的道德、宗教色彩则可以在秘鲁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中找到。可见,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渊源有自,深植于拉丁美洲现实和传统之中,决不是“无根的游魂”。切·格瓦拉的“新人”还可以回溯到墨西哥著名思想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在1925年出版的《宇宙种族》(La raza cósmica)一书中提到的“新种族”:一种将所有种族融于一身的“梅斯蒂索”(混血)种族,这个“新种族”将创造一种“新文明”,超越由萨克逊美国所代表的与种族灭绝、种族隔离相联系的旧文明。(66)José Vasconcelos,La raza cósmica,París:Agencia Mundial de Librería,1925,p.16.拉丁美洲的基本特征正是“梅斯蒂索”或种族融合,因而,“梅斯蒂索”的拉丁美洲具有超越种族主义的使命。美国及西方世界的种种迹象表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并没有成为过去,“新人”所承载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精神仍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