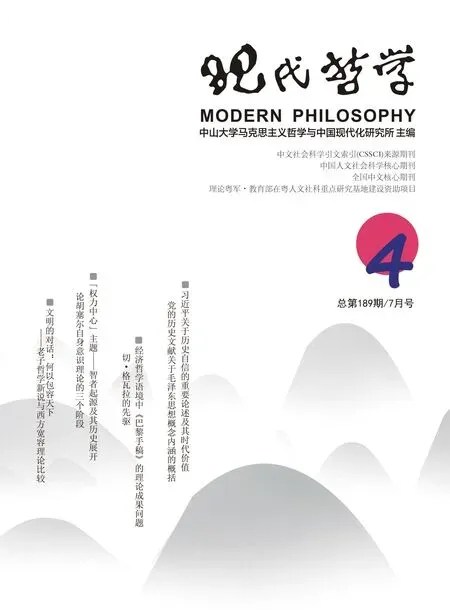天地、先祖、君师:《荀子》“礼有三本”思想新论
——兼谈“天地君亲师”问题
2023-12-20翟奎凤
翟奎凤
长期以来,我们看儒家论人的存在维度,多局限于狭隘的人伦社会关系,如常说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其中“父子、夫妇、兄弟”是家庭关系,“君臣”是政治上下级关系,“朋友”是一般性社会关系。实际上,儒家论人的存在维度是立体、多元的。与五伦相比,“天地君亲师”常被称为“五大”。明代中后期之后,“五大”的影响越来越大,与五伦一起成为儒家社会文化的重要标志性特征。“五大”的最早形态是“三大”即“父师君”。《国语·晋语》载公元前709年,曲沃武公伐翼,杀哀侯,欲胁栾成从己。栾成拒绝武公并说:“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父母是生命的给予者,教师是文明的传授者,君王是生活的保障者。这里强调了“父生”“师教”“君食”的恩情重于泰山,只有以死来报答;如果因为一些利害关系而背叛父、师、君,那就不是人。这里的顺序是父-师-君,“君”排在最后。《礼记·檀弓上》说:“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致丧三年。事君有犯而无隐,左右就养有方,服勤至死,方丧三年。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这里也是把“亲”“君”“师”并提,“君”在第二位,与《晋语》相比都是把“父、亲”置于最前。东汉《白虎通德论》说:“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师。”这是把“君”放在最前面。此“君父师”后来更通行地表述为“君亲师”,影响很大。“君亲师”为三尊,需要人们无限敬重、感恩。
《礼记·礼运》说:“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这句话也见于《孔子家语·礼运》。这里在父、师、君之外,提出天与地,并且突显了君的权威性,君可以统摄天地、亲师。《荀子·礼论》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这段话在《大戴礼记·礼三本》《史记·礼书》也有出现,只有个别字句的出入。这种表述把“天地”“先祖”“君师”看作礼的三个根本纲领,而且把君师看得很重要。五伦的人伦关系,没有“师”的位置,也没有天地维度。与此相比,“礼有三本”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有三本”,突出了“天地”和“师”的重要性,“天地”有神圣性、超越性,“师”代表着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这样,“三本”所确立的人的存在维度就是立体的,是十字打开的。荀子“礼有三本”的论述,表明儒家礼的精神贯通天、地、人,联通宗教、政治、人伦。
多数学者认为,明清时期流行的“天地君亲师”观念源自《荀子·礼论》“礼有三本”的思想。钱穆说:“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1)钱穆:《晚学盲言》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93页。目前,关于荀子“礼之三本”具体内涵的阐释还不够深入,对明中期以后“天地君亲师”观念流行的复杂情况,需要进一步深层次学理辨析。同时,我们需要对传统“天地君亲师”观念进行反思,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阐释,以与今天的时代精神相适应。
一、天地、先祖:生之本与类之本
“天地者,生之本”,《大戴礼记》作“性之本”,清代汪照说“生性古义通”(2)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上册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6页。,“性”即“生”的意思。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天地是万物生命的本源,或者说开天辟地、天地交通,万物才产生。《易传·系辞》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化万物、生生不息是天地最大的德性。《易传·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万物都是由天地交合而产生的,这实际上是把天地看成一种大父母。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说法,大概流行于战国时期。尽管早在《尚书·周书·泰誓上》就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但这篇文献是伪古文,是后起的。与之相近的表述是《庄子·外篇·达生》所说的“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荀子·礼论》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这是强调天地交合产生万物。《礼记·郊特牲》说:“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吕氏春秋·有始览》说“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天地合”即“天地合气”。《黄帝内经·至真要大论》说:“本乎天者,天之气也,本乎地者,地之气也,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论衡·自然》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天地合气,生化万物,就像夫妇交合生孩子,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观念。
《礼记·礼运》说:“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如果结合这句话来理解,那么“天地,生之本”似乎也可以指天时、地财对人的重要性。《荀子·天论》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这里以天时、地财、人治为人之生存不可或缺的三个重要方面。《礼记·礼器》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天时”应该主要是指寒暑风雨、四时节气等,“地财”主要是指土地上可以为人所用的资源。当然,“天时”与“地财”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寒暑风雨日照,地财也谈不上,《管子·牧民》就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
如果说天地是万物生命的本源,那么先祖则是人类的本源,因此说“先祖者,类之本也”。《礼记·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类似的,《孔子家语·郊问》载孔子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显然,“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与“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的意义结构是对应的。“本乎天”可以说即是“本乎天地”,广义上的天包括着地,“天地”也可省称为“天”,说“天地”重点还是在“天”。“万物本乎天”,人作为万物之一,自然也是“本乎天”的,《春秋繁露》就说“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广大无极,其德昭明,历年众多,永永无疆”(《观德》),又说“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为人者天》)。在古代,祭天有无上的神圣性,高于祭祖。《春秋繁露·郊祭》说:“《春秋》之义,国有大丧者,止宗庙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丧,废事天地之礼也。父母之丧,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废郊也,孰足以废郊者?”(3)董仲舒此说也是发挥《礼记》相关论述,如《郊特牲》说:“祭之日,王皮弁以听祭报,示民严上也。丧者不哭,不敢凶服,汜扫反道,乡为田烛。”古代帝王把每年祭祀天地作为国家重大神圣活动。《春秋繁露·顺命》说“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无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万物之祖”可以说就是“生之本”,“阴阳”相当于父母、先祖,天地是大父母。
天地在整个礼的体系中有着本源性、纲领性作用。礼本源于天地、效法天地、以天地之道为纲。对此,《礼记·乡饮酒义》说:“古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礼记·丧服四制》说:“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韩诗外传》卷5说:“礼者,则天地之体,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春秋繁露·奉本》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以德多为象。”这些都可谓是以天地为礼之本体的不同表述,一方面礼本源于天地,另一方面对天地的祭祀又是礼最重要的部分,或者说礼的重要功能就是事天地之神。《礼记·哀公问》载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荀子·礼论》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天地、先祖在排序上要先于君师,有着更重要的本源性、基础性意义。荀子还说:“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贵始;贵始,得之本也。”“天太祖”即以太祖配天,“得之本”即“德之本”,强调崇敬天、祖是德之基。
在古代,礼制等级森严。《荀子·礼论》说:“郊止乎天子,而社止于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只有天子才有权利祭祀上天。《礼记·曲礼下》说:“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天子祭天地,诸侯、大夫依次递减,而士人只能祭其先祖,而且士人与天子祭祀祖先上也有区别,天子可以祭祀七世祖先,随着爵位的递减可祭的祖先也缩小。《荀子·礼论》说:“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持手而食”即庶人,老百姓没有权利立宗庙。《孔子家语·庙制》也说“天子立七庙”“诸侯立五庙”“大夫立三庙”“士立一庙”,而“庶人无庙,四时祭于寝”,庶人只能在家里祭祖,不得单独立庙。可见,在祭天地、祭先祖问题上有着鲜明的政治等级制。
近代康有为对“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多有讨论,他说:
郊社祭天地,报生之本也;禘尝祭祖宗及所自出,报类之本也。故祭莫大于郊社禘尝……众生同生于天,则万物一体,昆虫草木皆同气也;众民同出一祖,则万民同胞,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故凡人有大族谱焉,凡天所生万物是也;有中族谱焉,凡同黄帝祖所出之人类是也;有小族谱焉,今之族姓是也。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者,小族谱也,仁之始也;仁民,中族谱也,仁之中也;爱物者,大族谱也,仁之至也。(4)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标点有改动。以下相关文献均出自此版本,不再详述。
康有为这里“大族谱”“中族谱”“小族谱”之说颇有意思,对“生之本”“类之本”的说明生动形象。同时,在他看来,“天地者,生之本”是仁的根源,“先祖者,类之本”是孝的根源。他说:“然天地者,生之本;父母者,类之本。自生之本言之,则乾父坤母,众生同胞,故孔子以仁体之;自类之本言之,则父母生养,兄弟同气,故孔子以孝弟事之。”(5)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康有为全集》笫6集,第380页。他认为,仁孝统一是孔子之教的重要特征。
二、君师者,治之本
从早期来看,最高统治者往往身兼教化功能,也就是说,君与师是合一的。《尚书·商书·泰誓上》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这段话在《孟子·梁惠王下》引作“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政教合一,最高统治者同时即是最高的老师。应该说,荀子总体上也表现出较强的君师合一的思想主张,甚至是君亲师合一;对广大民众来说,帝王是父母,也是老师。《荀子·礼论》中多段论及三年之丧的问题,并认为“君之丧”也应该三年,甚至应比三年父母之丧有过之而无不及: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以三年事之,犹未足也,直无由进之耳。
君王既是衣食父母,又在精神文化上教化大众,因此,荀子这里把君主看得比父母还重要,君既是父母,也是师,这样君亲师就是一体的。《荀子·致士》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国之隆”比“家之隆”更为重要,君主大于生父。这实际上就讲到忠孝问题,忠与孝有统一性,也有紧张性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忠与孝是统一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忠臣必孝子,对父母不孝的人很难是真正意义上的忠臣。同时,忠君,积极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建功立业,实现自身价值,也是扬名父母、孝养父母的重要途径。当然,有时忠孝不能两全,儒家也是选择舍小家、顾大家,但绝不会为了某种不正当、非正常或者被异化了的“忠君”,而抹杀、背叛孝亲之情。在儒家看来,孝亲之情是正常人格建立的基础,是为人之本。因此,荀子过于夸大隆君师、强调隆君师的权威性,虽有其一定合理性,但也有其流于刻薄寡恩之法家的危险性,从而游离儒家人之为人的基础。(6)以色列汉学家尤锐(Yuri Pines)认为,荀子的这种观点是“对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主流儒家’传统的偏离”;《论语》和《孟子》都将家庭关系摆在政治责任之上;在郭店出土的文献,比如《六德》则表达得更激进,其将为父亲服丧的重要性置于为君主服丧之上;由此看来,政治上父权也比君权更重要。对此的争论,参见彭林:《再论郭店简〈六德〉“为父绝君”及相关问题》,《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2期;魏启鹏:《释〈六德〉“为父绝君”——兼答彭林先生》,《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2期;李存山:《再说“为父绝君”》,《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以]尤锐:《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孙英刚译,王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7页。
荀子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大略》)就此而言,荀子也可以说有民本思想的因素。在荀子看来,“君”的基本功能就是“能群”。他说:“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君道》)如果说“君”的功能主要是社会管理、政治治理,让社会安定有序、人民丰衣足食,那么“师”的主要功能应该说就是人文化成、道德教化。荀子非常重视礼,说“礼者所以正身也”,而“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师是礼的规范者,这样的“师”就是“圣人”,“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修身》)。
荀子往往“师法”连用,如说“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修身》)。荀子对师法的重视也是以人性恶为前提的,如说“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荣辱》),又说“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积,非所受乎性”(《儒效》),还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
“性恶”更多是在自然人性的趋向上而言,要扭转此向恶的趋势,就必须有师法、善法因缘的外力熏染。荀子说:“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性恶》)可见,荀子并非绝然主张性恶,其论性恶一是就人性自然趋向而言,二是就众人之性而言。他没有完全排除有些人“性质美而心辩知”,即天性善良聪明,但即便这样,也需要有贤师良友的护持,需要闻见尧舜禹汤之道、忠信敬让之行,才能日进于仁义、天天向上,否则在邪恶的环境中,也会陷于罪恶。因此,荀子非常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大略》)这句话强调师傅的重要性,国家的兴衰取决于能否尊师重教。当然,荀子这里所说的“师”与“法度”密切关联,有着很强的政治性、伦理性。而在荀子最高的“师”实际上还是圣王:“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正论》)“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解蔽》)他还解释“圣王”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解蔽》)这样来看,圣王即是内圣外王,“圣”偏重人伦道德,“王”偏重创制立法。
在荀子看来,如果性善,人人都天然善良,就不需要圣王和礼义;正因为性恶,圣王与礼义的价值才得以彰显。荀子说:“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性恶》)这种意义上的圣王可以说即是君与师的统一,是大一统之明君。荀子还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妇,是之谓至乱。”(《王制》)这里作为“礼义之始”的“君子”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即是上面所说“起礼义,制法度”的“圣王”,“君子”“圣王”为人道之极,可以与天地参。“参天地”的说法在《荀子》及先秦典籍中多有出现。“与天地参”或“参天地”,一方面从德性境界上来说可谓上下与天地合流同化,另一方面从功用方面来说则表示其社会功勋可以比拟于天地生化万物,意义重大。
可以说,作为“治之本”的君师,其理想的统一形态是圣王。在没有“圣王”、君与师分离的状况下,应该说“师”是最为重要的。康有为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人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祖宗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三本孰为大?曰:师为大。人恶知天,圣师告我天而尊天;人恶知祖父,圣师告我祖父而亲祖父;人恶知君,圣师告我君而事君。生与类皆由造物,治则在人道。君之所治人道,曰礼义名分,纲纪政令,教化条理,文章正朔,衣服器械,宫室饮食事为,无一不出于师,无一不在师治之内。”(7)康有为:《圣学会后序代岑春煊作》,《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65页,标点有改动。当然,这里所说的“师”是“圣师”,是孔子之类的“至圣先师”。
三、“天地君亲师”并提与香火牌位祭祀
东汉晚期道教经典《太平经》说:“太上中古以来,人益愚,日多财,为其邪行,反自言有功于天地君父师,此即大逆不达理之人也。”(8)《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第六十三》,王明编:《太平经合校》上册卷47,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41、142页。此以“天地君父师”为五大神圣性重要存在。徐梓认为,“在《太平经》中,用的是‘天地君父师’这样一组概念。尽管它与‘天地君亲师’有微小的差异,但没有本质的区别,可以看作是‘天地君亲师’完整序列的最早出处”(9)徐梓:《“天地君亲师”源流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01页。。据刘宗周《人谱类记》载:“王文康公父训诲童蒙,必尽心力,修脯不计,每与同辈论师道曰‘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师位何等尊重。”(10)[明]刘宗周:《人谱·人谱类记五·旷馆职》,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25页。徐梓认为,这里的“王文康”是北宋王曙,“如果这一记载可信的话,则王曙父亲的说法,就是继《太平经》的‘天地君父师’之后,‘天地君亲师’的最早提出”;目前,基本可以判定“‘天地君亲师’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开来、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是在明朝中后期”。(11)徐梓:《“天地君亲师”源流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01、102页。徐梓还指出:“当然,这一说法见于明朝人的著述,有可能是刘宗周的追记,甚至有可能是用明朝末年已经通行的‘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径直表达王曙父亲的意思。”
明朝弘治丙辰(1496),刘麟在《山东按察司副使邵康山墓志铭》中说,邵康山“左图右史,检饬蠲静,屏几盘盂,悉有箴铭。操觚染翰,遇天地君亲师字,必敛容端楷,虽造次亦然”(12)[明]刘麟:《清惠集》卷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4页。。可见,明代中期“天地君亲师”在一些知识分子已具有某种特别的神圣性,但这里还只是对其持敬重之情。黄浑在《潜谷邓先生元锡行略》中说,邓元锡曾“修家祠,上则天地君亲师,左则祖,右则社,日有参,朔望有祭”(13)[明]焦竑:《国朝献征録》卷114《儒林》,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橒曼山馆刻本。,这表明此时“天地君亲师”成为一些人拜祀的对象。阳明后学杨起元说:“五常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大曰天地君亲师。师友以道合者也,尊则师,亲则友,道无形,故师友之功隐。五常、五大之有友与师也,犹五行之有土也。”(14)[明]杨起元:《证学编》卷1,明万历四十五年余永宁刻本。杨起元把“天地君亲师”称为“五大”,与“五常”人伦之道并称,认为师友以道合,如五行之土,这把师友的意义看得很高。明儒李材说:“修身为本,只有一个本,随身所接,无非末者。延平曰:‘事虽纷纭,还须我处置。’毕竟宰天宰地宰人宰物,运转枢机,皆是于我。离身之外,无别有本。虽天地君亲师亦末也。”(15)[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5册《明儒学案》(三)卷31《止修学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51页。这里强调“身”为本,家国天下实际上也是“末”。这里把“天地君亲师”看作外在于人身的重要神圣性存在,但即便如此仍是“末”。晚明高僧智旭在《周易禅解》卷1中说:“屯明君道,蒙明师道,乾坤即天地父母。合而言之,天地君亲师也。”(16)[明]蕅益智旭撰、刘俊堂点校:《周易禅解》卷1,武汉:崇文书局,2015年,第23页。可见,“天地君亲师”观念也影响到晚明佛学界。明末陈龙正在《志是而教妄》一文批评佛教时说:“我循自然,彼拗本然,天地君亲师为五大,至彼而独知有我,举五大而咸倍之。”(17)[明]陈龙正:《几亭外书》卷2,明崇祯刻本。陈龙正以“天地君亲师”“五大”为儒教区别于佛教的重要特征。明末朱舜水的《天地君亲师说》一文,全文五段文字对天、地、君、亲、师大义予以分别阐说。文章最后朱舜水还自评说:“此文虽分五段,然总是一意。中间通以孝字贯之,盖孝为百行之原也。师者立教明伦,统承天地,故第五段总包前四段在内,读者须自理会。主敬是一篇骨子,却一字不露,中间更有主意在,明者当自得之。”(18)[明]朱舜水撰、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41页。这句话强调“孝”与“敬”贯穿“五大”,而“师”又为五大之统领,突显了“师”的重要性。
“天地君亲师”观念的流行在晚明的一些小说中也有表现。如《西洋记》第14回载,张天师对万岁爷说:“天地君亲师,人生于三,事之如一。故此小臣为着家师,戴此重孝。”(19)[明]罗懋登:《西洋记》,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99页。又如《封神演义》卷3载,姬昌向纣王解释说:“臣虽至愚,上知有天,下知有地,中知有君,生身知有父母,训教知有师长。‘天、地、君、亲、师’五字,臣时刻不敢有忘,怎敢侮辱陛下,甘冒万死?”(20)[明]许仲琳:《封神演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3-74页。可见,在晚明“天地君亲师”观念已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到了清初,杨光先激烈攻击天主教与西洋历法,在《辟邪论》(1659)批评天主教“令皈其教者,必毁天地君亲师之牌位而不供奉也。不尊天地,以其无头腹手足,踏践污秽而贱之也;不尊君,以其为役使者之子而轻之也;不尊亲,以耶稣之无父也。天地君亲尚如此,又何有于师哉!此宣圣木主之所以遭其毁也。乾坤俱汨,五伦尽废”(21)[清]杨光先、陈占山校注:《不得已》卷上《辟邪论中》,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第25页。。此时,“天地君亲师”牌位供奉被视为信奉儒教的重要象征,与西方的天主教信仰存在着严重冲突。清初姚文然说:“今三尺童子莫不知天地君亲师,乃师之功德,所以与天地君亲配者,在此笔与舌而已。”(22)[清]姚文然:《姚端恪公集》外集卷10,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清初廖燕说:“宇宙有五大,师其一也。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君,四曰亲,五曰师。师配天地君而为言,则居其位者,其责任不綦重乎哉!”(23)[清]廖燕;屠友祥校注:《二十七松堂文集》卷11《续师说》,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277页。这里也是以“天地君亲师”为“五大”,所云“宇宙有五大,师其一也”有点模仿《老子》第25章所说“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廖燕也是特别强调“师”的重要性。清初魏礼对此评论说:“天地君亲师五字为里巷常谈,一经妙笔拈出,遂成千古大文至文。”(24)同上,第278页。可见,在清初“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在民间已经很流行。康熙年间石成金说:“天地君亲师,此五件,世上都该感激,都该设牌位早晚焚香叩谢。切不可懈怠,做个忘恩负义的人。”(25)[清]石成金编:《俚言》,《传家宝全集》第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第6页。感激、感恩可以理解,但早晚焚香叩谢确实有点过了。
康熙年间程汉舒在笔记中说:“今乡村人家,中堂之上,必贴‘天地君亲师’五字,不知起于何时。人要看得此五字重大,亦不至大无忌惮。”(26)[清]陈弘谋辑、苏丽娟点校:《五种遗规》卷3《训俗遗规》,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312页。中堂上贴“天地君亲师”,在民国后乃至今天一些农村仍很流行。雍正即位后对至圣先师孔子褒谕有加,“追封五代,并享烝尝”,他在上谕中说:“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人所宜重。而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自古师道无过于孔子,诚首出之圣也。”(27)赵之恒、牛耕、巴图主编:《大清十朝圣训》第12册卷32《清世宗圣训》,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1107页。徐梓认为,“‘天地君亲师’被全社会特别是士人所接受,成为风行宇内的祭祀对象,和清朝雍正皇帝《谕封孔子五代王爵》有关。雍正皇帝的上谕,主要标树的就是‘师’。正是借助这道上谕,‘师’才最终完全确立了在‘天地君亲师’这一序列中的地位。”(28)徐梓:《“天地君亲师”源流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04页。由此,“天地君亲师”观念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进一步加大。到了晚清时期,周寿昌在《天地君亲师》一文中说:“俗以天地君亲师五者合祀,比户皆然。”(29)[清]周寿昌撰、李军政标点:《天地君亲师》,《思益堂日札》卷9,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32页。乔松年说:“今俗以天地君亲师五者书于一牌,而朝拜之。”(30)[清]乔松年:《萝藦亭札记》卷7,清同治刻本。可见,在晚清拜祀天地君亲师在社会上非常普遍。影响所及,琉球等地也有此风俗。1756年,周煌同翰林院侍讲全魁受命前往琉球,册封尚穆为琉球国中山王,于次年正月回国,他在《琉球国志略》中说“贵家始有祠堂,又多以‘天地君亲师’五字供奉”(31)[清]周煌撰、陈占标校:《琉球国志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24页。。
车锡伦认为,“天地君亲师”五字排位出自明代中后期的罗教。罗教代表作《五部六册》多处说:“一报天地盖载恩,二报日月照临恩,三报皇王水土恩,四报爹娘养育恩,五报祖师传法恩。”(32)《叹世无为卷》(五部六册之一),明刻本。1596年,罗清的私淑弟子苏州和尚兰风在为《五部六册》作“评释”时将这“五恩”概括为一“颂”:“天地君亲师,行藏原不昧;古今圣贤道,动静自分明。”(33)清光绪十二年莆邑通明堂刊《开心法要·破邪显正钥匙卷》卷上之一。车先生认为,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五字牌”的最早出处,认为“它虽源渊于荀子的‘三本’说,内涵却有变化,比如‘师’便指‘祖师传法’,带有帮派的意味”(34)车锡伦:《天地君亲师牌位的出处》,《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第100页。。应该说,罗教扩大了“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位的社会影响,但到底是否为其最早出处,还很难说。前面提到邓元锡在修家祠时就立了五字牌位,这应该说早于罗教;同时期的骆问礼也开始著文批评立“天地君亲师”神位的民俗现象。
四、余 论
明代中后期乡俗拜天地、供奉天地君亲师神位现象流行,当时一些学者站在正统儒家立场对此持严厉批评态度。如曾任南京工部主事的骆问礼批评“拜天地”社会现象时说:
乡俗凡事必拜天地,亦有供天地君亲师神位者,礼殊不经。自古天子祭天地,诸侯即不得祭矣,而况于大夫士庶?……考之经传令甲,并无拜天地之文可见矣。然则士庶不礼天乎?曰:出秩刍以供郊社之祭,此其礼天地之职分也。(35)[明]骆问礼:《祭礼·拜天地》,《万一楼集》卷47,清嘉庆活字本。
骆问礼认为,祭拜天地是天子的特权,诸侯都没有资格,更何况平民,这是严重僭越,违反了礼的精神。“秩刍”指按规定数量交给官家的草料,老百姓没有资格祭拜天地,只能为君王天子祭天作些服务性工作,提供祭祀所需物品。这个看法流露出君主社会等级制对百姓的轻视,甚至可以说是蔑视。明末大儒张履祥针对当时设置家堂、以“天地君亲师”为香火之神的社会现象也作了批评:
今按家堂香火之神,名义安仿?至于天地君亲师五者,以为民生所重,则有之矣,而立一主以祀之,则无义矣……故谓此主之立,直是无义,人未之思耳。(36)[清]张履祥撰、陈祖武点校:《丧祭杂说》,《杨园先生全集》中册卷18,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32页。
与骆问礼的看法类似,张履祥也认为如是祭祀上帝、后天意义上的天地,是天子才有的特权。至于“君”,如果是说去世的先君,则皇家九庙自有祭祀;如果是当今圣上,则不应该奉为祭拜之神。至于“亲”,祠堂已有先祖祭祀。至于“先师”,如果是指孔子,则国学、府州县学、书院都有崇祀;如果是教导过自己的老师,实际上很多人在老师活着的时候与乃师感情就不深厚。骆问礼、张履祥将祭天地、祭天看作天子的特权,平民不得祭天、祭天地。与他们的观点不同,康有为认为这是据乱世的表现。在作于1904年或稍后的《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简称“国教折”)(37)唐文明认为,“国教折的写就大概在1904年或稍后……国教折最能代表康有为流亡期间的孔教思想,他在流亡期间的其他地方谈到孔教问题的,主旨基本上不出国教折”。(唐文明:《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1-152页。)中,康有为引述了《谷梁传·庄公三年》的“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并说“《论语》子路请祷于天,孟子曰:‘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然则孔、孟大义,许人人祷祀天帝矣”(38)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97页。,强调人人皆有权利祷祀上帝,专制社会帝王独享祭天权也是据乱世的表现。所引孟子这句话,1901年康有为在《孟子微》中解释说:“恶人可祀上帝,则当时民间人人皆祀上帝,可知此大地通行之礼,乃知惟天子郊禘祭天,为据乱之制。孟子传平世之学,固知人人祭天,乃平世之制也。”(39)康有为:《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88页。显然,康有为把人人可祭天、可以祷祀上帝,看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与骆问礼、张履祥相比,康有为的这一看法可以说有重要的启蒙和思想解放意义,体现了民主、平等的现代精神。
到了清代后期,“天地君亲师”崇祀现象与多种信仰杂糅,变得更加复杂。如郑珍在《遵义府志》中说:“士民家必设香火,位于中堂中,大书‘天地君亲师位’,旁列孔子、文昌、关帝、灶神各纸牌,多至十余位,少则通书一纸,旁止二小行,必承以板。有神主,即置其上。富者至为龛,镂饰种种,兼世奉释道像至三五罗列。板下,位‘长生土地’,并朝夕焚香,有祷祀,必于此。”(40)[清]郑珍、莫友芝编纂,遵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点校:《遵义府志》卷20,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第319页。针对这种现象,遵义士人李凤翧批评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冬至祀天于圆丘,夏至祀地于方泽,天地非其时不祭,非其地不祭,非其人亦不敢祭也。孔子,大圣;关公、文昌,明神,列于家庭亵地可乎?苗鬼、牛神、僧道、女尼杂于家龛俎豆之中,于理非宜,且祖宗之灵亦有所不安也。嗟乎!时俗之蔽,可以思矣!”(41)[清]郑珍、莫友芝编纂,遵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点校:《遵义府志》卷20,第319-320页。应该说,骆问礼、张履祥、李凤翧对以香火供奉“天地君亲师”的反思,站在传统儒家经学的立场来看,是有道理的。天、地、君、亲、师是为人所当敬重的五个重要存在,这合乎儒家经典,但以香火供奉祭拜,确实有些不类。天地或者天,是万物生命的本源;先祖(亲)为族类或个体生命的本源;“君”代表社会政治,可以表示人是社会性、政治性存在;“师”代表文化教育,是人类文化文明的传递者、发扬者。民国成立后,君主专制社会瓦解,一些学人主张把“天地君亲师”改为“天地国亲师”,以“国”来表示人的社会政治维度。一些现代新儒家又认为,国家是政治组织结构,不宜作为祭祀对象,应该改为“天地圣亲师”。如蔡仁厚认为,“天地是宇宙生命的本始,祖先是个体生命的本始,圣贤是文化生命的本始。这几个‘本、始’,都不可忽视,不可忘本。这是儒家教化传统最为核心的所在”(42)蔡仁厚:《孔子的生命境界——儒学的反思与开展》,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32页。其实,对于“圣”的重要性,康有为也早有强调:“非天不生,非祖不出,非圣不教;故天为生之本,祖为类之本,圣为教之本。”当然,这里所强调的“圣”包含着“师”的意义。(康有为:《三本堂落成奉安昊天上帝至圣先师祖先祭文》,《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182页。)。
近代严复基于“天地君亲师”观念对中西政教作了比较。他说:
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夫彼专为君,故所重在兵刑,而礼乐、宗教、营造、树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事,皆可放任其民,使自为之。中国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兵刑二者,不足以尽之也……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也,犹奴虏矣。为儿子、奴虏异,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43)[英]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3页,严复按语。
应该说,严复上述看法还是比较深刻犀利的。西方政治重在兵刑、重法治,政府的职权职责范围较小,很多专业的事情由社会自由发展。而过去中国帝王身兼“天地君亲师”,权利很大,有无限责任,政治、教化合一实则是一种道德的政治。
从观念上来说,由古代只有帝王才可以祭天祭地,到近代康有为强调人人可以祭天,这是思想的进步。由视天地为敬拜的对象,到以天地为性命灵魂的来源,与以身体源自父母相对,这丰富了天地与人的多元关联及其内涵的拓展。古典的“天地君亲师”观念,多是以“君”为中心、核心,有着很强的政治性。“君”统天地,兼亲师,往好方面说,这实际上就是对君王、对政治有很高的要求,这种“王政”是道德的政治性,君王既要为民父母,又要有天地神圣性,是一种圣王;而其弊端诚如严复所说,社会的一切裹挟于政治之中,民主精神与个体自由及其社会开放性难以发展。在“天地君亲师”观念后来的发展中,“师”的地位越来越凸显,朱舜水、雍正、康有为等强调五大之中“师”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观念的进步。我们今天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实际上也是强调“师”。可见,传统的“天地君亲师”观念,予以合理的解释、阐发和转化,在今天社会建构中仍可以发挥重要积极的意义。相对来说,笔者更赞成近代“天地国亲师”的说法,一些现代新儒家提出“天地圣亲师”,将“圣”予以独立强调,似无必要;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是人类文明传承者,内含着“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