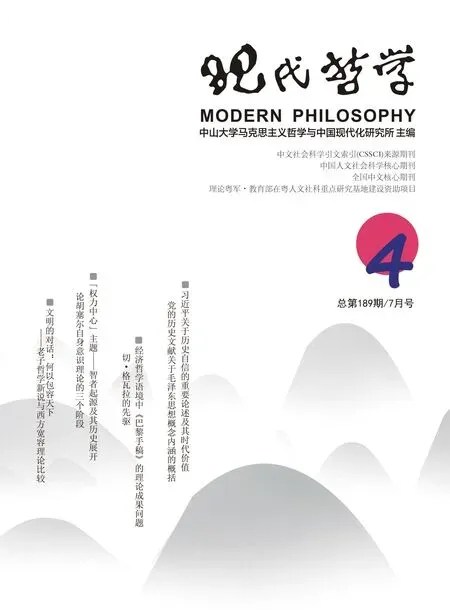恩格斯晚期的资本主义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2023-12-20斯迈尔拉佩奇凌菲霞黄文韬
[德]斯迈尔·拉佩奇/著 凌菲霞 黄文韬/译
马克思自19世纪50年代起专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恩格斯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还把资本主义经济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在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他与马克思有不同的侧重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法的关系”的内容是在现代欧洲与资本主义经济同步发展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关系”的反映。(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 页。对于原文所引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译者均已找出对应中译文。据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对资产阶级国家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也符合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还原主义解读,即法、国家和文化都只是经济的附带现象。相反,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关系,恩格斯主张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非还原主义解读。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资产阶级的法“虽然一般地依赖于生产和贸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对这两个领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它“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7页。因此,资产阶级的法不应被理解为只是直接的“经济的反映”(3)同上,第597页。。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与资产阶级国家的相互作用的分析,修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略显片面的理论,即在资产阶级国家中的“法的关系”的内容反映了“经济的关系”。
下文将分三个部分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首先,本文勾勒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详述的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对立,而恩格斯后来继续讨论了这个问题。接着,本文聚焦于恩格斯晚期著作对资本主义经济与资产阶级国家关系的分析。这里的分析也涉及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国家共同发展关系的重构,并为欧洲殖民主义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最后,本文将深入探讨恩格斯的分析在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的当代社会政治状况以及它们与中国的迫在眉睫的世界政治冲突等问题的潜力。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对立
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所有超越了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中,分工和贸易导致社会经济的对抗关系,后者固化为阶级对立。这些对抗关系会在市场经济中明确表现出来。其中的根本性对抗除了企业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抗以外,还在于商品生产者或供应者与消费者或顾客之间的利益冲突。生产者和供应者从高价中获利,消费者或买家从低价中获益。企业希望保持较低的劳动成本,而工人则希望增加他们的收入。市场经济中的这些对立关系伴随着激烈竞争:企业争夺市场份额,工人争夺工作岗位。
这种对立冲突的潜力在传统社会中仍然是隐蔽的,因为生产过程和商品交换受到阻止某些社会群体或阶层无节制地追求其经济利益的社会规范——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或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的制约。国家在维系社会阶级结构方面的作用表明,在所有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经济关系的对立至少是像暗潮般涌动着的。历史上社会弱势阶层的起义或富裕阶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使社会陷入动荡,这表明受分工制约的各阶层之间由经济驱动的冲突有可能升级。(4)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 44,Berlin:Karl Dietz Verlag Berlin,1956-2018. Bd. 3,S. 33 (以下简称MEW).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只有通过国家“干涉”,即通过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才能压制这种升级的潜力(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如果用系统理论的术语来描述,国家的管理职能在于遏制社会团体或阶层的“特殊利益”(6)同上,第537页。。国家只有把自己呈现为社会普遍利益的拥护者,并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这种与社会经济对立关系相反的表现来行动,才能有效地行使这种职能(7)MEW 3,S. 31 f.。然而,在以前所有的政府形式中,对不平等关系起到固化作用的社会规范都是在法律中实施的(8)MEW 3,S. 62.。这就证明了这样的假设:通过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所保障的制度框架,其目的在于让弱势群体无法认识和追求他们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国家被归入社会的“上层建筑”(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2页。,这意味着国家的系统职能包括遏制可被确定为隐蔽经济对立的结果的尚未解决的社会冲突。
社会和法律规范体系的历史演变体现着“人的精神的不同发展阶段”(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3 页。:从上古巫术-神话世界观到高派教会(high religion/church),再到现代性的启蒙运动。约翰·洛克示范性地提出的人权思想,对现代资产阶级宪政国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自洛克以来,“财产”权利是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核心,它一方面蕴含着解放的潜力:洛克通过赋予每个人对自己人身的所有权,推翻了奴隶制的规范性基础(11)John Locke,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4,§22-23.;他通过建立劳动财产所有权来反对封建特权。(12)Ibid.,§ 27.另一方面,洛克关于规范合法的财产必然是私有财产的主张(13)Ibid.,§ 35.为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提供了辩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摒弃这种狭隘的、资本主义的人权概念(14)MEW 4,S. 475.。
二、晚期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思想
在《反杜林论》(1878年第1版与1894年第3版)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中,恩格斯坚持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即对于最终由分工产生的社会冲突,国家至少要部分地与经济领域的对立关系相反,才能履行其作为系统的上层建筑在遏制社会冲突方面的职能(15)MEW 20,S. 167;MEW 21,S.165.。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法律在规范性上的进步——他认为是通向“真正人的道德”(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 页。的一个阶段——是出于国家在维持秩序方面的职能的具体要求,而这种职能本身是在传统社会规范受到现代侵蚀的背景下从自由市场经济中产生的。
恩格斯在遗稿残篇《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884年)与《反杜林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资产阶级工厂主与商人的利益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与想通过贸易壁垒阻碍长途贸易的封建领主以及身处行会秩序所制约的劳动力市场的传统手工业者的利益发生冲突(17)MEW 20,S. 249;MEW 21,S.392 f.。逐渐壮大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兴起的属地或民族国家的帮助下赢得了优势(18)MEW 21,S. 396.。此过程在系统功能意义上可以如此理解:行会特权和贸易关卡的取缔提高了经济效率;国家权力的集中遏制了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封建领主(和公社)之间的冲突(19)MEW 21,S. 392.。随着中世纪盛行的物物交换逐渐被淘汰(20)MEW 21,S.393.,货币被确立为——如恩格斯所称的——资本主义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 “平衡器(leveller)”(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1页。,亦即控制机制。恩格斯赋予了新兴资产阶级职业法学家在中央国家行政机构建设中的关键“反封建”作用(22)同上,第235 页。。他强调,只有通过没收封建财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才能占上风(23)MEW 21,S. 112.。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先于马克斯·韦伯提出从封建主义向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过渡的有关观点。韦伯在《政治作为天职》中表明,现代国家是如何通过“征用”地方封建的“行政权代理人”而发展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以官僚方式组织起来的“统治形式”的(24)Max Weber,Politik als Beruf,Mit einem Nachwort von Rald Dahrendorf,Stuttgart :Reclam,1992,S. 12 f;Max Weber,The Vocation Lectures:Science As A Vocation,Politics As A Vocation,ed. by David S. Owen,Tracy B. Strong,Rodney Livingstone,USA:Hackett Publishing,2004,pp. 37,38.。因此,恩格斯和韦伯认为,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及其通过高效的行政管理而实现的合理化,对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奠基性意义。
恩格斯在上述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说,国家权力一方面可与经济发展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另一方面可对经济发展产生反作用(25)MEW 37,S. 490 f.,这种观点在《反杜林论》里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的定义中得到具体展开:恩格斯所说的“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7页。。资本家对盈利的市场经济框架的典型侵犯是:通过垄断和卡特尔阻挠自由竞争,或试图通过对政治家和当局的非法干预——特别是通过腐败行为——使商业利润最大化。卢德派(Luddites,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捣毁机器运动的参加者)为反对技术革新所进行的斗争是工人的侵犯行为。他们愤怒地反对资本家使用机器并以他们为代价增加商业利润,但却迁怒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然而,如果没有后者,社会主义所追求的“自由王国”就只能是幻想:“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6 页。;自由王国只有通过技术革新来取代人类的劳动能力才有可能实现(28)Marx,Das Kapital,MEW 23,S. 452;MEW 25,S. 828.。因此,资产阶级国家必须打击卢德派的暴力行为以及企业主侵占国家资助基础设施和教育人口所需的收入的企图,否则它将面临社会无政府状态或经济崩溃的风险。因此,它必须维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普遍利益,反对相互冲突的特殊利益。
随着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在以货币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93 页。面前,个体经济活动者的发挥空间愈发缩减。股份公司在这里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自19世纪中期以来,这些公司为大规模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资金(30)MEW 20,S.259.。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最后一章中,恩格斯认为,“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1 页。。这如何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信念——即资产阶级法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保障巩固了企业主与工人间的权力悬殊状态——相协调?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必然性概念一方面意味着因果关系或系统功能意义上的决定性,另一方面蕴含着伦理要求。(32)Habermas,“Zwischen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Marxismus als Kritik”,ders. Theorie und Praxis ,Frankfurt a.M. :Suhrkamp Verlag,1971,S. 228-289,hier S. 244.如果把恩格斯的论述理解为把这些要素联系起来,就可作如下阐释:资产阶级国家只有通过民主化进程,才能在日益千篇一律的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履行其不可或缺的维持秩序的系统职能。但是,只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这种民主化就仍然是初级的,具有虚幻的性质。这意味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基本系统性危机中,人们要么再次放弃民主化进程中的所有成果,要么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继续推行政治民主化的尝试,从中作出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恩格斯并未为他的观点提供精确的论证。然而,他简短而分散的阐述却与韦伯的理论融通一致,韦伯强调,存在诸多缺陷的资产阶级国家有一种民主化的趋势。(33)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5,Hrsg. von Johannes Winckelmann,Tübingen:Mohr Verlag,1972 (以下简称WuG),S. 567 f.韦伯把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张”和国家权力的“官僚化”称为现代性的“两大合理化力量”(34)WuG,S. 419.。恩格斯已经表明了它们之间互为条件的关系,其中经济基础居于更根本的地位。韦伯则区分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35)Max Weber,Soziologische Grundbegriffe,ders.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Hrsg. von Johannes Winckelmann,Tübingen:Mohr Verlag,1982,S. 541-581,hier S. 565 f.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行为,是指行动者总是追求“自我的目的”。(36)Ibid.,S. 565.相对地,在价值理性行为里,“信念”是以“特定的自我关系本身的无条件内在价值为指导并不计得失的”。(37)Ibid.,S. 565.然而,在现代自由主义宪政国家中,工具理性成为了价值理性的建构性要素 。经济关系逐渐转变为典型参与者追求自身利益的市场关系,这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它是一个工具性意义上的合理化过程。在现代中央集权国家中,由于官僚化程度的提高,统治者愈发具有非人格化特征(38)WuG,S. 124.。这使得国家决策的合法性(legality),也就是形式上的正确性,成为其正当性(legitimacy)——亦即社会接受度要求的核心。自由主义宪政国家给予公民自主追求生活目标的权利。国家只要求他们尊重他人的自由。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只要是在合法的框架内都是被允许的。自由宪政国家的指导性价值理性标准是保证每个公民都有设定自己目标的自由,而且这些目标必须能兼容他人的行动自由。(39)WuG,S. 419,496 ff.在这个意义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资产阶级法律中是捆绑在一起的。恩格斯在上述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强调,资产阶级的法“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但它也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7 页。。因此,资产阶级的法必须以一种一致性的方式捍卫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系统利益,反对彼此对立的特殊利益。韦伯认为,规范的一致性作为价值理性的世界历史性进步的核心标准,其重要性日益增长。它在现代通过传统宗教标准的丧失而得到推进,并在资产阶级的法的“形式性质”之中得到彰显(41)WuG,S. 505.,构成了国家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框架。由于资产阶级的法至少在形式上赋予了每个公民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权以及——尽管是最基本的——自决自由,规范一致性的要求迫使资产阶级国家也要通过社会保障或亲属提供照顾的法律义务、慈善组织的税务减免等途径在经济上保障公民的生命。
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允许资本所有者不顾工人的生命权益而实现其利润最大化。恩格斯和韦伯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分析可解释的是,为什么在19世纪一系列法律得以制定,从而限制工厂的工作时间,减少童工,以及改善工作场所的保护措施并为人们提供医疗保健等。
如果资产阶级国家要有效地完成它的系统性任务,其行政部门就必须具备所需的专业知识。因此,国家行政部门必须向那些已经获得必要专业知识的人开放。国家官僚机构因而被纳入了原则上人人都能参与的劳动力市场。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化,一方面是由于它在履行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保障的系统职能时需要有资质的职业官员,这使得“经济和社会差距对承担行政岗位的影响”部分地均等化(42)WuG,S. 567.;另一方面是由于资产阶级法律的规范性框架。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化进程产生于现代性的“两大合理化力量”——即韦伯所说的“市场扩张”和国家权力的“官僚化”——之间的互动(43)WuG,S. 419.。
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缺陷,恩格斯与韦伯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解释。马克思与恩格斯强调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特性。由于企业可在经济繁荣期通过购置机器压低薪资水平,在经济萧条期则基于萎缩的劳动力需求压低薪资水平,因此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就已经包含了资本的累积。而资本的累积又为投资提供了条件。保障这些资金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为系统职能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任务之一(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95页。。资产阶级国家既要保障国民经济的有效运作,又要优先照顾资本家,这一事实符合恩格斯关于国家两面性的总体描述,即国家作为一种似乎 “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它应该“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而由此却同时在政治上固化了经济上的权力悬殊状态(46)MEW 21,S. 165.。
虽然韦伯本人也指出,资本的经济权力最终体现在政治权力中,但与恩格斯不同的是,他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民主化进程最大的阻碍在于“得到充分发展的官僚制的权力地位”,而不在于其阶级特性(47)WuG,S. 572,vgl. S.568.。每一个局外人在面对“在行政管理运作中训练有素的官员”时,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业余者”的位置,这样的局外人可能是议员、政党领袖,甚至是君主或贵族,更可能是 “人民”,因为他们是在行政管理领域外部的(48)WuG,S. 568.。由于国家行政管理要避免其维持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职能受损,就必须维护社会系统的利益,因此它必须抵制无能的或是党派的政治指令和干预措施。由此衍生的杜绝一切外部影响的趋势,有可能使民众的民主主权陷入瘫痪。然而,根据韦伯的观点,“尽量减少‘职业官员’的行政统治”并尽可能支持“人民(demos)”或者说 “公众意见”的直接统治这一基本民主要求是一把双刃剑:它相当于“现任党派领袖”的统治(49)WuG,S. 568.。韦伯对人民直接控制国家行政管理持有保留意见,这是由于他的核心观点,即政治的本质是斗争。在民主决策中,这种观点可以从一般利益服从于特殊利益的两种方式中体现出来:少数群体陷入不利地位;政治领袖或利益集团对多数人意愿进行操纵性引导,这些操纵者为满足自身的短期利益而不惜牺牲长远的共同利益。为了使议会对韦伯所要求的国家行政管理的控制能够增强公共福祉(50)WuG,S. 854.,需要政治活动家以 “伦理上负责的方式”进行这种不可避免的思想与利益的斗争。一方面,他们须与属于“终极目的的伦理”——韦伯认为耶稣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均属其典型代表——的虚幻理想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被政治商业的侍从主义体制和民粹主义蛊惑人心的成功前景所腐蚀。(51)Weber,Politik als Beruf,S. 67-73,cf. S. 31,38.韦伯在题为《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里的指导思想是,这种政治家至今实属罕见。
韦伯将政治与国家行政管理理解为两种对立的基本趋势与恩格斯对于国家的理解有颇多相似之处。韦伯认为,公务员“不应从事政治,而是要首先不带偏袒地[……]行‘管理’ 之职,且他恰恰不应做政客、领袖及其追随者一贯必做的事情:斗争”(52)WuG,S. 833.。相似地,恩格斯也将基于国家对暴力的垄断的“政治统治”与属于国家行政管理的“社会职能”对照起来(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86页。。后者须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1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阶级结构通过政治统治得以巩固。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在现代西方社会内部结构方面不如韦伯详尽,但它的适用范围更广,因为它包括了韦伯的理论所缺少的关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解释框架。(55)Engels,“Vorwort zur zweiten Auflage von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 (1892),MEW 22,S. 276.恩格斯认为殖民扩张的主要动力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为维持其稳定性,需要“增长和扩大”。(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5页。只要资本主义生产一直繁荣,企业与工人的利益冲突就可得到缓和,由经济困境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就能避免。不断扩大的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工人可根据供求规律提出加薪的要求。由此他们的消费可能性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大,而这反过来又有利于生产者和供应者。相反,当经济处于停滞或衰退期时,社会会由于失业增多以及广大民众的贫困化而变得不稳定。西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通过如下方式保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即以牺牲被征服的国家的手工业为代价,在当地为其工业产品创造输出市场,同时为西方工业提供廉价原材料。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下,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和国家领导人对经济增长受阻导致的不稳定结果的恐惧,彼此结合到了一起。
马克思和恩格斯跟后来的韦伯一样(57)Weber,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ders.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Bd. 1,Tübingen:Mohr Verlag,1963,S. 17-206,hier S. 37.,都相信,资本主义增长迟早会碰触到不可逾越的边界。恩格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作为“资本主义的机器”“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从而将“资本关系……推到了顶点”(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06页。。据恩格斯的观点,日益失灵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国家本应作为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却实际上为资本效命——之间对立的消失,从长久来看,会导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落。恩格斯断言,资本关系会在具有系统威胁性的增长危机中被推到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59)同上,第407页。恩格斯在这种辩证的转折中看到了两种可能性。他担心的是,在全球市场内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力量会引爆世界大战,以转嫁国内社会矛盾。(60)Engels,“Kann Europa abrüsten?” (1893),MEW 22,S. 371,373.他对这种战争结果的预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证实:“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00 页。他认为避免世界大战的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三、恩格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和韦伯的预言,即资本主义增长迟早会碰触无法逾越的边界,在过去几十年里成为了现实。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受到此前经年的“滞胀”危机——即在经济发展停滞的同时伴随着高通胀——的触动,西方经济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政策缩减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这确实缓解了通货膨胀,但也加剧了西方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新自由主义,即便是在社会福利被缩减的情况下,也试图通过刺激消费重新激活经济增长。由于产能转移至低工资国家,包括中国,消费品价格得到降低;同时信贷政策得以放宽。但西方国家却不能通过这种方式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从增长率来看,以大幅差距高居榜首的是金融产业,而其肆意的商业行为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62)Vgl. Joris Steg,Krisen des Kapitalismus. Eine historisch-soziologische Analyse,Frankfurt/New York:Campus Verlag,2019,S. 372 f.比尔·克林顿时期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拉里·萨摩斯 (Larry Summers)断言,西方国家2015年会出现一次“长期的经济停滞”。(63)Cf. Wolfgang Streeck,How Will Capitalism End?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London/New York:Verso,2016,p. 66 f.
恩格斯的断言,即面临资本主义最终的增长危机时国家会作为“资本主义的机器”“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当代西方国家。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为将全球金融体系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资本主义国家以纳税人利益为代价对银行和大企业施行了数十亿美元的救助方案。由此可见,正如科林·科鲁奇 (Colin Crouch)在《让资本主义适应社会 》一书中所强调的,当代资本主义靠“国家牺牲公共利益来将其从自身的矛盾中拯救出来”。当自由市场无力提供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所需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时,当代的资本主义就会显示出根本的矛盾性。(64)Colin Crouch,Making Capitalism Fit for Society,New York:Polity,2013,p. viii.那么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由市场实质上已经被国家代理人和企业代表之间的“交易”大为限制。(65)Ibid.,p. 9.按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的国家服务的私有化过程,使接管这些服务的企业占据了政治垄断地位并能由此对政治施加影响。科鲁奇强调,据此国家把自身打造成了一家企业。(66)Colin Crouch,Making Capitalism Fit for Society, p. 71.这也接近恩格斯的主张,即国家在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遇到系统性危机时会作为“总资本家”而介入。但此处还需注意两者强调的重点不同:恩格斯的理论是国家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而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管控的核心是金融领域。
恩格斯的担忧,即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领导阶层在经济增长陷入困境时会以发动世界大战的方式来转嫁国内社会矛盾,为我们解释当下西方与中国的世界政治对峙提供了启迪。北约组织以这一目标——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世界范围内保护民主和人权”——来论证其从北大西洋防御联盟向全球性干预力量之转变的合理性。(67)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l去年北约的“战略构想”指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逐渐加深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它们彼此强化的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企图,与我们的价值与利益背道而驰。”但西方国家自身也同样在破坏其声称要维护的人权和国际法准则。此处列举一些正在发生的实例。美国仍旧拒绝国际刑事法院就美国军队所犯战争罪的调查。2022年2月总统拜登征缴了阿富汗中央银行35亿美元境外资产,分发给911事件中的美籍受害者,而大部分阿富汗人民正在忍受饥饿。(68)https://www.faz.net/aktuell/politik/biden-beschlagnahmt-afghanische-Auslandsguthaben-bei-der-fed-17799255.html2022年9月,德国政府准许向沙特阿拉伯出口武器,而沙特阿拉伯军队正在也门犯下战争罪。(69)关于德国的武器出口,请参见https://www.tagesschau.de/investigativ/monitor/ruestungsexporte-saudi-arabien-jemen-101.html 人权观察和联合国也门问题知名国际和地区专家小组记录了沙特空军对也门平民的轰炸,参见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22/country-chapters/saudi-arabia,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GEE-Yemen/2020-09-09-report.pdf
北约组织以维护全世界的人权和国际法的目标来掩盖其作为全球干预力量的真实动机。这些动机是什么,也不难发现。在过去几十年由新自由主义引领的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重心已经发生转移。产能向低工资水平国家的迁移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建立为迄今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其经济增长率远超西方国家。这削弱了西方通过殖民主义获得的全球经济实力。西方国家将中国在经济和国际政治上的崛起视作威胁,因为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会激化其内部的社会冲突并将之升级为暴力冲突。若言此说为耸人听闻,请见2021年1月特朗普支持者所造成的国会山骚乱事件。
北约组织试图以其新的角色定位来从军事上挽回西方所丧失掉的新殖民主义全球霸权。其注定失败的结局,可从西方权力在中东、中亚和南亚以及法属非洲的衰落中清楚见得。当下西方媒体对政客及军事长官的“与中国之战迫在眉睫”言论的轻率报道,与一战前欧洲政治的肆意妄为相差无几。德国发行量最大的严肃报纸——《南德日报》竟在2023年3月9日写道:“澳大利亚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第7页),仿佛战争如斯乃世界上一平常事件而已。
恩格斯认为,阻止正在上演的世界大战这一毁灭性危机的唯一机会,就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从而超越资本主义。我认为我们当下再次面临此情境,只有通过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带来持久的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