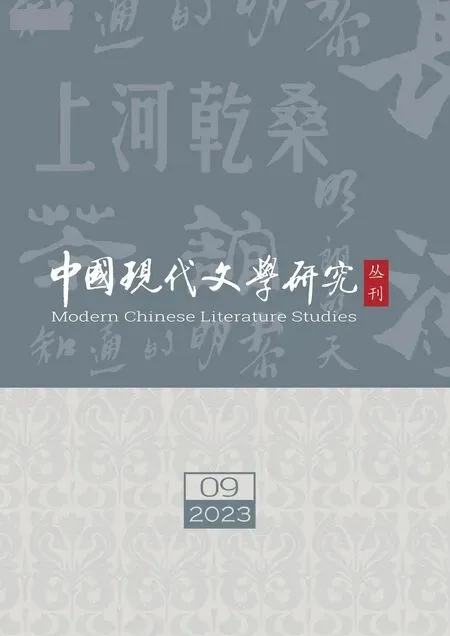论贾平凹《山本》的“民族志”书写※
2023-12-20张博实
张博实
内容提要:贾平凹在《废都》《怀念狼》《秦腔》《老生》《山本》等文本里,对人事、事物、历史、文化的深入勘察和呈现,拓展了文学表现的诗性空间和审美维度。贾平凹对自然的敬畏,对俗世生活的深透理解,使他在处理人与历史、人与现实、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终极性思考时,生成大量超越理性的直觉经验和精神幻象,形象地传达对存在、自然、生命的领悟和理解,在更加广阔的视域呈现历史和人性。本文主要剖析贾平凹的《山本》,厘清上述复杂元素的“关系与结构”,探究诸多的可能性在“民族志”书写中的萦绕与再现。
一
贾平凹在长篇小说《山本》的后记里,表达了对文本叙事方式的深切思索,和进入历史、人性及存在世界进行探掘的写作诉求:“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和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了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1贾平凹:《〈山本〉后记》,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26页。贾平凹始终重视写作与现实、历史、人性、存在的内在关系与表现深度。贾平凹仿佛意欲写出一部秦岭的“世说新语”,提供一部有关这个世界的生命哲学。自然和大历史如何才能真正进入一个作家的内心?如何建立独特的艺术审美维度和深度?如何能使写作智慧灌注于文本的灵魂?这些“形而上”与“形而下”交织的问题,始终缠绕并构成他持续叙述的动力或写作发生学。
贾平凹面对现实和历史的谦卑态度,对一切事物怀有敬畏之心,使得他的小说气象和格局,渐渐呈现出大江大河般的雄浑与开阔。一方面,他凭借自身的勤奋、天赋和才情,展现文本张力;另一方面,他多年来对“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的整体美学追求,也使他最大限度地在复杂的语境中,悉心地调整对经验世界的感悟和感知,呈现历史、自然和生命之韵味。贾平凹在《山本》后记中提及的“铜镜”“地藏菩萨”,既是文本中时时影响人物、富于“神示”的“器物”,也是作家进入存在世界的想象通道。“胭脂地”墓穴中出土的铜镜是曾照耀过另一时空的“器物”,井宗秀将其转赠到陆菊人手上,既有“轮回”“自慎”的意味,又像信物喻指两者之间的神遇。在“符号学”意义上,它或许已经“涨溢”出所谓“理性”和“逻辑”的统摄边界,指示着某种超出“客观”之外的神秘存在。当人与事都携带了“不确定性”“不可控”因素,在理性与非理性双重视域下的想象、虚构和写实之间,故事、情节、人物、意象充溢着传奇、模糊的特性。贾平凹的洞见能力,能够同中见异、“无中生有”,呈现世界的“原生态”样貌,并以一种接近“民族志”叙述的路径探掘世间的奥秘。
贾平凹在审美思维和叙事逻辑上,不仅对事物本然万象的虚幻感进行剥离,还试图揭示艺术表现的“铜镜”所折射出的精神、灵魂的“山海经”。他将写作的形态,比附为一只手表背面的通透和“暴露”,完全在于作家要透析时间的本性和自己写作的初衷,思考和探索究竟什么样的意志力能找到引导写作主体的原动力,最终能够清明舒朗,直抒胸臆。“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1贾平凹:《〈山本〉后记》,第526页。无论是“铜镜”“郎中”,还是“地藏菩萨”,都表明贾平凹多年来对写作神性,对“文运”的敬畏和重视,以及揭开世间深层存在之谜的灵魂诉求。这些理念或念想,决定贾平凹写作的“不变肉身”。而那裸露的“转动的齿轮”,则驱动叙述形态,延续写作惯性,凸显出作家的生命意识和强烈的存在感。作品中的诸多“物象”,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关于自然和人生的隐秘经验,而且由这些经验所渗透出来的人与事之间,都是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对冲”,成为对世界进行诗学描绘与把握的重要层面。更主要的是,贾平凹对事物神秘性的呈现,极大拓展了文学表现的诗性审美维度。正因作家对自然的敬畏和体悟,对俗世生活的深透理解,使他在思考与表达人与历史、人与现实、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时,生成大量超越理性的直觉经验和精神幻象,能够自由地在文本里阐幽抉微,在对存在的细部修辞中,获得对事物深入的体察和领悟。贾平凹在《商州》《怀念狼》《秦腔》《古炉》《老生》《山本》等系列文本中,再现了神秘学—心理学—历史学交互作用下所展现的独特、复杂情境。
1990年代初,胡河清在《贾平凹论》中曾从神秘学的视角,解析和阐释了贾平凹写作的叙事价值和意义,以及文本所隐含的文化底蕴。他还将贾平凹的写作美学,归结为“表现了一种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深度模式和东方神秘主义传统参炼成一体的尝试”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51~52、197页。。胡河清在《中国全息现实主义的诞生》一文中,还特别强调从1985年以来,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取向发生了一次具有史诗性意义的伟大迁移。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学艺术始终处于一种高度统一的文化规范之中,不能形成独特个性的话语系统。3胡河清:《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51~52、197页。新的写作话语范式的建立,必然要涉及叙事背后的观念调整和变化;同时,也关乎作家写作的自我意识、地域性和文化心理的构成。这些,亦可视为贾平凹写作可能产生神秘性的重要因素。
从《废都》《怀念狼》,到《秦腔》《古炉》《老生》,贾平凹的叙事策略越发渗透着神秘主义内涵,及至《山本》,可谓是“登峰造极”。仔细考量《秦腔》《山本》等与神秘主义诗学的关系,可能会让我们体悟到更深远的文化视角,并展现出文学叙述中现代民族志学的精髓。对存在、人性的发掘,对历史进程中魔幻性、纯粹性、民间性的叙写和反思,对自然、人事中模糊状态的呈示,以及对与其相关联的俗世文化密码的美学破译,弥散出贾平凹《山本》神秘诗学的深厚意蕴。20世纪以来,一些作家乐于书写“大历史、小人物”,贾平凹更在意揭示俗世间的“神性”“不可知性”。他注重“大历史”如何进入作家内心,进而表现人类情感复杂的向度。这恰恰是重现民族深层记忆,重新与历史对话的精神自觉。贾平凹对当代小说创作的新探索愈臻成熟,不仅完成了其个人文学个性风格的升华,也实现了审美层次、审美价值及意义的不断拓展。
贾平凹的写作提供了文化背景下的民族独特存在形态与变革的历史情境。张学昕曾提出贾平凹“世纪写作”的命意:从早期的《商州》《浮躁》,到《秦腔》《古炉》《老生》《山本》的历史叙事时间恰好是一个世纪。1张学昕:《“原来如此等老生”——贾平凹的“世纪写作”》,《当代文坛》2017年第4期。贾平凹逆着时间的河流追溯而上,检视近百年中国大历史的流变。这些叙事或“故事”,不仅呈现出中国的历史“脉象”在现当代政治、军事、经济等因素以及文化背景下的革命性驿动,还繁衍出中国北方的人文历史、自然地理的复杂面貌,构成“北方写作”的滥觞。从某种程度上说,贾平凹的写作源于文学传统中的“北方文风”的底蕴及其文化积淀。“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2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封底”。秦岭在贾平凹的叙事中被赋予了人文坐标值。《废都》《秦腔》《山本》等重要文本,全方位地打开了贾平凹的审美视域,令其寻觅到新的叙事方位和姿态,而审美倾向上的“位移”,更显示出作家的造诣。
二
在《山本》里,每一个人的存在方式、选择的路径,都仿佛“命中注定”“顺其自然”。尤其是生死问题,成为每一个人不可逾越的鸿沟。小说里每一个有名字的人物,似乎都与死亡紧密地连在一起。他们的死法也是千奇百怪。在秦岭,聚积着各派力量,刺激出大量博弈,人谋与天意,偶然和必然,隐藏在人性、事物和自然的关系或结构中,呈现着莫名而费解的冲突。
《山本》注重呈现人的命运的“无意识状态”。“陆菊人怎么能想得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带来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涡镇的世事全变了。”这句全书的“起始句”,给这部小说奠定了基调。井宗秀在父亲离世后,为寻找父亲五百块大洋埋藏地点而苦恼。他在昏睡中听到梦境里的声音,提示他“我到齐门生家去”。井宗秀没有直接找到五百块大洋,但辗转被“引至”陆菊人临产的杨掌柜家。“骑着门槛生”的谐音,令井宗秀意识到此事与杨家的关联。果然,杨掌柜在自家得子的大喜之日,应允将那三分“胭脂地”给予井宗秀尚未安葬的老父。日后井宗秀竟然在挖掘墓坑时发现了一座古墓,墓里随葬的古董卖出一千八百块大洋。从此,井宗秀开始慢慢地发展自己的生意,壮大自己的势力。这块早年被十二岁的陆菊人发现必将“出大官人”的胭脂地,引发出传奇性的“天意”,也成为小说叙事线索以及“延展”故事情节的结构性“龙脉”。井宗秀与陆菊人之间微妙的情感关系,构成整部作品叙述的“龙骨”,两者没有儿女情长,唯有灵魂之“神遇”。井宗秀事业的风生水起,都与陆菊人对他默默的“祈盼”息息相关。麻县长偶然处理卷宗的笔起笔落之间,井宗秀的人生、涡镇的命运就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偶然性”的机变导致的人物命运之意外与逆转,在《山本》中比比皆是。
《山本》时常有意制造许多令人感到颇为吊诡的事象,从而彰显出存在的神秘性。井宗秀陆续返还父亲欠下乡里人的互济金时,白起找到井宗秀,说他也交给互济会三个大洋,只是收据丢了。井宗秀虽然有些怀疑,但还是付了。结果白起夫妇双双“鬼魂附体”,让白起将赖去的三块大洋还给井宗秀。贾平凹将大量诸如此类的怪事逸闻写进小说,不仅增加了叙事的传奇性和魔幻性,还为人物形象蒙上神秘色彩,透露存在世界的不可知性和隐秘性。这也是理性、非理性世界杂糅的表现。整个文本书写出社会历史动荡情境下,碎片式的、“不觉悟”的个人命运,和20世纪中国历史的极度复杂性和“萌生性”。《山本》里有名有姓的死亡者大约有100人,死法各异,却几乎都是瞬时毙命,事先则少有征兆。不知“死”,焉知“生”?究竟都有哪些事关存在隐秘性的元素和“变数”,可以悄然地改变人事、命运的惘然和茫然,构成撬动人事、自然发生“机变”的隐性法则?
贾平凹写北方“秦岭志”,要写出某种神秘性的力量,赋予民族历史以隐喻和象征,比附于国情、世情和人情,甚至“集体无意识”的存在。贾平凹写北方,骨子里是想写尽有形之态,想“实中悟空”。这种“空”并非一无所有,它是所有的有形实体的基础,一切生命之源泉。因此,我们会在这些文字里,感受到一个庞大的、无形的精神气场。
三
格非曾提出《金瓶梅》中“超级叙事者”的问题:“这正是历代批评者所津津乐道的那个‘佛心’或‘佛眼’。在《金瓶梅》中,一方面,作者通过直接的议论或通过叙事代言人来描述并评价人物的言行;另一方面,作者也借助于这个‘超级叙事者’,通过高高在上的佛或者仙的眼光,来打量尘世中的一切,并建立起最终的价值判断。由于这个‘超级叙事者’的存在,居于‘众生’地位的人,其所作所为是善还是恶,都变成了过眼烟云。”1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148页。《金瓶梅》《山本》都选择通过“佛的眼光”来审视存在世界,无疑可以为呈现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隐秘关系构筑起更开放的通道。作家对存在本身展开终极性的探寻,文本所呈现的情境和引申义,势必获得智慧、超越世俗性认识的最大值。这种“超越性”视角为《山本》的叙述打开了新的审美视域,使文本呈现出全新的可能性。贾平凹的《山本》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它构成了《山本》的叙事美学和神秘美学,也构成对人的理性作出深切感性体悟的一个新的面向。
《山本》写出了浩瀚时间之流、生活之流、生命之流,它是一部秦岭的人物志,也是秦岭的草木志、动物志,或者说,就是一部当代版的“山海经”。有论者指出,“从《山本》与《老生》及各后记的对照与分析中,可以清晰感应到两部长篇小说确然存在某种内在关联”2马杰、李继凯:《贾平凹长篇小说副文本研究——以〈山本〉为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在很大程度上,《老生》是《山本》的重要“前奏”或“纲要”,是贾平凹写作《山本》之前的一次自我整理。这种“整理”,是贾平凹打破以往叙事惯性,沉浸事物本身和内里,进行对类似“宇宙之心”所做的深入探寻。贾平凹写作的“另一层”向度,正由此而生。
与其说《山本》的独特性、重要性来自叙述视角和策略,不如说源于贾平凹新的叙事哲学的生成,这与神秘主义诗学息息相关。“好和坏,快乐与痛苦,生和死都不是属于不同类的绝对经验,而是同一实在的两个方面,是同一整体的两个极端。所有对立面都是两极的、也就是统一的。这种认识是东方宗教传统中人们的最高目标。”1转引自灌耕编:《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山本》仿佛憋足“一口气”要穷极“世相”的本色状态及其神秘幽径,所以,当事物越发呈现出复杂性时,作家就可能对文本的形态更加追求简洁的风范。
《山本》的叙事浑然一体,“形散神不散”。整部《山本》50余万字,不分章节,渐次演进,看似随心所欲,但是脉络清晰分明,其中有重要的逻辑引线。在《山本》中,几乎所有的对立面,都是相互对峙的。但又并非都是两极的:亮和暗,胜和败,好和坏,呈现出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这种观念,是东方生活、存在方式的基本原理。所有的对立面都是相互依赖、融为一体的,它们的冲突很难会以一方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国民党部队、军阀、游击队和土匪,镇上的“大户人家”,以及涡镇的一切生灵,内在的纠葛和冲突此起彼伏,不一而足。他们都在各自存在伦理的牵引之下,演绎出祸福无常的存在寓言,探寻正义的逻辑。
四
“山本”是一个具有象征、寓言或隐喻的能指符号。它在叙述的时空坐标、文本题旨、历史脉络、人事风华等层面,追求摇曳生姿、涵摄深远的美学形态,亦“有意追求史诗风格”2季进:《刹那的众生相——贾平凹〈暂坐〉读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虽然近年来贾平凹的文本叙事始终在做“删繁就简”的形式减法,但他在坚持整体叙事格局的开放性气势方面,更加专注于细部修辞的力量。贾平凹在叙事层面上“去伪存真”,越写越自然,越写越放松,历史、现实中的人性、自然,都呈现出一种“超然”、旷野式的“裸露状态”。
《山本》中最凸显贾平凹叙事功力的,是他对于小说叙事结构的整体性把握,以及虚构力对叙事策略和文本结构的巨大影响。他的叙事在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叙事革命。程德培阐述了作家讲故事的方法的重要性和革命性:“虚构作品总是离不开模式与范式的:有头有尾,虚假的暂存性,虚假的因果性,貌似确凿的描写,脉络清楚的线索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小说无法摆脱的东西。”1程德培:《捆绑之后——〈黄雀记〉及阐释中的苏童》,《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贾平凹的《山本》,就是虚构对范式的彻底性消解。贾平凹小说写作内在的、本质性的新变,就是叙事上深度的“反既定性”与反“模式化”,即以写实的方式,实现叙事的虚构价值。在“《秦腔》时代”,贾平凹已经在叙事策略上作出重大的调整。相对于那些结构宏阔的乡土叙事,贾平凹选择单向度的线性叙事结构,采取自然时间节律,不刻意地拟设人物、情节和故事之间复杂、交叉递进的逻辑关系。他并不是夸大生活细节后的历史发展的“逻辑”,而是追求朴素的“原生态”叙事。其叙述本身,也不对乡村社会及其复杂状貌作任何主体性推测或理性评判,而是以貌似琐碎的细部场景或乡土生活形态,构成平淡或庸常的生活实存,复现生活的肌理。
生活本身都是不完整的、破碎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文学叙事对价值、意义的寻找,以及对历史或现实的诗学呈现,最重要的是需要既“空灵”又“落地”,即在结实的物理空间,积压出醇厚的、“贴地”的灵魂能量。只有在创作理念上,摆脱陈腐的、惯性化的小说叙事结构的预设性,放弃以往固化的“社会—历史”文本结构形态,并且深入反思对人物个性、所谓“典型性”的过分强调,才能避免人物与存在世界的割裂。《秦腔》《古炉》《山本》中,贾平凹的叙事逐渐开始“淡化故事”,“轻叙事逻辑”,这是对既往文学、写作理念的重新思索。唯此,生活本身以及存在世界的神秘性,才能摆脱“中规中矩”的结构方式,自然地在叙述中彰显出来。贾平凹崇尚《易经》中的“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他从存在世界的“群形”中获得文本的结构、形式,将这种“透视性”视角,引向对“众生”的观照,作家所体验到的所有事物、人和事件,都被纳入“别样”的基本统一体内。其中事物和人的个性,它们的差别、对立、冲突、间离,都相对地存在于包罗万象的大格局之中。文学所要做的事情,究竟是记录、下载,还是复原、重现、重构,是作家写作中无法回避的叙述伦理。只要触及其一,势必关涉想象力、叙事逻辑和诗学。叙事若想超越历史或存在世界的所谓“玄表”,何其难哉,而“全知视角”的“佛性”品质,让叙述尽可能地接近了事物的“原生态”。
《山本》里几乎没有太多的“主观时间”。在这样的文本境遇之下,对人物、事物的臧否,对人性的探赜索隐,就很少受到进行自我反省层面的影响和干预。而对人性、事物究竟应该持有“超脱”姿态,还是“理解”“包容”的叙事伦理,则属于文化本质上的差异和分歧。前者意味着超越自我的道德选择,它与东方传统存有内在的关联,它将人性的善恶美丑都统统置于自然的、客观的观照范畴。《山本》中,作家以那种几乎接近“零度叙述”的情感温度和极度沉静的“内气”,抑制住自身的生命感性,对观照对象作出“原生态”的叙事选择。较少主观性的渗透,情感质量看上去也很微弱,也会造就神秘主义“出没”的间隙和空间。“裸露”式角度的观照和写法,对生死的沉静态度,对俗世人生浓厚的感悟力,还有“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秦岭的山川河壑大起大落,“秦岭深似海”“路瘦蛇蝎乱,潭黑鬼声骇”1贾平凹:《山本》,“勒口诗句和后记”。,无不构成神秘主义浓厚的氛围和区域。对于井宗丞、井宗秀两兄弟不同的人生选择,贾平凹没有表现出“挖掘”任何意义层面的诉求,而是让他们在“秦岭深似海”的命运沼泽里,大起大落,“水随天去”。或正如孙郁所言,这就是“贾平凹的‘道行’”2孙郁:《贾平凹的道行》,《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破译“神秘性”,是读懂贾平凹小说的关键。死亡的随意性、偶然性,牵扯出人物命运的多舛和“莫测”。作家的职责就是要描述出那些尚处于幽暗之中,尚未被理性的辉光所辐射的事物和角落,发掘某种事物存在或表现的可能性。这是贾平凹超越个人经验的有限性,竭力抵达浩瀚无际的存在本身,衔接事物与事物之间断裂性的词语历程和张力性之创造,是现代与传统、现代与古典的朴素对话。贾平凹的神秘诗学,是有质感的,是有强大生活经验支撑的,是从生活中自然生长出来的。
五
表面上看,贾平凹叙事的神秘美学指向,是让个体似乎都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不自觉地应对着混乱不堪的世界。可他们无论是什么身份,作出哪种选择,冥冥之中都有不尽的撕扯和纠葛,而且直接关乎“地藏菩萨”与人、自然、灵界的种种神秘关系。贾平凹对世界、对存在等事物,进行文化上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探索,可以让我们竭力去捕捉曾被“幽灵化”世界的可能性、“可考性”。
《山本》主题具有多义性。表层叙事的驳杂显示着事物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需要理性的整饬或重构。所以,《山本》中的神秘美学,不再具有宗教、巫术等精神外形,而衍生为朴素的诗性世界观。关于这一点,毛峰在《神秘主义诗学》一书中曾有论述,“神秘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把握世界把握生命的诗性世界观。它如其本然地看待无限的宇宙,深知有限的人类对无限的宇宙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宇宙作为无限存在,其本源、意义过程和归宿是神秘莫测的”,“在处理无限的、神圣的事务时,理性仅仅是条件而不是准则,在这些领域,诗意的、直观的、神秘的把握方式才是构筑人文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基本精神”,“这种世界观作为一种生命态度,是将天人感应、物我相通、物我相融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人不役使万物,也不为万物所役使”。1毛峰:《神秘主义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页。对于文学叙事来说,神秘本身就可能已经构成生活的深度,它以保护自然和本真生命的态度,汇入了影响深远的生态主义、人文主义,并将尊重人的命题提升到诗学境界。
孙郁在论及贾平凹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时,曾谈到贾平凹小说的文体、美学传承。在他看来,贾平凹文脉的源头并不在我们“今天”的传统里,在其文字的后面有古朴的东西。“我曾经好奇地想,他是自觉地浸染于旧的叙述语言里,还是陕西生活的原态暗示了什么?在那时期他提供的是新的文本,而在老一辈读者眼里,那些不过还是旧的东西。孙犁的夸赞,好像是在这新旧间的朴素之美。”2孙郁:《贾平凹的道行》,《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孙郁以“内觉丰富”评价贾平凹的作品质地。在《山本》中,我们看到贾平凹的叙述,已然化用了曾被描述的具有“明清文字的柔美”,且汲取两汉时期文体上的简约和硬朗,“史的味道”更加丰沛、浓郁。而贾平凹文体所蕴含的古朴之气,与“旧”和“内觉”之力达成了某种默契。
另外,贾平凹喜欢沈从文、张爱玲、孙犁的文字。生长于大西北的贾平凹近于阴柔,又不乏阳刚之气,自觉或不自觉地欣赏“狐气”和怪异之气,还“夹带了一些鬼气,是巫道里的东西”1孙郁:《贾平凹的道行》,《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因此,贾平凹写作的“在地性”是嵌入文字骨髓里面的。从整体上考量《山本》这部长篇小说,完全可以用“山本”即人本,来概括这部小说的人本意义和价值。而“铜镜”、“地藏菩萨”若隐若现地发出充满智性和神性的力量,无形地增添了事物和存在的奇崛之意。
贾平凹的写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影响,无论是情感积累还是文化积累都内化到了潜意识深处。这种积累有着深厚精神自觉性和心理承载力的文化积淀。这种积淀已经化为写作主体的那种浑沌、本色甚至本能的质地。从《秦腔》和《古炉》,我们看到贾平凹向域外文学叙事方法的选择性摄取。但对叙述技术和策略的借鉴,终究还是迅速为强大的传统基因所取代。他的写作之“本”,逐渐建立起属于民族自身的“现代性”意识,并注重人性内核和人性的自然性层面的发掘,将朴素的写实作为有激情、有力度、有深度、有形式感的追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扬弃”吧。
《山本》在诸多方面进一步冲破精神、心理和文化的局限与藩篱,平易、从容地讲述中国故事。尤其在处理“传奇”和“离奇”,以及神秘、隐秘和隐喻之间关系时,贾平凹试图“打开”许多历史的“死结”,复现清寂、空漠的寥廓时空,走向澄明。但是,这似乎又是一次虚妄的“挣扎”和梳理。南帆指出贾平凹《秦腔》关于乡土生活衰颓的情景,呈现出的“细节的洪流”,令人陷入“找不到历史”2南帆:《找不到历史》,《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的困惑之中。《山本》似乎与《秦腔》一样,都无法摆脱农耕文化和乡土变迁的意识形态规约。若要寻找事物的“起源”和兴衰的证据,爬梳生命、命运之根脉,就会异常艰难。而两者所依赖或“推崇”的叙事法则,都是在简洁与传神、写实与魔幻之间,铺展开对人与世界无尽的细部想象和存真,宗教、神话、传说、习俗甚至巫术,都参与到凸显人性、命运的过程之中。这两部长篇小说,在叙写生命、苦难、欲望、死亡及其命运的悲剧时,充满乡间和世俗的粗鄙、琐屑和凌乱。空心、无根、悬浮和事物的自然性,构成生活、存在世界的结构性乖张。人们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常常使得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判断,不免显得沉重而无奈。因此,我们在这里几乎难以捕捉历史运动的整体性面貌,也难以轻易地洞悉事物发展的“本质”和“真相”。从这个意义上看,“神秘”作为一种叙事美学或策略,已成为小说叙事结构的有机元素和重要成分。这里的秦岭,也已经不再仅仅是作品中塑造的故乡之外的大环境、大语境、大情景或地理坐标,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文化场域,更是一个文化、地理意义上的更加广阔的存在。贾平凹叙事的精神目标,不仅在于思想的经纬或灵魂的维度,而且还在于缠绕于历史、人性之间的情感置放,也是隐逸在世界深处的美学投射。贾平凹有能力将我们带回到历史现场,因为在叙事的尽头沉潜着“大叙述”的历史力量和逻辑。其最终目的,就是避免、遏制历史不断被叙事所解构、改写的妄想和冲动。而且,漫长的历史、复杂的人性,还有时间沙漏之下的人文、自然生态,究竟构成一种怎样吊诡的密码和箴语?那个“铜镜”和“地藏菩萨”,与一个民族的人文生态之间,存在着怎样神奇的联结?这些,尚且需要我们在沉潜文本的同时,从更深层的认知、审美、哲学的层面,作出我们的理解,并且深入阐释出构成贾平凹创作的文化、精神语境、情境的文化基因。当然,这也是贾平凹文学叙事对我们的接受美学、文化和文学理念的深度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