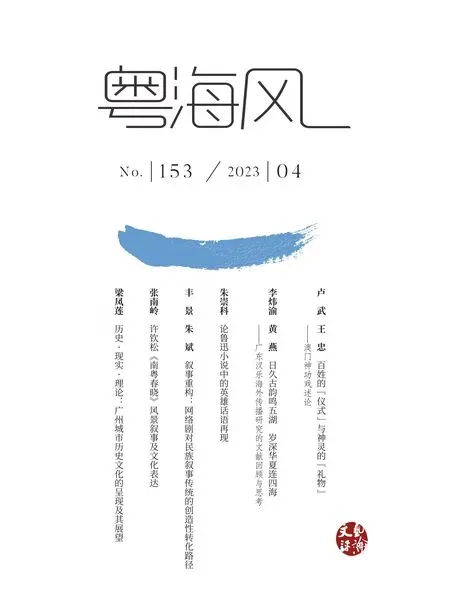历史·现实·理论:广州城市历史文化的呈现及其展望
2023-12-20梁凤莲
文/梁凤莲
任何一种人文社科研究的源起,都离不开不断的反思与追问。
对于广州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遗产,如何保持扬长避短发展自己优势的选择,这是与其他城市的区别所在。一座有魅力、有潜力的城市,需要有不同的氛围、不同的格调,需要有不同的建筑、不同的街巷,需要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生活方式,由此而展示着不同的文化模式、不同的文化面貌。真正让城市因超越而卓越的,真正能有吸引力和引领效应的,不是它与其他城市的相同之处,而恰恰是它的奇异独特之处。
由是,“每一个历史地理的爱好者,都是自然的爱国者”,此说不无道理,时空感唤醒的情感共鸣和精神塑造,所具有的价值效应,可能还有待被我们不断地加深认识。城市记忆,就是城市中曾经存在的所有个体记忆的总和,更是社会更迭变迁的历史遗传的总和。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知识并不意味着理解,研究导向的是理论的总结。
文化是历史性的,从来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基于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如何打开视野,选取哪些角度,来描绘历史、诠释过往,才能让时间与空间形成的坐标,立足于以本土为基础,而建立一个既有时间脉络的广度、又有空间伸展的宽度的演进图景。
历史文化研究的情感、概念与策略,如同陈寅恪先生对治史者的一个要求,即研究历史文化的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也就是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倡的“共情”能力。
同样,情感与立场对历史文化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影响,情感关怀与立场中的客观公允的关系问题,才能呈现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下,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诸如敬畏之心、文史不分家、慎用概念等等,就是要避免把历史文化研究变成简单的复制或者剪接,避免道听途说断章取义,就是要把时间流脉和空间延伸的起承转合讲明白,树立起比较明确的问题意识,把相应的人文关怀融汇进去,把研究与叙事融合起来,使有的放矢的判断既有合理度,也有可信度。
学术境界,说到底是一种精神境界。此在的探寻与思考,其实就是在确证自己所承接和承传的那一种取向与观念的认知,确证历史与现实的合理传递路径,最终向内心的认同回归。
而守望的精神境界的指向,就是去把握这座城市的精神根基,发掘和阐释其现代价值,为一座城市的精神血脉的延续和传承做出不懈的努力。有传统,有根深叶茂的土壤,才可以呈现出本土岭南文化独特的、地理物候的风情特点、人文风俗的鲜明特色、独树一帜的魅力光彩。
没有典籍,就没有华夏文明。同样,没有历史,亦就没有广州文化的来踪去影。时间的快速流逝,发展的变化莫测,覆盖着、有可能亦遮蔽着很多的真相,如此说来,谈历史谈文化,可能是奢侈的,更是必需的,借古鉴今,知人论世,求真务实,拓展视野,历来都是愿做“有识之士”的“有心人”的日常修炼,如同龚自珍有诗为证:“多识前言蓄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面对浩如烟海的种种过往与书写,如能做到可判断都加以判断,未可认定者暂且存疑,立足本土文化和社会根基,将历史感与整体观结合起来,正视存在于现实的是一种生活,消匿于历史的便是一种文化。作为生活,自然是烟火日常,而作为文化,尤其是文化研究,确实是需要认定判断其价值要义的。能知晓一二,恐怕已经要穷尽毕生的心力了,兼具这样的通识,从来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易事,唯此只能心存敬畏的良知。
在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这条道路上,以不同的方式,达成我们的目的。如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所说的:“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如今,总的社会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尝试回答“城市历史文化是什么”这类的问题时,我们的答案显然标注了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与位置,从而形成了更为开阔的答案中的一部分,即我们是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我们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气沉沉的过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活跃于现实生活中的过去。时间的节点上有呼应,文化的流播上有回响,依托岭南文化而强大的广州城市文化,不仅是地缘的概念,也是文化融汇创新认同传承的同一体。
尤其重要的是,“一切历史是思想史”,城市文化研究的过程恰恰是以自身的观念,对过往的关注重新加以构建。历史与文化着重在解释与传播,而这一过程也充满了富于想象的理解力。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新命名,作为一种理论创新,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岭南文化积淀着岭南人民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我们的使命就是创新传统文化,让岭南文化成为整个大湾区的共同财富,让依托岭南文化而强大的广州城市文化研究的坐标建构起来,前赴后继,生生不息,走向未来。
一本书从念想起,到观点清晰框架成形,再到章节一步一步地完成,历经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从来都在反复思考的追问中。让思想成为学术的风骨,思考有了深度和探索,学理才不会肤浅,才会有可能形成一些创新。
而所谓学术的规范规整,其实就是思想的清晰进而明朗,逻辑分明,起承转合有序,去除陈腐,去除芜杂,去除似是而非,才能让思想站立越来,传播开去。
同样,如何让思想成为学术的风骨,也就是构建一种理论框架的脊梁?思想有深度,学理有根基,这框架的脊梁才会挺立,才能达成言之有理有据的共识。
共识的达成尤其需要依仗两种尊重,一种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另一种是对现实生活的尊重,并致力于从历史与当代现实中找到内中的渊源和互相推动、互为因果的规律,这就是让历史与现实贯通起来的重要性。
显然,历史是当下的历史,而现实则是历史有所选择的延续。超越旧的学术思想,才有可能拓展新的研究局面,而这样的新局面具有传承性,并不会在快速的变化中速朽或被置换。时间不会停滞,思想与认知也不可能停滞。把握好对时间与空间的理解,这样的认知才可能是丰富和生动的。
我们生存在一个巨大的转折时代,几代人适应的历史结构在发生变化,所熟习的思想与精神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如是,观念与理念何以会不改变,又怎么可能不改变?这不过是时代变迁的其中一个板块、其中一个链接而已。
改变也好,创新也罢,都不妨说是培养对新生文化的熟悉的过程,这成了动力之源,由是创新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关键则在于这样的创新,是从内往外生发出来的,没有什么能阻挡这种突破,在这个意义下,创新就是一种有利有益有效的传承。
对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一样,保持当代性,也就是此刻的在场性,才会对历史文化产生有效的理解,而非处于一种刻舟求剑的错位关系中。探寻文化怎样在城市的更新发展中找准定位,无非就是:回归传统,走进现代,塑造自我。同样,解答文化怎样在城市中找回价值、重拾自信,依然就是:向文化源头的自觉回归,对地域个性的自觉彰扬,对时代需求的自觉转换。
我们的历史的确源远流长,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起伏和反复,似乎不是为了另起炉灶,而是为了延续传承,所以,我们才有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才有一以贯之的文化传递。我们一直认同着祖宗创设的文明,我们也一直恪守着对故土的守望。我们秉承的是爱国主义,有大国才有小家,有国家才有家庭,传宗接代的意识牢不可破。中国历史不仅是以文明的面目存在,更是以国家的面目存在。正如英国教授马丁所指出的,“这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文明!文明没有出现断层,国家兴衰只不过是一个摔倒再站起来的动作而已。”“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人之所以自认为中国人,不是因为民族身份的认同,而是因为两千多年文明成果的认同……中国是一个早已成熟的文明体系。”
所以,我们是如何思考历史的?我们是如何认知社会发展变迁的?思考与认知两者如同双翼,彼此有不可或缺的关系,不然,任何的呈现与前行都难以起行。所以,没有书写与讲述,很多东西就会消失、消亡。这一观点,在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诗人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判断里,更有着无与伦比的份量,他说:“有故事的人,写故事的人,统治着这个世界。”想来也不无道理,事实确是这样,时间的一切过往,无不经由我们的书写与讲述,表达和呈现,来认知历史,认知文化,来连接记忆,甚至来反思现在,构想未来。文化创新的同时,需要文化保护。有遮蔽,就会有发现;有断裂,就会有连续;有解构,就会有建构。所以,发现话语背后观念的演变,并对之进行富于价值的解读,意义就存在于这种解释的框架中,这也正是文化研究持续推进的动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好,一个区域的文化也好,要对整个国家甚至是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必须具备两项条件,一是以自身固有的本土文化为基础,二是能吸收外来文化作为滋养及补充。文化创新,往往发端在从多种、多元文化接触并存的交汇时代,并在其间碰撞及交替中产生出来,同时创新亦带来了融汇。前提是,要建立一套具有消化与吸附功能的理论体系,交流与融汇,趋同至认同,都需要强大的自主理论原则,才能在多元中融汇,在融汇中创新,这是一个有机的环环相接的整体。
如何讲述和呈现广州这座城市独特的城市文化,就如同如何讲述多元立体的世界,不管是历史还是文化,显然都有着巨大的意义。以真诚和敬意观察世界,一切都可以是鲜活的,时间与空间相互关联,人与事互为因果,城市的生长与日常的生存彼此见证,无论是可见的现实还是不可见的历史均有生命。
个体的研究风格是自然形成的,不是把陈述手法当风格,或者是有点含糊的观点、有点小情趣之类的意思就够了,而是与思想、与历史、与更宏观的思考关联起来,写什么写好什么并不是个人的手法以及技巧的问题,而是境界与情怀的问题。因而,“历史学就是历史科学”这样一个判断,应该敬畏对待。所谓无用之用,人文科学就是关于价值的科学。
学者所依仗的是一种端正的纯粹气质,个体所读过的书、吃过的苦、受过的伤,最终都会成为这种气质所包含的一种光源,映亮前行的路。真正的学者,学术的目的当然也并不能是超功利的,而只是超越了世俗的功利,从而与人生有意义和有意思的探索之终极目的联系起来。
人文学者的心胸应等同于家国情怀,尽可能谦恭地做一个精神家园的守护者、公理与正义的传播者、富有真实价值的承传者和捍卫者。人们通常所说的精神长相,是一种看不到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正是所谓的“心有境界行则正,腹有诗书气自华”。
按照老一辈致力于历史学的求实传统的导向,学术理路和学术精神,是学跨文史,既研究历史,也书写历史。研究与叙事并举,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是老一代史学家治学的精髓所在,也是最值得我们反思和继承的精华,完整体现了历史研究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的基本精神。
如何把握历史学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就内容而言,历史学是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母体,就方法而言,历史学游走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就未来而言,历史学包含了各种非虚构的巨大空间。
所以,历史学是在科学与艺术之间,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历史学的科学基础就是史料的可信度、解释的合理度。这两点,集中体现在历史研究中。同时,就历史学的人文性而言,也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关乎历史学的本源与主体,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的四个基本要素即时间、空间、事件和人当中,人是连接其他要素的关键。所谓叙事,接近于艺术,是追求美的;所谓研究,接近于科学,是追求真的;而历史叙事,是在研究基础上的叙事,在求真的基础上求美。
上海学者张伟然先生在《谭其骧先生与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谈及,如何科学地揭示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他解读谭先生的见解,认为,只有对历史时期的地理要素有了相当的理解,才有可能科学地提示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这就带出如何认知行政区与自然区、文化区域的互有关系。显然,这是关乎历史地理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视角如何选取的关键问题。
毕竟,在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引证、考据、索源已是常态,已不是难事,重要的是怎样去推动学科研究往前走,怎样在固有的材料上进行探索的创新,除了发现、认证,还有更为重要的,那就是判断,对所有的历史与现实材料作出有效的判断与立论。
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的首页就写下了这样的要求:“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和敬意。”
如何做到历史地理解土地、文化、时间流变与人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客观地梳理事实、了解相互之间的影响与关联,最终才会发现真正的原因,得出持之有理有据的结论。就事论事,或者碎片化地了解,是很难产生整体的认知的,甚至对那些碎片化本身的来龙去脉也很难认清,而只有通过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才能洞见历史文化在时间发展河流里,彼此相处、彼此融汇、彼此见证的真相。
每一个区域、族群,尤其是民族,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历史文化权利,就像保护生命与财产一样地传承繁衍着,生生不息。社会史既是文化史,亦是个人史,全部个人的经历构成了社会史的总和,全部个人经历的轻重构成了社会史的重量。经历与记忆,以及记录,是历史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理顺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是弥足珍贵的。
所以,一座城市必然携带着自有的品相和风貌,从历史的风烟中一路走来,城市的味道、格调、语言、风景、文化等等,就是它自身不可置换的元素,人们依此而去认知与认同一座城市的属性。
寻找一本书的立足点,如同寻找专业研究上的新的自我,有所发现和有所创新的自我。而寻找自我的同时,也是寻找一座城市的自有的存在感,去弘扬一座城市生命的存在价值与分量,从而才能向外输出这座城市的观念,输出其感召力和影响力。
文化除了积淀、蜕变、完善,还有如何梳理、如何研究,更有如何判断、如何呈现的关键问题。这正是让广州城市文化出新出彩的强大的光源。这就是我称之为原动力的所在。
广州的城市文化善于亦勇于自我激活、自我创新,最大的长项就是能从融汇而来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从不同的历史上的一切经验中,复活并蜕变成为自己的养分,变身为图强发展的活力和毅勇,最终成为探索与发展的动力之源。上接南越气象,旁及域外交流,下启新变之路,在视野的拓展与高度的洒脱上,成就了一座城市引领上的跨越。
无疑,广州城市文化发展的真相就在于,在每个不同的节点,催生与成熟了城市的某种发展。可见,如何造就了城市的崛起,提升了城市的地位,形成了城市的特色与魅力,都是有历史脉络可寻的。
由此,广州城市文化研究的建构,理论创新的导引,就显得尤为重要。不妨设定:岭南文化作为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础,而广府文化则是源泉,那么,把广州城市文化实际建构成一个优良的平台,才能有效地有价值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的人文纽带。
所有的探索与努力,都是为了去接近更具说服力的真相,去把握更有认同效应的判断与立论,以便更好地认知,我们所处的城市——广州,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我们生存其中的文化,是怎样的一种城市文化。
换一个角度,换一种表述方式,我们是否对本土文化的源流发展多一些尊重,多一些敬畏?历史对继往开来的广州,在不同的节点上作出了重要的选择,尤其是百年以降,而广州则在这种选择中作出了值得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新老广州人自信与自豪的承诺和担当,由是,广州的城市文化不同凡响、不负使命!
黑格尔告诉我们,所有历史都是精神史,是精神已经完成的及精神已经形成的东西的历史。任何有现实人文意义的历史研究,都存在着一种思想与研究的主客体之间的同一性,是把从古到今的不同的走向,去连接起相通的桥梁。研究与梳理历史,并非为了单一地去关注那些外在的、偶然的、与我们并没有多大关联的东西,而志向恰恰相反。
超越旧的学术思想,才能拓展出新的局面,而这样的新局面具有传承性,并不会在快速的时势变化中速朽或者被置换。时间不会停滞,思想与认知也不可能停滞,把握好对时间与空间的理解,这样的认知才可能是丰富和生动的。
我们生存在一个巨大的转折时代,一整代人适应的历史结构在发生着变化,所熟习的思想与精神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为此,观念与理念何以不改变,又如何可能不改变?这是时代变迁的其中一个板块。创新也不妨说是培养对陌生文化的一个熟悉的过程,因为充满了探索与发现的动力之源,所以创新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关键恰在于,这样的创新是从内往外生发出来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种突破,在这样的意义下,创新就是一种有利有益有效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