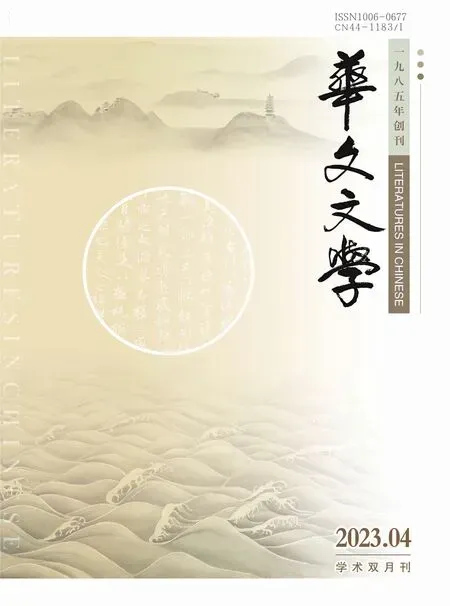史料钩沉联结两岸,拾贝补遗破陈立新
——评《文海拾贝——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考与年表编撰》
2023-12-19黄桂波
黄桂波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史料匮乏问题由来已久。2002 年,刘俊教授指出:“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①2003 年,袁勇麟教授针对“资料垄断”现象,提出“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发展路径:“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②2015 年,吴秀明教授也强调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需要协同合作:“世界华文文学史料是一个庞大的题目,至目前为止还基本处在自发的、零散的状态。学科‘历史化’及‘史料学’的建设,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改变过去各自为政的做法,将史料工作纳入协同创新的体系当中,使之组织有序,与整体华文文学研究协调一致。”③2017 年,刘红林研究员则以宏观视角探讨华文文学史料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华文文学资料库建设与资料共享的建议。④
显然,2022 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程桂婷等合著的《文海拾贝——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考与年表编撰》正是顺应“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发展趋势而诞生的。这套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两岸整合研究的赴台文人佚作辑录与年表编撰”(程桂婷主持)的研究成果,其研究对象是“赴台文人”。关于“赴台文人”的研究,在此之前有2010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远清《几度飘零 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以及2016 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吴十洲《归去来兮 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但前两者主要借助相关史料研究这一群体赴台后的活动,重在研究;而这套书则回归史料本身,重在整理。正如程桂婷所言:“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这个群体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特别是海峡两岸长期对立的特殊状态,给史料的搜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该课题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史料、辑校佚作、编撰尽可能详尽的文学年表,从而为出版更完善的全集和推动进一步的整合研究打下基础。”⑤
整体来看,这套书运用“研究(史料)—编撰(年表)—选校(佚文)”的“三维一体”编撰思路,基于“全面性”、“时间延续性”以及“学术补白”等标准,有条理地进行“史料选考”“年表选编”“佚文选校”。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从史料研究、年表编撰和佚文选校这三个维度来探究这套书的创新之处及优劣得失。
一、史料研究:补正纠偏、考掘新见
在“史料研究”方面,这套书一共选登了19篇“赴台文人”研究论文,包括台静农、林语堂、梁实秋、覃子豪、王平陵、谢冰莹和纪弦7 位作家。诚如胡适所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从这些论文来看,作者们秉持大胆的批判意识和审慎的考证态度,不迷信偏信学界权威观点,避免造成以讹传讹的学术乱象;同时敢于破除“陈见”,确立“新见”,既有借助史料补正纠偏的基础操作,亦有考掘史料阐释新见的深度思考。
即便是学界看似成熟权威的观点,我们也须保持合理的质疑意识,而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如此才能促进史料研究的良性发展。譬如《〈台静农全集〉补正》一文,程桂婷不但辑录补充自己发现的集外佚文,而且不迷信《年谱》和台湾学者罗联添的相关说法,重新考证小说《遗简》《铁窗外》《白蔷薇》《历史的病轮》《被饥饿燃烧的人们》《死室的彗星》的发表时间、发表刊物以及初次发表时的署名与题名等问题。针对“归属致伪”⑥的史料问题,程桂婷撰写了《林语堂佚简释读与笔名“岂青”献疑》一文。首先,她利用林语堂书信自述对“岂青”是否为其笔名提出质疑;接着根据《宣城植树记》和《安庆印象记》这两篇署名“岂青”的作品的发表地点——安徽,进一步说明林语堂于1934 年到过安徽但并未前往宣城和安庆,由此证实这两篇作品并非林语堂本人所作,推翻了学界已有观点。⑦
由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笔名众多,因此笔名成为发现佚文的一条必由之径,漏掉作家的一个笔名,意味着署此笔名的诗文的散佚,新发现作家的一个笔名则意味着大批佚文的重现。⑧在《新发现林语堂笔名与佚文二十九篇考论——兼谈林语堂的汉译活动》一文中,程桂婷意外发现以“予宰”为署名的若干译文,并从时间、所发刊物、原著的语种及覆盖面、汉译的水准与风格、译介对象的具体内容和译介对象的文体风格六个方面,细致地论证“予宰”为林语堂笔名。⑨
除了借助史料补正纠偏,考掘史料阐释新见也是重要一环。诚如金宏宇所言,对佚作的价值阐发当然应该是有关该作的内容、形式、文本关联、历史脉络等全方位的价值阐发,但最终都应该指向作家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史的地位问题。⑩譬如程桂婷在分析佚文的基础上,强调林语堂汉译活动“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重要性:“较之于参差驳杂的他人汉译之作,林语堂本人的汉译作品无疑更能反映他的语言风格与翻译水准。因此,搜集、整理、研究林语堂的汉译之作或许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也是必要的工作。”[11]又如范桂真通过史料的爬梳,对王平陵战时创作活动作了全面评价:“王平陵写于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十分丰富,不仅发表了对战时小说、诗歌、移动演剧等各种体裁的文艺观点,也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为读者了解特定的时代背景提供了很好的素材。”[12]再如朱晓莲在挖掘谢冰莹集外小说后,对其小说进行全面分析,并做了一个总体判断:“谢冰莹的文学之路,是一条发现生活美的原型寻觅之路,也是一条心灵跌宕的逃亡之旅。无论是赴台前还是赴台后,她的小说创作都独树一帜,是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较为完善的结合,并拓宽了女性文学的审美范畴。我们应该在注重史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客观公正地还原其本来的历史地位与文学价值。”[13]
此外,在史料研究过程中,我们也要时刻警惕“避讳”心理,克服主观偏爱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以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进行理性客观的评判,避免出现“美化(或丑化)形象”的学术陋行。显然,书中作者们做到了这点。虽然研究对象是“赴台文人”,涉及海峡两岸问题,但作者们仍旧坚持客观公正的学术立场,实事求是地还原历史真相。譬如程桂婷虽提及覃子豪对郭沫若非常崇拜景仰,但同时也强调他并未因崇拜而丧失自我立场,这从一段引文便可看出:“郭先生对于裴多菲的诗的不感兴趣,是出乎意料之外。但是,我对于裴多菲的爱好,并没有因郭先生的不感兴趣而减轻。”[14]又如朱晓莲在探究谢冰莹小说创作思想变轨的原因时,并未为她掩饰辩护,而是全面客观的分析,认为这种左翼立场的转变既是谢冰莹的主动选择——因为1931 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她被开除党籍,亦是适应20 世纪50年代台湾政治高压的被迫自保行为。[15]
二、年表编撰:眼观两岸、拾遗补全
在“年表编撰”方面,这套书一共撰写了2 个“集外拾遗简编”和4 个“文学年表”,包括林语堂、梁实秋、覃子豪、王平陵、谢冰莹和纪弦6 位作家。年表或年谱作为作家生平的重要记录,具有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意义,因此对年表或年谱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史实准确清楚,但由于种种原因,并非每一部年表或年谱都能达到这一基本要求。[16]当前很多作家的文学年表版本众多,普遍存在高度重复、互相抄袭的情况;由于不加考证的抄袭沿用,甚至导致以讹传讹的现象。
而这套书的可贵之处在于,立足海峡两岸学界研究现状,力避简单重复,尽心搜罗集佚,填补学界空白,以飨后学。在编撰思路上,不同作家也有所区别:对于学界研究较多的作家(譬如林语堂、梁实秋)采用较为简单的“集外拾遗简编”形式呈现,以便于后续编纂“集外佚文拾遗”之类的书籍;对于学界关注较少的作家(譬如覃子豪、王平陵、谢冰莹和纪弦)则采用较为细致详实的“文学年表”形式呈现,以便于后续作家全集的编纂。这有效避免了“一刀切”的简单重复,针对性地为学界提供后续研究资源。
关于“集外拾遗简编”部分,著者们立足海峡两岸研究现状,显示出“简明谨细”的特色。譬如《林语堂集外拾遗简编》一文,程桂婷首先梳理了林语堂各类选集、文集乃至全集在海峡两岸的出版现状,认为学界对林语堂编年书目已有详尽的整理,为避免赘余,特此编纂《林语堂集外拾遗简编》;接着,她突破传统的编年体编目方式,将所搜集的林语堂佚文分为三类:林语堂中文著作类、林语堂汉译著作类和林语堂英文原作经他人汉译类。此外,对于陈子善已发现的六篇佚文不再收录,编目文章凡署名“林语堂”的均不再标注。如此更为简明清晰地突出林语堂创作的丰富性,响应了钱锁桥教授的编辑理念:“真正的《林语堂全集》应该如本编目所示,包括林语堂英文原著(中、英、德文)以及他自己所作的译文(英译中、中译英、德译中)”[17],从而对现下《林语堂全集》多被“林语堂英文原著的他人汉译之作”充斥的现象予以批判。[18]
在“简明”的同时,著者也有“谨细”的一面。虽然如《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对于译名划一的一个紧要提议》等文章,在朱立文先生所编《林语堂著译及其研究资料系年目录》或钱锁桥教授所编《林语堂全集书目》中有编目,但具体文章并未见于以上选集、文集或全集;为了方便日后编撰“林语堂集外佚文拾遗”之类书籍,仍将其收录,并另加脚注说明。[19]
关于“文学年表”部分,虽然作家属于“赴台文人”,但著者们在编撰年表时并未制造“断裂”,没有刻意说明赴台前和赴台后的界限和区别,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凸显的是“统合”意识。除了《纪弦文学年表》划分为大陆时期、台湾时期和美西时期外,其余作家文学年表均无强调区分,标示格式前后一致。
从细节处看,可见其“穷尽求全”的特征。著者们在编撰文学年表时,除了标注作家作品的发表时间,也会将其创作时间列出。譬如覃子豪诗歌《竖琴弛了弦》于1934 年8 月8 日创作于青岛、并于同年9 月14 日发表在《华北日报》第8 版[20],王平陵文章《人才的陶冶问题》于1941 年11 月20日创作于南岸、并于次年6 月1 日发表在《读书通讯》第67 期[21],谢冰莹文章《忆太仓》于1937 年12 月16 日创作于汉口、并于次年1 月1 日发表在《抗到底》(汉口)第1 期[22]等,这有利于把握作品创作的时代语境,深化对作品的理解。而年表中对同一作品的不同出处予以标注,譬如覃子豪诗歌《三月》于1936 年7 月20 日发表在上海《今代文艺》创刊特大号、又于1937 年2 月以《三月的阳光》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职业市市刊》半月刊第6 期[23],纪弦诗歌《半岛之春》于1999 年12 月1 日发表在《香港文学》第180 期、又于2000年8 月28 日发表在《诗世界》第3 期[24]等,则有利于作品不同版本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书所编的“文学年表”,除了按照常规的“著译系年”(包括作品发表情况、文学周边活动等),还涉及一些作家的生平经历,这实际上已经接近“年谱”的范畴。诚如徐鹏绪所言,作家的著译年表和系年,实际上也可归入年谱之中,表与谱之间并无严格的区别;附录在文集全集之后的简约的年表,既记作者的生平活动,也录其创作、著述、翻译等事项,与附录之年谱本无不同。[25]而通过这些生平经历,譬如覃子豪幼年丧母、长年与妻儿分隔两地、晚年罹患癌症备受折磨,谢冰莹三次逃婚失败被迫与萧明结婚、1937-1939 年间多次患病、1956 年皈依法门,纪弦一生辗转流亡多地、晚年嗜酒多病因此险些丧命、婚姻美满与妻子白头偕老等,有助于我们了解“赴台文人”的人生处境,以更好地把握他们的创作动机和思想倾向。
三、佚文选校:顾全文体、兼及时间
在“佚文选校”方面,这套书一共选校了75篇“赴台文人”集外文,其中覃子豪的集外文25篇(包括诗歌类13 篇、小说类2 篇、散文随笔类及其他10 篇)、王平陵的集外文25 篇(包括戏剧电影类5 篇、小说类5 篇、散文随笔类15 篇)和纪弦的集外文25 篇(包括诗歌类17 篇、散文类及其他8 篇)。
根据程桂婷的说法,由于所搜寻的“赴台文人”集外佚文数量过多,辑校任务繁重,再加之课题结项时间临近,因此这套书采用“选校”的方式进行部分辑校。虽说是“选校”,可辑校者们却并不马虎,秉持着一定的标准——顾全文体、兼及时间。关于这个标准,程桂婷在前言有所说明:“‘选校’的标准大致来说,注重考虑两点:一是尽量顾及文体的全面性,如一个作家在小说、剧本、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等多个领域都有著述,我们会在各种文体中各选一些集外文进行辑校;二是尽量顾及时间的延续性,如一个作家从发表处女作到最后的封笔之作,往往有几十年的时间段,我们会在各个时期各选一些集外文进行辑校。至于‘校’的程度,我们是尽量保留了原文的风貌,只对明显的脱字、错字、衍字酌情加以订正。”[26]
通过比照“选校佚文”的原刊文章可以发现,辑校者们确实做到了“保留原文风貌”,主要将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并对部分明显的脱字、错字、衍字酌情加以订正。譬如王平陵《房客太太》“她占据了周先生全部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27]中的“全部”,原文写为“全”,此处增添了一个“部”字,为脱字订正的结果。又如覃子豪《记蒲风》“短短的几年的新诗运动”[28]中的“短短”,原文写为“矩短”,此处为错字订正的结果。再如王平陵《房客太太》“真的和一位出身不甚清白的女子同居了”[29]中的“真的”,原文写为“真的,”,此处删去了一个逗号,为衍字订正的结果。
此外,辑校者们不仅注明佚文的原文出处,而且还细心地对文中一些名词的不同译法进行注释,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意。譬如覃子豪《吉尔吉兹》中的“伊斯塞克湖”现在通常译为“伊塞克湖”[30]、《怀念波兰罗德薇》中的“斯宝那沙”现在通常译为“斯宾诺莎”[31],王平陵《生意经》中的“弥尔东”现在通常译为“弥尔顿”[32]、《新生活与文艺运动》中的“柴孟霍夫”现在通常译为“柴门霍夫”[33],纪弦《重庆的“四夜”》中的“虞赛”现在通常译为“缪赛”[34]、《二十五年前的张伯伦》中的“玻赛尼亚”现在通常译为“波斯尼亚”[35]等。
总而言之,《文海拾贝——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考与年表编撰》(上下册)这套书,实现了在纷繁复杂的史料文海中识别并拾掇出“宝贝”的学术初心。在史料研究方面,其突出特色是补正纠偏、考掘新见,既有借助史料补正纠偏的基础操作,亦有考掘史料阐释新见的深度思考。在年表编撰方面,其突出特色是眼观海峡两岸、拾遗补全,立足海峡两岸学界研究现状,力避简单重复,尽心搜罗集佚,填补学界空白,以飨后学。在佚文选校方面,其突出特色是顾全文体、兼及时间,既顾及文体的全面性,也考虑时间的延续性。这有利于打破“两岸学术分断”的僵局,统合海峡两岸对这一群体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对“赴台文人”个体的文学史定位、抑或是群体研究史的推进、甚至是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发展,都有突破性意义。
当然,凡事总归无法做到十全十美,这套书在整体质量上是值得肯定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瑕疵。在史料细节上,譬如《覃子豪文学年表》提及1941 年6 月10 日译诗《回忆》(普式庚作)发表于《江南文艺》第1 期,实际上应为《江南文艺》第1 卷第1 期[36];《谢冰莹文学年表》中提及的《白将军印象记》,文章全称应为《白将军印象记——女兵谢冰莹的一封简信和一篇文章》[37];《纪弦文学年表》中“10 月,痖弦夫妇归台途径旧金山”的“途径”应是“途经”之误[38]等。在编撰思路上,既然著者在《林语堂集外拾遗简编》中将林语堂的中文和汉译著作分开标注,而《梁实秋集外拾遗简编》中的梁实秋汉译作品也不少,从思路的一致性上来看,是否也可以同样进行分类标注呢?最后,笔者作为读者再向著者们提出一点期待,以供再版时参考。诚如前述所言,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发展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学者的共同努力,著者们作为这一方面的探索者和先行者,或许可以适当作一些关于史料整理研究方面的经验总结和方法分享,相信这将会对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研究的后来者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指导,更好地推进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史料化”转向。
①刘俊:《从研究白先勇开始——我与世界华文文学》,《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陈辽主编,昆仑制作公司2002 年版,第297 页。
②袁勇麟:《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回顾与展望》,《甘肃社会科学》2003 年第1 期。
③吴秀明:《“文化中国”视域下的世界华文文学史料》,《文艺研究》2015 年第7 期。
④苏世华:《华文文学的史料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 年第4 期。
⑤[26]参见程桂婷等著:《文海拾贝——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考与年表编撰》(上册)·前言,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1 页,第1-2 页。
⑥所谓“归属致伪”,是指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如果某些作品作者归属不当也会致伪,普遍的情形是对伪书(文)或他人之书(文)未加辨识而误归某作家名下,譬如《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 年版)误收署名“孤桐”的一篇小说《绿波传》,其实该小说是另一“孤桐”即江苏东台人蔡达的作品。参见金宏宇:《现代文学的史学化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第51 页。
⑦⑨[11][12][13][15][17][18][19][20][21][22][23][24][36][37][38]参见程桂婷等著:《文海拾贝——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考与年表编撰》(上册),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28-35 页,第17-24 页,第27 页,第119-120 页,第135 页,第134 页,第216 页,第216-226 页,第217 页,第234 页,第304 页,第356 页,第235 页,第444 页,第242 页,第357 页,第431 页。
⑧⑩参见金宏宇:《现代文学的史学化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第28 页,第39 页。
[14]覃子豪:《郭沫若先生——东京回忆散记之二》。转引自程桂婷:《覃子豪与郭沫若的交游及其翻译事况钩沉》,《文海拾贝——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考与年表编撰》(上册),程桂婷等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76 页。
[16]参见杨惠、谢昭新:《作家传记中的史料问题——以张子静、季季著〈我的姊姊张爱玲〉附录“年表”为例》,《华文文学》2015 年第1 期。
[25]参见徐鹏绪:《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表谱文献》,《东方论坛》2015 年第6 期。
[27][28][29][30][31][32][33][34][35]参见程桂婷等著:《文海拾贝——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考与年表编撰》(下册),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195 页,第54 页,第195 页,第12 页,第86 页,第157 页,第263 页,第278 页,第30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