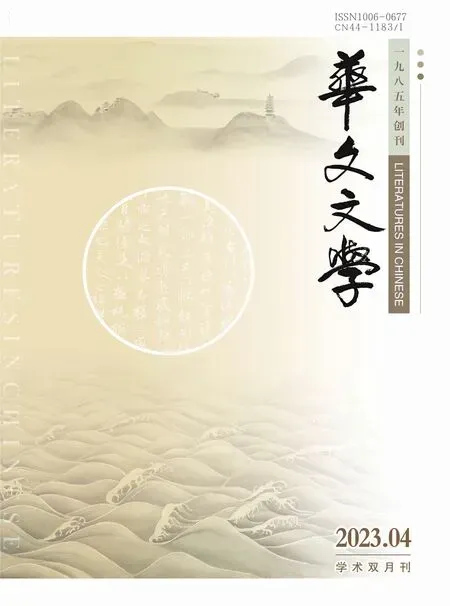聂华苓的翻译共同体研究:合/和译、创译与世界主义
2023-12-19谢攀樊星
谢攀 樊星
引言
在二战后的美国文学史上,创意写作项目(Creative Writing)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许多杰出的当代美国作家都曾接受过创意写作的训练。而在众多创意写作项目中,“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简称IWP)较为独特。1967 年,聂华苓与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在爱荷华大学成立“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地作家来爱荷华交流。拍摄于1973 年的纪录片《想象共同体》(Community of the Imagination)的开头宣告这个国际文学计划的宗旨,“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小说家、批评家、记者、散文家和翻译家,他们首次齐聚一堂,共同探索孕育人类最高语言表达形式的无形品质”。①时至今日,这个闻名遐迩的文学共同体以更多样的形式促进世界各地作家的交流。但鲜为人知的是,它也是翻译共同体。在这个文学计划中,翻译承担着重要的角色,而聂华苓既是这个翻译共同体的推动者也是翻译的实践者。在主持IWP 期间(1967-1988 年),她翻译了重要的《毛泽东诗词》(1972 年)(被誉为首部权威的毛泽东诗词英译集)和《百花齐放文集》(1981年)(“百花时期”的文学和文艺评论首次系统性地译介海外)。近年来,聂华苓再次受到国内文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②,这些研究和报导均提及聂华苓对中西文学交流的重要贡献,但未从翻译角度予以重视,更未关注到作为翻译共同体的IWP 的存在。鉴于此,本研究将梳理这个翻译共同体中的译介活动,探究聂华苓在共同体中的翻译观念、翻译行为和共同体思想。
一、作为翻译共同体的IWP
在IWP 未成立之前,安格尔就提到:“在20 世纪接下来的日子里,每个国家都将拥有两类文学:一类是本国作家的创作,一类是对他国文学的翻译。这第二类文学将对第一类文学的作者带来灵感”。③随后在1976 年,聂华苓和安格尔在《为何译在爱荷华》(Why Translation In Iowa)中称:“‘国际写作计划’相信所有人,无论肤色和语言,都是一个共同的群体,在这个不平衡的世界里努力站稳。这项计划同时相信,世上所有文学,无论语音和文字(有何不同),也是一个共同体,都来自这些智者身上相同的古老的想象”。④无论是“两类文学”还是“一个文学”,它都反映出翻译的重要价值以及聂华苓与安格尔对翻译的重视。翻译共同体形成的原因首先很简单,这些作家来自世界各地,彼此语言不同、文化相异,他们之间的交流需要翻译。曾在IWP 驻地交流的美国诗人威廉·里根(William Riggan)回忆道,除了日常的研讨会、小组讨论和文化参观外,IWP 还会专门提供语言指导会议和翻译服务。⑤所以“这里每天都上演着翻译”。⑥
当然,翻译的不仅是日常的对话,更多的是文学的交流。如果这些作家希望将自己或本国的作品翻译成英文,该组织便从“翻译工作坊”(Iowa Translation Workshop)指派相应语言的译者,或者同时邀请一位不懂原语的美国作家,由作者、译者和美国作家三方共同完成这项翻译任务。冰岛诗人西于聚尔·马格努松(Sigurdur Magnusson)曾在美国年轻作家米克·费杜洛(Mick Fedullo)的协作下将冰岛现代诗歌编辑成册,翻译成英文出版。⑦许多时候,这种翻译合作由驻地作家们自发而成。波兰诗人阿图尔·弥则斯基(Artur Miedzyrzecki)刚到爱荷华,驻地的美国诗人约翰·巴特基(John Batki)便将其14 首诗歌翻译出来,最终汇成诗集在美国出版。⑧弥则斯基在驻地期间也将美国诗歌翻译成波兰语发表在华沙的文学刊物上,最终汇成诗集出版。除诗歌外,这种作家间互译的浓厚氛围还促成了其他文学体裁的翻译。乌干达作家拿撒勒(Peter Nazareth)在第二次受邀来访期间以九天时间完成了一部小说的创作,这引起许多驻地作家的关注。来自波兰、日本、印度和以色列的作家分别摘译该作品,将其发表在本国刊物上。⑨还有作家私底下翻译了拿撒勒的作品。有一天他收到一同驻地交流的前南斯拉夫作家大卫·阿尔巴哈里(David Albahari)的信。信中写到,“我十多年前曾翻译过你的文章,现在寄给你,名字叫做‘东非作家的社会责任’……可能还有其它翻译作品,其他译者翻译的,我试着找找看”。⑩如果与他者的交流是翻译的开始,那么翻译便是与他者进行深刻交流的开始。许多作家便是在这样的翻译共同体中建立起深厚友谊。[11]此外,戏剧翻译也是日常的文学交流活动。芬兰剧作家因克瑞·基尔皮宁(Inkeri Kilpinen)回忆道,IWP 曾专门组织戏剧活动小组与爱荷华的戏剧学院交流,将芬兰语戏剧临时翻译成英文供在校学生讨论和欣赏。[12]这些作家的交流不限于文学活动,还体现在对翻译本质与实践的探讨。萧乾在驻校期间曾与聂华苓一起讨论翻译的问题,他们都反对那种逐字逐句的翻译,认为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将原文的精神忠实地传达出来。[13]
在聂华苓和安格尔担任负责人期间,翻译是IWP 重要的交流成果。在二人的组织下,共有11 部来自不同语言的现代诗集被汇编和翻译成英文出版,这些均是受邀作家和爱荷华翻译工作坊的共同成果。此外,许多作家在交流期间的创作和返回故土后的回忆录也被整理和翻译出来。1976年,为庆祝IWP 成立十周年,聂华苓和安格尔将1967 至1976 年部分受邀作家的作品整理汇编,译成《来自世界各地的书写》(Writing From the World)一书出版,同年组成专栏在《爱荷华评论》(Iowa Review)第2 期和第3 期发表。1984 年,聂华苓和安格尔将1977 至1983 年部分受邀作家的作品进行整理,组织译者翻译成英文,在《爱荷华评论》第2 期发表。在1987 年庆祝IWP 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两人又将部分受邀作家的回忆录进行整理并组织译者翻译,一部分汇编成书《来到爱荷华的世界》(The World Come to Iowa)出版,一部分以专栏形式在《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第3 期发表。正是在这个翻译共同体中,聂华苓也与其他译者合作,翻译了《毛泽东诗词》(The Poems of Mao Tse-tung)和《百花齐放文集》(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
二、以“合”促“和”:“商榷式”翻译模式的探索
翻译理念指对翻译(或相关)问题的思考。在IWP 翻译共同体中,作为译者的聂华苓常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翻译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原文中异于目的语读者意识形态的表达,如何翻译原文的俗语、文化词和双关语,如何将诗歌的精神传递出来等等。所有问题的解答都指向两个更根本的问题:“原文该由谁来译”,“译者该如何处理他与作者、其他合译者、目的语读者的关系”。聂华苓在其翻译手稿“合/译:作家的看法”(Co-translation:The Writer’s View)[14]以及由其编辑书册的跋序中阐释了自己的见解。
(一)合译模式
在这篇与安格尔合作的手稿中,聂华苓一开始便指出许多亚洲作品在英语翻译中受损严重,原因在于译者模式的选择。从语言文化身份来看,原语译者难以保证高质量的目的语表达,而目的语译者难以保证对原语文化的正确理解;从职业身份来看,普通译者难以像作家那样传达文学的精神。即便像翟理斯(Herbert Giles)这样优秀的汉学家,虽然翻译散文时语言充沛多姿,但翻译诗歌来也时有呆板无趣。聂华苓主要指表达上的困难;意能会,但语难寻。如何把理解到的意思恰当地放到新的语言当中,这是译者常遇见的问题。
面对这个问题,聂华苓提出合译(co-translation)模式。在英译集《百花齐放文集》的前言中,聂华苓专述一节提到这种在翻译共同体中常见的翻译模式:由中国译者和美国译者共同努力,前者把握意义,后者把握语言。这对译者的语言文化能力提出要求,“中国译者不仅要有理解原文的能力,更要有理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语言表述、词汇的能力,而美国译者需要始终保持流畅直接的英语表达,避免因语言的花里胡哨而令翻译变形”。[15]该合译模式对译者的职业身份提出要求:无论译诗还是译散文或小说,最好还是需要作家的参与,因为翻译不仅意味着对语言趣味和文化内涵的把握,还意味着对原作精神的把握。在聂华苓看来,作家在共情上比常人更准。聂华苓在《百花齐放文集》的序言中大致记录了这种模式下的翻译流程。合译小组由三人组成:懂英文的中国人、美国作家、聂华苓。首先,中国译者和美国作家共同完成初译稿:中国译者以句子为单位提供直译本,阐释原文中的文化、政治或历史内涵;美国作家在此基础上调整语言和句式结构,完成初稿。其次,美国作家对全文反复润色,提供地道流畅的二稿。最后,聂华苓比照原文对二稿逐字逐句校对,遇到不解或不满意之处,便与其他两位译者协商,完成三稿。
聂华苓提到合译是常见的翻译模式,但这个在爱荷华的翻译共同体的合译模式却有特殊之处,那就是这群译者来自原语场和目的语场,他们能面对面交流,对原文的意义和译文的语言同等重视。这得益于翻译共同体所提供的公共空间。这些译者们在爱荷华驻地交流,能够保证日常碰面,进而保证了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密切交流。
(二)和译思维
在聂华苓看来,确定合译模式之后,译者还会面临两种问题。第一种是广泛存在的问题,即译者是屈从于作者还是独立于作者。这种主客身份的选择绕不开译者对原文译文关系的认识。第二种问题是合译模式下的常规问题,即译者如何处理自己与其他译者之间的冲突。对这个问题,聂华苓有一段精妙的隐喻说辞,“有时候,我们三人之间会发生各种战争:文化上的、文学上的、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的。我们会起争执,会指责对方文化或政治沙文主义,漠视他国民族传统,会指责对方英语用词别扭或者矫情做作,了无欣赏语言的能力。这是一场生动而激烈的对抗,关乎语言、文化、想象和自我”。[16]为此,聂华苓提出和译(co-translation)的解决方案。所谓和译,即是和谐共生。
就第一个问题,聂华苓指出译者应该与作者和谐共生。其一,译者并不屈从作者。翻译是创造性活动,因为创作本身也是翻译,“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其本身都是翻译。作家将脑海里的思想付诸纸上就是翻译”。[17]拉布昌耶尔(La Bruyère)说“自从有了人,自从有了思想,言尽矣,我们来世太晚”。[18]虽然思想不完全是原创的,但由思想到语言这个翻译过程被认定是创造性的,那么语言转换的翻译过程也理应被视作是创造性的。既然翻译是创造性的,那么译者就不该是虔诚地匍匐在作者跟前。其二,译者并不完全独立于作者,翻译只能给予原文半条生命。[19]聂华苓虽然反对在翻译中追求字句上的对等,但她支持意义、感觉和想象的对等:原文本并未被抛开。她虽然认为译者应该使用与自己意气相投的语言,但她同时也坚持翻译的思想和意义是作者的:作者并未被抛弃。她虽然支持诗无至善,意不能由言完达,但她也认同译者挖掘的言外之意仍旧是作者的意。归根结底,聂华苓明白意义的阐释空间是开放的,但她也认同这个空间是作者给予的,所以阐释也是限制性的。用她的话说,“当沉浸在翻译中时,我们会感受到作家本人就在身旁,叮嘱我们要更用心些,更费心些,这样才好把他的思想或想象感知出来”。[20]所以站在作者面前,译者既不服从于他又不独立于他,而是合为一体,和谐共生。
就第二个问题,聂华苓指出译者与译者之间也要做到和谐共生,因为交流离不开理解和妥协。聂华苓提到,合译的过程常常既让人欣喜又令人抓狂。抓狂的是大家时常会上演上述提到的论战,三人间要不断地询问、解答、质疑、辩护;欣喜的是最后大家总会互相妥协,达成一致。虽然到最后并非所有人都完全满意,“但和译意味着和谐共生,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21]聂华苓所期望的译者与译者间的和谐共生,实则也是译者与读者间的和谐共生。确切地说,这里的读者是译者心中的隐含读者。所有的论战,文化的、政治的、语言的,实则是美国作家对中国表达的不了解、不认同,甚至是不理解。比如,“挂羊头,卖狗肉”,中国译者坚持翻译成“selling dog meat under the sign of a sheep”,但美国作家认为这难为英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在与聂华苓合译汉诗时,对于“胭脂泪”的表达,安格尔表示这在西方文化中完全是丑态。[22]这两位美国作家均把自己想象成普通的英语读者,对汉语的某些表达提出不解或质疑。但在聂华苓看来,面对文化和历史语境之间的鸿沟时,译者应该引导读者切身地投入到作者的创作背景中,以避免完全从目的语文化去解读。聂华苓所做的便是与这些隐含读者展开对话,以尽量求得他们的理解。上述“狗肉”和“胭脂泪”的文化内涵最终在译文中得以保留。当然,有些内涵实在难以传达的也会删去。但无论是删还是留,聂华苓和译思维的关键是译者与其他译者,甚至是隐含读者展开了坦诚的对话,相互理解。
聂华苓的合译模式与和译思维是对连续体,合译是基础,和译是最终归宿。合译给不同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有效交流提供可能,而和译则为交流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聂华苓的翻译观显示其对可译性的坚持,“有人认为翻译不可译,只是给原诗、原剧和原小说蒙上毫无生气的面纱。但我们认为翻译能让原文的血液透过面纱,让原作说话”。[23]这种可译观相信文化之间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同时承认翻译的困难。但认识是逐渐深刻的,翻译同样是由粗到精的过程,一时之难并不意味着永世之难。
三、张力与陌生化:“创造性”的翻译实践
聂华苓的合译模式与和译思维对其翻译行为两点要求。其一,作为读者,她应该尽量与作者达到和谐共生,既不“负”于作者,又不“缚”于作者。其二,作为合译者与作者,她要尽量与其他译者和目的语读者达到和谐共生,既要保持异质性,又要让读者理解。基于这两点要求,聂华苓在翻译中极力追求译本的创造性。
聂华苓对庞德的汉诗创译极为推崇,认为其译诗是所有汉诗英译的典范。[24]在翻译诗歌时,庞德强调意象的传达,不求充分呈现全诗的意义,但求意象的精准描绘。[25]顾明栋认为庞德的译诗属于“作者型翻译”,是在原诗的启示下磨砺原创的艺术,是对原诗的塑造和超越,不同于满足读者知性需求的“读者型翻译”。[26]聂华苓虽推崇和模仿庞德的译诗风格,但并未走向“作者型翻译”那端,而是始终认为原文的意义和译文的语言同等重要,并不把翻译当作原创艺术的锤炼。所以聂华苓的诗歌创译介于两种翻译之间。这种平衡在其诗歌翻译中表现为,通过语法手段强化意象的认知体验,但并不变更诗歌的意象内容。
聂华苓的诗歌合译作品有《毛泽东诗集》以及《百花齐放文集》的诗歌部分。本节以她与安格尔合译的《西长安街》为分析对象。[27]该译诗最初出现在那篇未明时间的手稿中,后收录在《百花齐放文集》中。《西长安街》为卞之琳1932 年所作,诗人通过对意象的精心布局表达他对现实与历史的思考。本文接下来借助认知语法,分析聂华苓处理原文意象时的创译手段,以下面两个例子说明。
原文:仿佛有马号,一大队骑兵,
在前进中,面对着一大轮朝阳。
译文:There seem to be bugles,
bugles blown on horses,
a great cavalry marching
towards the bigwheel ofthe morningsun.
“马号”在原文中是静态名词,在译文中变为“名词+被动语态”结构(bugles blown on horses)。添上动词“blow”,译文呈现出动态的画面:“马背上有人吹着号子”。而动词性表达指涉过程,会描述随时间变化的情景,能让读者逐步且更真实地感知这个过程。[28]巧妙地是,“仿佛有马号”在译文中被拆成复合句,主句与分句的连续阅读使读者仿佛能渐次感受到号子和马匹的逼近,视觉和听觉逐渐清晰明朗。“一大轮朝阳”中的重点意象是“朝阳”;“一大轮”做修饰词,但在译文中却被译成名词结构“the bigwheel”。当常见的“修饰词a+名词b”结构变成“名词a′+名词b”结构时,名词a′会上升至指示中心的位置,成为读者认知的重点。[29]因此“the big wheel”成为认知焦点。当读者的目光随着号子、马匹、战士由远及近时,他不再只是跟随者,而是直接与战士的目光融合在一起,眼前呈现出巨大的“圆”。这种意象的强烈冲击,颇有“长河落日圆”的壮阔之感。
原文:长的是斜斜的淡淡的影子,
枯树的,树下走着的老人的
和老人撑着的手杖的影子,
译文:Long are the shadows,slanting,dim,
Dead tree,old man walking under,
stick supporting him:
首先是修饰词后置。在侧显表达式中,修饰词后置会使首级焦点落在修饰词而非所修饰的名词上。[30]“长”在原诗中是重要的意象特征,“长的影子”、“长的红墙”、“长的蓝天”、“长的冬天”、“长的沉默”,表现出画面的无声和缓慢。聂华苓在译文中借助修饰词后置凸显“slanting”和“dim”意象特征。这既加重了读者对这幕死寂画面的认知,还放缓了读者的阅读速度,增添了伤感。其次是名词化处理。名词更易对事态展开完整扫描,展现无时间性和静态特征。[31]原文中后两行诗为“修饰词a+修饰词b+修饰词c+名词”结构,被译成三个并列的名词结构“tree”,“old man”,“stick”,这使本该陪衬的意象全都独立出来,变成名词意象。最后,这三个意象的翻译属于省略结构。省略结构能使词成为焦点,使词的联想放射性凸显。[32]这三个意象的并列构成庞德的意象迭置,即意象彼此独立但又相互融合,组成意向群,在瞬间释放能量,传达出作者饱满的情感。[33]通过三种语法结构的巧用,聂华苓使原诗中的意象特征呈现得更加深刻,使意向群的交互指涉更加复杂,也使得整体画面更加死寂,使死寂更加漫长。
总之,在本诗中,聂华苓通过布置意象和移译汉诗的语言风格,违背了英语文法,使其译诗具备庞德体式的张力和陌生化效果,但同时又以语法手段达到了译者、作者、读者的视域融合,使其不坠入“作者型翻译”之端。
四、翻译共同体精神:从生命经验到世界主义
自IWP 成立起,迄今为止已有1500 余名来自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种族、语言、文化的作家来此地驻校交流,而时至今日(在聂华苓于1988 年退任主持人后),翻译在这个组织内扮演着更系统更稳固的角色,比如成立“国际翻译工作坊”(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Workshop),专门开展翻译交流活动。聂华苓曾在自传中写道,IWP 成立的初衷只是自己一时激动的突发奇想。[34]但事实上,IWP 自成立初就蕴藏着两人以文载道的世界主义观念。聂华苓在大陆时曾经历军阀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苦痛,在台湾时因其《自由中国》文艺主编的身份和反对台湾当局独裁高压的文艺政策而遭到监视和恐吓,所以她早期的作品里多是台湾社会里边缘人的愁苦和失落。安格尔曾在二战期间游历欧洲,亲眼目睹纳粹分子在德国的罪恶和人们对纳粹的恐惧,同时感受到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火热力量,于是奋笔写下诗集《心火怒焚》(Break The Heart’s Anger)(1936):“德国的酒鬼、英国的胆怯,纳粹在作恶,维也纳在枪战,只有苏联充满信仰和希望”。[35]聂华苓曾评价安格尔“是个典型的三十年代美国知识分子,理想主义,反对纳粹,向往社会主义”。[36]所以,当聂华苓在爱荷华的湖畔对安格尔说要不建立一个世界文学组织而安格尔满脸狐疑时,想必两人内心中也有着同样的声音在微微颤动。邓如冰发现,被邀请至IWP 的作家多来自遭遇纳粹铁蹄的东欧国家、遭日寇侵略的东南亚国家、遭种族骚乱和经济困顿的南美和非洲国家,所以在她看来,IWP 成立之初具有“左派精神”,让“受难者”能够在文学交流中“相互理解、同情、救助和慰藉”。[37]被邀请去IWP 驻地交流的蒋勋这样评价这个文学共同体,“作为创作者,你能不能扩大,扩大到最后你就是一个人,你必须用人作起点,你最后最终的关怀也还是个人,那我觉得这就是IWP 给我最大的印象”。[38]当面对不同世界的“受邀者”、“受难者”或“交流者”,IWP 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实则也反映出创办者和组织者聂华苓(和安格尔)的世界主义精神。
聂华苓(和安格尔)对于翻译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看法曾遭到某些学者的质疑。刘羿宏基于IWP所处的冷战背景,从殖民史和帝国史视角对IWP的翻译计划展开探讨。[39]他认为安格尔所言的“两类文学”实则将翻译变成“二等文学”,将他国文学置于等级结构之中;而聂华苓(和安格尔)所坚信的“一个文学”将英语放在优等地位,这实则助推了英语的霸权主义和中西文化的同质化;而她所坚持的纯文学则是诗学权威的象征。在刘羿宏看来,聂华苓的翻译共同体、合/和翻译观和创译行为在追求文化同质化和诗学权威的过程中维护了美国的文化霸权。从赞助人的角度来看,IWP确实在冷战时期得到由美国政府官方部门资助,用来执行美国的文化外交。[40]但是,文学计划赞助人的意图并不意味着文学参与人的意图;文学计划在时代背景下被赋予的功能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文学参与人的目的。事实上,聂华苓本人多次谈到她对政治不感兴趣。尽管在英语作为强势语言的背景下,将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翻译到英语市场时,确实存在迎合英语国家对他国文化的看法、期待与想象的风险,巩固了英语的语言霸权。[41]但是,英语的语言霸权与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和各国的语言政策等诸多方面息息相关,并非单一由翻译造成的。
聂华苓的世界文学理念反映的是人类经验的共性,非所谓的文化同质化。聂华苓曾以此表达不同地区文化的关联,“我和许多地区的作家认识以后,读到他们的作品,发现中国人的命运,也就是20 世纪的人的命运”。[42]爱荷华的驻地作家同样感受到这种生命经验的共性,“他们发现,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声音虽然不同,但它所表达思想和情绪确是相通的”。[43]张隆溪也相信经验的通性,而“不相信那种把东方和西方看得如此迥异不同,以致其思维和表达的方式竟不能彼此理解”。[44]张隆溪坚持同一性是因为他看到西方当代和后现代理论过分强调差异,割裂了文化的共同之处,阻碍了跨文化对话的可能。而聂华苓对这种割裂感也有体会。在对比美国20 世纪早期作家和当代小说家,她提到许多当代小说家“没有使命感,没有社会意识,在创作上不能超越个人的思想和感受”。[45]当然,追求经验的共性并不意味着抹杀差异。聂华苓虽然主张创造性翻译,但是并未走向“作家型翻译”那端,而是始终兼顾原语的语言特征和文化内涵。而且,聂华苓并非只在英语中发现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在其翻译生涯的早期和中期(1950 到1960 年代),她也一直将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译介至中国文坛,希望学习西方的写作手法,而这正是因为她看到人类生命经验的共性。
正是因为相信不同生命体的经验的共性,聂华苓才更相信翻译之于人类命运的力量,“随着世界如久放的橘子慢慢变小,来自不同文化的民族都会逐步靠近(无论多么不情不愿和满腹狐疑),这个世界的余年可用一句简单的话语表示:‘翻译,或者死亡’”。[46]所以聂华苓(和安格尔)并非将翻译置于二等地位,或是用翻译来巩固英语的霸权地位。相反,她至始至终将翻译放置超然的位置,而她所关注的非美国或英语的霸权,而是整个人类的命运。
①[39]Yi-hung Liu,“The World Comes to Iowa in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and the Translation of Mao Zedong”,American Quarterly,2017(3),p.61.
②台湾学者应凤凰推出《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聂华苓》(2012 年);香港著名导演陈安琪拍摄《三生三世聂华苓》纪录片(2012 年);香港《明报》推出聂华苓专题(2015 年);《当代作家评论》以聂华苓为封面人物进行介绍(2020 年);俞巧珍在《华文文学》发表《聂华苓文学年表》(2022 年第4 期)。
③Ivar Ivask,“Introduction”,World Literature Today,1987(3),p.365.
④[23][43]Paul Engle.,Hualing Nieh,“Why Translation in Iowa”,The Iowa Review,1976(2),pp.2,1,1.
⑤William Riggan,“A Personal Encounter with the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Notes and Thoughts”, World Literature Today,1987(3),p.375.
⑥Hualing Nieh.,Paul Engle,“The World Comes to Iowa”, World Literature Today,1987(3),p.371.
⑦Sigurđur Magnússon,“A View from Iceland”,World Literature Today,1987(3),p.399.
⑧Artur Miedzyrzecki.,Ewa Krasińska,“Engle’s Country”,World Literature Today,1987(3),p.402.
⑨⑩Peter Nazareth,“Adventures in International Writing”,World Literature Today,1987(3),pp.383,384.
[11]György Somlyó.,David Kornacker,“Iowa City,Five Years Later”,World Literature Today,1987(3),p.405.
[12]Inkeri Kilpinen,“Richness of Variety”,World Literature Today,1987(3),p.394.
[13]Qian Xiao,“A Ferry,a Window,and Now a Bridge”,World Literature Today,1987(3),p.408.
[14]Co-translation:The Writer’s View 一文收藏于爱荷华大学档案馆,篇幅达23页。该文献由聂华苓与安格尔共同撰写,详细记录了她俩翻译诗歌时的对话和对翻译的思考。但因数据匮乏,未能确定该文献时间。
[17][19][20]Hualing Nieh.,Paul Engle,“Co-translation:The Writer’s View”,[EB/OL].[2019-8-21].https://iwp.uiowa.edu/sites/iwp/files/Co-TranslationTheWriter’sView.pdf,pp.4,11,1.
[15][16][21][24]Hualing Nieh.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pp.li,liii,liii,lii.
[18][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58 页。
[25]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1,p.15.
[26]顾明栋:《读者型翻译与作者型翻译——谈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翻译理念》,《山东外语教学》2020 第6 期。
[27]由于本研究的重点为聂华苓,同时也为论述方便,本文将全程用聂华苓或聂译本等核心字眼,但并不否认安格尔在这篇译诗以及翻译共同体中所作的贡献。
[28][33]丁国旗、范武邱:《认知诗学视角下的意象分析与翻译——以庞德的“在地铁车站”为例》,《外国语》2016 年第1 期。
[29]Reuven Tsur,“Deixis and Abstractions:Adventures in Space and Time:Adventures in Space and Time”.In Joanna Gavins.,Gerard Steen.(eds.).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London:Routledge,2003,p.43.
[30][美]罗纳德·兰艾克:《认知语法导论(上)》,黄蓓译,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119 页。
[31]Ronald Langacker,“Nouns and Verb”,Language,1987(01),p.90.
[32]Hugh Kenner, The Pound Era,London:Faber and Faber,1972,p.187.
[34][42]聂华苓:《三生影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版,第313 页,第575 页。
[35]Eric Bennett, Workshops of Empire,Iowa: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15,p.82.
[36]聂华苓:《鹿园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第213 页。
[37]邓如冰:《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WP)——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历史语境》,《文艺争鸣》2019 年第10 期。
[38]参见陈安琪指导的记录电影《三生三世·聂华苓》(2012 年)。
[40]IWP 的官网悬挂着标题“WRITERS AND CULTURAL DIPLOMACY:A CORE MISSION OFTHE IWP”(作家与文化外交:国际写作计划的核心使命)。https://iwp.uiowa.edu/about-iwp/cultural-diplomacy.[2021-06-05].
[41]Minae Mizumura.The Fall of Language in the Age of Englis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
[44]张隆溪:《道与罗各斯》,冯川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12 页。
[45]聂华苓:《没有点亮的灯——美国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1 年版,第1 页。
[46]Paul Engle.,Hualing Nieh,“Foreword”,The Iowa Review,1984(02),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