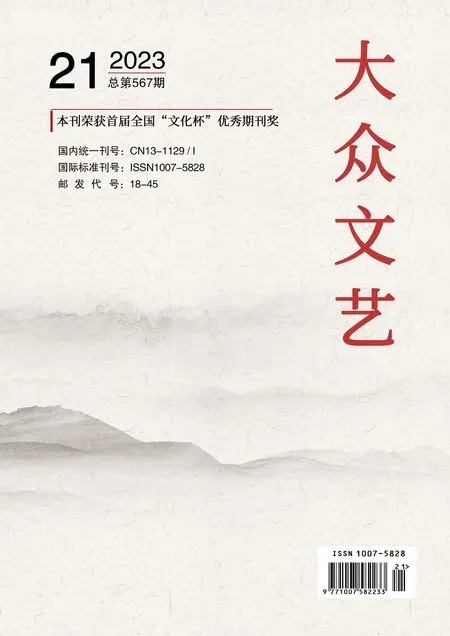浅析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宗教与非宗教意蕴
2023-12-19刘俊辰
刘俊辰
(延边大学,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133000)
狄更斯的《双城记》一直是一个深受中外学者关注的研究热点话题。然而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从现实主义的单一角度入手的。将狄更斯在这部作品中共同体现出的现实主义批判与人道主义关怀视为一种作家无法调和的内心矛盾,并且结合了狄更斯的生平将这种矛盾解释为“他对生活困苦的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与怜悯;本人对上层阶级的向往与憧憬”[1]之间的矛盾。然而如果从宗教与非宗教的多角度切入,作者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就是不矛盾的。宗教的部分表现为作品洋溢的救赎意识及诸人物体现出的《圣经》母题。而非宗教的部分表现为作品独特的“血描绘”和对暴力反抗阶层压迫的批判。而作者厚植文本的人道主义情怀则可以看成这两部分的重合区域,充当二者的纽带,既有宗教意蕴,又有非宗教意蕴,赋予了作品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一、基督的救赎——拯救与被拯救
古希伯来文化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精神养分之一。《圣经》是这种文化的载体。相比于其他宗教著述,《圣经》最突出的特点是拯救意识。《旧约》中,耶和华第一次在世人面前显露他的名时,就告诉世人:“我是耶和华,我要……救赎你们脱离他的重担”①。《新约》中,耶稣在山上的宝训里有“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②。《圣经•旧约》与《圣经•新约》的成书年代不同,作家群体也不同,但拯救意识是一以贯之的。狄更斯深受基督影响且谙熟《圣经》内容,在双城记的宗教意蕴中,拯救意识处于核心地位。
作者为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安排了若干对多向度的拯救关系,构成了作品的救赎关系谱。在这张关系谱中,露西小姐处于中心位置。露西小姐的形象切合《圣经》中“圣母”这一母题,正像许多中世纪圣母题材的油画作品一样,她是整个阴暗基调的《双城记》中的一束光。金黄的头发,洁白的皮肤,绝美的容颜,令世人为之倾倒。同时她又善良宽容而博爱,周身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她用女儿对父亲的亲情的爱拯救了年老而精神受到重创的马内特医生,令他重新恢复神智。又用爱人之间爱情的爱拯救了侯爵侄儿达奈先生,令他找寻到了真正的幸福。她用倾慕与被倾慕者之间复杂的情感拯救了卡顿先生,令他在无尽的颓废与堕落中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同时她又是被拯救的。忠实的银行办事员洛里先生和达奈先生帮助她找到了自己的父亲马内特医生,实现了一次拯救。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恢复神智的马内特医生以其十八年巴士底狱牢狱之灾的经历在反抗军中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多次挽救了众人,这是二次拯救。卡顿牺牲了自己救出了身陷绝境的达奈,间接地拯救了露西,这是三次拯救。其中卡顿与达奈之间的拯救关系又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二者本是情敌关系,而且卡顿在初识达奈的时候就表示“我很不喜欢你”。他觉得二人唯一的相似处可能就在于长相。一方面卡顿是“老贝利”当红律师斯特莱福的助手,是一条被隐藏在“老虎”背后的“豺狗”。他虽然才华横溢但总在幕后工作。长期的抑郁不得志使他总是通过酒精麻痹自己,“散乱的头发”成了标配。另一方面达奈是隐姓埋名来到伦敦的法兰西贵族后裔,做法文教师谋生。俊朗的容颜和优雅的风度受到了马内特父女的一致认可,同时也是一众追求者中露西小姐唯一青睐的。二人构成了文本的“双城”隐喻。就像是硬币的两个面一样相貌神似,然而一光一暗;一个朝气蓬勃,一个暮气沉沉;一个严谨正派,一个玩世不恭的特质却又迥然相异。但是在深层价值观念上两个人又有惊人的一致性——拯救意识。达奈为了救昔日的老管家抛下伦敦的安乐窝重回动荡的法兰西结果身陷囹圄。卡顿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做一件比我所做的好得多,好得多的事”,毅然替换下达奈,做了断头台上的“第二十三个”。在拯救达奈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救。
此外,体现在马内特医生、达奈、卡顿等人身上的“复活”意识也极具宗教色彩。一次救赎代表着一次“复活”。复活在《圣经》中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指向。上帝之子耶稣为救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复活代表着新生。马内特医生坐了十八年监狱神志恍惚,只会在昔日仆人德发日的阁楼上做鞋,经女儿的拯救后得以重获新生。达奈与卡顿之间的拯救也代表着二人的“复活”。卡顿先生在赴死前不住地重复耶稣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也直接揭示了这一行为的宗教意蕴。这样的复活又暗合《圣经》中耶稣受难这一母题,为作品增添了神圣的光辉。
二、现实的残酷——压迫与被压迫
《双城记》的非宗教意蕴主要体现在作者为我们构筑的法国大革命的酝酿及爆发这一历史蓝图上,是饱含现实主义批判意识的。在这一历史蓝图中,作者又格外偏爱对鲜血的描绘,这股鲜血有贵族压迫平民时平民流下的血,也有大革命发动后贵族流下的血。是压迫者的血同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血。作品一开始写到德发日夫妇的酒馆打翻了一桶葡萄酒,引得圣安东的贫民们哄抢的场景,首次将鲜红的葡萄酒和鲜血联系到了一起。底层人因为长期的贫困根本喝不起酒,在哄抢葡萄酒的时候“就好像发狂的野兽”一般,营造了一副人间炼狱的景象。同时也为下文埋下了伏笔,因为在大革命爆发后,愤怒的底层人民真的将鲜艳的红酒变成了鲜血,让它从贵族的脖颈上喷涌而出。血的象征意味也就更加明显了。
大革命并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作者用了冗长的篇幅为大革命的爆发做了铺垫。我们可以看到侯爵为了满足片刻的淫欲杀害了佃农女孩一家,女孩的哥哥反抗后被刺身亡在他们看来也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小疯狗!一个农奴!他逼我弟弟拔出剑来,我弟弟就一剑把他刺倒了——像一个绅士那样”。贵族的车马在城镇里压死了一个孩子,也只不过是付一个金币了事。“你们不是天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巨大的阶层矛盾使得民间蓄积了一股可怕的复仇力量。德发日太太每天都坐在她的椅子上编织,她织的每一个花纹都代表一个她想杀掉的贵族,德发日太太是民间复仇力量的具象化人格化。这股复仇力量在愤怒的贫民攻占巴士底狱以后达到了顶点,“四处都在起火”,法兰西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街上的革命军甚至可以因为一个路人衣着华丽些就把他送上断头台,革命后的共和国完全浸泡在了鲜血里。
不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并没有完全站在所谓“人民立场”上对革命进行歌颂,对贵族进行毫不留情的否定,而是站在了一个冷静的“第三者”立场上描绘了这场血腥冲突中的双方。虽然他以犀利的笔触控诉了贵族对平民犯下的罪行,“我从未见过这种受压迫的意识,像火似的喷发出来……我见到它潜伏在这个快死的孩子心里的时候,才见到它爆发出来。”但当平民起义以后,他又以同样犀利的笔触控诉了“革命”的人民,“自由、平等、博爱,要么死亡”的法兰西犯下的罪行。我们在狄更斯的笔下看到了失去理智的、愤怒的、扭曲的、像野兽一般的人群,院子里的磨刀石会一直工作到拂晓,每一个革命军身上都沾满鲜血。“他们,由于长期受到那可怕魔法的迷惑,已变成了野兽,在红旗下,在宣布了他们的国家处于危急之中后,动乱不已”。与之相对的是被关押的贵族显得优雅、从容、冷静。被复仇烈焰吞噬最深的德发日太太最后也因复仇而死,保留了一丝人的理智的德发日先生得以存活,这种艺术处理也非常耐人寻味。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双城记》中的现实主义意蕴并不是教唆人们去“革命”,而是揭示了一个“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样一个公理。作者极度憎恶掌权者对弱势群体的压迫剥削,但也不推崇被压迫者的暴力式革命。《双城记》写了伦敦与巴黎两座城市,作者极力渲染巴黎发生大革命以后的惨状也隐隐地规劝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统治者不能再继续盘剥人民,否则也会迎来法兰西贵族同样的结果。同时也告诫英国人民暴力革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因此不可以暴力革命。这种崇尚非暴力仁爱思想的底层逻辑就是作者所秉持的人道主义原则。这种原则也充当了《双城记》宗教与非宗教意蕴之间的桥梁。同样的原则我们也可以在与狄更斯同时期稍晚一些的另一位大师——列夫•托尔斯泰身上见到。
三、人道的光辉——怜悯与被怜悯
人道主义指一种强调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的思想体系。在《双城记》中,这种肯定体现为作者超阶级的怜悯。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也就是恻隐之心。而这种怜悯就接近我们所说的“恻隐之心”。
弱者与受苦难折磨者是值得同情的,这一点与基督教义中的拯救意识接近,然而却并不一致。基督教讲求“因信称义”。只有虔诚地笃信上帝才能成为义人,成为义人是得救的前提。当审判日降临之时,经过天使的拣选,一切义人将升上天国,而不义之人将堕入地狱。所以不义之人也是不值得拯救的。然而在《双城记》中,狄更斯的怜悯却无私地施与了所有人。他对处于压迫之下艰难的平民保有深切的同情,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情一个马上要被处死的贵族税务官:“如果这个七十多岁的不幸的罪孽深重的人,还不明白这个理由,只要他能听见这回答的喊声,就会打心眼里明白过来”。尽管他曾经视人民为牛马,在愤怒而扭曲的人潮面前,这个贵族税务官也只是一个可怜的老头儿。在狄更斯看来任何剥夺他人生命的做法都是不可容忍的,包括革命者以革命的名义剥夺这位贵族的生命。
这种人道主义的二律背反也集中体现在德发日太太身上。德发日太太是一个颇具现实主义悲剧性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是在作者笔下完全丧失了怜悯心的形象。她全家被侯爵屠戮殆尽,以遗孤的身份在圣安东隐姓埋名数十载,她存在的全部意义似乎就在于向贵族复仇。作者对这个可怜的女人依旧施与了同情,然而德发日太太的复仇却在大革命开始后一发不可收,逐渐走向失控,她本人也走向疯狂,甚至不断地牵连无辜。她完全不念及马内特医生昔日救人的情分起诉了达奈,使得本来已经脱险的达奈又一次坠入绝望的险境。甚至在得知露西一行人可能会逃走之后,决定背着德发日先生处决掉这些人。德发日太太的冷酷甚至让自己人感到害怕。同为革命军的雅克三号“出于极度的畏惧,才对她那样尊敬。”丈夫德发日先生也觉得她做得太过火,然而她却认为“德发日无疑是一位好同志,然而他却不可原谅的同情一个贵族!”在作者第三人称的叙述中,“她绝对没有怜悯心。即使她曾经有这种美德,也荡然无存。”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革命领袖最终死在了追击露西一行人的路上,而且是被自己的配枪打死的。这样的结局无疑蕴含着作者的个人情感,反向论证了《双城记》的人道主义立场。
四、结语
我们可以看到,仅仅从某一个视角来审视《双城记》都是片面的。这部作品由宗教成分、非宗教成分以及人道主义底色三个部分构成。这同时也解释了作者在若干对人物关系中表现出的看似矛盾的立场。
然而我们还是要明确一点,《双城记》蕴含的这种复杂意蕴是有其局限性的。在作者看来,只要每个人都秉持着仁爱之心,世间就不会有苦痛不会有压迫,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幼稚的观念。作者“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对贫民表示同情,对贵族表示痛恨。但是在革命胜利之后,狄更斯又对贵族表示同情,并反对农民阶级的武装反抗。”[2]每一场暴力的社会变革都是旧社会积重难返的产物,是阶层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的集中爆发,这种血腥的冲突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一路走来,有权势有地位者不会良心发现地停止剥削下层民众,即使偶发善心也只是在不触及自身利益的范畴之内。下层民众也不会停止怨恨当权者的剥削,如果民众没有反抗,不代表民众不怨恨,只代表民众的怨恨还没有积蓄到暴力反抗的程度。从这一点来看圣安东区人民的暴动是必然的,巴士底狱的沦陷也是必然的,这是封建法国蜕变成现代法国不可避免的过程之一,田园牧歌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继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属于工业的时代。但这并不代表狄更斯的观念就毫无可取之处,心怀仁慈,博爱地处事,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值得赞扬的。
注释:
①引自《圣经•出埃及记》.
②引自《圣经•马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