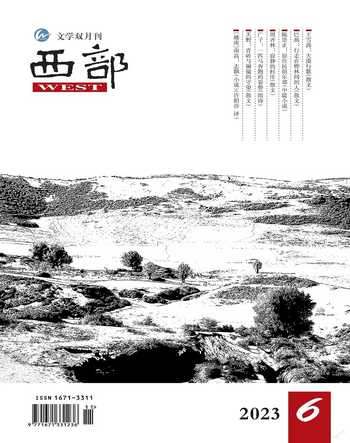包袱(短篇小说)
2023-12-18王棘
王棘
如今他又回来当搬运工了。他还是像以前那样,每次都比别人多扛一个袋子,别人坐下来休息时他也不停,只偶尔喝上一口冷水,就算是歇息了。他还是穿着那双黄色帆布鞋,裤子上的洞也还没补——比以前更大了;上身是军绿色的秋衣,看上去也有些年头了,袖口、领口都已磨破,背心处显出一大片黑色,那是汗水打湿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布紧贴着他的皮肉,隐约可以看出他那笔挺的脊柱,还有背上的条状肌肉。
他以前认识的、和他一起在这里干活的那帮人,现在只剩下明德一个人还在这里扛包。中午吃饭时,明德跟他说,在他去矿上的这一年,以前的那帮兄弟,全都陆陆续续去干别的营生了,有回村里的,也有去别的城市的。明德说他也是刚回这儿搬货才十多天,他去建筑工地当了半年小工,只拿到五千多块钱,后来包工头也跑了。明德还说他曾卖过水果、贩过粮食,可似乎他干哪行,哪行就不景气,后来实在没本钱可赔了,一时又找不到其他营生,就只好又回这儿来了。这儿辛苦是辛苦了点,但每天都能拿到现钱。明德问他怎么也回来了?
他说他们那个矿塌了,“埋了两个人,消息让人捅出去了……”。明德听着点了点头,说他之前也考虑过去矿上,但他老婆死活不让他去,说是那里面太危险。“她宁愿让我少挣点,也不想我去冒那个险。其实想来也挺有道理,咱们这儿的矿基本上都是黑窑子,没一个正规的,那玩意儿,简直就是拿命作赌注呐,”明德说,“我这人胆子小,可不想英年早逝,我还有娃娃要养活呢。”
他只说了一半的真话,他们那个矿的确发生了塌方,埋了两个人,但消息被压下去了,矿上分别赔了那两家家属三十万元钱,这事就当是没发生过了。他之所以不再去矿上,主要原因不是这次塌方事故,是家里的事,他不愿让别人知道,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塌方事故发生后,矿上给他们放了三天假。他以前都是月底发了工资才回家,他想到这次可以在家里多待几天,工友死亡给他带来的阴郁沉闷的感觉稍微缓和了一些。回到家里,他看到孩子一个人在炕上躺着,这孩子不哭也不叫,他扮鬼脸逗他,他才露出一个笑脸。他坐在炕上等了十多分钟,还不见孩子妈回来,他想她估计又去打麻将了,可这样把孩子独自扔在家里的行为实在有点不像话,万一孩子打翻水壶烫着怎么办?或者是外面的人进来,看到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门还大敞着,把孩子抱走了怎么办?他又想到他去矿上不在家的日子她就是这样看孩子的,心里的那把火越发熊熊燃烧了起来。
他来到院子里,房东那只灰色土狗看见他高兴地发出嗷呜嗷呜的叫声,他看到房东家的门虚掩着,里面也没有打麻将发出的声音。她一定又去外面玩了,他心想,拳头握得更紧了些。“狗日的!”他骂了一句。他走上台阶,推开门走进房东家,心想着问问王哥知不知道她去哪儿了。接着他就看到了那幅画面。可能是听到他的推门声,他才从她身上下来。他看到两具慌乱、赤裸的肉体,迅速退了出来,下意识地以为是王哥从外面带回来的女人。他退出来后,慢慢觉出不对,他虽没看清,但那个女人的反应不对。是她,他猛然醒悟。他站在门口等着,过了有五分钟,房东打开了门,他看到跟在后面的她,可不是她么!他一拳将房东打趴在地上,他试图站起来时,他又一脚将他踹倒。女人一声不吭,冷漠地看着他们。房东趴在地上不动了,等着他的拳打脚踢。他看到女人嘴角露出一抹鄙夷不屑的笑,他一把揪住她的头发将她拖回到他们住的南房里,给了她一巴掌。她跌坐在地上,还在笑着,吐出一口血唾沫。孩子就坐在炕上看着,他的脸上也带着笑意。他的儿子是个傻子,他的老婆是个婊子。他一下子泄了气,坐在灶台上无力地说:“明天就搬家,这是最后一次。”她从地上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坐到炕上,什么都没说。
天黑后,明德说什么也要拉他一起喝一杯。他跟着明德来到他家,明德向女人介绍了他,“这是兴东,”明德拉着他的胳膊让他坐在椅子上,“就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的,搬运站最能受的那个,记起来了吧,他两年前去了矿上,现在又回货运站来了,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们竟然还会见面,这就是缘分吧。你快給我们弄几个菜,我们得好好喝一顿。”
女人让他们先坐,“我这就去给你们准备下酒菜”。他看得出来,这是个贤惠的女人,他们夫妻之间感情也很好,他能从他们对视时的眼神看出来,他又想起明德说他女人不让他去矿上的那番话,他有点羡慕明德了。
明德拿来了酒瓶和酒杯,不一会儿女人从厨房端出来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他们便喝开了。他问明德怎么还没孩子吗?“在学校里呢,”明德说,“他住校,只有周末回来两天。”
“读初中了吗?”他问。
“嗯,今年刚升初一。”
“看不出来你的孩子都这么大了,看上去你比我还年轻些。”他说。
“我属虎。”
“我属耗子,”他说,“你比我小两岁。”
“我结婚早。”
女人又给他们端上来几个菜,他跟明德说叫弟妹一起吃吧,明德喊着问女人还有菜吗,没有的话一起吃吧。“还有一个,”女人在厨房里大声回说,“你们只管喝你们的,不用管我。”
“咱们喝咱们的,”明德说,“她说不用管她。”
“兄弟你命真好。”他发自内心地说。
明德问他在矿上那两年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每天都提心吊胆的?那次事故发生时你在干啥?你看见那两个人的尸体了吗?”
他喝了一口酒,说一开始那几天是有些害怕,但后来就习惯了。他告诉明德死的那两人是爆破组的,他是装车组的,离得比较远。“只听到一声轰隆声,我们都以为是正常作业,后来才听说有两人埋在里面了。”他夹了一筷子菜,“尸体我们没看见,我估计不一定找得见,他们怕再塌了,那两个可怜鬼连祖坟都入不了了。”
“也是他们命不好。”明德说。
“是啊,”他说,“都是命。”他觉得自己的命也不好。不过他转念想到,既然是命,那你就受着吧,抱怨也没用,该干啥时干啥,一切都是注定了的。“尽人事,听天命吧。”他说。
他们一直喝到八点多,明德要骑摩托送他回去,他不让,他说他走着回。“咱们俩都没少喝,”他拉着明德的手,不让他去推摩托车。“我不用你送,也没多远,不要让弟妹担心。我走着回去正好在路上清醒清醒。”
明德和妻子一直将他送出巷外,他走出去一百来米,回头看到明德正佝着身子在路边呕吐,他的妻子在旁边帮他拍着背。微风拂面,他脸上的汗被吹干了,一路上他回想着在明德家之所见,他觉得那才像是一个家,是丈夫和妻子的正常相处方式,他又想到自己,他觉得自己真是可怜,他从没从她那里感受到过一丝丝爱意,她是一块捂不热的石头,他就算把她揣在怀里含在口里,她也还是一块冷硬的石头,她不懂得爱别人,从来只想着自己舒服、快活,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她除了自己,谁都不爱——就连她自己生的孩子她也不爱。
他越想越气,停下来,坐在路牙子上抽烟。他一连抽了四五根,后来他站起来时感到一阵恶心,他扶着一棵树呕了几次,但什么也没吐出来,他的脑袋里越发昏,继续蹒跚着往家里走。他感到口渴难耐,不知道还有多远,脚下的路似乎旋转倒挂了起来,他在倒立行走,他眼里看见的一切也都头尾倒置。一切都是假的,他心想,没有什么是坚固牢靠的,就连土地也不是。
他进家后,先喝了一大缸冷水。他坐在炕沿上喘着粗气,此时两个孩子已经睡着了,他们头挨着头,并排躺着,他趴下来把脸贴在小儿子的头上,他的脸感到一阵温热,这个才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个傻子。她坐在地上的板凳上看电视,他起来将电视关了,双手抱住她的腰将她往炕上拖。她扭动挣扎着,后来她一把将他推倒在地,他像一摊烂泥般跌倒在那儿,他知道,无论如何,他们之间这场无声的战争最后都是以他的惨败收场。他双眼迷离地看着她上了炕,她一件一件地脱衣服,像是在表演一般,脱得一丝不挂。她站了起来,迈动脚步,走到炕的另一边,将电灯拉灭。现在她躺下了,钻进了被窝。他似乎能听见她的呼吸,她的心跳,他的眼前又現出她那丰腴的肉体,他扶着凳子站起来,摸索着上了炕。
他脱光衣服,钻进她的被窝,爬到了她的身上,他感觉自己的肉紧贴着她的肉,她没反抗。她的头歪在一边,她从来都不看他,他有些生气,仿佛内心蒙上了一层屈辱的薄雾。他停下来,用右手掐住她的下巴将她的头掰过来,他趴下来将头顶在她的头上,他们眼对着眼。
从他们搬到这里后,他在家里闲了十多天,他是要看住她,他不让她出院门,那十天里他们一句话也没说,每天晚上,他都会如今夜这般钻进她的被窝,不管她愿不愿意。第一天晚上,他一直用手捂着她的嘴巴,摁着她的头,让她面对着自己——至少姿势上面对着。有时他也希望她再次怀孕,一是因为李聪是个傻子——他终于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他想再要个孩子,一个正常的孩子;还有一个原因,他想着她若是怀孕了,可能会收敛一些。
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房东从她身上下来的那一幕,这是他第一次抓到她的现行,之前在村里,人们就传说她和别的男人有染,他一直将信将疑,现在他开始相信那些传言了。她一直都不是个守本分的女人,不然也不会未婚先孕,他们结婚后不到七个月她就生下了李明,他是在她的肚子显出来时才明白过来她们家为什么那么急着把她嫁给他,并不是看中了他这个人,而是为了避免那耻辱在自家暴露。他们也怕丢人。
她倒是从来都无所谓,似乎根本就不懂得羞耻为何物。完事后,他仍压在她的身上,后来他睡着了。他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把他推下去的,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在自己的被窝里,身上盖着被子。他起来烧火做饭,她还在睡着,他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装睡,他不去管她,他把饭做好,自己吃了,把剩下的热在锅里,然后便出发去搬运站。
路上他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有点贱,别人家都是男人在外赚钱,回家后女人侍候男人,他呢,不仅要赚钱还要侍候她,侍候她也就罢了,她还给他戴绿帽子。最后,他只能归结为自己命不好。
只有白天在货运站干活时,他什么也不想,暂时把所有烦恼都忘掉了,他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手上、肩上和要扛的麻袋上,他不知疲倦地在麻袋与汽车之间来回着,汗水将他的秋衣全都浸湿后,他干脆把它脱下扔在一旁,光着膀子扛,他的肩膀磨出了血也浑然不觉。后来还是明德强拉着他到阴凉处,他这才稍微歇息了一会儿。明德将自己擦汗的毛巾扯作两半,把其中的一半给了他,让他垫在磨破了的肩膀上。“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干活的。”明德说。有人打趣说他是钢铁之躯,干活机器。“他永远也不疲倦,是这里这伙人中精神头最大的,比他年轻的也不如他挣得多。”另一个人说。
五天后她跟他说了第一句话:“我要吃烤鸡。”这场冷战就这样结束了。他出去给她买烤鸡,他知道自己不能拒绝她这个要求,她虽是过错方,但永远是常有理的那一个,因为他比她更害怕失去,害怕失去这个家。
孩子们也像是收到了那个破冰的信号,一如燕子感到春天来临一般,他走出家门时听到李明高兴地说今晚要吃鸡肉了。“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吃过鸡肉了啊?”孩子问他妈。他没听见她说了句什么,孩子们又欢快地叫了起来。
他就着一只鸡腿喝了一小盅白酒,她问他前几天在哪里喝成那样醉醺醺的?他跟她讲了明德请他去他们家的事。她问他用不用回请一下?他说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可能是看他喝了酒,这天晚上他们吃完饭后,她破天荒地洗了一次锅。
这天夜里,他从女人身上下来后,平躺在她的身侧,在回自己的被窝前,他附在女人的耳边低声说:“赵二花,你是我的女人,你给我记住了,你若是再让我发现和其他男人勾搭,那就不是一巴掌的事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到时会如何做,他的目的是让她知道,这次就算是过去了,但绝不能再有下次。她什么也没表示,后来他快要睡着时,她突然又钻进他的被窝,紧紧抱住他的身子,这一瞬,他以为她回头了,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脖颈,他们相拥着沉入睡眠之中。
半个月后的一天,她跟他说让他把李聪送去幼儿园。他说李聪那样,送去幼儿园不是白花钱么。她说白花钱也得送去。“我受不了了,”她说,“他不断地在我眼前晃悠,我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现在一看到他我就心烦,哪怕我出去找点活干赚他的学费也成。”
他低头看了看他的小儿子,他双眼茫然地看看父亲,又看看母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的嘴里流出涎水,他到现在还一句话也不会说。
“那好吧,我们把他送去幼儿园,希望那里的老师能教会他点什么。”他说。
“我看够呛。”她悲观地说。
他们不再说什么了,每次说起这个孩子,都会让他产生一种被老天愚弄的感觉,他心想自己按说也没做过什么缺德的事啊,为什么所有不好的东西全落在自己头上。他回顾自己这三十多年的人生,赫然发现自己一直都是被迫做出选择,一次次无奈地接受着命运向他抛来的一个个包袱。
“要是生他的那天晚上,那个接生婆没倒提着他的腿猛拍他的屁股的话,他可能活不过来。”她说,“我有时想,他现在这样活着还不如当初不醒过来呢。”
“谁也没想到他会是个傻子。”他仿佛又看到那天晚上自己站在门口焦急地走来走去的身影了,当他听到那声“哇”的哭声时,内心是那么地激动和高兴,如今那些情绪全都被酸楚与不甘取而代之。他是没有未来的,有时候这样的想法会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我们都是没有未来的,我们同在一条船上。
六月初六、初七、初八这三天城里有庙会,前五六天,他从那条赶庙的街上路过去货运站时就注意到已经有不少商贩开始支摊子了,这是这座小城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人们俗称“六月庙”,这几天的街上,甚至比春节时的人都多,各种卖衣服的、卖吃食的摊子沿街摆开,除了这些,还有“鬼屋”、蟒蛇表演,以及海盗船、碰碰车等新奇玩意。他只陪她和孩子们逛了一天,第二天就又去货运站了,他没觉得有多大的意思,而且他发现她花钱太大手大脚了,只一天就花了六七百块钱,这差不多是他扛七八天麻袋才能挣到的。她像是泼水一般就把钱花出去了,似乎看见什么都喜欢,她从不考虑他赚这点钱时多不容易,他也不好说她什么,她一向都是如此,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能做的只有弯下身子去努力赚钱,有时候他想只要她好好跟他过就行。
這两天在货运站搬货的人几乎比往常少了一大半,不用说他也知道人们是去赶庙会了,明德也没来,昨天他就没来。后来庙会完了,明德还不见来货运站。开始他以为明德肯定又找上别的营生了,不会再来了。他有些伤感,这帮人里,他只和明德关系最好,也只有明德不经常拿他开涮,会拉着他到阴凉处歇息,他觉得这次明德有点不够意思,他就是不来了,也应该跟他打声招呼啊,他们那次喝酒时不是还互相称兄道弟吗?他闷闷不乐地将麻袋扔在汽车上,心想可能明德从来就没把他当兄弟,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那天中午他听见几个工友在议论明德,说明德在庙会期间骑摩托被一辆面包车撞了。他问:“是真的吗?”一个工友说:“不会有假,我那天亲眼所见,那辆面包车本来想跑呢,但庙会上人太多,他没跑成。明德的腿受了伤,是他女人追着拦住的那辆车,估计能赔他们一些钱。”
这天晚上散工后,他买了两袋奶粉和几斤鸡蛋来到明德家。他进去时明德女人正在院子里晾衣服,她对他的到来表现得很是吃惊,她把他引进家里,他看到明德正躺在炕上看报纸。“我听说你被车挂着了,顺路过来看看你。”他说,“怎么样?伤在腿上?”明德指着地上的椅子让他坐,女人给他倒了一茶缸开水。“这儿被撞了一下,”明德用报纸拍拍右腿上白色纱布裹着的地方,“估计得休养三四个月。”
“我见你庙会都过完好几天了还没回来上班,以为你又去做生意了,后来还是听赵小军说你被车撞了。”
“这下成了大伙的笑料了,”明德苦笑着说,“也是我骑车子不小心,幸运的是只有我自己受了点伤,坐在后面的老婆孩子都没事。”
“嗯,以后骑摩托可得小心点。”他说。
明德和妻子要留他在家吃晚饭,他说家里老婆孩子还等着他呢,“等你好了我再来和你一起喝酒。”他说。明德说这次他不方便送他了。他回到家里时,孩子和女人已经吃过了,他问他们吃了什么,李明说是从外面买的荞面凉粉。他给自己煮了一碗挂面。
“现在村里人估计正在锄第二遍地。”吃完饭看电视时他说。他想起在村里那会儿的日子,他觉得在村里与在城里是两种不同的活法,他更喜欢在村里,虽然种地不如打工赚钱,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总感觉自己不属于脚下的这片土地。当他穿行在城市的柏油马路上时,他感到不踏实,远不如踩在家乡的土地上自然,尤其是当他在太阳落山后往家走的路上,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这里并没有他的家,他们只是暂时寄居的人,他们随时都会无家可归。
“管他锄几遍呢,跟你也没关系了。”她不耐烦地说。
在村里时,她从不去地里,人们都说他娶了一个菩萨,他知道这是在挖苦他呢,他也没办法,她就是那样一个好吃懒做的女人,他若是多说她一句,她都会和他生气,又要跑回娘家去,他只能忍气吞声,一个人忙里忙外;她心情好时,他回家还能吃上一口便宜饭。
“明德的腿被撞断了。”他换了个话题。
“明德是谁?”她眼睛仍盯着电视机。
“一个跟我一起在货运站干活的。”说完,他站起来出了家门,她对他说的那些全无兴趣,他不想再没话找话了。他到外面的巷子里抽了根烟,他抬头看天,天上一颗星星也没有,他吐出一口烟雾,往巷口走去,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是觉得无聊,没劲。
这段时间,她忽然爱上了吃狗肉。她隔三岔五地炖狗肉吃,每次不等他走进家门,在巷口就闻到了空气中弥散的那股肉香味。他也跟着沾了光,在她炖狗肉的那些日子里,他回家后不仅不用再自己做饭,还能就着喷香的狗肉喝上一小盅酒。可能是吃了狗肉的缘故,他明显觉出对那事她比以前兴致高了很多,也更加主动了。
李明一开始是拒绝吃狗肉的,他宁愿吃干馒头也不喝一口肉汤。后来有一天她炖了一盆狗肉,骗李明说这次是驴肉,李明在她的再三哄劝下尝了一块,她问他好吃吗,他连连点头说“香,真香”。等后来他们告诉他他吃的是狗肉时,他已经深深地爱上这“驴肉”了,他说他没想到狗肉这么好吃,难怪那么多人喜欢,他不再承认自己说过的关于永远不吃狗肉的话。
七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他从货运站回到家里,看见家门锁着。他开门进家,坐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她回来,李明和李聪也没回来——按说他们早就放学了——他重又锁了门,出发去李明读书的学校,看门的老头告诉他说学生们早就走光了,教学楼也已经锁门。他又去了李聪所在的幼儿园,这次他没白跑,幼儿园老师怪他来得迟了,就因为他们家一个孩子,害得她等了这么久。他连连向老师道歉,领着李聪回到家里。他们还没回来,这会儿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他猜他们可能是回孩子姥姥家去了。他有点生气,她连声招呼都没打就走了。
第二天他送李聪去幼儿园后,又照常去了货运站,他心想今晚他们要是还不回来,他明天就到他丈人家去接她。这一天他都在心里寻思自己什么地方又惹着她了?她就这样一声不吭地走了。再说你走就走吧,怎么还带上李明,她这么一闹,李明又要耽误不少课程,而且还给老师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她做事怎么就不过脑子呢?
晚上他回家后,看到门上还挂着锁。他没进家就急急忙忙去幼儿园接李聪去了。幼儿园老师问他这两天怎么不见孩子的哥哥,“以前不都是他哥哥顺道带他回去的吗?”他说孩子哥哥这两天请假了,没去学校。他带李聪在外面吃了一碗羊杂粉,回家后他感觉这次跟以往不同,首先是这两天他们既没生气,也没打架,而且以往她跑回娘家从来不带孩子的。他的心里惴惴不安,总觉得不对劲。这天晚上一直到十二点了他都还在被子里辗转反侧,他想不通她这次是为了什么。
天还不亮,他就起来了。他开始做早饭,这些年来,他每天都是这么早起床,几乎从没睡过一次懒觉。从他们结婚到现在,每天的早饭都是他做,在村里时人们就都说他既当男人又当女人,就差自己生孩子了。他早已习惯了这些调侃,谁让他天生命苦,没别人有福气呢。早饭做好后,他叫李聪起床,帮他穿好衣服,让他洗脸吃饭,吃过饭后他送李聪去幼儿园。
他坐的是上午九点的班车,到老丈人家时已是十点多了。家里就只有他丈母娘一个人,她显然没想到他会来,问他怎么独自来了?于是他便知道赵二花没回这里来。他说前天赵二花没回家,他以为她回这里来了。
他看到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掠过一抹无奈、失望的阴影。“你们又怎么啦?”她说,“我前两天还说这两年你们搬到城里后好点了,你们这次又因为什么生气了?”
他说这次他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他说他早上出去的时候她还好好的呢,等晚上回去,她就没在了。“她已经两天没回去了。”他陈述道,“她还把李明也带走了。我以为她回这里了,她不回这儿还能去哪儿呢?”
“你再好好想想,”丈母娘说,“她在城里有没有什么朋友?”
“我不知道,”他说,“我每天天一亮就出去干活了。”他颓然地跨坐在炕沿上,下意识地从裤兜里摸出烟盒,点了一根烟。
中午老丈人从地里回来听他说了事情的经过后,一连说了两遍“胡闹”,最后叹了口气,说:“我们也没办法,从小到大,我们俩说话她从来不听,她有她自己的主意。我也能理解你的苦衷。”
他看着眼前的这个老人,听着他说出的这些话语,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她所伤害的远远不止他一个人。
老丈人让丈母娘出去买了一袋花生米,拿上酒瓶和酒杯说他这两年难得来一次,要好好跟他喝一顿。“你也别去想她了,说不定今天晚上她就回去了,”老丈人拿起酒瓶将两个酒盅倒满,“她要是想藏起来,你再怎么找也找不着她,还是喝酒吧。”
“您说的对,”他说,“我不找了,她要是回来,我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还接着以前的日子过下去,她要是不回来,我就当没有过她这个人。我说这话您可能不爱听,但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老丈人举起酒杯说,“其他的也别再说了,喝酒啊。”他们互相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大口。
后来他们谈论起今年的年头、庄稼的长势,他的话多了起来,虽然已经离开农村三年多了,可他对这些一点都不陌生,说起来头头是道,他说他骨子里永远都是个种地的。后来喝着喝着,老丈人躺下睡着了,他下地说他该走了,他跟丈母娘说要是赵二花这次真的不再回去的话,那他这是最后一次来这里了。丈母娘一直将他送到村口的候车室,她说就是她闺女不回去,他什么时候想来她们老两口也都欢迎他。
回到家后,他躺在炕上睡了一下午,醒来后他想起该去幼儿园接李聪了。这次没迟到,他到幼儿园门口时已经有不少家长在等着了。过了十几分钟,听到孩子们的叫嚷声了,然后他便看到他们欢快地从他身旁拥挤着过去,奔向那些等待着的大人们。他看到自己的儿子了,李聪木然地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还没看见他。他的心里涌上了一股难以言说的情绪,快步走上前,牵起孩子的手。
他从附近街上的大妈们口中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之前看到她和一个收狗的贩子很熟络,那人经常送她狗肉……他不再找她了,也懒得送李聪去幼儿园,每天不到中午就喝得醉醺醺的,一連六七天没去货运站。
她不会再回来了。确定了这一事实后,他像是放下了一个扛在肩上多年的包袱,心里感到一阵轻松,同时还有些不太习惯,但他知道,没有她他照样能生活下去。他扔掉了所有的酒瓶,拿起扫把着手打扫一片狼藉的屋子。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他心想。至少我还有李聪,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