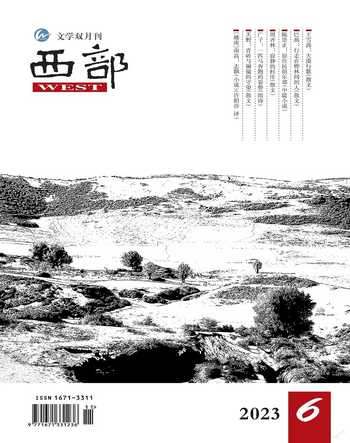两个孩子(小说)
2023-12-18石蓝/著许阳莎/译
〔越南〕石蓝/著 许阳莎/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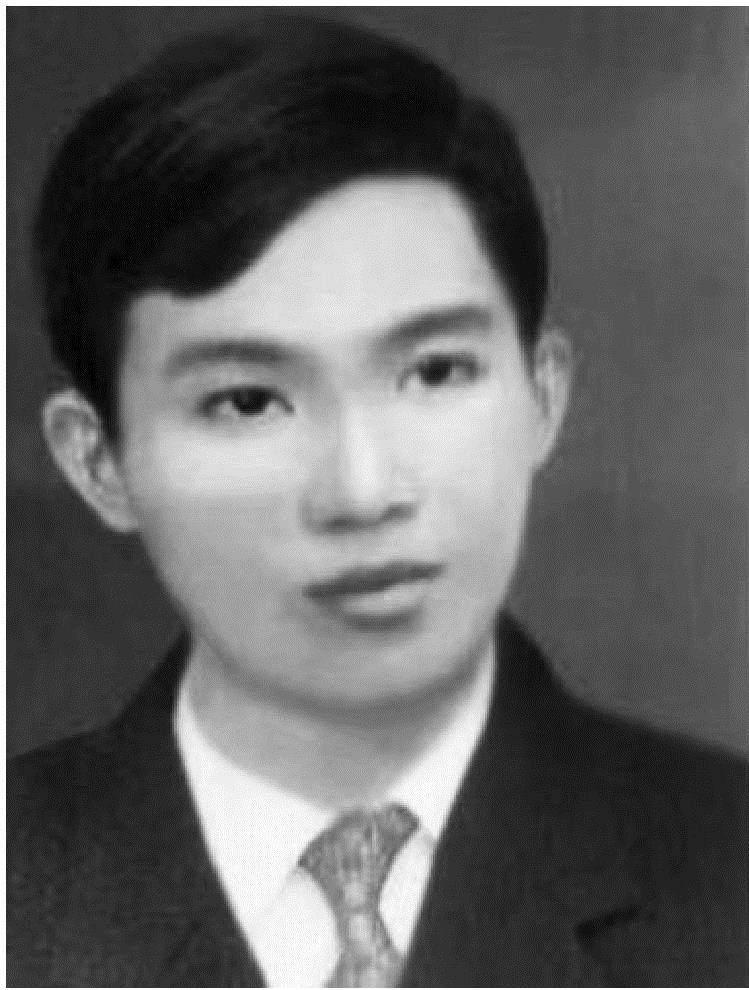
阮祥荣(1910-1942),后改名为阮祥林,笔名石蓝,是越南现代文学史上不可绕过的著名作家。石蓝原籍河内,生于官宦之家,是家中幼子。父亲阮祥襦为外交官员,母亲黎氏参亦是官宦世家之女。阮祥襦与黎氏参生有6子1女,其中阮祥三(一零)、阮祥龙(黄道)和阮祥荣(石蓝)都是越南现代著名文学团体“自力文团”的重要成员。石蓝曾中秀才,后来休学,1931年起跟随两位兄长从事报业,开始为《风化》《今日》《周日小说》等报纸撰写文章。1935年,石蓝担任《今日》报主笔。1942年,石蓝因肺痨去世,年仅32岁。
译者的话:
石蓝的小说多聚焦穷苦人在多舛命运下的生存状态,如乡村中的贫苦农民、繁华城市里艰难谋生的小市民、以体力活为生的人,尤其关注旧社会甘于奉献与牺牲的妇女。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季初冷风》《院子里的阳光》《两个孩子》,及长篇小说《新的一天》。石蓝的作品一般被归为现实主义流派,但与辛辣讽刺的南高、描摹黑暗的吴必素不同,石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以“温爱”观察和书写人间,他笔下的人物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下,都闪烁着如炬如烛的人性光芒,因此他的作品始终洋溢着仁爱心与人的心灵美。读石蓝的小说,可以读出每个在时代洪流里艰难喘息的小人物对彼此的爱重和友善,也能读出石蓝对他们平等的感同身受的爱。
石蓝在自力文团中自成一派。他以抒情小说见长,作品不注重情节,较少出现事件、变化与冲突,而是深入人物心理,状写缥缈朦胧的人物感受,笔触含蓄温情,轻柔细腻,情感浓郁。他极擅长观察、倾听万物隐蔽的脉动,因此能以极富形象质感与感染力的细节吸引读者。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不同,石蓝并不主张用文学呼吁革命、教化群众。他认为人性中隐藏着难以言说的偶然成分,会在某些细微琐碎的事件的触发下,改变人的个性、人格甚至命运。石蓝相信偶然是生活中的必要因素,他只想做一个提醒者、启发者,引导人们注意自己身边及心灵深处那个无限宽广、深邃的世界。那个世界或许正在隐秘安静地运行,但某一天会大放光芒,当人们认识到它的存在,也就认识到了人生的意义。
《两个孩子》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初越南一个平常的小镇黄昏,这里时间的流逝不以钟表上的分秒计算,而以更鼓声和天色的变化来标记,古老陈旧得像被隔绝在现代文明之外。从初更到持更,从晚霞漫天到黑暗笼罩,作家的笔如一个精密的变焦镜头,时而拉长至小镇俯瞰图、集市远景,时而聚缩至阿莲小小的铺子里、阿迪家微弱摇晃的灯影下。他们的身影和命运如同黑暗中单薄的灯火,如此渺小脆弱,不被看见。他们又如此向往光明,每天晚上9点到站的火车,是小镇昏暗日子里唯一的一抹亮色。火车带来城市的喧嚣和灯火,让阿莲短暂瞥见河内的一角,但那个世界陌生新奇、深邃无边,“使她思考一会儿便头昏脑涨”。火车驶过,他们最终还是隐没于黑暗,隐没于往日熟悉的蛙鸣、萤火虫、甘蔗渣与榄仁树的世界,这或许也是二十世纪整个越南乡村的真实写照。
小县里集市上空响起初更的鼓声,一声一声向远处震荡而去,呼唤着黄昏。西边的天空红似火烧,云和晚霞如将熄的煤。眼前村子里一排竹林渐渐黯淡下去,在天的布景切割出分明的线条。
黄昏,黄昏已至。黄昏静谧轻柔如一首摇篮曲,隐约可闻田野间轻风送来的声声蛙鸣。昏暗的小铺子里,蚊子开始嗡嗡作响。
阿莲静坐在黑色竹笼旁,黑暗渐渐浸透了她的双眸,乡村黄昏的忧愁渗入她纯真的心灵——阿莲懵懂不知何故,但她感觉在这白昼将逝的时刻,心似浮沉在广袤无际又朦胧难以言说的忧愁之中。
“姐,我把灯点起来吧?”
听到阿安说话,阿莲起身回答:
“再等等也行。你出来,来我这里坐,里面蚊子太多了。”
阿安把手里的火柴放在桌上,走出门外,与姐姐一起坐在竹榻上。竹榻下陷了些许,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这竹榻马上就要散架了,姐。”
“嗯,等我告诉妈再买一个新的。”
姐弟俩于是小心翼翼地静坐着,望着小街。万家灯火渐次亮起,卖粉的阿美伯家掛着的灯,阿九爷家曳动的美国灯,还有旅店里绿色的装饰灯……
各家灯火投射到街上,使沙砾闪烁发光,小石块一边亮,另一边又落寞地暗着,路看起来更加坑洼不平。
街上的集市早已散了。人亦散尽,喧嚣不再。地上只剩星星点点的垃圾,柚子皮、柿子皮、龙眼叶子和甘蔗渣子。一种潮湿幽幽气味升腾起来,白日的热气和再熟悉不过的尘土气味互相交织着,使阿莲姐弟俩以为这便是土地、家乡独特的气味。三三两两卖货晚归的人,正忙着收拾货摊,扁担既已系在箩筐,他们还站着互相再闲聊几句。
集市边几户穷苦家庭的孩子们弯身跪在地上来来回回寻摸着,捡拾几根薄竹,毛竹,或者卖货人留下来的任何有用的东西。阿莲看着他们,心中难抑恻隐之情,可她也掏不出钱给他们。
直到天色晦暗,阿莲姐弟俩才看到一个小男孩提着水烟筒,背着两只椅子在街上走过,他的母亲阿迪跟在后面,头上顶着一个竹榻,双手挑着满满当当的东西,那是她全部的货摊。
“阿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摆摊?”
阿迪把竹榻放在地上,逐个摆好喝水用的碗,良久才咂嘴回答道:
“哎,早点晚点又有什么差别,能挣几个钱呢!”
白天,她勤勤恳恳捕鱼捉虾,到了晚上才在榄仁树下、砖堆旁摆开摊子卖水。能卖给谁呢?那几个挑米的工人或车夫,偶尔还有县上的几个杂役兵,或有几个办事员喊人来打牌,兴致勃勃地跑来她的摊子喝一碗鲜茶,抽几杆老挝烟。钱赚不了多少,但每天傍晚她都来这儿摆摊,从夜幕初临一直到暮色四合。
她摆好竹榻和椅子,挪了挪美国灯,坐下开始包槟榔。小男孩则忙着点火煮茶。这时她才抬起头来和阿莲聊天:
“你呢,你还不摆摊吗?”
阿莲一惊,轻叫一声:“糟了!”随即站起身来催促弟弟:
“快进去关铺子,不然得给妈骂死了。”
阿安回答道:
“姐,今天妈不一定来。妈还忙着舂米嘛。”
每日天色将暗之时,阿莲的母亲都会顺路来铺子里看一看,她吩咐阿莲一到初更鼓声响起就关铺子。但今天阿莲怔怔看着街上竟忘了。
她赶忙跑进铺子里熄灭灯盏,收起黑色竹笼,阿安则去找门闩。姐弟俩照看的是一间小小的杂货铺,自阿莲的父亲失业,全家离开河内来到乡下定居,阿莲的母亲便张罗起这间铺子。铺子是从一个掉牙老妇那里租来的,仅用粘着日报的竹子隔开。阿莲的母亲让阿莲照看,她自己还忙着米店生意,晚上姐弟俩就在这里睡觉,守着铺子。
阿莲清点了老挝烟,把剩下的香皂装进箱子,口中一边喃喃算着账。今日是赶集日,但卖货收入仍少得可怜。
“中午你是不是卖给了阿力婆两块香皂?”
阿安想了一会儿,答道:
“对,她买了两块,还有阿之婆赊了半块。”
阿莲伸手去够算盘,开始数钱。但铺子里闷热异常,蚊虫肆虐,她迟疑了一会儿,把钱放进匣子里,说:
“算了,明天再一起算吧。”
阿安望着姐姐,就等着这一刻。姐弟俩匆匆忙忙,一心想关了铺门,坐在竹榻上欣赏街上的光景。阿莲掏出系在腰间银链的钥匙,把钱匣子锁上。她十分宝贝这银链和钥匙,并为此感到骄傲,因为这是她成熟、能干的象征。
“哈,小女孩儿在干什么呢?”
话音一落,便紧跟着一串吃吃的笑声,阿莲姐弟俩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进来了。那是阿诗婆,一个半疯的老妇人,常在阿莲的铺子里买酒吃。阿莲知道她的性格,便默不作声打了一壶酒给她。阿莲不敢看她的脸,心里有些发颤,只希望她快些走。
她端着酒,仔细打量了一番,发出清脆的笑声:
“呵,阿莲妹真乖啊,今天给我打了满满一壶。”
阿诗婆仰起头,一饮而尽,然后咂咂嘴,摸出腰包,掏出三个铜板放在阿莲手上,摸摸她的头,才拖着蹒跚的脚步而去。姐弟俩默然伫立,看着她吃吃地笑着朝村子的方向逐渐远去,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
天色开始黑起来了,这夏夜柔媚如丝,伴着缕缕清风。街道和小巷子渐渐被黑暗吞噬,各家各户大门紧闭,除了三五间商铺还亮着,微掩着的门隙透过一丝亮光。小孩子们聚集在路边说笑打闹,使阿安的心里蠢蠢欲动,盼望着能加入他们一起玩耍,但怕母亲怪罪他不听话,不好好看铺子,姐弟俩只能静静地坐在竹榻上,眼睛却始终停留在那些在黑暗中缓缓移动、晚归的人影上。
无边天幕上,繁星争相闪烁发光,偶有萤火虫低掠过地面或爬进树枝里,划过几道光痕。
阿莲和阿安静默无言,抬头望着星星,寻找银河和神农星后的鸭子座。对于这两颗稚嫩的心,宇宙深邃无边、奥妙无穷,而又陌生新奇,使他们思考一会儿便头昏脑涨。于是姐弟俩再次低头望向地面,望着阿迪的摊子上方摇晃的灯投下的熟悉光圈。往县城的方向,另一束微弱昏黄的光在黑暗中晃晃悠悠,时隐时现……
阿安指着那儿对阿莲说:“姐,那儿,阿超伯的粉摊到那儿了!”
扁担吱呀吱呀的晃荡声清晰如在耳旁,粉的热气随风迎面扑来。阿超伯走近了,他把扁担放下来,蹲下身子,重新点火,往竹筒里吹气。他的影子投在地上,一直被拉长到巷子两边的栅栏。
阿安和阿莲闻到粉的香味,但在这个小县里,阿超伯卖的粉是太过奢侈昂贵的东西,他们不可能买得起。
阿莲回想起在河内的日子,那时候阿莲的母亲还很有钱,她品尝过很多美味新奇的东西,还能在还剑湖边玩耍,喝那些红红绿绿的饮料。但记忆并不清晰,在阿莲的印象中,河内只是一片灯火通明、耀眼璀璨之地。河内有太多的灯了!自阿莲一家搬来这里,自有了这间小商铺以后,每天晚上她和弟弟都得坐在榄仁树下的竹榻上,与他们相伴的,永远只有周遭街道黯淡的夜晚光景。
夜对阿莲来说再熟悉不过,她并不害怕。
夜色已然完全成熟,通往河的路、经集市回家的路、每一条回村的小巷,都浸没在深深的黑暗中。此刻只剩下阿迪的一盏小灯和阿超伯的炉火照亮一小块地;在阿莲的铺子里,灯光微弱,稀疏的亮光透过竹篱。县里所有的街道现在都聚缩在阿迪的水摊处。还有盲人卖艺老伯一家,坐在草席上,白铁盆就放在面前,但他并未唱歌,因為没有人来听。
阿迪手拿着一根干枯的香蕉树枝,拂去货物上的苍蝇,缓缓开口道:
“这么晚了他们还不来啊?”
她说的是县里几个兵,老书记员的家人,她的熟客。阿超伯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今天那些先生家里有打牌的,他们用不着出来喊人。”
盲人老夫妇拉起独弦琴来,似加入他们的对话,琴声悠长绵延在静谧中。他们的小儿子在地上爬着,爬出了草席,淘气地拣出路边埋在沙里的垃圾。这些黑暗中的人们无比渴望某种光亮的东西,给他们每日贫苦的生活带来一点鲜活。
困意袭来,阿安和阿莲都已经睁不开眼皮。但他们还是强撑着再熬一会儿夜,然后再关门睡觉。母亲嘱咐他们要一直熬到火车停站——因为铁轨就经过他们铺子门前——再卖点东西,说不准还有几个人来买。只是一如每夜,阿莲从来不指望还有人来买东西,况且他们最多就买一盒火柴、两包香烟。阿莲和弟弟强撑熬夜有其他的缘故,他们等着要看火车。
九点,从河内来的火车会经过小巷,这是每天晚上最后的动静。
阿安已经躺下,把头枕在姐姐的腿上,眼皮马上就要落下,还不忘嘱咐姐姐:
“姐,火车来了要叫醒我。”
“嗯,你睡吧。”
阿莲为阿安摇着扇子,轻抚他的刘海。弟弟的头在阿莲的腿上渐渐沉重起来,阿莲静坐着不敢动弹。
透过榄仁树叶的缝隙,星星依然闪烁,一只萤火虫附在叶面下,黄绿荧光一闪一闪,偶尔便有榄仁花轻落在阿莲的肩上。阿莲的心平静不起一丝波澜,生出许多模糊而莫可名状的感受。
持更鼓声敲响,短促而干涩,并未传得很远,而后沉没在黑暗中。街上人影寥寥,只阿迪摊子前的椅子上有几个劳工坐着喝水,抽着老挝烟。但不一会儿,便有两三个人提着灯笼走出去,灯笼摇曳,灯火明灭,人的影子被拉长。那是几个旅店杂工,正要去接从省里回来的主人。阿超伯伸长脖子朝火车站的方向望,喊道:
“信号灯到那儿了!”
阿莲也看到青碧色的灯光紧贴地面,有如鬼火。接着火车汽笛声不知从哪里响起,在黑夜中被杳渺的风拉长。阿莲赶忙叫醒阿安:
“快起来,阿安。火车来啦。”
阿安站起身来,用手揉揉眼睛,好让自己完全清醒。
姐弟俩听到连绵的汽笛声,火车一直长鸣进入铁道岔。一股白烟从远方升起,紧接着是乘客的低声喧嚣。这几年买卖惨淡,所以在这里上下站的人也少了,有时候姐弟俩苦苦等待却不见半个人影。往日在火车站开有几家小饭馆,迎接到站的旅人,灯一直会亮到半夜。但如今全都关门了,火车站死寂黯淡,与街上的光景并无二致。
姐弟俩没等多久。汽笛声响彻云霄,火车轰隆隆地驶来了。
阿莲拉着弟弟站起来,看火车一节一节地从眼前一闪而过,每一节车厢都明亮如昼,连地面也被照亮。阿蓮匆匆瞥见气派豪华的车厢里人影高低攒动,铜镍器物亮闪闪的,就连玻璃窗也在发光。
继而,火车驶入黑夜中,留下红色炭火苗在铁轨上方飘飞跃动。姐弟俩还怔怔地望着最后一节车厢上车灯留下的红色光点,漂浮许久方才隐匿在一排竹子后边。
“今天火车上没什么人啊,姐。”
阿莲攥着阿安的手,久久没有答话。今夜的火车不似平常那样热闹,人少了,似乎也没有那么亮了。但他们是从河内来的!阿莲静默无言,放任思绪缥缈。河内遥不可及,河内明媚而欢快,河内喧闹而蓬勃。那是一个对阿莲而言迥异的世界,一个与阿迪姐的黯淡灯光和阿超伯的微弱火光迥异的世界。
黑暗仍包覆着周遭,这是乡村的夜。而外面,田野广袤无边又沉寂无言。
“好了,睡吧,姐。”
阿莲拍了拍弟弟的肩膀,在竹榻上坐下。阿安也坐下,头倚着姐姐的肩膀。火车汽笛的回声渐渐弱下来,终于消逝在黑暗中,侧耳也不再能听到。天上的星星仍在闪动。此刻小县才真正平复骚动,只剩下黑夜,剩下持更鼓声和犬吠声。
火车站的方向,夜影笼罩着归家的人影,阿迪姐正收拾货摊,阿超伯挑着扁担走回村子,而盲人夫妇不知何时已在草席上打起盹来。
阿莲回头,看到阿安也睡得正香,手里紧紧地攥着她的衣襟,头仍靠着她的肩膀。阿莲环视周遭的夜,凉风渐起,萤火虫早已消匿踪影。她蹲下来,把阿安搀进铺子里,眼皮也快支架不住。她小心把门闩好,把黑色竹笼上的灯拧暗,然后走到阿安旁边躺下。她把头枕在手上,闭上双眼。
白日的感受逐渐在她心里沉淀平息,她周围世界的影像也渐渐在眼中模糊起来。阿莲感觉自己活在一片莫测的缥缈之中,就如阿迪的小灯只照亮一方狭仄的土地。但她只想了一会儿,眼皮便沉重起来,继而浸入静谧的梦乡中,静谧如街上的夜,沉寂而充满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