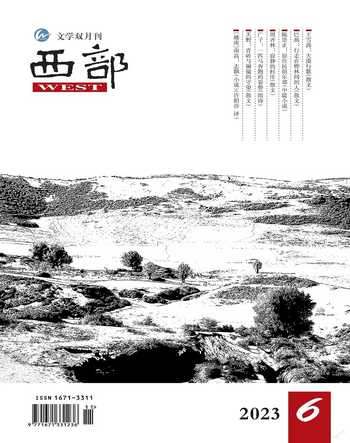醋缸(散文)
2023-12-18孙童翌
孙童翌
我在爷爷家后院的木头门前烧干草和干树枝,火苗蹿起来,我得用手里的铁锨压住。黑烟熏得我直掉眼泪,三奶远远叫我,招呼我过去。醋坊酿的醋好了,她在醋坊正带着人挖醋糟,沉淀原浆。
尝尝,酸不酸?我伸过手去接,手还没收回来,就闻到浓浓醋味。三奶催着我往嘴里尝,我只尝了一小口,就酸得不得了,脸都皱在一起。
最近几年,这个原本安静的小村庄被打造成了旅游景点,各地的人蜂拥而来。开始建起博物馆、古戏台、四小作坊,复原了过去的一些村落古迹。那些在游客看来新奇、特别的展品,其实都是我小时候玩过、用过、吃过的寻常物件。
我从小跟在爷爷屁股后面听故事。春天的第一缕微风吹起羊圈顶上用红砖头压着的油毛毡,我趴在窗台上听爷爷讲1950年那个寒冷的春天;夏天拖拉机的突突声响彻整个村庄,我拎着大茶壶坐在阴凉坡里,爷爷和一起种地的人在旁边说些酸话;秋天村民都在收麦子和鹰嘴豆,爷爷给我一根长树枝赶羊,一路编些神神鬼鬼的故事吓唬我。冬天漫天雪花落在地窖盖子上,爷爷从地窖里挖出来洋芋给我和奶奶烤着吃,讲他们俩的爱情故事。奶奶很少唱歌,只在那时唱一首我没听过的红歌,调子大约像是“洪湖水浪打浪”之类的。我小小的脑子里装着千奇百怪的故事。
我从没听过三奶讲故事,我凑在三奶跟前求她给我讲故事,讲酿醋的故事。三奶的故事很长,长到我觉得一个人不该有如此漫长、丰富的一生,怀疑大多是编造出来哄骗我的。
三奶的老家在甘肃,和爷爷当时一样,都是逃难来到新疆。整个村子的人都为了填饱肚子而发愁,勤劳的人家夏天挖些野菜,忙忘了的人们,只能苦苦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
三奶的姑姑家孩子多,农忙了整整一个夏天,来不及存储些过冬的粮草,等到冬天真正到来的时候,一家人忍饥挨饿,等不到第二年燕子飞回房檐下。因为寒冷,又没有充饥的食物,人只能躺在炕上,在并不厚的被子里露个眼睛。长久保持一个姿势,慢慢地,眼睛不聚光了,最后彻底失去神采。
三奶家早早备下了野菜,煮了吃一个冬天,倒也能充饥。没有面粉就搅一点糊糊喝,稀饭也只放小小的一把米。我没吃过苦,从来没想象过这样的场景,在我家喝稀饭或者糊糊,都是就着馍馍炒菜。我就问三奶,汤太稀的话,为什么不就点馍馍。三奶笑了,爷爷也笑了,还有围坐在一起的人都笑了。我才突然意识到,连熬稀饭、烧糊糊的米和面都没有,又哪来的大馍馍呢?
三奶总有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我疑心她是讲出来逗我玩的。说在当时,有一个人给有钱人家做饭,每次和完面都不洗手,等回到家把手浸在锅里,用手上沾着的面粉烧一锅糊糊给家里生病的婆婆喝,维持生计。有一天大雨倾盆,等女人回到家时,手上的面粉全被雨水冲走了,女人在院子里痛哭。
“来新疆后生活就变好了?”
“变好了呀,人都能吃饱了!”
到新疆后迎接我们的,是热情的大队领导和邻里亲朋,即能吃饱肚子,也住进了能挡风遮雨的屋子。
爷爷来到新疆后,种起了地,养起了猪,还娶到了朴实勤快的媳妇。三奶来到新疆后,学了酿醋的手艺,也勉强维持住了生计。三奶的酿醋手艺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前几年,为发展旅游打造的四小作坊才建起来的时候,专门找了三奶酿醋。一酿,就酿了许多年。
我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看着爷爷家后门那块地,从草窝变成作坊。十几年前,那里还是荒地的时候,长满了杂草,各种各样的野花在杂草中间开着,我要想摘一两朵好看些的花回来,裤子上必定要粘上许多苍耳草。草窝里常年拴着一头驴,那驴总在我午睡的时候梗着脖子大叫。后来想想,大约是因为我午休了,它隔着院墙瞧不见我,才昂头大叫。等我也昂起头回它一句,它也就不叫了。搞得十里八乡都知道了,李家的孙子会学驴叫。
四小作坊具体是哪四个我有点记不清了,原本的旧民居被分割成好几间,放着打铁的工具、柳条编成的小筐、蒸馍馍的笼屉,还有好多超出我认知和记忆的旧玩意儿。好几次我带朋友去参观的时候,那些玩意儿就用“旧农具”这个称呼一带而过了,再也没有像小时候那样拿起来摆弄过。
另外几间连排的屋子从中间打通,满墙画着酿醋的工艺步骤,连同酿造工具大咧咧摆在那里,倒也不怕旁人偷学了去。后来三奶说,那技术没个三五年的实践经验,学不到精髓。
我溯不清真正酿造技术的源头,只知道当时大多数人家,都有自己酿醋的老手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渐渐都失传了。当时,庄稼人打完场,家里都有收获的麦子和麸皮,混合调味,发酵后便是醋糟,醋糟再经过沉淀得出原浆,原浆经过熬煮才有了醋。这是我仅凭眼睛看、耳朵听,粗学到的酿醋过程,但真正动起手来,怕是我这个半瓶子晃荡的水平,只酿得出糟,酿不出醋来。
又过去好多天,等醋都沉淀好了,醋坊的人又叫着三奶去煮醋。干柴被烧的在火炉里噼里啪啦炸开小花,醋蒸汽氤氲缠绕在屋子里窜来窜去,把在场人的衣服都熏的酸溜溜的。我身上也沾了醋味,但却不觉得那味道难闻,我把袖子蒙在鼻子上使劲闻。醋味和洗衣液残留在衣服上的味道混在一起,加上水汽蒸腾,使我突然想起在南方念书时,那个雨下不停的傍晚,在宿舍楼下的小食堂里吃的一碗酸汤馄饨。
所有流程走完,酿好的醋被封存在一口大缸里,和爷爷家盛水的大缸不太一样,这个缸的缸壁更厚,也够深。三奶说,沉到缸底部的醋汁最浓郁酱香。几个女人围坐在大缸旁边用瓢舀醋,拿小篓子分装,装好了在景区的篝火晚会上卖。我眼巴巴看着,既不插手帮忙,也不舍得就这么回家去,听着她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被那香味吸引,脚下不自觉越凑越近。三奶装到最后一篓的时候,数了数装好的数目,朝我咂了咂嘴。
“赶紧来,尝一尝,好醋,酸酸的!”
我几步走近,因为太迫切而差点同手同脚了,佯装镇定地将嘴唇靠近三奶手中的瓢。浅尝已经满足不了我当下馋嘴的贪念了,我毫不客气地喝进一大口,酸得差点蹦起来。又酸又辣的感觉刺激着我的唇齿,经过咽喉,最后流进胃里,在我的胃里燃烧,像火一样。但随即嗓子里又渗出细腻绵长的粮食的味道,温温柔柔将那辛辣、酸麻包裹起来。我竟舍不得咽下去,这劳动人民最朴实的智慧成果震撼着我,一时间我竟分不清,哪个才是真正的醋味了。
三奶舀着分装完的满满一缸醋,嘴里仍不停说着,极力向我们展示那满屋飘着的一篓一篓醋的味道,是多么香醇;那黑得发紫发红的一缸一缸醋的颜色,是多么艳丽。眼睛不小心扫过那个大缸,缸壁上竟有一条细小的裂缝,裂缝处渗出一滴醋汁来。我脸皮薄,极力压制住自己想要伸出舌头去舔那一滴醋的欲望,终究还是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失败了。我的脸贴近缸壁,舌头飞速前进、后退,那滴醋终是进了我的嘴里,在唇齿间左拥右抱后,带着味觉的不舍,冲进胃里去。还未来得及脸红,我咂巴咂巴嘴,还是准备再去三奶面前凑一凑,企图再获得些口腹之欲的满足。
装好的醋一篓一篓贴上标签,在每周五、周六举行的篝火晚会上售卖。我躲在角落里,偷偷瞧着那些第一次品尝这种醋的人的神态。他们大多被醋的酸和辣吓退了,在尝到第一种味道的时候,就急着用手里的矿泉水去冲,冲淡了辛辣,也就等不到谷物香气的回甘。但也有人一下就尝到了,在阳光、土壤、雨水的作用下,竭尽全力生长出来的,每一粒粮食所带来的厚重的味道。他们在暗无天日的大缸里发酵,那些尝到味道的游客被那股力量鼓舞着,在熊熊燃起的篝火前尽情跳啊,舞啊。那是大地的力量,谷物传递来的,我们人类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力量。
我也湊过去,混在游客中间,拿小小的一次性纸杯倒些醋出来,好像醉酒的欢愉一般,融入人群中去,我身体里的味道也在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