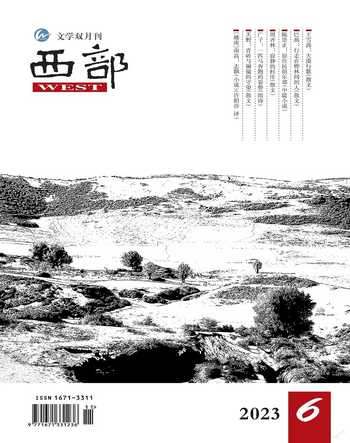大漠行歌(散文)
2023-12-18王雪茜
王雪茜
沙漠迷路与日月同辉
途中我们的车掉了队。目的地塔科1井似乎越来越远了。看不见任何油田的路标,手机没有信号,前面的三台车联系不上。我与同车的贵州作家陈丹玲都是第一次进沙漠,初次见到浩瀚的沙海,她不由脱口而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事实是既无人烟,更无狼烟,落日呢,更早着呢。掠过眼前的,只有或粗或细的胡杨,聚拢着身前或大或小的沙丘。交替闪过的还有开着粉红色细花的红柳、靠近路边的骆驼刺,以及枯黄错落的芦苇草格。胡雁声断,驼铃路赊,还真的是:“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
前一天从库尔勒去轮南时,在塔里木沙漠公路邊见到的青杨挺拔得令我吃惊,所有的枝叶一律紧密地向天空刺展,树身瘦削冷硬,好像随时准备出征的列兵。在西部,我见过的树大抵如此,馒头柳、圆冠榆、沙枣、槐树……可以统称为冲天树。而在东北,几乎所有的植物,即便是白杨,也都是枝条懒散、旁逸斜出。矿工诗人陈年喜送过我一本散文集,书名叫《活着,就是冲天一喊》。他说,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当天我们在塔里木河附近见到的那片胡杨林,无疑是这句话最恰当的注解。它们并不枝繁叶茂。有的看似枯死,没有一丝绿色,可根荄牢坚,枝干仍旧保留峭拔的样貌,苍劲有力,即便是最细瘦的弱枝也在冲天长啸。它们或如身披铠甲的武士,长矛在手,虎目炯炯;或如仰头的黄羊,奋蹄疾行;或如竖角的獐鹿,腾挪跳跃。而更多的胡杨半生半死,有的树身已枯,只在斜枝上鼓出一丛绿色;有的上下身皆已苍黄,却在树腹部刺出新枝。当地人称胡杨“三千年不死,死后三千年不倒,倒后三千年不朽”,想来树同人一样,也是有气节的。
俗世显达轻如土,凛凛风骨不可欺。
此时,我们已在大漠里盲转了四五个小时。漫漫黄沙无边无际,无论哪一个方向都是同样的样貌,寂静和焦虑像一张纵横交错的大网,越收越紧。我们再也无心对窗外的风景指指点点,也不再对发现的陌生植物大呼小叫。偶尔路过的运输车喘着气呼啸而过,只留下一股决绝的黄烟。
沙漠深处的路凹凸不平,我们的身体机械地上下颠簸,耳朵灌满了风声。更糟的是,我们的车发了脾气,发出拖拉机一样的轰隆声。“可能是消音器破了。”司机小方说。小方是个新手,不免有点紧张无措。车里一阵沉寂,我感觉身体的某一部分像车窗外炙热的光线一样抖了起来。
“兔子!”小方低声喊道。果然,车左前方蹲着一只毛色青灰的野兔,直愣愣地盯着渐近的车子。
“它是有多久没见到人了?竟不知道躲车。”
“可能它连自己的同类都很难见到吧。”
是的。在沙漠腹地,别说是人,连一只鸟儿都很难见到。
第一天进沙漠参观,刚过轮探1井时,一只全身乌黑的大鸟,从左侧的树林中飞出,越过公路,向高处的沙丘飞去。起初我以为是乌鸦,问了轮南2井的工程师,说是乌鸫。这让我着实吃了一惊。进疆前,我正读法国作家缪塞的小说集,在兰州转机间隙,恰巧读到小说集的最后一篇《白乌鸫》。我生活的鸭绿江口湿地是众鸟迁徙的“加油站”,鸟类资源极其丰富,却从未见过乌鸫鸟的踪迹。未料,机缘巧合,一入西部,就与乌鸫不期而遇。后来我知道,乌鸫是南疆地区常见的鸟类,它与乌鸦明显的不同处是,它的嘴是黄色的。
远远地,终于望见一座钻塔。此时在沙漠腹地望见钻塔的心情,不亚于在埃及见到金字塔。有了钻塔,沙漠就有了心跳,就永远不会死去。沙丘上出现了两个红点,红点渐近,是两个石油人,四十多度的烈日下,一人手执一卷图纸,一人身背一捆设备,不知在探测什么,像当初那些在沙漠中开山辟路、建塔设站的石油人一样,在大漠中,他们如一粒沙一样渺小,可在我们眼里,他们却无比伟岸,我第一次觉得生命是如此顽强而伟大,令人敬畏。
不记得哪位作家说,读懂了沙子,就读懂了生命。我想说,读懂了生命,也就读懂了沙子。
手机有了微弱的信号,时断时续。两天的沙漠奔行,我发现,有钻塔和采油树的地方,手机才会有一点信号。联系上队友,我们导航到当天的起始地哈得一联合站,会合后重新向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小镇进发。
车子一驶上柏油路面,立即停止了颠簸,心脏仿佛被柔软的绸缎轻轻拂过,久违的幸福感涌上心头。看了一眼时间:二十一点四十分。此时,视线右边的沙谷里仿佛忽然间金光漫溢,浑圆金黄的太阳渐渐靠近沙平线,视线左边的沙谷却被青灰色笼罩着,一轮与太阳同样硕大的银色圆月从云层里钻出来。在同一沙平线上,日月同辉,遥相呼应。俗世的一切烦恼刹那间烟消云散。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壮美的画面,我们惊叹不已,直觉感到,这一定是上苍对我们沙漠迷路的额外赏赐。
车行至沙漠公路288公里处,在左侧的沙丘半山腰上,赫然出现了两行醒目的大字: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而我,再也不觉得这不过是一句毫无温度的口号了。
大漠水井房与李乃君的口琴
大漠行车,常常六七个小时才能到目的地。看着天山就在前方不远处,却似乎怎么也走不到山脚。司机小方说,看山走死马。真的是这样。寂静塞满了每个空隙,像正午的温度一样越升越高。一片黄沙中,除了胡杨、红柳、骆驼刺、蓼子朴、苦马豆、蓬柴草等沙漠植物,见不到寻常花草。去桑吉途中,视线意外碰上了五颜六色的花朵,领队贴心地让我们停车休息。这些花儿种在沙漠路边的水井房前,填满了房前屋后,尽管只有蔷薇和太阳花,却色彩浓烈,开得正旺。
在塔里木,我觉得万物都竭尽全力,太阳和月亮远大于其他地方,水果的甜度值达到极致,天蓝得很不真实,云朵如同油画家随意涂抹的杰作,就连白昼都要拉长两个多小时,晚上九点半,太阳才会渐渐落下沙丘,我的身体和作息竟完全适应了这种错觉,夜半三更仍不觉疲倦。
这条沙漠公路每四公里设一个水井房,抽取地下的盐碱水浇灌路边的护沙植物。之前我们也路过几个水井房,要么房门紧锁,要么只有一条拴着的狗,落寞得眼皮都懒得抬。
我们一行人欢悦地涌向铁皮小房子。守水井房的是一对老夫妻,六七十岁的样子。他们从老家西安来到这里工作已经九年了。房前的土台上晾着新摘下的黑枸杞,六七平方米的房间里放着两张简易单人床,一只猫卧在靠墙的床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床边水桶里是新摘的枸杞枝。两位老人热情地邀我们品尝,我第一次尝到新鲜的枸杞,成熟的果实甜而不腻,甫一入手,便汁水横流,手指即刻被染成了青紫色。
水井房旁边是一间杂屋,摆着老人自己采摘晾晒的枸杞、肉苁蓉、锁阳、罗布麻、野西瓜等。这里离塔里木河不远,老太太每天早晨六点多出门拦车去塔河附近采摘,有时到八九点钟才能拦到车,采摘期只有短短一个月,他们靠卖这些滋补品贴补生活。“水每两周运来一次,每次两桶。”老太太说。相比于老头儿的沉默,老太太的话匣子一开,像是雨水季节塔河的水奔涌出来。大家围在老太太身边,听她介绍各种滋补品的功效,只一会儿工夫就把她的存货买空了。货架虽然空了,老太太的话却越发多了。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人,她兴奋得眼睛发光。
而我,却被她种的花草吸引了。在这样人迹罕至的沙漠地带,他们弄来这么多花土,想来是颇费周折的。他们为什么背井离乡,来到这荒无人烟的沙漠,甚至可能无法叶落归根,其中的缘由恐怕无人知晓。花儿自顾自开着,鲜有人欣赏,而让花儿落地生根,也许意味着老夫妻已经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临行时,加了老人微信,他的微信名叫“大漠6号井”。
每天吃过晚饭,不管多晚,我都要在周边走走,去寻找菜园子,看看油田人在沙漠里种下了什么蔬菜。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中,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热爱菜园子,如此珍惜每一种瓜果蔬菜。桑吉公寓、克深公寓、博大公寓,都有自己的菜园子,西瓜、甜瓜、豆角、黄瓜、南瓜、茄子、大葱、卷心菜、油麦菜、西红柿,应有尽有。也种玉米、向日葵、山楂、桃树。
“沙漠里色彩太单调了,我要种点菜。”库车负责种菜的阿布来提对我说。他是新疆本地人,三十岁,普通话不太熟练,腼腆老实。他挑了一只又圆又大的西红柿,塞给我。在菜园的一角,他种了成片的月季花,而库车公寓的大门外,是一片由向日葵和翠菊组成的花海。
在沙漠里填土,种菜种花,不也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吗?
我不禁想起,在参观库尔勒石油展览馆时,在各种岩心、钻头及各年代各式采油用具中,我的目光被一支青灰色口琴吸引住了。它孤零零地躺在那些冷硬的工具中,显得另类而渺小。尽管铜身斑驳,字迹仍清晰可辨,琴身左上角刻着几个繁体字:群众超级口琴。左下角的字是:原名石人望。右下角写着中央口琴厂出品。这是一支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厂的口琴,展品备注是烈士李乃君用过的旧物。我端详着李乃君的黑白小照,短发,戴着一顶红五星棉帽,眉眼敦厚,目光平和。
我急切地在网上搜索她,却只有只言片语。1958年8月18日,依奇克里克地质勘探区遭遇山洪袭击,五名地质勘测队员遇难,其中就包括李乃君。资料显示,依奇克里克油矿位于新疆南部,属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天山南麓的大涝坝区域。地质勘测队员们从1958年开始钻探依奇克里克构造,依奇克里克油田是在塔里木盆地发现的第一个油田。李乃君当时是塔里木地质队114队队员,毕业于新疆矿业学校,时年二十岁。
当年在没有路的沙漠,女孩们是如何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没有详细记载。只说,那里地质十分复杂,陡崖壁立,水沟纵横,从驻地到工作地点要走六七个小时,翻山越岭,跨沟爬崖,收工回来只能顺原路返回。有时她们返回较晚,遇到陡坎阻隔,只能在野外的沟底过夜,靠点燃梭梭草取暖熬到天亮。同事回忆她很能干,性情活泼,爱唱爱跳。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大漠的落日下,吹著口琴,眉眼敦厚,目光平和,望向黄沙深处。
人迹罕至的大漠,一抹绿色可以浓情如干邑,一朵鲜花可以燃放似烈火,而一支口琴同样可以让尘土吐露出星辰的声音。
沙尘暴与一卷手绘地质剖面图
在新疆,一天经历四季是常态。从塔中出发时,还是艳阳高照,刚过塔里木河,便见前方乌云堆积,像一群黑色的蛇四散游动,一会儿乌云又消散了。过轮南时,车前方一团浆白色尘雾由远及近,急速聚拢过来,刚刚还湛蓝的天空,完全被沙尘暴吞没了,雪白色的云朵亦被这一团呼啸而至的暗白色沙尘裹住了。风不大,没有想象中飞沙走石、黄沙弥漫的场面,路两边的沙尘被风的手捋出一缕缕白烟,贴着路面波纹样追着前车的尾巴飘散而去。能见度越来越低了,路两旁的植物也完全隐身在沙尘中,天地之间只有渺茫混沌的一片,仿佛鸿蒙初辟,令人一时间神思扶摇,恍惚不知身之所在,不禁自问:“吾谁与从,归彼大荒?”
不容多想,前方却又豁然开朗,沙尘暴散去,植物脱去丧服,天空和道路霎时恢复了本来的样貌,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沙漠里几乎每天都有一场沙尘暴。”小方说。
“我错过了什么?”从睡梦中醒来的陈丹玲一脸遗憾。
她错过的当然不仅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
老子言:“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在大漠,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敬畏生命,必得要先敬畏天地。
从主干道转到伴行路,“轮台”两个字像两颗被敲落的星子,闪烁在眼前。边塞诗人岑参有两次从军西域的经历,他的“轮台诗”使轮台成为千百年来高挂在西域边关的一轮明月,谁不会背诵他的名句:“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一想到我们与岑参一样,“忽来轮台下”,望着同样的边月,吹着同样的边风,便觉天涯相逢,古今同脉,必当“相见披心胸”。而边功已竟,吹角已熄,都护府旧址已成宾馆,龟兹小镇商贾熙攘。白驹过隙,沧海桑田,延续的,唯有胸中不变的浩然之气!
在克深31井,钻头已深入地下7952米,还将继续深入至8115米。带着地温的岩屑样品闪着暗色的金属光泽,按不同深度摆在小木格子里,油味依稀,陌生又新鲜。经施工队允许,我捏了几粒岩屑,用废图纸包好,留作纪念。前几天参观深地塔科1井时,小说家荆歌捡拾了一小块来自地下5856米深处的小石子,并拍照在朋友圈发文说:“带回家镶金当个挂件。”地下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我想,我们自己也终将是泥土的一部分。
工程师拿出一卷随钻地质录井剖面图,令我吃惊的是,这是一卷全手绘剖面图。图纸是一截一截粘贴接续起来的,接口细致,展开大约有16米长,一厘米代表五米的深度。且随着钻井深度的不断增加,手绘图也将继续延长。我仔细观察图上的各种数据:钻时、岩性、气测显示、井身结构、伽马、电阻率、声波录井剖面、全烃、C1……对我来说,这些陌生的专业术语因这卷手绘图而有了温度。
工程师说,如今只有在塔里木油田的施工现场,才能见到手绘地质录井剖面图,这是塔里木油田的传统。这卷图纸并非一人所绘,而是多位工程师接续绘制而成,但手写的字体、字号如出自一人,图纸的每个细节都浑然一体。
我后来在塔里木油田油气工程研究院看到过很多设计图,可没有一张是手绘的。在电脑绘图已十分成熟并完全普及的当下,为何在探井工地要手绘剖面图呢?
工程师说,电脑绘图打印出来尺寸小又不连续,现场实际用起来不方便,手绘剖面图不管是在桌子上还是在地下一展开,整体的趋势和规律看起来一目了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凡是新到工地的工程师,都要加入到手绘图的队伍,自己手绘的图,心里面比谁都有数。手绘的过程,也是加深数据印象、熟悉地下状况的过程。
我心里一热,是啊,手绘图带着绘图者的温度,是一卷倾入了感情的图纸。小时候,我妈亲手给我织的毛衣,几十年了,我始终不舍得丢弃。凡是手工制作的物品,已不仅仅是物品了。在各项技术突飞猛进、凡事讲求效率的今天,手工行为本身已显得弥足珍贵。有时我们需要慢下来,才可以看到生活本身的模样。
手绘图最下方的一行小字,让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动了一下。图纸来自辽宁的印刷厂。一卷手绘图,便一下子拉近了故乡与大漠数千公里的距离。
之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我们见到了一条由10400块钢板铺成的飞机跑道,长800米,宽45米。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塔里木油田为勘探开发塔克拉玛干沙漠油气资源,在沙漠中铺设的一条飞机跑道。油田设备器材由这里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大漠深处。这条沙漠腹地的飞机跑道,正来自我现在工作的城市——丹东。当时,塔里木油田负责引进钢板跑道的刘翼,与当过抗美援朝飞行员的空军司令部司令王海,曾是在丹东工作时的战友。刘翼找到王海,空军司令部支援了三套跑道,分别在满西1井、塔中1井和塔中4井。我们见到的,就是塔中4井的跑道。
日落时分,我们终于到了天山脚下,这是天山南路支脉秋里塔格山,山脚下便是579国道,天山上流下的雪融水滋润了这里的土地,克孜尔河和卡拉苏河环绕下的草甸子绿植丰茂,骆驼成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