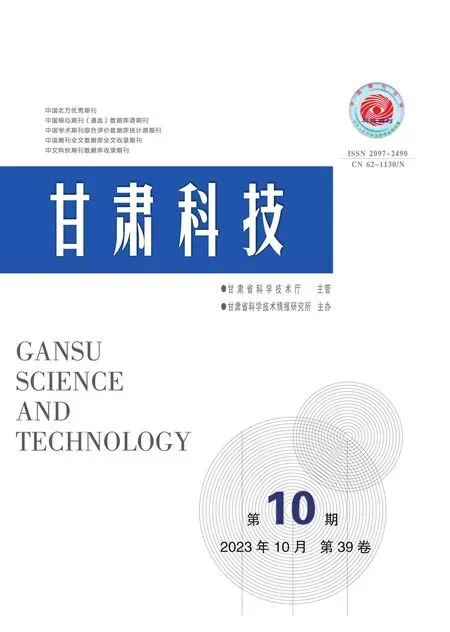基于“治未病”思想指导疫病防治的策略*
2023-12-18金成强郭姗姗张依恒
金成强,黄 敏,郭姗姗,张依恒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治未病”是指在疾病未发生或未传变之时,预先采取果断措施,积极防止其发生、发展、传变、后遗及复发。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来的“防病养生”谋略,是迄今为止中国卫生界所遵守的“预防为主”战略的最早思想,是中医预防医学的精髓,与后世医家提出的“防病”重于“治病”的理论一脉相承,与现代医学“三级预防”思想殊途同归。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有些疫病传染性强,载毒量高,并发症多,病死率高,在目前尚无特效药物的情况下,疫苗接种还不能有效阻断病毒传播,故疾病预防就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以中医“治未病”思想为指导,探讨当前全球持续不断的疫病之临床防治思路。
1 中医药对疫病的总体认识
在中医文献中,所言之“疫”,是指自然界疫疠之气,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传染病。最早记载疫病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在《素问·刺法论》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天牝为何?即鼻子,说明疫病是经由呼吸道传播的传染病。吴又可在《温疫论》说得更为透彻:“疫气盛行,所患者重,最能传染”[1]。《难经正义》则道“疫者……遍相传染者是也”[2]。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每个时期均无法避免各种疫病的侵害。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先后发生过300多次规模较大的瘟疫流行。相较于公元6世纪和14世纪两次世界性的鼠疫,分别导致人口锐减1/5和1/3,中国古代的人口数量维持相对恒定,从西汉到明代,一直保持在4 600~6 000万人。即便到了清代,据《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统计,这一时期的瘟疫流行超过以前任何时期,而且还催生并壮大了中医温病学派,但是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长,至乾隆年间达到2亿多人[3]。可以说,中医药一直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保驾护航,而且在如何预防和治疗疫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 “治未病”思想在疫病防治中的应用
2.1 未病先防
即注意四时养生、呵护身心、预防疫病的感染。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古人善为医者,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提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事之前。”表明未病先防的重要性;《素问·刺法论》中记载“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强调了顾护正气、避其毒气的疫病防治主张。
2.1.1 养护正气
《黄帝内经》中记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指出养护正气的重要性。正气的充盛,首先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类面对大自然变动不居的环境,不能被动接受,而应主动调整以适应之,天人合一、相辅相成,遵循“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其次不排除自身机体的阴阳平衡,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这种阴阳相对不平衡的状态最易感受外邪侵袭,而且感邪后疾病发展、变化更迅速,病情更严重,此为同时疫病后有无症状、轻症、重症之分,及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疾病者预后差[4]的主要原因。王琦院士的体质学说[5]提出除了平和质的正常健康状态外,其余八种均为偏颇质的亚健康状态(气虚质、气郁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特禀质),建议人群根据自身不同的偏颇体质状态,早期求医调治,加之自身合理饮食、调畅情志、规律作息,以期人体阴阳平衡。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如果机体正气充盛,病邪难侵;或虽已侵,正气亦会迅速祛邪外出,如疫病中的无症状感染者,即为如此[6]。“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7]。目前疫苗接种也可视为提高人体自身“正气”的举措。
2.1.2 避其疠气
发病的条件取决于“邪正胜负”,若正气如常,但邪偏重,正气则相对不足,也会染疾。故中医认为正衰是发病的内在因素,邪盛是发病的重要条件[8]。著名医家吴又可《温疫论》所云:“夫疫者,感天地之疠气也。疠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别有一种疠气也”,指出疫病有别于其他疾病。《汉书·平帝纪》中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即是古人对患疫病者采取集中隔离,“避其疠气”,防止疫病扩散的有效举措。疫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为飞沫经呼吸道传播和近距离密切接触患者的分泌物、排泄物而传播,所以取消大型集会,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交通管制,阻止人员大规模流动,也是防止本病爆发和传播的主要措施;结合现代预防医学防护体系,加强对临床医护人员,尤其是疫区一线医务、警察、边防及后勤保障等高危感染防控人群的防护。同时要求疫区人员加强个人手卫生与环境卫生,做好个人卫生清洁及居所、办公环境消杀;还可采用佩戴香囊和局部环境中药熏蒸的方法以避秽祛邪等主动预防[9]。从而“避虚邪以安其正”。
2.2 既病早治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强调了疾病早诊、早治的重要性。当前疫病防治提出新的“六早”防治原则: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就是要关口前移,要重视先兆,及早地防治,既要整体把握疾病特征,还要有“因人制宜”的个体化诊疗方案。
2.2.1 药物调治
疫病病因为“疠气兼秽浊之邪”,病理因素为寒、湿、热、毒、瘀、虚。范逸品等[10]认为本次疫病性质为虚实并见,故治疗应扶正兼祛邪。治疗原则为宣肺清热、化湿解毒、扶正祛邪。治疗重点在“开鬼门、洁净府”给邪气以出路,因势利导,“火性炎上”,使毒热之邪向上从肺卫宣泄而散;“湿性重浊”,湿毒之邪向下从二便分消而去。主张分型辨治:轻型(湿热袭肺),普通型(湿毒蕴肺),重型(疫毒闭肺),危重型(内闭外脱)。合理使用“三方三药”;“清肺排毒汤”,涉及《伤寒杂病论》中的多个经方,组方严谨、攻补兼施,适用于疫病之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的治疗。普通、重、危重型患者还应该标本兼治,加用清开灵注射液、参附子注射液等药物;危重型内闭外脱可用苏合香丸(温开)或安宫牛黄丸(凉开)。“谨察病机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中国地域辽阔、南北方气候差异明显,具体辨证时还需考虑中医三因(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当然还可依据患者病情需要给予氧疗、抗病毒、辅助呼吸等综合措施尽快逆转病势。
2.2.2 心理干预
疫病不但对人体生理健康产生严重危害,也会对患者的心理状态产生诸多不良反应,如出现不良情绪反应:愤怒、焦虑、恐惧、悲伤、无力感、无助感、抑郁、担心、害怕、烦躁、愤怒。出现认知能力改变:注意、记忆、思维、决断等能力受限,一些患者会有感觉失真、无法集中注意力、犹豫不决、自责、身心疲惫、食欲降低或暴饮暴食、容易抱怨、失眠、回避行为、自伤甚至自杀行为,还可出现过度防护,如反复洗手、一遍遍消毒等。还会因不良情绪刺激而引起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症状:口干、出汗、心慌、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头痛、肌肉酸痛、消化不良、胃胀、腹痛、尿频、尿急、月经紊乱、二便失调等;甚则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影响。对于这类症状,短期内非针药所能及,所以早期心理干预对病情的演变及预后有积极的作用。
2.3 既病防变
认识并掌握疾病的传变规律,控制疾病在局部或本系统,防止其进一步转变和进展。清代叶天士提出“先安未受邪之地”;汉代张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既病防变理念,一直以来都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2.3.1 分期辨治
疫病早期病情相对稳定,临床症状较轻,若此阶段未行有效措施,则病情有可能迅速加重,甚至危及生命。要在发病初期5~7天截断病情发展之势,扭转病邪由表入里传变的趋势,是治疗的关键步骤。据疫病发展的一般过程分早期、中期、重症期、恢复期,临床治疗上既要分型辨证,也要分期辨治;大部分患者早期为湿热阻遏肺卫,使肺卫之气不得宣畅,继而化热成毒、伤津耗液,毒热内闭、邪无出路遂转重症,进而邪陷心包、伤营动血、内闭外脱成危候。叶天士《温热论》曰:“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指出了疫病不同阶段治疗的大法。要求我们治疗时精准掌握病邪所处阶段,或祛邪为主,或祛邪扶正平调,或扶正为要,步步为营,快速截断病程,使轻型、普通型尽快痊愈,避免向重症或危重症转变,尽快使重症或危重症逆转为轻症,降低死亡率,减少并发症。
2.3.2 中西互补
每次疫病流行,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并不断优化中医药治疗方案,在预防性用药、轻症速愈、阻断轻症转重症、重症辅助治疗、减少并发症、降低致死率、后期快速康复和减轻西药毒副作用等层面上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有其明显的优势。现代流行病学的管控手段和西医的氧疗、液疗、辅助呼吸、血滤、ECMO等急危重症抢救和生命支持技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两套理论体系指导下的优势互补,可获得1+1>2的救治效果。通过历次疫情中医药的介入、参与治疗可以看出,即中西医在不同阶段发挥各自专长作用的现代疫病防治模式,是中国特色疫病防控之路的优势所在,为后续疫病防控提供了样板模式。
2.4 愈后防复
既病后初愈,虽病情悉除而正气大伤,或余邪未尽,要积极采取相对应的调护措施、巩固性治疗手段以防止疾病复发和保证机体顺利康复。
2.4.1 辨证调护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劳复证治》:“伤寒新差后,不能将摄,因忧愁思虑,劳神而复,或梳沐洗浴,作劳而复,并谓之劳复。”《伤寒论·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自愈。”指出“食复”“劳复”“房劳复”的成因并给出相应的调护措施:“复则诸症复起,惟脉不沉实为辨。轻者静养自愈,重者必先察其虚实。虚则调其营卫,和其脏腑,待其表里融和方愈。误用攻下清凉,必致不救”(《重订广温热论·温热复症疗法》)。若患者愈后遗留低热、乏力、食欲不佳、心烦、口干等症,舌淡苔薄而干、脉弦,给予小柴胡加石膏汤加减口服;若咳嗽、乏力、倦怠嗜卧、不思饮食、大便不调,舌淡苔薄、脉沉细,予四君子汤加减口服;对于肺纤维化,常用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药物;力争“除恶务净、不留后患”。故疫病初愈后,一定要重视后天之本的调护,“调脾胃,安五脏”。以易消化、高蛋白的食物为主,多食水果和蔬菜,忌生冷辛辣油腻海腥之品。还需节房事、慎起居、畅情志、勿过劳。凡是违反人体自身作息规律及损耗正气的活动都不宜进行。
2.4.2 全面康复
“临床治愈并不等同于疾病的完全康复”,适度的体育锻炼,如日光浴、游泳、散步、太极拳、八段锦、呼吸操等,可因人而异,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常习练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促进机体功能恢复;对老年或重症愈后患者给予肢体功能康复;对肺功能差的患者需行专科康复;对出院后暂不能胜任工作岗位的需行职业康复等。综合研判疫病影响情况及客观条件,社区可建立由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等组成的社区心理和社会工作服务团队,及时发现具有心理疾病风险的人员,做好针对性心理康复训练和社会工作服务。总之,关注患者的身体、心理及社会能力提升,力求全面康复。
2.4.3 中医保健
传统的中医适宜技术对于提高机体正气和促进康复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如中药熏洗、艾灸疗法、经穴推拿、耳穴压豆、刮痧拔罐及针刺疗法[11],简便易行,有些可在医生指导下治疗,有些可居家自我操作,安全有效。中药熏洗:抓取适量艾叶、花椒置洗脚盆内,开水冲泡,待水温时熏洗双足。艾灸疗法:选取关元、气海、三阴交(双侧)、足三里(双侧)等穴位。穴位按摩:选取内关(双侧)、曲池(双侧)、中脘、足三里(双侧)等穴位。拔罐疗法:选取肺俞(双侧)、脾俞(双侧)、肾俞(双侧)等穴位。耳穴按摩:揉搓耳轮、提拉耳尖、下拉耳垂、鸣天鼓。耳穴压豆:选支气管、肺、内分泌、神门、脾、肾、交感等部位。绿色疗法,国人依从性高,易推广使用。
2.5 择时防发
因为疫病对温度比较敏感,低温时病毒活力越强,秋末寒冬及初春季节相对高发,常可先时而治。“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冬季北方干燥、寒冷,南方阴冷、潮湿,人们一般久居室内,缺乏户外活动、缺少阳光照射,“阳气”不足;有些地方冬季缺乏新鲜的蔬菜水果,使得钙和维生素的摄入不足;按照国人养生保健理念,习惯于冬季进补,容易引起一些基础病的发作(如痛风、糖尿病、胃肠道疾患等);以上因素均可导致人体免疫力低下,“正气”亏虚,“邪气”易侵。且秋冬季节是感冒、流感的高发期,普通感冒、流感及疫病的初期症状相似,有时不易分辨,必要时流行病学调查及实验室监测尤为重要,此时应积极预防感冒、注射流感疫苗。另外,春节期间大范围人员流动、家庭聚餐等活动对疫病防控也是不小的挑战。故在特定季节及时段预防疫病的传播尤为重要。
2.6 适时随访
因为有些疫病患者出院后还有基础病需要进一步治疗,部分患者可能存在着肺功能差,西药治疗后的副反应,甚至个别患者可能会有肺纤维化的发生和进展问题,所以患者出院后2周和4周视病情恢复及患者自身条件均需要到医疗卫生机构复查,包括肺功能、胸片、血常规及心理测试等检查检验指标,希望所有出院患者都要密切监测随访,以保证这些患者顺利康复。鉴于目前检测方法的不同,采样的准确与否,检测试剂的敏感性以及患者自身免疫功能的强弱不同,会出现个别“复阳”病例,对于这类人群,还是要医学隔离,严格按照疫病患者处置流程来进行管理。目前来看,早期给予中医药干预,“复阳”的病例整体发生率在我国还是较低。“复阳”病例大部分没有明显临床症状,极少数会出现影像学上有明显的进展,需密切观察,必要时给予相应处置。持续阳性的病例尽管很少,但也要密切关注。
3 讨论
目前,随着全球历次疫病的发生,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巨大破坏,给人类生理、心理上的双重压力都是有目共睹的,人们都期盼着疫病早点结束,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然而,通过多年的观察,证实疫病不会在短期内消失,疫苗接种及药物研发远远赶不上毒株的不断变异,且变异后的毒株载毒量更高、传染性更强,所以,我们既要有战胜疫情的信心,也要有与疫病长期共存的心理准备。
在疫病防治过程中,除了遵循“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等基本原则外,还要依托“政府主导,社会配合,个人服从,家庭堡垒”为主的我国疫病防治经验;除了必要疫苗接种和药物干预,同时要对国民进行大量的科普宣传和健康教育,旨在能使老百姓提高对此疾病的认识,提升自身抵御疾病的能力,掌握疾病预防要点,消除不必要的思想负担,患病后要积极配合医生规范化的治疗,“全民参与、医患合作”,共同抵御疫情。
当前医学模式已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医学研究的目地也随之转变,从治到防,其重点已从“治已病”转向了“治未病”,即对人类大健康的研究,尤其对于全球性重大传染性疫病,更是防重于治。历年来如“治未病”高峰论坛的召开,以及“治未病战略联盟”的创立,中医“治未病”以其特有的医学防治理念与实践已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多次疫病防控实践,也充分显示出其思想在疾病防治中的强大生命力和重要指导作用。故不断继承、发掘、完善中医预防医学理论体系,将“治未病”思想充分运用到疫病防治工作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