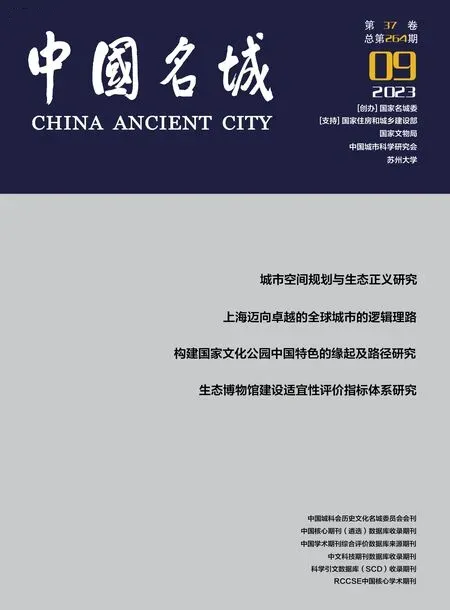构建国家文化公园中国特色的缘起及路径研究
2023-12-16刘容
刘 容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国家文化公园是党和国家在新时代夯实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繁荣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文化工程,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筑重要国家文化标识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要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6年来,国家相关部委和相关省市密集出台相关重要文件和规章制度,助推国家文化公园迅速从规划理念到建设落地。目前,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体系已形成以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为核心的基本框架,目前正加快建设发展[1]。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是我国首创①,由国家助推规划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彰显了中国特色,构建起国家文化空间体系[2],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我国重要文化工程,需要体现国家性[3]、凸显整体性[4]、兼顾公众性[5]。
1 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文化公园的必要性
国家文化公园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本质上看,它是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的吸收、借鉴和扬弃,也是基于我国国情,融合多国、多类型文化及自然资源综合保护利用的创新举措。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我国首创的重要文化工程,继承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重要研究和实践成果,彰显了我国文化遗产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
1.1 国家文化公园理论溯源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我国的重要文化工程预示了当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方向。总体来看,国家文化公园理念主要起源于基于欧洲文化背景提出的“文化线路”,基于美国文化背景提出的“遗产廊道”,以及我国学者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线性文化遗产”和“廊道遗产”等概念[6]。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基础较复杂,需要梳理国家文化公园的基本逻辑进路和发展流变。
1.1.1 文化线路: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起源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积累的过程。通过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WHC)、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CIIC)等相关机构的助推,大致经历了3个演变阶段。在演变过程中,既继承了前期相关理念,又反映了演变过程中最新的文化遗产保护趋势,最终通过《文化线路宪章》的颁布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特殊类型[7]。
第一阶段为起源阶段。肇始于欧洲委员会1987年施行的“文化线路”计划,旨在“以文化合作的形式提升对欧洲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认同,保护欧洲文化多样性,鼓励文化间交流,协助调解地区矛盾”[8]。文化线路是指一条道路围绕某个主题,穿越若干国家或地区,能典型地体现欧洲的历史、艺术和社会特征。可见,欧洲文化线路具有明确保护内容和主题,有具体实现路径,有文化整合和认同功能,体现欧洲特征。从本质上来看,欧洲文化线路是一种区域文化整合的工具,服务于区域整体发展目的,属于一种区域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计划,还未兼顾国际文化交流,不具有世界意义。
第二阶段为完善阶段。在欧洲文化线路计划的实施推进下,1993年欧洲第一条文化线路——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路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随之,欧洲文化线路的相关理念也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在2005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吸收了欧洲文化线路相关理念,提出了新的文化遗产类型——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s),认为“遗产线路由一系列物质遗产元素组成,其文化意义来源于跨国家或地区的人员交流和多维对话”[9]。显然,遗产线路更强调线路的文化意义,并且这种意义来源于跨文化和跨地域的文化交流。比之欧洲文化线路,遗产线路更强调世界文化多样性存续以及持续交流的意义。就本质而言,遗产线路和文化线路的内涵是一致的,因此诸多国际组织和学界也将“遗产线路”称作“文化线路”,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也是一种特殊的线性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更强调在前期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基本理念和共识基础上,在吸收整合前期线性遗产[10]、运河遗产、系列遗产[11]等相关类别过程中,对文化线路有形物质基础进行更具操作性的界定,同时也进一步强调了文化交流的具体内容,肯定了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因素与物质文化因素具有同等价值。在可操作层面上和可识别度方面比欧洲文化线路更完善。
第三阶段为成熟阶段。随着文化线路研究和实践如火如荼地开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深入探索文化线路遗产的标准和内涵,对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线路遗产进行了认定。文化线路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遗产已受到国际遗产界的广泛重视。2008年10月4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第16届大会上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就文化线路的识别、认定、保护等达成共识。《文化线路宪章》认为“文化线路是一条交流之路,可以是陆路、水路或其他形式,具有实体界限,以其特有的动态和历史功能特征,服务于特定、明确的目的”[12]。《文化线路宪章》对文化线路的定义基于欧洲文化线路的研究实践,同时也融合了世界遗产中心的系统研究成果,是对两者的继承、融合和提升。它肯定了文化线路是具有一定功能的交通路线,更强调文化线路必须根植于区域、国际和大陆之间进行思想文化、商品物质等的交流。同时,进一步提出文化线路是一个动态系统,它既可以连贯不同区域和国家,也可以整合过去、现在和未来,让不同空间和时间在文化线路上延伸、融合和发展,因此文化线路才能立足过去、现在,助推其所覆盖区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文化线路的理念也为展现国家文化公园的中国特色带来启示,“文化线路是文化的交流和整体价值的呈现,不是单向的文化传播,希望在未来的世界文化拼图里,中国文化能够成为很重要的一块。”[13]
1.1.2 遗产廊道: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借鉴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s)概念主要发源于美国,是美国基于本国自然和文化遗产分布实际、相互融合构建的综合性保护举措。从理论上讲,它主要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之后兴起的“绿色廊道”(Green Way)理念及相关实践。绿色廊道主要是指人类、动物、植物、水等经过或流经的自然或半自然通道或区域[14]。显然,绿色廊道更强调通道的自然属性,而遗产廊道在绿色廊道基础上更看重区域内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协调保护。遗产廊道是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15],不像文化线路重点关注历史文化及文化交流,遗产绿色廊道将视野拓宽至与文化资源密切相关的自然资源领域。但遗产廊道并不是简单强调文化和自然的融合,它具有典型的地方代表性、现实关注度和工具理性。首先,遗产廊道对地区和国家而言具有典型的历史文化或自然环境地方特性,遗产廊道保护应反映国家或地区的典型历史、民族或宗教特色,区域之内的建筑或环境,从结构形式或功用方面具有地方典型性且持续受到当地的相关保护和持续利用。其次,遗产廊道建构的重点不是单纯对过去的复原,更看重相关资源在当代的发展衍化和对现实的持续影响,如黑石河峡谷遗产廊道就反映了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地区早期人们定居、工业化和环境衰退的整个过程。最后,遗产廊道的构建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强调通过对自然和文化资源的联合开发,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和旅游业全面发展,如伊利诺伊和密歇根运河国家遗产廊道,是连贯伊利诺伊河与密歇根湖的运河航道,对开发五大湖区旅游价值及了解芝加哥城市发展史具有典型意义。此外,遗产廊道虽然具有典型地方代表性,但是它也属于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层面立法并制定相关规划制度对其进行保护,因此遗产廊道也具有典型国家代表性。
国内学者还基于美国遗产廊道相关理念,创设了“廊道遗产”(Corridor Heritage)的概念,认为此概念可以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中国化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廊道遗产通常是体量庞大、跨越多个不同的地理单元(行政区或自然地理区域)或文化单元(民族、种族、宗教群体、语言族群)的大型线路,或水路或陆路。它是历史上形成的,并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民族交往起到过重大的推动作用;能够体现民族精神、塑造意识形态,是国家文化身份或民族身份的象征;廊道遗产不仅本身是遗产,而且在它沿线区域分布着较为丰富的文化、自然和非物质单体遗产,因此它可被视为遗产体系。”[16]显然,廊道遗产强调国家文化发展的背景和立场,且站在综合发展的视角上重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调统一发展,比之遗产廊道在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侧重上更强调文化资源的价值。并且,遗产廊道保护对象是基于线路本身资源构建的体系,而廊道遗产则强调线路本身及所依托的整体区域,着眼于大尺度区域整体协调发展。因此,廊道遗产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游览路线或文化景观开发,而是一种立足区域自然文化资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规划模式。
1.1.3 线性文化遗产: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基础
国外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理论的深入发展促进了我国文化线路遗产的进一步保护利用。部分中国学者在上述理念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文化线路遗产留存现状,提出了“线性文化遗产”(Lineal or Serial Cultural Heritages)的综合理念。线性文化遗产并不是国际公认的一种遗产类型,而是国内学者根据文化线路遗产研究发展实践而创设的一种概念。单霁翔认为“线性文化遗产是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族群,往往出于人类特定目的而形成一条重要的纽带,将一些原本不关联的城镇、村庄等串联起来,构成链状的文化遗存状态。”[17]线性文化遗产继承了文化线路遗产的基本理念,强调具有一定物质基础并能呈现区域内文化交流和融合。线路依托的物质基础不再局限于线性或带状的区域,还包括沿线串联的城镇、村庄等。显然线性文化遗产关注的对象更广,线路本身不是研究实践的终点,它更像是一个中介,连贯所涉区域并进行联合保护。它更强调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族群化发展,为区域单个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创设了公共空间。因此,线性文化遗产是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综合理念,它基于学术研究成果,却超越了相关学术研究的界限,整合了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等相关研究成果的特色,突出文化遗产对区域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实践意义。
国家文化公园正是在吸收线性文化遗产和廊道遗产概念基础上,依托我国现有国家公园制度,在文化强盛和民族复兴大背景之下,创设的一种跨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特色模式。虽然国家文化公园目前还没有较统一的学术定义,但是有学者对其进行描述。李树信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传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文化信仰和价值观为主要目的,实施公园化管理经营的特定区域。”[18]李飞、邹统钎强调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途径和意义,“通过构建生活共同体,加强遗产命运与民族命运、国家命运之间的密切关联。”[6]戴俊骋提出“在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空间、管理三大要素基础上,探索横向与纵向两对关系,强化价值研究的系统框架。”[19]彭兆荣揭示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功能,“通过一系列实践和实验活动,灌输一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连续性价值于公共活动或文化遗产中,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特征。”[20]同时,学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公园的一个分支”[21]。
1.2 国家文化公园与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异同
虽然国家文化公园肇始于欧洲文化线路和美国遗产廊道,但是它并不是简单继承延续西方文化遗产理论,而是对其扬弃超越。
从设立诉求来看,国家文化公园和欧洲文化线路都旨在提升国家或区域文化认同。国家文化公园主要通过打造重要文化标志[22],增强文化自信[18],凝聚文化认同[2]来推动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这与欧洲文化线路旨在“以文化合作的形式提升对欧洲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认同”[8]基本一致。但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举国之力助推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肇始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欧洲文化线路是一种跨国家和跨区域的线性文化资源,通过文化线路的整合,保护文化多样性,鼓励文化交流,化解地区矛盾。保护文化多样性是文化认同的前提,文化认同的目的是化解地区矛盾,这种认同的内生动力和凝聚效果弱于国家文化公园。
从客体对象来看,国家文化公园、欧洲文化线路及美国遗产廊道都依托区域文化和(或)自然资源。欧洲文化线路及美国遗产廊道的客体对象基本局限于本区域文化和自然资源,不是依托国家力量全国推广的建设模式。
从体量上来看,文化线路及遗产廊道是基于单一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而国家文化公园所依托的资源具有国家代表性,是一个区域内诸多文物和文化遗产集合而成的文化遗产网络。因此,国家文化公园与之相比,客体对象更复杂,覆盖的区域更辽阔,最终目的不再局限于文化遗产保护,而是借此推动整个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
从基本功能来看,国家文化公园、欧洲文化线路及美国遗产廊道的功能有同有异。欧洲文化线路和美国遗产廊道最初都是作为交通路线而使用的,是人们通过路线交流互动产生的文化遗产,经过岁月洗礼目前已构成沿线民众共同享有的文化记忆,文化线路的功能“除了线路本身主要功能之外,也会附着宗教、商业和行政等其他不同的功能”[23]。我国长江、黄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曾经也是主要的交通要道,目前仍承担流通功能,但长征和长城显然并不是为了交通交流功能而建成,它们讲述中国历史上重要历史事件,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此,我国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更加多元化,承担着“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22]等功能,更肩负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地区战略功能。
从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我国首创的重大文化工程和重要文化理念,在文化全球化历程中的确受到欧洲文化线路和美国遗产廊道等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影响,但又与欧洲文化线路和美国遗产廊道存在重大差异。如何在全球化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基于欧洲文化线路和美国遗产廊道探索适合我国的国家文化公园发展路径,有必要从我国基本国情、文化特色及文化建设现状出发,立足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基本经验和制度安排,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展道路。
2 构建国家文化公园中国特色的路径
国家文化公园是建设文化强国大背景下,基于我国既有文物保护成果和相关制度,积极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吸收我国国家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遗址公园等实际运作基础上的综合创新。但国家文化公园由于与国外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相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且从提出到建设仅6年,因此还需立足我国实际,大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路径。
2.1 吸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夯实国家文化公园中国特色的根基
国家文化公园是新时代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重要国家文化标识的重大文化工程。邹统钎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批准设立,为打造国家文化重要标志、坚定国家文化自信、增强国民文化认同,整合具有国家代表意义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实行公园化管理运营,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22]。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具有强大的国家意志背景,有利于国家文化战略布局。它不仅关涉文化遗产及相邻区域,更关注这些文化资源背后所秉承的民族文化记忆、文化认同及对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因此国家文化公园中国特色构建的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4]。国家文化公园中国特色的构建同样应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革命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独具特色的代表性文化形态,是构建国家文化公园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是国家文化公园保护传承的中华民族文化根脉。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中华民族文化标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中国特色的重要载体。构建国家文化公园中国特色须深入挖掘、生动展现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重要文化标志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并激发其活力。
2.2 立足我国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奠定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框架
1961年3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180处,启动了我国文物保护实践工作序幕[25],构建了国家、省、市、县四级文物保护单位分级体制,形成了全国各地文物保护网络体系。截至目前,我国已开展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共核实确认766 722处不可移动文物[26]。2019年10月,国务院发布通知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国保单位共核定为5 058处,包括古遗址1 194处,古墓葬418处,古建筑2 160处,石窟寺及石刻307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952处,其他27处,国保单位总数比较多的省份是山西、河南、河北、浙江和陕西[27]。60多年来,文物保护单位制度逐步将全国重要文化资源纳入保护监管体系,已形成种类多样、保护与发展兼顾、遍布城乡的文物保护网络系统,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搭建了既有工作框架。同时,文物保护单位本身也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资源和基础。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最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本身就收录了不少线性文化遗产,诸如京杭大运河、秦直道遗址、黄河栈道遗址、剑门蜀道遗址、井陉古驿道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在建的一些国家文化公园就是依托线性文化遗产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设的,如长城、大运河等。可以预见,未来将有更多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依托。
因此,基于现有文物保护单位普查、评审和保护成果,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既可高效构建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文化价值,又可进一步助推点状分布的单体文物保护单位构建整体价值,从而提高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社会、经济综合价值,促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文物保护单位发展相得益彰。为此,应依托国家、省、市、县四级文物保护单位工作基础,以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核心,串联具有重要国家文化标识的文物群体系,打破过去单个文物保护单位各自为政的局面,凸显历史长河连贯作用下的整体价值,真正以国家文化标志建设为指针,激发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活力。
2.3 吸收线性文化遗产申遗经验,树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示范
我国重要文化线路遗产申遗,促进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国际交流接轨,提升了我国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成效。2005年10月,ICOMOS第15届大会暨科学研讨会形成了《西安宣言》,直接推动我国正式开展相关线性文化遗产申遗工作。随后,通过整合线性文化遗产沿线文物保护单位,丝绸之路(西安至天山段)和中国大运河于2014年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受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前沿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我国从2006年开始也将大量线性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类型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京杭大运河、黄河栈道遗址等,推动了我国跨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这种跨区域的文化遗产联合保护制度深刻影响了我国既有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发展趋势,给当前跨区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应全面梳理线性文化遗产类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遗经验,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资源整合参考样本。
在我国,文物保护单位制度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存在齐头并进现象,两者之间有时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交集和融合。具有线性群体分布特征的线性文化遗产申遗本身就是对国内文物保护单位制度的整合和提升。目前,在建的长城国家公园和大运河国家公园,也是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城和大运河,充分借鉴文化线路申遗国际经验的创新性工程。今后,应充分整理长城、大运河等线性文化遗产跨区域协同联建的经验,形成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示范,以利于今后其他同类型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形成文化遗产与自然资源联合保护的中国经验。
2.4 依托各类型国家公园建设,整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基础
学界有观点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公园的一个分支”[21]。我国于2017年提出建立国家公园,大力发展国家公园体系[28]。目前,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虽然国家公园主要保护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尚未考虑中国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资源,但是基本保护模式和管理体制仍然值得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参考借鉴。
此外,我国也开展了一些文化和自然资源联合保护工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奠定了现实基础。1985年,开建了第一处遗址公园——北京团河行宫遗址公园。2010年开始,国家文物局陆续命名了三批、共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颁布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条例》,建设了北京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四川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文物考古类遗址公园,开启了依托历史文化资源、结合自然生态环境、提升公众生活环境和文化体验的探索[29]。随后,陕西省文物局于2017年开展了文化遗址公园建设工作,进一步拓展文化遗址公园建设保护对象和范围。各类型文化资源类国家公园从形式上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奠定了现实基础,但它们主要是依托点状不可移动文物的小规模建设,与依托跨区域线性文化遗产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存在本质差异。需要进一步梳理当前各类型文化资源类国家公园建设布局和现状,出台整体的统一的规划,整合沿线分属的不同区域和部门,建设协调管理机制,在文化主题统领下,基于已有建设基础,高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
3 结语
国家文化公园理念是我国首创,它的中国特色构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构建国家文化公园中国特色的最大理论诉求,就是将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外其他文化遗产保护话语体系进行区分。虽然国家文化公园是对国外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的借鉴和超越,但是国家文化公园中国特色的构建不能仅靠非此即彼的“他者效应”来简单呈现,而应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背景,在彰显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等具体文化工作实践及理论话语中充实具体内容。国家文化公园尽管是国家主导的,但是不能仅靠国家意志从上到下进行惯性助推。在我国,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是和谐统一的,应充分激发公众参与的意愿,提升国家文化公园的公益性,彰显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人民的宗旨理念。同时,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美好生活的开创者,也是构建国家文化公园中国特色的创造主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人民群众的集体创造,最终都需要通过国家文化公园载体建设进行具象化的呈现。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这才是国家文化公园中国特色构建的最本质要求。
注释:
①国际主要英文文献数据库(Springer Link、Science Direct、EBSCO、web of knowledge、Scopus、PQDT 和Google 学术)搜索引擎均无国家文化公园(National Cultural Park)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