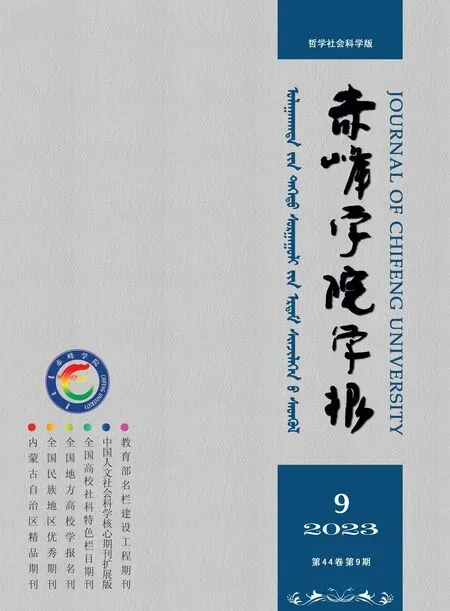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考古发现研究综述
2023-12-13李荣辉
李荣辉
(内蒙古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上土城村北,古城面积约4平方公里。对于遗迹的性质,同治十年(1871)成书的《和林格尔厅志略》说:“上土城在厅北十八里,基址尚存,周围约二十里许,相传元顺帝后俺答汗所居。”①据胡钟达、薄音湖等学者研究,②俺答汗修建的归化城在今天呼和浩特市区一带,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并非俺答汗居住地。
1934年和林格尔县人刘汉鼎编纂的 《和林格尔县志草》载:
成乐县城,秦置在今县北土城子。
定襄郡城,在县北二十里土城子,城周十六里,其门四,内城二百五十步见方,东南隅有营垒遗迹,即成乐城也。③
1937年成书的《绥远通志稿》载:
案上土城所在地,以水道方望及其建筑之宏阔暨遗迹残毁最甚各点推之,颇似汉定襄郡所治之成乐城,亦即后汉北魏所谓盛乐,而拓跋氏踵事增筑以为北都者也。④
《绥远通志稿》认为上土城村古城为汉代定襄郡郡治成乐县,北魏早期都城盛乐,其主要依据的是《水经注》的记载:
白渠水西北,迳成乐城北。《郡国志》曰:成乐故属定襄也。《魏土地记》曰:云中城东八十里有成乐城,今云中郡治,一名石卢城也。⑤
云中城是今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城东80里的成乐城即今土城子古城,《绥远通志稿》的观点后来被驹井和爱接受,⑥1961年李逸友《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墓发掘简介》、⑦1964年陈国灿《大黑河诸水沿革考辨》⑧都沿用了这种观点。
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是从1943年开始的,从时间跨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49年以前)
1943年在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协助下,东亚考古学会委派驹井和爱等人对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并进行了试掘,发掘时间是1943年10月22—31日。驹井和爱采用了探沟发掘法,在古城内打了12个探沟,每个探沟宽2米,长30米,每日用工50人。驹井和爱在古城中南部表土下数寸发现了宋代瓦当和瓷器残片,在古城东南部距离地表两三尺的地方发现有汉代砖瓦、铜镞、铜钱等,铜钱包括五铢、半两、大泉五十等。根据发现遗物,他推测遗址内最北边是北魏盛乐古城,毗邻宝贝河拐弯处是辽金振武镇,东南方是汉代成乐城址。⑨此外,他在古城中南部金代遗址发现大定六年铭文砖,由此可以确定金代雄佛寺的存在。⑩
驹井和爱的试掘是第一次对土城子古城进行科学的调查和发掘,他绘制了遗址的平面图,根据出土遗物对古城遗址进行了分期,发掘过程中发现了汉代的排水沟以及排水沟所用的陶制管道,在城址东南角汉代古城内外的地表采集了磨制石斧和彩陶片。[11]驹井和爱所绘的平面图相当精确,图中所绘台地上两个圆形建筑基址,其中之一,因为采石已经被破坏。他所发现的汉代陶制排水管道和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片在后来的发掘过程中再也没有发现。驹井和爱的考古调查报告为我们今天研究土城子遗址保留了珍贵的资料。
驹井和爱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足之处有:第一,当时对北魏时期考古遗存发掘较少,缺少可供参考的资料,把本属于唐代的土城子北区定为北魏盛乐;第二,发掘资料没有经过整理,仅发表过一个简单的调查报告。
二、第二阶段(1949—1979)
第二阶段的考古发现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5年在古城西侧西窑子村发现一座唐代砖室墓,出土绿釉塔形器一套,但这座墓葬的材料没见报道。[12]1959年当地村民在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在古城内发现一瓮窖藏货币,陶瓮内有西汉到唐代的货币7万多枚,约500公斤重。这批钱币有汉文帝四铢半两、五铢钱,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货泉、布泉,北魏孝庄帝永安五铢,北齐文宣帝常平五铢,北周武帝五行大布,隋代五铢,开元通宝、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这些货币中最多的为开元通宝,总计67000枚。赵爱军等人根据唐代钱币的年号推测窖藏埋藏的时间应不晚于唐德宗建中年间。[13]
土城子遗址比较集中的考古发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1960年1月,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队李逸友在土城子北面干渠内发掘4座古墓,同年4月17至5月19日为配合水利渠道工程,张郁等人对古城东部边缘地带进行了清理试掘,与此同时,田沛林等在距离古城北城墙约200米处发掘了7座墓葬。[14]1960年对土城子采用了探方式的发掘方式,对古城东部水渠通过的地方进行重点发掘,并解剖了四段城墙,这次发掘的成果有《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发掘纪要》[15]《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发掘报告》[16]《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墓发掘简介》。[17]
20世纪60年代考古发掘取得的成绩有:一,通过对四段城墙的解剖和城内遗址的试掘,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把古城的地层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战国晚期到西汉,第二期是东汉到北朝初年,第三期是北朝中期到隋唐,第二期遗物不同于第一期、第三期,也与内蒙古地区北朝中后期的遗物有差别,这是拓跋鲜卑定居盛乐不久,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二,南城东墙不是一次修筑而成的,最早建成年代是西汉,东汉以后到西晋时期有一个增修的过程。北城唐代城垣建在汉魏文化层上,建城时间在初唐,唐城的补修应在王忠嗣设立金河县以后,安史之乱爆发时期。三,在南城第一发掘区找到了一处大型建筑遗迹以及建立在之上的大面积居住遗址,对北城的部分街道及街道两旁的建筑基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四,在第一发掘区发现了分属第一期和第二期文化层的两个窑址,在南城东城墙和北城墙边缘发现瓮棺葬墓,有的瓮棺葬被压在城墙下面,在古城北城墙附近发掘了11座砖室壁画墓。[18]
第二阶段考古发掘与研究不足之处是:一,没有发现战国地层下春秋时期的遗迹。二,为配合基本水利建设,此次发掘侧重于古城东侧水渠两旁,受发掘范围所限,对古城整体文化面貌认识有限,特别是对辽金元时期的中城遗迹没有涉及。三,受时代的限制,对考古发掘资料没有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因为技术原因,壁画墓的图像资料没有保存下来,壁画墓的年代定为晚唐至辽初。近些年通过对墓葬出土的绿釉鹦鹉壶等器物的研究,这批墓的年代应该在辽初,原断代偏早。四,北城的建城年代是否是唐初,其增补的时间是否为安史之乱爆发时期,尚需进一步探讨。
三、第三阶段(1980年至今)
第三阶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始于1986年。这一年土城子村村民赵德俊在古城东取土时发现一把青铜短剑,这把剑是在距地表2米左右被发现的,与短剑一起出土的有一匹马的骨骼,马骨在下,短剑在马骨的上面,青铜剑上面刻有文字,经李学勤解读,此铭文为“耳铸公剑”。[19]这把剑的出土说明早在东周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已经与中原存在文化交流。
1988年和1989年苏哲前后两次调查了土城子遗址,并指导牛世山、罗文华对土城子遗址进行了测绘。苏哲的主要贡献有:一,主要调查了中城,找到了中城城墙东门与北门两处门址,发现了门址地面堆积的大量素面筒、板瓦残片,指出此处原有门楼之类建筑。二,在东门遗址发现漆瓦,他根据《晋书·石季龙载记》的相关记载和大同永固陵出土的类似瓦当,认为这种瓦当应为北魏盛乐遗物。三,在中城2号台基发现残石佛像和小型佛座、莲花兽面瓦当等辽金遗物。四,在中城南部临河处和东墙内侧发现了蜥蜴形纹、变形云纹、S型纹和YSX形组合纹四种瓦当,他结合《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发掘报告》的分期,得出“中城南部、南城北墙延长线以南,直到今宝贝河东岸地区都属于汉盛乐县城、北魏故都盛乐城范围之内”的结论。[20]
1994年,在土城子古城南1.5公里处的南园子村发现一座唐代墓葬,由于这座墓葬被冲沟冲出后遭到盗掘,部分随葬品是收缴回来的,随葬品的原来位置及数量不清。魏坚通过墓葬出土的唐武宗时期铸造的“会昌开元”断定此墓为唐代晚期至五代时期的墓葬,并根据墓葬特点归纳出三点:墓葬中出现酱釉穿带瓶、凤首穿带瓶、高领穿带罐、鹦鹉壶等器物,具有强烈的北方游牧文化特色;墓葬中出现的塔形器与佛教有关;墓葬中出土的贴塑陶器的花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壁画主题和墓葬结构又有中原风格。他认为墓主人可能是受中原汉文化影响较深,但仍保留一定民族传统的北方少数民族。[21]
1996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土城子古城周围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了战国、汉代和隋唐时期的墓葬8座,这是在土城子周边第一次正式发掘汉代墓葬。这次发掘的材料仅公布了两座汉墓,一座位于土城子古城东南,另一座位于古城东北的公布营村南,两座墓的形制相同,都为长方形竖穴砖室墓。发掘者根据墓葬出土器物与墓葬形制判断,这两座墓的年代与召湾M70的年代相差不远,时代为西汉中晚期,且这两座墓与汉代成乐故城有关。[22]
土城子古城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始于1997年。1997年7—11月,为了配合达—丰超高压输电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线路经过地点进行了调查和勘探,同时在北城北部进行考古发掘,共布方7个,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出土了三彩釉碗和邢窑白釉窄环圈足碗。1999年10—12月,为了进一步了解北城的布局情况、地层堆积状况和文化内涵等问题,又对古城遗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调查和勘探,重点勘探了东西城门、瓮城、街道、大小煤山等,勘探面积3万平方米,同时在北城西南部进行考古发掘,共布方28个,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发现作坊遗址、水井、窖藏及越窑青釉瓷碗、三彩釉注壶、邢窑瓷器等。
2000年6—12月,为配合盛乐经济园区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古城遗址周边发掘墓葬的同时,在中城(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址)近北部布方4个,在南城(汉代城址)布方20个,共发掘900平方米。这次发掘发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遗迹,并出土了陶壶、陶罐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器物。2001年5—12月,为配合209国道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段扩建及盛乐经济园区建设工程等,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古城遗址周边发掘墓葬的同时,对古城遗址的中城、南城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勘探,勘探面积约8万平方米,发现了中城的东门、西门、北门,南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瓮城、北门等遗迹。这次共发掘1640平方米,解剖城墙10处,发现了中城南部战国时期的城墙,确定了中城北朝时期城址范围,此外,还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遗存。在土城子古城遗址历年发掘中,这是第一次发现春秋时期的地层。
2002年11月15日,在土城子古城东南上土城子村足球小学发现一座唐代砖室墓,墓主人是刘如元,他的官职是“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太常卿”,为振武军武官,死于贞元十四年(798)。[23]这座墓葬保存完好,出土明确纪年墓志,为研究唐代中期呼和浩特地区墓葬葬俗提供了实物依据。2005年,土城子周边发现一座早期被盗的唐代砖室墓,墓主人是贺廷俊,在振武军任职,官职是“游击将军、左金吾卫大将军、试光禄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24]贺廷俊史书无载,从墓志可知,贞元四年(788)他在对奚人作战的时候死于疆场,《新唐书·奚传》载“贞元四年,与奚共寇振武,节度使唐朝臣方郊劳天子使者,惊而走军,室韦执诏使,大杀掠而去”。[25]贺廷俊应死于这场战斗。
1997—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前后9次对古城外围墓葬区进行了大面积勘探和考古发掘,共勘探面积150万平方米,勘探古墓葬2000多座,发掘了从春秋到元代墓葬1680座,战国和汉代时期的墓葬数量最多,出土各类文物共计万余件。
2005年陈永志发表 《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考古发掘主要收获》,介绍了1997年以来的考古收获,公布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春秋晚期的墓葬、具有秦文化特征的墓葬、具有鲜卑早期文化特点的鲜卑墓葬和器物群、唐代纪年砖室墓等,在文章结语部分,作者将考古材料与土城子相关的历史记载作了对比,勾勒出土城子古城的历史沿革。[26]
2003年,李强发表《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出土的战国、汉代瓦当》一文,对土城子古城出土的战国、汉代瓦当进行了分期,通过类型学的分析,区分出了战国和汉代瓦当。[27]
2006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土城子周围发现了21座辽墓,并进行了发掘。这批墓葬有18座砖室墓,3座土坑墓。第一阶段清理了6座墓葬,出土了14件精美瓷器和6件陶器,其中1件盘口褐釉瓷瓶和1件褐釉瓷注壶十分罕见,因而尤显珍贵。这些辽代墓葬排列密集、有序,带有明显的家族式墓葬区特征,并且在已发掘的砖室墓中发现壁画,由此可见这一家族当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28]
2006年以后,对土城子古城的研究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研究方式,而是引入了多学科研究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体质人类学的应用。
2007年,顾玉才对土城子1997—2002年度发掘的战国时期289座墓葬中的人骨做了体质人类学鉴定,共鉴定个体265例,并以这批材料撰写了博士论文。顾玉才研究的主要创新点:一,以土城子遗址出土的人骨材料为出发点,对先秦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古中原类型居民”的分布与迁移情况作一个较为系统的总结,他认为土城子战国中晚期居民体质类型与东亚蒙古人种有较多的一致性,与北亚蒙古人种较为疏远,这应该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向北拓地后的移民有关。二,对土城子战国居民人骨进行了同位素研究,同位素显示这些居民食物摄入主要是C4和C3类植物,联系到墓葬中出土动物骨骼并不多,说明狩猎业和饲养业在经济生活中居于次要地位。三,根据钵罐相扣的丧葬习俗推测土城子古代居民一部分可能来自邯郸及其以南赵国所属地区。[29]
顾玉才第一次全面地对土城子古代居民人骨作了研究,他的研究为探讨土城子古城战国时期居民的来源提供了人种学上的支持。
2007年,松下宪一结合考古材料对呼和浩特周边拓跋鲜卑至北魏时期的都城和陵墓进行了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一,拓跋力微对汉代成乐县城址作了必要的修缮和加固,南城内没有类似后世宫殿等大型建筑,中城始建于北魏时期,辽金时期仍在沿用,北城建于唐初,振武军移镇金河后增修了城墙。二,盛乐金陵是定襄之盛乐城附近设立的拓跋皇陵,云中金陵是云中之盛乐宫附近设置的皇陵,未冠地名的金陵是盛乐金陵或云中金陵的略称。[30]松下宪一提出拓跋力微利用了汉代成乐县城的观点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他对中城修建于北魏时期的推测也与考古发现相吻合,但他提出盛乐金陵与云中金陵为两地的观点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2008年,顾玉才对土城子1997—2002年发掘的战国中晚期墓葬人骨进行了性别和年龄鉴定,发现土城子古代居民死亡年龄主要集中在青年期、壮年期和中年期这三个年龄阶段,男女性别比为2.9:1。他认为战争使土城子古代居民死亡年龄提前,也导致城内居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31]
2011年,刘玉成利用土城子古城2001—2003年出土的152例战国颅骨材料进行了牙齿病理学研究,研究的结果是土城子古代居民口腔疾病患病率较高,而且患病后都没有治疗过的迹象,这种情况说明土城子古代居民的饮食以富含碳水化合物的淀粉类食物为主要来源。[32]2015年张群利用土城子2005年出土的34例战国人骨标本材料进行了体质量研究,通过与井沟子居民体质量的对比,得出土城子居民多为守城士兵的结论。[33]
2018年,包桂红、陈永志等执笔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两座东周墓葬的发掘》发表,这篇考古简报中公布了一座东周时期具有晋文化特色的围沟墓,墓葬年代大致为战国中期。他们认为这座墓的形制和殉人等葬俗可能受秦文化影响,反映出战国中期晋文化和秦文化在此地互相交融。从墓葬所处的位置、规模来看,墓主人级别较高,围沟内的殉人为家仆或战俘的可能性较大。[34]
2022年李荣辉、陈永志对土城子古城周边出土的刘如元墓志进行了考释。文章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与唐代中期以后河朔三镇的胡化不同,而与唐朝都城长安保持着一种文化向心力,这与唐朝中期以来,振武节度使一直听命于朝廷,历代节度使都由中央任命有关。[35]
结语
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是内蒙古地区黄河流域建城时间较早、使用时间较长的古代城址之一,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汉代在这里设置了定襄郡,移民屯田,开拓了北部边疆。曹魏时期拓跋鲜卑定都盛乐,以此为起点建立了北魏王朝。唐朝时期中央政府在此设立单于都护府、振武军,加强了对边疆的治理。在整个北部边疆开发史上,土城子古城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的典范,也是民族交融的一个窗口。和林格尔土城子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先可以建立以土城子出土文物为标尺的黄河流域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代序列和谱系;其次,结合文献中土城子地区历代行政沿革的演变和历史事件,尤其是影响北方民族历史乃至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历史借鉴;再次,可以部分还原历史时期呼和浩特地区的社会生产生活、文化交融面貌;最后以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的文化遗产为切入点,系统阐述具有农牧文化交融特征的内蒙古地区黄河文化的孕育、演进与发展的历程,进而为国家黄河文化战略提供借鉴和学术支持。
注 释:
①[清]陈宝晋撰,李晓秋校勘.和林格尔厅志略[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13.
②胡钟达.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初探[J].内蒙古大学学报,1959(00):105-115;薄音湖.从板升到库库河屯的建立[A].薄音湖.青城论丛[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8:102-110.
③[民国]刘汉鼎撰,李晓秋校勘.和林格尔县志草[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207-208.
④[民国]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第二册)卷12·古迹·故城[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83.
⑤[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3:74.
⑥⑨[11][日]驹井和爱.关于绥远的汉代成乐县遗迹[A].中国都城渤海研究[M].雄山阁,1977:72-78.
⑦[12][14][17]李逸友.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墓发掘简介[J].文物,1961(09):30-33.
⑧陈国灿.大黑河诸水沿革考辨[J].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02):109.
⑩[30][日]松下宪一著,王庆宪译.拓跋鲜卑的都城和陵墓——以呼和浩特为中心[J].草原文物,2011(01):111-120.
[13]赵爱军,等.和林格尔唐代窖藏货币[J].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S4):41-43.
[15]张郁.和林格尔土城子试掘纪要[J].文物,1961(09):26-29.
[16]张郁.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发掘报告[A].考古编辑部.考古学集刊·第6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75-203.
[18]张郁.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发掘报告[A].考古编辑部.考古学集刊·第6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75-203;李逸友.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墓发掘简介[J].文物,1961(09):30-33.
[19]专家:呼和浩特出土“耳铸公剑”是晋文公祭祖之器[EB/OL].http://inews.nmgnews.com.cn/system/2015/06/15/011706478.shtml,2015-06-15.
[20]苏哲.内蒙古土默川、大青山的北魏镇戍遗迹[A].国学研究(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545-558.
[2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县南园子墓葬清理简报[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519-524.
[22]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321-326.
[23]陈永志.和林格尔县上土城村发现有明确纪年的唐代古墓[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01):93.
[24]墓志尚未公布,收藏于内蒙古考古文物研究院.
[25]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 219·北狄[M].北京:中华书局,1974:6175.
[26]陈永志,等.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考古发掘主要收获[J].草原文物,2006(01):9-16.
[27]李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出土的战国、汉代瓦当[A].内蒙古出土瓦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43-49.
[28]内蒙古阴山南麓发现大规模辽代墓葬群[EB/OL].http://news.sohu.com/20060428/n24304575 2.shtml,2006-04-28.
[29]顾玉才.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遗址战国时期人骨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7.
[31]顾玉才.和林格尔土城子战国居民人口学及相关问题研究[J].考古学报,2008(01):575-580.
2○3刘玉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遗址战国时期居民的牙齿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1.
[33]张群等.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遗址战国时期人群的体质量[J].人类学学报,2016(04):572-584.
[34]包桂红,陈永志,等.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两座东周墓葬的发掘[J].考古,2018(05):61.
[35]李荣辉,陈永志.唐代单于都护府故地新出土刘如元墓志考释[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22(03):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