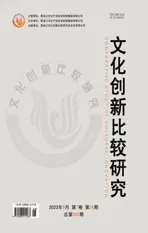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记忆的代际变迁研究
2023-12-12柴华
柴华
(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内蒙古鄂尔多斯 017000)
李素梅教授将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界定为:“形成于蒙古族生存、延续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与蒙古族人民生产生活实际相适应的内容与形式,并在蒙古族儿童中广为流传的综合性娱乐活动。”[1]
位于内蒙古大草原上的内蒙古自治区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就是在本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环境下,逐渐形成的一种世代相传,并深受儿童喜爱的民族传统文化。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不仅具有很强的娱乐性,还能促进蒙古族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增进了蒙古族儿童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党和政府一贯重视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也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中不断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现实危机。当下生活中,蒙古族儿童口中讲述的游戏,如“王者”“吃鸡”;爱不释手的玩具,如 “乐高”“任天堂”等,是其祖辈和父辈在他们童年时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而祖父辈童年时玩的 “海中亥”“赛马” 等传统游戏及 “沙嘎”“蒙古象棋” 等可供把玩的物品,正逐渐淡出当下蒙古族儿童的生活,成为蒙古族长辈脑海中封存的记忆。那么,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是什么因素引发了这些变化? 这些问题引起了笔者的思考。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梳理20 世纪60 年代—21 世纪10 年代出生的蒙古族人关于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记忆的内容,探寻影响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记忆代际变迁的因素,进而探究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的传承路径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方便取样的原则,笔者选取内蒙古自治区E 市和T 市共50 名于20 世纪60 年代—21 世纪10年代出生的蒙古族人为研究对象。其中20 世纪60年代出生的研究对象共5 人,包括男性3 名,女性2名;20 世纪70 年代出生的共8 人,包括男性3 名,女性5 名;20 世纪80 年代出生的共11 名,包括男性7 名、女性4 名;20 世纪90 年代出生的共14 名,包括男性6 名,女性8 名;21 世纪00 年代出生的共7 人,包括男性4 名,女性3 名;21 世纪10 年代出生的共5 人,包括男性4 名,女性1 名。
1.2 研究方法
1.2.1 收集资料的方法
笔者采用访谈法,首先以开放式问题 “关于小时候玩的,您都能想起什么?” 作为沟通的开始,让分享者自由回忆与表达。对于个别分享者出现 “不知从何说起” 或 “词穷” 的情况,研究者则会抛出具体问题来引导分享者,如 “对于小时候的游戏,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您经常和谁玩、在哪里玩? ”“您当时有玩具吗,是些什么玩具,从哪里来的? ”。
1.2.2 分析资料的方法
首先,逐字转录并反复阅读原始资料,从原始资料中抽析出 “地点”“玩伴”“内容”“玩具” 和 “体验” 五大类属;其次,在每个类属下,逐一对每位分享者的资料进行编码和归类;最后,将所有编码按照年代汇总到一起,进行比较与总结。编码示例见表1、表2。同时发现,20 世纪60 年代—21 世纪10 年代出生的蒙古族人记忆中的童年游戏变迁与当时所处年代的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鉴于此,采用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对20 世纪60 年代—21 世纪10 年代蒙古族人的童年游戏记忆进行剖析。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游戏记忆中不变的本质
赫伊津哈认为,“游戏的乐趣在于有一种被抓住、被震撼、被弄得神魂颠倒的心理状态”[2]。访谈过程中,尽管笔者与分享者在语言沟通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从分享者回忆及分享童年游戏时所表现出来的神情和动作中可以感受得到,这种不受时空限制的、百感交集的复杂情绪正是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在分享者内心深处最直观的印象。
2.1.1 自由愉悦、紧张刺激的游戏体验
“游戏的本体性是为游戏而游戏,驱使儿童游戏的根本性动因是游戏自身的价值,即娱乐性,而非外在价值。”“体验是一种情不自禁地沉迷其中、专心致志、物我两忘的心理状态和存在状态。”[3]无论是攻苦食淡的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承上启下的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日新月异的21 世纪,分享者们在回忆自己童年游戏时提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自由”。这里的 “自由”,一方面,是指空间环境的自由,不管是一望无垠的广阔草原,紧密相邻的宽窄巷子,抑或是现代化的城市公园、都为蒙古族儿童的游戏活动提供了无拘无束的游戏环境;另一方面,是身心体验的放松,在游戏过程中儿童可以暂时抛开放牧、耕种、作业等琐事,做游戏的主人,自主决定和谁玩、在哪玩、玩什么、怎么玩,尽管也会受到游戏规则的制约,但这些规则都是经过同伴协商制定的。
在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中,除了益智类、语言文字类、歌舞表演类游戏外,主要还有体育类游戏。体育类游戏是以强身健体和娱情悦性为主要目的,包括博克、赛马、射箭、抛布鲁等。通常这些游戏是以竞赛的形式开展,场面十分激烈,不论是亲身参与者还是围观助威者都会不自觉地沉浸其中,个人情绪随着赛况的起伏而波动,既紧张又刺激。可见,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作为蒙古族人们最普遍、最有趣的娱乐活动,能够使蒙古族儿童的精力得到合理宣泄,有益于儿童的身心健康。
2.1.2 民族亲和、文艺体育的游戏功能
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不仅能使儿童益智健体,从小熟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而且能潜移默化地使儿童产生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凝聚民心、增强民族认同感的作用,上述的体育类游戏就体现出蒙古族人民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在游戏过程中,不仅参赛的儿童相互配合、协作,即便是旁观者也会被紧张激烈的比赛氛围所感染,不自觉地融入比赛中,为同伴欢呼加油。可见,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将个人荣誉与集体荣誉融为一体,对从小培养蒙古族儿童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亲和力起到重要的作用。
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还是蒙古族儿童文艺体育发展的生成点。“只有让游戏成为游戏,其独特的教育性才能发挥到最大程度。”[4]蒙古族传统舞蹈与蒙古族儿童歌舞游戏有异曲同工之妙,如 “筷子舞”“盅碗舞”“骑马舞” 等。此外,很多体育竞赛活动也都是由蒙古族儿童玩耍的体育类游戏演变而来,如 “摔跤”“骑马”“射箭”。因此,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不仅有娱情悦性的功能,还有民族亲和、文艺体育的功能。
2.1.3 留恋惋惜、希冀传承的情感寄托
儿时游戏经历所带来的满足感和欢愉感在分享者的心间仍能久久回味。但在感叹童年游戏快乐与美好的同时,不少21 世纪之前出生的分享者表现出对童年游戏经历的留恋,对传统游戏逐渐消逝的惋惜及对传统游戏回归重建的希冀。
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中蕴含的民族意识需要传承,通过游戏,蒙古族儿童能了解祖父辈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技能,加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是蒙古族儿童社会化的必然过程。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中蕴含的民族情感需要传承,通过游戏,培养蒙古族儿童不惧困难、坚强勇敢的精神意志和积极开朗、乐观善良的性格品质;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中蕴含的民族智慧需要传承,通过游戏,培养蒙古族儿童长远发展的眼光和团结友好的人际关系,这种格局意识甚至延续到分享者的学业和事业中,使人受益匪浅。但是受工业化、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正在日渐消逝,分享者们在提及当下的儿童已经几乎不玩传统的民间游戏时,不免神情落寞,感慨惋惜。同时,也纷纷表示希望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2.2 游戏记忆的代际变迁——基于人类发展生态学的分析
2.2.1 游戏群体的消解
“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是国家调节、干预和指导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政策。”[5]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了略宽于汉族的生育政策。1950 年以来,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大致经历了4 个阶段。第一阶段:鼓励发展人口阶段(1949—1970 年);第二阶段:酝酿和准备计划生育阶段(1971—1981 年);第三阶段:适当放宽生育政策阶段(1982—2015 年);第四阶段:全面二孩、三胎政策阶段(2016—至今)。
在鼓励发展人口的20 世纪60 年代,对于 “逐水草而居” 的蒙古族人来说,每个家庭子女满堂,蒙古族儿童同伴群体的数量充足。在提倡计划生育的20世纪70 年代,党和政府对汉族居民广泛开展计划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 “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的政策。“内蒙古的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始于1988 年,2002 年公告的人口政策中规定:‘蒙古族公民,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夫妻双方均为非城镇户籍且从事农牧业生产,已有两个子女均为女孩的,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三个子女’。”[6]在此少数民族人口政策下,蒙古族人口自然增长平稳。
1981 年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委联合发文《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部分人为了能够享受政策红利(如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政策、少数民族就业政策、民族地区扶贫优惠政策等),纷纷更改民族成分,多数与蒙古族通婚家庭所生子女也均选报蒙古族成分。因此,20世纪80 年代蒙古族人口的社会增长率(即更改民族成分和民族通婚家庭子女选报蒙古族成分) 十分迅速。直到1989 年国家民委、公安部发出《关于暂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蒙古族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在人口数量减少的影响下,蒙古族儿童与玩伴的关系也因之而改变,游戏群体在实质上呈现出逐渐瓦解的表现。
2.2.2 游戏场所的区域化与商业化
游戏场所为儿童游戏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其大小和性质均影响着儿童游戏的发生和发展。20 世纪80 年代之前,蒙古族人多居住在搬迁方便、装拆灵活的蒙古包中,出门即是广袤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天空和成群的牛马,蒙古族儿童可以没有阻隔地、自由自在地奔跑、追赶、玩闹。20 世纪80 年代,城市化发展还未明显波及牧区,在政府 “搬下来、稳得住、能致富” 的政策号召下,蒙古族牧民过起了定居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居住空间由草原上的蒙古包转变为由政府统一规划的砖木结构的房屋。虽然流动性较小,但儿童与邻里同伴结识后便能维持一种稳定持久的关系,于是屋顶上、大树下、地基里、巷子中随处可见奔跑嬉闹的儿童。20 世纪90 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作出了生态移民工程的重大决策,之后退耕还草、禁牧休牧等政策相继实施。传统以草原为生的蒙古族人不得不远离草原,在城镇居住的蒙古族人陆续搬进了单元楼,各家紧闭的防盗门打破了原本亲密的邻里关系,甚至对隔壁邻居都很陌生。儿童的游戏空间大幅度缩小,他们从大自然,从小巷子中消失了,只能选择小区楼下的空地、停车场、楼道或者离家较远的公园。到21 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使得儿童游戏的场地更加区域化、商业化,带有专门游乐设施的公园、有着新型设备的游戏厅获得儿童的青睐,同时电子产品的快速更迭,使得儿童足不出户便可在家中实现自娱自乐。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原本游牧生活的蒙古族人安定下来,蒙古族儿童游戏场所的范围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广阔的草原环境到局限的城市环境;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蒙古族儿童游戏场所的性质也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从非人为的自然环境到人为的商业环境。
2.2.3 游戏玩具的商品化与虚拟化
玩具是儿童游戏的物质载体,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玩具,能达到联结儿童彼此的情感与互动的目的。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内蒙古地区整体的经济、生活水平在曲折中严重滞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蒙古族儿童的玩具更多来源日常生活和大自然,如嘎拉哈游戏中的沙嘎是用羊或狍子等动物的踝骨制成;吉日格等棋类游戏中的棋子是随地捡拾的小石子等。玩具皆就地取材,制作便捷环保,且能满足不同年龄阶段和性别的儿童对于游戏的需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成为民族工作的重心[7],蒙古族居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与此同时,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发展,民族融合不断加深。因此,相较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20 世纪80 年代蒙古族儿童的游戏开始汉化,玩具材料也体现出汉族特色,如打沙包、拍纸片等游戏。但受制于家庭经济条件,20 世纪80 年代蒙古族儿童可拥有的成品玩具数量仍然有限,多数还是自制玩具。到20 世纪90 年代,内蒙古自治区被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发展大幅度提升,工业化速度不断加快,玩具实现批量化生产,由此引发的价格下降也为20 世纪90 年代的蒙古族家庭提供了购买玩具的物质前提,芭比娃娃、电动遥控汽车、仿真手枪、游戏机等玩具进入家庭,蒙古族传统玩具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到21 世纪,普及化社交媒体的宣传,以及独生子女 “小皇帝”“小公主” 的家庭地位对电子游戏产品的销售起到推动作用,受此冲击的蒙古族传统游戏和玩具逐渐消失在蒙古族人们的家庭生活中。目前,很多蒙古族儿童的传统玩具濒临消失,多出现在博物馆中用于展览纪念,或在教育机构中发挥宣传招生和启蒙教育的作用。
至此,蒙古族儿童的玩具经历了从就地取材到批量生产,从自然到虚拟的更迭,也使儿童从 “玩具的制作者” 变为 “商品的消费者”。
2.2.4 游戏文化的汉化与市场化
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作为一种传承的文化形态,在传承过程中承载着蒙古民族自身的社会文化价值。在条件匮乏的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媒体技术并不发达,儿童的学习任务也不繁重,很多蒙古族儿童读不到初中,便回到牧区帮助父母放牧、耕作。历此,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蒙古族儿童的游戏类型非常丰富。如:益智类游戏有嘎拉哈、帕日吉、蒙古象棋等;体育类游戏有博克、赛马、射箭等;语言文字类游戏有好力宝、说九九等;歌舞表演类游戏有筷子舞、盅碗舞等;以及源于生活的游戏有垒牛粪、挖跳兔等。
“1979—1990 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改革开放的探索时期,虽然同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比较明显,但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农牧业生产实现突破性进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族融合不断加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蒙古族儿童所接受的游戏文化逐渐汉化。随之而来的 “应试教育”“超前教育”,以及受此影响而大量兴起的 “兴趣班” 冲击和挤压着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的延续空间。“作业与功课成为压倒一切、占据儿童课余生活时间第一位的事情。”[8]电子产品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在丰富儿童娱乐生活的同时,更是导致幼儿足不出户、沉迷网络游戏的现象发生。传统的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日渐消逝,如今只有在蒙古族传统文化活动,如那达慕大会,以及以蒙古族文化为特色的教育机构中才能捕捉到其身影。
3 悟以往、知来者: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的传承
传承,是连接民族文化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历史之链。对童年游戏记忆的关注也是为了通过回忆重新审视过往,以便更好地面对现在。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必要思考,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的未来之路何往。
3.1 政策制定是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传承的制度保障
纵观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记忆的代际变迁,发现重大变迁时刻均会受到政府宏观政策的影响。如“少数民族人口政策” 使得蒙古族人口平稳增长,而《关于暂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 又使得蒙古族儿童游戏群体逐渐失落;“退耕还林、禁牧休牧” 政策使得蒙古族儿童的游戏空间由邻里之间走向封闭独立;“改革开放” 政策使得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儿童游戏的形式由 “人—人” 之间的亲密接触变为 “人—机”之间的冰冷互动,且游戏内容不断汉化。鉴于此,政府应继续从宏观制度上保障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的传承,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颁布相关的政策、文件或搭建共享平台,进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库建设,给予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相应的保护,确立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在社会中的地位,加深人们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认可。
3.2 正确的游戏观是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传承的思想基础
游戏既是一种活动的形式存在,也是一种精神的实质存在。席勒认为 “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游戏是人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和谐统一,是抛弃了二者限制的自由境界”[9]。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对儿童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分享者表示,正是在童年游戏的游牧蓄养、种植花草和自制玩具等经历中锻炼了身体、学会了热爱自然、感受到生命的意义,甚至潜移默化中掌握了计数、形状、空间等数学知识和想象、创造、审美等艺术情趣。这也充分印证了《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所倡导的,“要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得经验的需要”[10]。同时启示我们,切勿只关注游戏结果而忽视游戏过程及儿童的体验;家长应给儿童充分的时间和机会接触大自然,去玩自己喜爱的游戏;教育者应提供更多的传统游戏资源,让幼儿得以开发、组合、操作,使得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重新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
3.3 课程设置是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传承的新动力
时至今日,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必须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吸取现代幼儿教育的优良经验。而将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与幼儿园课程相结合,无论是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是对现行教育理念的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幼儿园应积极主动收集、整理和组织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资源,深入挖掘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的价值,并将收集到的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资源置于其对社会传统文化传承、儿童个体生命成长价值及儿童实际生存状态的背景下加以开发和利用,积极寻求幼儿园教育教学与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的有效整合和应用。
4 结束语
对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记忆的关注是通过追溯回忆重新审视过往,以寻求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发展的新动力。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对蒙古族儿童的认知、情绪情感、社会性交往能力等方面起着重要的教育作用,其还承载着民族亲和、文艺体育的功能。昔日游戏不再,为使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更好地面对现在,政府应继续从宏观制度上保障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的传承,家长和教育者应树立正确的游戏观,蒙古族儿童民间游戏应与幼儿园课程相结合,寻求其发展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