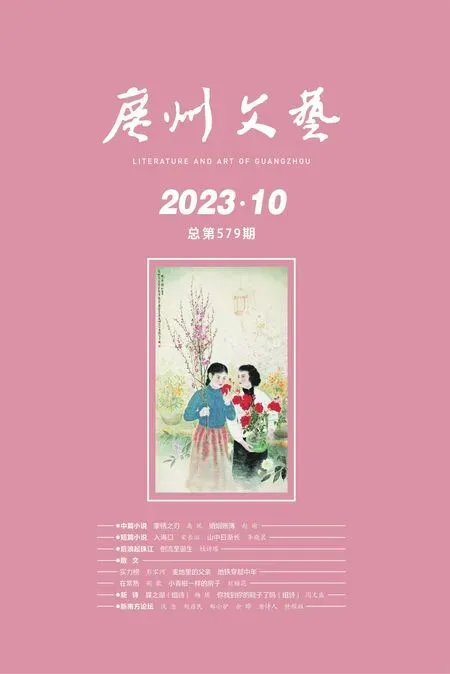写在“新南方”之“北”
——新南方作家访谈·郑小驴
2023-12-11郑小驴
郑小驴 佘 晔
佘 晔:小驴老师好!非常高兴能借《广州文艺》这块文学宝地跟您一起探讨个人写作与文学地理的相关话题。当代文学现场,从来不缺创作素材与引领一时的文学潮流,比如《人民文学》杂志富有前瞻性地提出“非虚构写作”,一时间非虚构作家作品迅速占领各大报刊的重要领地,蔚为大观。我想,在创作领域,紧接而来的便是今天我们所要着重讨论的“新南方写作”了。“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遥相呼应,成为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强势回归的典型创作潮流,并入选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学术研究空间和创作空间都将进一步得到延展。我比较好奇,想知道当您听到“新南方写作”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郑小驴:中国文学的领土和版图意识一向比较敏感,早些年流行各种“文学圈地运动”,作家要保持独立的写作姿态显得难能可贵。我想,首先是写作,才有“南方写作”和“新南方写作”,“新”指向的应是“写作”而非地域变化。对作家而言,无论处于何时何地,文学艺术性始终是最高标准,任何时候都高于其他一切。“南方”作为已经经典化的写作坐标,确实有着鲜明的文学属性,无论是中国、爱尔兰、法国、阿根廷还是美国文学,“南方”都蕴含着别具一格的美学特质,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对中国而言,南方作家语言上显得更为精致和讲究。春节期间和韩少功先生谈及南方与北方作家语言艺术上的差别,他也认为南方作家在语言艺术的自觉性上,要高于北方作家。
提起南方文学,很难绕开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等南方作家,是他们的作品重新定义了南方写作的美学特征。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笔下的生命体验源于血液和记忆,远非外来者所能感知和体验。我在海南生活六年,没书写有关海南主题背景的小说,原因在于语言和物候上的巨大差异性,外来者很难做到真正融入。没有真正地融入,写作必然会浮于表面,很难写出彩。
佘 晔:说实话,我对“新南方写作”的倡导与提法一开始是持保留态度的。一方面,因为对这一术语里面的“新”区别于“旧”,“南方”区别于“新南方”,甚至“南方”区别于“北方”“南方”区别于“南南方”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是必然要有所察觉的,只有将其放在大南方的地理谱系中加以讨论与区分,才能最终确证“新南方写作”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新南方写作”的含义和边界在不断的讨论与研究中,与张燕玲主编最初提出的“野气横生的南方文学”的诗学主张有了极大的丰富与扩展,就作家创作的主体意识而言,您如何看待自身写作与“新南方”的关联?
郑小驴:无论生活还是写作,我都身处南方,我的写作有着鲜明的湖湘印记,这是生命诗学的外在化显现。同时这也是屈贾意义上的南方,无须在写作姿态和文学主张上刻意强调。“新南方写作”是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正如你所言,只有将“新南方写作”纳入大南方的地理谱系中加以区分和讨论才有意义,厘清“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和“新南方文学”的关系很有必要,如果“新南方文学”针对的只是粤港澳大湾区以及相邻的琼、桂区域,那么它更倾向于地理空间而非文学意义上的概念,和传统而言的南方文学并无太大关系,二者无论文化传承,物候、风物、语言、风俗等都大相径庭,无法有效兼容和接轨。
佘 晔:我最初对您的关注缘于“湘籍作家”年度综述的写作,从2015年开始,坚持了五年。当然,现在您又回到了长沙,在大学中文系教创意写作,是从他乡归来的湖南作家了。特别您是从边地“新南方”海南回到“南方”湖南,或者说回到“新南方”之“北”,就“新南方写作”的话题而言,我认为这是写作从“新南方”迁移到南方的生动实践和巨大隐喻,也是作家文学空间突围的稀有经验。您的创作,一直是写在“新南方”之“北”,对此,您认同吗?
郑小驴:我没想过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北方”作家,这确实有些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回过头来看当年选择海南,除了一些现实的考虑,更多的是力图精神上的突围。写作需要走出舒适区,需要多一些经历和冒险。我那时笃信写作不应该过早地与生活和命运达成和解,小说家天生是与某种阻力相抗衡的人。
佘 晔:接着上面的讨论,从早期的《1921年的童谣》《西洲曲》,到后来的《蚁王》《大罪》,再到最近的《南方巴赫》,与“新南方写作”意图呈现的野蛮、先锋、潮湿、幻魅、蓬勃等特质相比,我认为您的创作不仅仅满足于此。由此追问,我们湖湘地理写作的特质是什么呢?它与“新南方写作”存在同构吗?
郑小驴:野蛮、先锋、潮湿、幻魅、蓬勃等美学特征,也是我长期以来的写作追求。无论早期的《天花乱坠》,还是近年来的《骑鹅的凛冬》《去洞庭》《南方巴赫》等作品,都鲜明地具备这些特质,并几乎贯穿我写作的所来之路。
佘 晔:当下有关新南方写作、海洋书写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我认为这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国家战略密不可分。我曾有幸在东莞看到粤港澳大湾区的VR未来影像,也许在未来的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当它变成现实,我深信,我们的大南方抒写必将展现更宽阔的视域和更丰富的尺度。批评家杨庆祥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中对新南方写作的理想特质进行了四个方面的界定: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和经典性。在看到新南方写作经典性缺失的同时又抱有期待,对此,您期待吗?或者说,新南方写作的经典化将何时到来?
郑小驴:“经典化”某种意义上是个时间单位,因为经典化需要时间的洗刷和沉淀,这必然需要经历一定的等待过程。我当然希望“粤港澳大湾区”的明天越来越好,也许用不了十年时间,它就会迎来崭新的一面。但文学有自己的规律,它很难受其他属性所支配。举个例子,经济发达的地区,文学未必繁荣,二者并不成正比,相反我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学反倒有着隐约的期许,因为它们尚未被同质化,依然保留着鲜明的本土特质。说起文学视域,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越是本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想强调一点,首先是世界的,才可能是民族的,文学必须跳出“椰壳碗外”,只有具备世界性的宏观视野,用现代性的目光重新审视本土原始经验,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这可以解释拉丁美洲能产生一大批影响世界文坛的文学作品,而很少有人对毛里求斯土著文学感兴趣的原因。同样,“写好了中国农村,就写好了中国”也具有互文性,只有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族上透彻了解中国,才能深刻了解农村。我们不要被目前一些外在的东西所迷惑,很多作家都搬往大城市生活,这不过是大城市的“文学虹吸效应”罢了。
佘 晔:再回到您的创作,为致敬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您写了同名作品《天鹅绒监狱》,用一座艺术家监狱暗指生活的种种困境,借此探讨中国式“镣铐美学”的意义和价值;新作《南方巴赫》也可视为对福克纳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致敬,“我”与艾米丽的缘分起于网络,终于虚幻,在无法退却的思念、寻找、等待甚至奔逃中,感悟爱的悸动与人的成长,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性。您如何看待外国作家作品对您个人创作的影响?由此念及,中国内地作家、世界华文文学、“新南方写作”群体等具有特定含义的中国文学(作家作品)主动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与建构,我们还将做哪些具体的工作?
郑小驴:我曾经说过,当今的小说洋溢着“透明”的热情,那是一种一眼便能望到尽头的故事,已经沦为类似口香糖的一次性消费品。关于叙事技巧、风格、语言、结构、悬念、隐喻、细节的探讨已经降到最低的标准,一切都在为清晰的主题和健康的思想让道。中国加入WTO已经二十多年,文学也应具有全球化的文学视野,我们每个写作者都是文学共和国的公民。对现代性的追求,对小说形式、技巧的探索应永无止境。我希望“新南方写作”不仅仅是对“南方写作”某种姿态的“标新”,而是将范围进一步扩大,与世界文学接轨,在更大的文学疆域插上“立异”的旗杆。
佘 晔:我曾经论及,您笔下的小说人物多是些难以融入社会的边缘人或有挫败感的青年弱势群体。社会、家庭、伦理、体制在不同人物身上的投射,无形之中使他们的命运发生着偶然或必然的改变,深刻地揭示出时代与历史的风云在个体身上留下的不同程度的伤痕,这种痕迹在同时代人的写作与经历中更能感同身受,正如《南方巴赫》中明星组合S.H.E、QQ空间、漂流瓶等元素在80后一代读者心中产生的怀念一样。您是在“新南方”之“北”进行着对“同时代人”的塑造与抒写。最后,可否分享一下您最新的创作动态以及未来创作的着力点,在期待您给湖南文学带来创作高峰体验的同时,也一同期待“新南方写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终将创造的经验与成就。
郑小驴:我是湖南人,我的血管流淌着湖南人血液,如今我生活在这片熟悉的土地,无论山河故人还是物候风情,都一一滋养着我的写作。我有些写作上的计划,不乏湖南元素的书写,写得很慢,日拱一卒,希望未来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