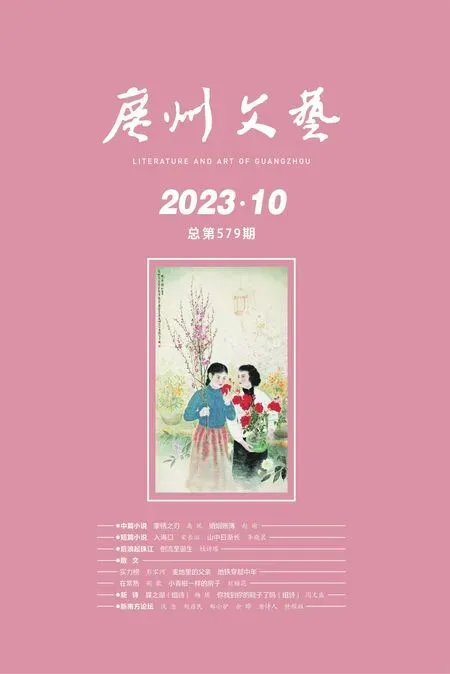在自信心的摧毁与重建中,我向着文学的来处一步步靠近
——新南方作家访谈·沈 念
2023-12-11刘启民
沈 念 刘启民
刘启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采访您。从《时间里的事物》开始,您的文学语言就独具一格,兼有了现代主义的细腻与传统文学的温润。那么在您的写作生涯中,有哪些文学大师的作品,对您的写作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又是什么契机让您主动地亲近他们呢?
沈 念:谢谢。你的提问一下把我拉回二十多年前,我参加工作后疯狂阅读的那段时光。那时我在一所厂矿学校当老师,租居在一幢旧楼顶楼,老房子隔热效果极差,有一年暑假,我就坐在像个蒸笼一样的屋里,靠着一台哗哧哗哧响的电风扇,在大汗淋漓中读完了博尔赫斯的全部小说和《尤利西斯》。
如果像剥笋叶一样地剥掉那件毛茸茸的外套,我的青春时光拥有过的美好,最后残留的核心,激励我鼓足人生勇气的就是阅读。我的阅读偏西方的作家作品居多,我的阅读史也是写作的成长史,那些西方经典作家作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照亮过我的暗夜。这个名单是很庞杂的,如果一定让我梳理,印象最深的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夫卡、鲁尔福、福楼拜、福克纳、卡尔维诺等。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也滋养过我,比如鲁迅、沈从文、彭家煌、阎连科、余华、韩少功、格非等。阅读中有时带来的是雷电交加,让人深受打击,没有信心再去写作;有时是金光万丈,仿佛自己可以驾驭世界毁灭前的诺亚方舟,也就是在自信心的摧毁与重建中,我向着文学的来处一步步靠近。时至今日,阅读仍是消弭我人生孤独的一种修为,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只要回到书房里,我就立刻可以回归安静的状态。人过中年,非常真切地明白,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件事就已不得了,做自己热爱的事,享受这件事过程中的欢欣和苦闷,我非常知足。
刘启民:最近的两三年来,您的写作姿态、写作内容似乎逐渐趋于纯熟。《世间以深为海》《灯火夜驰》《大湖消息》,尽管在关注对象的表层不大一致,不过从某个角度上也都可以归结为对大地之上失语者、沉默者的关注与挖掘。对此,您是否有着自觉的写作愿景?
沈 念:年轻时,每次回到家乡县城,就会四处走街串巷,最喜欢去看那些深居简出的普通百姓。南门堤巷住了一群盲人,过去主要以算命为生,后来有一部分开了简单的按摩店。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为我提供了写作的素材,我由失明者写到失忆者、失语者、失梦者等。这种直接从生活中为写作供氧的经验,会让写作非常有真实感,但这种经验不可复制,也容易随着与生活的远离发生断裂。从这个维度出发,我愿意做一个大地上的行走者,更愿意持续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境遇。每位普通人的境遇一定有着不寻常的地方,如何去发现、挖掘、成像,是我作为写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后来为了写《大湖消息》,虽然有过去许多年的生活经验基础,但还是反复地回到洞庭湖走访。这是一种对时间的确认,对生活变迁的确定。作家是时间里的人,也是改变时间的人。作家在这个时代里生活,就是在创造新的时代与生活的文学记忆。我的下乡经历、记者工作,不仅为我的写作,也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我在这个窗口盼望,看着外面的日月星辰、风霜雨雪,看着走过的足迹和擦肩而过的众人面孔,愈加会从心底告诫自己,认真对待你笔下的文字和眼前的世界,努力写出可以信任的希望和灵魂。这算是我的写作上的一个自觉愿景吧。
刘启民:从早期的作品,到最新的《大湖消息》,我留意到有一种叙述结构和口吻在您的写作史中逐渐稳定、明晰下来,即由一个“我”来观照、书写周遭的外部世界。“我”仿佛是一个人间的游历者,去体验并撰写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您对这样一种叙述结构有自觉吗?您觉得它的形成跟什么有关呢?
沈 念:刚开始写散文,我在写作中形成的思维定式,是习惯由“我”引领读者历览世间、周游世界、感受人生冷暖。以至在后来的虚构叙事中,这个“我”依然被我强调,叙事结构和叙述口吻看得出清晰的影像,甚至变得自觉。我不敢说这种自觉是好的,但它是个人性很强的。它的形成,与写作者介入生活与写作的方式有着深刻而内在的关联。
刘启民:在写作的体裁上,相比于小说,散文是您更擅长的领域——鲁奖作品《大湖消息》就是例证。在您看来,散文体裁相比小说有哪些便利和优势?
沈 念: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最擅长的文体,或者说在外界被认为写得好的文体,所以才会有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之别。也有几种文体能兼顾的作家,但大家心中也只会突出出色的某一点。作为愿意挑战或写作题材与手法宽泛的作家来说,显然都想成为兼顾多文体的人。我也想尝试,或者说是挑战。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的导师阎连科有一次批评同学们没有野心,这种野心其实是指竞争之心、挑战之心。我写作之初,写过诗,后来放弃了,现在主要以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来写作,介入不同的题材。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作家在一直不断探寻和解决的问题,这两方面没有轻重、先后。它会考验你对文体的认知,考验你的生活、知识、思想、情感储备等。我在对自己体验感受深入的领域,会用散文表达多一些,对需要打开更多想象空间的时候,会青睐小说的形式。所以说我在散文驾驭上的优势,还是在于体验深切,因为深切的体验,更容易引起读者共情吧。
中国是个散文大国,古人就已经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散文篇章,“五四”时期又达到了一个散文的高峰,并确立了现代散文的基本框架。我们依然在仰望高峰和在框架之内进行写作,这几年有了突破边界的感觉。有人会讲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实际上文学史的更新就在于变化,任何的探索都会有失败,但你要创新就必须探索。西方现代主义、现代派小说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如果这种影响不疏导它,可能会变成一种干扰,但把它捋清晰了,就会帮写作者重构一种表达。当下语境下,我们的散文书写也应该进行现代叙述意义上的写作。如果说,依然按照过去的路子、话语系统,就会陷入一种传统、经典没法儿超越的境地。文学创作最重要的还是个人性的呈现,没有个人性的东西,就没法儿标识出你的创作特征,可能就是所有人在写同一本书,那你创作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这是我很警惕的。可以说,我在散文里的探索比小说写作走得更远一些。
刘启民:当代的许多湖南作家,往往在临“水”时的写作感觉都散文化了,偏向于抒发性情、描绘情境。如在益阳清溪的周立波写下的《山乡巨变》,当然也包括韩少功定居汨罗后的《山南水北》。您出生成长于岳阳,后来也长期伴着洞庭湖生活,您觉得洞庭湖对您的生命感觉、写作姿态有哪些影响?
沈 念:我在洞庭湖畔生活了很多年,过去并没有深度思考我和湖和水的关系,人过中年,内心逐渐清澈,回望故乡,也是在归去来的过程中,突然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水给了这片土地灵性、厚重、声名,也给了人刁难、悲痛、漂泊,更是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和源泉。但一个难题横亘眼前,面对兴衰变化、原始状态与人工修复,站在审美与人性的双重角度,孰重孰轻,又如何做到不偏不倚,就会成为写作的难度。故乡于我,既是熟悉的写作,又是有难度的。
从本质上说,我对水的认知,是因与那里的候鸟、麋鹿、植物、鱼类而打开的,更重要的是与渔民、保护工作者和志愿者的相遇、相识、相知而加深的。多少次“归去来”的经历,既是回溯光阴往事,也是体察时代变迁。以前我们看到、听到的是人与水的斗争,人从水中的索取,今天的“退田还湖、生态修复、十年禁渔、守护一江碧水”,已经成为人的自觉与自省。面对湖洲之上的生命,我努力让书写视角变得多维。鸟不只是属于天空,鱼不只是属于流水,植物不只是属于洲滩,人不只是属于大地,他们都因为水而联结在一起。水的内涵远比我们见到的模样要丰富、复杂。我带着敬畏、悲悯、体恤,沿着水的足迹寻访,见识了不同季节和生态下的大湖景致,在大湖人身上看到比湖更广阔的性情、心灵。我和他们一样,从水流之中获得力量。我写湖上的日月星辰、风霜雨雪,也写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有情有义的水世界,写水的田野志,写人对生活与自然的领悟,也是写下我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意识。
刘启民:近年来,杨庆祥等批评家提出“新南方写作”的概念,用以概括这两年岭南、两广、港澳等地作家们蓬勃、灵动的写作,以区别北方作家雅正的文风。您怎么理解“新南方写作”?您近两三年的写作,其实也有着回归土地、观照大地生命的倾向,您觉得您的写作与“新南方写作”有何异同?
沈 念:新南方写作,关键是在“新变”。当下的直观理解,新南方写作主要是地域边界的扩展,更偏向于南方以南。这是以往地方性写作的范畴。每个作家都会有他的领地。我觉得新南方写作,不只是地域标志上的扩展,广度之外的深度和复杂度是更重要的,应该是建立在地域之上的写作手法特征化、表现主题多元化等新的变化,有着更为丰饶、繁复、细密、内秀、外放、混沌、浑厚等多种可能性。
我在回顾创作之路时发现,我一直就是在处理从河汊众多、江湖交汇的洞庭湖所生长起来的地方性格、地方经验和地方故事。这是典型的地域概念上的南方写作,但我必定是有新时代的元素加入的。或者说作者的写作理念就是“新”的根本所在。我写水,写湖,写湖区万物,试图写人与物身上散发出的许多气味,水腥味、泥腥味、草腥味等,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鱼腥味”。这是一个地方写作者要守护和传承的,也是需要继续挖掘和深耕的。也许写作者深挖精耕在一隅一地,不离不弃,可能一辈子白写了,但也许又生成了其他意义。好作品的点睛之笔、气质不同之处恰恰就在于个人性,因为这种个人性(鱼腥味)是自然与地方性所滋养并生发(创造)出来的。我想,新南方写作就是要拓展个人性、建立新的个人性。
刘启民:听说您正在书写一部扶贫题材的长篇作品,那是您告别洞庭之后的又一次朝向现实的蓄力。为了这次写作您做了哪些努力?写作中又有什么样新的感受可以与我们分享?
沈 念:准确地说不是扶贫题材,而是一部新乡土叙事作品。我聚焦的地域是南方乡村,具体是在湘西山区。这两年我不断跑下去,去记录那些出走与归来的故事。我反复提醒自己,要真正地身心扎进去,写出它与时俱进的时代之变、生活之变,也写出乡土书写的文学之变。这与我写作洞庭湖不一样,它是刻在我生命中的,是非常熟悉的,但把目光转到一个与生活有距离的地方,让我有了很多警惕。在长篇写作上,我是一个新手,而我愿意我是写作上的新手。是新手就会如履薄冰,是新手也意味着初生牛犊,可以没有负担横冲直撞。
我在写作中特别关注作品的“气”。气息要流动,一气呵成;气韵要自然饱满;气质要贴近书写的对象,同悲共喜;气魄要壮烈激荡,成为作品的灵魂所在。我不是那种有远大抱负的人,但也正是这种“没有”,让我能在一条认定的路上不管不顾地往前走。人都须为选择而背负,好的或坏的、绝望的或倔强的努力。任何一条道路都不会是坦途,文学亦是如此,前面虽有风景摇曳,也得先穿过荆棘和丛林、沼泽与沟堑、黑暗与破碎。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肉体抑或精神,人类所面临的很多困境(生存、精神),那些纠缠不休的问题,大多是相似相通的。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围绕着“人”进行着不同的书写,所以我希望我的写作能不断创造一种新变和越来越阔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