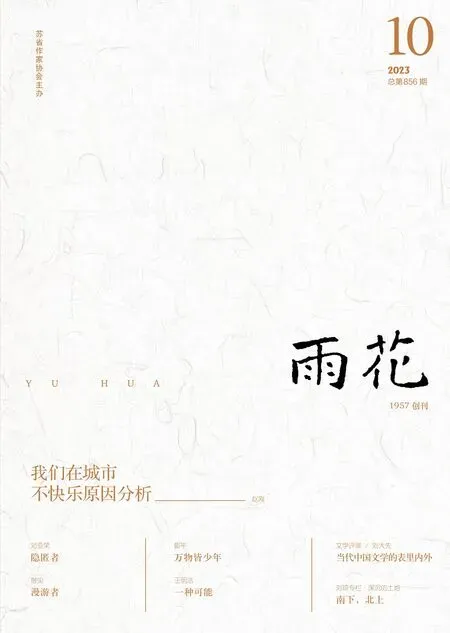县城美人
2023-12-11洪放
洪 放
她坐在二楼的月光里
夜空湛蓝,圆月浮动在天幕之上,若即若离,如同时光中的许多往事,总是游离于时光之外。没有人能说得清所有往事之后的悲欢,也没有人能看得透所有往事之中的哀乐。月光朗照,整个青桐慢街都被笼罩在月光之中。这是最适合与往事相会的时刻,也是最能感知那些过往岁月冷暖与深浅的时刻。
她坐在二楼的月光里。她安静得融入了她身后的美人靠。
慢街是青桐最有故事的一条老街。直尺形,直尺的两边几乎相等,都不过两百米长。街是青石板街面,一米来宽。青石板两边各有一道半寸深的车辙。房子都是砖木结构,一楼为砖,二楼为木。前临街,后临青桐河水。一年四季,房前是人来人往的脚步声,房后是不舍昼夜的流水声。而她,一直就坐在二楼的月光里。她几乎成了月光的一部分,也成了青桐人故事中最隐秘与梦幻的一部分。
老街已经很静了。三百年前,有人在青桐河西岸建起了第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两百年前,慢街已经初步形成了直尺形的街景。同时,那些南来北往的商人和行者,从街南的小码头上岸,一脚就跨入了慢街。他们带来了皮毛、盐、丝绸,同时又将青桐山里的土特产带了出去。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风月。他们将这条直尺形的老街一点点地改造,最后,它成了一条浆声灯影里的花街、酒街。那些二层小楼,笙歌不息,丽影绰约;多少人在此停下了脚步,多少人在这慢街的梦境里,耗尽了青春、泪水与未来。
她只是慢街最后乐章中的一个音符。
她的美,却永久地停驻在慢街之中。
她是青桐一个异样的存在。当年,在郊区的小四合院里,文弱而孤傲的区公所秘书就啜着小泥壶,边感叹边对年轻人说:“在青桐,一定要去走走慢街。而且要在晚上。只有到了晚上,慢街才回到了从前。那是一个多么香艳繁华的时代啊!”
他感叹着,脸上也浮着一层月光般的魅气。
于是,雨后月夜,一群年轻人,二十来岁,从郊外区公所出发,走过蔬菜队的菜园子,从杨家大屋后面的小巷里穿过,再上东大街的南小街。南小街上渍着很深的雨水,那正是梅雨季节,青桐最江南的日子。青桐河里传来青蛙的“咕咕”声,想来青蛙们正在水草之上,对着月光歌唱。南小街的尽头就是溪桥,溪桥那边就是慢街。在过溪桥时,大家突然停下了。月光如水一般倾泻,一整条慢街,像铺着一层银子,在晃悠着。这银子的底色,是那些黑色的二层小楼。而在影影绰绰之中,楼的砖与木都消失了,只有通透的月光,照着那些晃悠的瓦片、亮着雨水的麻石条、木格子的窗棂,以及二楼那微微伸出的小阁—她就坐在那里,像一块玉生长在月光里,又像一把簪子,斜插在慢街已然朽毁的发髻上。
“她有从里到外的冷。”有人说出了声。
是啊,冷,比月光更冷。大家都感到了沁寒。大家都凝视着月光中的二楼,二楼晃悠着,美人靠晃悠着,她也晃悠着。终于,一切都晃悠成了一层更加绵薄的雾气。等我们跨过桥时,这一切都已不见了。
一群年轻人对美的第一次探索,就被慢街彻底地绾结住了。
其实那些年,在青桐城里,慢街与其他的街道,慢街上的人与其他的人,彼此之间总隔着一层河水。看似透明,却格外冷漠。有月光的夜晚,她一直坐在二楼。她将慢街的夜坐成了青桐人的谈资;她不理会,也不辩解。传说中她已经十几年没有下楼了。她最后一次下楼,走在慢街上,还是那个被拖去批斗的下午。她回来后从二楼跳下摔断了腿。青桐人说:她是有意的。也有人说:她那双从江南走过来的腿,经的事太多了,也真的走不动了。“她从江南走来”,这是青桐人所知道的她的历史中最明白的部分。其余的,她仿佛尘灰,无法清楚她的根,也无法理清她的过往。有人说她十六岁就到了慢街,跟着一个富家公子一道过来的。富家公子将她送进这二楼,便永远离开了。还有人说她是二十多岁过来的,而且带着一个孩子。只是那孩子后来死了,她便一个人一直住在这二楼。
如果说慢街曾是一束烟花,那么,她就是烟花中最灿然的那一朵。
但如今,她比青桐河的水还冷。她坐在月光中的二楼,她的美已经失去意义。她只是旧时代遗留在新时代的一个纪念物。她甚至以冷和决绝,与这个她全然走不进去的新的时代,提前做了告别。
慢街的一部分二层楼房在风雨中倾倒了。人们走在废墟上,有人从废墟中挖出了精致的瓷器,有茶壶,有烟嘴,有玉簪,有扳指,当然还有一些小巧的花瓶。这些瓷器、玉器无一例外地深藏在黑暗里。它们躲过一些岁月,却最终在慢街的倾倒中显露出来。那时已是20 世纪80 年代末期了。这些瓷器、玉器被堂而皇之地摆到了旧货市场,而且都标明了“慢街瓷”。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称呼,慢街并不是它们的产地,却成了它们重新回到这个人世间的标识。而最为轰动的一件慢街瓷上居然标上了“慢街美人”。旧货市场的老板说:它来自那个月光中的二楼美人。那是一块玉佩,上面的图案是“红袖添香夜读书”。靠近书本的地方,洇染着一片血丝。有人便问老板如何得到了这块玉佩,老板不答。也没有人去慢街问坐在二楼月光里的美人。玉佩被老板当作镇店之宝,但据说在一个月夜不翼而飞了。
新世纪来临的头一年,直尺形的慢街倾倒得只剩下一小片残山剩水了。她依然坐在二楼的月光里,青桐河水从溪桥流过,发出激越的声响,如同一个人拍打着栏杆,在沧桑地歌唱,并期待着应和。在冬天的一个月夜,我独自走到慢街,推开掩着的木门,从厅里直接上到了二楼。一壶茶正在冒着热气,散发着清香,但人却没了。月光照在美人靠上,我摸了摸,寒凉彻骨。我的心一紧,赶紧下楼,跑到街道上。我没有回头,一直跑上溪桥。再回头,她竟然坐在二楼的月光里,她晃悠着,像一滴墨点到了宣纸上,慢慢地,慢慢地晕散开来……
所有青桐人都记得:那年冬天第一场雪是场大雪,慢街在大雪之中彻底消失。雪停后,人们在清理慢街她的二层小楼时,只找到了一把梳子,却一直没有找到她。
到底是去吃油条,还是去看她?
她就在城墙根边,一字并排的三口锅是她的摊位。一口锅炸油条,一口锅炸糍粑。还有一口锅,形象特殊。它是一只由一米高的铁皮桶加工出来的,锅底烧炭火,锅身贴朝笏。朝笏是青桐一种独有的小吃,形状与古时百官上朝时所持的朝笏相似,其寓意也正是纪念青桐曾经有过的冠盖满京华的盛世。朝笏夹油条或者糍粑,是一套标配。而创造这标配的,正是她。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大家都喊她“炸油条的”。她也乐得大家这样喊。她将头发向后扎起,不高不低、不肥不瘦的身材,正好与这三口大锅适配且服帖。没有风雨的日子,摊位是敞开的。头顶青天,后临青桐残存的最后一段城墙,面前是青桐河。而一旦天气转阴,或者下雨、起大风,便有一支巨大的雨伞,罩着这一整个摊位。早晨六点刚过,摊位前便排起了长龙。这是青桐二十年来从未改变的一处景观—于是,便有了这从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到底是去吃油条,还是去看她?
从一开始在城门口摆一只锅的摊子,到现在有三只锅的摊位,她一直笑着。她的笑是恰到好处的。笑得太过了,让人觉得轻浮;笑得太浅了,让人觉得应付。她的笑,是正好笑到牙齿尖的那种,是从牙尖漫向嘴唇然后漾向整个脸的那种,是轻风吹动一池春水却没有一丝丝声音的那种,是月夜里桂花香甜却异样静谧的那种。她笑着,把刚从铁皮桶里拿出的金黄的朝笏从中间切一刀,但不切断,将正沸腾的锅里的油条捞起,在铁漏上控油,然后折叠着夹在朝笏中间。别看她手小,但巧。朝笏夹着油条,松紧正好,不冒不漏,看着舒服。她将包好的朝笏油条递给后面的人,后面的人竟有些迟疑。她又一笑。她并不看队伍,但她仿佛有一双天眼,她清楚这摊位前所有人的面孔、神情,甚至知道他们从青桐的哪一条街道过来,知道他们吃着油条时的感受,以及在人间烟火之中,这些或老或少、或久或短的客人们的平常生活。
青桐人也同样一眼望穿了她简洁的历史—食品厂下岗女工,在城门口支起一口锅炸油条。二十多年前,摊位转到了老城墙根边。一直到现在,青桐城里很多东西都没了、都变了,但她没变。她每天早晨五点半准时出现在城墙根边。六点,她的第一锅油条会准时出锅。她知道青桐人那个著名的问题。有时,她会在早晨开张之前和上午十一点收摊子时,忽然地想一想。想着,她也没有答案。然后,她笑着,说:这哪是个问题?本来就不是问题嘛!不就是吃块朝笏,包根油条,夹块糍粑?这难道也是问题?
真的,这不是问题。相比于这近三十年的岁月,那些只不过是草叶上的一滴水,尘埃里的一粒灰。她一开始到这老城墙根边时,城墙根边的土里刚长出一棵不到一尺的小树。如今,它长成了一棵快两丈高的青桐树。青桐树枝干光滑,只在树冠部分生长出浓密茂盛的宽大叶片,这好像成了她这个摊子的旗帜。那些过往的客人中,她看着有人来了,有人消失了。有人某一天开始,减少了一套;有人某一天开始,增加了一套。减少与增加,正是生命的常数。这一切,不悲不喜,不声不响,不问不答,都是在偶尔抬头的一瞥之中了然。有时,她也会说一声:日子总得往前过的。有时,她会笑着问:新来的,吃得惯吗?更多的时候,她忙碌着,只在帽子里的头发露出来时,才用手掠一下。很多人就在那一掠之中呆怔着,他们甚至希望那一掠就此打住—他们希望看见朝笏、油条和糍粑,更希望看见她莞尔一笑,和不经意地往额头前的一掠……
在青桐,人们对于美有着严格的界定,同时也保持着适当的敬畏。青桐河水从老城墙根前年年流过,她这个摊位在流水的声响中,风雨无阻,安静而素朴地存在了二十多年。人们吃她贴的朝笏、炸的油条与糍粑;人们被问及:到底是去吃油条,还是去看她?也只有这个问题能在青桐成为一个光明正大的问题。而且,所有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且都不说出来。问题如同老城墙的那些青砖,久了,经过的日子多了,便长出了青苔。那是一种只有青桐才有的泛着蓝光的青苔,特别是春天夜晚的黑暗中,那蓝光有一种令人心颤却矜持自守的美好。
有人不远万里回到青桐,早晨专门到老城墙根边去吃朝笏夹油条。他也排队,也等候,也不语,也在接了朝笏和油条后点点头离开。但是,她是记得的。她记得他少年时的样子,记得他离开青桐时的样子。她记下了无数张面孔,夜深人静时,她会像放电影似的,在这些面孔中穿梭。而他,还有无数的那些面孔,离开青桐的,还在青桐的,他们都记住了她。有些美是不动声色的,有些美在时间的长河中,仿佛青桐河水中的那些水草,年年都生发出明媚。她背后没有故事,她的所有的故事,就是老城墙根边的朝笏、油条与糍粑。她的美已经融入其中,如同朝笏、油条和糍粑,深入,持久,平和,得味。
当然,青桐人也同样看见:在老城墙边的摊位上,头十年,一个男人和她一起在锅边跑来跑去,后来,那男人不见了。再后来,那男人剃着光头,坐在轮椅上;五年前,男人从轮椅上下来,拄起了拐杖;现在,男人会跛着脚,在摊位后面和面、揉粉。而在青桐树下,一个小女孩,长得和她一样美。小女孩唱着歌,跟青桐树一起长大了。有一天,小女孩问她:到底是去吃油条,还是去看她?
她看着涵蕴一切美与时光的青桐河,回头却说:他们是来看城墙!
偌大的剧场和舞台,就她一个人了
架上累累悬瓜果,
风吹稻海翻金波,
夜静犹闻人笑语。
没有伴奏,没有观众,没有灯光,没有舞美—偌大的剧场和舞台,就她一个人了。她站在舞台中间,看着空荡荡的台下。台下那些黄色的木制简单座椅,此刻都安静得让人心痛,它们久违了掌声与那些看戏人所赋予的温暖。它们呆立着,还原成了原始的木头。就像这偌大的剧场,也正在一步步还原成基础的水泥、钢筋、蜂窝状的石棉、玻璃、橡胶、铁钉、木头。没有了戏与戏中人的剧场,只不过是一个废弃的空间。它同那些废弃的村庄、废弃的工厂、废弃的防空洞、废弃的石桥,以及废弃的人没什么区别。即使这一刻,她站在舞台上,也难以抵抗这弥漫的废弃感。连同这舞台,破旧而失去生气的地毯,横七竖八暴露的电线,已经碎裂了的白炽灯,还有耷拉着的两边幕墙上的提词灯箱,它们……她看着,眼里溢着泪水。她唱着,声音一起,整个剧场和舞台,仿佛同时被高明的剑客挑动了神经。她感到脚下的地毯动了下,又动了下。她心里想:原来它们也都还是活着的。它们是在等着我吗?
她继续唱道:到底人间欢乐多……
这最后一个“多”字,每回唱时,她都充满想象。那是一个多么有意思、多么能让人回味的字啊!她想起童年的那片大湖,湖边风吹浪涌,一只小船从遥远的天际慢慢滑向岸边。船上人撑着长篙,唱着乡村小调。那小调淳朴、欢快、戏谑、动情。她听着,跟随小船沿着湖岸奔跑。那时,她尚不知自己的美。而她的美,却如湖滩上的小花,野性而随意地开放着。终于,船靠岸了,船上人停了小调,看着她。她忽闪着湖水一般的大眼睛说:“你刚才唱得真好听,我也要学!”她没想到,这个上岸的渔民成了她的第一个师父。她跟在他后面唱道:
小女子本姓陶,
天天打猪草,呀儿哟;
昨天起晚了,今天要赶早,
呀咳依儿哟,
今天要赶早,呀咳依儿哟。
她俏皮、清秀、灵气,几乎集中了这湖水、湖草、大地、星光与露水的美。她唱着,跳着,湖风将她的声音传遍大湖四周。有人说她是从湖水中跑出来的会唱歌的鲛人,有人说她是从大湖那边的青桐山上走下来的山中百灵,当然,也有人说她是湖水中倒映出来的魅影,她的眉宇间总是含着一缕无法说出却烙在深处的忧伤。她不自知,依旧唱着,跳着。十岁那年,她唱进了戏校。十五岁那年,她进入了当时正红火的青桐剧团。三年后,她成为剧团的主角,就在这偌大的剧场里,她演刚刚解禁的老戏《小辞店》。她演得投入、风流,将柳凤英“演活了”。青桐人排着长队进入剧场,一些外县的人也来到青桐加入了看戏的队伍。
哥好比顺风的船扯篷就走,我好比那波浪中的无舵之舟。
哥好比春三月发青的杨柳,我好比那路旁的草,我哪有日子出头?
哥去后妹好比风筝失手,哥去后妹妹好比雁落在孤洲。
她一口气唱下三百二十句,荡气回肠,有怨有恨,有爱有怜,有梦有醒。剧场和舞台,站满过道的看戏人,都静了。台下的静,台上的情感投入。她没想到:就在那三百二十句唱词之后,就在某一个瞬间,她突然爱上了舞台上的人,她心生恍惚,分不清是在戏里还是在戏外。她扑倒在舞台上人的伞下,所有的看戏人居然都接受了这临时的加戏。她唱着,眼含热泪望着伞中人。她十八岁的心一下子打开了,却在这舞台上一下子又被收拢了。她如同一匹丝帛,在高潮处迸裂,她唱道:
蔡郎哥啊,再会冤家,再会冤家,再会冤家!
这人世的冤家啊!青桐从此多了一个传说。而她,并没有从戏里回到现实。那个伞下的人调走了,这事甚至惊动了师父。师父专门从湖边赶来,他说:“戏是一生的事,情是一时的事。戏是天,情是草。”她点点头,关闭了刚刚打开的蚌壳,让珍珠进入了黑暗。她只留存了唱戏的光明,而拒绝了更多的星光。她在剧场里,在舞台上,在青桐人的目光和想象里;她唱戏,甩着水袖,颠着碎步,陪着戏中人喜怒哀乐。她成了名角,成了光阴中一颗被青桐人反复擦拭的宝石—她没有俗世,只有舞台上和戏里的爱恨情仇。她没有名字,只有舞台上和戏里一个个角色的名字。青桐人将她印在画册里,写在志书里;青桐人觉得她就是为戏而生,她就是戏,戏就是她。她走在大街上的步子,是戏中人的步子。她说出的话、做出的事,是戏中人的话、戏中人的事。青桐人甚至在街心广场,以她为模特,专门立起了一尊雕塑《戏魂》。
她心里的珍珠早已被磨成满腔的泪。然而,她记住了那句话:戏比天大!在天面前,她比尘埃还渺小;她已非她,除了戏,她已无她。
四十岁那年,剧场一下子静了,戏台一下子静了。青桐人将目光转向了另一重花花世界。她其实知道,这样的日子终究会来。但如此之快,让她所有的一切几乎粉碎、封存、支解和湮没。她病了,病得很重。一场大手术后,她独自站在剧场里,偌大的剧场和舞台,就她一个人了。真的,就她一个人了!
她继续唱:到底人间欢乐多!
可是,欢乐呢?这些活过来的舞台、布景、椅子、灯光、字幕、电线、墙壁,还有它们背后的二胡、笛子、琵琶、扬琴、鼓、锣、大钹、小钹……它们都欢乐了吗?没有,一点也没有。它们只不过是再一次在她的声音里,作最后的告别。她唱不下去了,她的嗓子疼痛,喉咙发紧;她的头炸裂,眼睛血红;她身体僵直,四肢石化……她轰然倒在了舞台上。
冥冥中,她似乎听见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描药》,那个呆如木鸡却深情无限的书生,又幻化成了十八岁那年那个伞下的人。他唱道:
一要清风一两整,
二要天上两片白云,两片白云,
三要中秋三分月,
四要银河四颗星,
五要观音瓶中五滴水,
六要王母头上发六根,
七要仙山七枝灵芝草,
八要龙王头上八条筋,
九要石头人九颗胆,
哪里找我的好九妹啊,
英台妹啊,
十要泥菩萨怀中十颗心,
十味药草无一样,
怕只怕我的好九妹,
英台妹,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