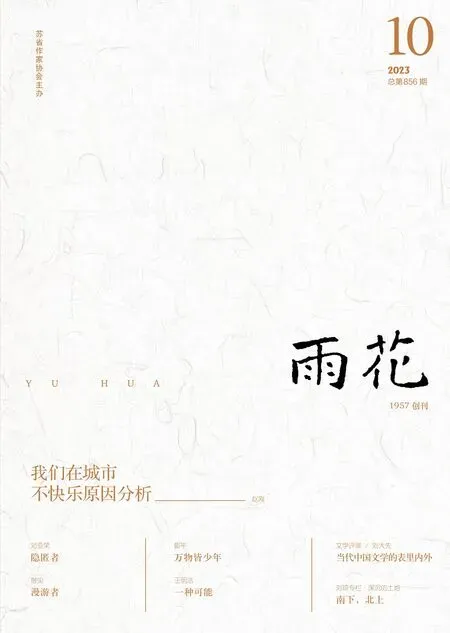青春期琐记
2023-12-11简默
简 默
鲁南。郭城。
我曾经说过,举家北迁是我们家族史上的一件大事。日夜被乡愁缠绕的父亲,为这次北迁精心筹划和准备了十几年,终于在我即将升入初二的那个暑假前夙愿得偿。为此,他不仅成功说服了母亲,让生在贵州长在贵州的她经过漫长的犹疑与动摇之后,最终毅然下定决心,洒泪挥别父母兄弟姊妹们,追随他来到陌生的北方。关于母亲北迁,有一个笑话:她担心北方吃面食,没有大米,自己被南方养大的胃适应不了,就反复地问父亲,要去的地方能吃到大米吗?父亲蛮有把握地说能,母亲才下了决心。父亲没有食言,从定居下来那天起,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到处奔波为母亲购买大米,不仅温暖了母亲物质化的思乡之欲,也满足了我们兄弟俩的胃。
而且父亲煞费苦心地选择了郭城,这个交通便利、出产煤炭和传奇的小城—那时这儿还到处是玉米地、果树林和茅草土屋。其实当时他至少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比如说一个叫固镇的江淮小城,郭城仅是其中之一,但他仍然选择了它。在这上面,父亲其实有点私心,也动了些小念头。我想主要因为郭城属于真正的北方,捋着它出发到埋下父亲胞衣的那个小城费县,不过百余里路程。郭城与费县是一棵地瓜秧上同父同母生出的两块地瓜,尽管连着各自脐带似的根系,但都通向裸露在外的同一条母根。就像父亲青年时怀揣着理想被一列火车从济南拉到了东方机床厂,“到南方去”“到南方去”是点燃他热血的火焰,到了中年又追赶着乡愁被一列火车拉回了郭城,“回北方去”“回北方去”是踢踏前行的滚滚车轮。
一列被漆成春天颜色的火车,载着父亲、母亲、我和弟弟从都匀站出发,“哐当哐当”,一路逶迤起伏,穿桥钻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江苏时缓时快地踮着脚向后退去,湘江、赣江、长江水浪打浪地挽手涌来。地势渐低渐平,视野信马由缰,又见水稻,遍地青绿,泼洒丈余大写意。我莫名地有些兴奋,仿佛早就盼着这一天。这次旅行坚决而彻底,整整三天四夜,火车最后在黑夜戛然刹车,到郭城吐出疲惫的我们。我们举目无亲,像一个个等待被认领的包裹。其实在陌生的郭城和熟悉的沙包堡之间,我们都是被脚步驱赶的盲流。
步我们后尘,半个月后,那些被捆绑了手脚钉进木箱子的家什与我们团聚了,它们是被一列锈迹斑斑的火车拉来的。至此,这次迁徙完成了。黔南沙包堡少了一户王姓居民,鲁南郭城多了一户王姓居民,我们的脚步挺进在天平似的两地间,对两地都无甚影响,却因此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
比如说我。
暑假后开学第一天,我转到了郭城中学。到了这一天,这一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
也是在这一天,郭城中学历史上一下子爆出了两件无颜载入校史的丑闻,并迅速像病毒一样在校园内外流传开来。这让地处荒凉城区的郭城中学猛然热闹起来,像一叶可怜的小舟颠簸挣扎在小城的舌尖与耳鼓间,各种猜测和谣传像水泥和碎石子混杂在一起,被倒进搅拌机里反复飞速地旋转滚动,搅得一塌糊涂。最忧心忡忡的莫过于那些女生的家长。他们是花季生命的父亲母亲,曾经为灿烂花季骄傲、自豪和心疼,但现在却坐卧不宁、茶饭不思,有的筹划着给孩子转学、办理休学,有的甚至干脆让孩子退学。
两件丑闻都指向男人的生理欲望,而这正是女生的家长最担心的。
晨读课开始后,班主任老师将我简要地介绍给了同学们,然后我坐在了靠门边的第三排,班主任出去了,大家开始扯着嗓子读书。我惴惴地打量着周围,我的同桌是一个女生,矮个、圆脸、短发,前排是一个男生,个头比我高,腰杆儿挺直,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恰好挡住了我的视线,却看不到他的脸。正在这时,班主任去而复返,进门站到了门边,一脸的严肃,似乎还有些萎靡,空气立即凝固了,读书声自觉停止了。大家都抬脸望他,等待他说些什么,他却不看我们,叫着一个人的名字,说你出来一下,我惊讶地看到他竟是朝我招着手,叫的却不是我。我前排的白衬衫应声站了起来,迟疑地离了座位,缓缓地向前走去,身体有些摇晃,脚步有些踉跄,柔而黑的头发有些起伏波动,当时我感觉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因为他的肩头也在不由自主地战栗。他在我们火力密集的注视中,终于挪到了门外,跟在班主任身后朝办公室方向走去。胆大的同学起身扒着墙上的窗子往外看,只看到了他的背影,还有同学下了座位蹑手蹑脚地踱到门前,样子滑稽可笑,抓着门框探出半边脸往外看着,他像被马蜂蜇着了似的缩回头说:哎哟,警车!
警车?大家似乎都预感到了什么,但还是不敢肯定它是否与“白衬衫”有关。
前排的书一直那样子摊放着,像两只掌心摊开平放到一起,定格在了第一页,新的学期刚刚开始呀!要定格到啥时候呢?没有谁知道。
挨到了下课,消息像夏日的雨点扑面打了过来,一下子粉碎了我们的想象和猜测。“白衬衫”叫建强,他母亲是这个学校的历史老师,他因为强奸幼女而被告发,被警察推进警车带走了。基本事实如此,具体细节究竟是啥样,说啥的都有,不一而足。
但有人亲眼看到,“白衬衫”被带走时双手戴了手铐,衬衫被掀了上去,蒙住了头,露出了白皙的脊背,白得醒目而耀眼,像一件紧身的白衬衫。
一直到白衬衫被带走,我都没注意到他的脸。本来我是能够看到他的脸的,就在他离位走向前,过了第二排、第一排,向右拐向门口的时候,但我着迷似的被他的白衬衫吸引住了,目光像口香糖黏住了白衬衫,又追随它出了门,最后像一片叶子忽忽悠悠地栽了下来。这过程至多一节课的时间,四十五分钟,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共同在一起的时间。
那书继续那样摊放着,定格在了第一页,第一节是语文课,老师讲的就是这一课,可书在人去,空荡荡的座位像塌陷的地面,多少目光都跟着掉了进去。
上午放学后,那书和书包不知被谁悄悄地拾走了,我们猜是建强的母亲。
第二天,后排的一个男生坐上了这个位子,他个矮、脸黑、鼻尖上有颗黑痣,我从未见他穿过白衬衫。
听说建强被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劳教了。他或许永远不会回来了,即使回来了接着上学,也不会坐在郭城中学的这个位子上了,对这点我们都十分肯定。
与同学们处久了,渐渐地熟悉了,说到了建强。有同学拉我到一面橱窗前,指着里面一张半身照片,说这就是建强。被定格的建强面庞宽阔,眼神俏皮,笑容灿烂,像一个动感强烈的动词,我一下子记住了这张脸,白衬衫反而退居到了脸后。
有一天,同学朝校园的甬道上努努嘴,小声说那就是建强的母亲。我看见一个老人低着头蹒跚前行,漫天黄叶旋舞如飞,追赶着她,像黄蝴蝶围绕着她,映衬着她的满头白发,其实她才刚过四十岁呀,据说那头发也是在建强被带走的当夜一下子全白的,像顶着一头愁绪的秋天芦苇。
几年前,我在小城的人流中邂逅了建强,我肯定地认为那就是建强,是因为那张脸,又让我想起了某个动词。快二十年没见了,他长高长胖了,戴上了眼镜,只是眼神冷漠,笑容也荡然无存了,似乎成熟稳重了许多。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他偶尔瞥我一眼,很快将目光移到了别处,我认为他根本没看到我,也许看到了也记不起啥了,他的眼睛里除了冷漠与平静,没有一丝恐惧与不安,我是一个无法让他重拾往事与回忆的陌生人。
我跟一个同学说了这事,他听了我的叙述后,肯定了我邂逅的就是建强,并介绍说他劳教了几年后,又在外地上了几年学,回到小城后在银行谋了份差使,娶妻生子,但他改了名,也不跟过去的同学来往,仿佛在努力忘掉过去。
下午,我们正在上课,警车一天之中第二次光顾了郭城中学,同样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就像啥都没发生似的。
这次带走的是一位方姓体育老师。下午有他的课,他正在操场上教同学们做仰卧起坐,办公室来人喊走了他,到了办公室,四个警察已经在那儿等他了,他蓦地全明白了。其中一个警察问他:你是方某某吗?他机械地点头。那警察冲他扬了扬一张纸片,说你被逮捕了。他竟下意识地探出了双手,另一个警察“咔嚓”给他锁上了手铐,他被押着推入警车。他没来得及换衣服,仍然穿着那身运动服,脸色苍白像失血了,额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但就在抬脚上车那一刻,他无限留恋地回头望了教学楼一眼,并与站在楼道上扶着栏杆看热闹的一位女老师对接了一下眼神,那女老师脸“唰”地红了,扭身进了办公室。
这一切都是一位当时自始至终在场的老师描述的,他有着非凡的语言表达才能,因此我们听上去像是在看电影,也许电影本身就是生活的翻版,身临其境的电影其实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方某某的罪名是诱奸幼女。那些花季生命的朵数是抽象的,也是惊人的。
据说他与学校的几位女老师也有染。我同学大庆的父亲是学校老师,他家与一位女老师住对门。几乎每天入了午夜,别人早已睡觉了,那家男人都会暴打那位女老师,可能挥舞的是鞭子,也可能是皮带,听得见有人赤脚在屋里没命地奔跑,从这间屋到那间屋,响亮的“啪啪”声抽在肉体上如裂帛,女人撕心裂肺的叫喊与压抑不住的哭泣四处逃散。男人边打边怒吼着追问她跟其他男人的关系,问得最多的就是方某某,折腾够了天也快亮了。这一夜夜惊心动魄,一朵朵黑色梦魇被女老师以血与泪浇灌了,怒放在少年大庆贫乏单调的梦境里,他一次次地像鲤鱼挺身被惊醒坐起。
大庆神秘地跟我说了后,每天早晨上学后,碰到那位女老师,我都会装作不经意地观察她,搜寻她来不及愈合的伤口。我发现每次她都精心化了妆,脸上敷了粉,嘴唇描了口红,但这些粉和口红肤浅薄弱,无力遮住那些青肿淤血,一次次地揭露和出卖了她。奇怪的是她还笑得出来,而且是那种不讨好谁、矜持自负的笑,仿佛雨中一朵伤痕累累又粉面朝天的牡丹花,显得楚楚可怜,不容亵渎。许多年后,我才认识到,这是一个一次次地嚼碎了牙齿往肚里咽,努力将残破的生活像七巧板一样拼接好,然后从容不迫地端到大家面前的女人。
方某某一审就被判了死刑。公开宣判那天是阴历十月初一,上午,我们不上课了,被组织去观看。像过去一样,会场设在了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上,罪犯站成了一排,他们统一穿着囚服,剃了光头,脖子上垂挂着牌子,上面黑字赫然写着名字、罪名、宣判结果,名字被两根鲜红的斜线交叉钉死了,他们反剪的双手被警察牢牢地抓住了。
有人借助扬声器高声讲话,声音回荡在空旷的广场上空,“嗡嗡”声像千万只蜜蜂一齐扇动翅膀。终于讲到了方某某,人群霎时安静了许多,这是因为那天我们全校师生都去了,广场上有一大半都是我们的人,讲到了一个与自己常见面打交道的人,大家感兴趣于他究竟干了啥坏事,被定了啥罪。我说过,我到郭城中学的第一天下午方某某就被带走了,因此我至今没有机会见到他。我踮起脚,目光穿过许多葫芦瓢一样漂浮的人头,看到最前排偏左的一人低着头,刚剃过的头泛着青色,在阳光下像灯泡一样晃眼,但我还是没看清他的脸。据说他长得不错。他脖子挂着的牌子上,白底黑字上被打了红×。
公开宣判完了,准备游街了。方某某他们被推上了草绿色的解放牌无篷汽车,他们并排站在了车栏杆的两旁,仍然挂着牌子,仍然被反剪双手捆绑着。最前方的一辆警车头上立着口大喇叭,反复地解说着他们的罪行,引领着方某某他们的车将郭城几条主要街道走了个遍,惹得人们都跑出来站在路两旁观看议论。
我想跟着再看看方某某长啥样,但大庆一把抓住了我,嘀咕道,跟我来。我跟着他悄悄地游离出了队伍,穿街入巷,来到了两扇黑漆木门前,他推开“吱吱呀呀”的门,进去跟里面说了句话,风风火火地推出了辆大金鹿自行车。他从前面掏上了腿,催着我快上车。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去看枪毙方某某。我听明白了他是想去城外那片乱葬岗,那岗在铁路下面,四周没有人烟,过去是乱丢死人的地方,现在则成了郭城的刑场之一。大庆将车子蹬得很快,车子像肋生双翅飞了起来,我骑坐在后面,风像子弹呼啸着掠过我的耳际,我的衣服灌满了风,鼓胀了起来仿佛就要炸了。拐上了通往乱葬岗的那条土路,车子猛地断链了,倒向了一边,我和大庆摔到了地上,车轮仍在快速地转动,仿佛继续去追赶那要命的枪声。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的刑场不在乱葬岗,而是沙河南的那片荒地。
我到郭城中学第一天,它就以两件沸沸扬扬的丑闻欢迎我,让我很长时间都替那些女生心有余悸,为那些被摧折的花季生命惋惜不已,也羞于承认自己是郭城中学学生。
建强和方某某被带走的第二天,学校开始在各班级清查收缴一本叫《××之心》的手抄本。建强和方某某都是看了这书,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见这书有多么大的毒性和诱惑力呀。
而方某某正是一切罪恶的源头,是他在郭城中学第一个传抄了这书,并送给了自己的男女学生抄看,其中某些女生不幸成了他的猎物。
我们班方某某曾经带过,又出了个建强,是重灾区。班主任安排班长在班里逐个搜查书包,那时金庸、琼瑶之类尚未大举进入校园,因此一无所获。
这么声势浩大的行动,又没彻底讲清楚这是本啥样的书,只笼统地斥之为黄色一类,听说过的、没听说过的,都被勾起了好奇心,蠢蠢欲读,就像后来上生理卫生课时,关于男女生殖教育那两章,老师有意回避不讲,要我们自己看或不许我们看,无论怎样都会使这两章迥然独立于其他章之外,仿佛长势良好的麦地里突然蹿起了两根大葱,大家课上不好意思看,放学回家按捺不住好奇,关上门对照着自己身体看了个够,还不忘将另一章瞧了一遍。
某日下午放学后,在电影公司正拆迁的废墟里,借助残垣断壁的掩护,学勇从贴身的衣兜里摸出一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片说,《××之心》,你看不看?学勇是我们这些人中比较早熟的一个,会唱很多哥呀妹呀的情歌,还会讲许多和尚光头洗澡之类的厕所“荤段子”。我的心猛地一动,接着紧了一下,学勇看出了我的犹豫,假装往兜里装说不看就算了。我迫不及待地伸过手去,迭声说看,看。学勇坏坏地笑了笑。那叠纸片只有三张,攥在手里却像抓住了个惊天动地的大秘密,手轻轻抖动,手心出汗。回到家胡乱扒了几口饭,我支走了弟弟,转身插上了门,小心地掏出纸片展开了,夹在了语文课本间。纸片是用圆珠笔手抄的,字迹小巧娟秀,不是学勇的字,像是个女生写的,由于汗浸和折叠的缘故,有些地方已经漫漶不清了,需要仔细辨认才能读下来。我看着这纸片有些眩晕,可以听见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像在扬臂擂鼓,又像青蛙争先恐后地跳入了池塘,我觉得嗓子冒烟,似乎那颗心越提越高,张嘴就要滑出来。我定了定神,趴在桌上从头到尾看完了那三张纸片,眩晕得更厉害了。我长吁了一口气,不敢再看,小心地收好了,开门站在水龙头下,咕嘟咕嘟地灌了一肚子凉水……
第二天我像逃避蝎子一样将纸片还给了学勇。
入冬了,天气渐渐转冷了,学校进入了休眠似的平静。学勇、大庆、海涛和我,结伴偷偷跑到了城外的沙河,沿着河一直往南走,有片荒地,是郭城的刑场之一。河水没有结冰,太阳有气无力地照在上面,似乎还冒着袅袅热气。大庆提议:我们游泳吧,几个人一齐响应,除去了衣裤,仅穿着条短裤,准备下水。海涛忽然挑逗地问学勇,有人说你只有一个蛋仔?然后一脸坏笑地盯着学勇。学勇被激怒了,像只好斗的公鸡,上前“唰”地拉下了短裤,愤愤地说,看好了,谁只有一个蛋仔?学勇的脸憋得通红,眼睛迷离恍惚,我读出了和我内心一样的东西—火,他手足无措,样子有些痛苦,借口躲到杨树林里尿尿了。
海涛捉弄了学勇,不再管他了,和大庆涉入了水中。我一直很相信自己的预感,它们总在事前轻描淡写或电光石火地提示着我,又在事后嘲笑我的偏执与疏忽,包括隐入杨树林的学勇,我预感到他避开了大家是另外有事。我悄悄地跟在了他身后,远远地我看到他仰躺在落叶间,一把扯下了短裤,他弄脏了自己,然后像死了似的不动了。
我不敢惊动他,但我看到的情景暗示和刺激着我,我渴望表达和喷发,被内心那团火燃烧殆尽,化灰化烟。我不顾一切地跳入了河中,河水冰冷刺骨,激得我打着冷战,浑身涌起了鸡皮疙瘩,我有些绝望,自虐地往水里扎,让水没过我,我用力地揉搓我的短裤,日夜残留的痕迹融化了,手心又黏又滑,水面上浮起了白而碎的泡沫。我感觉火正一点点地消退,水正一寸寸地淹没我,我和我的体温逐渐与水合为了一体。上岸后我特意瞅了瞅那一嘟噜器官,只见它卑怯地缩身了,像一颗拧回去的螺丝,又像一只丑陋的蚕蛹。
晚上,我发起了高烧,满口胡话,吓得母亲慌忙给我盖上了两床棉被,我透彻地出了身汗,溻湿了所有的衣服与棉被,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那晚我究竟说了些啥,没人听得懂,也不会有人在意。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不过是身体与内心压抑不住的呓语,在寻找表达的途径与通道,就像学勇弄脏自己的方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