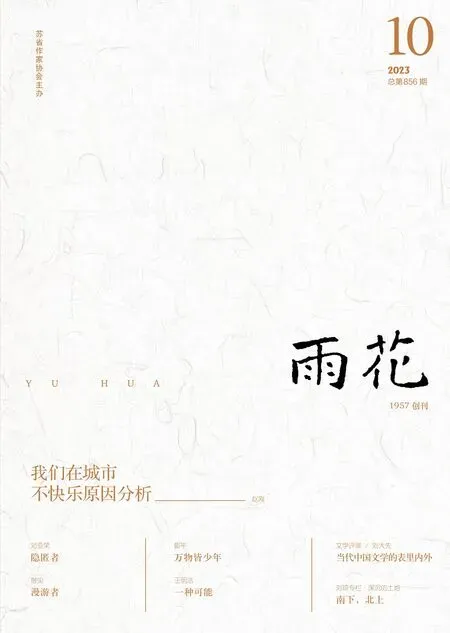漫游者
2023-12-11指尖
指 尖
凛冽的寒风将漫游者无比准确地射入村庄秩序井然的内部之后,开始掀翻他棉袄上大小不一的洞,试图在黑青色的棉絮中寻出他凌厉的秘密触角。漫游者无力地用左手紧紧抓着肩上的空布袋,站在五道庙,尘垢斑斑,茫然无措,像一个束手就擒之后又被遗忘的人。早饭刚过,午饭时间尚未到来,暖村的家家户户,虽大敞着街门,但都缩在屋里吃烟、做针线、等风停。他似乎很为自己来得不巧而感到羞愧,但无法克制的饥饿像一股又一股不能违逆的风,推搡着他不得不成为一支箭矢,闯进村庄来。他的棉衣太大,需要一根绳子来绑在身上,这样当他蹲下来的时候,整个下半身就可以藏在棉袄里面。
早春的阳光渐渐漫过低矮的窑洞,漫过庙院里长青的古柏,趴在南梁的背脊上。喜鹊从远处飞来,停在墙头“叽叽喳喳”地散布消息。是村里的狗们嗅出了漫游者携带的气息,陌生的,危险的,无法接受的。狗们仗着主人的威仪,开始冲出各自的街门,聚集在五道庙,对着漫游者张开大嘴,不停咆哮。整个村庄成为一个回音器,将咆哮声不停放大、加厚、变深,“嗡嗡”地回荡。
等我们这些小娃娃跑到五道庙的时候,漫游者正站在最大的那块青石上,后背紧紧贴着身后干枯的柰子树,手里的棍子四下里胡乱挥舞,被寒风皴得又黑又红的脸上,薄厚不一、深浅各异的尘灰遮掩了他的表情,但我们从他的眼中,还是窥见了恐惧的光,带着泪意。他面前,近十条大小不一的狗围成个半圈,对着他龇牙、吠叫,进进退退中,试图靠近他。
后来我们替他解了围,作为交换,他告诉了我们他的年龄、住址,以及来暖村的目的。这是一个来自河南延津的十岁乞讨者,他为我们描绘出一幅陌生画面:汹涌的黄河水一夜间猛涨,吐着白沫裹着泥沙,“轰隆隆”仿佛惊天动地的雷声,流水冲垮了他们的田地和房屋,吞没了粮食和牲口,扑灭他们的灶火,逼得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沿路乞讨,以求生存。我们不信,温河刚刚解冻,水还小得很。他把左手上挂着布袋子,右手里握着棍子的手臂张开,说黄河是一条很大很大的河,有这么大,河里面翻涌着无数的泥沙和尸体,有马和猪的,也有人的。“八九”一过,黄河上游的冰块开始融化,那些冰比房子还要厚还要大,随着泥沙流到下游,我们那里地势低矮平缓,流水漫过河岸,到处泛滥,差不多每年都遭灾。那怎么就你一个人来村里了?他说,其实是一家人都来你们这里了,我哥去了河对岸那个村子,我爹留在了河上游那个大村。
虽然不到饭点,但漫游者也吃上了食物。吉祥从家里端来一碗酸菜,漫游者的碗竟藏在他的腰带里。怪不得风大呢,有人嘻嘻笑道。酸菜倒在他的碗里,吉祥手里的那根筷子也递过去,他蹲下来就狼吞虎咽地吃。用一根筷子吃饭看起来很怪异,我们便嫌弃吉祥少拿了一根。吉祥辩解道,是他妈刻意吩咐的,说是有忌讳。漫游者并不在意,及至吃完后,用腰带仔细擦拭筷子,确保干净后,又递给吉祥,还作揖感谢。之后将他的碗舔干净,重新别回腰带里。
所有人都将警惕的触角礼貌收回,到午后,他的口袋里装了大半袋子食物,有玉米,有窝窝,还有胡萝卜干。当暖村看不见的出口随着他的消失彻底封闭,风又悄悄回到墙角的腐叶间,开始探头探脑酝酿一场黑暗大戏。那时,我们全然无觉,只是笑嘻嘻地学着漫游者的语调,对着迎面而来的婶婶们不停地喊“大娘,大娘”呢。
漫游者在四月摇身一变为扛着木弓的弹棉花者。我们的弓箭是一根秸秆做成的,因其脆弱易折而被我们嫌弃。但我见过用铁丝做成的弓箭,那是在亲戚家的红柜子上,它跟一辆铁丝自行车一起摆在座钟前。趴在柜子边上,我看了一下午,直到阳光从窗户抽离,将它们推入昏暗的深处。而现在,漫游者背着硕大的木弯弓,随着袅袅炊烟,在黄昏降临时,仿佛沙场归来的英雄。
背着木弓的漫游者被安排在废弃羊圈的窑洞里,有人送来电石和灯盏。五更里,我们被一种奇怪的声音从梦中拽回来了,“嘣嘣嘣”“嘣嘣”,“咚咚咚”“咚咚”,似乎鼓槌敲击鼓面和鼓边,轻轻重重,疏疏密密。我们艰难地睁开双眼,又疲惫地缓缓合上。在散发着电石呛人气味的窑洞里,他从早到晚都在弹棉花。暖村所有人家都在拆被子、拆冬衣,那些乌青死板的棉胎们从包裹它们的棉布中露出真容,虚假而令人失望。我们不相信,穿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花棉袄,点缀着菱形图案的、小花的、小树的棉袄里面,居然被大人塞入这样丑陋而乌黑的棉花。而那张每天睡在里面的,带着阳光香气的被子,竟然隐匿着这么多灰尘、碎屑、虫子尸体、笤帚枝和破棉花。
漫游者显然是神仙派来帮助我们的人,让我们从这些破棉花中脱身,重新回到雪白的、清洁的、喧腾的、热烘烘的温暖中。但我们从未进入过漫游者的操作现场,真切见证棉花苏醒重生的过程。更多时候,我们就站在门外远远地观望,窑洞里飞絮漫天,似乎正在发生一场硝烟弥漫的战争,而漫游者既是这场战争的指挥官,同时也是进攻者和守卫者。他的木弓、木弓上褐色的牛筋弦,以及木槌、铲头,都是他的精良装备。有次我们亲眼看着他从窑洞里出来,浑身沾满了白白的棉絮,头发上、眉毛上、胡须上、衣服和鞋上都是。面对眼前这个看起来像个白毛怪的家伙,我们“哗”地一下全笑了。
夜里,漫游者不知不觉消失于遥远而寂寞的他处。黑洞洞的窑洞里,那些长着翅膀,到处飞舞,找寻落脚之处的棉絮也消失了,整个暖村陷入万籁俱寂之中。妇人们已将旧被面和家人的棉衣外罩缝补妥当,小孩的衣服袖口和衣摆处拼接了一条新布,此时正夜以继日把棉花缝进被子和棉衣之中,她们要赶在五月初一前将它们全部做完。我们常常被母亲们喊住试冬衣,漫游者让我们在试穿一件冬衣的过程中满头大汗。
有天我们被一个很大的声响吓了一跳,漫游者这回是个爆玉米花的人,拥有一架黑铁爆米花机,机器出口套着一条长长的纺布袋,还有一个铁炉子和风箱,他坐在饲养处的炭场边。我们是第一批赶到他跟前的人,但那时他的机器已经在运转中了,周围并没有一粒爆米花的影子,让我们怀疑刚才的响声是他自己爆给自己的。接下来我们参与了他将玉米粒和几粒糖精倒进机器,开始转动手柄,到将机器往袋子口一放的全过程。不久后,他手持一根铁棍往手柄处插,我们便四散开去,躲在柰子树后面,草垛后面,矮墙后面,捂住耳朵,探出一只眼睛,等待惊天动地“砰”的一声。那是让我们心醉神迷的时刻,带着热烘烘的温度和玉米香甜的气味,仿佛幸福来临。早已有小孩跑回家,用搪瓷缸从瓮子里舀了少半缸玉米粒,又从厨房的小瓶子里倒了四五粒糖精包在纸里,掀起炕席,摸出一个二分钱硬币,飞也似的跑回饲养处,搪瓷缸迅速被塞入由簸箕、碗或者量斗组成的队伍中。
更多时候,我们是哄抢从长口袋里跑出来的爆米花的人,哪怕我们已爆好了爆米花,装在簸箕或笸箩里,送回家里,临出门的时候还装了一兜,但重新回到漫游者身边,我们还是会捡拾地上那些披着金黄外衣的爆米花,即便它不小心落在了一堆牛粪旁边。那时,我们的母亲们也加入了观望漫游者技艺的行列,满面笑容,陶醉于氤氲袅袅的烟雾和香气,不停地往嘴里送爆米花,来自她们口腔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听极了。
最受暖村人欢迎的是成为电影放映员的漫游者,他常常秋天来,戴一顶鸭舌帽,穿蓝色中山装、白球鞋。暖村的每户人家都渴望漫游者来家里吃饭,但遗憾的是,这种盼望大多时候会落空。他不常来,一年一两次,大队的派饭是按照一队二队轮流的。所以,他一来,轮到的人家总是挑最好的食物来招待他。
暖村作为黄土高原上的村庄,驻扎在沟沟坎坎起起伏伏的土塬之间,粮食以玉米、谷子和土豆为主,每家最好的饭菜就是酸菜白玉米面饸饹。因气候原因,暖村只种植少量白玉米,所以分到各户更是少得可怜。寻常日子,每家都舍不得吃,只有过年或者八月十五才拿出来,磨成细面,做饸饹吃。偶尔也做馒头的表皮,但因为这是件不易操作的工艺,也很少做。白玉米面看起来很像小麦面粉,颜色发白,细腻,做起来也讲究,里面加的黏面不能是常见的略微发红的粗制榆皮面,是要掺加工更精细的白黏面。漫游者得到厚待,暖村人的愿望就是他能多来几回。
在庙院里,他的放映机发出低低的匀速的“哔哔”声,从机器里射出来的光线中充满暗夜的物质—清冷的哈气、露水,还有即将封冻的泥土、硬邦邦的牛粪、人们的呼吸声。电影放映员沉默、冷峻、不苟言笑,是最像漫游者的漫游者,他随着投射于银幕的那缕强光漂移在村庄上空,用我们未知的力量,不动声色地巡游一番之后,再从另外的出口和入口赶赴其他村庄,从秋天一直到深冬,让每场电影都结束在瑟瑟发抖的寒夜。
有一年,温河的列石在很短时间内承受了一支漫游者队伍的重量,他们走进阁洞,分散进入所有的暖村人家。这一次他们以军人和军队的形式出现,在短暂的二十天时间里,他们完全打碎了我们对漫游者的刻板印象,毫不掩藏地展览着完全不同于暖村人的面孔、语调、姿态和习惯。
从他们到来的那天起,暖村唯一的泉水边上,全是穿军装的漫游者,他们让每家每户的水缸都满溢溢的。我的母亲很为不用站在泉口厚厚的坚冰上吊水而欣慰,虽然她不得不将自己的窑洞腾出来,跟我和祖母住在一盘炕上。似乎我们家住了一个官职大的漫游者,因为他会带馒头回来给我。而我问过禾苗和田园,她们并无此幸运。
他们让暖村变得庞大而充实,庙院里操练声响彻云霄,街上随处都能看到绿色的身影,他们操着陌生而特别的口音从我们身边走过。当他们就要离开时,作为一年级学生的我,将为漫游者们献上生命中的第一次正式表演。我母亲不得不进入漫游者暂住的窑洞,用钥匙打开箱子,取出我表演要戴的新帽子。我跟在母亲身后,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了。这已不是我所熟悉的窑洞,母亲和父亲还有我的味道完全被漫游者的味道淹没,那是肥皂和汗液混合而成的味道,陌生而刺鼻,原本墙上贴着的年画也被一张很大的地图替代。那个军官模样的人弯下身,用宽厚的大手摸着我的头顶,小朋友,是不是今天下午有你的节目啊?漫游者操着陌生的口音,但奇怪的是,我完全听得懂,我点点头。直到一股熟悉的樟脑丸味道传来—那是母亲柜子里的味道,我帽子的味道—我才惊醒过来,拉住母亲的衣襟。
一夜之间,漫游者群离开暖村。直到快过年时,漫游者重回以往秩序,一个人推着独轮车进村,白毛巾在额前系了一个结,风尘仆仆。据说他来自平山,那时我才知道,我们眼中暖村平坦的山河,竟然是一座山峰的截面。也就是说,世界并非一座山峰一条河流这么单调,它由无数座山峰,无数条河流组成,大得无边无沿。而平山就在我们居住的这座看不见边界的山峰脚下,那里有河流和麦田,盛产红枣和红薯,漫游者来暖村,需要在半夜里出发,用五六个小时的时间,爬完由十八个弯盘亘的公路,才能出现在结冰的温河边。寒风中他从暖村的西阁洞里钻进来,露出白白的牙齿和红红的牙龈开始喊叫:“红薯、大枣、柿子、黑枣有得换无。”应该是一个疑问句,但我们听来却是肯定句。
起初,我们不明白,他用红薯、大枣、柿子、黑枣要交换什么,直到有人担着两筐炭出现。我们曾无数次听大人们说,暖村就坐落在一片煤田上面,每年深秋,村里会给每家发煤炭,那时我母亲发愁的是如何将那两小平车煤从二里外的煤矿拉回来。村里的男人,大多都是窑黑子,一到中午,他们头顶电石灯,脚踩高筒雨靴,浑身漆黑地回来,瘆人的眼白扩散着窑洞深处的阴冷、潮湿和神秘。就像红薯大枣是暖村人的稀罕物一样,原来漫游者的稀罕物是煤炭。当然,像我们家这样缺劳力的人家,就没法去跟他交换,那些黑炭在煤场里,它有硕大的形状和无法估算的重量,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抬回来的。但我们会用玉米去换,他说玉米是回家喂猪的。有人试图用一碗抿圪斗去换他几个柿子,但被他拒绝了,他掏出自己的干粮,居然是一个雪白的馒头啊,馋得我们都暗流涎水,随着他的咀嚼和不停吞咽,羡慕和渴望油然升起,要成为一个平山人的梦想,就在下午暖烘烘的阳光里生出形状,并随着漫游者远去的背影渐渐凝结,成为春天门边缝隙里依旧鲜艳的柿蒂。
漫游者也会是穿着雪白塑料底黑布鞋的货郎担子,通过展览五颜六色的颜色和头绳来获取暖村妇女小孩的信任,当他走后,留下的颜色成为一个个令人惊喜的谜底之花,开在我们的枕头和床单上。一个扛着长板凳的磨刀漫游者,将暖村人家的刀具磨得削铁如泥,弥补了暖村男人们的遗憾。有年秋天,看秋的人还抓住过一个偷玉米的漫游者,并将她扭回村里,用麻绳将她的双手朝后绑了。漫游者样貌不同、性别不同、状态不同,但即便如何乔装改扮,我们还是能够通过他略带局促的神情、恍惚躲闪的眼神、略带讨好的语气,乃至他身体和唇齿间散发出的陌生气息,将他(她)准确辨认出来。
记忆里留在暖村最久的漫游者,是一个牧羊人。那时候,村里听力迟钝的牧羊人正在一天天见老,他发红的头发和胡茬渐渐变白,双腿间的缝隙越来越大,已不能赶着羊群爬梁跨沟,甚至从野外卧地回来,他都会生好几天病,他只能跟羊群待在羊圈里,晒晒阳婆,喂喂草料。漫游者就像掐算好暖村近六十只羊急需一个娴熟的牧羊人一样,他跨过温河,穿过阁洞,没有在五道庙停留片刻,直接找到大队部。那年月,牧羊人的报酬是按出勤计工分,年底结算,工分再换算成粮食和少量现金。村里的男劳力,农忙时候最高的公分是九分到九分五,女劳力一般是八分到八分五,所以队里给漫游者定的公分是一天八分工,死分死记。不止如此,队里还批准他住在村里的空窑洞,而不是羊圈。空窑洞是暖村五保户宝玉大爷的住宿地,位于暖村中央地段的一挂两进院的西南角,虽然街门看起来很普通,但里面住了大大小小十五六口人。宝玉大爷故去之后,窑洞由住在同院的侄儿继承,已闲置两年,漫游者的入住,一家人并无异议。他每天夜里从羊圈回来,享受着前后院的接迎,仿佛也是一大家人中的一员。村里人质朴憨厚,对待外人总是和和气气。年轻的单身漫游者用勤快和嘴甜,很快就让大院里的人卸下了防备,作为他打扫院子、担水的酬谢,他也会吃到一碗热腾腾的和子饭,省去了他自己烧火做饭的烦恼。
几个月后,连我们都接纳了他。卸掉披风的漫游者,的确是一个称职的牧羊人,熟知在什么时间将羊群领出村庄放风和入圈,怎样调动羊群走慢、走少、吃饱、吃好,并能及时发现羊群的异样以及母羊发情产羔的情况。
有天夜里,我三岁的妹妹在炕上蹦来蹦去,“嘎嘎”笑个不停,母亲的呵斥并未产生效果,惹得我祖母磕着烟袋锅得意不止,乃至奚落正在看书的我母亲没出息,连个小孩都管不了。就在这种怪异的气氛中,我们突然跌入黑暗深渊,我听见母亲惋惜地叹了口气。祖母烟袋锅里的烟丝随着她的呼吸明灭闪动,这都来了好几天了,该停了。妹妹在黑暗中还在“嘎嘎”笑,且能听见她的小脚在席子上蹦跳时发出的响声,有电的时候这声音倒未察觉,现在这声音之大令人惊讶。突然,“咚”的一声,妹妹的笑声消失了,正在纳闷之际,妹妹的哭声响起。我母亲刚把煤油灯点着,转身回头时,看到妹妹正趴在地上,左臂曲在身体下面,额头和脸蛋上都蹭了灰,母亲赶紧把她抱起来坐在炕沿边上,祖母下了炕,倒了一摊水在妹妹跌下去的地方,让哭闹的妹妹在里面照“娃娃”,然后手在泥水里划了两下,将泥水抹在了妹妹的额头,这一抹,才发觉妹妹额头蹭破皮了。妹妹后来不哭了,但她的左臂却像假的一样,比右臂长了一截,有经验的祖母马上说,这是脱臼了,快,找放羊的。
母亲拉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就往村中走。漫游者的窑洞里空无一人,还在羊圈没回来吧,母亲低声嘟囔。一阵欢笑声从东屋传来,显然他们家点了电石灯,毛头纸糊的窗户上,影影绰绰映着人影,母亲推了我一下说,你喊八月婶子,我便高喊了一声,窗户上的人影便定住了。谁呀?八月婶子粗闷的声音传来,门便开了。漫游者站在八月婶子身后。
漫游者对妹妹说,你伸出手,叔看看。
我妹妹警觉地靠在被子上,我母亲便哄她说,过来,妈抱抱。
三岁的妹妹在那一刻预感到了大人们的阴谋,我后来想,都说小孩长着天眼,也或者是漫游者不小心提前将真实的自己暴露了,让她失去了信任。
祖母用钥匙打开柜子上的锁,取出一小块黄晶晶的冰糖,乖,你过来给你糖吃。
妹妹最终没有承受住食物的诱惑,她慢吞吞走过来,我母亲一把抱住了她,她正要挣扎哭闹,甜滋滋的冰糖到了她唇边。
漫游者这才有了机会,他捏着妹妹的手,看看就好了,说着猛地将左臂向上一提,妹妹“哇”的一声便哭了,张开的嘴巴里,那块冰糖在她舌头上颤抖。漫游者黑红的脸庞闪过一旁,笑着说,好了。
传闻漫游者将终止漫游的使命,他会回到遥远的北乡窝铺,把自己的户口迁来,从此成为暖村的一员。我们为他要去一队还是二队争论不休,有人说他肯定会选择二队,因为八月婶子在二队。那时,关于漫游者跟八月婶子的传闻已经由风和炊烟,经由暖村妇人的渲染传到了我们这些娃娃耳中。似乎八月婶子家里那十几口人也默认了他们的关系,让传言变成理所当然的存在。漫游者不再开灶,也不再洗衣,所有这些八月婶子都承担下来,作为回报,漫游者将自己的粮食、自己存攒的积蓄都给了八月婶子,还给八月婶子置办了闪光的确良衣服和涤卡裤子,乃至承诺年底的工分分红也将归八月婶子所有。八月婶子的女儿比我小两岁,她出门玩耍的时候会跟我们说,她叫她二爹,二爹给她买糖和大寨饼子吃,还割了猪肉。
没有人能提前预知,事件倘若照这样发展下去会怎样。但来年春天,漫游者离开了。他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的时候却带着一个包袱,据说包袱里是八月婶子替他做的两身新衣、两双新鞋。听说两人泪眼相别,但关于其中的缘由,大人们却绝口不提。
正月,我跟祖母走亲戚,路过五六个村庄,穿过长长的笔直的街道,终于看到老姑姑家大门的时候,我突然醒悟,此刻,我跟祖母、跟暖村里的每个人,都可能是漫游者,我们从熟悉的场景走出,再进入一个陌生的、包裹严密的、全然不同的村庄。祖母带来了自己蒸的馒头,那里面包着放了糖精的红豆馅,还有几十个饺子,是用暖村土地上长出来的白萝卜做成的,当老姑姑咀嚼它们的时候,眼里涌出了浑浊的热泪,她说这是暖村的味道,她打小喜欢且在牛村永远做不出来的味道。祖母还带来了一支会开出黄色花朵的玻璃翠,从手巾里拿出来,放在一个黑瓷碗里,并嘱咐老姑姑,要等枝条有了根再往花盆里栽。我看见了老姑姑窗前花盆里那些熟悉的花叶,分不清哪些来自暖村,哪些去往暖村。世上所有的村庄或许并非如铁桶般牢不可破,那些从四面八方到来又远去的漫游者,就像风云或者雨雾,他一定要带来一些新鲜的、陌生的、让人感兴趣或者隐秘的事物和印迹,在改变和摧毁村庄旧有秩序的同时,替代和补偿并开启新的秩序。在老姑姑家,我跟表姐们跳另一种格子游戏,操作更复杂的翻线线,同时我也把自己的羽毛毽子送给了她们,教给她们挽花的技巧,并交流着在彼此听来略感陌生的口头禅……漫游者的功用,大约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