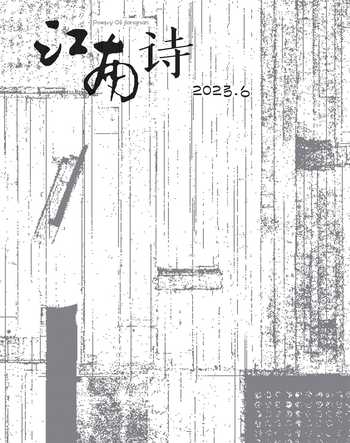生活或者战斗
2023-12-08游子衿
游子衿
认识世宾是在他年轻时候,20多岁,大学毕业后骑着一辆摩托车,每到周末就从鹤山往广州跑,去见他的诗友们:东荡子、黄礼孩、温志峰、浪子、陈小虎、江城……那时候他和广州的一帮诗人一起办了一个诗歌民刊《面影》,而我在梅州办了《故乡》,我们因此相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广州的一个夜晚,在一条散发着臭气的河流边,喝啤酒聊诗歌。那晚还有陈初越、张郁晖在一起,约好的江城没来。
见面之前读过世宾的诗歌,感觉是一种质朴的抒情。他的诗歌里没有太多的象征、隐喻,以及其他一些炫技的成分,而是直接走向言说的中心。会有一些技巧的成分,但都是为了言说的生动而出现的。这样的诗歌,既不那么前卫,也不显得落后,决定诗歌质量的,往往是它展示了什么,而不是它怎样去展示。这是世宾的诗歌的一贯风格,我们今天读他的诗歌,和他初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相比,在风格上看不出有丝毫的改变,他一直就是那样写诗的。我曾多次批评他数十年都在用一种方式写诗,看不到改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想来也许没有必要,因为每个诗人的写作方式都不同。
当然那晚没有说起这些。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处于葳蕤勃发的状态,荒地上冒出了新绿,充满了生长的欲望。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话题,这些话题当然与诗歌有关,但散乱,缺乏方向性,以至于初越感到话不投机,中途告辞。我当时也是孤身走在现代主义旷野上,还没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向,已经许久没有写诗。所以那天晚上到底谈了些什么,我已经彻底忘记了,只记得世宾喝起啤酒来是一把好手,一瓶一瓶地干下去……
那晚的他只是谈论,并不像后来显得那么好斗。
世宾是土生土长的潮州人。潮州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著名的“华侨之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小时候的世宾清秀、机灵,像所有小孩一样好动,爬树、游水,在田野中奔跑。父母都是教师,出身于教育世家,他几乎也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但最后,他成为了一个诗人。
我看过他中专毕业在小学教书时的照片,戴着一副眼镜,青春羞涩的微笑,让他看起来还有一点儒雅,但在我第一次见他时,那一点儒雅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青年奋进的气息,壮实,带着一点莽撞与迷惘。他几乎不谈诗歌之外的话题,但这些谈话多流于枝节,在一些横截面上停留过多,他和那个时候在广州的诗歌兄弟一样,每次见面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诗,但别的诗人几乎无法参与他们的讨论。我曾在一个夜晚去圣地居的一家大排档见他们,在场的还有东荡子、老刀等人。老刀喝醉了,拿着手机在和前妻没完没了地争辩着什么。世賓和东荡子在讨论诗歌,但我听了很久,也没弄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那不是我不具备理解的水平,而是他们显然围绕这一个问题谈了很久,导致这个话题已经失去了方向。
那晚好像是第一次见东荡子,他说没读过我的诗歌,暂时不对我做什么评价,但对我具备的女人缘表示了适度的愤怒。是的,在场还有一位带着眼镜的女人,是他当时的女朋友。
东荡子无疑是对世宾影响很大的一位诗人,他是一位出色的诗歌鉴赏家。因为僻处梅州,和他们一起的机会不多,我不清楚他在诗歌道路上具体给了世宾哪些建议。相比他们的作品,能看见一些接近的东西,尤其是世宾这些年的诗歌,似乎更接近了东荡子诗歌中的某种艺术特征。但他们长年累月关于诗歌的谈论的细节,外人是无从得知的。世宾无疑非常珍视这份友情,在东荡子去世后,他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为这位老友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
我和世宾同岁,说来也是同一茬出道的诗人,但我们在诗歌写作上极少交流。这不仅仅是因为地理位置上的阻隔,更多的是性格的原因。我和世宾与其说是诗友,不如说是生活中的朋友,我去广州时必定会去找他,他也会到梅州来找我。我们在一起游游荡荡,吃饭喝酒,一起处理爱情生活中的麻烦事。至于诗歌,各写各的,很少拿到桌面上来讨论。前一阵子在潮州举办世宾新诗集《交叉路口》的交流会,评论家陈培浩说,我和世宾写的是完全相反的两种诗歌,这话没毛病。也说明诗人之间其实不需要有同样的艺术追求,才可以做朋友,只要在品格上彼此认可,相处起来心里舒服,友情就可以持续下去。在广州的诗歌圈里,世宾经常强调诗人交往的基础是“友谊和诗歌”,友谊就是气质、性情相投,使人在一起快乐;而诗歌使人深邃,两者互相深化。
我想世宾的诗歌风格和他的性格有关。相比很多人,他的心思单纯得多,因而也勇敢得多。他的勇敢体现在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上。在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他在鹤山市政府就职,正儿八经的一个公务员。两年后,他就辞职了,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这个选择本身是需要勇气的。辞职后,他进了《南方都市报》当编辑,在广州租了一个简陋的楼顶单间住下。这份工作没干多久,也辞职了。具体原因依然不得而知,后来约略听他说起,对报社的人事关系并不能适应。书生意气,大抵如此。其后打过一些零工,收入不稳定,生活想来有些困顿潦倒。那时候和他偶尔通一下电话,也感觉到语气的低沉。
勇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还有这么一件往事——
世宾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校门口遇到几个“白粉仔”在纠缠一个女学生,路人都敢怒不敢言。世宾路见不平,上前喝止。一番争执后,双方约定时间、地点决一胜负。结果是世宾依时前往,“白粉仔”却不见踪影。如果说,这是少年意气使然,还有一件事,则是内心正义的选择。多年前,世宾的一位女同事不堪同单位败类欺压,出具一份声明,以证自身清白,请求单位同事签名作证。世宾了解事情的原委,痛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的这位女同事后来跟我说起这件事,说,我一辈子都会尊重世宾。
这份尊重当然也影响了我。
我的生活中缺乏这样的勇者,我自己也不是。我的勇敢只在诗歌生活中存在,在社会生活中我是一个软弱可欺的人。
在诗歌生活中,世宾当然也是勇敢的。
世宾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诗人,他一直都要求自己的诗歌介入社会生活,成为嵌入这个时代的一块砖。可能很多人还记得,在新世纪之交,世宾在广州发起了“诗歌污染城市”的运动,组织一批诗人,把印成传单的诗歌贴满了广州的大街小巷。这个运动是成功的,为越来越小众的诗歌狠狠刷了一把存在感,市民和媒体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据说他们在贴传单的时候,“相关部门”人员发现了,也只是不失礼貌地劝阻,并没有很过分地对待这些举止怪异的行为艺术家们。
但在诗歌写作上,要成功地嵌入这个时代并不容易。2009 年,为寻求突破,世宾躲进小洲村三个月,写出了一批现实题材的诗作,对当时发生的各种社会现象、事件进行诗歌还原与批判。结果可想而知,那批诗歌写得更具有新闻价值,而不具备诗歌价值。包括他那首很多人都读过的《碎了》,还遭我专文痛批。
理念上的形成是容易的,技术上的抵达则需要长时间的磨练。广州是一线城市,来来往往的诗人不少,带来各种诗歌理念的碰撞,身处其中,内心的骚动应是持续不断,紧迫感油然而生。但这种快节奏,却常常破坏了诗歌写作者应有的状态,那就是:沉潜,还有就是放松。一个诗人,如果内心里有个声音,时刻告诫自己:我应该写什么,我不应该写什么,那就是另外一种不诚实,会毁了自己。巴别塔不可能一天建成,建造巴别塔的技术也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那时埋头硬闯,却又找不到出路的世宾,内心应该是苦闷的。但那时候广州的诗歌生活,却又是丰富多彩的。入夜,诗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大约是世宾、东荡子、江城、黄礼孩、浪子、安石榴这么一些人,喝酒,聊天,一群人站在午夜的街头,唱起忧郁的歌。歌词大多是自己写的,我曾听世宾唱起过这么一段:“……姑娘,今夜我们相对而坐,黑色夜空缀满星星,你为什么不说?说出心中的爱情?我望着你,冰凉的面容,望着你,比我的忧伤还长的黑发……”
他说,那是广州诗坛最好的时候,生机勃勃,充满朝气,青春的气息在城市的上空荡漾。
2003年,世宾和东荡子、黄礼孩共同提出了“完整性写作”的诗歌概念,并完成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专著《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这本书于2005年在民刊《诗歌与人》发表,2009年正式出版。随后,由世宾、陈培浩主编的《完整性写作(上、下卷)》出版,汇集了主编者以及耿占春、谢有顺、夏可君、王小妮、蓝蓝、沈苇、朵渔等国内一众大咖的理论文章和诗歌作品,为“完整性写作”站台或背书。当时,我已读过世宾完成《夢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后的初稿,对其观点表示认同。事实上,关于“完整性写作”的核心提法,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无法不认同的。
——“完整性写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创伤性生活的修复,使具有普遍性的良知、尊严、爱和存在感长驻于个体心灵之中,并以此抵抗物化、符号化和无节制的欲望对人性的侵蚀。通过对现实的评判而抵达人的完整,以人的完整照亮现实的生存,直至通过语言重新建构一个诗性的、诗意的世界。
——诗人在他的日常生命里,通过对人类文化的吸收,重建一种新的生命意识,或者说,从日常的、庸俗的生命意识和自我定位里抽身出来,建立一个完整的诗歌人格,以此观照世界,想象新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通过语言把这世界制造出来。
——“完整性写作”要求诗人不断地去追寻人格的自我完善,以良知去观照现实和想象世界,并努力通过语言去创造一个宽阔的、有尊严、有存在感的世界,努力抵达人类的精神深邃之处。
在我看来,世宾“完整性写作”的提出,更像是对这个时代的诗人提出了道德要求,以及对诗人使命感的重申。它本身不具备什么新意,但在当时口语诗、下半身写作等低智商写作泛滥的中国诗坛,它又是有针对性的,像一面鲜亮的旗帜,在风雨中树起,让人重新看见崇高和勇敢并未在中国诗歌中消失。当时尚健在的老诗人郑玲读了《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有这样的诗人,在广州我不再感到寂寞。”
世宾和他的朋友们希望“完整性写作”成为一个诗歌流派,但至少目前为止,这并没有成为现实。一开始云集的诗人、理论家们,自然是表示了认同,但也仅仅是认同而已。对诗歌,他们都有自己已经成型的认知体系,或已经明确的诗歌道路,不可能中途弃之。况且在技术层面,它没有足够地体现挑战或打破现有写作方式的力量,使“完整性写作”停留于一个目标,或一种理论,没有更长久的追随者去实现它。或许世宾也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做一些努力,但近年来,我已经很少听他谈起。
又或许他是不愿意跟我多谈,因为每次和我说起诗歌,若我真实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我们总是会有一番唇枪舌剑,然后就是我很快选择沉默不语。其实他不知道,我是“完整性写作”的认同者,并觉察到它的时代意义的。但我依然有我自己的路要走,认同是一回事,追随又是另外一回事。其他的诗人也大致如此。尤其在广东,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诗人们在一起兴致盎然地谈天说地,回去各写各的诗歌,要他们抱团前行,基本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世宾选择了一种决然的姿态。几乎在任何场合,他都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宣扬他的诗歌观点,不容别人反驳,也不容别人保留,缠斗到底,完全是一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姿态。结果是那些年月,我好几次都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周围的人,坐着的,站着的,等他说完,都不再说话。长时间的静默后,世宾站起来,一个人离开,完成了一个诗坛孤勇者的造影。
“完整性写作”的实施,需要时间,需要一批更年轻的诗人,从更早的阶段,走上这条道路。
但“完整性写作”对世宾本人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当时,他从浪子、黄礼孩等人的书堆中抱走了所有具有参考价值的书籍,黄卷青灯,呕心沥血,20多年来一直在创建和完善这个理论体系。在东荡子去世后,他又往前推动了一步,提出“境界美学”。“完整性写作”的每一个节点,都深深浸透在他的血液里,在生命中流淌。他以后的诗歌创作,都是遵循着其中的准则。
2022年,世宾的诗集《交叉路口》出版。
他的家乡潮州为他举办了诗集分享会,我应邀参加。潮州和梅州是毗邻的两个城市,都是“华侨之乡”,一衣带水,潮客文化相互交融,两市的诗歌界一直来往密切,诗人们更是哥哥、妹妹、姐夫之间的关系。举办一些重要的活动,都会互相邀请,不仅仅因为世宾是我多年老友。
我们在宽阔的韩江河畔见面。1969年出生的世宾已经53岁了。减肥成功,让他的身材显得修长挺拔了些,依然是留着胡子,但和鬓角一起,都有些花白了。他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眼睛偶尔会看着风吹来的方向,看起来不像以前的斗志昂扬。我比较喜欢他现在这个样子,一个诗人,不要总是像一个战士。
分享会举办的时候刚好遇上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奖,其获奖理由为:“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勇气,这个词再次来到我们面前。杨克在发言中分析了中国作家在诺奖评选中的一些情况,关于理想主义在诺奖中不断被强调等。分享会并没有沿着诺奖的话题延续下去,因为勇气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世宾的写作中并不缺乏。我翻阅了一下《交叉路口》里面的诗篇,看见世宾类似《光从上面下来》这种大而无当的诗歌其实是比较少了,他已经更多地关注那些具体而平凡的事物,从中发现一些微小的诗意并提升其价值,体现自己对“完整性写作”目标的趋近。
这未尝不是一个真正令人欣慰的转变,主持分享会的陈培浩也在这方面为他做了辩护。面对我和诗评家向卫国的批评,世宾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说什么。我想这也没什么,每一个成熟的诗人,都知道自己的灵魂被什么所笼罩,星空广阔,无须争辩。
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院子不大,但坐满了来自粤东周边城市的诗人,以及广州来的诗人,韩师的教授、学生。大家轮番发言,有赞赏,有抨击。操办这次活动的丫丫不知躲到哪个角落,偷偷啃我给她带的盐焗鸡翅去了,但现场还有几位不认识的女士,气质优雅,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她们显然不是诗歌圈子里面的人。
第二天一早,礼孩坐我的顺风车去潮汕高铁站乘车回广州。一段比较长的路程,需要40分钟。一路上,我们谈论世宾的诗歌,以及一些往事。慨叹岁月匆匆,我们的身体都大不如前了,该做的事得赶快去做,该写的诗得趁早写。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上世纪末的一个早晨,世宾、小虎和我沿着梅江河岸漫无目的地走,走到梅州迎宾馆时,我们进去上洗手间。我和小虎很快就出来了,在门口等世宾,等了足足有两分钟。世宾经常向我们夸耀说自己的肾功能有多好,我知道他所言不虚。我跟礼孩说,肾是身体的发动机,世宾的身体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他一定还能为诗歌做很多的事情,并且,比我们都将活得更久。礼孩说是。顺便告诉大家的是,礼孩经过漫长岁月的寻找,终于和一位潮州女孩走在了一起,即将成为一位潮州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