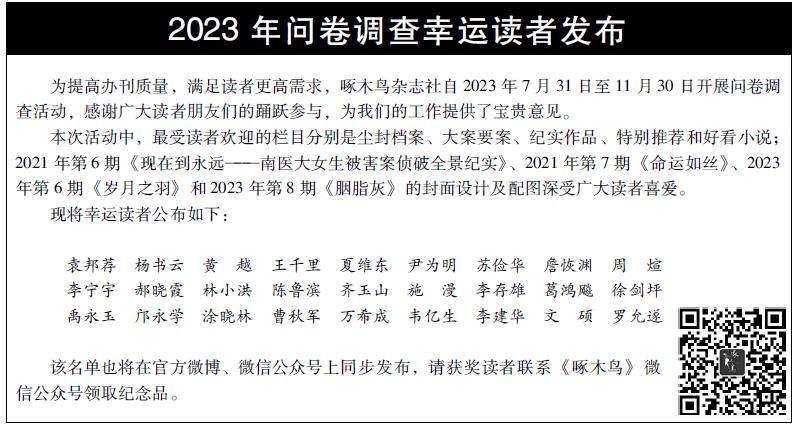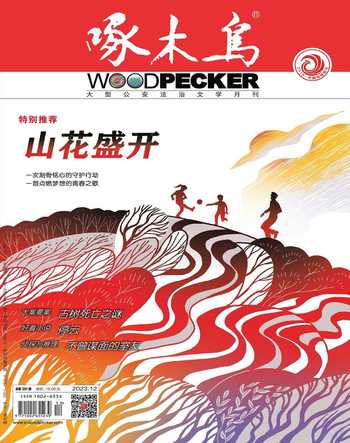不曾谋面的室友
2023-12-06王力
王力

事情要从我收到一件陌生的包裹说起。我没有网购过任何东西,于是断定包裹并不是寄给我的,但地址没有写错,收件人仿佛待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我把包裹丢在角落,希望室友趁我不在时过来拿走。以前追女孩儿吃闭门羹时也是这样,买了一大篮子高档水果放在女孩儿门口,得到的回复是“你悄悄拿走吧”。当然,那时候我是不希望拿走的,而此刻,我却巴不得这个来历不明的玩意儿赶紧消失。
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一看,包裹依然躺在角落里。我立即意识到对于这类玩意儿是不能苛求它自己迈步离去的,有只手精心打包好了一切,所以同样也得有只手把一切都解决掉。
于是,我大度地任凭这位不速之客分享我狭小住处里的一大块地方,继续上班、睡觉,睡觉、上班。我的人生意义仿佛全在这里了。从前那些自己做得津津有味、天真爱冒险的梦以及充满诗意的远方一股脑儿消失在身后,生活淡得像一杯白开水,怎么也品不出味道来。可是,谁不是这个样子呢?除非生活里发生点儿新鲜事来解解乏。哪怕往白开水里放入一粒糖,味道也就不同了。我有些腻歪地想,那个包裹或许就是一段离奇经历的开头。
既然那位不曾谋面的室友忘记了这茬儿,我就得代行职责。想必有位商家焦急地等待着一位客户确认收货,运气好的话还能得到五星好评。人与人的命运总是休戚相关。我拿来剪刀小心翼翼地将包装袋划拉开,里面露出一层新的包装袋。我又将包装袋划拉开,露出的还是包装袋。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玩过的俄罗斯套娃,负责打包这个包裹的老兄大概童年玩具里也有一个套娃。
我一连剪开了五层包装袋,里面的东西还是没有现身,我没了耐心,将拆到一半的包裹又丢回角落里。把它忘到一边后,我继续过着单身汉清贫又自在的日子。下了班去超市里买处理的水果,每到周六下午跑着去两条街之外的超市抢购打折的红薯,像这种精打细算的日子虽然有点儿费脑子,过得倒也充实。相比之下,那种花钱如流水的日子,到最后往往不知道钱究竟花在了哪里,内心只有陣阵空虚。
唯一能改善生活的方式就是一时灵感突发写上一篇文章投给报刊,运气好的话能够发表,然后拿到一笔稿酬。可是我已经有很久没在报刊上发表过作品了,就像一位美人步入迟暮之年,周围关注的目光立刻消失了大半。尽管现实残酷,我依然奋不顾身地写着。
那天晚上,我照例趴在书桌上敲字。无意间抬头,发现窗外似乎有双眼睛在注视着我,只是一闪而过就被我捕捉到了。刚开始,我还以为那是猫的眼睛,老旧小区里总有许多无家可归的猫。有时候我会给它们丢些火腿肠、鱼干之类的东西,就当是行些善事。
不过,这会儿我可没有空搭理它们,我低下头继续干活。当写作告一段落,我站起来活动身子时,发现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着我。那似乎并不是猫的眼睛,而是人的眼睛。因为,即便在夜色中,它也是那么深邃,仿佛潜藏了很多秘密。
活跃在夜色中的往往是窃贼。我不禁哑然失笑,倘若来我这里偷东西,那只能说明他的眼神真的不太好。我这里能偷的也就是桌上那台旧电脑,要是有人把它偷走了,只能把它送到废品收购站,而不是二手电器交易市场。
倘若不是窃贼在踩点儿,那就一定是一名偷窥者。我不禁火冒三丈,趁着活动身体,慢慢向门靠近,然后,突然开门冲了出去。我看见了一个快速离去的背影,就像一只冲进黑夜的猫。我不知道对方究竟看到了什么,心里奇怪地预感到,这个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果然,没几天,那个身影就再次出现在我的窗外。我屏气凝神,打算给对方来个出其不意。结果我还是慢了半拍,对方再一次迅速奔入夜色,只有仓促的脚步声在巷子里回荡。我站在月光下,不知所措。
冥冥之中,命运仿佛冲我打了个响指,一道符咒随之摆在我面前。与此同时,我的创作也陷入了瓶颈。我费尽心力写完的一个故事,自己一遍看下来就觉得索然无味了。这样的东西肯定不会得到编辑的青睐。我开始憎恶那个身影,它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眼前,让我的创作莫名其妙地陷入困境,生活中也有了股莫名其妙的怪味儿。
这股莫名其妙的味道不知从何而来,但它就在我的房间里飘荡,有那么点儿肆无忌惮的意思。这种味道让我厌恶,又无可奈何。它能够隐藏踪迹,就像我那位不曾谋面的室友。我只好去买了瓶空气清新剂,生活又多了一笔开支,我内心极其不快。
我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梦到黑暗中有人蹑手蹑脚地走进我的房间,将一件东西藏进壁橱里,随后突然消失不见了。这个梦似乎在暗示我什么。醒来后,我起身去打开壁橱,奇怪气味的谜团在这一刻揭开了。两只腐烂的死老鼠!我强忍住恶心,将它们装进垃圾袋扔了出去,然后给房东发了条信息。
我说:“你的房子里有老鼠。”
想不到房东没好气地回复:“老小区别说死老鼠,就连死人都有,怕的话住大别墅去。”
他一句话戳中了我的要害,我默默闭上了嘴,买来老鼠药撒在房间里。那股气味并没有完全消散,房东的话在我的脑海里回荡——“就连死人都有”,这究竟是随口一说,还是真有其事?
那股诡异的味道又在我的房间里作祟了!我再次打开壁橱,瞬间惊呆了。两只老鼠赫然陈尸其中!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我明明已经将它们清理出去了,此时,我怀疑自己压根儿没有这么做过。就算是老鼠自己跑进来并死在这里的,也不可能这么巧吧!
第二天出门前,我将一些面粉撒在地上。面粉只是非常浅的一小层,加上室内光线昏暗很难被发现。有一天我回来后,看见面粉上清晰地显露出一只脚印。那一瞬间,我打了个寒战。这就意味着,在这方狭小空间里活动的人不止我一个。
我首先想到房东。可房东大呼冤枉,表示那些天他一直在其他城市游玩。见我不相信,房东还把微信朋友圈截图发给我看,上面显示的地点的确不在本市。我并未就此消除怀疑,我知道朋友圈是可以造假的。
我拍下脚印发给房东看,房东竟然回了句:“你自己带女人回来,事后忘记了吧。”
我气不打一处来,质问他凭什么这么说。房东说:“一看就是女人的脚印,你别告诉我,长这么大你连女人的脚都没见过?”
对于单身汉来说,住处有女人出入或许是生活变好的征兆,可我却是满脑袋的问号。看房东不像是在说气话,或者推诿之类的话,任何事情中旁观者的思维向来最客观。我仔细看了看脚印,的确是女人的脚没错。
至此,我那位不曾谋面的室友总算露出了点儿形迹。竟然是个女人。对此我既感到尴尬,又有些兴奋,期待早日见到她的庐山真面目。但是又一次打开橱柜时,令我火冒三丈的情形又出现了!两只腐烂的老鼠横躺在里面。我敢保证我此前已经将它们清理出去了。难不成它们活过来又回到这里再次死去?
夜晚,那个神秘的身影依旧会在我的窗外出现,两者似乎有什么关联。
之后一天,我外出办事提前回来了,还没走到住处门口,就看到令我目瞪口呆的一幕:有个女人堂而皇之地拎着一袋东西进入我的住处,等她出来已经是两手空空。内心的震惊让我一时忘记了冲上去将其逮个正着,等回过神来,对方已经无影无踪。
直到站在门前,我的脑海里还有一刹那的疑问,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开门进去,熟悉的味道迎面扑来,指引着我来到橱柜前。打开门,两只腐烂的老鼠赫然在目。眼下我都已经懒得发脾气了,我找人换了锁,当新钥匙交到我手中时,我期待生活应当回归正轨了吧。
可是,我在梦中仍会闻到那股味道,醒来之后打开橱柜,里面空空如也。它似乎已经成了我的一个梦魇,久而久之,我的心也麻木了。
夜晚,窗外那双眼睛依旧在注视着我。那个人肯定不知道,我看似在敲字,实则在酝酿将其一网擒获。我关了灯,假装上床休息,眼睛却注视着外面。即便屋内关了灯,对方依旧在那里徘徊着,仿佛某些事还没做完。我下床悄悄走到另一侧的窗户前,打开窗户轻轻翻出去,可我脚落地时还是发出了声响,好在这时有只夜鸟发出一声怪叫,掩盖了我弄出的动静。我已经离黑影越来越近,对方浑然未觉。
我忽然冲上去,一个过肩摔就把对方撂平在地,对方发出一声惊叫,听声音果然是个女的。她挣脱我的手,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半埋怨半嘲諷地说:“打女人算什么本事?”
我一时语塞。女子走进月光里,我看清了些她的模样,居然有些眼熟。对了,她就是此前往我住处放死老鼠的女人。那个脚印八成是她留下的,还有那个包裹估计跟她也脱不了干系。她的身影已经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一个抓住真相的机会就这样被我放跑了。
回到住处,我的目光再次落到那个拆了一半的包裹上,我再次拿起剪刀,像是对准一个惊天秘密。我不厌其烦地一层层拆下去,总算让我探到了秘密的中央。可是,那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
大失所望之余,我更加坚信是那个女人在搞恶作剧。我拿起最外层的包装袋仔细看了看收件人,上面居然写着我的名字。再看名字后面的联系方式,并不是我的手机号码。由此,我也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那位不曾谋面的室友居然和我同名。
更加让我想不到的是,房东突然找上门来,还有两位社区工作者。一开门,房东就指着我对他们说:“你看,人不是好好在这里吗?”
一名社区工作者问了我的姓名,我如实回答。他们将信将疑地对视一眼,朝房东点点头就走了。我一把拉住房东,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房东轻描淡写地说:“小区里有个人好久没出现过了,好像还跟你同名。”
我问道:“他住在哪里?”
房东已经转身离去,扔给我一句“不太清楚”。看得出,他对这件事并不上心。对此,我也不感到奇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只是故事,落到自己头上才叫事故。人们大多如此。
又是一个夜晚来临。我无意间抬头,正好与窗外那双眼睛四目相对。她又来了!真不晓得她在搞什么名堂,我不信她敢当着我的面把两只死老鼠放到我屋里来,也懒得再冲出去将她一把揪住。令我想不到的是,她居然主动来敲门了。
作为单身许久的人,大晚上给一位年轻姑娘开门,不免有些心潮澎湃。她仿佛是刚从月亮中走出来,浑身洒满了银霜。我第一次看清她的脸,那是一张美丽的脸庞,即便在夜色中,黑暗也丝毫没有掩盖她的美。
我礼貌地问:“你好,有什么事吗?”
她没有回答,问了我另一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
我如实说出自己的名字。下一秒,她美丽的脸庞陷入惊讶中。我不知道她究竟在惊讶些什么,只听她喃喃自语道:“不可能,他不可能还在这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意识到她知道这里此前发生的事情,便问道:“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如梦初醒,转头又跑进了夜色中。如此反常的举动,令我忍不住怀疑自己遇上了精神不正常的人。第二天回到住处,我看见门上贴着张纸条,上面写着:“尽快离开这里。”
纸条上的意思再清晰不过,但这句话背后的意思让我摸不着头脑。难道这间屋子里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住在这里的人都会大祸临头吗?恍惚之中,我又闻到了那股味道。我赶紧跑过去打开橱柜,里面什么都没有,那股味道仿佛来自虚无。我的心里忽然升起一阵惶恐,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自己身处巨大危险之中浑然不知,还以为躺在温室里怡然自得。
我一刻都待不下去了,连夜打包好东西搬离。我给房东发了信息,房东回复:“大半夜抽哪门子风?”我不去理会他的挖苦,只想快些离开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新的住处很安静,到了晚上也没再出现站在窗外盯着我看的人,写到一半的故事也有了新思路。生活总算平静了。我意识到,只要拥有平静的生活就足够了,不希望再出现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来搅乱我的一汪静水。
终于有个夜晚,我鬼使神差地沿着记忆中的线路再次走到那里,看见一个身影伫立在夜色中,像是一尊雕像。我走到她的背后,她依然凝视前方,没有发觉地上多了一道影子。直到夜风吹动我的衣服发出轻微声响,她才转过头来。
我看到了她脸上的诧异。她问道:“你还住在这里吗?”
见我摇了摇头,她的表情瞬间舒缓下来。
我听见她告诫道:“不要再来这里,一步都不要踏入。”
“到底为什么呢?”
“不要多问。”
“不知道真相,我会睡不着的。”
“知道了真相,你会更加睡不着。”她的声音犹如警钟敲打在我的心上。
我转身离去,走了没几步突然回过身来大声问道:“原来住在这里的人是不是出事了?”
我看见她的身体明显一颤,语气尽力维持着平静。她说:“他只是离开了而已。”
“搬到哪里去了?”
“他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
对于这个答案我有些意外,又问道:“你怎么知道他离开了?”
她掏出手机打开一位微信好友的朋友圈,对方名字跟我一模一样,想必就是此前这里的住户。他的朋友圈有一条动态,内容是与这个城市告别,背景图片是高铁站前的广场。广场上有很多行人,在地面投下各自忙碌的影子。
看来他们互相认识,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既然人都已经走了,她每晚来这里又做什么呢?还故意把死老鼠放在橱柜里。
关于这个问题,她是这样解释的:那位住户走之前有笔债务没有跟她结清,所以她经常来这里看看对方有没有返回。时间长了,她渐渐失去了耐心,内心开始怨恨,所以想通过放死老鼠的方式来宣泄内心的不满。同时,她也就此前对我造成的困扰表达了歉意。还有个问题她没有解释清楚:既然他们只是普通朋友,她怎么会有那间房子的钥匙呢?只有一种解释说得通,那就是他们关系非同一般。我意识到,她对我说了谎。
尽管内心疑窦丛生,我表面还是不露声色,问道:“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她又翻出一条微信朋友圈给我看,发圈人还是那位室友,内容是:“拥抱新的开始。”文字后面分别跟了太阳和加油的表情符号。这条朋友圈“说说”没有配图,但有定位显示,的确是在另一个城市。
她说:“人都走了,一切都该结束了。”
我点点头,但内心对真相的探寻并未就此打住。那个人的身影是解开所有迷局的钥匙,对于我来说,只有找到他,一切才能结束。
我说:“我想加他的微信,你能推给我吗?”
她一愣,说:“你为什么要加他的微信?”
“我们先后住在同一个房间,还同名同姓,茫茫人海中这种缘分真不多见。”
她有些犹豫,最终还是把微信推给了我。
我加上好友后发过去一句话:你好,我和你住过同一间出租房,我们还同名。
他回复了四个字:幸会幸会。后面还跟了两个握手的表情符号。
我问他:你目前在哪个城市呢?
他发过来一个定位,说:有时间过来玩,你一定不会后悔。
我回复:好啊。
刚刚聊上就邀请我去玩,我感到有些意外,他似乎是个自来熟的人。虽然我们的名字一模一样,性格却是迥然不同,我是个慢热的人。
我想到了那件包裹,并且告诉了他。他回复道:“哈哈哈,送给你好了。”我若是告诉他,那只包裹是由许多包装袋层层组成的,他一定会觉得我在捉弄他。因此,我知趣地保持沉默。
我正盘算着该以什么样的理由去那个城市时,机会突然来到了我面前。单位更换了职工疗休养的合作商,作为首次合作的福利,对方提供了一项疗休养套餐,地点竟然就在那个城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那里。
由于报名人数太少,此次疗休养差点儿没能成团。我刚一到达那座城市,就给他发去了消息,并分享了位置。老半天后,他回过来一个惊讶的表情符号,大抵完全没想到我会来。
我试探性地问道:见一面呗?
他回复:我排排时间看。此前热情的邀约顿时显得言不由衷。
几个小时后,我看见他发了条微信朋友圈,是关于养生的一条顺口溜,显然是为了带货。我念了一遍,感觉还挺有味道。我又看了一遍顺口溜,留意到下面还有个手机号码。我忽然有了个想法,以买东西为借口与他见面。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专门去买了张新的手机卡。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电话接通后对方是个女人。女人似乎得了感冒,说话声音听起来有些变声。
即便生了病,也毫不影响對方保持头脑清晰。女人首先盘问了一番我的个人情况,有些方面问得特别细,就像一次身份验证。幸亏我事前做了周密准备,每个问题都答得滴水不漏。消除怀疑后,女人马上向我表达了歉意,表示自己其实卖的都是逃税的奢侈品,因此格外谨慎。
我们约定了交货地点,交货时间在晚上。我电话里问她:“不能上门提货吗?或者送货上门也行。”
她回答:“抱歉,不方便。”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买个补品也搞得跟特务交换情报似的。不过我意识到一件事,见面前最好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此次见面可能会是他本人来,也有可能他安排别人来,而他本人则在暗中观察。吃这碗饭的人大多长了不止一个心眼。
我在大街上走着,看见一条蜿蜒的弄堂,里面七拐八绕的,仿佛有很多名堂。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竟然来到一家美容店门口。真是奇了,这种地方还会有美容店,店老板难道不怕天天门可罗雀吗?店名叫“一次性变脸”,这是什么古怪的名字?好奇心让我迫不及待地推门进去。
一个年轻男人从吧台抬起头,笑容可掬地说道:“欢迎光临,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
我说:“你们这儿主要有什么服务?”
男人接下来说的话让我惊诧不已。“我们可以帮你暂时改变面部的某些特征,当然,那只是一次性的,持续不了太长时间。”
我问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男人回答说:“那就说不清了,可能你想暂时躲避债主,但又不得不出门去。可能你不想让前女友认出你来,也可能为了某些不寻常的会面。”
他最后一句话让我心里一紧,这不正是我当前需要的吗?我坦然接受了他的服务,结果证明他也不是个说大话的人。再次站在镜子前时,我相信,哪怕是我父母见到我都不一定能认出来。我高兴地付了钱,顶着一张崭新的脸走出店门。
男人在后面招呼道:“再来啊!”
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来,也许吧。
见面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对方的警惕心。我只是对面部做了乔装而已,而对方直接戴上了一只大号的口罩,面部除了眼睛以外的部位全都遮挡住了。
交完貨,我付了钱,对方冲我点点头,转身就走。全程居然半个字都没有说出。我站在原地,目送着夜色中那个远去的背影,忽然感到有些眼熟。我也判断不出对方究竟是男是女,只隐隐觉得那是个女人。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看着一地月光,久久没有睡意。我再次给他发了消息,对方回复很快:最近生意忙得晕头转向,有些事情说过就忘记了。
我揶揄他道:当老板就要日理万机,逃不掉的。
他回复了一个憨笑的表情符号,之后就不说话了。我能够感觉到,其实他是不愿意跟我聊天的。
第二天下午,我看到他发了条微信朋友圈,背景图片是电信营业厅的柜台,内容是表达对电信服务的不满意,也显示了定位。看到这里,我立马有了方向——去跟那个柜台的工作人员聊一聊。
我不知道这个城市里究竟有几家电信营业厅,手机上一查顿时吓了一跳,乖乖,大型的营业厅就不下一百家。我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必须做到精准定位。幸运的是照片中的柜台上贴着一张广告纸,内容是刚刚推出的一项入网套餐。我打客服电话进行询问,很快就获知了那家营业厅的地址。
提起与他的纠纷,工作人员至今一肚子气。听她发完牢骚,我笑着说:“因为这点儿小事发脾气,看来这位先生实在没有风度啊!”
工作人员立马反驳道:“那人不是男的,是个女的,年纪轻轻脑子却不好使,我嘴巴都快讲干了。”
我问她:“你确定是个女的?”
工作人员无比笃定地回答我:“绝对不会错的,就是个女的。”
我似乎又离真相近了一步。可惜除了记忆中一个模模糊糊的背影外,我没有那个女人的任何照片,不然拿给工作人员一看,很可能立马真相大白。从营业厅出来后,我一直站在那里等,直到那位工作人员下了班出来。
见到我,她一脸诧异地说:“你怎么还没走?”
“等你啊。”
“等我?”
“是啊,想请你吃个饭。”
她的脸飞快地红了起来,用一种言不由衷的语气说道:“我有对象的哦。”
我分明看见她左手食指上戴着一枚戒指。一位有男友的姑娘通常情况下是会对其他异性保持必要冷淡的,就连说话语气也应该如此。
我直接戳穿了她的谎话:“哈哈哈,是嘛,那我觉得你手上的戒指恐怕戴错位置了。”
她立马低下头去,脸上的红色更加鲜明了。对方的心理防线已经松懈下来,我趁机拉了拉她,说:“走吧,不要拒绝一位男士真诚的邀请。”
一顿美餐过后,她开门见山:“天底下没有白吃的饭,现在可以说说你想要我帮你做什么了吗?”
我也毫不掩饰:“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人。”
“男人还是女人?”
“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
我看她明显愣了一下,估计她此前从未听过这么离谱的话。
“你为什么不找警察帮你呢?”
“我怕他们以为我神经不正常。”
“的确有些离谱。”
“那你能否帮我呢?”
她耸了耸肩,说:“吃人嘴软,我想我已经没有选择了。”
“谢谢,对了,怎么称呼你?”
“戴玲玲。”
“好的。我想找的就是那次对你发脾气的顾客。事实上,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找这个人,但有迹象表明,我要找的人和那天你见到的人可能并不是同一个。”
“你的意思是,有人利用别人的身份在从事某些不正当的勾当。”
她果然很聪明,我也更加有了信心。
“你说的一点儿不错。”
戴玲玲忽然想起了什么,说:“我突然想起来,那人虽然是个女的,但是登记用名像个男人的名字。”
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在我的脑海里冒出来:我那位不曾谋面的室友压根不在这个城市。所有的一切都是有人冒用他的身份、交友工具等制造出来的假象。倘若真的如此,那么他此时又在何处?是否还在人间?这些问题都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戴玲玲按照我的吩咐联系了对方,说明其电话卡在月流水转移备案时遇到点儿问题,需要本人前来确认。为了确保对方肯定会来,戴玲玲还强调如果规定期限内不来办理,卡内余额将会被冻结。如此做法有点儿滥用职权,不过她甘愿冒一冒险。
这一招奏效了!等对方来到柜台,戴玲玲按照流程对其进行了月账单流水确认的操作。柜台上巧妙隐藏了一台微型摄像机,将对方的整张脸都拍了下来。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对方戴了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不过足够了!我确认那双眼睛此前多次进入我的视线。尽管我心里早已隐约预测到了,但还是感到非常惊讶。她居然也在这个城市,而且冒充那个和我同名的人。而那个人现在又在何处?
西餐厅里,戴玲玲饶有兴致地将一块煎牛排大卸八块,我却连刀叉都没有动。戴玲玲很快将自己的煎牛排吃完,又端起罗宋汤慢慢品着。到底是局外人,一身清闲。而我与她刚好相反,此时正陷入深深的迷茫中,即便美味的煎牛排也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戴玲玲已经把自己那份全部吃完了,看着呆若木鸡的我,说道:“先吃点儿东西,好吗?”
我拿起刀切了一小块牛肉,送到嘴里食不知味地嚼着。她大概知道我这会儿并没有什么闲情,主动帮我将牛排切成小块。我注意到她的手法很娴熟,切开的每块牛排都差不多大小。我与她四目相对,看见她眼睛里有几分担忧。我拿起刀叉将牛排一块块送进嘴里,又将罗宋汤喝得一滴不剩。看得出来,她在为我担心。
见我吃了东西,她脸上的担忧舒缓下来,还拿起纸巾帮我擦了擦嘴。她对我说:“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件事交给警察去做。”
我并不认同她的想法:“眼下也没有充足证据证明这是个案子,哪怕告诉警察,估计他们也未必肯理会。况且我如今卷入其中,就有义务把真相找出来。”
她笑了起来,说:“你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你错了,我哪怕撞了墙也会接着往前走。”
女生通常不太会对一个爱钻牛角尖的男生产生多少好感,但是听完我的话,戴玲玲臉上浮现出明显的赞许。我也好意思再开口请她帮忙。
那个女人居然主动联系我了,说是他们推出了一份保健品套餐,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当然有兴趣,这可是送上门的机会啊。我问她有多少,她回复要多少有多少。好极了,我可以马上展开自己的行动。
关于接下来的行动我是这样安排的:联系上她,谎称我把业务介绍到了单位,有很多同事都有意向购买,然后由单位工会主席出面与之商谈。当然,我需要请戴玲玲来假扮工会主席。
对金钱的渴望是人性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把本钱下足,不怕她不会上钩。关于我的这个计划,戴玲玲没什么异议,唯一担忧的是那个人此前也见过她,到时候很有可能会被一眼识破。对此我有办法,只要带她去趟“一次性变脸”,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约定好时间,见面前两个小时我才带着戴玲玲来到“一次性变脸”,老板打趣道:“以后女朋友就成路人甲啦!”我们都笑了起来。老板的技术真不赖,经过他的一番操作,戴玲玲的脸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离开之前,老板无意间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警觉。他说:“你帮我在女性中间打广告了吗?如果是这样,下次可以在男同胞中也夸夸我。”
我停住脚步问他:“最近有很多女士来过吗?”
“在你们来之前的半个小时,就有一位女士来过,说是要谈一桩买卖。我就搞不懂了,谈买卖怎么也需要变脸,难道想黑吃黑不成?”
我看向戴玲玲,发现她也是满脸惊愕。我们同时意识到了什么,对老板说了句“再见”就匆匆走出店门。老板的声音从后面追上来:“有需要再来啊!”
我们步履匆忙地走在大街上,刚才老板的话让我们都明白了一点:我们准备得还不够充分。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准备好一切。戴玲玲按照原定计划去见那个人,额外带上了袖珍录音笔和照相机。添置这两样东西费了我不少真金白银,倘若平时我肯定会犹豫,但眼下对真相的渴求已经让我义无反顾。
会面安排在莫顿宾馆的包间里,钟点房,一小时三百元钱。莫顿宾馆所有房间都临街,这为我某些行动提供了便利。在莫顿宾馆对面祥友客栈的一个房间里,我站在窗前,手里拿着一只星特朗高倍望远镜。只要将这种望远镜举到眼前,对面房间里的人脸上,哪怕一粒微小的痣都别想逃过我的眼睛。
按照约定,电话铃声响起我就赶到戴玲玲那边去。此时在望远镜的视野里,我看见一个人进了房间,戴玲玲礼貌地请对方坐下,并送上一杯热茶。
这次她没有戴口罩,脸部进行了巧妙的伪装,但那双眼睛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在黑暗中记住的东西,往往印象特别深刻。我确信是她无疑,一切都是她精心编排的,她用某种手段让一个人消失了,并且放出烟幕弹制造对方远行的假象。
此前,戴玲玲曾问我:“你觉不觉得自己有些多管闲事了?”
“一点儿也没有。”我回答得斩钉截铁。
我看见她们坐下来后交谈得很愉快,但没过多久,她脸上的笑容忽然变得阴冷。她冷笑着说了句话,戴玲玲的笑容立马僵住了。察觉形势不对,没等手机铃声响起,我就冲出了房间,能把她直接摁在地上也行,虽然会被警察训斥一通,这会儿也顾不上了。
等我冲进房间,躺在地上的人竟然是戴玲玲,还有一个陌生男人,那个女人已经不知所踪。我赶忙将戴玲玲从地上扶起来,她的一侧脸颊有些微淤青,我怎么也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那个女人竟然敢动手。
戴玲玲却说:“不是她打的,她给了我张纸条就走了。”
说着,她把纸条交给我,上面写着:“永远别想找到他!”
我问她:“她刚跟你说了什么?”
“她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我内心深深地被震惊了。原以为稳操胜券,结果自己的一举一动全在对方的掌控之中,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那双深邃的目光难道可以看透人心?
提到脸上的伤,她说:“那个人走后不久,有个男人冲进来,往我脸上打了一拳就走了。”
我首先想到是她的同党,后来得知完全是个误会。那个冒失的男人与此事无关,他最近遭遇了失恋,原因是女朋友的闺蜜说了他不少坏话,导致女朋友下决心与他分手。伤心愤怒之余,他决定对前女友的闺蜜实施报复。这天,他打听到前女友闺蜜会来莫顿宾馆,于是找到这里,不料搞错了房间号,害得戴玲玲白白挨了一拳。被警察带走前,男人真诚地朝她鞠躬道歉。
戴玲玲对他说:“以后不要这么冲动了。”
男人忽然转过头对我说:“她很不错。”
男人走后,戴玲玲摸着脸颊无奈地说道:“你看吧,多管闲事就没好下场。”我望着人来人往的大街,各怀目的的人在我的视线里匆匆闪过,那个女人已经逃之夭夭了。我长久沉默不语,内心深深怅然,最后,戴玲玲拉着我离开了。
疗休养结束,我该离开这个城市了。戴玲玲来送别,劝我道:“听我的话,剩下的事情交给警察吧。”
我微笑着点头,与她握手告别。
回到自己生活的城市,出了高铁站,我沿着广场走向地铁口。看着被阳光点亮的街景,我想起那位不曾谋面的室友当初也是这个时间点离开这里,而且发了微信“说说”。当我看到地上自己的影子时,竟然瞬间呆住了。
我在同一时刻来到这里,同样都是背对着太阳,然而,投在地上的影子居然与照片中室友投在地上的影子完全不同。眼下哪怕没有享誉世界的夏洛克先生在一旁指点,我也能猜到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与发表时间并不一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用了一天时间来做试验,结果证明那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在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
更加讽刺的是,几乎同一时刻那个微信又发了一条新动态,内容为:“出发,下一站兰州。”文字下方还煞有介事地配了张机场的照片。为了印证我的猜测,我请从事IT行业的朋友帮忙检测了一下,朋友经过一番高科技手段的操作后告诉我,照片是从网上下载后处理的。
微信上显示他已经离这个城市越来越远,而事实上,他极有可能一步都没有离开过。我又想起那个问题:他此时在哪儿?在大数据时代,一个人想要隐藏行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跑到深山老林里面,与狼群猛兽一起过茹毛饮血的生活。
今时此刻,他究竟在哪里呢?我努力让大脑保持清醒,把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都串联起来,冥冥之中似乎有只手朝着一个方向指去。
我回忆起住入那幢房子的情形:前一位房客拖欠了好几个月房租,东西还在房子里,人却玩起了失踪。二房东在联系无果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将房子转租给了我。对此,原房东并不知情,再加上我们同名同姓,他就更加难以察觉。
这里面的疑点是:如果那位房客是为了逃避房租而跑路,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东西一块儿带走。他的做法给人感觉就像出了趟门,然后再也没有回来。可是之前我已经证实,他大概率没有离开这个城市。他似乎是躲入了某个隐秘空间,也许是主动,也有可能是被迫。我突然意识到,我原来的住所还没好好搜寻一番。
我在微信上问原来的房东:“那个房子租掉了吗?”
房东说:“租掉啦!一个女的租走了。怎么着,又想住回来了?”
我说:“是啊,可惜晚了一步。”
朦胧夜色里,我踏着月光来到熟悉的地方。曾经我坐在屋内,外面有个身影注视着我。如今我们的位置倒了过来,我站在外面,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屋里。
我潜行到窗前,屋内没有开灯,地上摆着两支白蜡烛,微弱的光芒将她的背影照亮。我注意到那两支蜡烛的位置就在橱柜前方。眼前的情景像是个小型的祭奠仪式,屋内的人似乎还在说些什么,我屏气凝神倾听着,终于有只言片语传入耳中。她应当是在和心爱之人互诉衷肠,可是屋内就她一人,另一个人呢?
我看见她端起两只碗,将其中一只碗里的东西倒在地上,然后将另一只碗里的东西一饮而尽。那应该是酒。我想,她为何要对着橱柜呢?蜡烛对着橱柜,敬酒也对着橱柜,莫非她的情郎就在橱柜里?然而活人怎么会在橱柜里呢?除非是……我听见脑袋里“嗡”的一声,那是真相一瞬间打开的声响。可笑的是,此前我为了寻找这位不曾谋面的室友东奔西跑,结果却是他一直都在我身边,和我同处一室。我哑然失笑,内心却是满满的悲凉。
就在我破门而入的时刻,鲜血已经从她嘴巴里冒出来,在她白皙的肌肤上留下一抹猩红。
她手朝橱柜一指,说:“我绝对不会让他离开我的。我把他留在了这里。”
我打开柜门,里面是个狭小的空间,根本无法容纳一个人。我敲了敲里面的墙体,从声音判断背后还有更大的空间。我没费什么周折就打开了暗藏的门,里面果然别有洞天。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双脚,脚踝处被一圈绳索捆住,这双脚无论如何都不能自由行动了。
我顺着脚一直看去,眼前是一具没有生命体征的尸体,也是个彻底失去自由的人。白色的生物在他的体表狂欢,这是唯一的生命迹象。简直令人作呕。我还看见一双茫然睁大的眼睛,灵魂似乎想从这里挣脱出去。他大概至死都不会明白,自己为何会落入桎梏。
身后一个冰冷的声音对我说:“他就在你身边,一直都在。”
我猛地转身,正要说“是你杀了他”,然而,一记闷棍抢先落在我头上,我倒在了她面前,意识逐渐模糊。我看见屋里燃起了火光,却已无力逃离。平时出门前,我都会把屋里的电源切断,想不到我一生谨慎,最后结局竟是葬身火海。意识消失前,我的脑海里只有两个字:恶魔。那具美丽的躯体大抵是被恶魔占据了,我们三人都将丧生于恶魔的爪下。
再次睁开眼睛时,我看到戴玲玲站在我眼前。我问道:“你跟我一起死掉了吗?”
她笑了起来,说:“恰恰相反,我把你从阎王爷手里拉了回来。”
她扶我坐起,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说起事情的原委。原来,她一直跟在我后面,从那个城市一路跟来,见我被女人击倒便立刻冲进屋。
我苦笑着说:“你要是晚来一步,我估计已经变成烤乳猪了。”
“那可不,想好怎么谢我了吗?”
“看来一顿烤乳猪是逃不掉了。”
她眼珠子转了转,说:“烤乳猪没兴趣,烤全羊倒可以考虑,不过得原汁原味那种。”
我说:“那得去大草原上吃了。”
“不然呢?”
我们在笑声里达成了共识。
接着她问我:“你现在后悔这么做了吗?”
但我还没得到全部答案:“对了,那个女人现在在哪里?”
她指指我背后的白墙,说:“就在你隔壁,人还没醒来,医生说能不能醒就看今晚了。”
我是希望她能醒过来,把真相彻底揭开。可惜我这个心愿最终没能达成。凌晨两点,她永远离开了人世,将那团我迫切想揭开的谜底一同带走了,我大概只有等自己百年后才能找她当面问清楚了。
出院那天,戴玲玲来接我。我们一同走出医院大门,此时那个女人还躺在太平间里,静静等待法律的最终判决。我回身望了医院一眼,忍不住说道:“可惜了。”
她问道:“可惜什么?”
“可惜她没能把最后的话讲出来。”
“这很重要吗?”
“当然,那位室友也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去。”
她点点头。
我问她:“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爱得太深,因爱生恨了呗。”
对于这个回答,我有些惊讶:“就这么简单吗?”
“你以为呢?大事说到底不都是由小事導致的吗?”
她的话让我想起看过的一本小说,是世界三大推理小说大师之一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代表作之一:《尼罗河上的惨案》。故事中一系列惨案的源头就在于一个女人对心爱的男人超出理智、极度自私的爱。起初叫人觉得不可思议,仔细想想又感觉在情理之中,毕竟人性都是相似的,尤其是在狭隘方面。或许我们应当长久地站在阳光下,保证内心的罪恶不会蠢蠢欲动。
她说:“你就别关心这么多啦,还是想想怎么兑现自己的承诺吧。”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你是指什么?”
她望着我:“你说呢?”
“噢!”我恍然大悟,“我说的话当然算数。”
我们下午就买了飞机票,第二天就置身大草原之中了。她如愿吃到了原汁原味的烤全羊,我们一起骑着马在草原驰骋。风迎面吹来青草的香味,还混着她的体香。夜晚,草原上举行篝火晚会。我们换上当地人的装束,与他们一起在火堆前翩翩起舞。柔和的火光映在她年轻美丽的脸上,在我眼中变作一幅独特的风景。后来,我们的手牵在了一起。
一支舞蹈结束,当地一位长者走到我们面前和蔼地說道:“祝福你们。”
我们对视一眼,彼此都看清了目光里的含义。晚会上,有位歌手开始弹奏吉他,口中高唱那首《听闻远方有你》——
“听闻远方有你,动身跋涉千里,追逐沿途的风景,还带着你的呼吸,真的难以忘记,关于你的消息,陪你走过南北东西,相随永无别离,可不可以爱你,我从来不曾歇息,像风走了万里,不问归期……”
草原夜晚,熊熊燃烧的篝火,经典动人的歌声,我们深深陶醉其中,牵着的手始终没有放开。后来,我问长者怎么知道我们的事,长者双手在胸前合十,用极其虔诚的语气说道:“是神告诉我的,神知道一切。”
回来的飞机上,我们还在聊着大草原的见闻,后来又聊到了那位蒙古长者。飞机从高空降落,我忽然问她:“长者说的话可以当真吗?”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目光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然后有无限的惊喜涌上来。我瞬间明白了她的心,与我的心一样。
直到下了飞机,她才说:“虽然考察期有几十年那么长,但是我不介意让你先上岗锻炼。”
我牵起她的手,紧紧握在手心,接着又放在胸口。
我说:“走吧,现在就把契约签了。”
我们像两只兴高采烈的燕子,向民政局的屋檐飞去。这是我这辈子干的第二件疯狂事。如果日后有人问起,我肯定会说,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疯狂。
责任编辑/张璟瑜
插图/子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