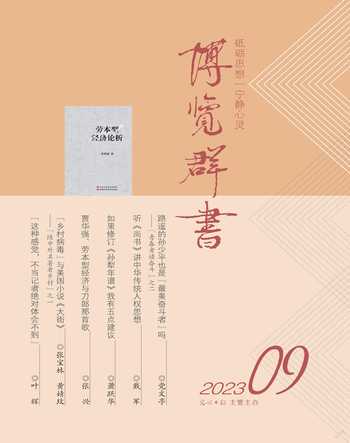“这种感觉,不当记者绝对体会不到”
2023-12-02叶辉
叶辉
2023年4月中旬,我们几个光明日报退休老记者去昆明旅游,顺便探望了在昆明安度晚年的记者部老主任王茂修。那一晚,老同事把盏欢聚,共话《光明日报》的辉煌历史。聊起我们共事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微醺中的老王,神采飞扬,看着乱发满头的老王,慨叹烈士暮年,英雄老去,心里填满苍凉,与老王交往的旧事一件件浮现在眼前……
我1983年从杭州大学毕业,工作问题几经周折,1984年2月中旬才到光明日报报到。
记者会上,我初识老王,他中等身材,敦实健硕,步履稳健,方面大耳,相貌堂堂,当时他是驻四川和云南两个站的站长。记者会上,一批当时如日中天的名记者介绍了各自的采访经验,驻湖北站长樊云芳介绍了写人物的经验,驻山西站长梁衡介绍了写批评报道的体会;驻上海站长张贻复介绍了写头条的经验,老王则介绍了在西藏采访的传奇经历。正是这些名记者在那个风流激荡的岁月里,推出一篇篇典型报道、批评报道、问题报道,掀起一道道波澜,引发一次次震荡,把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镌刻进光明日报的记忆里。
彼时的《光明日报》还沐浴在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的巨大光环里,还处于创刊以来最辉煌的历史阶段,许多名记者采写的报道一次次轰动全国,如陈禹山、苗家生等采写的张志新,王晨、张天来采写的遇罗克,樊云芳、丁炳昌的名篇《追求》,驻上海记者谢军采写的星期天工程师韩琨,这些报道都引起巨大的轰动。
当时的老王于我是神秘的,我只知道他是名记者,特别擅长写批评报道和问题报道,但对他的个人情况却知之甚少。说真话,当时的老王给我的印象是:威严、沉默,不易接近,我有些怕他,他目光犀利,平时路遇,偶尔扫我一眼,我会马上避开。我们属于两代人,加之我个性木讷,不善交往,对他一直敬而远之,直到1991年他出任记者部主任。
老王上任的消息传来,我正在浙西采访。那是我职业生涯最出活的阶段,那次5天跑了龙游、衢州、开化等地,发回5篇稿件,其中4篇上了头版头条。后来我才知道,稿子都是新任记者部主任老王处理的。也许正是这次采访,老王对我有了印象,后就经常给我派活,让我承担重点报道选题,全国各地到处跑。
我一直以为老王沉默寡言,大谬!一次在记者部见他与常务副主任殷毅聊天,两人眉飞色舞,笑声朗朗,话题所及,针砭时弊,臧否人物,嬉笑怒骂,妙语如珠,古诗词张口就来,语言生动幽默,机锋相搏,思辨互见,每有精思迸溅,便会电光石火,相视大笑。
1993年,《光明日报》华东片记者站站长会议在杭州召开,此时我的老领导、老站长卢良已调离,我成了手下没有一个兵的唱独角戏的站长,作为东道主,我迎送兄弟站站长,应付会务,忙得脚不沾地。会议结束那天,老王让我陪他下基层采访考察,可记者站唯一的一辆桑塔纳要送站,我深感无奈,刚好浙江农大有一辆送饲料的卡车要下基层,我慌不择路,决定陪主任搭乘这辆卡车下乡。用大卡车送部主任,我心里感到实在不恭,可我面子薄,羞于开口向人借车。老王见我愁眉,问清情况,说:“大卡车有什么不好?我在云南经常是11号轿车(指步行)呢!”我这才舒了口气。
那时,浙江公路路况极差,卡车驶过,砂石泥路尘土飞扬,滚滚尘埃从车窗缝隙中钻进,劈头盖脸洒落老王全身,我深感歉意,老王却一路云淡风轻。
1993年是我职业生涯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被破格晋升副高,报社为我举行了第一次新闻作品研讨会,入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而这一切几乎都与老王的垂爱有关。事后方知,推荐我参评国务院特贴,老王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众站长皆很优秀,我资历浅,学历低(大专),年纪轻(39岁),可老王却极力推荐我。
那次基层采访,他提出要到我老家看看。我老家蛰居在临海一个叫温家岙的山坳里。到山村后,乡亲们围上来热情问候,老王兴致勃发,拿个相机,不时蹲下身子抓拍我与村民见面的情景。
临海听说光明日报来了一位大主任,非常重视,市委书记安排宴请。可老王却不愿去:“晚上可否住你们村?市委书记的饭局不去也罢!这里是你故乡,我很想了解这里耕读传家的文化。”
碍于我的坚持,老王勉强去赴宴,可那晚的宴请气氛沉闷,市委书记问东问西,希望王主任能透露一些上头信息,他却用沉默的盔甲将自己包裹,我很尴尬。
老王面对官员是如此,面对喜欢的场合又是另一副模样。鲁迅是老王的偶像,鲁迅的名篇他能大段背诵,如《在酒楼上》《故乡》。他一到浙江,就提出要到绍兴“朝圣”。从临海回杭途中,我陪他去了绍兴。那天,老王兴奋至极,参观完鲁迅故居,绍兴友人已安排宴请,他非要去咸亨酒店做一回孔乙己。木板桌、長条凳,老王往凳上一坐,一只脚已搁到凳子上,要一壶绍兴佳酿,点了茴香豆、盐煮花生、臭豆腐等几碟下酒菜,老王容光焕发,抿一口酒,故做兰花指状撮一颗茴香豆放进嘴里,冲我做个鬼脸,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
老王在云南的情况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王茂修,四川乐山人,苏东坡的乡邻,1937年生,上中学时受范长江、斯诺等人影响,一心想当记者。1960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如愿成为《光明日报》驻云南记者。
老王目光敏锐,观察细微,疾恶如仇,好打抱不平,又富有同情心,天生是当记者的料,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写了许多好稿,常有批评报道引发当地地震。
老王国学功底深厚,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淫,性格中既有杜甫的豁达乐天,又有着忧国忧民的悲悯情怀,他见不得群众受苦,容不得欺凌百姓,每闻不平事,就会拍案而起,以笔作刀,与邪恶斗,与强权斗,与一切恶势力斗。他热心为知识分子鼓与呼,对存在的问题则予以批评,批评报道一篇接一篇,在云南四川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风浪,知识分子对他感恩戴德,而一些被批评者却恨之入骨,避之犹恐不及。
1982年末,老王自成都回昆明过年,利用探亲机会沿途采访。途经家乡乐山时,亲朋故旧纷纷来访,其中亦有上访者。有意思的是,一上访者竟是乐山市纪委书记。
纪委书记上访,所为何事?
原来,乐山市苏稽区有个公安员叫邹学林,1981年在苏稽区沙咀街当街建了一幢住宅,房子横占街面三分之二。房子开建时,此事就被反映到乐山市委,市委明确指示:停工!邹学林充耳不闻;市纪委出面制止,不听,大吵大闹。一个共产党的公安员竟如此为所欲为,当地群众敢怒不敢言,忌惮此人后台太硬。
此事在当地影响恶劣,乐山市委派调查组调查。调查结束后,市委、市纪委、市公安局一起找邹学林谈话,他仍气焰嚣张:“我没有占谁的地方,我是经过批准的,如果段君毅(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批准我在天安门广场盖房子,我也盖!”
市纪委下达处分邹学林的决定,却无法执行。
乐山市纪委书记为此找到老王:“这事只有你能管,只要你把这事曝光,事情才有可能解决。”
对这个家乡一霸,老王并不陌生。1980年,苏稽区发生一起殴打教师事件,一教师揭发考试作弊受到打击报复,参与作弊者反诬揭发者是诬告,教师惨遭毒打,幕后策划殴打教师的正是邹学林。老王曾作报道:《维护党纪伸张正义乐山市委处理迫害教师事件》(1980年7月15日)。点名批评幕后策划者是邹学林。
乐山市委处理了作弊者和包庇施暴的官员,邹学林却未受到任何惩罚。
那篇批评报道惹怒了邹学林,他对老王秘密进行反调查,企图报复,发现老王的身份和影响力后,才未敢轻举妄动。
1983年1月23日,《光明日报》刊出老王的报道:《有恃无恐肆意霸道乐山市苏稽区区委委员邹学林拦街建房激起公愤》,指名道姓,报道还配有新房当街而立的图片。报道刊出,引起轰动,中纪委书记韩天石见到报道,直接给乐山市纪委打电话指示:限期拆除,开除党籍!
这次,邹学林没能逃脱惩罚,他被开除党籍,房子被拆。
拆房那天,苏稽区居民倾巢而出,鞭炮声震耳欲聋,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
老王除恶非此一件。全国拐卖妇女儿童的恶劣风气,因他的一篇报道得到遏制。
一次老王去巴中采访,途中口渴,下车到一人家讨水喝。这户人家家徒四壁,壁上悬挂一些照片,其父亲是老红军。主人无意聊起,他的儿子、老红军的孙子被拐卖了。此事触及老王一直在关注的拐卖妇女儿童问题。四川是拐卖妇女儿童的重灾区,老王不走了,留下来采访。
被拐男孩刘毅,巴中县人,经查,人贩子以450元的价格将男孩卖到河北。男孩曾祖父是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游击大队长,被还乡团杀害;祖父邓耀祖曾在红二方面军某师任职,1945年牺牲;祖母刘文素,1932年参加红军,1980年去世。
刘毅被拐卖后,巴中县公安局干警曾陪同孩子父母找到孩子被卖的河北某县,但当地公安局态度冷漠:“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里连公社书记都买娃娃呢!”
人找到了,当地公安局却不让领走,要孩子父母交钱取人,理由竟是“不能叫人家(买孩子的人)人财两空”。最终孩子被领回,孩子在买家的生活、医疗等费用由孩子父母出。孩子父母没钱,只好由巴中县公安局垫付。
老王很快完成了《刘毅被拐记》,发内参后,中央领导做了批示。随后,公开报道刊出,引起轰动,钱学森看到报道给报社打电话,说自己一夜未眠,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怎么还有如此恶劣的事发生,感到非常难过。这一报道,推动了全国打击拐卖妇女儿童运动的开展,中央和有关省都专门成立打拐办,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得以制止。
老王疾恶如仇,却极富同情心,对底层群众的苦难寄予无限的同情。
1985年腊月二十八日晚上9点,有人敲开老王家门,是镇雄县副县长彭世铭和县四套班子负责人。
镇雄曾是云南有名的学大寨县,一个偏僻落后的赤贫县。年关临近,全县20多万群众缺粮,许多家庭揭不开锅,该县习惯,农民将玉米放在煤上烤了连芯一起吃,结果导致遍及全县的氟中毒。缺粮的现实,压得分管副县长彭世铭喘不过气来,领着四套班子到省里求援,但跑了多个部门无果。无奈中,彭世铭找到了记者。
听罢彭世铭的叙述,老王心情沉重。此次他从四川回滇路过镇雄,曾走访农户,一农户家徒四壁,户主下地去了,把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孤零零丢在家里,这孩子一丝不挂光着身子在地上爬,全身叮满苍蝇。彭世铭描述的惨状,他理解。
20多万人无粮过年,问题严重!老王详细了解缺粮的原因及现状,彻夜未眠写成一份内参。他思忖,时近年关,内参发上去,要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再来解决问题,远水难解近火,解决问题必须靠当地。第二天,他带着内参,直接找到省长和志强。
老王同和志强很熟。和志强原是一名地质工程师,在破格任用知识分子时一步登天,被破格提拔为省长。
“我们新班子刚组建,宜服补药而不是泻药。你这个内参能不能先不发?问题我来解决!”
老王要的正是这句话。当晚,和志强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决定给镇雄县拨 30万斤粮食、3000万元钱,让20万群众先过好这个年。
《光明日报》驻云南记者站原站长、老王的后任徐冶曾和我讲过一件事:一年中秋,徐冶陪老王到会泽县大海梁子采访,途遇几个孩子,衣衫褴褛,满脸菜色,询问方知,他们因贫辍学放羊。老王拿出几个月饼送给孩子,孩子竟不知此为何物,老王见状,搂着几个孩子失声痛哭:“解放这么多年,老百姓还饭都吃不饱,我们对不起他们啊……”
云南中科院植物所科技人员罗季杰,妻子是农民,5个孩子都没户口、没口粮,生活窘迫,但落实政策困难重重。老王夫妻对他很同情,经常资助他全国粮票。发明周林频谱仪的周林、科技流浪汉刘忠笃,老王一直为他们呼吁,直到问题解决。
2016年,老王来杭州,我陪他游西湖。我問:当记者最大的乐趣是什么?老王略一沉思,答:发现重大新闻时。他说,在发现重大新闻的刹那间,全身会有一种触电般的极度快感,这种强烈的冲动是驱使记者写出好新闻的前兆。
“这种感觉,不当记者绝对体会不到!”老王说。
我的体会是,记者发现重大新闻线索时,与猎犬发现猎物时的感觉一样,电影里常有这样的镜头:猎人牵着猎犬,一旦发现猎物,猎犬就会狂躁不安,不断跳起来企图挣脱绳子扑向猎物。
“老王你像一种动物——猎犬”我开他玩笑,“一旦发现猎物,就会犯‘狂躁症’。”
他哈哈大笑:“没错,我就是一头猎犬!”
老王曾采写过一篇引起很大反响的人物新闻:《鼎山公社“冒尖户”周朴由后进变先进》。那次去基层采访,途中通讯员给老王讲了个笑话:巴中县开了一个冒尖户现场会,一个叫周朴的冒尖户做了典型发言。周朴曾是个小偷,偷过生产队的粮食,偷过邻居的鸡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他勤劳致富,先富起来的他,检讨自己过去的行为深感不安,决定给那些被偷的农户和生产队还钱。老王闻此,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个典型意义重大,一个底层小人物的变化,凸顯出时代新精神。“猎犬”马上调转车头扑向“猎物”。老王的稿子配评论在《光明日报》刊出,马上引起轰动。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老王的信条是: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接近人民,只有接近人民才能接近真理,才能发现重大题材。
一次老王下基层,夜住车马店,隔壁两住客聊兴很浓,扰他清梦,睡不着,干脆听他们聊天。两人聊的内容是:高县城里一幼儿园老师带学生春游,途遇拖拉机刹车失灵撞向孩子,老师奋不顾身抢救孩子负伤,老师的英雄事迹传开后受到上级表彰。可当英雄得到一台电视机的奖品后情况逆转,赞颂变成了妒忌,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污水脏水泼向英雄,英雄抑郁得生病住院。老王一听,“狂躁症”顿发,一夜未睡安稳,次日直奔高县,于是就有了光明日报的名篇:《高县城里的叽叽喳喳》。稿子刊发后,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杜导正批示:“希望记者多写这一类为本报增光的好报道。”
老王思维敏锐、超前,他是全国最早提出生态问题的记者,生态报道连篇累牍,为保护生态呐喊。
老王曾赴西双版纳考察自然资源和动物资源,独自深入原始森林探险,不说森林里的熊、犳、狼等猛兽,仅毒蛇、蚂蟥、马蜂,就让人恐怖。在傣族村寨,毒蛇一个晚上咬死几头牛,三只马蜂能蜇死一头牛,而叮在牛身上的蚂蟥挂下来像镰刀。他到达的头一天,一头野象踩死一名小学老师。老王没有退缩,坚持深入原始森林采访,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系列报道,在《光明日报》内刊上连载,引起中科院的关注,中科院古人类研究所根据他的报道线索,派出考察队赴西双版纳考察。
改革开放初期,云南鼓励开荒种地,毁林开荒还能得到奖励,全省由此掀起砍伐森林狂潮,西双版纳原始森林被破坏得满目疮痍。老王痛心之余,奋笔直书,1980年2月20日,批评报道《我们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刊出,反响强烈。云南省派人上北京,告老王的御状。老王不怕,一鼓作气发了七八篇报道,引起国务院的重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受命带队到云南调查。
老王就像堂吉诃德,一个人在为生态而战。他批评30万人围湖造田导致滇池生态遭受严重破坏,长篇通讯《围湖造田始末记》刊出,云南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载,一时洛阳纸贵;他为金沙江生态遭破坏呐喊,为大围山保护区遭破坏呼吁,他首开西藏生态保护万里行先河,参与黄河溯源万里行,他像着了魔一样,竭尽全力呼吁,尽一个记者的责任。
20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扬眉吐气、得到重视和任用的好时代。老王作为名记者,与官场接触很多,有许多当官的机会,多少次天上掉馅饼,官运砸到他头上,他却不为所动。
1977年,云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省委党校校长颜义泉很欣赏老王才华,欲调他到党校任办公室主任,想让他过渡一下,出任昆明市委书记,他谢绝了。
老王有个朋友叫韩天石,昆明一家小厂的副厂长,韩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初期便是四级干部,因受高饶集团案牵连,被下放到昆明。老王与他长期厮混,结成忘年交。粉碎“四人帮”后,韩天石复出,任云南省省长,后调任北大党委书记,再调任中纪委书记,一次次欲调老王做他助手,均被老王婉拒。
胡耀邦任总书记后,提出干部实行“四化”。干部“四化”的一个具体举措是,中央决定各省从普通知识分子中选拔出几名优秀分子经短期培训直接进入省部级领导班子。云南推荐了老王,中组部找他谈话:到中央学习半年,回来担任要职。可他却“不识抬举”,又谢绝了。
云南友人对我说,这个老王,不可救药!就像他的乡邻杜甫,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又像诗仙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
老王的友朋以及他笔下的人物,或居庙堂,或成达人,或成富翁,老王依然故我,天马行空,以笔作枪,剑行天下,甘当穷记者。
老王说,直面了无数的惨淡人生,看多了数不清的人间不平,即使是到拨乱反正时,许多事仍难解决。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有一支“金不换”的笔,有光明日报这个坚强有力的平台。他觉得能为人民说点话,能为一些“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小人物鸣冤叫屈,排难解纷,为他们树碑立传,这是他的快乐,是他的责任,他的人生意义也在这里。
云南有个接骨医生冯成林,老王因车祸手臂骨折,请他医治,20多天后就能骑自行车上街。老王以自己的经历,写成一篇《接骨奇遇记》。报道发出后轰动全国,冯成林顿时名满神州。后来,冯成林开医院、办药厂,成了富豪,为感老王之恩,欲送老王一栋别墅、一辆好车,而且上午说定,下午兑现。虽然此时老王祖孙三代仍蜗居在40平方米的房子里,但他还是谢绝了冯成林的一番好意。
杜甫有一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忧国恤民之情跃然纸上:“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两句诗用在王茂修身上,恰如其分。
退休后的老王,默默地生活在昆明,昔日名震西南的一代名记,而今已垂垂老矣,但一谈起激情燃烧的记者岁月,他的眼睛里便会精光闪现。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当记者!”他说。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