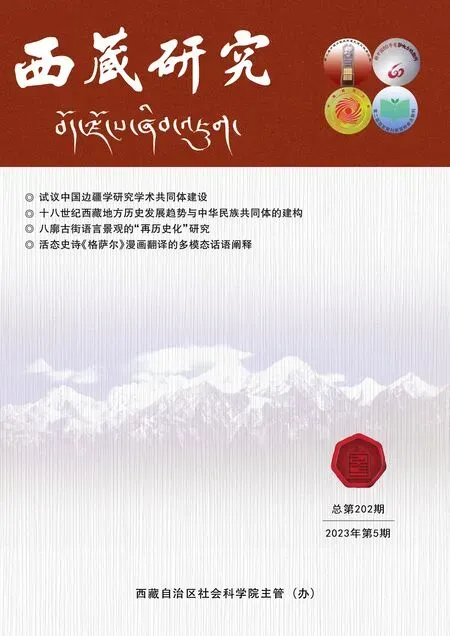三动元与藏语动词的再分类研究*
2023-11-30才华群诺
才华 群诺
一、引言
语言学界一致认为,动词是句子的核心,在一个完整的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中,动词支配着其他成分,决定句子的整个格局。因此研究动词的语法语义范畴对语言学、语言习得及计算语言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动词研究皆始于动词的分类。动词分类问题的探讨从未间断过,自21世纪以来,很多学者突破传统研究视角,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运用新兴理论和方法,从句法标准和语义特征两大方面对动词作出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句法标准方面,根据能否重叠,动词可分为助动词,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判断动词,趋向动词,表示存在、变化、消失的动词,描写性动词,使令动词,非持续、非自控性动词等不可重叠动词以及可重叠的能够控制的自主动词。(1)张明辉、孙宗美:《21世纪汉语动词分类标准问题研究综述》,《辽东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107页。根据有无带受事名词词组的潜在能力,动词可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又可分为潜及物动词、单及物动词和双及物动词。(2)徐杰:《“及物性”特征与相关的四类动词》,《语言研究》2001年第3期,第10页。根据论元,动词可分为一元一位动词、一元二位动词、一元三位动词、二元二位动词、二元三位动词、准二元动词、三元一位动词、三元二位动词、准三元动词等。(3)袁毓林:《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1—375页。语义分析方面,通过类型学、英汉对比、(4)夏晓蓉:《英汉V-R结构与非宾格现象》,《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3期,第172页。现代神经网络科学方法(5)Tao Yang,“Computational Verb Neural Network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Cognition,Vol.5,Issue 3,2007,p.57.等不同角度,深入研究动词的位移特征、(6)朱蓓:《现代汉语位移动词研究综述》,《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61页。使动特征、(7)格桑居冕:《藏语动词的使动范畴》,《民族语文》1982年第5期,第27页。动相特征、(8)左思民:《动词的动相分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74页。情状特征、(9)张松松、沈菲菲:《汉语动词分类的认知研究》,《扬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122页。言说特征、(10)刘大为:《意向动词、言说动词与篇章的视域》,《修辞学习》2004年第6期,第1页。心理特征等,以此把动词分成不同小类。基于数理逻辑的题元理论、概念框架理论把动词分为移动类动词、出现类动词、领属类动词、交易类动词等。归纳起来,动词的分类基本围绕基于表层的句法功能和基于深层的语义特征角度进行,其中配价语法和格语法所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
动词的表层句法结构是属于个体语言的具体行为,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句法组织,而动词跟句法成分之间的深层语义关系,对所有语言而言都是相通的。动词的句法形态分类因语言种类而有所不同,但其语义分类具有一定普遍性,可应用于一切语言。
针对藏语动词,大部分研究都围绕其语义特征、形态变化及构词方式等进行。随着计算语言学的兴起,藏语动词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领域、多角度的特征,取得了大量成果。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和计算语言研究所首次将格语法和配价理论引入藏语语法研究中,提出一种藏语动词的再分类(11)陈玉忠、李保利、俞士汶:《基于格关系和配价的藏语动词再分类研究》,语言计算与基于内容的文本处理——全国第七届计算语言学联合学术会议论文,哈尔滨,2003年,第284页。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一种基于传统句法语义分析层面的藏语动词分类(12)江荻:《现代藏语动词的句法语义分类及相关语法句式》,《中文信息学报》2006年第1期,第37页。方法。这些研究虽有一定开创性意义,但未见后续相关研究报道。现代藏语动词分类方法都侧重于藏语信息处理需求,没有充分考虑藏语本身的语法特点和理论框架,并很难与藏语传统文法相统一,甚至相去甚远,因而未能得到藏语言学界的重视和肯定。不论是传统的分类方法,还是基于现代语法理论的动词分类方法,都基于动词的某一属性将其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别。因分类标准不一,难免出现交错现象,很难达到“博而不杂,约而不漏”的分类要求。
Fillmore格语法研究动词跟名词成分间的语义关系,属于普遍语法理论,也是动词语义特征描述的有力依据。在描述动词的深层语义关系时,常常又会遇到语义角色的称谓混乱,缺乏角色测定标准,实际上动词词义分析得到的角色与句式中的应用出现了角色间的不对应现象等系列问题。配价语法根据动词所能支配的名词性成分数量对其进行分类,但未说明为何动词有不同价数。能否用语义格来解释动词的价数,也就是说在格语法和配价语法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本文以Fillmore格语法为基本参照语法,在继承藏语动词传统分类方法的同时,对其进行合理拓展,继而提出一种具有普遍性质的动词分类方法。
二、藏语句子的基本结构
藏语传统语法与格语法间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描述藏语的众多语法中,格语法最接近藏语本身的语法特点。任意一个藏语单句都可形式化为:
体词1+虚词1+体词2+虚词2+体词3+虚词3+……+谓词
从格语法角度来讲,藏语句子可以分成多个形如“体词i+虚词i+谓词”的语法单位。该语法单位是介于短语和句子间的一个特殊的、独立的形意结合体,称为格结构体。格结构体中的虚词i标识着体词i与中心谓词间的语义关系,称为格助词。

老师 施格 学生 于格 数学课本 空格 发放
(老师给学生发放数学课本)
该句是唯一被分解为三个不同格结构体的句子。

数学课本 发放
(发放数学课本)

学生 给 发放
(给学生发放)

老师 发放
(老师发放)
因此可以说,藏语句子由一个或多个格结构体组成。格结构体具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即“NP+Ki+VP”。其中Ki可能是一个格助词,也可能是一个空格标记,或者是表达某种特定语义的助格词。

对藏语句子来说,只要正确识别并标注了格助词Ki,也就基本完成了藏语的句法、语义分析。藏语句法、语义分析可以一体化研究,不分先后。
三、传统的动词分类法


小孩 施格 衣服 空格 穿
(小孩在穿衣服)
例2中,“小孩”是动作“穿”的发出者,即主体;“衣服”是该动作所影响到的事物,即客体,在动作实施过程中,主体和客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所以把“穿”归为主客可分动词。

小孩 空格 学校 于格 去
(小孩去学校)
例3中,“小孩”是动作“去”的主体,同时,“小孩”也是被该动作影响到的客体,因此称“去”为主客不可分动词。
几乎所有文献都将藏语动词的这个分类翻译成“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13)格桑居冕、格桑央京:《实用藏文文法教程》(修订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419页。但它们属于不同的语法研究层面,及物与不及物是动词的句法属性,而动词的主客可区分性属于语义层面,两者不可等同。
动词间的这种语义区别,在句法中呈现为不同搭配关系。比如,在以主、客体可分动词为核心的句子中,主体后必须附带表示“施事—动作”关系的格助词,客体不附带任何格助词(可视为添加了一个“空格标记”)。由主客不可分动词主导的句子中,主体(亦客体)与动词间只能添加“空格标记”。这一现象说明,藏语动词的语义分类直接影响其句法结构,决定了动词的配价数目。
此外,藏语中的某些动词有与其对应的表示“使动”的单音节动词,有些以“动词+使(然)”形式组成的使动短语,至少与三个名词性成分搭配才能表达句子的基本意义。

妈妈 施格 小孩 于格 衣服 空格 (给)穿
(妈妈给小孩穿衣服)
例4中,“妈妈”是使然动作“(给)穿”的主体,“衣服”是该动作影响到的客体,“小孩”是动作的于体,是动作的接受者。对于该动作,因为主体、客体和于体是三种相互区别的不同事物,所以在句子中要显现主体、客体及于体,三者缺一不可。在语句中,主体后面附带“施格助词”,于体之后是“于格助词”,客体之后为“空格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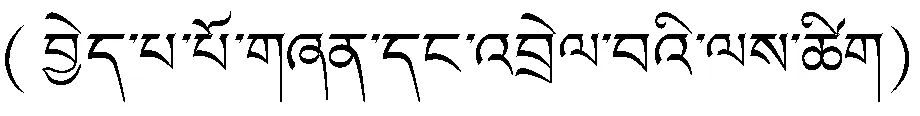
综上所述,藏语动词的基本语义关系与其句法结构间存在一定联系。从这个现象出发,可以研究格语法和配价语法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四、三动元及基于三动元的动词分类法
在语言学中,通常把句子结构中的体词成分称为动词的论元成分,论元成分所扮演的语义角色是动词的论旨角色。一个动词的语义结构中,有些论元成分是必须出现的,跟动词的基本意义有直接联系,称为动元;而另一些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地点、工具和方式等,称之为状元。在格语法中,动元语义格称为强制格,状元语义格称为自由格。
那么,表达一个句子(或谓词)的基本意思,至少需要多少个动元?

结合以上分析,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个动词都有三个动元,即主体、客体和于体,但三个动元间可存在兼类现象。也就是说,有些动词的三个动元是相互区别的三种事物,有些动词是两种事物,而有些是同一种事物,相应地,句子中就出现了三个、两个或一个动元。
根据动词的主体、客体与于体三者间的可区分性,将动词分为五大类,该方法是基于三个动元的动词分类,每一类动词对应不同的句法结构和语义关系。
(一)Ⅰ类动词()
Ⅰ类动词的主体、于体和客体是彼此完全区分的三种不同事物(见图1),基本句型为主体+第三类格助词+于体+第二类格助词+客体+第一类格标记(即空格标记)+Ⅰ类动词(或Ⅰ类动词短语),主要表达“主体让于体对客体做某事”之意,影响客体状态的实际动作在主体指使下由于体完成。主体的动作指向于体,影响客体,动词具有“外向性”特征。三个动元在句子中出现的前后顺序,取决于话题或上下文语境。

图1:Ⅰ类动词

老师 施格 学生 于格 作业 空格标记 (使)写
(老师让学生写作业)

另外,此类动词和动词短语也可用于表达“主体对于体做了什么”之意(见例6)。

老师 施格 学生 于格 课本 空格 发放
(老师给学生发放课本)
该类动词所表达的动作中,影响客体状态的实际动作在主体指示下由于体完成。在动作实施的整个过程中,主体、于体和客体始终是不同的三种事物。
(二)Ⅱ类动词
Ⅱ类动词三个动元间的可区分性如图2所示。动词的于体和客体为同一种事物,主体是另一种事物,基本句型为主体+第三类格助词+客体(同为于体)+第一类格标记+Ⅱ类动词(或Ⅱ类动词短语);或主体+第三类格助词+于体(同为客体)+第二类格标记+Ⅱ类动词(或Ⅱ类动词短语),表示“主体对客体实施动作,从而影响客体的状态”之意。动作始终从主体指向于体或客体,所以此类动词的动作从主体趋向于体或客体,具有“外向性”特征。

图2:Ⅱ类动词

他 施格 水缸 空格 砸烂
(他把水缸砸烂了)
例7中,动词“砸烂”的动作中,受影响的客体和动作的接受者同为“水缸”一物。所以,在“水缸”和“砸烂”间既有“受事”关系,也有“于事”语义关系。因为客体的影响很明显,在句法结构上采用“重客体、轻于体”的形式。

学生 施格 老师 于格 看着
(学生在看着老师)
例8中,动词“看”的动作中,“老师”既是客体,也是于体,但该动作不会影响到客体的状态,其句法形式采用了“轻客体、重于体”的结构。
(三)Ⅲ类动词
Ⅲ类动词三个动元间的区分关系如图3所示,主体和于体不可分,而客体是有别于它们的另一种事物,基本句型为主体+第三类格助词+客体+第一类格标记+Ⅲ类动词(或Ⅲ类动词短语)。因为动作总是指向于体,所以此类动词的动作会指向主体本身,具有“内向性”特征,表达“主体(对自己)做了某事”之意。

图3:Ⅲ类动词

母亲 施格 茶 空格 喝
(母亲喝茶)
例9中,动作“喝”的客体为“茶”,主体实施者是“母亲”,于体也是“母亲”。

学生 施格 老师 空格 看见
(学生看见老师)
例10中,“学生”既是“看见”的主体,也是这个动作所趋向的于体,“老师”是客体,是动作的内容。
(四)IV类动词
IV类动词三个动元间的可区分性如图4所示,主体和客体不可分,为同一种事物,所以主体实施的动作影响到的是主体本身的状态,基本句型为主体+第一类格标记+于体+第二类格标记+IV类动词(或IV类动词短语)。

图4:IV类动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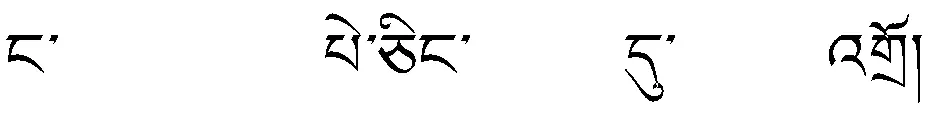
我 空格 北京 于格 去
(我去北京)
例11中,“我”是“去”的主体,也是被动作影响到的客体,而“北京”是动作的终点或方向,即于体。
(五)V类动词
V类动词三个动元间的可区分性如图5所示,主体、于体和客体均不可分,为同一种事物。所以只用一个格结构体就能表达句子的基本意思,基本句型为客体+第一类格标记+V类动词(或V类动词短语),表达“主体怎么了”之意。该类动词一般具有表示“状态性”特征。

图5:V类动词

图6:动词的三元分类

小孩 空格 睡着了
(小孩睡着了)
例12中,“小孩”是“睡着”的主体,也是被该动作影响到的客体,同时也是该动作指向的于体。
五、藏语中的语义兼类现象
藏语中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语法问题,即在动词和同一个名词间添加的格助词,因地区而异。比如“我”与“走”之间,卫藏人喜欢加上“施格标记”,而安多人则不加格标记(但可理解为添加了“空格标记”),说明不同地区的人对动词与名词间的语义格有着不同理解。语言学中称此类现象为“语义兼类”,如同“词性兼类”一般。一直以来对藏语的语义兼类问题,未有一个统一的语法解释。
通过前文提出的动词分类方法,可以很好地解释语言中的语义兼类现象。
我 施格 相信
(我相信)

我 空格 相信
(我相信)
例13中,对于动作“相信”,“我”既可扮演“主体”角色,是该动作的实施者;又可扮演“客体”角色,是该动作所影响的事物。所以说,“相信”和“我”之间存在语义兼类。在实际交流中,说话者根据当前语境,从语义兼类中进行选择,以突出其话语的重点。
我 位格 一支笔 空格 捡到
(我捡到一支笔)

我 施格 一支笔 空格 捡到
(我捡到一支笔)
例14中,“我”对于动作“捡到”来讲,既是“主体”也是“于体”,因为该动词以“获得”为主要义项,而“获得”所指向的“于体”就是“我”。因此,“我”和“捡到”之间的语义格是兼类的,“我”既是动作的“主体”,也是动作的“于体”。所以卫藏人喜欢使用“于格”表达动作于体,而安多人则喜欢使用“主格”来表达动作的主体,两种搭配各有自己的语义侧重点,没有对错之分。
另外,一个动词的主体、于体和客体是表达其基本意思必不可少的三个核心论元。因此,任何动词的基本句型中必定出现三个核心论元。因为三个论元间可能存在不同的兼类度,所以动词的基本句型也可分为三类:动词+三个论元,动词+两个论元,动词+一个论元。从形式上看,动词就有了不同的基本配价数量。
通过这种思路,可以解释为什么汉文或英文中有些动词要带双宾语,有些动词只能带一个宾语,而有些动词则不能带宾语的语言本质,进而能够揭示格语法和配价语法理论间的内在联系。此外,该分类法对计算语言处理的语义标注工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自主与不自主、使动与自动等基于传统语法范畴的分类方法不是平行的、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交错的。“及物动词大部分又是自主动词,有少数是不自主动词。不及物动词大部分又是不自主动词,少数是自主动词。及物又自主的动词内有一部分兼为使动动词,极少数兼为自动动词。不及物动词(包括自主、不自主)中有一部分兼为自动动词。”(15)黄布凡:《古藏语动词的形态》,《民族语文》1981年第3期,第2页。
基于三个基本动元的动词分类方法,不仅继承了藏语传统语法的根本思想,而且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传统分类体系,更好地体现出动词间的句法、语义差异。该分类方法能够自圆其说,能做到“不杂、不重、不漏”的分类基本要求,并且能够对藏语“语义兼类”现象进行合理解释。
基于句法语义一体化的藏语动词分类法,将动词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三元相互独立的动词集合,第五类是三元合一类动词集合,其他类则代表了至少两个动元不可区别的动词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