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水稻的岁月
2023-11-28汪志
文|汪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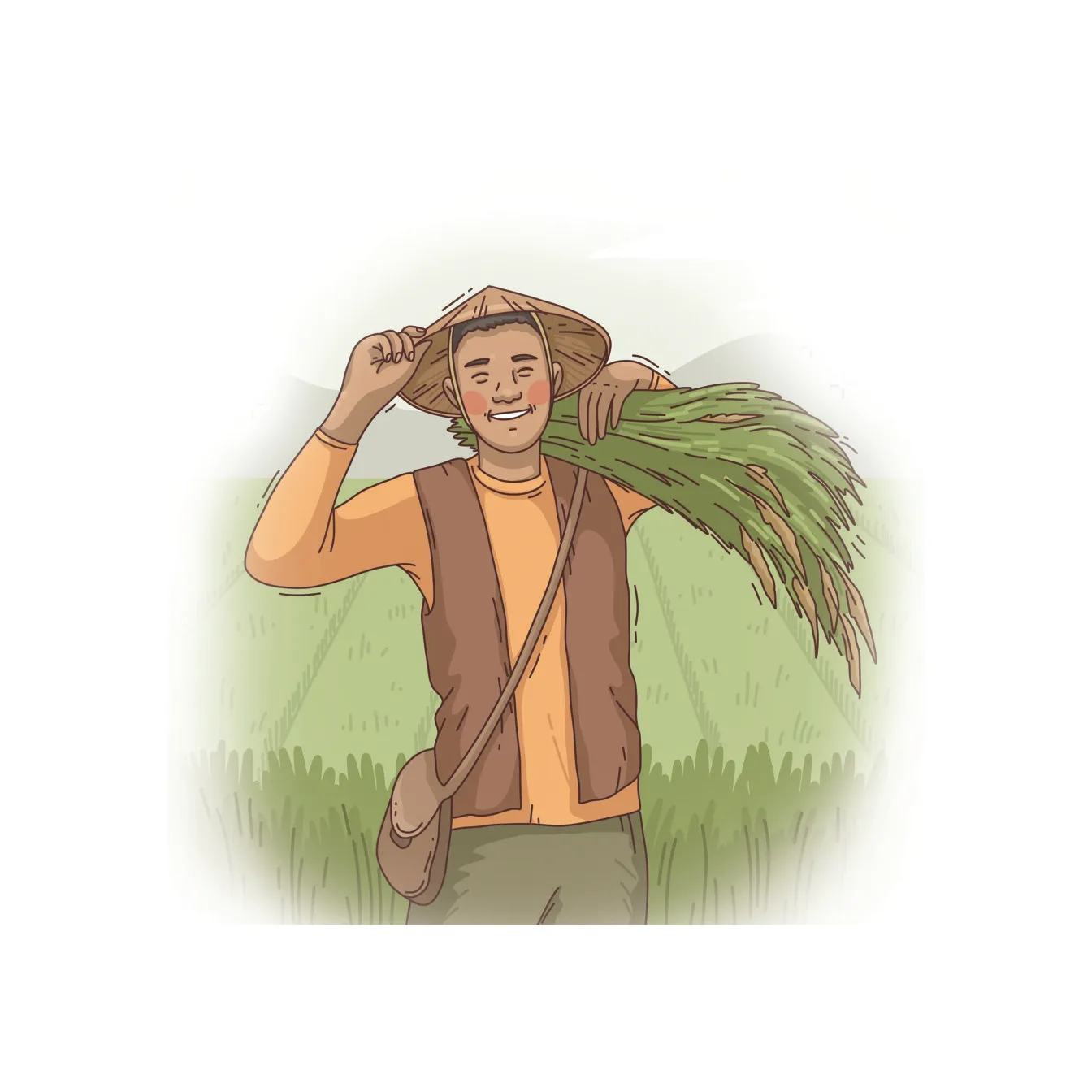
天蒙蒙亮,父亲就喊着我的乳名:“三娃子,快起来,和我们一起割水稻去……”
记忆中,从七八岁到二十岁,家乡那片富饶的水稻田就留下了我的身影。我在父亲由轻到重的呼唤声中醒来,揉着惺忪的睡眼,很不情愿地从蚊帐中钻出来,喝下母亲早已烧好的几碗粥,光着脚跟在大人背后走向稻田。一年当中的割水稻又开始了。
我出生于上世纪60 年代的南方农村,那时家乡水稻一般种植两季。早稻成熟收割后,得立即赶在立秋前栽插完第二季晚稻秧苗,越早越好,晚了,收成会减少甚至绝收。
割稻子是当时农活中最累、最苦、程序最多的一种,夏收这一茬尤其如此。“双抢”即抢收抢栽,因后面还要栽插下一季水稻苗,所以,夏收的时候不能把稻田里的水放干,只好在水田里割稻子。没有经历过的人不知个中滋味。
土地承包后,我家里有十几亩水稻田,父亲总是胸有成竹地根据每块田里稻子的成熟度来决定先收割哪块稻田。从小父亲就教我,弯腰割稻时,左手抓住水稻中部,右手持镰刀把水稻根部割断,然后再一把把放齐……不一会儿,一大片稻子被割倒了,起先那一整片金黄的稻穗不见了,在镰刀割稻的“嚓嚓”声中,一块块稻田露出了整齐的稻桩。
由于夏季天气炎热,一般都是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开始干活了,一直割到天黑才回家。在水田里弯着腰割稻,满脸满身始终淋着汗水,一时视线模糊或若有分神,锋利的镰刀就有可能“亲吻”你的手,如今我手上的好几处刀疤依旧还在。此外,整天在水里浸泡的手由于无数次地与粗糙的禾梗摩擦,刚开始常常会把手指磨烂,磨出一道道血漕,手指时不时地被禾叶尖刺着,钻心的痛。等到手指磨出老茧后,才不觉得痛了。
临近中午时,骄阳似火,稻田里的水都被晒烫了,站在密不透风的稻田里,更让人热得喘不过气来,满身泥巴犹如泥猴的我们“扑通”跳进旁边的河塘。河塘表层的水也是热的,必须下潜到水底,才能感受到一丝清凉,那是一种沁脾的凉爽。我们不停地浮上来换气,之后再下潜。
留守家里做饭晒谷的爷爷奶奶用大水壶送来茶水或早晨吃剩的稀饭,让我们“打中尖”。片刻的清凉,温热的茶水,换来一丝暂时的惬意。看自己身上,胳膊上、胸脯上已然留下一条条被稻叶划扫的红痕,汗水流过,感到一阵阵刺啦啦的疼。还没歇一会儿,大人又吆喝起来:“赶快割,早割早完……”
为了及时翻耕抢种,我们往往割完一块水稻田就立即进行脱粒。早先用的是一种木制的四角斛桶,正方形口的四条边各约一米长。脱粒时,四角边各站立一个人(一般都是成人),我们这些孩子专职抱着刚割下来的稻苗,裸露着身子,只穿个短裤衩,不时弯着腰将一把把稻苗从泥田里抱起来,再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泥田里,来来回回,将稻苗递给四角斛桶边的大人。
大人们双手捏紧水稻茎后部,双手向上扬起,在空中划一个弧圈,接着用力往斛桶梯面摔打,谷粒就在惯性作用之下掉了下来,这叫“摔稻”。拍打水稻时,双手还需稍作抖动,这样有利于已脱粒的谷物全部撒落于斛桶内,防止谷物在再次上扬中抛撒。
“摔稻”过程中,大人们还要连续把手中这把水稻翻转摔打几次,直至谷粒完全脱落。这样原来沉甸甸的一大把水稻,经反复摔打后,稻谷已基本脱落在斛桶中,手里剩下的只是一把稻草了,如此反复……
到后来,随着两人脚踩打禾机的使用,脱粒更省力更方便快捷了,但仍需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人工将田里的稻苗抱给脱粒人。轰隆隆的齿轮转动声、哗啦啦的脱谷声汇聚成一股夏日农场的旋律。大人们一只脚用力支撑着躯体,一只脚用力踩着打禾机脚踏板,双手紧紧握住稻把,摁在滚轮上用力转动。
随着打禾机一步步“消灭”了周边刚割下来的稻苗,我们疾驰在泥巴田里,从越来越远处将稻苗抱回来快速递给大人。在大人身体的晃动起伏中,谷粒唱着欢快的歌,离开了稻草,飞入前方的斗中……割完的稻子就地脱粒后,先将稻谷挑到场地上晒,接着把稻草扎起来挑到岸上去晒。稻谷稻草晒干后,还要挑回家,稻草用作耕牛过冬的草料和生活燃料。
这样的收割一般要持续20天左右。
虽然收割稻子辛苦,但对于农民来说,丰收的喜悦要胜过辛苦千万倍,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甘甜的。这番艰苦与欢乐也成为融入血液的记忆,使我在以后的人生中学会了隐忍、无畏、坚强……
现如今,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我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收割粮食是用大型收割机整片整片地收割,一边收割一边把粮食打出来用汽车拉走,根本不需用人工去割,还有专门的收割队伍跨区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