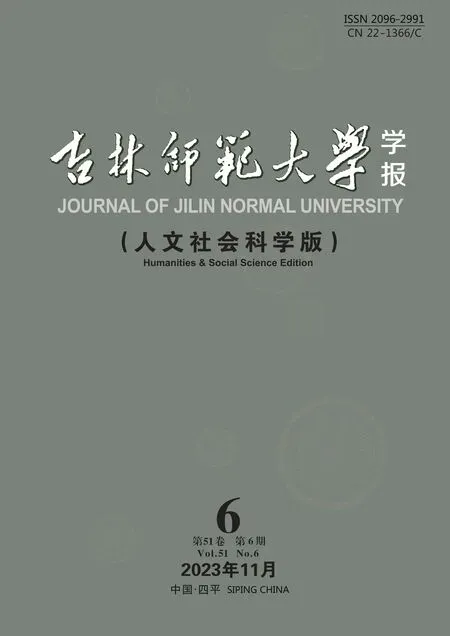从满族家谱探析满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2023-11-27孙守朋宋清颖
孙守朋 宋清颖
(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00)
满族家谱作为满族群体发展变迁的文字载体,记录着家族的繁衍与传承。现存的满族谱书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满汉文化的交融。目前关于满族家谱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①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李林:《从家谱中探讨满族文化的发展——满族家谱研究之一》,《满族研究》,1987年第4期;何溥滢:《满族他塔拉氏家谱中的汉文化因素》,《满族研究》,1993年第1期;杜家骥:《从取名看满族入关后之习俗与文化》,《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孙明:《论满族家谱序言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满族研究》,2014年第4期;李学成:《满族老姓汉化的历史嬗变——以满族八大姓为例》,《满族研究》,2016年第2期;杜家骥:《清代满族家谱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柴星男:《浅析满汉文化交融在满族谱牒中的体现》,《戏剧之家》,2018年第30期;阎丽杰:《中华传统文化视野下满族家谱的文学元素》,《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何晓芳:《满族民间家谱满汉文体书写嬗变的历史叙事》,《地域文化研究》,2021年第4期;张欣阳:《满族家谱体现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2月7日,第6版,等。,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满族家谱的内容、史料价值及其受汉文化的影响等方面,很少有透过满族家谱对满汉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故此,本文以满族家谱为核心,多方位、多角度对满汉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行探索。
一、满族家谱功能的融合与发展
汉族家谱的主要作用与功能为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和睦族收族。满族受汉文化影响纂修家谱,满族家谱的基本功能与汉族相同,但因满族发展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民族特点,满族家谱具有其独特的作用与功能。
(一)记述满族姓氏源流
明初女真人多以居住地或部落名称为姓,沿用辽、金、元时期的旧姓,据《皇朝通志·氏族略》统计旧姓共有35 个。《满洲源流考·金君姓氏考》记载:“《金史》所载姓氏,均与满洲氏族相合,第译对字讹,今悉据八旗姓氏通谱改正。”[1]86八旗制度的建立打破了原有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姓氏相同的满族人分驻各地,同宗的满族人亦分属不同旗分,相互之间称名而不称姓的习俗无法延续。随着满汉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满族逐渐学习汉族冠汉姓,称满族原始族姓为“老姓”。如《满洲苏完瓜尔佳氏全族宗谱》记载:“关姓者,乃满文瓜尔佳之译音也。凡满洲关姓,虽有旗佐不同,殆无不为我瓜尔佳氏之同族也;溯自有清龙兴辽沈,定鼎燕京,开国元勋,庶有八大家之称,而我瓜尔佳氏即其一也。于是乎,内而阁臣,外而疆吏,暨各省下之驻防旗族等,咸不乏我同族。”[2]2《牛庄萨克达氏族谱》记载:“始祖姓萨克达氏,讳里富哈,择本城东门外吉地而葬之,即为立主[祖]。始祖之呼,盖本于此,从此即以‘里’字为姓也。”[2]553从满族共同体形成到离开长白山入关,满族被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汉族文化深深吸引。满族人民为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同时也为方便各地分支追溯祖先源流,将满族老姓首字或音译或意译成汉文,同时在各家家谱中详细说明本族满族老姓,依然保留着满族本身的姓氏。故而“说世系”辨明原始族姓,成为满族家谱的一项功能。
(二)“溯本求源”,维系满族亲族联络
汉族家谱有着强烈寻宗问祖和维系宗族的目的,满族家谱基于汉文化的影响及其特殊的民族文化,亦具备此功能。满族先人在历史上曾经历了多次迁徙,规模最为庞大的是清朝建立全国统一政权后,满族八旗大量人口“从龙入关”,大部分被派驻各地,这就使得同宗同族的满族人被分散。《吴俄尔格氏家乘·谱序》记载:“尝闻国有史,家有谱,所以昭信纪实,重本笃亲,使世世子孙乃昭然知所自出焉。况沧田几变,支派繁衍,又经东西迁析,若非笔之于谱,则奕而下茫然莫考,未有不相视如秦越者,故家谱之作于繁衍之日者固亟,而作于迁析之后者尤不可缓也。”[2]698《满洲苏完瓜尔佳氏全族宗谱·序》记载:“苟无谱书以记载,恐宗支藩庶,难保无紊乱之虞。故于民国四年,经家叔宝泰公遵旧日之谱书,复参考而修纂,追源溯本,别派分支,编集成书,籍垂久远。揆诸斯举,诚谓善矣。无如日居月诸,星霜屡易,延及今日,数载于兹,其中之死者若干人,生者若干人,统京、奉、余、杭之间,又不知为数几许。前谱既未能加入,后谱又无人纂修,长此以往,姑无论后世小子有遗弃之虞,即骨肉至亲亦不免视同陌路。予也厕[侧]身学界,苦无余闲,然笃念同族,不禁生亲亲之感。”[2]3《伊尔根觉罗氏谱书·谱序》所述:“现届前清逊政,国体变更,旗署裁撤,各旗署户口档册均失根据,旗族渊源将要泯灭,宗谱如不乘时而修,再拖延数年,将不堪设想矣。思之痛心,言之浩叹,是以余等,怵然惊惕,编辑谱书,而须臾实不可缓也。”[3]12《福陵觉尔察氏谱书》:“迨顺治元年,奉旨命班布理之长子达喀穆、次子他察,均着看守福陵外,其余从龙入关,因差而分驻防焉。只以族繁支茂,旗官世职,难以枚举。”[2]744以上满族家谱清晰地记载了族内各支拨入其他旗分的情况,而在通信费时费力的清朝,可想而知,同宗族的各个支系一旦由于驻防或其他原因分散各地,彼此的联系将会变得十分艰难,同宗族各支便很难得知其他分支的消息,几世之后宗支紊乱的可能性大大提升,甚至可能有些支系与其宗族失去联系而无法得知其先祖姓名。为了维系亲族之间联络,使得宗族子弟知其统系来处,满族家谱详细记载了各支迁徙与人口情况。由此可知,满族家谱维系了各宗分支之间的联系。
(三)承袭官职,有案可稽
在清代,满族家谱除了具有鉴别亲疏远近功能外,还是承袭官职的重要凭证。为了维护等级承袭制度,谱书一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顺治年间,定旗员于承袭官爵时承造家谱,故将有分亲支子孙不行造入者,降三级调用。若承造家谱,将同祖亲属姓名疏忽遗漏者,罚俸三月。”①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0《兵部一》。“(顺治)三年奉旨,嗣后八旗世袭佐领,家谱内着将原立佐领人之子孙,按其名数尽行开入,如一谱不能尽书,即缮两谱具奏”②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30《八旗都统二十》。。雍正五年(1727)议准:“嗣后凡系世职家谱,预取保结,校对钤印,存贮本旗衙门。遇有世职缺出,查对明晰,奏请承袭。”[4]825《佟氏宗谱》记载:“览八旗定议,进呈家谱,可知承袭及继嗣,嫡派承袭之有分嗣,将袭职之家谱并敕书抄录定分,移送王大臣处查办等云,是八旗之家谱固与敕书并重。”[2]1092八旗佐领中世管佐领、勋旧佐领和八旗世爵均属世袭性质,因此在承袭官职时,为了证明血统渊源,必须附家谱以为证,体现出家谱在满族承袭官职中的重要地位。满族在编修家谱时,若疏漏子孙亲属姓名,则要对有关人员进行惩罚。因此,满族家谱因“承袭”需要,多以简单记载身份的谱单为主,与汉族家谱形成鲜明对比,更像一种档案户口册。
满族家谱的基本功能与汉族家谱相同,但满族家谱因满族自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衍化出既具有汉族风格,又具有满族特色的新功用,可见在生活之中满汉民族文化与风俗的交融。
二、满汉文化交融在家谱内容上的体现
满族入关后,在与汉族的交流和交往中,二者在文化和思想上均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渗透。满族家谱作为满族民族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充分显示了汉文化对满族文化的深远影响。
(一)按字排辈,体现宗法制度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施行的宗法制度是以家庭为核心、由父系家长制转变而来,并以血缘远近分配权力的一种制度,而此制度的文化核心是对血缘的高度重视。宗法制度在命名上的体现,一是在于无论子女均冠父姓,二是以族谱中的辈次命名。这种取名方法是以父姓加辈分字再加上名,而用这种方式取的姓名,从姓氏和辈分字便可知其血缘远近及长幼尊卑。这种命名制度对于封建社会维系等级身份制度和人伦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满族入关之前在取名方面并未有按照排字取名的习俗,入关后较早仿效汉族按字排辈取名的是清朝皇室。康熙皇帝为其子孙拟定排字,按辈分取名,上行下效,这种取名原则在清朝民间也逐渐流行。如《镶黄旗佛满洲哲尔金佐领下王氏谱》详细记载了王氏家族一世祖至第三十世所用字,上十辈为“达、平、太、阿、那、士、德、魁、贵、升”[2]525。《萨克达翁氏宗谱》更是单独记载翁氏宗派取名所用字达40字之多。[2]588有些满族家谱虽未正式记载字辈,但我们据世系可以推知。如根据《正蓝旗满洲萨格达氏宗谱》的世系记载可知,第六世至第九世所用字分别为文、里、吉、福。上起皇室,下至宗族,都逐渐和汉族一样在取名中使用字辈。不同阶层的满人群体随着与汉族宗族的共处,在满族家谱中也逐渐体现出宗法制度,映现了满族在与汉族交往的过程中受到了汉人宗族礼法的影响。
(二)推崇儒学,接受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为孔子所创,中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勇,它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在满族家谱中,处处渗透汉族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清入关以前,皇太极时期已经形成崇尚儒学的风气。皇太极自幼受教于龚正陆等汉族文士,内心向往儒家文化。他在位时平等对待满汉两族人民,推崇儒学,为满族吸收儒家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清朝历代皇帝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纷纷效仿汉族统治阶级,将“三纲五常”“孝治天下”等儒家伦理思想推而广之。这点在满族谱书中体现得较为典型的是《吴俄尔格氏家乘》中的满文碑文,碑文多次提到“妇道”一词,如“妇人之道,殉夫而死者,缘于无嗣”[2]705“克尽妇道,堪谓内室之楷模”[2]705。碑文大致讲述的是一位无嗣孀妇一心殉夫求死的故事,此事报送礼部后,礼部“奉旨旌表,赏给立牌坊银两”[2]705。同时碑文记载“凡吾族人,见此碑石,当敦孝悌,重节义,以传之永久”[2]708。女子的殉夫求死行为在清朝被称为“楷模”,而对“夫为妻纲”事件的嘉奖,足见随着与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已深深印入满族人的心中。
(三)汉文取代满文成为书写语言
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人创制满文,皇太极时期对其加以改进,清朝建国后推行满文。17世纪中期以后,由于满汉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逐渐形成汉文取代满文的趋势。早期的满族家谱还有用满文撰写的,但18—19世纪的满族家谱则多用汉文撰写,很少有满汉文对照之处。从满族家谱所使用的文种也可以看出满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呼兰府志》记载:19世纪末年,满族人“能通清(满)文者,不过百分之一;能操清语者,则千人中一二人而已”①(民国)黄维翰编:《呼兰府志》,1915年铅印本。。如《正蓝旗佛满洲乌苏哈拉家谱》为满汉文双语所写家谱,谱单中存在三十余处满文谱注,至今虽已近200年,但保存较好的满文谱仍颇具价值。《马氏宗谱》首次修纂于乾隆年间,但原本遗失,现存谱书为后人据前本续修而成,虽为石印本,但在谱书中仍可见满文姓名与汉文并用的情况,可知族中依然存在懂满文的老人,但汉文已逐渐被满族人所推崇,故而使用满汉双语来进行撰写。《瓜尔佳纳音关氏谱书》记载“历代相传至今,若不译成汉文,急力修葺,而满字再行失传,所遗家族之历史,只字不识,岂不成为无用之废纸也”[2]796。于是,“满文公牍经验颇多”的关祥玉将满文谱译为汉文,并印刷成书。《宁古塔正黄旗梅和勒氏宗谱》记载:“于民国五年兴修宗谱,规定族秩,恐满文失传,改修汉文,迄今二十余年。”[2]661以上两本家谱直观地讲述满文已近失传的状况。《满族赫舍里康族世谱》初修时即用汉文书写,族人至此已不通满语。前两本家谱满汉文尚且并存并互相对照,而后一本初修之时便完全使用汉文,此番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文逐渐替代满文在满族人交流和记述中的地位。这进一步说明了满文在满族的历史舞台中逐渐退场,汉族语言文字对于满族的影响便可略见一斑。
三、姓名方式变化,循从汉族礼俗
满族入关以后,具有数千年文明传承的汉文化对满族产生了深远影响。满语姓名是满族文化中重要一环,满族人以汉名逐渐代替满名,可谓是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一)“满姓变汉姓”
在满族形成阶段,姓氏绝大多数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组成。清朝定鼎全国后,满族人与汉人深化交往交流交融,满族姓氏受到汉文化影响,逐渐定为单一汉字,即单音节形式。
满姓变汉姓有三种形式:取满族老姓首字谐音作汉姓,富察氏简化为“富”,瓜尔佳氏简化为“关”,赫舍里氏简化为“赫”。以满族老姓汉译为姓,钮祜禄氏汉译为狼,便以同音字“郎”为汉姓,尼马哈氏以汉译“鱼”为姓,巴颜氏汉译为富有,便以“富”为姓。取先世首字音为姓,即“随名姓”。如《赫舍里王氏族谱全书》记载:“天福系索罗长子,缘外祖之嗣。因冒其籍而继其姓。以‘王’易‘索’,遂永世焉。”[2]247因先世入赘,故而此支赫舍里氏随之改姓为王。随着满汉民族间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和交流,越来越多的满族人为符合时代发展和称呼方便而由满姓改为汉姓。满族人取汉姓的行为,是随着与汉人间的交往产生的。满族家谱反映了满族学习并接受汉族文化的这一历史进程。
(二)名字变化,效仿汉人取名习尚
满族入关以前,满族人对于其姓名蕴含的意义并不考究。对于这样一个以狩猎为主要生存手段的民族,姓名只是他们用来称呼和区别彼此的一种工具。以努尔哈赤家族为例,如多尔衮(词义为“獾”)、阿敏(意为“后鞍桥”)和博和托(意为“驼峰”)等与禽兽、狩猎相关的名字一直被沿用,这在汉族鲜少得见。入关前的满族人还热衷于以数字取名,像那丹珠(七十)、乌云珠(九十)等。而在满族入关以后,与广大汉族人民共同生产生活,汉文化对满族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满族在对名字的取用上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1.以汉文数字取名。以数字取名是许多少数民族的风俗。《康族世谱——满洲赫舍里康氏族谱》记载第五世佛宁又名七十二;《京都吉林宁古塔三姓等处镶黄旗陈满洲关姓宗谱》中可见七十八、五十六、六三、八十、六十一等数字名;《常氏宗谱》中第二世和第三世共8人,仅1人姓名无数字,四儿、六儿、七十、五十七、五十三、六十五、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二、七十八、八十四、八十七、九十、九十一等汉文数字名在世系中频繁出现。据满族家谱可知,清入关后这项习俗依然盛行。满族入关以前,是以满语数字为名,如乌云珠(九十)、尼音珠(六十)等。入关之后,以满语数字为名者并不多见,以汉文数字起名者屡见不鲜,这反映出以数字取名的满族旧俗已经具有鲜明的汉化色彩。
2.名字文雅化。入关前满名中出现率较高的奴、儿、厄等粗鄙字眼已慢慢淡出满族家谱,满族人开始以汉文取名,选取文雅、优美的字词,如明、灿、桂、芳等字词,借此美化自身的形象。这种用字选词,不仅是取名习俗的变化,而且反映了满族对汉族文化的接受程度与欣赏。如《满洲苏完瓜尔佳氏全族宗谱》第十二世恒企、文岱、世杰、忠明,第十六世恒玉、文喜、荣恩、承恩、庆恩、德海、德山、德喜、德明、德昌、德清、德亮、德安;《汪氏宗族谱书》第十世逢泰、逢唐、逢禹、逢辰、逢书、逢瀛、逢瀚、逢睿、逢淇、逢昱、逢臣、逢谦、逢亭、逢洲、逢尧、逢渠、逢石、逢滨;《那氏族谱》第六世永明、永亮、永隆、永兴、永清、永宁,第九世广来、兴德、长德、兴茂、兴海、兴有、兴盛、文镐、文焕、文荣等。
3.名字寄托对美好愿景的追求。汉族在名字的用字方面,偏好于福禄吉祥,此习俗对满族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上至皇室王公,下至寻常百姓,皆喜欢在起名时用蕴含福寿吉祥寓意的字词。满族人借汉字寄托对子孙后代的美好愿景,体现出满汉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交融。如《姜尔佳氏族谱》第六世福宝、福禄、祯宝、常禄,第八世福德、福太、福宽、福海、福有、福恒、福深,第九世德禄、德纯、德成、德海、德庆、富明、富春、富住、富顺、富太、富临、富钟、富生;《富察氏谱书》第十四世云升、云鸿、云瑞、云祥、云龙、云凤、云福、云功、云泰,第十六世明海、明春、明耀、明长、明祯、明金、明德、明恩、明连、明国、明景、明群、明成、明本、明喜、明宝;《完颜世谱书》第九世恩福、德喜、连惠、连喜、连禄、福祥等。
入关以后,满族的取名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体现出明显的汉化色彩。从形式上看,满族逐渐以汉姓为姓氏,以汉文取名者也逐渐增多。在取名方面,日渐注重用词文雅、按字排辈和图吉祥等与汉族取名一样的习俗,使得满族在取名方面刻上了汉文化的深深印记。
四、满汉通婚,民族融合
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统治,制定并推行了一些限制满族人与汉人的婚配政策,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无论是统治阶级上层还是普通百姓,满汉通婚现象在整个清朝都是存在的,而且在乾隆以后,满汉通婚越来越多。
在清代满汉通婚中,汉军旗人是两族通婚的桥梁和纽带,他们既可以与满洲旗人通婚,也可以与汉人通婚。如明代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后代在入清后隶属汉军八旗,《李氏谱系》对嫁入李氏的满洲八旗女子及出嫁至满洲八旗的李家女儿之出身及生卒年进行了详细记载:“八世李荫祖,娶祝氏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都统、世袭二等阿达哈哈番祝世胤之女,生于明崇祯庚午年六月十八日午时,国朝顺治辛卯年诰封恭人,己亥年再封一品夫人,卒于顺治己亥年七月初九日亥时,年三十,公殁合葬。继娶觉罗氏三等侍卫、世袭一等阿达哈哈番觉罗氏达哈塔之女,生于顺治戊子年八月十五日子时,无育,自十七岁守节,至康熙癸巳年四月二十五日巳时卒,年六十有六,以子官诰封一品夫人,与公合葬”[2]980;“八世李辉祖,娶郎氏一等阿达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户部郎中兼参领郎公廷辅之女,生于明崇祯癸未年三月初三日申时,国朝康熙丁未年诰封淑人”[2]981;“八世李兴祖,娶纳喇氏吏部尚书马希纳公之女,生于顺治庚寅年七月十九日午时,诰封夫人”[2]981;“九世李,娶觉罗氏内弘文院大学士、吏部尚书加一级觉罗公伊图之女,且其女二,俱伊氏出,长适觉罗,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觉罗公孙果之子”[2]976;“十世阿思哈尼哈番李林隆,继娶西林觉罗氏内大臣席尔根公之孙女,生于顺治己亥年四月初四日未时,诰封一品夫人,卒于康熙甲戌年正月十五日子时,年三十有六,与公合葬”[2]975;“十一世李杰,继娶马家[佳]氏正白旗副都统嗦尔希公之孙女,生于康熙丁未年十月十九日子时”[2]976;“十二世李建基,杰公长子,娶郎氏满洲镶黄旗副都统郎公之女,生于康熙辛酉年三月十五日巳时”[2]977。
虽然有清一朝,在满汉通婚方面多有政策限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没有那么严格,查处后对其的处罚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减轻。到了清末,满汉之间的通婚已经不受任何限制,甚至不再受到舆论的谴责。
有学者在研究东北吉林地区《他塔喇氏家谱》记载的婚嫁情况时发现:“共得719例,其中与当地满洲旗人结姻者为509例,占总数的71%。与汉姓通婚为210例,占总数的29%,这210例中,明确为汉军旗人的为80例,其他130例中,很多是明确写作‘民籍’汉姓人。其未写民籍的汉姓人,满洲旗人当很少。”[5]“统计数字还表明,这210例与汉族血统通婚之事中,该家族男性娶汉姓之女者又占大多数,为158例,占75%。而该家族之女嫁汉姓人者较少,为52例,占25%。进一步说,在这一满洲旗人家族与汉血统人通婚事例中,该家族所娶汉姓女生育的满汉混血的满洲旗人,要多于该家族出嫁给汉姓人的满人女所生育的汉满混血汉人”[5],“这一家族有记录的婚姻人口有近十分之三是与汉族血统人通婚,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反映出东北地区不设驻防满城而散居各镇、屯的驻防满洲旗人与汉人通婚较多的情况。由此产生其后裔的满汉民族融合,也可想见”[5]。
从以上所列满族家谱中的婚娶情况,我们可知即便清代满汉通婚关系受到“旗民不婚”“旗女不外嫁”等种种限制,但在旗内依然存在着大量汉军旗女和汉女嫁入满洲八旗以及满洲旗女嫁入汉军旗等现象,也有少量满洲旗女嫁给汉人,而在通婚的过程之中,汉文化与满族文化从最小单位的家庭中开始交互融合。
五、满汉文学元素融合
与家族有关的人与事一般都可写入家谱,因而在满族家谱中,一些族人的文学作品或与族人有关系的人也在其中,如作序的作者。有情感的地方就会有文学的存在,因为文学是审美情感的表现形式之一。满族家谱中有大量用汉文编写的家谱,其中有情感灌注和歌颂赞美等文学元素,因而形成了文史互映的现象。其实,满族家谱的编修可以显示出一个家族的文学修养。满族家谱孕含着丰富的满族民间文化资料,也包含了大量的文学元素。优秀的满族家谱文字往往文采飞扬,激荡人心,满族家谱的文学元素不可忽略。为了写好满族家谱,满族人积极学习汉文经典书籍和历代文学名篇,学习诗词格律,因而编纂出来的满族家谱体现了满汉文化交融。[6]
(一)修辞优美,蕴含汉文化
在满族家谱谱序和祭文中,经常运用恰当的修辞方法,使其写得颇有文采,词语隽永,从而增强了家谱的可读性。好的满族家谱往往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既不失历史之真,又不失瑰丽之色,让后人更加喜欢阅读和传承。满族家谱所运用的文学修辞方法主要有对仗、排比、比喻和借代等。如《马佳氏族谱·祭文》:“国家隆报功之典,视亡如存;朝廷笃念旧之情,有加无已。尔图海,谟猷重地,弼亮元臣,服事累朝,多历年所。入参密勿出总戎,行柱石之望攸归,鼎钟之铭不没,奄逝一旦,辇盖痛奚穷。呜呼!泉壤沈冥,良抱股肱之戚,河山巩固,永彰带砺之荣。载展几筵,庶其歆格。”[2]153“临朝思社稷之臣,抚几切腹心之寄。尔图海才德全备,忠爱性成,既有翼以有冯,复不矜而不伐。成劳茂著,报礼宜隆。呜呼!气炳日星,嘉明良之既遇;云归乔岳,缅飏拜以如存。三锡牲牢,用光原壤”[2]153。满族家谱在编写过程中善于运用修辞手法,使得家谱能够吸引读者,传承了家族文化。如“国资良弼,纪勋绩于旗常;礼重明禋,萃芬芳于秬鬯。惟嘉猷之未艾,宣特典之优崇”[2]153。“德必追崇,俾泽流于封树;功宜报祀,爰宠锡以尊彝”[2]153。满族家谱既是家族的历史文化记录,又是代代传承的文学作品,可观可赏,使子孙后代对满族家谱充满兴趣。如“功在旗常,诞畀优崇之典;荣施堂构,永垂奕叶之光。维乃绩之可嘉,斯惟馨之宜荐。尔图海殚心奉职,宣力服劳。出典戌麾,寄干城之重任;人参密勿,作心膂于王家。秉奉国之诚、初终无间;凛匪躬之义,夙夜惟寅。念尔殊勋,频加渥泽,考彝章而立祠宇,灵爽式凭;因时序而奠几筵,蒸尝不替。所司竣事,牢醴载陈。呜呼!风度犹存,念谋猷于往昔;系纶重布,荷宠锡于无穷。庶克祗承,尚其歆格”[2]153。《吴俄尔格氏家乘·谱序》记载:“虽时移地易,而按谱以稽,森若雁序,不致茫然莫考,视若秦越,辟诸黄河之水千里九曲,其穿龙门、过积石以达于海者,皆同源星宿也。”[2]699以上谱文所撰内容对仗工稳、修辞雍容文雅、词句朗朗上口,足见修谱人深厚的文学底蕴。
(二)引经据典,源出汉文典籍
随着满汉生活交集与日俱增,至清末,满族对于中华民族经典文学作品已十分熟稔,在族人取名方面源出经典。如《镶红旗满洲邓氏族谱》记载:“天启”源自《左传·闵公元年》“以是始赏,天启之矣”[7]46;“其昌”出自《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为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7]39;“天钧”源于《庄子·齐物论》“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8]22。《康族世谱——满洲赫舍里康族世谱》记载:“明志”出自《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9]135;“明德”源于《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①《礼记·大学》。。《库尔喀地方舒穆禄氏家谱》记载:“克勤”出自《尚书·大禹谟》“名言克勤于邦,克俭于家”②《尚书·大禹谟》。;“有德”源于《周礼》“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③《周礼·春官·大司乐》。;“永年”源于《尚书》“资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④《尚书·周书·毕命》。。以上所举均可展现满族吸收汉族文化,逐渐融会贯通,学养不断提高,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满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三)诗歌抒情,传汉文化瑰宝
诗歌是汉文化的瑰宝,来源于上古时期的劳动号子,后发展为民歌及祭祀颂词,是一种以富有韵律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来表情达意的文学体裁。满族在汉文化的濡染下,开始形成借诗歌抒情和抒怀的习尚。在满族家谱之中存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诗歌,有歌颂祖先的,有关乎祭祀的,有御试诗,也有抒发个人情感的。如表达宗族情感,《佛满洲佟佳氏全谱》中的“万枝归一本,千派总同源。定鼎功常在,承恩世不休”[2]312。如抒发解甲归田、抱子弄孙之个人情感,《吉林成氏家谱——正黄旗汉军吉林成氏家谱》中的《中宪公归里诗》:“吾谋适不用,归卧旧田庐。去矣冠裳远,萧然风月疏。青山容对酒,白发渐盈梳。招集儿童辈,还来读我书。”[2]1078包含寓情于景和节日抒怀的御试诗,体现了满族的文化与景观特点。在《吴俄尔格氏家乘》中存有许多御试诗,如下页表1所示。

表1 《吴俄尔格氏家乘》御试诗文表
尽管清朝一再强调“国语”(满语)学习不要荒废,然而满族无法避免与广大汉人交往交流,无法不学习汉语言。语言是掌握文化的基础,满族在学习汉语后进一步娴熟掌握了汉文化,在编修满族谱书时,接受了汉族传统文化因素。
六、结 语
满族入关前,满族家谱初始于“结绳记事”。满族各户都有“子孙绳”,一根以五彩线拧成的线绳,若生了男孩,便系上一把小竹制弓箭;若生了女孩,则系上代表女性的彩色布条,这便是满族先民最初用以记录家庭成员的实物载体。入关后,随着八旗制度的确立,旗丁分属各个旗档之中,这种户口档册就是“子孙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世袭职位需以家谱辅证身份,亦使得满族修家谱风气日盛。乾隆以降,满族渐染汉族文化习俗,自身素质得到提升,在撰修家谱上也吸收了汉族家谱的体例和内容。满族家谱在体例上沿用汉族家谱的欧体、苏体或欧苏合体,内容较之前也愈发完善,同时仍保留了一部分满族特有元素,如满文和旗属等。满族在与汉族日渐紧密的交往之中,深受汉文化熏陶,满族家谱也逐渐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满族自身文化因子在其中也得到体现,最终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满族家谱。满族家谱是满族学习、吸收和融合汉文化的重要成果,反映出满汉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对于满汉交往交融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