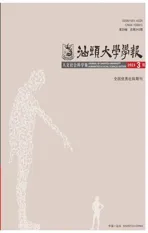《马尔多罗之歌》中的崇高与恶
2023-11-26刘宇婷
刘宇婷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引言
18 世纪以来,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崇高重新进入美学视野并成为一时讨论的热潮,此时的崇高开始与恐怖和痛苦的体验联系在一起。伯克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中总结道:“凡是能够以某种方式激发我们的痛苦和危险观念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以某种表现令人恐惧的,或者那些与恐怖的事物相关的,又或者以类似恐怖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事物,都是崇高的来源。”[1]36伯克的崇高观念一方面综合了同时代如艾迪生、休谟等人崇高思想的经验主义式观点,另一方面对康德划时代的崇高分析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转折意义。
一般来看,崇高意味着无限性、无序性,往往形容能够体现出庄严、伟大的气魄,且具有震慑力量的事物。崇高物体往往是无形式的,由于自身的宏大威猛,在一开始给人带来具有压迫感的痛苦体验,但这种痛苦随后又伴有另一种释然的愉悦,换句话说,崇高感是痛苦的快乐。尽管对崇高的专门研究最早是在文学艺术的批评中兴起的,当我们称某一作品具有崇高性时,它既可以是在朗加纳斯意义上由思想、情感、辞藻、措辞、结构几个要素构成的雄浑、豪放的文体风格,也可以是现代作品中的暴力美学和哥特式恐怖等,而康德式的崇高又将我们引向心灵的理性、道德维度。如果说美对应着和谐、平衡和善,那么崇高往往与无序、混乱以及恶相关联,这实际上为文本阐释带来了更多启发。正是在崇高的经验上,我们发现了进入《马尔多罗之歌》并透视其作者洛特雷阿蒙的一条路径。
一、《马尔多罗之歌》中的崇高与恐怖
初读《马尔多罗之歌》,读者定会被其中种种恐怖场景和骇人意象所震撼。这部创作于19 世纪的散文诗篇幅不长,仅由六支歌组成,每支歌又分为数个小节,是英年早逝的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唯一一部完整作品。与其说《马尔多罗之歌》是一部散文诗,倒不如把它看作一篇小说。因为这部作品虽然没有整体连贯且环环相扣的情节,但主要围绕着马尔多罗的种种事迹和他对人类、世界的看法而展开,具有很强的叙事性。洛特雷阿蒙在世时并不十分出名,真正使他和这部作品进入公众视野的,是20 世纪初期超现实主义者的发掘和推崇。《马尔多罗之歌》对恶的鼓吹,对暴力、恐怖的大肆渲染,各种精妙而出人意料的比喻,以及对人类社会毫不留情的挖苦讽刺,正投以安德烈·布勒东为代表的一批超现实主义者所好。
《马尔多罗之歌》的恐怖首先来自于主人公马尔多罗毫不掩饰的残忍天性。作为一个“天生的恶棍”,马尔多罗在行凶时丝毫不抱有一丝怜悯和犹豫,就算对纯真无邪的儿童,他也仍在幻想“用剃刀割下那粉红的脸蛋”,或是“趁他毫无准备,把长长的指甲突然插入他柔嫩的胸脯”[2]7。对于另一个跟随着他的十岁小女孩,他又想象:“我可能会在一个失去理智的时刻,抓住你的双臂,像洗衣拧水似的扭曲它们,让它们像两根枯树枝似的发出断裂的响声,然后使用暴力让你把它们吃下去。”[2]52在杀戮手段方面,马尔多罗的想法总是层出不穷,而真正的恐怖在于,他伤害他人并不为了将人置于死地,甚至这一切不是出于具体的仇恨,他杀戮仅仅是为了杀戮本身,即杀人这一行为或杀人的过程。马尔多罗是一个天生的虐待狂,他在想象中编织了种种细节,如魔鬼一般用“镰刀”、“剃刀”,用“长长的指甲”如何切入人的身体,或损害其某个部位,使读者为之惊惧。他出入于坟前、墓场、疯人院等阴森的场所,使一场场杀戮更具阴郁气息,而即使是在山顶、海边或树林里,马尔多罗也将其渲染得如“坟墓一样庄严”。总而言之,一切都被哥特式的恐怖所弥漫。在这地狱般的世界里,所谓“造物者”也如同死神一般邪恶,他的“双脚浸泡在一个宽阔、沸腾的血池中,血池的表面突然浮起两三颗谨慎的人头,又立即以飞箭的速度沉下去,好似绦虫穿过便壶中的物体”[2]61。当造物者仍生活在一个如同“便壶”般的充斥着血腥和污秽的场所,残忍无情如地狱中的死神时,他创造的世人又如何呢?无非是一个个同样阴险狡诈的恶魔。
然而奇异的是,正如《失乐园》中反抗上帝的撒旦一样,尽管代表着邪恶,马尔多罗却在一次次狂暴的交战中燃起了一种崇高感。当我们惊异于作品中的暴力和恶行时,往往忘了其以“马尔多罗之歌”为名正是为了“歌唱”、烘托马尔多罗这一形象,因此,作者有意从文体形式、意象选择到人物塑造等方方面面来实现这一目的。《马尔多罗之歌》并不遵循统一的叙述方式,有时使用第一视角,有时使用第三视角;有时以书信的方式展现马尔多罗内心的独白,有时又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来讲述他的事迹,而有时则直接由马尔多罗本人来进行叙述,有时又以大段的对话来推动情节。读者需要对文本有一定的熟悉度才能够明白讲述的对象究竟是谁,在翻越这第一个形式的困难后,读者又将马上迷惑于马尔多罗的身份:马尔多罗究竟是人是怪,抑或是神?他看似是一个男人,而后又变成了阴阳人、两栖人,甚至又化作一只虱子、一条巨大的章鱼。一切都陷入变幻莫测的不定性中,作者洛特雷阿蒙对各种怪诞意象的叠加,大量排比、比喻的使用,无时不刻增强了迷幻、诡异的氛围。
尽管以马尔多罗为主人公,《马尔多罗之歌》同时也以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大自然的怪力乱神,让读者仿佛来到了《山海经》中的世界。这其中既有滔天的噬人巨浪,也有张牙舞爪、成群结队的凶猛动物,马尔多罗本身的狂暴也更像是来自于未经开化的原始自然,而不是在所谓的理性教化后更加伪善、丑陋、软弱、狡诈的人类——他致力于与这样的人类划清界限。在第一支歌的第9 节中,作者用十个段落的排比歌颂“古老的海洋”,以海洋的恒常和平静来讽刺人类的多变,以海洋的谦虚来讽刺人类的自负,以海洋的博爱来咒骂人类的忘恩负义,而后的情节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马尔多罗对大海的爱,或是作者洛特雷阿蒙对大海的痴迷。第二支歌的第13 节在刻画马尔多罗的性格及其与自然的关系上具有代表性,这一节中马尔多罗化作两栖人,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与一艘遇难的船以及海中的鲨鱼相遇。
在第二支歌的第13 节中,马尔多罗再次敞开心扉,讲述着自己的孤独和他对另一个相似灵魂的渴望,但对于同伴,他总是宁缺毋滥,当一个青年和一个美丽的女子试图接近他时,马尔多罗冷漠地拒绝了他们,直到他在海边的岩石上观测到一艘巨型军舰。此时,天色黯淡,一场风暴将至,呼啸的海风、爆裂的雷声、霹雳的闪电带来末日般的沉重感,人在大自然的狂暴中无能为力,军舰的船帆被海风撕成碎片,整只船变成一座“活动坟墓”。“遇难船鸣炮发出警报,但是,它在缓慢……庄严地下沉。”[2]82这句话如箴言般反复出现,仿佛不断响起的末日鸣笛,像是在向人类宣示,面对大自然的审判,人类的任何反抗都是徒劳。在不断沉没的游轮上,受难者竭尽全力逃脱苦难,“有时一个老婆子因恐惧而发疯,像牛一样吼叫,想在市场卖个好价。有时,一个婴儿发出一声尖喊,使人听不到操作指令。”[2]82-83一时间,死者的呼号声、雷电的霹雳声、海风的呼啸声混杂在一起,而这些恐惧的嚎叫也被海浪、狂风、雷鸣的震耳欲聋所掩盖。在这“没有星光的天空下”,“血与水混合”,大海吞噬了一切,不管任何人以求生的努力来试图战胜死亡,都将必然走向失败,因为即使他们将要成功游上岸边,死神般的马尔多罗又将在悬崖上用步枪将他们击毙。
在这难以名状的强烈风暴中,只有马尔多罗能够幸免一切苦难,而这反而更令人心生恐惧,因为他对自己的人类同族没有一丝怜悯之心。正因如此,马尔多罗显得像是唯一战胜巨浪和风暴的胜利者,一个生命的审判者,一种诡异的比肩大自然的强力感和威严感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紧接着,一群鲨鱼闻到血腥味聚集在难船周围,将受难者的肢体当作他们的“鸭肝酱”“清煮肉”和“红色奶油”,它们为了争夺食物而展开激烈的斗争。马尔多罗帮助一只强有力的母鲨杀死了其他竞争对手,随后,两位强者——马尔多罗和母鲨——在各自身上“发现如此多的凶猛而感到惊奇”,“怀着相互的赞赏,怀着深深的尊敬”,当读者以为他们要展开最后的殊死一搏,一分胜负时,他们竟然“满怀庄严和感激,像兄弟或姐妹一样温柔”,在暴风雨的洗礼、闪电雷鸣的欢庆中,将海浪视作婚床,交织在一起。这是多么令人惊颤的奇异结合!一个嗜血的两栖人与一只同样凶猛的母鲨,无视物种的规律和自然的肆虐,在一系列紧张的斗争和血腥的杀戮后,完成了一次似乎是宣告胜利的完美结合。
马尔多罗在此仿佛散发着神性,他变成了一切的主宰,既审判着那些内心丑陋的人类,又战胜了变幻莫测而残暴无情的自然。他的胜利和超越又不仅仅在于此,而是在于遇见了和他相似的、具备一样思想的伴侣,这桩可怕而又庄严的“婚事”使这个凶险的海难故事回归至新的和谐中,使人在遭遇了难以名状的恐怖后终于趋于平和,体会到非比寻常的、劫后重生般的快感。尽管这种和谐和平静是恶者所创造的,但是这个恶却是超越性的恶,它建立于对另一种更为普遍的人类之伪善、软弱的恶的反思上,以否定性的颠覆面貌昭然于世。康德式崇高中想象力与理性的和解在此完成了奇异的变体,凶狠的母鲨象征着自然的杂多,鲨群吞噬着人类的残肢断体,昭示着人无法比拟、更无法统摄的强力。而马尔多罗的胜利不是理性的胜利,他的强壮正在于宣告理性在启蒙的进步后讽刺性的失败,此时真正具有崇高性的是超越理性的自我的爆发,这是以恶的面具示人的马尔多罗的胜利与和解。在此我们将进一步认识到,与其说马尔多罗是恶本身,不如说他是纯粹欲望的化身。
二、马尔多罗的崇高与恶魔之恶
在法语中,马尔多罗(Maldoror)一词与意为“黎明之恶”的mal d’aurore 谐音,黎明代表着生命的初始,黎明之恶即象征着生命之恶。因此,正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一样,“马尔多罗之歌”就是一首“恶之歌”,洛特雷阿蒙像他的前辈波德莱尔一样,借马尔多罗这个形象高唱着恶的颂歌。与美象征善对应,崇高往往与恶相互关联,这个恶既是形象的不对称的、奇形怪状的丑陋,也可以是道德上的邪恶。马尔多罗坦言自己是“天生的恶棍”,尽管他多年以来一直掩饰自己的邪恶本性,但随后还是整个地投入到“恶的生涯”中。他像歌颂善一样为恶声张,从不为自己的恶行进行辩护,甚至以此为荣嘲笑人类借行善来作恶的虚伪。马尔多罗几乎将人类的道德准则整个调转过来,以极恶而不是至善为最高的道德追求,这种纯粹的恶的意志类似于一种魔鬼般的恶。
康德认为恶是人的本性,恶具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恶是人性的脆弱使然,他/她即便知道正确的道德准则,但没有坚强的意志去履行而选择作恶;第二种恶由于心灵动机不纯,人把道德动机和非道德动机混为一谈,并且不将道德准则作为唯一充分的准则来遵从,在道德动机之外还有其他自爱动机,这在康德看来是善的名义掩盖下的私人利益的恶;第三种恶是心灵的恶劣,它是人心的败坏使然,这种恶是人有意为之,将道德法则完全置于自爱法则之下,尽管这时人看起来按照道德法则行事,但是完全背弃了道德法则。康德认为,主体是能够自主进行选择的自由主体,人既有向善的意念,也有趋恶的意志,选择向善或趋恶都是主体自由意志的权力,但主体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真正的恶在于意念,一个人的善恶不在于他的外在行为,而在于这个人内心的道德意念。如果人在内心知道这个行为是恶的但仍然为之,这个人就是真正的恶的主体。这三种恶的形式实际上都是自爱法则与道德法则在人心中的博弈,恶是自爱法则战胜道德法则的后果,总的来说,是人心灵软弱、不纯和败坏的体现。
但是马尔多罗的“纯恶”不在这三种恶的范畴之内,在他那里完全不存在任何所谓的道德动机,马尔多罗蔑视一切美德,他的恶更倾向于康德在这三种基本形式之外的“恶魔之恶”。这种恶魔般的邪恶完全把理性原则排除在外,它不再将善与恶看作是二元对立的,非理性原则取代了道德原则。此时,主体的自由意志是纯粹的恶的意志,恶即是主体的法则。这种“恶魔之恶”模糊了善恶的界限,与根本恶的三种形式相互冲突,它既不在理性范围之内也不在感性范围之内,所以康德认为,这在人身上是不可能的。康德对这种魔鬼般的邪恶或“恶魔之恶”虽有提及,但没有进行系统的考察和论述,而齐泽克则接过了这一关于“恶魔之恶”的讨论。
“恶魔之恶”不受自爱原则也不受道德原则主导,在齐泽克看来,它是被康德所排除的第四种恶,在这种情况下,“恶设定了他的反面,换言之,恶不是外在于善而与善对立着,而是成为善的形式。”[3]145康德并没有把人性的根本恶这一原则贯彻到底,而是将至善看作人类理性的最终目的。理性的法则遵循一种无条件的“应该”,符合法则的一切行为就是“善”的,人的自由意志就在于其能够自己设立法则规定自身,自由意志就是善的意志。正如康德指出,“道德律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纯粹实践理性的真正动机就是这样的情况;它无非是纯粹道德律本身,只要这法则让我们发觉我们自己的超感性实存的崇高性,并主观上在人们的心中,在他们同时意识到自己的感性存有和与此结合着的对他们在这方面很受病理学上的刺激的本性的依赖性时,引起了对于自己更高使命的敬重。”[4]100-101康德将道德律视为至上的崇高,它是“产生在野性的、纷乱的、未经驯化的狂暴自然与超越任何自然感性的理性观念之间的张力”。[5]217然而这种以善为目的的道德命令常常被诟病为一种纯粹的形式规定,它只关乎“应该”,而不涉及行动的具体内容,是一种定言命令。也就是说,康德强调的道德法则没有告诉我们义务是什么,而只是告诉我们应当履行义务,这不过是为义务而义务。齐泽克正是在此进行了置换,这也是他或拉康所说的萨德的调转,即以恶的意志置换康德的善的意志,这样一来,主体就依据并仅仅依据恶的法则来行事。康德的道德法则内在地隐藏着它的否定面,崇高的法则实际上等同于邪恶法则,用齐泽克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限的思想认为是道德法则的崇高庄严性的,其实无非是一个疯狂的、虐待狂的上帝的邪恶”[6]271。康德式的崇高实际上并不在于任何外在的客观事物,而最终指向内心的道德法则。然而此种具有本体性意义的崇高的道德律法只是一具命令的空壳,其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深渊般不可预测的主体。
马尔多罗所代表的,不正是这种“疯狂的、虐待狂的”魔鬼般的极端邪恶吗?恶是马尔多罗的唯一动机,他赞美恶、歌颂恶,他的恶行甚至不是出于自我保存的目的,而是一种没有任何目的的形式行为。从这个角度而言,康德的“你能,因为你必须!”所代表的自由意志再次显示出它的大他者①大他者(the big Other)是拉康-齐泽克精神分析中的常见术语,通常意义上的大他者指的就是象征秩序,它代表着整个社会网络一系列的秩序、文化、律法等等,决定了主体对现实的认知,甚至结构了主体的无意识。可以说,大他者在我们的日常现实中无处不在。式的崇高性,马尔多罗仍然陷入了对于法则的绝对的无条件的遵从中,即“你必须去这样做,至于具体做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尽管这在表面上来看是出于自由选择。这样一来,善与恶的界限被模糊了,恶被抬升为最高的伦理原则。马尔多罗那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它们是一回事,表明我们疯狂地采用最荒谬的办法来达到无限的热情和枉然?”[2]9的感叹直接暴露他更为本真的真实所在。此时马尔多罗重拾了主体在成为理性主体之前的激进否定性,成为“恶魔之恶”这种极端的恶本身,也正是在这时,马尔多罗散发出一种崇高之美,他的“无限的热情和枉然”实际上朝向的是拉康所说的原乐②原乐(Jouissance)是拉康的精神分析中一个重要概念,它也被译为“快感”“享乐”“执爽”等。原乐不同于享乐(enjoyment),尽管它在英语中常被译为“enjoyment”,它是一种极度的亢奋,更多具有一层性的涵义,但也不能完全等同于性快感。原乐与享乐的单纯愉悦不同,它是一种痛苦的快乐,对应于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提出的超出以享乐为目标的快乐原则,是朝向死亡的悖谬性体验。从另一层面而言,原乐是主体试图打破象征秩序,以尼采式的酒神精神试图获得的永恒愉乐。获得原乐往往意味着对父法的违越,但原乐又终究是不可获得的,主体能获得的只是原乐的剩余。,一种禁忌但却诱使人不断追寻的终极的痛苦的快乐。他弃绝了善恶的象征法则,返回到前主体非理性的黑暗与恐怖中,无休无止地追逐着被禁忌的欲望。但这种追逐注定又只能是“枉然”,因为原乐终究是无法获得的,占有原乐也就意味着肉体的死亡。马尔多罗其人本身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他没有一个确定的形象,在男人、阴阳人、两栖人、公猪、蚂蝗、章鱼等等之间随意变幻,可以说他就是原乐之恶的化身,而唯一将这些形象统合起来的是作为主人能指的“马尔多罗”这个名字,在这个主人能指下,潜藏着深不可测且无法完全捕获的“黎明之恶”。
三、洛特雷阿蒙与萨德式主体
无恶不作、嗜血成性、施虐成瘾的马尔多罗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十八世纪法国臭名昭著的色情作家萨德侯爵。萨德侯爵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本人放荡的私人生活和他充斥着施虐情节而有悖伦常的小说,在拉康看来,萨德是一个倒错式的施虐主体,他不断对他人发号施令的行为使其看似是主人,而实际上只是他者求原乐意志过程中的手段,因为他始终将自己置于驱力对象③驱力(drive)在拉康那里即是死亡驱力。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具有生存驱力和死亡驱力二种趋向,生存驱力指的就是为了生命体的延续和发展,趋于自我保存的驱力,而死亡驱力则相反,意指人想要回复到生命原初状态的一种惰性的死亡倾向。拉康对驱力的概念进行了拓展。死亡驱力可视为人类的侵凌性,它既可以是对他人他物的破坏欲,也是对自身的毁灭欲。驱力的目标是原乐,但驱力并不以欲望的满足为目的,因为原乐是不可获得的,所以驱力对满足的寻求也是不可能的,它的唯一执着就在于追寻原乐的过程或动作本身,因此驱力总是在做以原乐为中心的旋转运动,而驱力主体也总是执着于这一同一反复的失败运动。的位置。这也就是说,一方面,萨德式的主体将他人仅仅化约为一个为达到自己行为目的的客体;另一方面,他本身也是大他者的工具,致力于为他者提供快感。拉康的另一著名论断“康德同萨德”即是在说明,从无条件的服从律法以及以绝对法则对主体发号施令这一方面来说,康德实际上是一个萨德主义者。这让我们更能透析萨德式主体的另外两个特征:第一,对受害者保持绝对的冷漠,不抱以任何同情;其次,主体的快感来源于大他者的快感残余,他的“享乐”其实是对痛苦的享受,这些痛苦不只是来自于他人的痛苦,更多的是主体自身的痛苦。
马尔多罗对受害者纯然的冷漠、明显的施虐倾向以及对上文所提及的“为作恶而作恶”的律令的绝对服从,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萨德式主体。二者对于大他者的臣服让他们的这一特质更加鲜明,且他们享有同一个大他者,即大自然。在萨德看来,大自然是唯一的创造者,而真正的毁灭也只有大自然才能完成,他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这样说道:“‘毁灭’是大自然的主要律则之一,毁灭的力量不可能是罪恶。如果一种行为很有助于大自然,那么它怎么可能伤害到大自然呢……谋杀并不是一种毁灭。进行谋杀的人只是改变了形式,他是把元素归还给大自然,然后‘大自然’这位巧妙的艺匠的手就立刻用这些元素重新创造出其他生命。”[7]71正如布朗肖所说:“萨德完全理解人充沛的主权,尽管人以对否定精神的确认而为了获取这种主权,是一种悖论的状态。这个被全面确认的完整的人,也是完全被毁坏的人。他灌注了全部的激情而又无情,他以毁灭自己开始,在这个范围内他首先是人,然后是上帝,接着成为自然。他因此变得独一无二。”[8]36马尔多罗不正是这种萨德式的“完整的人”吗?他否定除具有无限威力的大自然之外的一切,毁灭他人他物甚至伤害自己——毕竟人本身也是自然的造物。他讽刺咒骂虚假的造物主,试图超越人内心之丑恶而成为能够掌控万物的比拟自然的新神,因此只有面对古老的海洋时,马尔多罗才愿意拜倒在它的脚下,“献上全部的爱”。
然而,洛特雷阿蒙以马尔多罗揭开了萨德的秘密,即施虐者本人实际上也是一个痛苦的主体。从叙述上看,萨德在给他人施加痛苦的过程中获得快乐,而马尔多罗尽管残暴地伤害他人,表现得像是一个施虐者,但他自己也是一个受虐者,不仅从他人的痛苦中享乐,也从自己的痛苦中获得快感。洛特雷阿蒙在作品中无时不刻地强调着马尔多罗本人的痛苦:“我和我的受害者一样痛苦!”[2]10“那个不会哭泣的人(因为,他总把痛苦压抑在心中)。”[2]29每当听到受难者的哀嚎,他就“将一把利剑的尖刃插进”脸颊,并想“他们更加痛苦!”[2]83他不断吐露心声:“啊!如果你知道我从那时起多么痛苦就好了!”[2]114“痛苦”可以说是《马尔多罗之歌》的高频词汇,这种痛苦可以说是萨德式的主体在面对大自然这个法则时感到的某种先验的痛苦,它实际上是大他者对主体的折磨。正如萨德在小说中借主人公之口所说的,毁灭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终极的他者是邪恶的,由于不知道大他者到底想要什么,主体因为无法满足大他者而深感愧疚,他只能无条件地同样按照自然的毁灭法则来对待他人,不断地回应大他者的欲望,因为大他者的绝对命令就是要不断地享乐,但主体始终无法真正体会到大他者的那种出于原乐的极乐,他只能获得大他者的剩余享乐,因此在原乐的诱惑下,主体始终无法逃出这个封闭循环的深渊,正如拉康所说:“为了绝对地抵达物①这里的“物”或下文引用中提到的“原质”,都指的是“Das Ding”,它是拉康精神分析中颇为晦涩的概念之一,主要代表的是主体在进入象征世界后被阉割、被压抑且无法找回的原初性欲望,它位于象征界之外的实在界,原乐就产生于与原质的遭遇。从俄狄浦斯的情结的视角来看,原质作为永恒失落的对象,就是弑父娶母的乱伦欲望,所以,象征界的主体为了维持自我的同一,必须与原质保持距离,否则便会招致自我毁灭。但同样具有悖论性的是,主体又时时刻刻试图找回这个失落的对象,想要重新获得对母亲的占有。(Das Ding),为了打开欲望的闸门,萨德将向我们展示什么?本质上就是痛苦。他人的痛苦以及主体自己的痛苦,因为有时候它们仅仅是一回事。”[9]80从这个角度上而言,马尔多罗是比萨德更加萨德的萨德式主体。
与萨德小说中残暴的施虐主人公一样,马尔多罗无论如何只是洛特雷阿蒙塑造的一个形象。细心的读者会认识到,在《马尔多罗之歌》这部作品中,作者洛特雷阿蒙时常进入文本中,以讲述者和批评家的身份闪现,一来为作品塑造了一种史诗般口耳相传的生动效果,另一方面,又提醒读者作者本人的存在。《马尔多罗之歌》是洛特雷阿蒙唯一一部完整中篇作品,后者扑朔迷离的身世和死因为这部作品又增添了一丝传奇性,当读者试图了解作者而无计可施时,往往不自觉地求助于他的作品,并将二者等同,因此我们很容易将洛特雷阿蒙看作是一个近似马尔多罗的人物,二者在含义上也确实存在一些相关性。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实际上是法国作家欧仁·苏德的一篇充斥着渎神的反英雄人物的哥特小说中的人物,它还可以理解为“l’autre Amon”,意为“另一个亚蒙”,而“亚蒙”(Amon)是神秘学著作《所罗门的小钥匙》中所罗门七十二柱魔神中排名第七位的魔神,他被认为是地狱的诸多恶魔君主中权势最强大的一位。除《马尔多罗之歌》外,洛特雷阿蒙还留有两篇长诗,与《马尔多罗之歌》中对恶的大肆吹捧不同,两首诗显示出截然不同的旨趣。进而我们发现,在主人公和叙述者之外,还存在第三个人,那就是真正的作者本人,幼年丧母且神经质的伊齐多尔·迪卡斯(Isidore Ducasse)。因而,在真正的作者与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之间实际上隔了两层,迪卡斯通过两层艺术面纱的升华来掩盖自己的真实冲动。
在第一层面纱中,迪卡斯这个主体借洛特雷阿蒙的名义通过马尔多罗抒发了自己的死亡冲动,前者让这个他创作出来的虚拟形象代替自己享乐并接近原乐。原乐意志根本上是一种恶的意志,它隐藏着“无条件”“无意义”背后真正的意义,即侵凌性的主体通过僭越获得极致快感。在弗洛伊德看来,这样的艺术创作活动是压抑的升华,其作用是用新的目的置换主体的性驱力的满足,迪卡斯就以洛特雷阿蒙和他的马尔多罗来移置了自己破坏性的死亡冲动。而当洛特雷阿蒙侯爵变回名为迪卡斯的诗人,且仅仅是迪卡斯这一称谓下的主体时,他又成了一个赞美至善和希望的“文明人”。在署名为伊奇多尔·迪卡斯的《诗一》和《诗二》中,他不仅抨击持恶与怀疑论观点的写作,认为“忧郁和悲伤已经是怀疑的开始了,怀疑是绝望的开始,绝望是恶毒不同程度的残酷开始”,还一反寻常地赞美希望和善:“真正的痛苦和希望是不相容的。不论这种痛苦多大,希望仍然比它高得多。”“我不接受恶。人是完美的。心灵不会堕落。进步是存在的。善是不会减少的。各种伪基督、坏天使、永恒的惩罚、宗教全都是怀疑的产物。”[2]230-237这时的迪卡斯似乎在为自己辩解,称《马尔多罗之歌》对恶的描写是为了突出至善,对恶的研究是为了显示善,恶从属于善,只能为善服务。
迪卡斯在论述中所声称的文学中的善恶、美丑对比方式显然是受到了他所崇拜的大作家雨果的影响,而事实上他也确实曾写信把自己的作品寄送给雨果,恳请这位在当时已经赫赫有名的大作家能给他一些回复。而也是在那时,由于急切地渴望出版自己的诗歌,迪卡斯不得不妥协删减去一些过于骇人的片段,并解释“这种文学歌唱绝望仅仅是为了压迫读者,促使他追求作为良药的善”[2]264,以获得出版商的认可和批评界的评价。可以说,名为迪卡斯的主体始终困于他者的话语或欲望中,他无论在想象界和象征界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法获得认同,这就造成了伊奇多尔·迪卡斯和马尔多罗的自我分裂。迪卡斯幼年丧母,母亲的过早缺席使他永远无法得到作为第一位他者的母亲的欲望回应,从而难以克服俄狄浦斯情结,认同父法,在象征的菲勒斯中获得稳定的能指。尽管迪卡斯在《诗》中歌颂善,但在拉康的启示中,我们认识到这种不可接近的、不可能的至善不过是“被禁止的”的恶,它其实是对母亲的乱伦欲望。这种深层压抑和创伤不可逆转地影响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的迪卡斯,使他既一边大肆抨击怀疑与痛苦,努力获得社会的认可,又一边在他的想象性身份洛特雷阿蒙中宣扬离经叛道的伦理道德,沉迷于邪恶与死亡的书写。这间接造就了马尔多罗形象的不确定性,他亦善亦邪,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既是人,又是兽;既是阴阳人,又体现出明显的同性恋倾向,他彻底成为了一个倒错的主体。
或许我们可以在布朗肖的评述中寻找被隐匿起的洛特雷阿蒙:“洛特雷阿蒙将永远留在钉在墙上的白纸的另一面,在蜡烛的热度中无声的飘动,这样,通过这寂静的声音,迪卡斯‘这个渴望荣誉的年轻人’才仍然能够听到马尔多罗和洛特雷阿蒙这两个未出世的名字。”[8]83洛特雷阿蒙的创作呈现了一种充满纠结的不可呈现的核心,当他试图借文字来为纯粹自我内部深不可测的“恶”、为蜡烛般燃烧的欲望命名并赋予其形象时,总是要不可避免地遭遇象征的失败,而崇高正是诞生于这些永恒纠葛的无可名状、无可解释的否定性中。
结语
菲利普·肖在《论崇高》一书中总结道:“崇高往往出现于文本自相矛盾的时刻……崇高是看似相互对立的事物共同作用的结果:生与死、统一与分裂、神与人。”[10]25无论是认识马尔多罗这个艺术形象,抑或是深入作者洛特雷阿蒙的创作中,我们总能体会到这种根深蒂固的撕裂与矛盾感,这种分裂与矛盾渗透进邪恶的具象化描写以及对善恶的辩证反思中,将我们从康德式的崇高指向了以拉康-齐泽克式的精神分析的崇高,这即是说,崇高不再是启蒙理性,而是主体内部深不可测、不可接近的恶,一个纯粹理性的主体终将死亡,而纯粹欲望的主体致力于要显示自身。在此由于篇幅所限,我们难以对精神分析视域中的其他理念做更加深入的解释和探究。总而言之,马尔多罗的恶不是在二元对立的语境下普遍意义的恶,而是具有崇高性的恶。崇高本身隐含着善与恶的辩证法,抽象为纯粹的善与恶实质上是同一的,正如齐泽克所说:“善(Good)只是极端的、绝对的恶(Evil)的面具,是对残暴、淫荡的原质(Das Ding)的‘下流迷恋’的掩饰。在善的后面,隐藏着绝对的恶。”[11]277崇高的本体即是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