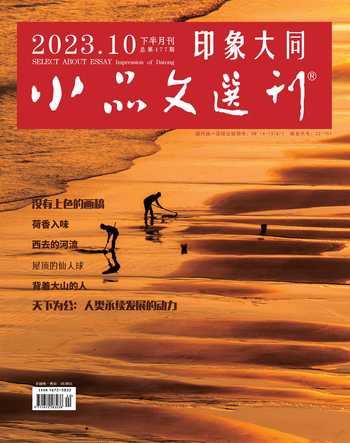唐朝的驿站
2023-11-22夏坚勇
夏坚勇

石碑的右侧是潼江,小晌午了,晨雾仍未散去,朦朦胧胧的一脉春江,水势很低调,隐约显现着几块鸭头似的沙渚,却看不到一只先知先觉的鸭,所以也不知水暖了没有。石碑的左侧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牛蜀道——现在当然修成了国道,编号很豪迈:108,似乎这道上走的都是绿林好汉。国道边的山坡上长满了柏树。柏树威严而沉静,让人想到不苟言笑的武士。没错,这里的柏树相传原先是三国时镇守巴西(阆中)的大将张飞所栽,不要以为这只是“相传”而已,仔细一想,张将军栽的就应该是柏树,他不会栽下春风杨柳万千条,更不会栽灼灼其华的桃树——虽然他们三个好基友结义是在桃园。
石碑上有阴刻的铭文:“唐明皇幸蜀闻铃处。”
唐明皇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清代因避康熙皇帝玄烨的“玄”字,改称明皇。根据这个称呼,不用看上款,我们大致可以断定这是清代的石碑。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七日,唐明皇一行来到这里的上亭驿,他是从长安往成都去的,所以叫“幸蜀”。皇帝出行离不开翠华摇摇的排场,但这一次是个例外,不是君王不“好色”,而是时势使然,他是逃难来的,所谓“幸蜀”其实很不“幸”,也就顾不上翠华摇摇了。如果一定要说“摇”,只能说风雨飘摇。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耀武扬威地开进了长安,老皇帝和太子一个往西蜀跑,一个往朔方跑,唐王朝还不够“飘摇”吗?而且现在他也不是皇帝了,儿子给他在皇帝前面加了“太上”两个字,这两个字的意思本来都很高端,但加了以后,他的地位反倒下来了。看来凡是用豪华的大词恭维人的,大多心怀鬼胎。太上皇帝,称号很牛很神圣,但说话的影响力只在户牖之内。诏书更不值钱,洛阳纸贱。那就不说话也不下诏书,枕着窗外的潺潺雨声,做梦。
上亭驿在梓潼城北的七曲山下,所谓的金牛蜀道,即从绵阳、梓潼经剑阁、广元越白水,进入陕西汉中,其中最为崔嵬奇险的则是从梓潼到广元这一段。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出川,那么到了梓潼,“蜀道难”的考验才算真正开始;如果你是入川,那么到了梓潼已经坡去平来,再往前朝成都去,路就好走了。唐明皇一行是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的,这一个多月的经历有如漫漫长夜的梦魇一般,始终在噩耗和惊魂之间颠沛流离。特别是在长安附近的马嵬坡,他心爱的贵妃杨玉环被哗变的士兵用一根白绫缢死在驿站。对于这个叫李隆基的男人来说,杨玉环不仅是一个可以侍寝的美丽的妃子——他身边并不缺乏具有性魅力的嫔妃,何况杨玉环已远不年轻——她早已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上亭驿的夜晚凄清而孤寂,夏天的雨往往金刚怒目,夜雨却例外。夜雨是慢性子,有如一个老者在翻着发黄的史书,有一搭没一搭的,翻到哪页是哪页。但不管窗外的雨翻到哪一页,太上皇的眼前总离不开贵妃的音容……
诗人后来描写那个夜晚,只用了一句:“夜雨闻铃肠断声。”其中既有写实也有艺术的渲染,说太上皇思念贵妃,恍惚中似听到贵妃熟悉的呼唤:“三郎、三郎……”一声声亲昵如酥。醒来后却四顾茫然,窗外风雨如昨,只有檐角上的风铃“叮当、叮当……”
《长恨歌》为白居易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历史上抒写爱情的长诗一共只有两部半:《孔雀东南飞》和《长恨歌》,这是两部;另外还有曹子建的《洛神赋》,写暗恋、单相思,只能算半部。这中间,《长恨歌》无疑是成就最高的。正是这部作品决定了白居易在唐代诗坛上的地位,如果没有《长恨歌》,他大抵只能和刘禹锡、元稹等人比肩。现在,他可以跨上一步,勉强和李白、杜甫站在一起了。《长恨歌》是一部致敬爱情的伟大史诗,不能说帝王和妃子之间只有性而没有爱情,他们之间产生爱情的几率和普通人一样高,甚至还要更高一些。因为爱情是需要经营的,他们比普通人有更多的闲情逸致用于经营;而柴米油盐的庸常生计则让普通人的爱情经营成为一种奢侈。对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白居易是由衷赞美的。但长期以来,主流评价却认为作者的思想倾向在于讽刺,最多也不过是同情而已。我不知道这些“主流”们在阅读《长恨歌》时有没有被感动过,如果被感动过,那他们的评价就是为了附和某种教条而言不由衷。如果没有被感动过,那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冷血动物,而冷血动物有什么资格来评价人类高贵的爱情呢?白居易自己是情场老手,也是在诗歌中描写女性的高手,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有好多是关注女性命运的,除《长恨歌》而外,例如《琵琶行》《上阳白发人》《井底引银瓶》《缭绫》,等等。无论关注的对象是宫廷贵妇、风尘娼妓,还是蓬门织女,他的目光中始终流泻着理解、尊重和欣赏,当然也有几分温情脉脉的缠绵意味。大师们都有各自的独门绝技,在对女性的体验和表达方面,白居易超过了李白,甚至也超过了杜甫。也许他写得太好了,以致引来了非议,例如清代的龚自珍。龚自珍这个人才气大,也狂,臧否人物常常惊世骇俗。他说白居易“真千古恶诗之祖”,理由是:“《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词,岂贵妃风度耶!”这话猛一听似乎有理,其实毫无道理。我想,所谓的“贵妃风度”大抵就是古典版加青春版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吧,那样一副尊容,有多少男人会真心喜欢呢?
杨玉环这个女人不简单,站在唐代诗坛最高端的几位大腕——李白、杜甫、白居易——都为她写过赞美诗,其中李白的三首《清平调》是面对面的赞美。“云想衣裳花想容”,这两个“想”何等好啊!好得只可意会,不可翻译。不信你译译看:“贵妃的面孔像花儿一样美丽。”立马成了小学生作文。有人说李白的诗中暗寓讥讽。扯淡!那是高力士说的,也只有高力士那种心态的人才会相信。在有些人眼里,不光是《清平调》,就连《蜀道难》也成了“讽刺玄宗逃难入蜀之作”。似乎离开了影射,世界上就没有诗了。《蜀道难》和玄宗入蜀有什么关系呢?李白的老家就在梓潼附近的江油,年轻时,他师从赵蕤,送老师回盐亭,梓潼是必经之地。送过了老師,他兴致来了就往上走,去剑阁、广元,体验蜀道的奇丽惊险,虽步履艰难却意气风发。当斯时也,山川、历史、神话、传说,全都成了诗神的奴仆,“噫吁嚱,危乎高哉!”这样气势逼人的诗句就只等着喷薄而出了。但李白出川时并没有走蜀道。蜀道太难走了,他走的是三峡水路。这大概是性格使然。出三峡,一叶轻舟,顺流直下,何等倜傥轻捷。他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人,如果走蜀道,一步一蹉跎,他还笑得出来吗?
就在唐明皇夜宿上亭驿大约三年以后,诗人杜甫从秦州辗转入蜀。他一路走一路写诗,一直写到剑阁。写诗易,蜀道难,一家人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一年才到了成都。他当然也要夜宿上亭驿的。驿站檐角的铃声依旧,触景生情,他会想些什么呢?在长安的大街上,他是见过杨家姊妹的,这有诗为证(《丽人行》)。他也曾因杨贵妃的死讯而吞声饮泣,这也有诗为证(《哀江头》)。无论是对贵妃的美,还是对李杨的爱情悲剧,他都是由衷赞美也由衷哀悼的。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他的《哀江头》其实已为五十年后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定下了基调。请看:“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马嵬之变后,杨玉环孤独地葬在渭水之滨,唐玄宗则往剑门关的深处渐去渐远,一对情侣,彼此再无消息。这样的句子如果混在《长恨歌》里,粗心的读者还真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后世的学者认为,《哀江头》和《长恨歌》可以互读。
其实杨玉环也是从蜀道走出去的,他父亲曾在蜀中做官,她亦在蜀中长大,山温水软的四川盆地滋润了她的好颜色。一个绝代佳人沿着金牛蜀道走向了京师长安,走进了王朝的权力中心。从她的背影里,人们读懂了一个词:乱世之美。在所有的美中,这是最无法无天所向披靡的,是美中的极致。极致的美和极致的权力结合在一起,那就莫怪天下大乱了。
好吧,现在让我们看看石碑的落款。果然是清代的。上款:“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仲夏月”;下款:“知梓潼县事昆明桂良才书”。
我对“光緒二十年”没有什么感觉,但一看“甲午”,而且是光绪年间的“甲午”,心头便不由得一阵黯然,随即又想到,梓潼的地方官为什么要在这个甲午年发思古之幽情呢?
这可能牵涉到对唐明皇夜雨闻铃的另一种解读,说当夜唐明皇在上亭驿遇见神仙托梦,告诉他唐军大捷,叛乱即将平定。第二天果然驿马来报,安禄山已死,请太上皇回銮。这是一个关于否极泰来挽狂澜于既倒的寓言,而在那个世纪末的甲午年间,危如累卵的大清帝国是多么需要这样的寓言。由此可以想见,那个叫桂良才的知县倒是一位忧时之士呢。
但我还是喜欢第一种传说,相对于成王败寇的政治游戏,只有爱情是不朽的。
选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唐朝的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