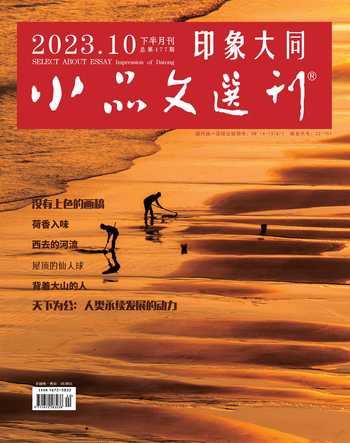一封走了六年的信
2023-11-22李钰
李钰

我坐在湖边,夏风习习,空气潮潮的,带着点水草的青涩和湖水的腥味儿。湖面上一片漆黑,只有航灯极有节奏地眨着眼睛。
还有两个小时,我就成年了。
看着漆黑的湖面,白天收到的匿名来信,那个字迹我再熟悉不过了,是奶奶的字,这信,不是久别重逢的惊喜,而是猝不及防的惊吓。
奶奶已经去世六年了,这信是六年前奶奶发出的,那这信怎么可以走了六年呢?还是天外来音,我一整天都处在思考中,我倒不是怕什么,我是在想,时间竟已经过去六年了,奶奶的样子在我脑海里渐渐淡去。人们常说,人最可怕的不是离去,而是遗忘。我从微信里翻出与奶奶的语音对话,企图努力回想起奶奶的容貌,可不看照片我都无法想起奶奶的样子。
父亲说,样子并不重要,记住那份好才是最重要的。
我看着手里的信,始终没有勇气打开。这封信应该是奶奶活着时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不管信是怎样的来源,奶奶的确离开我整整六年。
从我记事起,奶奶每天沉浸在书法与绘画中,享受着外人看来孤独的生活,年近六十的她总是有花不完的力气,白天陪我,自己写字画画,有时还要出席活动,晚上才能回家休息。我眨着大眼睛看向奶奶:“奶奶,您累不累啊?吃完饭就又要走了吧。”
奶奶笑眯眯地望着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不累。”
我仿佛听到了满意的答案,拉着奶奶手就往外走,“奶奶陪我玩。”奶奶也不反抗,放下手里的书由着我往外拉,一直拉到水池边,我停下来,看着石头桥犹豫不前。
“怎么了?怎么不走了?”奶奶蹲下身疑惑地问我。
“那石头滑,我不敢过。”我怯怯地说道。
“没事儿,你放心大胆地走,奶奶在后面呢,怕什么?”奶奶笑了笑,摸摸我的头,“去吧。”
我将信将疑地看着奶奶,最终还是踏出了那一步,前面几块都走得十分顺利,就要上岸时,我脚下一滑,重心向旁边偏去,扑通一声我就掉进水里,水不平静了,我从水底看到奶奶的脸晃荡着。我伸出手想要握住那只手,却捉了空。
我愣愣地看着湖面,记忆不断涌上心头。
奶奶爱读书,我也爱读书。
小时候常在奶奶家,一处平房院子,奶奶在这里已经住了四十多年,我在这富有年代感的小屋里住着,屋顶糊满了纸。屋子正中的柜顶上一直都放着毛爷爷的塑像。听奶奶说,在她年轻时候,每天下了班回家吃完饭就要拿上纸笔小板凳去听《毛泽东选集》的讲解,几乎是所有人都要学习,那些不识字的人也能背出选集里的内容。
“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互相猜忌,真夫妻都不能讲真话,万一你说错了,对方就把你告了。”奶奶坐在摇椅上,扇着蒲扇,手里还拿着那本《毛泽东选集》,卷起的书角都是翻阅的痕迹,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批注。
我趴在藤椅前,学着奶奶的样子,一笔一画地在自己的儿童读物上留下稚嫩的痕迹。
奶奶很少在我家留宿,不论多晚,都会让父亲送她回去。而我,是最不愿让奶奶回家的人。
“奶奶不走好不好?”我拽着奶奶的衣袖,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奶奶,同时偷瞄着父亲。
“奶奶回去换身衣服,明天一早就过来看你好不好?”奶奶蹲下身,用手抚摸着我的头。
“哇”的一声,我哭出来,摇晃着奶奶的手臂,“奶奶明天再走,明天再走好不好。”
显然,奶奶被我的阵仗吓了一跳,连忙哄道:“好好好,奶奶不走,奶奶陪着我的乖孙女儿。”奶奶把我搂到怀里,一把抱起走向卧室,“奶奶哄你睡觉觉喽!”
进了卧室,把门掩住,奶奶转过身看着我,“以后可不许哭了,这样可不好,犯了错就要承担责任,怎么能和爸爸耍赖呢?奶奶可就保护你这一次啊,下次可不许了,听到没有?”
我高兴地点点头,哧溜就钻进被窝,安稳睡去。
自那之后,我总是爱用奶奶当挡箭牌,每当觉察到父亲将要发怒,我就不舍地看着奶奶,奶奶心软就会留下护着我,只要奶奶在,父亲就不敢打我。后来父亲忍无可忍,识破了我的小伎俩,什么话都不说,即使我犯了错,也只是用眼神暗示我,那意思是,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转眼,他宛如一个笑面虎,开开心心地把奶奶送走,这才转过身收拾我。
我畏畏缩缩地窝在墙角,不敢看向父亲,听到皮带从裤子上拉下来的声音,我的心顿时紧张地怦怦乱跳,看着一步步靠近,迎面而来的人,这一刻,我多想奶奶在我身边,我冲向窗户边,企图奶奶听到我的声音后折回来解救我。
可惜我的愿望落了空,没等到奶奶回来,就挨了父亲的一顿打。
自那之后,我更是希望奶奶能够常来,最好是住下来。直到一天晚上,我起床找水喝,看到半掩着的门我就放慢脚步,想听听里面在说些什么。
奶奶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你怎么教育孩子我不管,但有一点,别打得太狠了。小孩子,调皮本就是天性,孩子那么怕你,见了你就躲,那是正常的父女关系吗?”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知道了妈,我自有分寸。”
我在门外,向奶奶投去一個感激的眼神。我蹑手蹑脚地回了屋,钻进被窝里,泣不成声。
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表现,不能辜负了奶奶的良苦用心。
奶奶一直都是一个要强的人,从小到大骨子里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从小,奶奶就想把这股劲儿传给我,让我和她一样。
人人都说孙女和奶奶像,现在的我越来越和奶奶像了。
记忆里,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培养我对书法的兴趣。奶奶深知言传身教的重要性,从不逼迫我要练什么,只是在她写字的时候把我放到旁边看着,我坐在摇椅上玩,奶奶在画案前有条不紊地往砚台里倒上墨水,再看看我。
每到这时我就会朝奶奶伸着手,嘴里咿呀咿呀地喊着,奶奶就把没沾墨的毛笔递到我面前,任我把玩着。玩腻了就要自己找点乐子,顺着椅子往上爬,企图爬到画案上,这是奶奶的大忌,她对待画案宛如敬重一位老者,即便三四天不画不写,也要把画案擦得干净。
因为奶奶爱它,才会和它产生共鸣,它才会甘心为你服务。倘若你在画案上吃饭,到处都是油,它不高兴你看着也不舒心,还怎么在上面创造出好的作品?
“对任何事物都要充满敬畏心。”这是奶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父亲的助力下,我三岁就在椅子上加了个牛奶箱子,坐在上面拿起毛笔写写画画,再大一点就开始描字帖,这是最让我头疼的事情,每次都想着偷懒。
学东西不能跟着家人学,总是下不了狠心。奶奶疼爱我这个孙女,很多时候放松要求,我就有偷空子的机会。
“说好你回家一周描五张,怎么就给我带了三张过来?还有一张是上次描了一半的。”奶奶指着我带来的作业质问道。
“描了,忘记带了。”我挠挠头侥幸地说。
“真的不是你没完成?”奶奶推推眼镜,“看着我说。”
“真...真没带。”我小声嘀咕着。
奶奶没说什么,坐回去批改我的作业,“这三张,拿回去给你爸看看,太不认真了,一张里面居然没有一个描的像样的字,太让我失望了。”
奶奶身上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每到这时我一句话都不敢说,只低着头,用力挤出几滴眼泪企图博取奶奶的同情。
奶奶佯装生气,别过脸不和我说一句话。我怯怯地拽拽奶奶的衣袖,一下午都乖巧地坐下认真临摹,不敢发一言,生怕惹怒奶奶把我不认真完成作业的事儿告诉父亲。我被迫坐在奶奶面前,乖乖地认真地写。我越写越好,这时奶奶的脸上就露出笑容,并告诉爷爷晚上做我爱吃的茄盒儿。
午睡是我儿时的一大难事儿,从小精力充沛的我根本不需要午睡,每到中午,全家就只我一人在疯玩,玩累了,下午就困了。
“这个习惯可不好,以后你和我们一起睡,睡不着也得睡。”奶奶给我下了死命令,“你一到下午就困,没状态,连字都练不好。”
“我不,我中午不困,看会儿电视就好了。”又开始肆无忌惮了,不服气地说。
父亲防止我眼睛近视,从小家里就不买电视,每周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能去奶奶家看一小会儿电视。尤其是中午新闻过后,就是电视剧,每天中午更新三集,三集过后,午睡时间到了。大人们该上班的上班,孩子们该上学的上学,而我就跟着奶奶到画室里练字。
奶奶若是让我睡午觉,岂不是连这点快乐时光都没有了?
“这怎么行?你的状态我都看得出来,困不困不是你说了算。”奶奶拍拍我的脑袋,“这件事情,容不得商量。”
从那之后,吃完午饭奶奶就招呼我午睡,我不情愿地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翻来覆去睡不着,不停地看着枕头边的闹钟,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我长舒了一口气,思绪把我拉回现实。一阵冷风吹过来,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如今,时间过得真快啊,和奶奶的点滴,仿佛都还在昨天。
奶奶发现,就算让我乖乖午睡,下午依旧打不起精神,眼睛不由自主地往下沉,不一会儿就不知道奶奶在讲什么了,像一只午间的慵猫,总打瞌睡,头刚一碰到身体,便马上抬起来,即刻又低了下去。
奶奶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奶奶是个行动派,想到哪干到哪,自从发现我下午没办法专注,就开始找原因,一路顺藤摸瓜才发现每天中午我都睁着眼睛躺着,根本不睡。
“睡不着。”面对奶奶的疑问我是这样回答的。
“怎么会睡不着?你下午还乏困呢。”奶奶不解地问。
我摇摇头,“我也不知道。”
奶奶看着我,心里默默叹气,“看来要牺牲掉我的午睡时间了。”之后的日子里,奶奶并没有先睡,而是坐在床边拿起一本书读起来,只要我翻身有动静,她就转过身看我,直到我睡着为止。
开始我极不情愿,总爱与奶奶作对,我闭着眼睛一会儿,就眯开一条缝看奶奶在干吗,奶奶仿佛猜到我会这样做,书也不看了,直勾勾地盯着我,我赶紧闭上眼睛又忍不住笑起来,扑到奶奶怀里,祖孙俩在暖冬的午后享受着美好时光。
渐渐地,我竟也能睡着了,下午起来果然有精神,直到晚上才困。午睡的习惯就在奶奶的监督下养成。
母親的电话打破了我的回忆。母亲催促我赶紧回家,她已为我做好丰盛的晚饭,等着为我庆祝十八岁生日。
烛光摇曳,窗外开始下雨了,淅淅沥沥,刚进五月的北方还是乍暖还寒,我对奶奶的思念不断。
父亲常对我说,奶奶是最疼你的,儿时的我不信,总觉得奶奶看到表哥更欢喜,心里总会不爽,现在想想,奶奶对我的爱润物细无声,点点滴滴已经融入我的生活里。
奶奶爱读书,儿时跟着奶奶生活的我也是如此,从识字开始我就读书,先从小人书看起,长大了就看报刊,杂志乃至四大名著。奶奶特别爱看报,家里的画报堆叠如山。老一辈的习惯便是什么都不舍得扔,父亲说,那辈人穷怕了,什么都没有,想要的东西都得靠自己攒着,万一哪天就有用了呢?
“我们那会儿哪有书啊报啊,那是最奢侈的东西,咱们普通老百姓很少能见到,家里只有一本《毛泽东选集》,那是要求一字不落地背下来的,要想看其它文字还得和送报的搞好关系,送点粮他们才会让你瞧上一眼。”奶奶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张挂历,“你看,这是当时的挂历,我当时就是照着这上面的风景画,奶奶现在还留着呢。”
奶奶打开那张尘封许久的挂历,三十多年了,纸张已泛黄,岁月沉淀在这上面,摸上去硬硬的,感觉一使劲就会碎掉。我看着这张纸,不敢相信,“奶奶把这个当宝贝?”那会儿的人吃都吃不饱,奶奶竟愿意拿粮食换了挂历。
不过想想也理解,任何东西对喜爱的人来讲,那就是宝,是精神食粮,比吃饱了更让人兴奋。
奶奶一直认为,见世面是孩子的必修课,趁孩子小,多带出来经见经见,孩子大了,什么都见过,自然临危不惧。其他孩子还在补课班对着ABC犯愁时,奶奶已经将我带到各种活动现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奶奶出席活动定会把我带上,让我在众人面前“露一手”,那会儿的我小,还不懂得那些鼓掌的、夸赞的人是为了买奶奶一个面子,并非我真写得好。
我得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被摆在桌上,别提有多开心,挺起胸脯下了场,目光中还带着不屑,神气十足。每逢过年,是我最忙的时候,各个家的对联都由我负责,其次还要写一部分出售。奶奶买好红纸,再掏出心爱的本子,上面记录着吉祥的对联,叠好格,蘸上墨,我照着模子一笔一画地写。那年,卖出去的第一副对联,是我人生中赚到的“第一桶金”。
“奶奶,那个阿姨买走我的对联了。”我激动地朝奶奶挥挥手里的钱,指着女人远去的背影喊着。
奶奶没说什么,只是对着我竖起了大拇指,眼里流露出欣慰。
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看着对联迟迟没人买失落不堪时,那个女人正是奶奶找来鼓励我的。
对联就在画室前挂着,等晾干的同时也方便人们看。
奶奶的画室并不大,一间普通的小房,里面应有尽有。奶奶爱养花,什么花都喜欢。奶奶说这就是创作灵感,看着这几盆花,浇浇水,照着临摹都是一件美事。窗外是爷爷的菜园子,虽产量不大,却也够家里吃了。每到下午爷爷在窗外浇水,我和奶奶在屋内写字画画,这一幕被有心人记录下来,成为小区里人们的佳话。
第一幅对联有了购买者,我的对联前突然多出好几个人,陆陆续续卖出好几幅。人不得不相信命运,在那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楼。”面前,一位中年女人驻足于此,她端详许久,和奶奶攀谈起来。
女人是一家装裱画店的老板,刚开张不久,就在奶奶家楼下,她看到我的字,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如果他还在,现在也和你一样大了。”女人摸摸我的头喃喃道。
她掏出钱买下最后一幅,也是她中意的对联,临走前还特意邀请我们改天到店里喝茶。殊不知,后来我竟成了那家店的常客。
“奶奶,我的对联都被人买走了。”我仰着头看向奶奶,等待奶奶的夸奖。小脸红扑扑的,眼里带着惊喜,我拿着那沓钱沉甸甸的,比收到压岁钱还开心。
“真棒,你的字已经有人买了,只不过......”奶奶迟疑道:“咱们家的对联还没有着落呢,咱们还得快点写。”说着,奶奶就拿出纸,给我叠好格,备好笔,就等我这位“大师”登场了。
日子过得飞快,我书法的进步肉眼可见。
班上不知何时刮起了一阵素描风,一支铅笔就能将物品呈现出生动形象,好看又简单。
我也心动了,吵闹着不学国画要学素描,“每天画大熊猫有什么意思?一只大熊猫画了这么多年,还是那样,我同学素描还获过好多奖呢。”
“素描是最简单的,你只要掌握好比例,是完全可以一比一复制出来的,国画才是绘画的精髓。”父亲对素描这件事儿并不赞成,他只希望我专一地学好一项,“绘画都是互通的,学会一项其它自然就会了。”
“就算学素描,你也要保证画一幅大熊猫,你确定想好了?”奶奶看着我说。
我犹豫了一下,想到同学画素描的样子,立刻点点头:“想好了。”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最有动力的,想到即将开启素描的第一课,画熊猫的我瞬间不觉得累,只想早早画完让奶奶教素描。
奶奶支起画架,坐在画架前,拿起削好的铅笔,眼睛仔细地观察面前这盆娇嫩的花朵,手中的笔轻轻移动勾勒出略显青涩的线条再抬头看看花,随即又专注地描绘着笔下的植物。
描线一笔接一笔,白色的素描本上渐渐萌生黑意。没一会儿,一盆具有动态的黑白的画就呈现在我面前,奶奶把画纸取下来,递到我眼前,“怎么样?开始练吧,今天就从线条开始吧。”
我迫不及待地坐到画架前,拿起铅笔,在纸张前比画着,脑海里是奶奶画画的样子。
“素描,朴素的描绘,没有色彩也不容虚假......”奶奶的话在我耳边回荡,“线条是素描的重中之重,不管是阴影还是物品图像,都是线条构成的......”奶奶站在我身后,握着我手,笔尖轻轻地触碰在纸上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
奶奶身上有一股淡淡的墨香,是我最爱的味道。
小时候我去奶奶家,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纸香与墨香,我贪婪地嗅着。纸上的墨水,笔尖的力度,都显得格外清晰。
兒时的我对任何东西只能保持三分钟热度,素描学了三天我就渐渐厌倦了枯燥的线条,“每天练线条有什么意思,我要能画出作品,花鸟鱼虫、人物那才好玩。”我不满地嘟囔着,这话被奶奶听见后,她放下手里的活儿,直勾勾地看着我,她的脸变得极其严肃,“学什么都要下功夫,谁不经历这枯燥的生活,哪个大师不是从基本功练起,是你提出要学素描的。”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铅笔一言不发,心里开始懊悔:比起来,还是国画更适合我,我放下手里的铅笔,不再羡慕其他人,只想心无旁骛地练好大熊猫。
我原以为日子就这样平淡、幸福地过下去,直到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体检结果出来我们才得知,眼前这个无坚不摧,从不生病的奶奶竟然病了,“这病啊,一查出来就是晚期。”大夫把体检报告放在桌上。
那天不知怎么回的家,直至晚上,全家围坐在客厅,鸦雀无声,桌子上放着那张体检报告。
“怎么可能,姥姥怎么可能会得这种病,是不是医生诊断错了,”表哥激动地站起来,泪流满面。“姥姥每天早上都去公园打太极,看着精神得很,怎么可能会得这种病,我不相信。”表哥嘶吼着,怀里紧紧地抱着沙发垫子,额头上的青筋突起,眼神恶狠狠地盯着那张报告单。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听你电话里特别着急,把我叫回来。”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子进了门,把钥匙丢在鞋柜上,坐在板凳上喘着粗气。
客厅里一片寂静,只有走廊的夜灯闪了一下,算是回应了父亲。
“别喊了,都睡了。”母亲打开门从屋里出来,“吃饭了没,冰箱里还有饭,给你热点。”
父亲点点头,拿起杯子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水,一饮而尽。“孩子们都睡了?那姐呢?”
“大屋里等你呢。”说完,母亲转身走进厨房,关上门,忙自己的事情。
父亲走到大屋,摸着黑找到开关,“你怎么不开灯,黑灯瞎火地在这儿坐着。”
姑姑听到响声,这才将头抬起,父亲有些惊讶,她红肿着双眼,当看到父亲时扑到他怀里又抽泣起来。“姐,怎么回事?家里出什么事了?”父亲焦急地等着姑姑说话。姑姑又坐在床上,松乱的头发垂在衬衫上,不到一夜,姑姑仿佛老了十歲。“老弟,看看这个吧。”姑姑有气无力地说着,随即又垂下头去。
父亲拿起桌上那张轻飘飘的纸,慢慢地坐在床上,不可思议地看着姑姑,“这......这是真的?”
姑姑在一旁沉默着,泪又流了出来。“明天我带着妈再做个全身检查,这次我找人细致地检查完,再做定论。”
“妈不知道吧?”父亲急切地问姑姑。
“眼下还不知道。”姑姑无力地回答,又说,“瞒是瞒不住的,迟一天早一天的事儿。”
父亲拿着那张纸什么也没说,就静静地坐着,双眼无神地看着窗帘那边。“如果,妈真的是癌症,那怎么办?”姑姑闷声问道。
姑姑说的话父亲并没有听见,显然他并未缓过劲儿来。
“吃点饭吧,吃饱饭再想。”母亲把饭端出来,盘里的包子还冒着热气。
夜里,大家都睡了,父亲悄悄打开奶奶房间,从门缝里看到奶奶睡得安稳,稍稍松了口气,轻轻合上门,坐在沙发上,看着那张体检单陷入沉思。
父亲一宿没合眼。
第二天清晨,全家早早就忙乎起来,姑姑带着奶奶一早就去了医院,父亲在医院门口等着。爷爷还和以前一样,吃完早饭准备去地里看自己钟爱的蔬菜,母亲出门上班,家里只留下我和表哥两人,我们不再似从前般打闹,安静地待在家里练字、看书。
两天后,姑姑和父亲坐在医生的办公室里,看着医生翻阅时凝重的表情,他们心里也一惊,揪得更紧了。
“确诊是癌症。”医生将单子递到桌前,观察着姑姑和父亲的神情。
姑姑小声又抽泣起来。
“不过也别太伤心,老太太还没彻底到晚期,去北京做手术,成功率应该高,但也看人的体质和心态。”医生这番话给了父亲和姑姑一丝希望也给了他们对未来的茫然。
父亲不知自己是怎么走出办公室的,姑姑在后面搀扶着奶奶,开上车朝回家的方向驶去。一路上,三人沉默不语,车上的空气静得可怕,谁也不知三人同时朝窗外望去,不约而同地流下眼泪。这时,父亲说话了:“医生不是说手术的成功率很大吗?姐,妈,都不要愁,医疗条件这么好,明天咱们就准备去北京。”父亲说得很坚决,凝固了的空气被父亲的决定打破了。过了一会儿,父亲又补充了一句,“也不是什么大病。”他说得极没有底气,声音不大。
傍晚,家里的灯暗暗地闪着,昏黄的灯光下,每个人的脸上都凝结着沉重。
“过来一下。”姑姑向父亲招招手,叫进屋里,掩上门悄声说:“你说要不要让妈清楚点病情?”
父亲坐在床上,双手扶额,“告诉还是不告诉呢?告诉妈,妈可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自己的病情,若是不告诉瞒着也不好......”父亲深吸一口气,下了很大的决心后睁开眼,坚定地说:“还是告诉吧,让妈自己心里也有个数,只是说得轻一些。”
“听你的,你决定就行。”姑姑轻拍父亲的背,“咱们也该出去了,不然妈在外面更会瞎想。”
父亲揉揉发红发涩的眼睛,脸上尽是疲惫,对着镜子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这才开门出去。
“妈,我和姐商量了一下,想了想还是应该告诉你,总要对自己的病情有所了解。”父亲坐在奶奶身边,不敢直视。他别过头去,双手紧紧地握着奶奶的手,没等姑姑和父亲再说话,奶奶开口了,她叹了口气,很明显,父亲感觉到她的手在发抖。“我知道什么病,你们也别隐瞒了,我能承受的了。这是天意,我只是担忧我孙女儿,以后没人管她了,她是块艺术的料。”
姑姑和父亲都愣住了,空气都凝固了,他俩久久没反应过来。奶奶像一块石头直挺挺地僵在那儿,脸色煞白,她似乎已经开始和病魔斗争了。突然她又开口了,说:“癌症,癌症,被判死刑了。”
“妈,妈。”姑姑摇晃着奶奶,把奶奶扶到卧室的床上,奶奶回过神来,渴望地望着姑姑。这一刻,奶奶不再是那个把家里一切重担都挑起的强者,而是一个小女孩,倒在姑姑怀里,双目无神。
母亲在浴室调好水温,叹了口气,闷闷地敲着奶奶卧室的门,“妈,水放好了,洗澡吧。”
姑姑拿起那张纸又放下,年幼的我还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察觉到家里氛围紧张,我靠在门框上不敢说一句话,生怕碰到雷区。
全家再一次陷入沉默,一直一言不发的爷爷再也忍受不了这样压抑的氛围,起身走到厨房打开油烟机,坐在灶台前抽起烟来,一根接着一根,从不间断。
我悄声走到奶奶的房间门口,门虚掩着,我顺手推开,昏暗狭小的屋子里,奶奶正在床上躺着,她听着屋外几人的对话,眼泪顺着脸颊流下。年幼的我也觉得这几天的时间,奶奶由一个坚强无比的人削弱得不堪一击了。她的泪不断流着。
奶奶见我进来睁开眼,想坐起来,慌忙擦干眼泪,温柔地看向我:“来,来,陪奶奶躺会儿。”
奶奶搂着我,盯着天花板的灯,许是盯久了,眼累,泪水从眼角又滑下。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奶奶哭,我的心也随着抽搐了一下。
我躺在奶奶怀里,感受到奶奶的身子在颤抖。
那份感受,还留在我的心中,好多年后,我才发觉那是一种死神降临的恐慌。
大地已经沉睡,除了微风轻轻地吹着,还有偶尔一两声狗的嚎叫,冷落的街道是寂静无声的。黑沉沉的夜,仿佛无边的颜料重重地涂抹在天际,就连微微星光也没有。
在医生的建议下,父亲和姑姑在北京给奶奶约上了床位,一周后,我们就出发去北京,这次,只有我、父亲、姑姑和奶奶四人。路上,父亲把车开得很慢,防止奶奶感受到不适。意外的是以往因为车速太快错过的风景这次竟都完美地捕捉到了。
奶奶望着窗外,心情复杂,姑姑和父亲心里难受却也不敢多问,只让我多陪陪奶奶,看到孙女儿,老人心里会好一点。可我明白,奶奶更多地是排斥,对所有人,对医院的排斥。奶奶自己就是医生,不用查也知道癌症的严重性,这些天,奶奶一直都在翻书,翻各种医书,只是想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得的。
夕阳斜挂在天际,窗外是一片金黄色,云也成了金色,透过窗户照在病床上,在冰冷的病房里,感受这世界带给的唯一温暖。
当天晚上,奶奶住进了医院,按照在家商量好的,姑姑晚上负责陪床,到了第二天我和父亲去替姑姑。
“医生的手术都约到下周了,咱们得一直输液,只能等。”姑姑把父亲叫到病房外,商量着奶奶的手术,“我刚问了,医生说根据妈现在的情况,手术成功率很大,咱们不用太担心。”
医院走廊上一片静寂,“嘀嘀嘀”地呼叫声音不断充斥着耳朵,到处都是病人家属们的哀叹声。护士走进病房做最后的检查,仔细安顿好病人后才将灯关掉,只留下夜灯。尽管姑姑声音压得很低,坐在病房内的奶奶和我还是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奶奶明显松了口气,闭着眼睛靠在枕头上,没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我悄悄地把滴液的速度调慢,看着滴管里的液体出了神,直到父亲进来招呼我回家,这才依依不舍地回头看看奶奶离开。
住院的生活是无聊的,每天什么都不能干,两只手上被插满了针管,只能躺在床上,电视里播着一部又一部电视剧。奶奶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一定要姑姑调出手机音频里的《黄帝内经》放在枕边,躺在床上闭目听着。奶奶还是想从中医里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她渴望活着。
每天下午六点,护士推着餐车到病房门口,家属们拿着饭盒出来,打好适量的饭放在小桌板上。液体注入得太多,奶奶没有胃口,只喝些暖胃的汤,往往姑姑打回的菜与饭都被我洗劫一空。
奶奶舀着碗里的汤看着我吃,就好似吃进自己的肚里一样,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笑着说:“你啊,家里的饭不比这儿好吃?你吃病号餐比家里还吃得带劲。”
“这儿就是比家里的好吃。”我吃得满脸米饭,抬起头 反驳道。
人们常说,病痛不光是身体上的疼痛,更是心理上的折磨。短短一周,奶奶就已经苍老得不成样子,与家里那个日日相伴我的奶奶判若两人。
奶奶挣扎着从床上坐起,苍白的面庞因痛苦而扭曲,细细的汗珠从额头渗出,好似每移动一下都是巨大的折磨。奶奶微闭着眼睛,静静地靠在床边静养,苍白的脸没有一丝血色。
奶奶的手术约在了一周后,“早上第一台手术,人人都想约啊。”姑姑削着手里的苹果感叹道。
“这还有讲究?排前排后只要做了不就行了?”我啃着姑姑削下来的果肉嘟囔着。
“这就不懂了吧?”奶奶笑着说:“做手术也是有讲究的,早上是一天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也是麻醉师医生思路最清晰,精神状态最佳的时候,第一台手术患者一般情况相对好,手术室人手也充足,大夫精力充沛,不会困乏。好多人都愿意多花点钱只为了能排到第一台手术去做呢。”当时,奶奶对自己的手术时间很是满意,奶奶在爸爸和姑姑不在时,悄悄和我说:“奶奶没事儿,你说呢?”我天真地向奶奶点着头。
手术前一周的时间,护士每天都会对病人进行体格检查,如果没有其他疾病的并发,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就能进行手术。
距离手术的日子一天天靠近,每天输液的药量也逐渐减少。直至手術前一晚,奶奶慌了。
天色已晚,为了不打扰其他病人休息,护士已经来催促好多回了,“只留今晚陪护的人就行,其余家属赶紧离开,已经是病人们休息的时间了。”护士打开门轻声说道。
我和父亲正要和奶奶道别,一直躺在床上的奶奶忽然抓住父亲的手,想说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将父亲的手慢慢拉到眼睛上捂住眼睛,牙齿紧紧地咬住嘴唇,胸膛剧烈地抽搐着,过了好半天,才缓缓地移开。
父亲坐在床边,红了眼眶,什么也不说只是抱着奶奶。四人的眼眶都湿润着。护士悄声关上房门,再没有进来催促过。不知这样待了多久,奶奶累了,就靠在父亲怀里睡着了。给奶奶掖好被子,我和父亲这才离开医院。
晚上的医院更加宁静,病房外的长椅上躺满了家属,没有枕头,没有被子,裹挟着一件大衣就进入梦乡。靠在长椅右侧的姐姐我认识,就在隔壁病房,经常碰面也就熟络了。她母亲也是癌症,她和父亲轮着陪床,她母亲死活都不愿治疗:“我这病怎么着都是死,早死早超生。”母亲嘶吼着,“我躺在这儿一天,你压力就大一天,输液住院都需要钱,咱家的钱还要留着给你买房,我这老婆子不值得。”
“妈你别这么说,没有你我要房子有什么用。”女孩泪流满面,紧紧地把母亲搂入怀里。
人们常说手术室外比教堂的祷告更真诚,见证了更多的生死离别与医生的无力摇头。冷风拂面,把我吹得清醒,父亲转头望向这栋大楼闪着的光亮,暗暗叹气,望向奶奶的病房心又揪起。
第二天清晨,我和父亲早早到了医院,医生说手术前八小时都不允许吃饭,四小时前不能喝水,奶奶不能吃饭,我们也跟着没吃。
奶奶五点就醒了,翻身的动静弄醒了身边的姑姑,奶奶看着天花板,一种隐隐的不安和担忧涌上心头,不管姑姑说什么,奶奶并不理睬。同病房的老人得知奶奶今天要做手术,拉开病床间隔的帘子递来一个苹果,“拿着,保平安。”
七点半,护士推着奶奶的病床走向手术室,临进手术室前,护士把苹果给了父亲。七点五十,画线;八点,奶奶被推进手术室。看着手术室大门缓缓关闭的那一刻,我抓紧了姑姑的手:“姑姑,奶奶会不会疼啊?”
“疼痛肯定有,但医生会给奶奶打麻药,能减轻很多。”
“那......您说,奶奶害怕吗?”我扬起天真的小脸,认真地看着姑姑。
姑姑愣了一下,拉着我的手坐在门外的长椅上,过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道:“肯定是怕的,手术终究是有风险的,只是奶奶从不说。”
手术过程是漫长的,等在门外的家属更是焦急。这是一场漫长而煎熬的赛跑,手术室外静得害怕。家属们坐在长椅上,双手捂着脸,不敢看别人,也不敢暴露自己情绪。
父亲和姑姑坐在门外,两人沉默不语,双眼紧紧盯着手术室三个大字。父亲偶尔起身走向护士站,得到答案后又坐回来,来来回回不知多久,苹果一直在他手里,他就像抓住了奶奶的生命。手术室的红灯终于熄灭。
父亲慌忙走到门口,姑姑拉着我的手也向前靠近,等待大门打开,手腕上的力度逐渐加大,直到我痛得叫出了声,姑姑这才下意识地松开手,随即又望向医生。
“手术很成功,等阿姨过了麻醉劲儿醒来吧,麻药散去再喝水,一天后才能吃点流食。”医生说着朝我们招招手,“不用太紧张,要时刻关注病人的心情。”这时,父亲忙着和护士推奶奶,手中的苹果掉在了地上,摔成两半,我看见苹果外面红彤彤光洁的很,里面竟然都坏了,父亲却毫无知觉,他忙得忘记了手中的苹果。
苹果已被人们踢到了一边,谁都没注意。
父亲感激地握着医生的手,千言万语溢于言表,只笑着说:“太感谢您,给您添麻烦了。”
护士推着病床进了电梯,我也站在角落里,床上的奶奶插满了管子,嘴里咿咿呀呀含糊着,说什么也听不清。
我从没见过奶奶这样子,凌乱的头发,蜡黄的脸,肥大的病号服把奶奶包裹起来,我总感觉奶奶死了,我想哭又不敢哭,跟在大人身后,急急地追着推着奶奶的人们。 病床又推回了病房,回到了以往的宁静。
那一晚,我和父亲都没回家,三人坐在床边,等待麻药散去,奶奶的意识恢复。
手术后的奶奶恢复得很好,可以说是以最快速度办理了出院手续,连医生都有些惊讶。术后一周,我们就回家了。
日子与往常并无不同,半年后,奶奶因为一场毫无征兆的高烧住进医院,仅仅一周后,就离开了我们。
又是一年五月,我重温着和奶奶走过的小桥,生日的激情散去,我鼓起勇气拆开那封走了六年的信,我与奶奶跨时空相见了,细细品读着温暖而熟悉的文字,难以抑制心中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