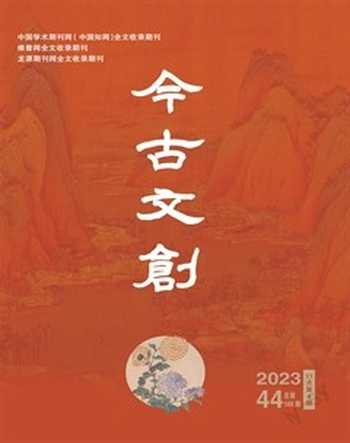玛丽 · 雪莱《福克纳》中的女性性别形象建构研究
2023-11-20阮世勤
【摘要】在小说《福克纳》中,玛丽·雪莱基于西方传统父权文化对理想女性的刻板印象,通过女性人物性别形象在个体外在形象、内在品质以及与实践相关的性别身份的认同上的叙述建构,将小说中的女性性别形象建构呈现为基于客体谱系传承的静态复刻。通过《福克纳》,玛丽·雪莱揭示了西方传统父权社会中女性个体性别形象建构的静态复刻模式。
【关键词】女性;父权;性别形象建构;静态复刻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4-004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4.014
基金项目:2022年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2022WTSCX190)。
出版于1837年的《福克纳(Falkner)》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女作家玛丽·雪莱的最后一部小说。目前学界对其评论较为有限,主要的关注点都集中于小说人物关系与玛丽·雪莱的个人经验的联系。梅丽莎·赛兹就认为小说《福克纳》中,玛丽·雪莱意图要建构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家庭生活”[1]。《福克纳》围绕女性角色艾莉西亚的失踪展开,叙述了约翰·福克纳及其养女伊丽莎白与艾莉西亚的儿子杰拉德·纳威勒之间围绕复仇、亲情与爱情的个体经历。从性别形象建构的角度来看,小说女性人物虽众多,但个体形象建构上延续的西方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别形象建构的刻板印象,呈现的是基于父权社会内女性客体谱系传承的静态模式建构。
在西方传统父权社会里,作为客体的女性个体往往被期待能沿袭父权社会文化对理想女性的性别形象建构的刻板印象。在《浪漫主义与性别》一书中,安·K·梅乐指出:“理想女性的建构,仅仅只是作为女儿、爱人、妻子和母亲,其存在仅仅是满足男性孩童和成人的需要,并且其个体品质往往被与她的美丽、顺从、温柔与关爱相等同”[2]。其中,“美丽”指的女性个体的外在形象规训;而 “顺从”“温柔”与“关爱”则更多的指涉的是女性客体个体的个人品质规训;“女儿、爱人、妻子、母亲”则强调的是对女性作为客体在父权家庭内的身份规训。《福克纳》中具有谱系传承关系的女性个体性别形象建构主要也是通过个体外在形象、个体品质以及个体身份认同等三个方面的静态复刻叙述来实现。
一、“美丽”的个体外在形象的静态复刻
视觉是一种重要场域权力技术:“男性对凝视的重视,不仅表达了统治阶级对女性身体意象的建构,还表达了统治阶级对稳定社会秩序的迫切需求。”[3]作为西方父权理想女性的个体外在形象品质,“美丽”是父权视觉“凝视”对女性身体投射的呈现表述,传递的是父权视觉投射理想的愿望。这种视觉投射的愿望在《福克纳》中女性个体形象的建构中具有集体概括性的叙述,其中的女性角色具有都是“美丽”的特征,只是具象化程度上有所不同。里弗斯夫人、艾莉西亚和拉比夫人,在小说叙事伊始都已经离世,是不在场的女性,其个体外在形象的建构依赖于男性角色福克纳的回溯性叙述以及其他父权男性主体的叙述。里弗斯夫人在叙述中所占的篇幅不大,但在有限的叙述中,福克纳还是描述了她所具有完美的个体形象特征:“她的外表温柔而又脱俗的”[4]。相较之下,作为里弗斯夫人的客体谱系传承的其女儿艾莉西亚的外在形象建构就丰富很多。在男性主体的视觉回溯性叙述里,艾莉西亚·纳威勒西方父权文化视域下作为女性客体个体外在形象的完美无瑕被反复地强调。男主人公约翰·福克纳对其个体形象的视觉呈现进行了具体描述:“她的美是如此耀眼,那乌黑东方式的双眼,有流苏版的眼睑,透着温柔而又有穿透力的火焰;完美的椭圆形脸庞;双唇要么微笑,要么轻容优雅地发出令人心灵神往的温柔又富有诗意的语句……”[4]通过这种对个体细节的具体叙述,如眼睛、脸型、嘴唇等,具体化了女性个体从西方父权理想女性的谱系传承中所沿袭传承的“美丽”品质的外在特征,以及其给男性所带来的视覺愉悦的体验,如“温柔”“富有诗意”。
小说《福克纳》中的伊丽莎白是约翰·福克纳的养女。作为孤儿的伊丽莎白·拉比之所以能引起福克纳的注意也是因为其美丽的个体外在形象特征:“她超凡的美貌,可爱的面容和丝般柔顺的头发都表明她是一个有人关爱的小孩”;“谁也不会对她无动于衷,她那银铃般的笑声直入人心田;时而严肃时而欢快的表情流露着爱的气息……娇小的小手的温柔触感和温暖红润的嘴唇;全部都那样的美丽动人”[4]。在父权男性的视觉中,和母亲“美丽的”拉比夫人一样,伊丽莎白的女性个体形象从孩童开始就一直沿袭了的父权社会理想女性“美丽”的外在形象品质,并且能使人产生愉悦的个体感受。这种对伊丽莎白的美丽的视觉描述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美丽”作为理想女性个体外在的与生俱来,指明了“美丽”作为父权理想女性性别形象建构的原生性,也是西方父权女性客体谱系传承的重要规训。伊丽莎白美丽的外在与窘迫的生活环境,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基于这样的视觉体验,福克纳深入探究了伊丽莎白的身世,并且最终收养了她。当然作为谱系传承的重要特征,“美丽”这一个体形象地外在特征并不会随叙事的时间的推进而有发生变化,是一种静态的沿袭性品质。只要女性一直处于场域内的客体位置,“美丽”就会维持。在小说中,随着个体的成长,伊丽莎白的“美丽”的外在形象就一直维持着,不管其经历过怎样的艰辛,并且使其随着叙事的推进获得了小说中越来越多男性个体的视觉投射,特别是年轻父权男性。
二、“温柔”“富有同情心”等个体品质的静态复刻
除了个体形象的“美丽”外,女性的个体品质,比如“温柔”“富有同情心”等,也是西方父权社会文化对女性刻板性别形象建构的重要规训,是女性客体谱系传承的重要内核。西方父权理想女性的个体品质在《福克纳》的女性谱系中也是以静态的模式来进行传承建构。与对女性外在形象的叙述类似,小说中女性角色在叙事中在场的时间不同,对她们个体内在品质的叙述在篇幅上有所差别。在男性的叙述里,对弗里斯夫人符合理想女性的个体品质是这样概括叙述的:“她是有情感而同情心的人。”[4]除了概括性叙述中,她理想女性的个人品质的展现则是以对离家出走的少年福克纳的照拂来进行简要呈现的。作为叙事发展的重要因子,男性对艾丽西亚个体品质的叙述就详尽很多。他直接向读者指出了艾丽西亚身上所具有的个体品质:“对他人的情感给予最强烈的同情”;“我曾经看到她对那些她关爱的人全身身心情感投入”;“她从来不发脾气,不生气;对作恶的人总是感到很伤心”[4]。在叙述中,福克纳甚至将艾莉西亚的女性个体品质的光芒,拓展到了其他非人的事物上,将其从父权的理想女性升华为天使般的“自然女神”:“所有的事物都爱她……林中的鸟儿都认得她……每一朵她拂过的鲜花都感知并且愉悦于她的存在”[4]。甚至在其叙述中,他多次直接用“天使”来指称艾莉西亚,而不是使用其个体的名字。
西方父权社会理想的女性个体品质也被传承复刻到了处于伊丽莎白的身上。在小说的相关叙述中,与其个体美丽的外在一样,伊丽莎白身上这些“温柔”“富有同情心”等等的女性个体内在品质仿佛也是与生俱来的传承,不具有发展性的静态复刻。拉比夫人在给艾莉西亚的托孤书信中这样描述:“她可爱的外在只是她完美性情的表现;虽然年纪小,却富有感性;她的脾气毫无瑕疵”[4]。在男性叙述里,对其个体符合父权社会理想女性形象的个体品质的话语更极具溢美之词:“一个纯洁的天使……一个被赋予了智慧、同情心、希望……和爱心的造物”[4]。当然,伊丽莎白的这些品质在个体实践中表现得更加突出:遇到离家出走的杰拉德时,她对他不幸的遭遇充满了同情,主动提供帮助他,希望凭借她的努力能“减轻他命运里的痛苦,用关爱来赢得他的信赖,并且使他幸福”[4];而在养父福克纳因个体创伤遭遇痛苦时,她作为父权女性的个体实践也是这些女性品质的直接表征:“她的感性也经常因为他的痛苦而受伤,但她善良的性格是如此富有同情心和隐忍,她的情绪从来不会因为安慰无果而被激怒”[4]。西方父权社会女性客体谱系传承的理想个体品质使得伊丽莎白也传承了艾莉西亚的“天使”形象。在其年幼时她就被男性叙述称为“小天使(cherub)”,在其成人以后,男性叙述称其为“天使(angel)”。这个指代的变化只标示了时间的流逝,对个体完美的内在品质则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她一直都是西方父权男性视域下的“天使”。
三、“母亲”身份的静态复刻
在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中,“顺从”一直以来都被归属到女性个体品质。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顺从作为对个体实践的描述的意义要远大于仅作为个体品质的概述,因为顺从指涉了一系列与客体身份相关的个体实践行为。在西方父权文化中,传承了理想个体形象与内在品质的女性的顺从,首先是对父权文化规训的顺从,接受父权女性谱系中个体的客体身份,认同父权文化中的母性等形象。表面上看来,父权家庭内,女性个体具有“女儿、爱人、妻子、母亲”等多重身份,但本质上最终都要归结于“母亲”,因为在父权社会文化中,女性个体“她为一个目的而存在:生育和抚养儿子”[5]。不论是女儿、爱人还是妻子,传承了理想女性个体外在形象与内在品质的客体女性最终都是要承担起西方父权文化所规训的照顾家庭、生儿育女的职责,认同西方父权家庭母亲的身份。因而,母性成了传统西方父权社会文化里女性客体个体身份认同的谱系传承的重要规训。
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指出在西方父权社会文化中,“妇女形象将妇女的世界局限在家庭之内”[6]。小说《福克纳》的女性角色,不论是否真的为生理上的母亲,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女性在西方传统父权社会里顺从的地位,被囿于家庭场域内,履行与传承着女性客体谱系中作为母亲的职责。由于丈夫里弗斯中尉长期在海军中服役,艾莉西亚的母亲里弗斯夫人顺从地接受丈夫的安排,被安置在乡村中,甘于乡村简陋的生活条件,任劳任怨抚养艾莉西亚,履行着西方父权社会对女性客体作为母亲的职责规训:“过着与世隔绝的简朴生活,住在一间简陋、低矮但风景如画、幽静的小屋”[4]。同样,在男性的叙述里,作为女性客体的艾莉西亚其个体实践都是围绕顺从传统西方父权男性主体的权力意志与主体实践展开的。“女性的一生没有任何独立自主的阶段,起初顺从父亲,而后顺从丈夫”[7]。在个体婚姻问题上,艾莉西亚顺从了父亲的主体意志,嫁给了比她年长许多但有权有势的博伊尔爵士,成了父亲兑换个体利益的牺牲品。而婚后,作为妻子的艾莉西亚,又顺从了丈夫博伊尔爵士对女性客体的圈禁,之前母亲那种幽闭的生活复刻到了她的身上。博伊尔爵士担心父权社会里其他男性觊觎具有理想女性形象的艾莉西亚,将她安置在了与世隔绝的乡村里,使得其远离父权社会的社交圈。对丈夫的圈禁,艾莉西亚毫无怨言:“他不是不善良,我没有权力抱怨……她是我的丈夫,因此我必须要以他为荣”[4],并且认真地承当履行她作为父权女性客体所被规训的母亲的责任:“在我的眼里,母亲比妻子更加神圣,我的人生都围绕我的儿子,在他身上我获得了无可指责的愉悦”[4]。而艾莉西亚也直言她顺从的个体实践是来自母亲的女性客体谱系传承:“她养育我是为了让我尽自己的责任,是为了让我也能成为一个母亲……我真诚希望能具有她身上所有的美德”[4]。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谱系传承,在福克纳的视觉里,在里弗斯夫人过世后,艾莉西亚和她的母亲出现了个体融合:“她母亲的天使般的内在和她的联结到了一起,合二为一”[4]。这种个体的融合使得个体的差异性消失,谱系传承的历时性从流逝变成永恒,使得女性个体的外在形象建构呈现为一种呆板复刻的静态复刻。
“在玛丽·雪莱的小说中,死亡的母亲的场域位置通常会被其他接受了场域规训的人物来填充,以延续符合场域规训的母性实践”[8]。除了上述显性的母亲形象,在《福克纳》中母亲的职责并不仅限于作为母亲的女性角色,顺从的父权母性在伊丽莎白的身上也是极具典型。在小说中,作为母亲拉比夫人与作为女儿伊丽莎白的谱系传承更多的是体现在照料的个体实践的临摹上。拉比夫人不顾个人安危,照料得了肺结核的丈夫,最终自己也不幸染病身亡。伊丽莎白亲历了母亲照顾父亲的整个过程,“看到母亲的悲伤,她不再玩耍,而是爱抚、亲吻她,要她微笑”[4]。而通过这样的耳闻目染,伊丽莎白也传承了母亲在家庭场域的照料病患功用,复刻了母亲为了父权家庭的维系做出自我牺牲的精神:“她从母亲的榜样中学到了,为了心爱的人的利益和幸福牺牲自我是最美好和值得赞扬的事”[4]。进而进入继父福克纳的父权家庭后,由于家庭内母亲角色的缺失,她担负起了照顾父权男性的职责。当听闻福克纳在战场上身受重伤后,她立刻前往去救治护理;当福克纳身陷囹圄的时候,她不离不弃地陪伴其身边。在福克纳的叙述中,伊丽莎白被比拟作“良药(medicine)”,而“她的微笑、她的眼泪、她的快乐或平静的悲伤轮流减轻他的痛苦,安慰着他”[4]。表面上,伊丽莎白这种母亲般的献身精神似乎具有主动性,但从深层次看,就如她的母亲一樣,她的关爱个体实践都是围绕父权人物,都是出于对父权男性的顺从,是对西方社会女性客体谱系中母亲身份的继承与责任履行。伊丽莎白是不会忤逆父权人物的意志的,她的个体实践都是受制于父权男性的主体意志,正如她自己所言:“他(养父)是一个我应该要服从的人,一个指引我的人”[4]。
四、结语
玛丽·雪莱的传记作者露西·马克多斯·罗塞蒂夫人认为小说《福克纳》显示出玛丽·雪莱“对角色的极佳的洞察力”[9]。作为一个生活在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女性,受限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阶段,不能期待玛丽·雪莱对女性角色能有多重大的突破性建构。但其基于西方传统父权社会文化对理想女性客体形象的规训,对小说中女性个体外在形象、内在品质与个体身份认同等性别形象方面的静态复刻叙事建构,揭示了传统西方父权社会文化中对女性性别形象缺乏个体特征的呆板谱系复刻的静态建构模式。虽然历史与现实已然不同,但是在现代社会文化中,对女性的呆板复刻的静态建构思维依然大量存在着,而也许只有突破这种静态建构的思维,接纳动态化的多元性别形象建构,西方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桎梏才有可能被打破,真正的性别平等才有可能实现。
参考文献:
[1]Melissa Sites.Utopian Domesticity as Social Reform in Mary Shelley's “Falkner”[J].Keats-Shelley Journal.2005,(54).148-72.
[2]Anne K.Mellor.Romanticism and Gender[M].New York:Routledge,Chapman and Hall,Inc.1993:109.
[3]黄鹤.被扭曲的身体: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女性形象规训与形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31.
[4]Mary Shelley.Falkner[M].Doylestown:Wildside Press,2003.
[5]艾德丽安·里奇.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M].毛路,毛喻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211.
[6]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M].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
[7]Bertrand Russell.Marriage and Morals[M].London: Routledge,2009:17.
[8]阮世勤.死亡与涅槃:玛丽·雪莱小说中的母性建构研究[J].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2020,(3):68-71,76.
[9]L·M·罗塞蒂.雪莱夫人[M].陈琳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27.
作者简介:
阮世勤,男,漢族,福建南安人,硕士,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国小说、电影批评、英语教学。